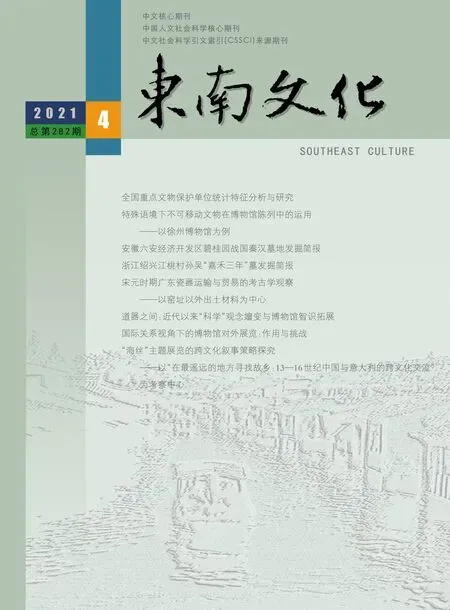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博物馆对外展览:作用与挑战
陈 莉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
内容提要:在国际关系视角下,博物馆对外展览既可以被归为服务于一国对外政策的文化外交,也可以被归为致力于长远宏观目标的人文交流。每个对外展览因动因不同,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通常作用包括形塑国家形象、搭建沟通桥梁、增进相互理解。与此同时,国内外政治形势、法律框架、国家政策等都是对外展览发生的重要背景和能够发生的决定条件,而展览能否真正改变观众的行为或态度又受到文化偏见的干扰,这就造成了博物馆对外展览影响力的不可控性和缓释性。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博物馆作为民族国家的形象代表,应当致力于在更高层次上将独特性转化成普遍性,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其他社会和文化同样注重的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博物馆自走向现代化以来就在民族国家社会中发挥着特殊的公共政治意义。对内,它作为民族记忆的保存中心,通过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建立“想象共同体”或“记忆共同体”,塑造文化认同[1]。对外,它作为“身份的国家表达”和“记忆机构”[2],以有形的方式体现一个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和愿景,争取相互尊重和理解,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在博物馆的征集、典藏、陈列/展览和研究功能中,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实现社会职能的关键。其中,对外展览[3]是博物馆联系国外观众、提高声誉、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和作用的主要因素[4],是开展对外人文交流、推动国家利益的重要形式和手段。
1851年,英国为了展示作为“世界工厂”的繁荣和昌盛,举办了世界史上的第一次博览会。除了各种各样有关科学、工业、经济的展览外,文化产品亦是各个国家馆中的重要展示,由此构成了国际艺术展览的雏形。1905—1906年,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的“世界之光”(The Light of the World)被大英帝国送往国外巡展,成为文献中可见的具有现代意义的首个国际展览[5]。中国博物馆对外展览的实践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初见端倪,作为研究课题到21世纪初开始引发学界关注[6],陆续有学者对其历史、现状、存在问题、策略建议等作了研究和探讨[7],另有一些学者在分析国外博物馆的文化外交策略[8]、外交合作机制[9]、博物馆外交[10]时也将博物馆对外展览当作一个重要方面加以研究。总体来说,国内学界对博物馆对外展览的研究集中于实践和经验的总结,对于这一活动背后的动机、存在的局限以及评估标准的探讨尚处于初级阶段。篇幅所限,本文将在国际关系视角下论述博物馆对外展览的作用和面临的挑战,以推动对这一课题的学理研究,为博物馆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一、博物馆对外展览的作用
以国际关系为视角,博物馆对外展览既可以被归为服务于一国对外政策的文化外交,也可以被归为致力于长远宏观目标的人文交流[11]。前者主要由政府主导。相对于其他对外文化传播手段,对外展览不公开表达政治意图,政治宣传意味更弱,更易于被观众接受,因此是“平行外交”[12]的完美手段,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一国政府的议程。后者除了政府主导外,商业动机、文化内在的推动力都是促成展览交流实现的重要因素。前者属于政治进程,而后者则属于社会交往进程[13]。在实践中,致力于文化外交与人文交流的对外展览有时并没有显著区别,相互交织的情况时有发生。动因的不同造成每个对外展览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形塑国家形象
致力于形塑国家形象的机构和组织并不仅限于政府和企业,而是包含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各种行为体,从总体上构成了国家建立积极联想的动态过程。在国家组织或授意下举办的对外展览,可以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弱化负面形象,进而获得他国公众以及他国政府对本国政治、经济目的的支持。
1934—1940年中日战争前后,日本国际文化关系协会(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Kokusai Bunka Shinkokai)利用艺术展览在美国塑造了一个与军国主义截然相反的日本国家形象,迅速改变了西方人对于日本形象的认知,巧妙地影响了美国舆论[14]。无独有偶,20世纪30年代,由于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和颁布反犹太法律产生了负面影响,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转向将艺术作为在美国进行政治宣传的一种手段。通过在美举办当代艺术展和文艺复兴展,意大利政府宣示了当代意大利与其辉煌的历史遗产之间的连续性[15]。而这些文化外交使得墨索里尼成功达成了目标——直至1940年墨索里尼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尽管出现了一些外交危机,但是美国从未中断与意大利的外交关系,甚至继续为意大利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提供非常有利的财政条件[16]。1935年,面对严重的日本侵华危机,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参展国,甄选了近一千件国宝级艺术品参加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17]。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而言,参与该活动表明了它是中国政权的合法继承人,是中国的合法代表,也是国际舞台上可以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一员。另外,南京国民政府还寄希望于展览取得的交流成果能够转化为切实的国际政治认同,从而争取到更多以英美为代表的盟军势力的支援。最终,“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不仅向世人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脉络和中国艺术的价值理念,同时也在形塑民族国家形象和推动文化外交方面获得了成功,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由此可见,在国际局势紧张时,一国政府利用对外展览开展文化外交,可以彰显其友好、文明的国际形象,达到争取盟友的目的。
二战后,对于建国不久的新兴国家,在海外——尤其是在西方——举办展览往往被看作是在国际社会的重要亮相。韩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于1957—1959年授命韩国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Korea)组织了韩国在海外举办的首个大型巡展“韩国艺术珍宝”展(Masterpieces of Korean Art),并将首站设在美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向美国公众展示了韩国文化区别于中国及日本文化的特征,力图在世界舞台上获得对韩国的文化认同[19]。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举办了1949年后走出国门的第一个大型展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20],并成立了承担文物交流任务的专门机构。当时,故宫博物院已闭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展览也已关闭。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受“乒乓外交”的启示向国务院递交报告,申请将展览推向国际[21]。展品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出土文物,目的是“增进我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22],稀释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中国破坏文物的舆论影响。
即使是对政治介入文化艺术有天然抵触的美国,也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在多国举办美国现代艺术展,包括1946—1947年在法国巴黎、捷克斯洛伐克多地举办的“推进美国艺术”展(Ad⁃vancing American Art),50年代中期在拉美、欧洲、亚洲和非洲巡展的“美国绘画之光”展(Highlights of American Painting),1964年先后在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举办的“艺术促进交流”系列展(Com⁃munication Through Art)。在这场宣传战中,美国政府将艺术作为有力工具,通过展览展示美国的多元化、对艺术的推崇和艺术自由[23],以取得文化外交的胜利,为美国“赢得心灵和头脑”[24]。尽管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逐渐将重心从国家安全转为在全球经济中建立主导地位,文化项目难以为继,但“9·11事件”(September 11 attacks)之后,美国高层开始重新考虑政治与艺术的联姻,推动文化在“反恐战争”中发挥外交作用。“9·11之后:归零地影像”展(After September 11:Images from Ground Zero)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在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以及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推动下,该展览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中东和北非城市巡展,以“反击有关美国的‘错误信息’”[25],达成其文化外交的政治使命——“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26]。由此可见,对外展览是民族国家进行选择性自我投射、建立与国家形象积极联想的有力武器。
(二)搭建沟通桥梁
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后,博物馆等国家文化机构一直在文化政策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就包括搭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桥梁,不管是发展文化旅游还是推动与他国的外交对话。例如,英国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自成立之日起就遵循议会在1753年制定的基本原则,担当着重要的外交行为体的角色。该原则提出“让观众通过展品,既包括古代的也包括现当代的,回答有关当代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27]。
在官方关系受挫时,博物馆可以作为建立非官方政治关系的安全空间,让协商渠道保持开放。这在伊朗与英国两国的文物互借中得到了最佳体现。2005年,大英博物馆举办展览“被遗忘的帝国:古代波斯世界”(Forgotten Empire:The World of Ancient Persia),并向伊朗的两家博物馆借展,其中多件文物是首次离开伊朗本土展出[28]。在展览开幕式上,伊朗副总统与英国外交大臣同时登台,而这在其他场合是不可想象的[29]。之后两国关系愈发紧张,博物馆一度成为两国仅存的外交关系渠道。当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居鲁士圆柱”(Cyrus Cylinder)最终出借给伊朗后,两国政府才缓慢启动其他讨论。此案例说明,国际展览因不涉及具体的利益,可以在国家间的关系紧张甚至恶化时发挥托底的作用,让两国能够延续交流直至关系改善。
2010年,“巴以和谈”重启不久即告中断,巴勒斯坦也面临着严峻的外部环境,与多国关系紧张。2011年,荷兰埃因霍温的范·埃比博物馆(Van Abbe Museum)将价值700万美元的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作品《女人半身像》(Buste de femme)出借给巴勒斯坦国际艺术学院(Interna⁃tional Art Academy Palestine),但荷兰在借展后两个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并没有投票赞成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尽管在政治层面上两国存在分歧,但对外展览可以作为一种人道和民间支持,为民间交流打开一扇窗,发挥两国未来关系试验场的作用。
在政治领域,重大的国家利益分歧往往导致国家之间出现摩擦乃至冲突,而承载着文化的对外展览通常表达的是“过去时”,与现实国际社会的纷争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另外,艺术本身具有淡化意识形态、追求人类共同审美的先天优势。基于以上两点,对外展览往往能够成为外交领域表达善意、缓解矛盾、恢复对话的契机,能够在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为未来关系的缓解提供一种可能。
(三)增进跨文化理解
在如今意识形态领域纷争不断的世界,从约瑟夫·奈(Joseph S.Nye)的“软权力”(soft power)[30]到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31],文化的意义愈发凸显。以国家之间的竞争为重点、致力于获得文化霸权的行为对于缓解文化冲突并没有帮助,更无益于增进不同国家民众之间的了解。采取对话性、合作性更强的方式开展文化外交,融入更多的国际主义理念才是最佳路径。进入21世纪,对外展览交流不再局限于推广或宣传,而是被更多地用于促进对话和增进理解。
2009年,在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的赞助下,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的“文化战士:澳大利亚土著艺术三年展”(Cultu⁃ral Warriors:Australian Indigenous Art Triennial)在美国巡展,以增进两国的相互理解、改善两国关系。展览不仅展示了澳大利亚土著在文化上的成就,而且没有回避他们所遭遇的社会问题以及在政治上所作出的抗争,并因此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32]。2012年,作为伦敦奥运会的官方文化项目“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Stories of the World)的活动之一,南京博物院的“中国珍宝展”(Trea⁃sures of China)在科尔切斯特城堡(Colchester Cas⁃tle)展出。尤为特殊的是,来自科尔切斯特吉尔伯德学校(Gilberd School)的10名学生在展览之前的2011年拜访了南京博物院并挑选了10件心仪的文物参展。有学生在回忆中写到,亲自到访中国并将“中国”带回英国与他人分享的经历让他们永生难忘;也有学生因为参与了这项活动而开始学习中文,尝试用毛笔画画,习练中国舞蹈。2013—2014年,南京博物院再次携手英国文化机构——苏格兰古代与历史遗迹皇家学会(Royal Commission on the Ancient and Historical Monu⁃ments of Scotland)共同策划了反映中国南京和英国爱丁堡两座城市发展史的文化交流展——“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展览将两座城市及其背后的两种文化、两种制度融合在一个展览空间中,并分别在南京和爱丁堡展出,以达到促进文化理解的目的。
总的来说,实物性特征和公益机构特性的结合使得公众对博物馆展览所蕴含的“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较易产生信任,同时其视觉冲击力可以触动观众的神经并留下持久性的影响[33],因此博物馆对外展览是让不同国家的民众了解彼此的异同及其背后深层原因的重要渠道。
二、博物馆对外展览面临的挑战
作为文化外交与人文交流的一种手段,博物馆对外展览一直被决策者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然而,这种信念隐含着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错误是将“文化”具体化,将文化当作一个很容易被呈现出来的事物,一个由内容——形象、思想和价值观——构成的实体;第二个错误是假设被包装在不同文化产品中的形象、思想和价值观的传播是一个线性的单向过程,只要传播发生,接收端(即国外目标受众)就会吸收这些产品中包含的信息。实际上,国家议程、法律框架、国家政策、文化外交目标等都是国际展览发生的重要背景和能够发生的决定条件,而展览能否真正改变观众的行为或态度,又由文化偏见的不同程度所决定。
(一)易受国际、国内政治的影响
艺术可以影响政治,却无法决定政治。1937年日本开始在亚洲推行霸权,日本国际文化关系协会“为世界文化作出贡献”[34]的基本主张与实际外交政策严重脱节,其在美国通过国际展览而提供的有关日本的“正确”和“准确”信息以及所塑造的国家形象——一个高度文明和伟大的国家——瞬间失去了吸引力[35]。1987—1988年,土耳其在美国华盛顿、芝加哥和纽约举办“苏莱曼大帝的时代”展(The Age of Sultan Suleyman the Magnificent)。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办展期间,《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美洲观察组织因土耳其当时的监狱环境、政治犯和库尔德人的待遇,再次将其列为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36],致使展览所塑造的土耳其的光辉形象显得格格不入。由此可见,国家形象的自我投射只有在实际的外交政策符合两国相互理解的基本假设时才有意义。一旦这种理解不存在,对外展览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而言,如果对外展览纯粹是政治性的,成为某种政治权力“劫持的符号”,那么它就会沦为宣传。一旦被看作是宣传,对外展览很快就会在政治上失效。作为象征而使用的艺术品要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效果,就必须超越其政治使命,并且政治议程越重要,艺术品就越应具有摄人心魄的美学力量,这样才有可能实现隐含在深处的政治目的[37]。因此,对外展览的效果不仅受到具体的国际政治环境的干扰,也受到国内政治干预和文化实践的影响。
(二)易受文化偏见的影响
“艺术品在不同的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含义。出于公共关系的目的使用文物,在文物的选择和组合上就必须聚焦和美化供外国观众消费的国家形象。”[38]各国政府在将展览推向海外时,为了在国际社会确立自己的地位,不得不考虑海外观众的原始认知,因此会选择具有高辨识度的展览主题,往往无形当中强化了固有的国家形象,放大了带有偏见的差异。墨西哥是一个拥有多样化文化遗产的国家,但是被海外观众熟知的却只有玛雅文明(Maya Civilization)和阿兹特克文明(Aztec Civilization)。特奥蒂瓦坎文明(Teotihuacan Civili⁃zation)、奥尔梅克文明(Olmecs Civilization)等因知名度不足很少能成为国际展览的主题,即使阿兹特克展览是票房的保证,它在展出期间仍然收到了很多负面评论。例如,观众在评论人祭时会使用反应强烈的词汇,如“令人作呕”“卑劣”“极可憎”[39],并将这种评论蔓延至对国民性的感受。
就中国来说,秦兵马俑展览是与图坦卡蒙(Tutankhamun)宝藏、死海文书(Dead Sea Scrolls)、庞贝古城(Pompeii)等比肩的受到青睐的国际展览品牌。据不完全统计,自1974年秦兵马俑被发现至2018年的四十多年中,以秦兵马俑为主题和包含秦兵马俑的展览在全世界近六十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二百六十余次[40],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然而,瑞典东方博物馆(Östasiatiska Museet)前馆长马思中(Magnus Fiskesjö)则认为秦兵马俑国际巡展展现的是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形象,弘扬的是帝国主义的“统一”思想,而对帝国的另一面——秦帝国对他国的征服和统治剥夺了他国自治的权利——则避而不谈;同时,他还认为展览反映了中国对历史观的控制、西方亲华分子的“不实”观点以及中国强大的“山寨”能力[41]。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当地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对展览效果的影响。事实上,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定格思维中,偏见和误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曲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威胁论”。例如,“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在大英博物馆展出时,西方媒体仍然会对展览作过度政治解读;一些评论攻击展览试图对一位独裁统治者洗白,是打着历史旗号的政治宣传[42]。尽管博物馆对外展览作为中国文化外交的工具在英国总体上取得成功,但受到思维定势的影响,研究表明有些展览仍然强化了长久以来有关中国的刻板印象和过时看法[43]。这种局限性在藏品来源国不参与策展的展览中尤为明显。在这种合作形式中,藏品来源国基本放弃了遗产的主体表达权,对选题的把控以及对展览的诠释能力都较弱,而主办方为了吸引观众会在无形当中选择能够让观众产生迅速联想的刻板印象的展品,导致展览更易受到文化偏见的影响。
(三)影响力的不可控性和缓释性
博物馆展览的观众不是单一和均质化的群体,而是一个“复数”群体——不仅是年龄与性别、政治与社会身份、知识结构与认知、民族与文化身份等多维度的复数,更是不同个体与群体的日常生活体验、艺术经验、文本经验、社会政治经验乃至伦理经验的复数[44]。跨文化展览受到的影响更多,包括展览来源地的想法、观念、目的,展览主办方的想法、观念、目的,观者自己的“文化包袱”——不成系统的想法、观念和非常具体的目的[45],这些都使得展览影响力变得不可控。
此外,刻板印象属于具有普遍性的心理认知误区,既不是朝夕形成的,也不易被改变。博物馆对社会的影响力主要通过公众影响力集合的方式体现[46]。个体从博物馆获得的知识和体验间接转化为对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但这种积累和影响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仅仅通过对外展览使得海外观众完全按照实施者的意图“想象”某一国家,这在短期内无法实现。
1953年,在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下,日本政府组织的一次大型的古代艺术展在华盛顿、西雅图、芝加哥以及波士顿展出。为了监测和评估展览如何影响美国观众的政治态度,在日本协会的赞助下,日本社会科学家作了一项评估观众反应的研究。研究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得出的结论是:对于被“巨型展览的大肆宣传”(block⁃buster hype)吸引而来的普通观众来说,展览的美学价值和政治“善意”都是失效的;对于精英观众来说,美学价值成功发挥了影响力,但即使这样,其政治影响力仍然为零。无论观众类型如何,展览仍然强化了美国人对日本人固有的态度[47]。由此可见,在目标观众不明确的情况下,观众的反应千差万别,展览的影响力很难被主办方事先预见。
综上,博物馆对外展览的影响力既不是立竿见影的,也不是可以简单量化的,通常是多层次、长期且复杂的。
三、结语
博物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对外展览是其中最复杂、最专业、耗资最多、规模最大的一项工作[48]。其本身所面临的挑战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这种活动是否必然能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抑或只是一种理想信念,其产生的影响力是否切实存在。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90年,塔马拉·阿纳斯塔西娅·塔拉索夫(Tamara Anastasia Tarasoff)就在《博物馆国际活动评估:以1978至1988年加拿大博物馆的国际巡展为例》(Assessing International Museum Acti⁃vity:The Example of International Travelling Exhibi⁃tions from Canadian Museums,1978-1988)中提出过。她认为虽然博物馆频繁开展国际活动,但却并不关注其跨文化性,同时,博物馆开展这样的活动既不对增进文化间理解的能力进行量化和评估,也不制定指导方针[49]。三十年多后的今天,她指出的问题在实践中仍然存在。
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情境之下,由于每个文化传统自身的根源性差异,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冲突和紧张,而非想象中的共生和融合。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文化生成来源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原始陌生,而达成某种普遍性社会观念的合理方式是超越文化的差异性,在各差异性文化传统之间寻求某种“重叠共识”,因此,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和认识至关重要[50]。中国博物馆作为民族国家的形象代表,应当致力于在更高层次上将独特性转化成普遍性,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其他社会和文化同样看重的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