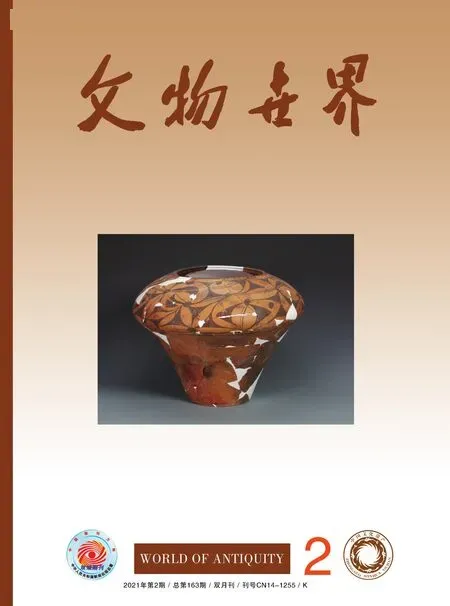山西仰韶时期考古的成就
薛新明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东部,东西宽约290公里,南北长达550余公里,大部分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境内各种地貌类型齐全,山地、丘陵占三分之二以上,西以滔滔南下的黄河为堑,东有巍巍太行山作屏,西南角黄河折向东流形成晋豫之界,北出塞外毗连内蒙古大草原,中部是低山、丘陵隔开的小型盆地,素称“表里山河”。随着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整体气温与湿度的变迁,各地生存条件也有变化,农牧业交界地带南北移动,是二者交汇融合的互动舞台。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特殊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不同区域的发现数量和发掘地点并不平衡,晋南的田野考古工作开展最早,发掘地点也最多:临汾盆地、运城盆地、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南侧和垣曲古城盆地比较集中,这些区域内聚落分布均匀密集,其他地区的遗址相对较少,规模也小,只有晋南的文化已经比较强盛时,才通过西部的吕梁山区、中部的盆地边缘地带向北传播。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个仅有一百年发展史的年轻学科,考古资料积累的主要手段是田野调查、发掘。各种遗存的发现、收集、整理和分析是对第一手资料最早进行的研究,调查、发掘报告是最直接和最接近发现、出土真实状况的认识;综合某个遗址、某类遗存的特点并和其他与此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认识更加全面、更有深度,资料积累与综合分析二者缺一不可。考古工作的方法总是在摸索中不断改进,多年来,学者们对相关课题的分析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从微观研究到宏观概括都有卓有成效的见识,但在每个特定的阶段,工作条件、主要目标、规划布局和研究思路具有时代特色,收集到的信息和公布于众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有必要将具有阶段性特点的工作范式及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可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6年李济等先生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
由于整个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刚刚起步的现代考古学缺乏一个安定祥和的外部环境,仰韶时期考古发现和研究自然受到了局限,但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先生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先生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梁先生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先生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
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先生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其实是一种多学科的探索,西阴村的发掘是地质学家袁复礼与李济先生合作完成的,不仅复原了遗址区的地质地貌,对石器原料也有研究。发掘结束后,他们将出土的软体动物和蚕茧分别请有关专家鉴定,1928年,李济又把那半个蚕茧带到美国华盛顿,找专业的机构去检测。多学科合作研究的理念和采取的方法为后世打下了基础、开了先河。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疑古学派对中国古史的质疑催生了一些学者对传说时代的考证与考察,李济对汾河流域的调查基于对传说中的尧舜禹夏的追溯,但史前遗址的发掘客观上奠定了这一区域在考古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先辈们坚实的步伐具有奠基意义。
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三十年和后十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山西的地方文物部门陆续建立,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以极大的热情对辖区内的古文化遗存进行了摸底调查和登记,来自地方文化或艺术单位、具有初步文物保护意识的人员深入基层,仔细调查核实并回收文物。为了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相关部门派人参加了国家组织的短期专业培训,具备了较系统的文物知识,很快成为业务骨干。由于山西历史时期文化积淀厚重,文物保护兼顾的范围较宽,接受培训的绝大部分人从事了晋文化、北朝文化的探索研究,对史前时期的关注相对较少,由于没有宏观计划和预设目的,发现史前遗存的地点又比较分散,见于报道的简讯、简报水平差强人意,未开展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发掘工作,然而,这些零星线索的可信度甚至超过后来的调查资料。
上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三十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1981年,苏秉琦先生与殷玮璋先生合作发表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划分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六大区系,提出了新的理论体系,其中的中原地区中心在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这里正是孕育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域,在中华民族、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山西是最早践行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学说”的地区之一,通过太谷白燕遗址的大面积揭露、汾阳杏花遗址和墓地的小面积发掘以及汾阳、娄烦、离石、柳林等地的专题调查,初步建立起了晋中及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春秋时期古遗存的排序。同时,对垣曲古城盆地的东关遗址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规模发掘,实证山西西南部确实是仰韶时期的核心区域之一。
本阶段后十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有了增加,但仰韶时期的调查与发掘范式没有变化,可喜的是,考古队伍中有了一些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考古工作者,尽管工作能力还需要在实践中逐渐提高,短期内还无法成长为主持重大学术课题的核心成员,但活泼的思想和扎实的基础决定了他们将会大有作为。
第三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在这一阶段初期,从业者通过不同方式接触到了国际上的一些考古新思潮,开始反思传统工作方法的得失,设计适合中国实际的模式,理念悄然发生了变化,虽然以构建物质文化序列和谱系为主要目标的工作仍旧是基础,但课题涉及的领域多样化,力图通过各地遗存表象的差异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多角度、多侧面地探寻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进步,梳理文明化进程的详细过程和关键节点,揭示引发各种变革的机制和动力,认识古人的审美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社会制度,进而复原具体的社会面貌。仰韶文化研究是最早引进新观念的领域,随着参与学者不断增加、技术手段逐渐丰富,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日益默契。
新的研究目标对原始资料的要求比较严苛,田野发掘工作模式也慢慢有了更新,基于国家控制主动发掘数量的实际情况,改变首先在配合基建工作中体现出来。1990~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第一线的科研人员将一些新方法运用到实践中,在试探和摸索中调整发掘的思路,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这种模式在配合小浪底水库建设的垣曲盆地诸遗址发掘中得到延续,对小赵、宁家坡、上亳、苗圃、下马等村庄当时所在地(现在这些村庄虽然名字未改,但大部分都因水库蓄水而迁移)的发掘,发现了从枣园文化的小小农家到仰韶中晚期的大型聚落,夯实了仰韶时期晋豫交界地区在中原的核心地位。
在实际工作中,年轻考古工作者得到了锻炼,积累了实践经验。近年来,各单位引进了许多新的设备和技术,更新了工作理念,不仅开展了航拍、航测、三维摄影建模,而且对重点堆积单位内的填土全部过筛,系统采集孢粉、植硅石、浮选的样品,人类骨骼、动物遗骸等专业类别的检测标本;研发田野考古工作网络平台(网络版数据库),将文字记录、测绘记录、影像记录统一收入数据库,系统、完整、有效地保存发掘过程、遗存出土状况的原始资料,为后期查询、检索、分析提供便利,彰显出整个学科的进步。
根据具体遗存的实际情况,邀请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参与工作,用各自熟悉的科技手段收集标本或记录遗物出土时的信息,对古代社会的不同侧面进行科学分析,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复原、种植作物的甄别、饲养家畜的鉴定、生产工具的改进、基础工程的流程、生活方式的变革等内容分别进行剖析,以详细的观察和精确的数据力图恢复古代社会的原貌、仔细梳理当时的生产体系,深入探讨社会的发展机制。新的思路和理念正引导着田野考古工作与学术研究的总体走向。
在新理念指导下,晋南地区重要居住址、墓地的发掘工作有了较大收获。2003~2005年发掘的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揭露了355座分属四个时期的墓葬,第一期瓮棺葬的葬具特点说明枣园文化晚期至北撖早期,不同的部族在陕晋豫交界地区频繁互动,催生了初期的庙底沟文化。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以一条河流或某个地理单元为工作范围的专题调查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进展。2002年秋和2003年春对芮城寺里—坡头遗址的调查,为后来的大规模发掘打下了基础。2000~2006年,对垣曲、运城两个盆地进行了区域调查,重新审视中原核心区域聚落的布局变化,反映了在数千年间文化的起伏与盛衰。多学科参与、运用新技术收集全面信息的模式对探索聚落之间相互关系、探讨区域社会复杂化的进程、还原一定阶段内社会分层及机构设置具有重要意义。
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2003年,在西距黄河约200米的吉县沟堡遗址清理了两座残存部分范围的半地穴式房址,发现了一件底边呈喇叭状筒状陶塑人面形器物,整体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墓葬或祭祀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类似的房址1991年在晋冀蒙交界地区、桑干河支流御河边的大同马家小村也曾发现过,两地发现的陶器均属于庙底沟文化,沟堡的器物比较典型,而马家小村的陶器形制却有一些东北地区的元素,分别发现于南、北吕梁山区的遗存为研究中原文化向北传播的途径、与北方文化于无声处的相互渗透、文化的远程交流等课题提供了新的资料,揭开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长期对峙与融合的大幕,完美地印证了苏秉琦先生“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远见卓识。近年来,吕梁山中段岚县荆峪堡、离石德岗等遗址的发掘,证实这里至晚仰韶中期已经得到开发,德岗遗址七座面积大小不一的五边形半地穴式房址颇具仪式感和象征意义,到底是建筑技术或理念的需要,还是其他特别的精神诉求?引起了学者们的思考。
晋中盆地的发现多见于周边地区,据史籍记载,历史上太原盆地中心位置有一个“昭馀祁”泽薮,汾阳杏花遗址和太原市区北侧的发掘表明庙底沟文化时期,太原盆地的边缘地带有人居住,霍太山的低山丘陵是晋中和晋南地区同期文化交流的媒介;至仰韶晚期,盆地边缘的清徐、平遥、太谷、祁县、介休、灵石等地都有一定规模的聚落,向北已经越过石岭关进入忻州盆地,成为南北部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通道之一。2006~2008年,区域调查新方法运用到忻州盆地北部的滹沱河上游,通过系统调查,结合定襄青石、原平辛章等位于盆地边缘区域遗址的发掘资料,证实这里仰韶晚期才得到开发,或许与太原盆地类似,当时忻州盆地中心也是湖水或沼泽,南北交流是通过盆地边缘达成的,仰韶晚期为龙山时期大规模进驻忻州盆地中心区域进行试探性开发。
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还处于摸底阶段。1997年,在上党盆地之东山口位置的黎城东阳关遗址发现了少量仰韶晚期的遗存,后来的调查或发掘比较零星,但以河流为调查单元、以聚落发掘为目标的理念在工作上得到实施。上党盆地与东部文化联系密切,东部重峦叠嶂的高耸峭壁并没有阻挡山上与山下部族的交流。位置偏南的晋城地区与晋西南黄河北岸的丘陵或低山接壤,文化特点与陕晋豫交界地区比较一致,但我们对这里仰韶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还比较粗浅。
通过以上各地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改变了以前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其他地区文化序列的被动局面。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仰韶文化最早提出时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定位十分宽泛,从目前的基本情况来看,不仅到底应该称其为时代还是文化,而且具体的表述学术界还有分歧;属于这一时期的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之间的关系还在争论;能不能将庙底沟文化及其所在区域称为“最早中国”也有不同的意见;甚至仰韶时期起迄标准的界定、再分期都有些模糊。近年来,学者研究涉及的领域有了扩展,对考古学资料的解析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涉及仰韶各个时期的社会形态、阶层分化、各种规模聚落之间的差别、上层人物的社会活动、经济形态的差别、社会结构演变等宏观课题;也有人对具体区域、遗址与古史传说、神话故事进行对应研究;还有人梳理各个阶段人类的心智发育、思想意识及世界观等上层建筑方面的进步。从考古学传承民族传统、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目标来看,这些无疑都是有益的,然而,至少目前为止,我们研究水平仍然有提高的空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相信随着学科的进一步成熟,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格局、底蕴会有提高,我们必须与其他学科学者默契合作,将各自的优势集合起来,从不同的角度解析,必然能够更深层次地探求历史或事物本身的本来面貌。希望年轻一代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