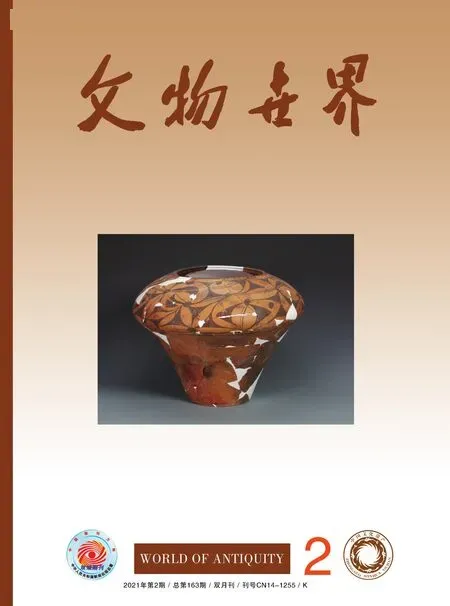百年仰韶考古发现与研究简议
戴向明
中国百年考古始自仰韶遗址的发掘。仰韶文化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由此开启的中国史前考古至今也走过了百年历程。简要梳理仰韶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史,可反映中国考古学,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在不同时期研究取向,研究内容、方法和观念等方面的变化。
一
1921年受北洋政府聘请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主持发掘了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其后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这在后来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仰韶遗址的发掘不仅开启了中国考古学,而且向世界证明中国有发达的史前文化。但安氏只是对考古有浓厚兴趣的地质学家,他没有掌握系统专门的考古学知识,因此当时的发掘不可能体现出考古地层学,在其后的整理分析中也不可能采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受当时流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影响,安特生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他不久之后到甘肃发掘马家窑、半山、马厂和齐家等遗址,也是为了证明中国彩陶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1]。安特生的局限性跟他的专业背景、时代背景都有直接关系。然而,他富有开创性的工作仍是有积极意义的,他通过实践将源于西方的考古学引入到中国,使之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而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的金石学。这门新学科又恰逢其时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相合拍,自诞生之日起就担当起了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使命。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有多位中国年轻学子负笈海外,到英美等西方国家学习考古,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返国,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先行者和开创者。
在这群为数不多的人中,首先就要提到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1926年,学成回国的李济主持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2]。选择此地发掘,除了当时一些具体社会条件的制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概是这里有与仰韶遗址一样的彩陶,李济想自己亲手挖出、亲自研究彩陶所代表的中国史前文化,追寻其来龙去脉。作为一个矢志要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找出源头的有家国情怀的学者,显然他和许多同辈学者一样,对中国文化西来说充满疑虑而力图有所突破。但李济在美国学的专业是人类学,似乎没有受过专门的田野考古训练,所以他也没有掌握科学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
被视为中国考古学两个轮子的地层学(又被称为层位学)和类型学(也被称为标型学)的发展成熟,是到1930和1940年代由另两位考古学家完成的。地层学成熟的标志是梁思永发掘“后岗三叠层”[3],梁先生赴美留学是在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应该有更好的考古学基础和理论方面的素养。类型学的成熟则是始于苏秉琦对宝鸡斗鸡台“瓦鬲”的研究,彼时虽有瑞典学者蒙特留斯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译介到国内,但苏先生似乎完全是靠自己的摸索而建立起一套类型学方法的[4]。这样,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不久,中国学者就在实践中掌握了考古学所倚赖的两大方法,并使之适合于本土的发掘和资料的整理分析,为战后学科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抗战爆发前,国内有影响、成规模的考古活动主要是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两家机构完成的,再有就是地质调查所对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从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积累起一套田野发掘方法与技术等角度来看,以中研院在殷墟长达十年的发掘与研究最富成效,因此那时的殷墟考古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是名副其实的。1930年代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确认了龙山文化,并由此引发出了梁思永、尹达(刘耀)等学者有关仰韶和龙山的年代与文化关系等方面的讨论[5]。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1940年代夏鼐先生通过在甘肃的田野工作,订正了仰韶(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的年代早晚关系[6]。
从抗战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受连年战乱干扰,10余年间缺乏大规模系统的考古工作。因此在中国考古学诞生后的最初30年里,有关仰韶文化的重要发现与研究主要限于仰韶、西阴村等少数遗址。在此期间,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严文明先生的认识,殷墟的发掘和研究已经体现出聚落考古的理念,并开始致力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讨[7]。这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形成初期就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
二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考古学也很快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仰韶文化的重要发现、重要工作也是接踵而至。1950年代开始随着机构设置、队伍建设的重新起步,做了许多考古调查,发掘了一些重要遗址。在仰韶文化方面,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和研究[8]。当时受苏联影响,为探讨氏族社会发展状况,对半坡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揭露,以现在眼光看,也可以说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最早的聚落考古实践。但限于当时的发掘和认识水平,从发掘到资料的整理分析都存在不少失误,特别是没有理清年代学的基础。其后庙底沟遗址的发掘有很大的提高,但材料的报道仍很简略[9]。这两个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此后有关两个遗址的分期、类型的分期和两者的年代关系成为相当长时间里新石器时代考古探讨的前沿问题。此外,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发现还有1950年代末发掘的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墓地,后来由张忠培先生最终整理完成的发掘与研究报告,为通过墓地分析来研究社会组织结构树立了一个典范[10]。
到1960年代,随着遗址发掘的不断增多,有关仰韶文化类型和分期问题得到广泛讨论。“文革”期间考古工作一度陷于停顿,到1970年代以后逐渐恢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对陕西临潼姜寨遗址近乎完整的揭露,这在以探讨文化类型、分期和年代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时代,再次显现了中国考古学从早期就有的、通过大规模聚落考古来全方位研究古代社会的传统[11]。此外,六、七十年代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就是围绕已经发现的仰韶、大汶口文化一些墓葬资料来探讨社会制度,特别是母系与父系、母权与父权的问题,不过在当时政治气候影响下,这方面的讨论大多有“以论套史”的教条倾向;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对社会问题的持久关注,正是基于这一点也才会有对姜寨仰韶聚落的大规模发掘。最近,张弛先生撰文指出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文化史”与“社会史”两种研究取向,可谓切中肯綮[12]。
然而,无论如何,不管是受有限材料制约,还是考古学天然需要先有一个完善的时空框架,抑或学界整体认知的阶段性,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主要的工作仍是不断获取新发现和新材料,不断完善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架构和谱系关系,多数人仍然主要致力于“文化史”的重建。正因如此,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在总结上述工作成果基础上,苏秉琦先生逐渐形成并完善了他的区系类型学说[13],并成为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研究内容,此研究脉络至今仍余绪未断。
“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各种思潮混杂碰撞、新思想与旧传统交错并行的时代。反映到中国考古学、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上,突出表现有如下几点:一是前述区系类型思想指导下的广泛实践,各主要文化区及其文化发展序列得以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二是以严文明先生对姜寨仰韶早期聚落研究和随后集大成的仰韶聚落与墓地研究为代表[14],将中国聚落考古提升到了一个高峰,且与世界上任何实际的聚落考古研究案例相比都毫不逊色,并为此后中国的聚落与社会考古研究创建了经典范式。三是从美欧传入的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新思潮对中国考古学界,特别是当时的年轻学人产生了强烈冲击,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讨论。
三
到1990年代,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开始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聚落考古理念及实践的悄然兴起,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此后的聚落考古,既有本土总结的经验与路径,也有国外传入的一些新观念、新方法,包括张光直先生的讲座和随后出版的著作[15],以及对西方区域系统调查的介绍和中外学者在此方面的合作所带来的影响。
从半坡到姜寨,以及诸如元君庙、北首岭、横阵、史家等墓地,皆集中于陕西关中的半坡类型,这些重要的发现为仰韶早期聚落与社会的研究提供了近乎完美的资料,而其学术价值也生逢其时地被一些卓越的学者所阐释,成就了中国早期聚落与社会考古研究的经典。到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发掘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6],又展示了仰韶晚期惊人的聚落内涵和发展水平,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从仰韶早期到晚期社会结构的变化。但当时有关仰韶中期聚落的资料还比较欠缺。这种缺憾从19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以来得到一定的弥补,这首先得益于在河南灵宝铸鼎塬的考古调查[17]和西坡遗址的发掘[18],中外合作在伊洛盆地开展的考古调查[19],以及我们在晋南运城盆地实施的区域系统调查[20],这些工作成果也都是通过践行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取得的。最近巩义双槐树等大型环壕聚落的揭示,又为研究中原腹地仰韶晚期社会发展状况填补了重要的新资料。凭藉这些接连不断的考古新发现和几代学者的努力探讨,学界对仰韶文化及其社会演变的认识也日益充实和丰满起来。
中国考古学在短短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个看似冷门的、小众的学科,却在各个时期都吸引了一些一流的大脑投入其中,使之在各阶段都显示出了很高的水准,在中国人文学科中独树一帜,长盛不衰。这其中隐含的奥妙是发人深省的。值此中国考古百年纪念之日,我们追忆以往几代学人筚路蓝缕的不懈探索,也期待来日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