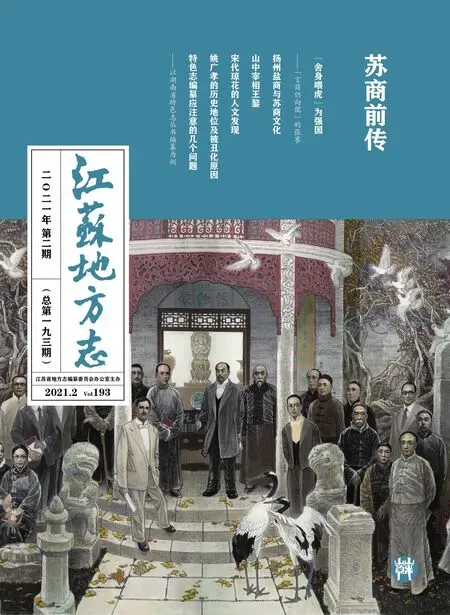破解二轮《萧山市志》的“千万之谜”
◎张海成
(河南长葛461500)
提 要:二轮《萧山市志》以1005万字的篇幅一举夺得全国新修县(市、区)志字数之首,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注释(该志主要体裁之一),还有第5册共300万字的“社会课题调查”,以及尚未正式出版的第6册80多万字的“口述历史”。文章对二轮《萧山市志》篇幅的“千万之谜”进行了剖析,认为采取“边注”“社会课题调查”“口述历史”等体例创新是形成《萧山市志》“鸿篇巨制”的主要因素,此外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是,该志的编纂者们认为:篇幅长的志书不一定不好,篇幅短的志书不一定就好,关键看质量;片面地强调控制志书的篇幅是不对的,这不仅束缚了修志人员的手脚,对志书的资料性也有很大削弱。
对于志书的规模,早在编纂首轮志书的时候,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下简称中指组)于1985年出台了《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其中规定:“关于各级、各类志书的字数,因地区差异较大,不宜作统一要求。总体规模不宜过于庞大,应当以既充实又精炼为原则。一般情况下,县志以控制在30万至50万字左右为宜。”中指组于1997年出台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明确:“志书的篇幅不宜过大,今后续修,字数要相应减少。”然在实际编修过程中,一些志书早已对此规定有所突破。如《萧山县志》(1987年版)95万字,还有相当多的县(市、区)级志书在100万字以上,其中《绍兴县志》410万字,为全国首轮县(市、区)级志书规模之最;《萧山市志》(2013年版)1005万字,为全国二轮县(市、区)级志书规模之最。很多人纳闷:首轮《萧山县志》是贯通古今的,近百万字情理之中,二轮《萧山市志》是续志,上接《萧山县志》的下限,主要记述1985年至2001年3月萧山撤市设区之时共计16年间萧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状况,为什么会有上千万字之多?它都写什么呢?《萧山市志》的“千万之谜”值得破解。
一、对“争议”和盘托出,是非让读者裁定
志书是一种资料性文献。何为“资料性”?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拿另外一种 “资料性”的工具书作比较。现在常用的《辞海》大多是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的版本,《辞海》(1980年版)有1342.8万字,之所以有如此庞大的“体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辞海》(1980年版)对所有有争议的词汇都“细说端详”。比如很有名的“司母戊鼎”,对该鼎称“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为此“人声鼎沸”,虽然2011年3月的央视《新闻30分》中正式公布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关于把此鼎统一称为“后母戊鼎”。那么,《辞海》(1980年版)面对这个争议采取的办法是,“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我把该说的都说出来,具体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所以在“司母戊鼎”这个词条里,《辞海》既说了所谓的“司母戊鼎”,也告诉读者这个鼎也有人称“后母戊鼎”。
《萧山市志》在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就采取了这种把“争议”和盘托出的做法。如排在“人物传略”中第一位的西施。可能是对西施“籍贯”的考证还不成熟,抑或是争议太大,首轮《萧山县志》并没有把西施列入“人物篇”,二轮《萧山市志》虽然把西施列上了,而且还是第一位,但由于对西施的死因拿捏不准,抑或是汲取了对西施“籍贯”的考证教训,编纂者将西施有可能包括坊间传说的“四种死因”全部以“边注”的方式一一呈现。正文中关于“西施”的词条区区288个字,而用于阐述西施死因的“边注”竟然528个字。纵览全书,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第二章“建置”中谈到萧山这个地方历史上曾被称为“余暨县”,但坊间关于“余暨县”这个名字的来历有多种说法,有据可查的就有三种,于是,编纂者又以“边注”的形式用119个字把这三种说法一一道来。可以说,《萧山市志》中,每出现一个新的名称,编者都会用“边注”的形式给出解释:《绍兴府志》里是怎么说的,乾隆《萧山县志》是怎么说的,嘉靖《浙江通志》是怎么说的,南宋嘉泰《会稽志》是怎么说的,《萧山县志》(1987年版)是怎么说的,等等。如果碰巧这些志书中又出现不一致的说法,编者会再一次不惜笔墨给你细说端详,让你“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二、以“边注”或附文深度解说指点迷津
《萧山市志》在谈到萧山市民的“教育消费”时说道:“萧山民众素有尊师重教之风,80年代中期起,萧山城乡居民的教育意识与日俱增。”这句话既平实又普通,似乎没有需要过多解释的地方。但《萧山市志》的编纂者觉得,如果不拿出些史料或者数据,就说明不了萧山“素有尊师重教之风”。于是,他们采取边注的方式,通过旁征博引来为萧山“素有尊师重教之风”添加340个字的注脚,而此段正文才34个字。滨海城市的特产之一就是海产品,《萧山市志》中,与“渔业”相关的章节里,作了细致入微的“解说”。比如:“10多年来,水产资源总体变化不大,但钱塘江鲥鱼已多年不见。每年6到7月,如期而至的蟹苗已形不成汛期。1至5月的鳗鱼捕捞年产量每况愈下,钱塘江天然水产资源衰退明显。”此段叙述乍看上去没有多少可再“赘述”的东西,依照我们通常的思维方式,顶多也就是对生僻字加一个拼音或者注释,比如这个鲥鱼的“鲥”字和鳗鱼的“鳗”字等。但志书的编纂者觉得有必要就鲥鱼的生活习性、烹饪时的注意事项、食用时的口感、蟹苗资源的盛衰、渔民捕捞工具的变革、当地渔业生产的基本状况等背景给读者一个详细交代,而此段交代达到1120个字,足足比正文多出4倍。
在某些情况下,编者觉得“边注”已不足以说明问题,必须采取另外一个容量更大的方式来阐释。如在介绍花卉苗木的时候说到一个传说,叫作“养狗管龙柏,龙柏烧狗肉”,意思是说,当年曾经有一段时间,当地人以为栽植龙柏赚钱,于是大批量栽植这种树木,不料后来市场发生了变化,导致很多龙柏砸在手里,苗农被迫拔出苗木当柴烧,这种情况和前几年的“蒜你狠”和“豆你玩”差不多,一般情况用三五句话即可说得明白,但《萧山市志》的编纂者觉得有必要把这个事的来龙去脉详细交代清楚,但又觉得仅用“边注”还不够,于是专门附了一篇文章《“龙柏烧狗肉”现象》。
动辄添加千余字的“边注”来说明一个坊间传说或者解释一个偶发现象,在《萧山市志》里已不是个案,随便一翻触目皆是,“释文”比正文的字数多三五倍的情形屡见不鲜。
三、不是辞海胜似辞海,以“边注”处理二轮志书上限与历史衔接
志书虽然号称“资料性文献”,但很多地方的志书名不符实,其“资料性”不尽人意,而二轮《萧山市志》则在“资料性文献”上做到了实至名归,名副其实。
首先,凡是带有“始于”的句式,都有比较详实的“边注”引经据典。比如,“萧山职工教育始于50年代初”,仅此句话,就加了一条340个字的边注,详细叙述了20世纪50年代萧山职工教育的发生发展和阶段性成果,数据详实,前后脉络清晰,言之凿凿,令人信服。再如,“萧山干部教育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了证明此说法,附加一条337个字的边注,证明萧山的干部教育早在1949年5月萧山解放时就已经全面铺开,确实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再比如,“5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附了一条419个字的边注。诸如此类的“背景介绍”在整部志书中随处可见,几乎每一项事物(包括基础设施)都会“溯及以往”,并且每一条“背景介绍”都不是三言两语,基本都可以独立成篇。比如在“城市管理”章“环卫管理”节中分别有街道清扫与保洁、垃圾清运与处理、粪便清运与处理、公共厕所和沿街卫生设施等项,此类事情在志书中通常都是一般叙述,基本是一笔带过,但二轮《萧山市志》对其中的任意一项都“溯及以往”,按志书的专业术语讲,就是都从事物的发端说起。如“街道清扫与保洁”的“边注”从民国18年(1929)记到1982年,将近500字。
其次,志书中对于所有第一次出现的与以前志书中的提法不相一致的概念或者词汇,都会用“边注”的形式给出详细说明。比如“行政村”,之前所有的首轮新方志等都是这样称谓,甚至全国许多地方的二轮志书和新近出版的年鉴都继续这样称谓,但二轮《萧山市志》直接称“村”或者“自然村”,不再使用“行政村”。由于是第一次出现了和以前不一致的称谓,编纂者就特意加了一个255个字的“边注”详细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原来,“行政村”存在于1937年到1945年的抗战时期和1949年至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专指当时在农村设立的基层行政区,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后,“行政村”被撤销,以后的所有规范性文件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称谓,各地志、鉴之所以继续这样称,其实就是一种习惯沿用,是不严谨的。
四、“社会调查”令人瞠目,“口述历史”绝无仅有
在众多学者和专业期刊还在为“口述可不可以入志”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二轮《萧山市志》专门为“口述资料”设置了专册。二轮《萧山市志》一共6册,其中第1至3册是志书的主体,设有总述、大事记、专志45 编,合计500万字;第4册为索引,100多万字;第5册是社会课题调查专册,300万字;第6册是口述历史专册,80多万字。二轮《萧山市志》在“编辑说明”中说:“六、使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广泛开展社会调查。调查成果编成《社会课题调查》专册。七、注重口述历史的方法,对文献资料起补充、印证和鉴别作用。口述历史成果编成《口述历史》专册。”也就是说,“社会课题调查”专册和“口述历史”专册,合计近400万字,占全志篇幅1005万字的40%,这个篇幅以及占比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在这之前,全国其他地方的志书对“口述资料”的使用还有点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好像自己是把“道听途说”的东西编入了方志。其实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前,足迹几乎走遍了全国,他广泛接触各阶层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收集了许多民间宝贵的历史资料,了解和熟悉了古代许多战场和地理环境,他做的许多工作实际上就是今天的“社会课题调查”和“口述历史”。只是今天的萧山修志人把这种事情做到了极致。
二轮《萧山市志》“社会课题调查”专册共分16辑,分别是萧山人的一天、萧山居民生活质量调查、萧山居民休闲娱乐情况调查、萧山居民择业观调查、萧山居民社交礼仪调查、萧山居民出行调查、萧山居民家庭车辆拥有与使用情况调查、萧山居民住宅情况调查、萧山居民“吃、穿、用”调查、萧山居民民间资本投资调查、萧山家庭教育观的变迁调查、萧山百岁老人状况调查、萧山妇女地位调查、萧山知识分子调查、萧山企业家调查、萧山民工生活及生存状况调查。拿“萧山人的一天”来说,仅仅这一个课题,就又细分出13个小题,其中包括萧山人一个工作日的生活及感受、一个休息日的生活及感受、不同自然特征者一个工作日的生活与感受、不同社会特征者一个工作日的生活与感受,等等。在第一辑最后,有2篇附录,一个是“萧山人的一天调查问卷”,一个是“萧山人的一天访谈记录”,仅其中的“萧山人的一天访谈记录”就详细记录了对27个人的采访实录,语言平实,现场感强,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问答自然,宛若昨天。二轮《萧山市志》“口述历史”专册共有92篇访谈录,口述者(受访者)有精英,也有平民,入志内容都是第一手资料,具有可读性、原创性。二轮《萧山市志》对社会课题调查、口述访谈所下的功夫以及对资料的搜集量在全国方志界尤其是对于县(市、区)级的史志部门可谓史无前例、绝无仅有。一卷在手,令人叹为观止。
一个县(市、区)级的志书竟然有1000万字,全国数下来也无出其右,旧志中的县(市、区)志书也有字数较多的,比如民国《鄞县通志》,有550万字,但距离千万还差太远。萧山人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杭州市萧山区史志办调研员莫艳梅认为,很多史志编纂者对于志书字数的认识存在误区:控制志书篇幅有明文规定,应该坚决执行;控制志书篇幅字数是符合实际的,至今没有过时;志书篇幅过长与文字不精炼有直接关系;志书篇幅过大妨碍志书的阅读与使用;志书篇幅关乎志书的质量与可持续发展。莫艳梅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些误区:一是因地制宜,择善而从,就篇幅过小的志书与篇幅较大的志书而言,后者在提升资料性方面会更有把握,而片面强调控制志书的篇幅,不仅束缚了修志者的手脚,对志书的资料性也有很大的削弱;二是篇幅短的志书不一定就好,篇幅长的志书不一定就不好,关键看质量,2008年《地方志书质量规定》没有明确规定志书的篇幅字数,也说明已经没有限制的必要了;三是志书的篇幅长短,主要取决于志书的体例、框架、记述、资料等,文字是否精练,与行文直接相关,对志书的篇幅不起决定性作用,如《萧山市志》“社会课题调查”与“口述历史”内容多达400万字,注释列为主要体裁之一,这就是该志篇幅大的主要原因;四是志书质量的高低,根据《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的衡量标准:观点正确、体例严谨、内容全面、特色鲜明、记述准确、资料翔实、表达通顺、文风端正、印制规范,而没有以篇幅字数为衡量标准,所谓志书篇幅超标一票否决,是不切实际的要求;五是随着志书电子化的发展,篇幅长的问题如不便检索、携带、保存、阅读与传播等问题,就不是什么问题了(详见莫艳梅:《谈控制志书篇幅的认识误区》,《浙江方志》2013年第3期)。无疑,莫艳梅的观点,为破解二轮《萧山市志》的“千万之谜”提供了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