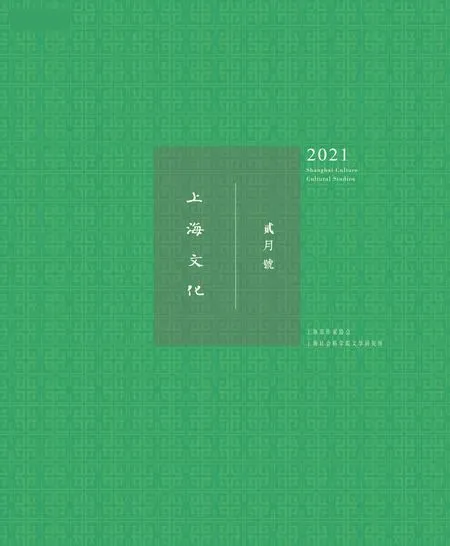游戏化生存:未来的艺术与艺术的未来
严 锋
电子游戏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飞速发展是人类文化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奇迹。很少有哪种文化产品能像它那样一出世就横扫文化消费市场。电子游戏迅速地赢得年轻一代的狂热拥护,并正从电影电视等强大的主流文化产品中抢夺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
在20世纪80年代电子游戏刚刚兴起的时候,它被视为低级幼稚的娱乐产品,腐蚀青少年心灵的鸦片,令人远离正常的人际交往的电子毒品。而今天,在中小学校里,如果你没有玩过《我的世界》和《王者荣耀》这样的游戏,甚至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每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数字产业展会,也是数十万游戏玩家们的狂欢盛会。2003年11月18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将电子竞技列为第99个正式体育竞赛项目。在2019年的电子竞技赛事奖金金额排行榜单上,仅《堡垒之夜》一个游戏的奖金总额就达到了6442万美元。游戏者不再是蓬头垢面、面色苍白、不善交际的怪人形象,他们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
对于电子游戏这种“另类”文化形态咄咄逼人的崛起,国内外的学术界也在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游戏者们中间,也早就出现了要为电子游戏正名的呼声,甚至已经有人在欢呼“第九艺术”的诞生了。电子游戏能算是艺术吗?它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之为艺术?它与已有的艺术在哪些方面具有可比性,有哪些独特性和潜在的可能性,对传统的艺术形态和观念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这些都是非常值得人文科学工作者严肃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
一、情感的强化
电子游戏能算是艺术吗?任何一个玩过《仙剑奇侠传》的人对此绝不会有半点怀疑。这是中国游戏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问世于1995年,迄今已发行八款单机角色扮演游戏、一款衍生经营模拟游戏、两款网络游戏、一款网络社交游戏和一款衍生手机游戏,还被多次改编成电视剧、漫画、小说,可谓长盛不衰,影响深远。
《仙剑奇侠传》第一代的开头,男主角李逍遥——也就是游戏玩家——在某渔村的一个小酒店里打杂,却志向高远,不甘心被老娘耳提面命,终于出走江湖,遍寻高人。机缘巧合,他结识了楚楚可怜的女主角赵灵儿。李凭借一招半式三脚猫的功夫护送佳人至苗疆千里寻母,并陆续结识了刁蛮任性的千金小姐林月如、天真烂漫的苗族巫女阿奴,牵扯出一连串缠绵悱恻的爱情纠葛。
《仙剑奇侠传》的游戏画面以45度斜向绘制,插配活灵活现的角色动画,描绘出诸如耕种、钓鱼、养鸡、打铁、洗衣等民风民俗。更时有松柏仙鹤、渔樵流水,配以丝竹之乐,烘托出古色古香的中国传统风味。战斗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打打杀杀,而是穿插了生动的对话和曲折的剧情发展。
更惊人的是,这是一部悲剧。在游戏的结尾,女主人公为了自己的心上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这是唯一的结局,完全不可逆转。多少少男少女在发现这个难以接受的尾声后,一遍又一遍地从头玩起,为的是要找到那谣传中的“第二种结局”,将女主人公起死回生,结果却仍然是只能徒劳地用他们的泪水浸湿键盘和鼠标。
许多玩过《仙剑奇侠传》的人都会信誓旦旦地向你保证这是一部荡气回肠的作品,艺术性超过一般的武侠小说,如单以泪水来衡量,则恐怕还在金庸之上。这可是了不得的评价!须知在金庸封笔、古龙仙去后的无聊日子里,我们已经虚掷了多少殷切的期待。如今这期待难道竟然落实在一个游戏身上?据我看来,《仙剑奇侠传》的文字确实不俗,但仅仅把文字分割出来凑成一部武侠小说的话,则无论如何不会有如此之轰动。是电子游戏独有的特点把自身的艺术性放大了。在通过观看、搜索、打斗、解谜、对话等一系列的操作后,“仙剑迷”们把自我投射在游戏的虚幻角色里,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参与感和认同感。
在太空模拟射击游戏《银行飞将3》中,人类在与外星侵略者基拉西的斗争中节节败退,总部把银河飞将布莱尔上校——也就是玩家本人,由影片《星球大战》中主角巡天者卢克的扮演者马克·汉密尔扮演——派到了前线。游戏在一片悲壮和失败的气氛中展开,布莱尔的恋人安吉尔上校在执行秘密任务时不幸被俘,在基拉西的宫殿里宁死不屈,怒斥顽敌,英勇牺牲。布莱尔承担了运送人类联邦赖以扭转战局的超级秘密武器的任务,不幸又因内部间谍的泄密而告失败。就在这时,帕拉丁将军(由影星莱斯·戴维斯扮演)来到布莱尔所在的母舰,向布莱尔亮出了人类联邦的最后一张王牌:基拉西人的家园基拉(相当于人类的地球)地质结构极不稳定,联邦间谍已经探明其最致命的薄弱环节,对准它发射高能核弹即可导致毁灭性的连锁反应。这一深入基拉西腹地的艰巨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主人公身上。帕拉丁对布莱尔说:
安吉尔牺牲了,但她的事业永存!
这是一句令银河飞将玩家热泪盈眶的话。你也许会奇怪,这句老掉牙的豪言壮语有什么稀奇?不错,这话对于传统文学的读者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如果安吉尔曾在《银河飞将1》中做你的僚机,替你挡住了无数飞向你的炮火;如果安吉尔在《银河飞将2》中作为母舰的舰长收留了你这个当时被许多人视为叛徒的人,并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你;特别是,如果你现在才知道在三代游戏中安吉尔之所以牺牲,正是为了先行深入基拉西领土,在沿路为布莱尔将来的漫长航程布下隐藏的弹药和飞船;如果在这个终极的艰难任务中,你能够一路上拣起安吉尔用她的生命埋下的伏笔,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安吉尔的期待;那么,你一定能够以独特的游戏的方式更好地理解“事业永存”这句话的史无前例的含义。
在传统的文学艺术中,同样存在着读者/观众对于自我的投射,但是在电子游戏中,这种投射活动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我是一个热爱文学并因此以文学为职业的中文系教师,但这辈子最难忘的艺术感受却是在游戏中得到的。很多优秀的小说,读过也就忘在脑后了;而一些情节平庸、思想肤浅的游戏,很多年后想起来依然激动人心。这就是体验和参与的力量。与传统文学艺术相比,电子游戏更注重玩家的体验,这种体验不仅是视觉的和听觉的,也不仅是语言文字激发的想象,而是由玩家通过身体性的操作,将多种感官与大脑的活动进行整合。游戏研究者格兰特·塔维诺(Grant Tavinor)认为:“电子游戏具有推动艺术发展的巨大潜能,就在于它能将观众拉进虚构的世界中,把虚构的情感与动作结合起来。电子游戏是交互性的小说,让玩家在游戏世界里既成为认知的主体,又成为行动的主体,他们因此就能够对那个虚构的世界发生影响,从而引导他们自身的行动。这也意味着电子游戏中的情感对于艺术哲学来说有着更为重大的潜在意义。”①Grant Tavinor, The Art of Video Games, Chichester, Weley-Blackwell, 2009, p.133.从某种意义上,电子游戏具有不同程度的“角色扮演”的意味,其过程有点像表演性的戏剧,但玩家不仅是传统的观众,也是舞台上的演员,而整个游戏空间的广阔性和自由度又大大超过了传统的舞台,让玩家能在其中尽情发挥和自我陶醉,体验创造、表演和观赏的三重快感。
电子游戏对情感的制造和强化,正是其媒介性的体现。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是人的延伸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大多数技术都产生一种放大效应,该效应在感知的分离中是十分明晰的。广播是声像的延伸,高保真的照相是视象的延伸。而电视首先是触觉的延伸,它涉及所有感官的最大限度的相互作用。”②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11页。麦克卢汉如果活到今天,他会看到电子游戏为感官的强化增添了全新的维度:身体。早期的电子游戏只有简陋的人机界面,玩家是用简单的游戏杆或者鼠标键盘进行操控,身体的动作及其与游戏世界的互动也非常有限。在今天,游戏硬件飞速发展,对玩家身体的开发和利用也日新月异。从带有各种力量反馈的新型游戏手柄,到Kinect、WII和Switch的体感控制器,再到人体定位、手势识别和眼球追踪,现实中的玩家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个眼神都能被游戏识别感应,也让玩家与自己投射的对象产生更大的认同、更深的沉浸与更强烈的情感反应。
麦克卢汉肯定技术和媒介的力量,但他也对其滥用保持警惕:“为了放大或增加人体官能的力量,我们放任自己,我们自我异化,这是邪恶的花朵或赘生物。”③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155页。情感是人类的纽带,也是所有艺术的基础。了解情感在电子游戏中的构成方式,因势利导,去粗取精,用而有度,对于推动游戏产业和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视角的解放
新的艺术媒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感,也带来了新的视角。在文学艺术中,叙事视角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作品的存在方式。同样,视角在电子游戏中也是一个极为核心的问题。早期的电子游戏一律是固定得死死的有限客观视角,比如20世纪80年代任天堂红白机上极为流行的《魂斗罗》《双截龙》之类,我们在屏幕上操纵一个我们看得见的小人走来走去,手持各种武器同坏蛋和怪物们浴血奋战。这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情形,既是客观视角,又包含了主观的成分,在传统的文学写作中很难看到。那个“我”既是我,又不是我,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一方面,我站在我以外的地方看见“我”自己(我灵魂出窍了吗);另一方面,我对这个“我”拥有全部的操纵权(可见我的灵魂没有出窍)。这个屏幕上的“我”同我极不相像。在某些游戏,例如《恐龙快打》中,这个“我”是一只非常难看的恐龙;在《铁甲威龙》中,这个“我”是一个散发着金属光泽的机器人。但是显然我对这个异己的“我”产生了认同。当敌人的拳头挥过来的时候,我不但指挥屏幕上的“我”进行躲闪,还会下意识指挥椅子上的真实的我进行躲闪,当“我”被敌人击中的时候,我感到沮丧和痛苦,还有仇恨,这种仇恨的感觉同生活中的仇恨的感觉一模一样。游戏中这种奇特的视角及其效应充分说明了主体性的脆弱和自相矛盾。人的自欺和认同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它甚至不需要借助罗兰·巴特所称的现实主义文学赖以生存的“真实化”策略。人对“他者”进行认同的渴望在电子游戏中表现得格外淋漓尽致。
这里说的认同(identification),也是弗洛伊德晚年非常关心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认同作用是精神分析已知的与另一人情感联系的最早表现形式,它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史上起一定的作用。小男孩会表现出对他父亲的特别兴趣,他希望像他一样长大,并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处处要取代他的地位。弗洛伊德把认同情结发展为集体心理学的基石。小孩在长大以后,对父母的模仿进一步发展为对他人(特别是集体中的领袖)的模仿,社会也就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①《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15-118页。
说穿了,认同就是突破自我、成为他人的一种渴望。我们看到,在电子游戏中,这种认同比传统文艺中更为强烈、直接和大规模地出现,而且表现得非常奇特。不光有对人的认同模仿,还有对动物的认同模仿。例如在冒险游戏《坏虫》中,玩家所扮演的主角是一只蟑螂,这简直就是卡夫卡《变形记》的翻版,以更为直观和体验化的形态呈现。体会一下你从一只被捕鼠夹夹住的奄奄一息的老鼠身上爬过时的感觉吧,这是一种令人恶心、震惊的奇异体验,与那么多从动物视角切入人类社会的先锋文学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玩完这个游戏,你会对危机四伏的蟑螂以及与此不无关联的人类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全新的理解。后现代是一个“视界融合”的时代,我们被各种各样的眼睛看,我们也用各种各样的眼睛去看,而电子游戏就是我们在新时代观看世界的新的眼睛。我们最终能和蟑螂的视界融合吗?电子游戏代表了一个新的大规模的认同时代的到来吗?
在电子游戏的发展过程中,视角变得越来越多样化。id公司推出的《刺杀希特勒》是最早使用第一人称视角的游戏之一。屏幕上那个可笑的小人消失了,我再也看不见“我”了,我所看到的与我应该看到的完全合二为一。这里面似乎消除了那种人格分裂的超现实主义的感觉,带来了一种极大的真实感。《刺杀希特勒》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并掀起了一股仿作的热潮。从此这种第一人称的形式在电子游戏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模拟类游戏中,游戏者眼前的景象与驾驶员的主观视角也是重合的。在《数字战斗模拟世界》等飞行模拟游戏中,它们模拟的对象由于本身也是主要借助电脑和键盘来进行操作,所以二者的视角融合达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游戏者用电脑模拟杀戮的过程,而在现代高科技战争中,真实的杀戮越来越依靠电脑来进行。虚拟的杀戮与真实的杀戮在操作上和视觉上有着越来越多令人不寒而栗的相似之处,如果这种视界的融合是未来的趋势的话,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必须对此保持强大的警惕。
电脑3D技术的进步,使得多重视角成为电子游戏在叙事过程中天然的巨大优势。很多冒险射击游戏都允许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主人公的活动。像FIFA和NBA系列的体育游戏也可以在比赛时任意地切换摄影机的角度。可以俯视,也可以45度角斜视,还可以用镜头追踪或者镜头漫游的方法。从客观视角到主观视角再到多重视角,这难道不正是文学叙事作品在历史上曾经走过的道路吗?在冒险游戏《错体奇航》中,主人公来到外星系女人国,自己变为女体,就像伍尔芙的小说《奥兰多》,又在一个地方遇到设计这个游戏的公司的老对头——另一个著名游戏公司(当然用的是谐音)在倾销拙劣过时的游戏,这种异质文本镶嵌的元叙述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是屡见不鲜的。
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杰姆逊认为,视角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形式的问题,其本质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为什么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会出现透视法呢?这是和笛卡尔的‘意识即中心’的观点相联系,和西方新兴的关于科学的观念相联系的,此外还有自然的统一化,以及商业的兴起等等原因。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到透视的出现是和经济、科学的发展,以及空间和人对自己身体的认识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①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到了现代,西方人不再相信透视是认识现实的唯一方法。现代主义的绘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摧毁透视、摧毁画框带来的整体性,要冲出的不仅是一种风格体裁,而且是一整套意识形态。现实不再是具有统一性的对象,观察者也不再是一位有统一性的主体。电子游戏体现的那种奇异的多重视角,恰好继承了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以来的空间化倾向,并可视为后现代的文化逻辑的最新表现形态。
你用谁的眼睛来看,站在哪一个位置上,你也就更容易建立什么样的思想立场。可是在电子游戏中,玩家往往可以同时拥有许多双眼睛,同时获得截然不同的立场。在一个名叫《德军秘密飞行武器》的模拟飞行游戏中,玩家可以扮演一个德国纳粹的王牌飞行员,驾驶着德军秘密研制的新式喷气战斗机,对抗盟军的空军,进而改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当然在这个游戏中玩家也可以选择参加不列颠皇家飞行队,或者参加美国空军,替盟军的胜利添砖加瓦。在几乎所有的即时战略游戏中,都会给玩家提供参与作战的任意一方的选择。电子游戏的战场就是一片解构的战场,在这片无厘头的战场上,历史比任何时候都更被颠来倒去,传统的正邪、忠奸、善恶等道德观念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加受到挑战。如果你今天做曹操,明天当刘备,后天是孙权,大后天甚至可以扮演貂蝉去一统天下,那样会预示着一个大规模的人格分裂时代的到来吗?这确实是电子游戏最容易受人诟病的一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电子游戏视为一种新的教育机制的话,玩家从不同的视角观看和体验世界,这也是把道德的判断、选择和责任从传统的教育者向被教育者转移的过程。在接受与参与选择,引导与主动发现,启蒙与自我启蒙之间,电子游戏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挑战与希望并存的文化空间。
三、媒介的融合
什么是艺术?几千年来人们对此争论不休,有一个电子虚拟社交游戏对此提供了他们的答案:“第二人生”。这是一个基于网络的虚拟世界,其玩家在游戏里叫做“居民”,通过移动的虚拟化身互相交流,参加个人或集体活动,制造可以出售的虚拟物品,甚至可以买卖虚拟的地产,从中获得真实的金钱。开发商的口号是:如果你在现实人生中失败了,那么就来我们这里开启你的第二人生吧。对“第二人生”的居民来说,艺术就是通过创造可能的人物与可能的世界,让人们突破真实世界的束缚,进行想象性的自我超越与自我实现。这又何尝不是艺术的目的呢?但在传统艺术中,可能的世界是有限的,自我超越也是有限的。更具体地说,就是受到各种艺术媒体的限制。例如,传统的小说、戏剧、电影等叙事艺术中,时空相对稳定,具有线性与不可逆性,这集中地体现为情节发展方向的固定化和结局的唯一性。这种形态的文学对读者的参与有着很大程度的阻遏。在古典时代,当不同的观念意识在同一部作品中容纳不下时,读者会推举他们的代表(多半是某一个续貂的作者)来实现他们的欲望。例如,《红楼梦》之后大量续书的出现,即可被视为读者“交互性”渴望的古典形态。
在《红楼梦》这样的传统作品中,还存在着一种隐含的交互性。对于这种交互性,我们今天用游戏的眼光能够获得新的认识。《红楼梦》的叙事以第三人称视角为主,但这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而是一种有限主观的人物视角,经常跟随人物的移动而不断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随着人物的视角进行观察、探索、感受。例如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来至荣府大门前,不敢进去。蹭到角门前,被几个闲人愚弄。后来经一个老年人指点,绕到后门才得以入内。对熟悉游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冒险RPG(角色扮演游戏)的场景,游戏人物来到某个市镇或城堡,探索未知环境,设法通过关卡,与NPC(非玩家人物,也即这里的“众人”)交谈,搜集线索,寻找解决难题的办法。如果我们制作一个《红楼梦》的RPG游戏,在这里就可以操控刘姥姥在荣府外面四处走动,发现有正门、后门、西角门、东角门。除了从大门进去太不合情理之外,其他几个门都可以作为行动的路线,在不同的选择中体现交互性和非线性。但是在小说中,刘姥姥显然只能从一个门中进出,如何交互?在作为小说的《红楼梦》中,对于这些门,我们还是有机会选择的,就是通过其他人的视角来实现。在刘姥姥之前,我们已经通过贾雨村的眼睛看到了。同样的门,在贾雨村的眼里自然是另种风景,别样意蕴。在这之后不久,刘姥姥无法穿越的角门被人突破了,那是黛玉。刘姥姥所见的“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在她眼里变成了“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但她与贾雨村和刘姥姥都看到了那个似乎永远关闭的大门。这个大门要到第18回,才终于为省亲归来的贵妃打开。
这种交互性的视角,使得《红楼梦》呈现出一种网状的、非线性的叙事模式,也是《红楼梦》的独特魅力所在,但是这种交互性在传统文学中并不常见,也受到文学这一艺术媒介在叙事形式上的限制。传统的文学作品一旦制作完成,其物理形态便固定了下来,这是一个一次性的创造过程,而读者的阅读过程也不得不呈现出线性的特征。尽管如此,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读者一直是最具推动性的因素,他们总是在不断试图超越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到了现代,文学面向读者的运作过程变得越来越明显,文学批评中也出现了读者反映批评、接受美学、阐释学等理论,文学的重心开始从作者向读者转移。有意思的是,这些以读者为中心的理论的提出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游戏,把游戏视为文本的开放性的原型。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沃尔夫冈·伊瑟尔认为:“阅读总是在选择中突出对象:或者是多样化的选择,这意味着包纳游戏的多种可能性,或者它自己开放于各种变化的反动而指向最初假定的角色。”①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汪正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0页。就文学史而言,也存在着一个交互性逐渐活跃和不断被释放的过程。特别是现代主义出现以后的文学,更多是一种读者的创造,作者在文本中留下了很多空白的、游移不定的点,读者的阅读本身也就变成了一种游戏。可以说,现代文学艺术正越来越走向游戏。随着电子游戏的出现,艺术中原有的游戏因素不断得到释放,获得全新的意义。
罗兰·巴特认为有两种文本,一种是“可读的文本”,读者小心翼翼地服从作者的意愿,循规蹈矩,无所作为;另一种是“可写的文本”,读者在这种文本中玩着无穷指涉的游戏,进行自由的创造,升级到了作者的地位,而原作者则失去了对文本的控制,降格为一个超级读者。可读的文本代表的是“愉悦”,而可写的文本代表的则是具有性快感的“极乐”。在两者之中,巴特心仪的是具有先锋性的可写的文本。②Roland Barthes,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5, p.4.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曾经在中国有过短暂的辉煌,但不久就悄然退场,余华等先锋作家又回归可读的文本的写作。其实,就是在他们最红火的时候,读者也很少在这些作品中体验到过“极乐”,更多的是阅读的烦恼。到头来大家还是宁愿在传统的文学样式和阅读习惯中安于循规蹈矩的小康之乐。这恐怕不能完全归结为中国先锋文学的生不逢时和水土不服,更根本的原因要去文本内部寻找。文学要变成巴特意义上的极乐游戏,首先要越过语言本身的重重障碍。放眼世界范围,先锋文学也早已式微。20世纪90年代电子超文本文学出现,曾被视为后现代主义在数码媒介中的新希望,但是到了21世纪也逐渐失去了动力。
如果我们再从一个更大的文化视野来看这些走向,就会发现可写的文本其实从未消失,反而走出了少数精英的文化实验,找到了全新的载体,并走向了极为广阔的大众文化空间,那就是网络、游戏和虚拟现实。在那里,大众进行着前所未有的自由创造和极乐的游戏。另一方面,电子游戏从诞生起,也在不断地从文学那里借取题材和表现手法,让文学以游戏的方式转世重生。大量的文学经典名著,如《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浮士德》等反复被改编成电子游戏。而很多电子游戏,如《陆空战将》《家园》《时空之轮》等,除了软件本身外,还会附带赠送一本精美的手册,这手册本身就是一部以游戏为背景的小说。在著名RPG游戏《上古卷轴5:天际》中,故事情节、人物和世界设定也以玩家的冒险旅途中能够收集的一本本书籍的形式呈现,书籍数量有820部之多。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根据游戏改编的小说和电影不断涌现。数码电影《最终幻想》就是根据同名游戏改编而成。《银河飞将》被拍摄成电影,改编而成的系列小说已经出了六部。续拍的《星球大战》,在电影进入院线的同时,同名的小说和游戏也同步上市,昭示着新时代一个艺术品以多种媒体同时呈现的前景。
除了这些职业性的创作以外,网络上出现了很多网友自己创作的以同名电子游戏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正在成为网络文学中的一大类别。例如曾经在网上流传很广的《帝国时代纯情版》就是佚名的中国网友以微软出品的策略游戏《帝国时代》中的一个小兵为视角,讲述了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这篇短短的小说有多种版本,而且前后风格极不统一,显然出自多人之手,又具有网络小说“合作化”的特点。
电子游戏与传统艺术之间,除了相互改编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相互渗透关系。在艺术手法和风格技巧上它们也彼此借鉴。例如,在晚近的电影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游戏式的光影效果。在情节的进展上,一些小说和电影也借鉴游戏的练级、生命值、解谜、攻关等套路,迎合观众新的心理需求。这方面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科幻电影《安德的游戏》,其节奏、视觉、调子、气氛都给人一种强烈的游戏感。游戏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3D特效的发展,不仅终于为这部小说提供了成功改编为电影的技术,也孕育了具备游戏审美观的新一代观众。
影视与文学一旦进入游戏,那就不止于简单的改编,而是开辟了全新的天地。在传统的艺术中,读者和观众可以观看不同的人生。在电子游戏中,玩家不仅是观看,还扮演、体验、创造不同的人生。玩家不仅是读者和观众,也是演员、导演、作者……简言之,就是世界的创造者。就媒介的融合而言,电子游戏为文学艺术增添了新的维度和自由度。
四、艺术的超越
在新一代艺术的融合中,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一种指向:越界。这是一个越界的时代,人类主体正在变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具有能动性,越来越不受局限,而电子游戏就是这一趋向的最新载体。电子游戏结合了小说、绘画、音乐、电影等传统艺术的元素,融技术、欲望、幻想、现实、逃避性、参与性、交互性于一炉。从前在其他艺术中由于媒介和技术的限制而受到阻遏的意志和欲望,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可以畅通无阻地宣泄出来了。反过来,在对这种酣畅淋漓的宣泄进行观照之后,我们又可以对它们以往在传统艺术媒介中受阻遏和限制的形态有更深切的认识。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催生了一个众声喧哗和主体性空前活跃的新世纪,我们在“赛博空间”到处可见对无限的可能性的渴望、无止境的选择、跨历史的狂欢。这种渴望,一言以蔽之,就是读者、观众、玩家们要扮演上帝的角色。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说作者死了,但是读者还活着,而且他们要做上帝。这是一种古老的欲望,但是也只有今天才为这无数“上帝”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虚拟空间是一个没有法律、只有游戏规则的空间,玩家可以为所欲为,宣泄各种欲望,不用担心自己会被抓起来。即使失败了,也还可以去调一个存盘文件,或者干脆就重新启动电脑。这是一场人类扮演上帝的游戏,而交互性就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成为上帝的努力:不受限制的视角,穿越时空的本领,创造毁灭的能力。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进步,电子游戏中的交互性会不断发展。虚拟现实是人对超越现实的渴望,可以说,一切艺术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虚拟现实。今天,虚拟现实有了全新的载体:电子媒介——更清晰直观,更活色生香,更让人沉浸其中。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在迅速发展,计算机将能自动创造出具有众多可能性的交互式情节。当人们所有的幻想都能够“真实”地对象化、影像化的时候,其身份和自我认同必将发生巨大的改变。另一方面,在虚拟变得越来越真实的同时,虚拟也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概念:虚拟经济、虚拟货币、虚拟社区、虚拟购物、虚拟教育……我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各种形态的虚拟。虚拟的现实与现实的虚拟,这两种朝向彼此的运动能够最终合流吗?这其实也是人类的一个古老的梦想的最新呈现:艺术的生活化与生活的艺术化。
席勒在《人的美学教育书简》中认为人的理性和感性存在着永恒的冲突,而游戏可以将这两者调和起来:“一言以蔽之,人只有在他是十足意义上的人时才进行游戏,只有在他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①《席勒文集》第6卷,张佳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0页。席勒所说的游戏是一种美学的理想,与我们今天的电子游戏看似非常遥远,骨子里还是有着相通的地方,它们都指向一种自由而又自律的状态。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席勒期许的游戏作为电子游戏未来发展的理想。
如果艺术也有制高点的话,文学和电影都代表过这个制高点。我认为,从现在到未来,更具有决定性的制高点是电子游戏。可以这么说:谁掌握了游戏,谁就掌握了人的想象;谁掌握了想象,谁就掌握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