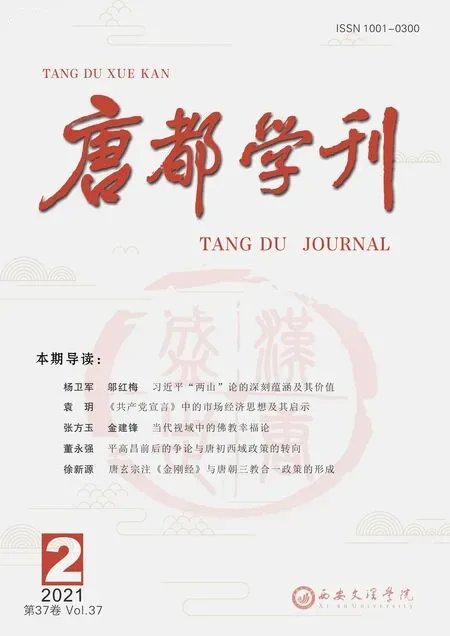休谟道德普遍化的困境与康德式回应
惠永照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道德判断是一种公共性活动,个人的道德判断需要被他人认可和接受,而道德内在地要求普遍化。休谟的伦理学从情感主义的立场出发,将道德感作为道德判断的依据,为了克服情感的私人性,休谟引入了同情和“明智的观察者”以寻求道德的普遍化,最终用作道德判断的道德感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道德感,而是建立在同情之上的“明智的观察者”的道德感。但基于情感的道德普遍化仍会陷入情感的私人性与道德要求的普遍性这一矛盾之中,因从情感中无法给出一种真正普遍的立场。康德早年对情感主义伦理学颇为亲近,后又疏离了情感主义而将道德最终建立在了纯粹理性之上,这一思想过程可看作康德对建基于情感之上的休谟式道德困境的反思与回应。
一、道德感:道德判断的根据
休谟所处的时代,在英国盛行以克拉克等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伦理学,认为每种事物都有一个规定其特征的本性,这种本性可被理性认识,事物根据其本性处于一定的关系中,由此得到了某种适合的关系,以至于某些行为比其他行为更适宜,而事物的本性和适当性足以决定义务。因此,理性主义基于事物的本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适当性来界定道德,“事物的性质规定了有关对与错的关系的一个独立的、先在的秩序,一个由理性所知,在神圣的意志、当然还有人的意志方面具有权威性的秩序。这个秩序是独立的,因为它不取决于我们关于它的知识,也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它是先在的,因为它是必然的和不可改变的,永恒的和普遍的。特别地,它独立于人性独特的构成,也独立于我们的心理特征。”[1]63
与理性主义伦理学相对立,英国产生了以“道德感”(moral sense)概念为核心的情感主义伦理学。人们一般把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归于莎夫茨伯利,因为是他提出了“道德感”的概念,但真正将情感主义伦理学构建起来并得以远播的是哈奇森。休谟的伦理学建立在英国经验论传统之中,又继承了哈奇森的伦理思想。在《人性论》第3卷,休谟首先批驳了理性主义的观点,他限制了理性的作用范围,将道德的基础从理性中转移了出来。休谟认为理性“只有在两个方式下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为。一个方式是:它把成为某种情感的确当的对象的某种东西的存在告诉我们,因而刺激起那种情感来;另一个方式是:它发现出因果的联系,因而给我们提供了发挥某种情感的手段。”[2]495简言之,在实践领域,理性的功能只有两个:一是确定对象的存在,二是为某一目的寻找最合适的方法。理性自身并不设定目的,目的是由情感、欲求来设定的,理性只是寻求能够满足目的的合适的方法和手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休谟说理性是情感的奴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休谟说宁可让世界毁灭也不让自己的手指受伤也是不违背理性的。除了不设定目的外,理性也不能推动行为。休谟认为理性是惰性的、不活动的,因而不能刺激我们的情感,也不能够引发一个具体的行为或制止一个行为,所以无法对我们的行为和情感产生影响,而道德准则恰恰是要刺激情感、产生或制止行为,所以我们的道德准则不可以来自于理性。
在论证了道德的区别不是来自于理性之后,休谟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道德区别是由道德感得来的[2]506。道德感是一种特殊的痛苦和快乐的情绪,道德感的特殊性在于它作为一种苦乐情绪一开始就带有公共性:“我们只是在一般地考虑一种品格,而不参照于我们的特殊利益时,那个品格才引起那样一种感觉或情绪,而使我们称那个品格为道德上善的或恶的。”[2]508如一个敌人身上表现出的某种优良品质对我们是有害的,但仍能激起我们的敬重。这样,道德感一开始就带有超越个人利益的特征。
道德感的功能在于做道德判断,通过特殊的苦乐情绪区分行为和品质的善恶。休谟说:“道德宁可以说是被人感觉到的,而不是被人判断出来的。”[2]506通过道德的苦乐感,可直接感受到道德的善恶,“一个行动、一种情绪、一个品格是善良的或恶劣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人们一看见它,就发生一种特殊的快乐或不快。”[2]507休谟的表述很容易让我们认为快乐是善的原因,一个行为或品格是令人愉快的,所以我们才说它是善的。但实际上,休谟的意思正好相反,一个行为或品格是善的,它才能够引起我们的愉快,所以快乐不是善的原因,善反过来是快乐的原因,快乐只是善的外在标志和认识途径,行为或品格所引起的快乐让我们认识到了善,所以休谟说:“我们并非因为一个品格令人愉快,才推断那个品格是善良的;而是在感觉到它在某种特殊方式下令人愉快时,我们实际上就感到它是善良的。”[2]507
为了更好地理解休谟的“道德感”概念,我们将其与哈奇森的“道德感”做一比较。休谟的“道德感”概念虽来自哈奇森,但与哈奇森并不相同。在哈奇森那里,moral sense可被翻译为“道德感官”,因他是在一种与外部感官类比的意义上使用moral sense的。哈奇森认为,在我们的心灵中有各种各样的观念及对这些观念的不同知觉,它们分别对应于不同的外部感官,如颜色观念对应于视觉,它的器官是眼睛;声音观念对应于听觉,它的器官是耳朵等等,但我们内心中的许多观念不能归于五种外部感官,如我们有关美的观念、道德的观念等,所以为了解释我们内心各类观念的来源,哈奇森主张在五种外部感官之外,至少还存在着四种感官,即内在感官、公共感官、道德感官(moral sense)和荣誉感官。
休谟并不承认一种感官意义上的“道德感”,休谟所说的道德感不是一种道德感官,而是一种道德感觉(感受),也就是不去考虑道德的生理基础,而只专注于与道德相关联的心理状态。所以休谟的“道德感”除了用“moral sense”之外,更多地用的是“moral feeling”或“moral sentiment”。总结起来,学者们认为休谟这样做的原因大抵在于:第一,避免对“道德感官”的批评。因为我们在生理上根本无法找到这样一个器官,所以道德感官只不过是一个比喻,然而这种比喻极易招致人们的非议。周晓亮先生认为:“休谟极少或几乎不用他人常用的moral sense一词,而是用moral feeling或moral sentiment。这也许是由于休谟不希望人们简单地将道德感当成与肉体感觉完全相同,因为自从道德感理论提出,对于是否能发现像眼、耳等外部感官那样的道德感官,就成为对道德感理论的主要责难之一,所以休谟在用词上突出道德感的情绪、情感的特点。”[3]第二,避免对上帝的依赖。休谟之前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包括巴特勒和哈奇森的伦理学,都建立在对上帝的依赖之上,休谟出于他的经验论立场否定了我们认识上帝的可能性,这样他就不能再次将伦理学奠基于上帝之上,所以胡军方说:“休谟似乎赞同道德感的功能性定义,而没有像哈奇森一样认为有这种内部感官的真实存在。如果承认了道德感是一种内部感官,那么这种功能的来源就要追溯到上帝的安排。我们发现,在哈奇森那里,我们的道德感、普遍的仁爱都是来自于上帝。休谟对哈奇森的这种做法表示了不满,因为休谟认为道德的基础是可以独立于宗教,依据经验和观察的方法就可以解释道德的基础。”[4]第三,感觉与情感是不同的,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正如卢春红所言:“出现这一变化的关键在于休谟意识到了二者之间的重要不同。……情感确实需要与感知觉打交道,在这一意义上,情感并不能与感官全然无关,但情感却没有专属于自己的特殊感官。将情感的来源指向某种感官,其实质是将情感混同于感知觉,以感知觉的方式来解释情感。”[5]
也许基于以上理由,休谟放弃了哈奇森式的道德感官,而作为情感的道德感与感官一样具有局限性,即无法克服与感官相类似的个别性和特殊性的局限。一个人出于个人的道德感所做出的道德评价如何能被他人接受,或者说一个人的道德感何以能够成为所有人的道德感。这表明用道德感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所面临的感觉的个别性与道德要求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这是一切想要从情感出发来界定道德善恶的观点都会面临的问题。所以,为了克服感觉的个别性,休谟就引入了同情。
二、从同情到明智的观察者:道德普遍化的尝试
同情是一种普遍的经验事实,而休谟对同情进行了新的界定,从而使其发挥了新的功能。在此首先需要区分两个概念:sympathy和empathy。Sympathy是对他人的不幸心存怜悯,但同情者与被同情者并不感受同种类型的痛苦:X同情Y,X感觉到难过,但X的难过在性质上与Y的痛苦不同。Empathy直到20世纪才出现,一般译为“共情”“移情”“共感”等,它是对他人的情感、遭遇等感同身受:X共情Y,那么X的感受和Y的感受在性质上是类似的[6]。比如面对一个家暴的案例,共情者会与受家暴者感受到类似的痛苦,比如(记忆的或想象的)类似的身体疼痛、伤心、恐惧、绝望等;同情者不必然感受类似的痛苦,但会体验到由受家暴者的遭遇激发出来的难过、愤怒等情绪。休谟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共情”一词,所以当休谟说“同情”时,他是在同情和共情两个含义上使用,并且更多的时候指的是“共情”。
通过《人性论》中的描述,我们可以将同情的过程分为以下两步:第一步,通过他人对话、举止和行为等,在经验的基础上对他人的情感形成一个观念,此时的观念只是我们所设想的他人的情感观念。休谟说:“当任何感情借着同情注入心中时,那种感情最初只是借其结果,并借脸色和谈话中传来的这个感情观念的那些外在标志,而被人认知的。”[2]349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只有他人的行为举止等外在的方面,而无法观察到他人的情感,行为举止在当下也是一些印象,但只是外在行为的印象,而不是他人情感的印象。我们有了他人行为举止的外在印象后,基于以往的经验会发生一系列的联想,这里包含了一种因果联系,即从外在的效果推理出这种举止的原因。休谟说:“当我在任何人的声音和姿态中看出情感的效果时,我的心灵就立刻由这些效果转到它们的原因上,并且对那个情感形成一个生动的观念。”[2]614比如看到一个人在流泪,由他在流泪可以推理出其流泪的原因:他的流泪是因为伤心。他的流泪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呈现出来的,但他的伤心是我们推理出来的,这时候伤心只是一种他人情感的观念。简言之,第一步是由他人外在的行为印象推出他人的情感观念。第二步,借助于与自我观念(或印象)的结合,情感的观念立即转变为一个情感的印象,这时情感的印象是在自我内心中呈现的,它与他人的情感印象是类似的。这一步的关键是将第一步获得的他人的情感观念与自我观念(印象)相结合,“自我的观念(或者倒不如说自我的印象)是永远密切地呈现于我们的,我们意识给予我们以自我人格的那样一个生动的概念,以至不可能想象任何事物能够在这一方面超越这种自我之外。”[2]349通过与自我印象的结合,“那个生动活泼的自我印象把足够的活力传给他人情感的观念,因而将其提升为我们内心的一个情感。”[1]76简言之,第二步的作用就是将他人的情感观念转变为自我的情感印象。
休谟赋予同情的作用是传递情感。人们之间之所以能够彼此同情,是因为:(1)由于一切人在心灵结构和身体结构上的类似关系,我们和他人都具有相似的情感和原则。(2)由于印象与观念的差异只在于强度和活泼程度上的差异,因而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3)由于观念联结的三个原则,即类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才能完成印象与观念之间的转化。正是由于同情,我们才可能感受到别人的情感,这样我们就能够走出自我的圈子,不再只沉溺于自身的利益之中,而对别人的利益也感到关切,“我们对社会所以发生那样广泛的关切,只是由于同情”[2]617。但从同情起作用的过程可以看出,同情虽然要超出自我来传递情感,但同情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或者说同情是有偏向性的,我们对那些与我们有关的人更加容易同情。休谟承认,在同情的过程中,我们情感印象的生动性和活泼性会随着类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而得以加强。比如我们更容易同情和我们有相似背景、相似经历的人(类似关系),我们更容易同情我们周围的人(接近关系),我们更容易同情我们的父母、子女等(因果关系)。这样虽然同情能够克服我们感受的私人性,使一己的感受能够超出自我的范围,但是这样的同情仍然是有局限的,它仍然无法满足道德所要求的普遍性,为此休谟又引入了“明智的观察者”(judicious spectator)。
道德感是某一个人的感受,同情虽然是某一个人的,但它却能超出自身,达到他人的感受,而明智的观察者就不再是某一个人,它本质上不是一个现实中的人,而是一个普遍的立场,是对我们各自特殊位置和特殊观点的超越。休谟说:“我们各人如果只是根据各自的特殊观点来考察人们的性格和人格,那么我们便不可能在任何合理的基础上互相交谈。因此,为了防止那些不断的矛盾、并达到对于事物的一种较稳定的判断起见,我们就确立了某种稳固的、一般的观点,并且在我们的思想中永远把自己置于那个观点之下,不论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如何。”[2]620这一段话表明,我们应当站在一个普遍的立场并以一种一般的观点来进行判断,这个普遍立场是一个取消了一切特殊立场、特殊观点的立场,这就是明智的观察者所处的立场,道德判断并不是由某一个处于特殊立场的个人做出的,而是由处于普遍立场的明智观察者做出的,而由这一普遍立场所获得的道德判断就能够被其他人认可和接受。
明智观察者的普遍立场看起来似乎满足了道德判断所要求的普遍性,但基于同情的明智观察者所能达到的普遍性仍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只要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特殊信息有所了解,他就无法真正克服对自我利益的偏私,如此他的同情就不可能无所偏向,所以如果想要达到一个真正的普遍立场,那些与个人特殊利益相关的一切信息都要被悬置。这样的普遍立场有一个代表,那就是罗尔斯所设想的“无知之幕”[7]。在原初状态中,与个人相关的一切特殊信息都被无知之幕所遮蔽,从而个人所能了解的只是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而对个人的一切都一无所知。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本质上是一种由理性主导从而达到的立场。所以说,虽然基于情感能够达到一种局部的、经验的普遍性,但道德所要求的普遍性是一种全体的、先天的普遍性,后一种普遍性是情感无法给出的,而只有可能从理性的立场给出。
从普遍立场看,道德感也变得含糊不清了。因为明智的观察者不再是一个实在的人格,而变成了一个虚拟的人格,这种非人格并不会产生现实的苦乐情绪,充其量只有一种想象的苦乐情绪。而这种想象的苦乐却仍然要受到想象者的个人立场的影响,因为我们没有人现实地站在一个普遍立场去经验,所以我们无法获得一种与明智观察者的地位相对应的普遍的苦乐情绪,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情感。有观点认为:“普遍观点并不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情感,而是对出于个人利益的情感的一种修正。”[8]这种观点认为,发挥道德判断的仍然是个人的道德感,普遍观点(明智的观察者)只不过是对个人道德感的矫正。这一观点也会面对两种挑战:其一,即便承认普遍观点的矫正作用,鉴于以上我们对明智观察者所能达到普遍立场的质疑,那么普遍观点对个人道德感的矫正效果就是存疑的。我们固然可以用正确的东西来矫正错误的东西,但如果用来矫正其他对象的东西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那么它的矫正效果自然也是有问题的。其二,如果我们真的达到了一种普遍的立场和普遍的观点,那么道德法则其实可以由理性推导出来,并不需要道德感。如此个人道德感在其中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所以当休谟走到普遍立场的时候,他的道德感学说就面临着一种自我取消的风险。
三、康德式回应
康德早年深受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影响,也曾希望将道德建构在某种类型的情感之上,但康德最终从情感主义中撤离而重新将道德建立在了理性的基础之上,主导这一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对道德普遍化的追求。对客观普遍性的寻求一直是引导康德寻找真正道德原则的动力和指南。康德一开始就认识到道德的原则必须是客观的和普遍的原则,“真正的德性只能根植于原则之上,原则越普遍就越是崇高和高贵”[9]218。所以,康德早期对情感主义的亲近和疏离可以看作是康德对建基于情感之上的休谟式道德困境的反思与回应。
休谟对康德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但一般认为休谟的影响更多是在形而上学方面,因为康德曾说:“正是大卫·休谟的提醒,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的独断论迷梦,并且给予我的思辨哲学领域的研究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10]康德的这一剖白承认了休谟在思辨哲学上对他的决定性影响。在伦理学上,休谟对康德的影响虽然不及哈奇森,但不代表康德对休谟的伦理学一无所知。在康德的藏书中,有一套1754—1756年出版的四卷本的休谟文集,收录了除《人性论》外的休谟大多数著作[11],其中也包括休谟的伦理和宗教著作[12]。康德也曾在伦理学的语境下提到休谟,在1765—1766秋季学期所写的课程通告中说:在伦理学上,“莎夫茨伯利、哈奇森和休谟的尝试虽然是未完成的和有缺陷的,但仍然在探索所有道德的最初根据方面走得最远”[9]314。
至少在1760年代中期以前,康德对情感主义伦理学是认同的,并在情感主义的引领下也对道德基础进行了探索。在写于1762年的论文《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中说:“表象真东西的能力就是认识,但感受善的能力却是情感。”[9]301这种感受善的情感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无法分解的关于善的情感”[9]301。在写于1763年、发表于1764年的论文《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中,康德虽然不再提及“无法分解的关于善的情感”,但他仍然认为道德的根据是一种情感的意识,即人性的美感和尊严感[9]218。
康德在这一时期之所以亲近情感主义,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那就是当时伦理学的研究从对人与世界或人与上帝之关系的形而上学思辨转向了对人性的经验性考察。开启这一“转向”的是霍布斯。尽管结论不同,霍布斯和卢梭都在使用这一方法。哈奇森在《道德哲学体系》一开篇就指出,道德哲学的研究用不着借助任何超自然的启示,只需要观察和研究人性的结构[13]。而康德在这一时期也接受了这一基本研究方法,康德在1765—1766秋季学期的课程通告中说:“由于在德性学说中,任何时候我都将在指出应当发生的事情之前以历史和哲学的方式思考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将阐明人们研究人所必须遵循的方法:不仅是被他的偶然状态加给他的可变形态所歪曲的、作为这样一个人被哲学家们几乎在任何时候都认错的人;而且是人的常驻不变的本性中,以及它在创造中的地位。”[9]314
对人性研究的认同使康德被情感主义伦理学所吸引,然而将道德建立在情感之上会面临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即情感的主观性、私人性、相对性与道德法则所要求的客观性、普遍性、绝对性之间的矛盾,即情感的不可普遍化与道德的普遍化要求之间的矛盾。展示这一矛盾的最佳例子就是仁爱。仁爱是哈奇森最为推崇的一种道德情感,他把仁爱类比为延伸到宇宙所有物体的地心引心[14]154。虽然哈奇森也承认仁爱会随着亲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相信“仁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扩展至全人类”[14]115。康德在《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中虽然也推崇仁爱,但已意识到了仁爱作为情感是无法真正普遍化的,认为仁爱一旦上升到它应有的普遍,那么它就是崇高的,但也更为冷漠[9]217。而在《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的评注》上,康德直接点明普遍的仁爱是虚假的,“在人类的博爱中有高尚和高贵的东西,但在人与人之间它只是空想。如果一个人以它为目标,那么他就是习惯于用渴望和无意义的希望欺骗自己”[15]。
正是情感的不可普遍化与道德的普遍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促使康德抛弃了情感主义而走向了理性主义,将道德建立在理性之上,从纯粹理性自身出发来形式化地建构道德法则。所以在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中,康德明确地说:“道德的概念,它们不是被经验到,而是借助于纯粹的理性被认识到。”[9]401康德也不提名地批评了哈奇森和休谟:“就道德哲学提供了首要的判断原则而言,它只有凭借纯粹的理性才能认识,因而属于纯粹的哲学,而伊壁鸠鲁把它的标准置入快乐与不快的感觉之中,受到指责是很有道理的;此外还有远远地在某种程度上追随他的新人,例如莎夫茨伯利及其支持者。”[9]402哈奇森和休谟正属于莎夫茨伯利的支持者之列。所以自教授就职论文开始,康德正式将道德置于纯粹理性之中,道德的基础不是情感而只能是理性。在康德成熟的道德哲学著作《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道德法则是出于纯粹理性的自我立法,从而是一条先验的绝对命令[16],它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理性存在者共同遵循的法则,其普遍性并非建立在经验之上,而是建立在先验之上,因而是绝对的、必然的。
综上所述,将道德建立在情感之上会面临情感的主观性、私人性、相对性与道德法则所要求的客观性、普遍性、绝对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情感的不可普遍化与道德的普遍化要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休谟伦理学的困境,也是康德伦理学在早期试图摆脱的困境,最终康德疏远了情感主义而走向了理性主义,将道德建立在了纯粹理性之上。然而正像休谟对克拉克式的理性主义的批评没有终结理性主义伦理学一样,康德对休谟式道德普遍化困境的批评与回应也没有终结情感主义伦理学,之后的西方伦理学一直都在理性和情感两个维度之间摇摆和对话,而伦理思想也正是在理性与情感的张力中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