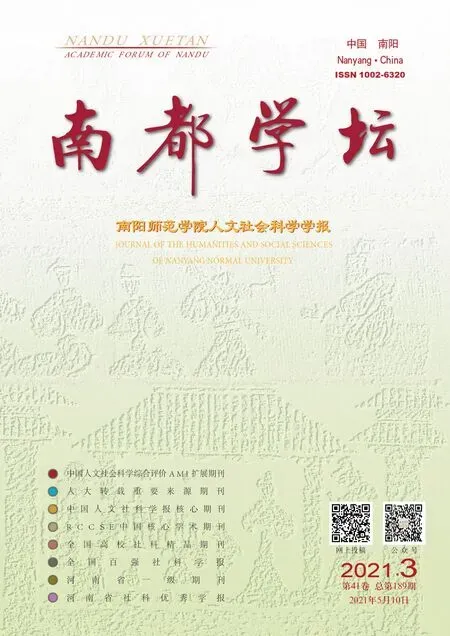论视听作品的定义与权利归属
——以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为视角
刘 鹏, 李馨怡
(华东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上海 200042)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电影作品要满足“摄制在一定介质上”这一要求,包括了对电影作品要以“摄制”的手段创作要求,也包括要求电影作品“固定在一定介质上”的固定性要求,而网络时代新型视听类作品诸如利用计算机制作的网络动漫、科幻电影以及网络游戏连续画面、体育赛事现场直播画面等,尽管其在表现形式和视听效果上与传统的电影作品并无本质差别,但是由于不满足电影作品“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的要求,由此引发了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争论,至我国《著作权法》启动第三次修订以来,“视听作品”的概念就被提出,最终在2020年新修订通过的《著作权法》第3条第6项规定了“视听作品”,至此正式确立了“视听作品”在我国的受保护地位。
本次修法用“视听作品”取代了“电影作品”,是对网络时代新型视听类作品定性争论的回应,然而新法中并未明确规定视听作品的定义,仅仅对作品名称的修改并未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新《著作权法》未规定视听作品的定义,其内涵与外延尚不明确,修法后新型视听类作品是否可以被当然地认定为视听作品仍存疑;其次,本次修法将“录像制品”这一邻接权客体保留,司法实践中区分二者的独创性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依旧延续;此外,在视听作品的权利归属方面,本次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将视听作品分类为“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与“其他视听作品”,并对二者进行了不同的权利归属规定,那么就需要明确二者的内涵与区分标准,但是这属于我国立法空白,因此会带来一定的适用难题;最后,本次修法对“其他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规定“当事人约定优先,无约定则归制作者”的规则,不利于其他视听作品的传播与发展。
二、视听作品的定义分析
我国2020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并未对“视听作品”的定义与分类进行具体的规定,如何界定视听作品的内涵和外延、如何区分电影作品和其他视听作品等问题值得考量,此外,对“录像制品”这一邻接权客体的保留,也让如何区分视听作品和录像制品这一问题依旧存在。因此,下文将从视听作品的构成要件、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的区分标准等层面对视听作品的定义作出分析。
(一)“摄制”非视听作品的构成要件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这一法定作品类型,本文将此合称为“电影作品”。《实施条例》对该作品进行了定义,其中“摄制在一定介质上”是电影作品的构成要件之一②参见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11项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摄制”是指通过摄像装置进行拍摄制作而成,而随着产业进步和技术发展,涌现出大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以 “摄制”方式创作的视听类作品,例如科幻电影和动画电影,其制作手段脱离了摄像机拍摄技术而采用新型创作技术,全部或绝大部分镜头均在计算机中绘制、编辑、合成,无需借助摄制装置完成。又如网络游戏连续画面也是利用计算机手段制作而成,这些表现为动态连续画面,带有伴音或无伴音的视听类作品,目前司法实践中法院更倾向于突破现行立法的字面含义,将其认定为“类电作品”。
以网络游戏直播画面为例,网络游戏直播是互联网技术和直播产业迅猛发展的产物。网络游戏直播所形成的连续画面,是指在网络游戏运行中所呈现出来的画面,包括静态的画面、单幅的画面以及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动态连续画面[1]。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性质认定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斗鱼案”中,法官在判决中认为游戏直播画面不具有独创性和可复制性,否定了其可版权性③参见(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191号民事判决书。,在“奇迹 MU”一案中,法院将网络游戏画面认定为类电作品④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 529 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 73 民终 190号民事判决书。,在“梦幻西游”案中,二审法院明确提出随着产业技术的发展,对一些未采用摄制等拍摄手段创作完成的视听类作品,应当予以相应的保护,最终将网络游戏直播所形成的连续画面认定为类电作品⑤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终137号民事判决书。。理论研究中,也有学者提出应当通过法律解释的手段,将网络游戏整体画面纳入“电影作品”中保护,即网络游戏整体画面的本质特征是动态的连续画面,其表现效果和创作过程都与传统电影相似度很高,在满足作品独创性的要求的前提条件下,应将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纳入“电影作品”中保护[2]。
然而,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电影作品要以“摄制”的方法创作完成的情况下,目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将利用计算机技术制作而成的科幻电影、动画电影以及网络游戏连续画面定性为“电影作品”,也终究是通过法律解释的手段来解决作品定性不明的问题,这仍然存在着司法判决和成文法适用之间不相协调的冲突,其本质原因在于,我国著作权法对电影作品的规定不同于《伯尔尼公约》的规定以及大多数国家通行的立法规定。《伯尔尼公约》中规定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表现的作品”这一作品类型①参见《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1款,英文原文为“cinematographic works to which are assimilated works expressed by a process analogous to cinematography.”,是将作品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创作方法”作为判断是否构成电影作品的要件,此外,《伯尔尼公约指南》中也指出,公约特别使用“表现的”一词,而不是“获得的”,用以强调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的核心在于表现形式,而非创作方式[3]。美国《版权法》中规定“电影作品和视听作品”是指由一系列连续画面组成,需要借助装置播放的作品,其载体的性质如何在所不问②参见17 U.S.A§101.。日本《著作权法》明确采用了“表现方法”这一构成要件,规定只要能够“产生与电影的效果类似的视觉或者视听效果的方法表现并固定于一定介质上的作品”就应当被认定为电影作品③参见日本《著作权法》第2条的规定。。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中规定了“有声或者无声的电影和其他由一系列活动画面组成的作品,统称为视听作品”④参见《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ll2-2条第6项。。由此可见,美国、日本等多数国家并未以“摄制”这一创作方式作为电影作品的构成要件,而是突出了电影作品的“表现方式”这一构成要件。此外,德国《著作权法》第2条规定受保护的作品包括“以类似摄制电影方式制作的著作在内的电影著作”[4],尽管此处强调了“摄制”的创作方法,但是第95条单独规定了“活动图片”,将电影作品的权利准用于不能认定为电影作品的连续画面或者连续音像[4],从而对那些不是借助拍摄装置创作而成的视听类作品予以相应的保护。
反观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规定的“电影作品”,不同于《伯尔尼公约》中将“表现形式”作为构成要件,我国立法是将“创作方法”即“摄制”作为电影作品的构成要件。随着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时代出现了大量无需借助拍摄装置,通过计算机技术制作而成的新型视听类作品,诸如科幻电影、网络动漫以及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等,而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将“摄制”作为电影作品的构成要件,这一规定不当限缩了电影作品的内涵和外延,提高了电影作品的认定标准,不利于对网络时代新型视听类作品的保护。本次修法用“视听作品”取代了“电影作品”的做法,是对网络时代涌现的新型视听类作品的保护问题之回应,因此本次修法将“电影作品”改为“视听作品”,明确视听作品不再以“摄制”的创作方法作为认定标准,有利于对技术发展下的无需采用摄像技术创作而成的新型视听类作品之保护。
(二)固定性是视听作品的构成要件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电影作品要“摄制在一定介质上”,这就是电影作品的固定性要件,是指已将连续画面固定在某种物质载体上,且仅指已经固定的状态,而不是指能够被固定的可能性[5]。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实践中出现了“随录随播”的体育赛事现场直播形成的连续画面,其不同于传统电影作品被“摄制在一定介质上”,其相关侵权诉讼纠纷频发,法律定性也存在较大争论。例如在“凤凰网赛事转播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我国著作权法要求电影作品应已经被稳定地固定在有形载体上,而现场直播采用的是随摄随播的方式,因此整体比赛画面并未被稳定地固定在有形载体上,不满足电影作品固定的要求,认定现场直播所形成的连续画面构成录像制品⑤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终字第1818号民事判决书。。而再审法院认定体育赛事现场直播所形成的连续画面构成类电作品,并且在判决中提出,我国著作权法仅仅要求作品具备“可复制性”即可,并未规定“固定性”是作品的构成要件,故电影作品无需坚持固定性要件⑥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民再128号民事判决书。。因此,本次修订的《著作权法》用“视听作品”取代了“电影作品”,但是并未明确其定义,视听作品是否要满足“固定在一定介质上”的要求,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现场直播画面的法律定性。
在百雀羚产品线结构中,除了“天然不刺激”护肤绿之外,还有零售价4元的百雀羚凤凰甘油,以及个人护理系列花露水等非核心产品。同时男士系列也是刚性不足,削弱了百雀羚的品牌属性定位。引领百雀羚飞速发展的新生力量是草本系列,净化品牌旗下的产品也许是百雀羚下一步要做的工作。不可否认,基于现实销售规模等因素的影响,百雀羚目前仍没有淘汰与品牌属性定位不兼容的老品,未来产品线结构如何进一步优化提升,对于品牌操盘者是考验。
一方面,视听作品的“固定在一定介质上”构成要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关于电影作品的“固定性”,即“已在物质载体上固定”这一要件,早在1976年为修改《伯尔尼公约》而举办的斯德哥尔摩外交会议上,各国就对此展开了争论,并未达成一致,最终《伯尔尼公约》在第2条第2款中规定:“本同盟各成员国得通过国内立法规定所有作品或者任何特定种类的作品如果未以某种物质形式固定下来便不受保护。”①参见《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2款的规定,英文原文为“ It shall, however, be a matter for legislation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Union to prescribe that works in general or any specified categories of works shall not be protected unless they have been fixed in some material form”.可见《伯尔尼公约》将作品的固定性要件交由各成员国来自行规定。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作品要满足“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要求②参见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的规定。,而针对电影作品,则规定了要满足“摄制在一定介质上”这一要求③参见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的规定。,前者是对所有作品的的一般性规定,指的是作品要具备能够被复制的可能性,后者是对电影作品要满足“已固定”要件的特殊规定,这一设定完全符合《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并无不妥。因此,上文中提到了“凤凰网赛事转播案”再审法院以对一般作品所规定的“可复制性”要件来否定电影作品的“固定性”要件,存在逻辑上的错误。
另一方面,将“固定在一定介质上”作为视听作品的构成要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关固定性要件的争论主要存在于现场直播所形成的连续画面的法律定性问题上,传播技术的进步促进了“随录随播”的现场直播产业的发展,现场直播所形成的连续画面是否能够被认定为视听作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视听作品是否要坚持“固定性”要件。美国《版权法》则将“已固定”作为作品能够受到版权保护的前提条件④See 17 USC 102 (a).,与此同时,美国《版权法》将“随录随播”的现场直播视为符合“已固定”的要求,即“如果是在被传输的同时得以固定,则属于本法意义上的已固定”⑤See 17 USC 101.,这是因为美国《版权法》缺少对广播组织权的规定,同时由于美国《版权法》规定“已固定”是作品受到版权保护的前提,这就导致随录随播的“未固定”的广播无法作为版权法客体受到保护,为了对广播组织提供专门的保护,这是一种法律拟制[7]。
与美国不同,广播组织权是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的一种邻接权⑥参见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45条的规定。,对于“未固定”的现场直播所形成的连续画面,可以通过广播组织权对此进行保护。此外,本次修法之后,将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控制他人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修改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转播”,这实质上是将我国的广播组织权的内涵进行了扩张,广播组织可以规制他人未经许可通过互联网转播行为,倘若取消视听作品的“固定性”要件,那么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而“未固定”的现场直播所形成的连续画面则会被认定为视听作品加以保护,这将在无形中架空本次《著作权法》修改的重要成果之一,即扩张广播组织权的内涵[6]。由此,视听作品坚持“固定在一定介质上”这一构成要件,用广播组织权来保护“未固定”的现场直播连续画面,有利于我国著作权法体系的逻辑自洽,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综上,本文认为,本次修法下的“视听作品”要满足“固定在一定介质上”这一构成要件,这不仅是区分视听作品与戏剧作品的表演、美术作品的放映甚至是作品与非作品表演的客观活动之必要要求,也是与我国著作权法体系设置了广播组织权来保护未固定的现场直播画面这一立法现状相适应的选择。
(三)明确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的区分标准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录像制品这一邻接权客体,用以保护除电影作品之外的任何已固定在一定介质上的连续画面⑦参见我国《著作权实施条例》第5条第3项规定,录像制品是指“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形象、图像的录制品”。,在我国的电影作品+录像制品二分模式下,区分二者的标准是作品的独创性,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系由作者独立完成,体现了作者的智力创造与选择判断。而对于区分电影作品和录像制品的独创性标准,我国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尚无明确的量化标准,存在一定的争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历程中,曾经一度删除了录像制品,本次最终修订通过的版本则保留了录像制品这一邻接权客体,由此我国立法仍然坚持视听作品+录像制品的二分模式,这是由我国著作权法体系决定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国著作权法立法模式整体上更接近于大陆法系国家,在狭义著作权之外设置了邻接权,对独创性不足的邻接权客体提供相应的保护。网络时代涌现的新型视听类作品种类繁多,其独创性水平也良莠不齐,例如随着手机、相机等移动拍摄设备的普及,出现了一些记录生活或者自然风光的纪录型视频,这些长短不一的视频往往是他人随手拍摄而成,那么对于这类记录型视频,应与融合了作者智力创造的视听作品予以区分,将其认定为录像制品进行保护,这有利于我国著作权法体系的整体协调。作品类型名称的修改,并不当然地降低视听作品独创性的门槛,判断网络时代的短视频、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等新型视听类作品的法律定性,要基于独创性标准,对那些独创性较低的连续画面,应当认定为录像制品,从而避免本次修法语境下视听作品内涵的无限度扩张与著作权的滥用。
在我国视听作品+录像制品二分模式下,区分二者的标准是“独创性”,关于这一标准,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论。以“凤凰网赛事转播案”的判决意见为例,二审法院认为要从独创性的高低来区分电影作品和录像制品,虽然体育赛事现场直播所形成的连续画面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是并未达到电影作品的独创性高度,将其认定为录像制品①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终字第 1818 号民事判决书。,而再审法院认为电影作品与录像制品的划分标准应为独创性之有无,而非独创性之高低,因此将体育赛事现场直播画面认定为电影作品②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民再128号民事判决书。。再审法院认为邻接权不涉及权利人任何对作品表达层面的个性选择和安排,因此由于涉案体育赛事现场直播画面具备一定程度上的智力创造与选择安排,则应当被认定为类电作品。本文认为,暂不去思考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是否具备独创性,再审法院将独创性的“有无”作为区分电影作品与录像制品的判断标准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未能明确认识到我国著作权法制度下所讨论的独创性的“有无”,仅仅是一种对程度的描述,也就是独创性的“高低”来界定的[6]。
我国著作权法采用著作权-邻接权立法体系,这不同于版权体系国家将作品视为一种财产,版权制度的创设是为了促进作品的流通和利用,更好地实现作品的经济价值,而著作权-邻接权体系国家对作品的独创性标准相对较高,认为只有反映作者个性、体现一定高度的智力创造水平的成果才能满足作品的独创性要件。诸如录像制品和表演活动,虽然其独创性未达到构成作品的标准,但是为了保护其传播者的利益,大陆法系国家在著作权法中设置了一种邻接权。而版权体系国家则不同,例如美国《版权法》就将所有已经固定的需要借助一定装置播放的连续画面作为一类“电影作品及其他视听作品(motion pictures and other audiovisual works)”进行保护③参见17 U.S.A§101、102.,英国《版权法》将所有能够产生影像效果的录制品认定为电影作品进行保护④参见英国《版权法》第5条的规定。。因此,在我国的视听作品+录像制品二分模式立法下被认定为邻接权客体的同一段影视作品之外的已固定连续画面,在美国和英国则会被认定为作品予以保护,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某些体现了个性化选择的表达应当被认定为著作权客体还是邻接权客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因此,对于我国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的区分标准而言,不能认为将该独创性标准认定为是有和无的区别,而是独创性程度高低的区别。
三、视听作品的权利归属规则分析
2020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对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作出了相应的修改,将视听作品划分为“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与“其他视听作品”,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权利归属规则,这一规定从我国著作权法体系上来看,存在一定的适用问题,下文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一)对视听作品权利归属进行分类规定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电影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电影作品中的“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且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①参见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15条的规定。。2020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17条对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则进行了分类规定,将视听作品划分为“电影作品和电视剧作品”和“其他视听作品”,分别确立两类视听作品的著作权权属规则。“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作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这并未在实质上改变现行《著作权法》中“电影作品”的权属规则。但是,“其他视听作品”的权利归属则“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制作者享有,但作者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这一规定使得区分“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和“其他视听作品”成为必要,对于视听作品的权属认定与利益分配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新法并未对“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与“其他视听作品”的定义与区分标准作出相应的规定,这就使得诸如微电影、网络电影、网络电视剧以及长视频和短视频等视听类作品能否适用新法第17条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规则,成了需要思考的问题。根据我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的相关规定,电影是“运用视听技术和艺术手段摄制、以胶片或者数字载体记录、由表达一定内容的有声或者无声的连续画面组成、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用于电影院等固定放映场所或者流动放映设备公开放映的作品”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第2条的规定。。同时根据该法第20条“未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的电影,不得发行、放映,不得通过互联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网络进行传播,不得制作为音像制品”的要求可见,《电影产业促进法》项下的“电影”,并未将不需要取得公映许可证的网络电影涵盖在内。关于电视剧的定义,也仅见于广播电视总局历次发布的电视剧制作、内容管理相关规定中,这些规则仅适用于在电视台发行的剧目,而对于仅在网络发行的剧目,并无法律规定明确构成电视剧。
对此,本文认为,一方面,新修订的《著作权法》项下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不应仅仅从发布平台以及行政管理标准角度来对其进行内涵的限缩,行政管理的标准与作品类型的区分标准并不能完全等同[6],凝聚了制作团队的创作成果的网络电影、网络电视剧也应当被认定为本次修法中第17条规定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从而进行合理的权属认定;另一方面,随着拍摄设备和视频制作软件的普及而涌现出的各类自制长视频、短视频,例如微电影、品牌方自制的创意广告视频、网络红人的美食视频以及一些情景类短视频等,从表现方式、制作水准上来看,与传统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并无实质性差异,如若将其纳入“其他视听作品”而与“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适用不同的著作权归属规则,并不合理。
(二)引入当事人约定优先的权属规则
2020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17条对“除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之外的其他视听作品”规定著作权“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制作者享有,但作者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这一规定创新性地将“当事人约定优先”原则引入视听作品的权属规则中,这一规定在法律适用中将会带来一定的问题。此处需要明确的是,本次修法将电影作品的“制片者”修改为视听作品的“制作者”,这一术语的变化并未对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主体产生实质性变动,制作者的含义应当是“组织制作并承担责任的法律主体”。
一方面,相比于新法第17条规定的“其他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约定优先,无约定时归制作者”,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委托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则是“约定优先,无约定时归受托人”。那么存在一种情况即组织制作并承担责任的视听作品制作者委托他人创作,在无合同约定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的情况下,适用第17条与第19条的规定认定著作权归属,将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这就产生了不同权属规则之间的冲突。因此,本文建议在未来的立法解释中对这一问题作出说明,或者在未来司法实践中发生此类视听作品著作权纠纷时,由法院为了第14条的规定有意义而优先适用该规定[7]。
另一方面,我国新法中对于“其他视听作品”的权利归属规定,实质上不利于“其他视听作品”的传播与发展。电影作品被视为“特殊的合作作品”,尽管合作作者众多,但是为了促进电影作品的传播与利用,各国普遍做法是将电影作品的著作权直接赋予制片者,意味着当电影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被使用时,他人只需要获得制片者的许可,就可以稳定地获得授权,从而简化了授权流程,并且有利于保证交易安全,至于电影作品中的编剧、导演、摄影等合作作者,则享有署名权,其相关经济利益完全可以通过与制片者签订合同进行内部解决,这种立法模式有利益维护电影市场交易机制的稳定性,促进电影作品的传播。而视听作品与电影作品相同的是,通常是在制作者的组织与负责下,由创作团队共同进行创作。本次修法对“其他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规定为“当事人约定优先,无约定则归制作者”,这容易导致第三人对其他视听作品产生著作权归属不明的问题,降低作品在传播发展中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从而不利于其他视听作品的传播与发展。本文认为,在本条的法律适用中,其他视听作品的著作权法定归属于制作者,而基于民事交易的意思表示自治原则,当事人之间对于著作权权属作出的约定应当有效,但是为了保证交易安全以及促进该类视听作品的传播与发展,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并不能够对抗善意第三人。
四、结语
2020年我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对“视听作品”的定义和权利归属问题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仅仅用“视听作品”取代现行法中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并未解决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相关争论。随着网络时代科技的发展,涌现出来的大量新型视听类作品应当得到合理的保护,“视听作品”的内涵决定了其保护的外延,视听作品不应以“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为构成要件,从而顺应网络时代下技术发展的潮流,对网络动画、网络游戏整体画面给予充分的保护;同时,视听作品需要满足“固定在一定介质上”这一构成要件,坚持从独创性高低标准去区分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合理限定视听作品外延,避免著作权的滥用。新法中对视听作品进行了分类规定权利归属规则,对“除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之外的其他视听作品”规定的权属规则与委托作品的权属规则存在适用上的冲突,并且“当事人约定优先,无约定则归制作者”的规定不利于其他视听作品的传播与发展。为了保证该类视听作品的交易安全,促进其传播与发展,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应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促进我国2020年新修订《著作权法》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更好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