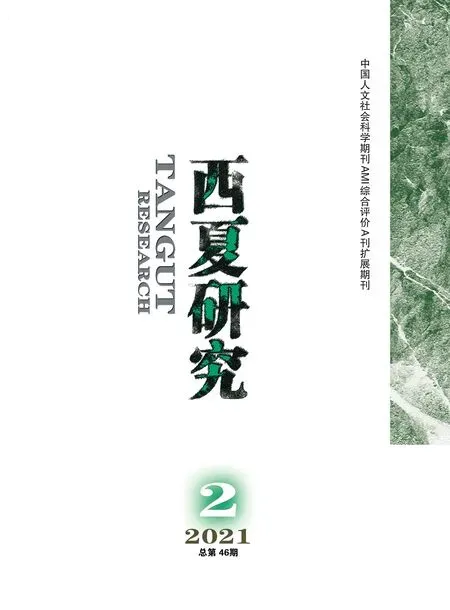宋代官员久任问题考论
□孙世达
所谓官员久任,指官员在同一职位或一个地方承担职事长达六年以上①,由于宋代官多阙少,久任也成为对某个岗位官员政绩突出的一种奖励。宋代官员久任问题是宋代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当时面临固定任期制度难以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时,朝堂上下所做出的一种解决对策。回顾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学界专家对宋代官员管理制度已有较为全面的研究。而就宋代官员久任问题,学界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现有的学术成果多是在论述官员考课制度、磨勘制度和官员任期制度时略有涉及②。因此,本文拟对宋代官员久任问题进行专门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宋代官员久任问题的历史渊源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古代官僚政治体系,官员始终是政府机器运转的基本部件,官员的任期时限不可避免地成为官员管理制度中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早在两汉时期,官员在同一职位或相同地方长期承担职事的现象相当普遍,官员“未尝不久其任也”[1]487。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员久任颇多:萧何任相十三年,“黄霸为颍川八年,张敞为京兆九岁”[2]488。而这一时期,官职大多没有明确的任期规定,官员的任期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在任官员的任期多以久任为原则。
两晋以降至隋代,随着帝国官僚政治体系渐趋严密,形成了明确的官员任期制度,即文武长官任期为四年,佐官则为三年③。至此,两汉以来的官员长期任职原则被完全打破。下及唐代,官员迁转频繁,实际任期大为缩短,“倏来忽往,蓬转萍流,近则累月仍迁,远则逾年必徙”[3]1417。中央为了加强集权的需要,严格防范官员长期在地方担任职务,官员久任的现象大量减少,官员久任原则逐渐成为任期制度的补充。
至唐朝开元年间(713—741),“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4]6889,玄宗大力整饬吏治,掌兵之官久任边地,虽然有“久任以责其成功”[5]2的功效,但却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祸根。唐政府为尽快消弭战乱,采取了姑息的政策,致使最终在地方上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而在数量众多的藩镇中,无论是在离心力强大的河朔三镇,还是听命于朝廷的东南财源型藩镇,都出现了许多节度使及其僚佐官员久任的现象。如:李宝臣任成德节度使十八年,刘总任幽州节度使十一年,皇甫政任浙东节度使十年等[6]191,197,295。接之的五代时期,五个朝代如“走马灯”般更迭频繁,不仅在中央难以建立起切实有效的官员任期制度,而且由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减弱,官员的实际任期极不固定。
宋初承袭五代之制,宋太祖、宋太宗为了不让宋朝重蹈覆辙,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7]3070,通过推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使“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8]269,宋代官员“三年一任”的任期制度开始逐步普遍推行。但由于建国不久,国家的管理体制特别是官员的任期制度还未成熟。虽于太祖开宝五年(972)颁布了诏令:“自今委任所司点检到官月日,才及三周年,便于除替。”[9]606同时由于统一战争的需要,边将帅守仍大多久任,“郭进控西山,何继筠领棣州前后二十年。……姚内斌在庆州、王彦升在原州,皆十余年不易其任”[10]598。与此相对,朝中大臣、各类官员久任也屡见不鲜,赵普任相十一年[11]8931,刘温叟任御史中丞十二年,“魏丕典作坊十余年”[12]268,刘蟠任发运使十四年[11]9389。此后,整个宋代都没有对中央官员的任期做出明确规定,特别是宰相、执政、侍从等重要中央官员,他们的任职年限长短往往由皇帝的旨意和特定政治环境所决定,对于这些官员久任现象,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地方官员普遍规定“以满三年为任期,满即除代”[12]559,尽管不同皇帝在位时期,对地方官员的任期做出过若干改动,制度上大体上仍是以三年为一任④。
但是制度逻辑往往会与社会现实出现不协调。自宋代中期产生的冗官问题长期存在,员多阙少的矛盾日益尖锐,铨司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待阙”人数,便酌情缩短在任官员的任职期限,加速官员队伍的流转速率,以使待阙人员可以尽快入职赴任。然而,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非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冗官问题,反而使“官守屡易,至有岁内再三改移。时序未更,已闻移去,觊望进擢,日俟迁升,决词讼则鲜肯究心,视公局则犹同传舍”[13]60之23。官员频易,人心浮动,奔竞之风盛行;吏治败坏,朝野上下纷纷呼吁“久任以责成功”[13]60之34。在此情况下,“久任以责成功”成为宋朝各级官员岗位上推行久任的重要原因和时代背景。
二、宋代久任官员职任主要类型
宋朝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任期大体上为三年一任,任满改易他处或寄居待阙成为官场主流。但也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官员久任现象,细加梳理,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财计之臣
众所周知,国家财政是任何政权组织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宋朝相当重视财政,自开国起便以“制其钱谷”[12]49为纲领,着手将地方财权收归中央,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财政运作体制。此外,所谓“财计者,国之气血也”[14]180,宋朝同样注重对负责有关财计的官员的委任与管理。
“财计之臣”包括上至中央三司、户部、太府寺、司农寺等机构长官,下至地方发运使、转运使副以及主管茶盐、坑冶等各类监当官(南宋时期还有总领所的长官)。他们与其他专管一般行政事务的官员相比,往往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长远规划和通盘考虑,因此,财计之臣如果频繁调动,任期过短,将会严重地妨碍财政管理的正常运作。仁宗景祐元年(1034)曾颁布诏令:“自今三司使副,在职未久,毋得非次更易。”[9]612哲宗即位后,文彦博针对财计之臣不久其任的问题上言道:“今之户部,实主邦计。尚书、侍郎、郎中、员外,未闻精选之任,唯见屡迁数易,欲使何人专任其责,国之大计安所望哉?”[12]9003至南宋依然十分关注这一问题,章如愚在论及“今之乏财之患”时言:
今之尚书版曹,所以总财货之权,其次则有司农,有常平,有转运,有坑冶,往往朝而处之、暮而易之,未有能通知其本末之所在者。……此其患在于士大夫以财赋之职为假途也。[15]741
文献增长规律的研究,一般以文献累积数据为依据[1],根据美国科学史学家普赖斯所涉及的理论[2],我们将创业研究近60年发表的文献各年分布和累积情况绘制如图1所示。由图可见,近60年创业研究发文呈一条平滑的上扬曲线,与指数增长规律高度吻合,拟合方程为y = 6.749e0.116x,说明创业研究还处于知识积累阶段。普赖斯按文献量增长变化情况将科学文献增长划分为四个阶段判断,创业研究发文目前正处于发展时期。
总之,宋代统治者为了克服财务管理中的“朝处而暮易”现象,尽可能的对于“干实之士,明于财计者”往往“使居钱谷之官,久于任使,毋亟迁徙”[16]1428。相应的,出现一批久于其任的财计官员:太宗时期,“以吏干闻”,善于理财的陈恕在任三司(盐铁)使期间,整顿税赋,改革茶法,使国家财政收入显著增加,深得太宗的器重,还曾获得太宗亲自在殿柱上题写“真盐铁陈恕”的殊荣,任职约十年之久[11]9199;孝宗淳熙年间,萧翥在户部“为贰为长凡八年”[13]60之40;而在地方上,仁宗朝,许元在江淮荆浙发运司任职十三年[17]3236;高宗朝,赵彬任陕西转运使九年[11]490;孝宗朝,赵汝谊任淮西总领八年[13]60之40;等等,通过“择通晚之人久其任”来达到“责之理财之实”的效果[13]60之23。
(二)监司帅臣
所谓“监司帅臣”,用以指代路分中的四司长贰,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由中央委任,是中央与地方相连接的关键节点,同时作为一路之长,具有财政管理、司法审判、维护地方治安、监察所部官吏等一系列职能,他们任期长短影响着下属州县的吏治民瘼。宋真宗时期,监司帅臣任期逐步缩短的趋势就已显露端倪,此后,臣僚们面对这种情况便纷纷上言献策。元祐六年(1091),刑部侍郎王觌上奏哲宗的札子最为直切要害,现兹摘列如下:
臣伏见诸路监司移易频数,坐席未暖已或有欲去之心。职事不安,岂能为经久之计。夫官不宿业古今之通患也。今虽员多阙少久任稍难,然中外官司犹颇有三年之法,至于监司岂可以责之速效,而转徙频数,比他官特甚。大率一路之间,郡县百数,巡历经年,未能周遍官吏之能否,民间之利病,非熟见而详察之未易得其实也,或数月而易,或期年而罢,则虽有高才远虑,何暇施为?甚者习为因循苛简以幸替去,弊事无所革,汙(污)吏不知畏长久之策,置而不问。故转运使财用日耗,提刑司、常平坊场之政浸以隳坏,此不可以不恤也。臣伏望朝廷立监司久任之法,明诏诸路监司以久任之意,使才高虑远者有所施为,因循苟简者知其无以逃责,则各思自竭而职事举矣。[18]803
他指出了监司长官任期长短与现实治绩之间的利害关系。一方面,由于员阙矛盾的日益尖锐,监司帅臣有“移易频数”的趋势;另一方面,在统治者的倡导和百官的呼吁之下,也出现了不少久任的官员。比如:真宗朝,宋搏任河东转运使期间“屡以秩满请代”,但朝廷认为其“善于其职”,以至“十一年不除代者”[19]1850;神宗时,鲜于侁兼领任利州路提举常平,体察民情,切实议定免役钱,任职达九年之久[11]10937;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至理宗宝庆二年(1226),汪纲任浙东提刑期间政绩斐然,久任达七年[20]7113;还有太祖时期,张铎任泾原安抚使十七年[11]9048;等等。因为往往“监司总一路,其风俗之厚,薄吏胥之欺诈,簿书讼狱之繁伙,非一朝一夕所能省察也”[21]85,只有长期在一路承担职任,“监司帅臣”才能切实地体察民情,整饬州县吏治。
(三)基层(州县)亲民官
亲民官,又称父母官,即治理百姓的地方官,“理治百姓,监镇知寨亦然”[22]46,包括知州、通判、知县、监镇、知寨等的各类地方官员。“百里之长,字民之要官也。”[12]488临民之官的任职时限不仅直接关乎着民生福祉,而且事关古代国家统治根基的稳固与否,当亲民官在地方上政绩卓越,考课优异时,朝廷往往会给予嘉奖,并延长他们的任职时间。仁宗在嘉祐六年(1061)的诏书中,就明确指出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诏曰:
朕观古者欲治之世,牧民之吏多称其官,百姓得安其业……岂今人材独少而世变之殊哉,殆以不得久其官故也。盖智能才力之士,虽有兴利除害、禁奸勤善之意,非稍假以岁月,则其吏民亦且媮而不为之用……今夫州县恃以为命者,守、令也。察其能者,使得久于其官,而褒厚以劝之,岂非所谓先务者哉![13]60之20
州县亲民官群体基数庞大,是宋代久任官员群体的主体。整个宋代,亲民官员久任的例子数见不鲜:开宝二年(969)至太平兴国三年(978)期间,焦继勋自接替向拱任河南府尹后 ,任职达九年之久[11]9043;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林迪任龙溪县知县期间“平易近县民”,深得民心,任职共九年[23]699;袁韶在嘉定十三年(1220)到绍定元年(1228)期间,“为临安府尹,几十年,理讼精简,道不拾遗,里巷争呼为‘佛子’,平反冤狱甚多”[11]12451;此外,蒋元振知白州十八年[11]3758;赵葵知扬州八年[11]12500;林葆光知丽水县六年[23]517;等等,都是遵循“守令之于郡邑,久任则可以立事”[24]601的原则。
三、宋代官员获得久任的方式与待遇
综观宋代久任官员的职任类型,无论是财计之臣,还是监司帅臣,抑或是州县亲民官,他们都占据着官僚政治体系中的关键位置,宋朝为了防止官员培植个人势力以危及统治,十分重视对这些官员的管理。特别是在“一年一考,三年一任”的定期轮任制度建立之后,官员任满后需要移仕迁转或寄居待阙,朝廷会根据其任内治绩功过的考课结果来予与升黜。在待阙期间官员的个人收入会受到严重损害,而久任则成为一种变相奖励。官员若要突破常规的定期轮任制度获得久任,除直接获得皇帝的信赖诏令除授之外,往往还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长官保举
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就会如脱缰的野马践踏一切。宋代以“事为之防,曲为之制”[12]382为祖宗家法,“凡要切差遣,无大小尽用保举之法”[25]1623。久任官员大多身居要职,并且在同一职位或一个地方长久任职,这便极其容易引起统治者的关注与怀疑。对于有专业技术水平要求,又需要官员长时段任事的职位,既要求官员在任期间有卓越的政绩,又要确保人选的可靠性。因此,长官荐举保任制度,便成为许多官员久任的方式之一。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诏曰:
官员要想获得久任,需要上级连书同罪保举再任。神宗熙宁四年(1071),同勾当汴口李宗善因为“明晓水事,治河得力”,得到都水监长官的荐举保任,在汴口任职达十二年之久[13]60之21。知归信、容城县宋彦图任职期间“在任无引惹”,“巡防不失事体”,元丰六年(1083)时,赢得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知雄州刘舜卿以及给事中韩忠彦的认可,二人以“彦图材武晓边事”,向皇帝保举再任,宋彦图由此获得了久任[13]60之22。此外,还有孝宗隆兴二年(1164),横州通判贾成之因广西转运提刑司奏举其“佐郡有方、为政不优”,最终获得皇帝的久任特诏[13]60之33。
(二)百姓举留
举留,又称乞留,官员在任满当迁之时,如果在任为政清廉,深受百姓爱戴,民众可以向该官上级或中央表达诉求,以使其留职久任。举留制度不仅是沟通民意舆情与朝廷官府的桥梁,又成为政绩优异官员获得久任的另一种方式。太宗时期,江东人蒋元振家境清苦,听闻岭南地区物价较低,便主动申请去白州做知州,在任期间“为政清简,民甚便之”,深受百姓的爱戴,在其秩满当迁时,“众辄诣部使乞留”[11]3758,由此蒋元振知白州长达十八年。除此之外,淮南转运使刘蟠任上“岁漕江东米四百万斛以给京师,颇为称职”,有效解决了京师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同时得到“部内僧道乞留”,最终久任淮南转运使达八年[11]9388。南渡初年,江安止知丽水县“抚安善良,严于治盗,邻郡寇至,率丁壮御之,寇退却,境赖以无虞”,秩满时“民愿留再任”,“在邑凡六年,代还之日,吏民泣送出境”[23]517。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有时并非民众自愿,有的官员或地方豪强特意在背后鼓动,故而宋朝政府对此多持有警惕,有些人甚至因此而弄巧成拙。
(三)自举留任
所谓自举留任,即官员将个人在任内的功绩表现汇报给上级,以申请在现任职位上继续承担职务。自举留任是长官保举与百姓举留之外,宋代官员获取长久任职的又一种方式。但与前二者相比,自举留任的久任方式并未得到宋代朝野上下的认同与提倡。如绍兴二年(1132)九月,知泰州张荣通过“自陈任内安集之功”来表达自己的久任意愿,朝廷“从其请”诏知其再任[13]60之27。随后不久,臣僚便纷纷上言“近士大夫贪冒苟得,巧图再任,帅臣、监司率任私意以应请求,讼诉交兴,风欲败坏,乞行禁止”[13]60之27。十月时,宋高宗为此特意下诏“今后除监司、沿边守臣外,余不许再任。仍令御史台觉察弹奏”[13]60之27。从中不难看出,虽然有一部分官员以自举留任方式最终成功久任,但这种方式完全可以看作是官员个人行为,是没有得到宋代政府给予制度保障的,同时也是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群体重义轻利、不居功自恃的为官理念相背离的。
此外,关于宋代久任官员待遇问题,同样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宋朝对于官僚士大夫的优待历来被世人所称道,单就从久任官员所获取的待遇上便可见一斑。一方面,宋代官僚群体日益庞大,员阙矛盾十分尖锐,令才干精敏、政绩突出的官员长久任职,直接使他们免受“待阙”的困扰,就此来说久任本身就是对官员的一种特别优待;另一方面,宋代丛脞芜杂的职官制度,官、职、差遣相分离的制度设置,却也使得宋代官员的人事管理变得更加灵活且富有弹性。皇帝可以运用多种手段来对久任官员以示恩宠,使其可以感受到皇恩之浩荡。具体看来,久任官员可以获得以下几种待遇。
1.稳定的俸禄收入。随着宋代员阙矛盾日益尖锐,“员多阙少,至有候一年以上方得差遣,既得差遣,待阙须近三年”,而在待阙期间,幕职州县官是没有俸禄收入的,京朝官所支领的俸禄也不高,以至于官员发出“居闲之日多,而禄仕之少”的感叹[12]9237。久任官员群体再任三年或六年以上,意味着可以稳定地获得相应的岗位俸禄收入,同时还有各种名目津贴和补贴。
2.褒奖与赏赐。褒奖和赏赐历来被视为古代帝王统御术中最基础的手段,皇帝通过下达褒奖诏书和赏赐财物的方式,对久任官员给予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奖励,既有利于培养官员的忠诚感,又可以促使官员治绩的保持与提升,达到“赏一人而千万人劝”[16]1235的效果。宋代皇帝多深谙此道,对久任官员往往不吝奖赏。如上文曾提及的蒋元振知白州期间为官清廉,宋太宗得知实情后,便对其进行下诏褒谕,并赏赐绢三十匹、米五十石,使蒋元振可以安心久任[12]706。
3.转官增秩与关升资序。宋代官制十分复杂,久任官员转官增秩不仅包含着官员职事官(即差遣)的升迁,而且还蕴含着寄禄官(即阶官)的提高。除此之外,宋代关于官职的除授还有特定的次序规定。以仁宗时期许元的做官经历为例:许元在淮南任官十三年,有效缓解了京师粮食的供应,得到了仁宗皇帝的信赖与久任奖赏,在这期间许元由发运判官,历发运副使,至发运使,职事官得到了升迁。同时,许元的寄禄官历经主客员外郎、金部员外郎、侍御史、刑部员外郎,终至工部郎中,与之相应的,其俸禄也不断增加。久任官员的待遇还会在关升资序上得到体现,如嘉祐三年(1058)诏“淮南等路都大发运使孙长卿令久任,将来如迁改,并依三司副使例”[13]60之20。
4.赐出身。宋代自开国以来便推行右文政策,通过科举考试逐渐成为做官的正途,官员进士出身的有无直接与其可差注的官职相连接,并且在官制设置上有出身官员意味着驶入“快车道”,迁转速度上会有大幅提高。因此,赐出身就成为了皇帝的奖励和慰劳久任官员的一种赏赐名器。皇祐二年(1050),“赐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金部员外郎许元进士出身。上尝谓执政曰:‘发运使总领六路八十八州军之广,其财货调用,币帛谷粟,岁千百万,宜得其人而久任之。今许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奖励以尽其才。’故特有是赐”[12]4064。
5.除馆阁。馆阁职最初多以文学之士应选,但随后便逐渐名衔化,与遥领相对,馆阁职成为表示文臣身份性质的荣誉头衔。除授职事修举的官员以馆阁职,成为久任官员特殊待遇的又一种体现。如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诏:“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河阳王序职事修举,治郡有方,除徽猷阁待制,令再任。”[13]60之25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诏:“显谟阁直学士、知镇江府张子颜除龙图阁直学士,令再任。”[13]60之37光宗绍熙元年(1190)诏:“直显谟阁、权发遣泸州王卿月除直龙图阁,令再任。”[13]60之38
四、宋代官员久任举措的作用和影响
无论多么精意覃思设计过的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都无法与实际完全契合,制度设计往往面临着难以落地的挑战,宋代官员的任期制度同样如此。官员如果任期过长,容易阿党比周、败坏吏治,甚者在地方形成割据势力,危及国家安全与稳定;反之,任期过短,则易使官员因循苟且,奔竞之风盛行,无心政事。宋代大体上实行三年一任的官员任期制度,是经过朝野上下深思熟虑地考量过的。宋高宗曾对官员一任三年的原因有过解释,“以三年为任,尤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规矩,三年则务收人情,以为去计”[16]1672。但是官员“乐于数迁而厌于久滞”[13]60之40的确是人之常情,再加上宋代冗官问题与员阙矛盾的长期存在,致使官员任期制度在施行的过程中遭遇严重的破坏,形成“内外之官,更易频数,政不修举,以至送往迎来,吏卒疲困,州郡借请,縻费帑廪,寝长奔竞,全隳靖共”[13]60之23的局面。宋代官员久任措施便在这种社会现实之下应运而生,它作为官员任期制度和迁转制度的补充和衍生物,产生了一系列积极作用和影响。
(一)有利于贯彻循名责实原则,促使官员职事修举
宋代官员队伍十分庞杂,官员能力素质良莠不齐,需要朝廷以“循名责实”为原则,“就其所长而用之”[12]4752。但是宋代官员选注和管理的实际过程中,却是“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又转而使之典狱,又转而使之治礼”[26]362,专业人才无法在特定的职位上施展才华。宋代官员在主体上仍是遵循“岁月叙迁”的方式原则,就算是特定的职位匹配到合适的人员,官员也会由于任期太短而治绩不显。官员久任制度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就会缓解这种状况。“文辞之士置之馆阁,晓钱谷者为三司判官,晓刑狱者为开封府推、判官”,为官择人,根据职任类型挑选特定的人才,“知礼者不必知乐,知乐者不必知刑”,不去苛求官员都是“通才”,“若得其人,不当数易,久任以责成功”[13]60之34,不拘泥于固定的任职期限,使官员摆脱任期的束缚,在较长时段里尽心政务,减少官员因循苟且、荒废政事的现象,使“有兴利除害、禁奸勤善之意”[13]60之20的官员,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来熟悉政务,促进官员职事修举。
(二)有利于上下之情相谙
一方面,官员“苟数迁,数易则人无固志,事多苟且”[27]1975,延长官员的任期时限,有利于中央与地方行政官员之间相互谙熟,保证政令的传达与畅通;另一方面,在日常政务行政系统中,宋代“吏强官弱”的问题严重,“外而州县,固已不胜其弊矣;内而百司,抑又甚焉”,主要是因为“居官者迁徙不拘岁月,而为吏者传袭及于子孙”[13]60之39,面对错综复杂的工作环境与烦琐冗杂的公务案牍,“虽有勤恪之人,宣力公家。于人情稍通,纲条稍举,已舍而他去。后来者或未能尽识吏人之面,知职业之所主,则又迁矣”,官员频易,致使“胥吏得以囊橐为奸,贿赂公行。”[16]2925相反,如果“官宿其业”,官与吏上下间相互熟悉,胥吏就会有所畏惮,“而无奸欺之虞”,久任官员也就能够“戢吏奸”,整饬吏治[13]60之39。百姓知其官员久任,就会安分守己,服从命令,“久任则人心信,服风化遂行”[13]60之24。此外,还有利于长久地贯彻政令,防止出现“更代之际意向或有不同,施设未免相反”[28]486的情况。
(三)有利于避免往来迎送,缓解民困
官员更迭频繁,官不久任,使地方上送往迎来的财政开支,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正常生活“,近者一二大郡,未一岁间至三数易,迎新送故,财计为之不支”[13]60之37。绍兴年间(1131—1162)“见一偏郡守臣迎送之卒,借请颇多,是时,米价踊贵,计其所入,计其所费,及八千缗”。就一偏僻之地耗费竟如此之大,以至于时人感慨:“呜呼!此中民几家之赋耶!夫以一偏郡守臣迎送之费,不赀如此,议臣但言财用不足,巧为色目,重敛于民。”[29]42此外,频繁的迎来送往,也给吏卒提供了上下其手、贪污腐败的机会,“至于嗜进之吏,耗公帑以事交结,又不在数中”[30]504。这样的公务迎送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是导致州县日益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从根本上切实地推行官员久任制度,使官员久于其任,才能有效地避免不必要的迎来送往,做到为官从政,纾缓民困。
当然,制度具有两面性,我们需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辩证地来看待,不可一味地对其进行褒扬和吹捧,同样应该关注到宋代官员久任制度的实际运行中所存在着的制度“漏洞”。宋代冗官问题严重,官员待阙时间逐渐延长,在这种政治大环境之下,催生出了一批钻久任规则“空子”的官员,他们虽然实际治绩平庸,甚至暴虐一方、残害百姓,却为了减少待阙时间,贪冒苟得,巧取久任。例如,宋仁宗时期,王逵在荆湖南路转运使期间苛征暴敛,“非理配率人户钱物上供,以图进用”,当地百姓深受其害,“苦于诛杀”[12]3872,但王逵却为突显政绩,便胁迫“荆南府进士、僧道、公人、百姓刘宗正等百余人,诣阙进状”举留自己,获取久任[31]863。此外,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监察御史胡舜陟又言:“政和以来,吏员繁冗,阙次难得,有援助者既得佳阙,到任未几,必求再任其甚有至三任、四任而不更者。……如知怀州霍安国、知密州郭奉世并再任。安国去秋方到任,治效未闻;奉世虽到任期月,亦无政绩。”[13]60之27官员们“巧图再任”,“帅臣、监司率任私意以应请求”,使得“讼诉交兴,风欲败坏”,而这种局面的出现,严重背离了朝廷推行久任制度的初衷[13]60之37。
五、结 语
总之,官员久任问题从属于官员管理制度的范畴,作为任期制度在实际执行中无法应对复杂的官场环境时的衍生品而存在。两汉时期,官员的任期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在任官员的任期多以久任为原则。随着帝国官僚政治体系渐趋严密,两晋时官员任期制度开始确立。自隋唐以后,任期制度处于不断尝试和调整的变动期,直至宋初才正式确定一年一考、三年一任的任期制度。但随着宋朝官僚群体日益庞大,员多阙少矛盾尖锐,任期逐渐缩短,人多奔竞之风,官员久任便成为了朝堂上下所做出的一种解决对策。
久任官群体主要包括财计之臣、监司帅守、州县亲民官等,他们除直接赢得皇帝的信赖诏命除授之外,还会通过长官保举、百姓举留、自举留任三种方式来获取久任,在久任期间,可以得到丰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这一制度的推行,一方面有助于贯彻循名责实原则,促使官员职事修举,也有利于避免往来迎送,上下之情相谙,缓解民困;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官员正常的迁转,特别是当考课不严时,易使官员贪冒苟得,巧取久任,危害一方。
归根结底,在宋代这个以皇权为整个政治体制运作的中心,中央对地方权力渗透力度加深,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细密化发展的特定时代里,处于权力顶端的皇帝,不可能不去顾忌这样的一个潜在威胁:分布在官僚政治体制内部的各式各类官员长时期地久于其任,是否会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导致代表皇权的诏书政令在层层下行过程中的威信力和执行力下降,甚者,情节严重时是否还会动摇自己统治的根基。因此,在权衡之下,官员久任制度绝不会被允许完全替代官员任期制度的作用,甚至只能附着在任期制度之上,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也是我们对宋代官员久任问题作出符合历史现实的相对公允评价的前提与基础。
注释:
①关于宋代官员久任问题,时人早已有关注,但对于官员在某一职位或一个地方长期承担职事多长时间才可视为久任,宋人似乎并未有确切的说法。展龙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官员久任是指官员在同一职位长期任职(六或九年以上),甚至直到死而后已。”(展龙《明代官员久任法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39页。)此外,考虑到宋代官员任期大体上为三年一任,笔者认为若以六年为限,超过两任即可视为久任的划分标准,似乎可以较为接近宋人在此问题上的认识。
②综合来看,关于宋代官员管理制度的主干已经清晰明确,但宋代官员久任问题还未得到充分的研究,邓小南先生的《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书中,对宋代的官、职的差遣、铨选、考课、磨勘等制度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论述;苗书梅在《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更为系统地将宋代官员的选任方式、除授制度、任官原则、官员管理分别论述,其中第三章的第二节定期轮任制度对地方官员任期制度所做出的议论对本文极有启发。此外,有关宋代官员任期制的文章都对久任官员略有涉笔,如倪士毅的《宋代宰相出身和任期的研究》(《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苗书梅的《宋代地方官任期制初论》(《中州学刊》1991年第5期)、邢琳的《宋代知县、县令的任期》(《中州今古》2000年第3期)、王瑞的《北宋地方官员任期制度研究——以知州、知府为重点》(《赤峰学院学报》2010年1月)等。
③详见王东洋《魏晋迄隋官员任期探讨》,《兰州学刊》2007年第2期,第161-164页
④详见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4-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