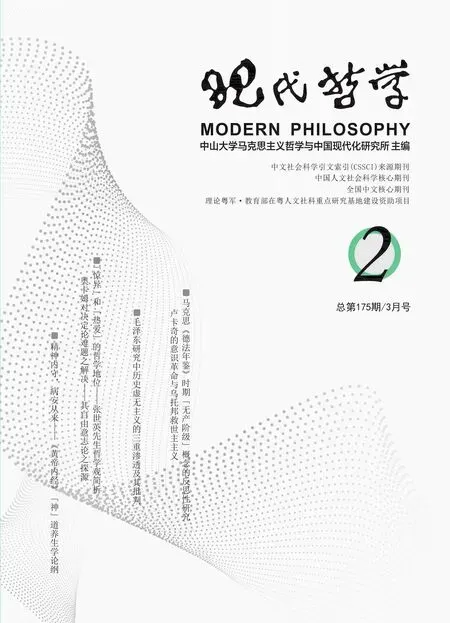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无产阶级”概念的反思性研究
邹广文 王吉平
无产阶级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它作为承担人的解放的革命主体,在青年马克思的理论中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首次提出“无产阶级”的概念,但这一概念并非毫无依据,它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为解决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统一问题所形成的。黑格尔由于受到斯密的影响,同时基于法国大革命之后不稳定的政治现实,将国家与市民社会放入伦理精神的运动和发展环节之中来考察,认为国家作为普遍性的理念具有合法性,市民社会作为居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中间领域依旧充斥着利益矛盾。这种特殊性的领域随着理念的运动必然要上升到普遍性的领域,包含普遍性因素的官僚政治和等级要素成为沟通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中介。然而,黑格尔的这一创制遭到马克思的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认为黑格尔采用中介因素并不能真正化解市民社会的矛盾,反而会加剧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同时,马克思进一步深化对普遍性的理解,认为真正的普遍性在于化解市民社会的矛盾,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革命。无产阶级作为实现社会革命的因素,无需任何中介,直接承担起人的解放的使命,成为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人的最高本质的普遍性希望。
针对无产阶级是否具有普遍性的力量以实现“人的解放”的目的,有的学者持否定观点(1)有的学者否认无产阶级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一种观点认为,普遍性特征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虚幻性。另一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概念自身具有模糊性,其实现人的解放的目的与阶级自身解放之间是分立的,无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参见方克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具有“普遍性形式”吗? 》,《哲学研究》1964年第1期,第40—44页;David W. Lovell, Marx’s Proletariat: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8, p.49.),多数学者则站在普遍性的立场为马克思辩护,认为无产阶级作为普遍阶级,是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变革力量(2)第一种观点采用异化的视角,认为私有制本身培养了否定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否定的生活状况中表现出异化,也恰恰在消灭私有制和克服异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普遍的阶级。第二种观点认为,资产阶级只具有相对普遍性,它带来的解放是将社会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无产阶级作为普遍阶级,其特殊利益与社会总体利益一致,它的解放与整个社会的解放是一致的。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实现对黑格尔“贱民”的逻辑变革,无产阶级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生,是实现自由的变革力量。(参见田毅松:《“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反驳与论证——基于异化论的无产阶级概念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第1期,第59—65页;唐文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第38—45页;Renzo Llorente, “Marx’s Concept of ‘Universal Class’: A Rehabilitation”, Science& Society, Vol.77, No.4, 2013, pp.536-560;汪行福:《论马克思的普遍主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7—15页;王代月:《由政治国家批判向市民社会批判的转折——〈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政治批判思想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4期,第23—28页;任劭婷:《从黑格尔“贱民”到马克思“无产阶级”的逻辑变革——现代自由的困境与出路》,《哲学动态》2017年第3期,第30—40页;夏莹:《论黑格尔的“贱民”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观念的结构性差异》,《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3期,第15—21页。)。针对学者们对无产阶级普遍性的不同看法必须弄清楚,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首次提出无产阶级的概念时,就从普遍性的视角赋予无产阶级以实现人的解放的政治潜能,但为何无产阶级作为普遍阶级能够承担起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又如何实现人的解放?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成为实现人的普遍解放的物质武器,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生成的逻辑理路,无产阶级作为化解德国物质利益难题的力量,更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法哲学的中介性要素,是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锁匙。
一、马克思论黑格尔法哲学的中介要素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基于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现状,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了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充斥着神秘主义,认为黑格尔到代表行政权的官僚政治与代表立法权的等级要素中,寻找市民社会过渡到普遍性国家的实现形式,这一路径是无效的。黑格尔的中介要素实质上是维护私有财产,无力消解二者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普遍性只有在适用于全体人民,而非某一特殊的阶级时才有效。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国家是一种普遍物,在国家中可以实现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面对德国内部的分崩离析,黑格尔认为伦理国家对德国非常重要,国家作为一种神圣的理念,是“伦理理念的现实”(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88页。。只有通过伦理国家才能积聚民族精神,早日实现德意志的统一。依照黑格尔的理论,伦理理念的运动要经历三个阶段: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其中,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和外在必然性,家庭则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作为特殊性领域,是伦理理念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其中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包含同业公会以及关注福利执行的民法机构等,“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4)同上,第198页。。但这种相互满足需要的关系具有特殊性和不稳定性,个人追求特殊性目的和需要的无限制的扩张,使得市民社会依然充斥着利益斗争,无法克服贫富之间的二元对立。当伦理理念要行进至代表普遍性的国家阶段,就必须借助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中介,而代表行政权的官僚政治与代表立法权的等级要素处于政府同人民之间,它们都扮演着“居间者”的角色。
黑格尔认为,从行政权看,“官僚是国家在市民社会中的代表”(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3—84页。。行政权代表国家的普遍性,自上而下对市民社会实行管理。行政权通过保护市民社会实现国家的普遍利益,如审判权保护市民社会的财产权,警察权为市民社会提供市政服务,包括路桥维修、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福利等。因此,行政权的主体即政府官僚等级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重要的中间等级,市民社会通过官僚等级获得有序的管理和组织,以合法的方式统一于国家。黑格尔指出,“中间等级也是国家在法制和知识方面的主要支柱。没有中间等级的国家,因而还是停留在低级阶段的”(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57—358页。。通过官僚等级作为具有普遍性的中间等级,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性个体借助外在的手段使个人的活动符合共同的规律和法律,并自觉进入更高层次的国家中。从立法权看,“各等级是市民社会在国家中的代表”(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等级要素作为市民社会的代表,是市民社会向国家派出的代表团。黑格尔认为必须在“立法权”中引入等级要素,“各等级的使命要求它们既忠实于国家和政府的意愿和主张,又忠实于特殊集团和单个人的利益”(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64页。。等级要素作为一种中介要素,其议员是社会生活某一领域的代表,这些代表成为议会等级要素后放弃原来的私人利益,获得新的政治效能,成为自觉维护普遍利益的政治等级。议员代表选民可以讨论参与政治,也可向不参与国家事务的市民社会普及有关政治知识。“各等级的真正意义就是:国家通过它们进入人民的主观意识,而人民也开始参与国事。”(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黑格尔认为,各等级的主要作用是补充高级官吏所不了解的社会基层的具体情况,并对官员进行监督。各等级的真正意义是防止同业公会、个人的特殊利益侵犯国家的利益。
然而,马克思看到黑格尔的官僚政治和等级要素作为居间者仍存在一些没有解决的冲突,官僚政治无法弥合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实质是以二者的分离为基础,是“国家形式主义”。首先,官僚等级与市民社会的联合与斗争始终是存在的。官僚政治的前提是同业公会作为“市民社会的国家”,市民社会通过同业公会实行自治。但在国家利益开始独立的时候,官僚政治开始反对同业公会;而一旦市民社会由于理性的推动逐渐摆脱同业公会,官僚政治又要竭力复兴同业公会,因为同业公会一旦衰落,官僚政治也就衰落。因此,官僚政治并无真实内容,其自身充满矛盾性。其次,黑格尔认为官僚政治使单一从属于普遍,但从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的四种途径来看,无论是通过混合选拔还是考试选拔官员,亦或是给予官员以稳定的薪俸、通过监督防止官员滥用权力,四种方式实际上都掩盖了特殊领域私有财产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仅仅只是暂时的妥协,是一种肤浅的二元论。至此,官僚政治的形式和内容、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是颠倒的和脱节的。官僚政治一方面是粗陋的唯物主义,使现实生活物质化,疯狂追逐私利;另一方面是粗陋的唯灵论,将意志推崇为始因滋生唯意志论,产生对权力的崇拜和任意性的想象。
此外,马克思认为,“等级要素是市民社会的政治幻想”(10)同上,第79页。。首先,黑格尔认为只有官员才真正掌握国家事务的知识,市民社会的各等级的知识都是出自贱民的见解,各等级要素仅仅是维护国家普遍利益、放弃自身集团私利的工具,他们甚至会为私人利益牺牲普遍利益。其次,马克思认为等级要素本身存在悖谬,黑格尔未从根本上消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反而承认二者的对立。一方面,市民代表只有进入议会成为等级要素才可能是政治等级,它为了成为政治等级首先必须放弃自己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私人等级是市民社会派出的代表,它只有按照市民社会的差别才能进入政治领域,是按照自身在市民社会中的构成获得政治意义。黑格尔在这里要求等级要素必须服从国家的普遍利益是极其荒谬的,它导致一个人的本质即国家公民与市民社会成员身份的分裂,国家公民作为国家的理想主义者,是完全与他的现实性不同的、分裂的存在物。马克思认为,成员身份的分裂表现出私人等级的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是对立的,等级要素仅具有政治上的形式意义。“政治上的等级要素不再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现实关系的实际表现,即它们的分离。”(11)同上,第94页。那么,黑格尔为何不直接去讨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而对等级要素这一行将消失的中世纪的遗留物倾注如此热情呢?因为市民社会作为私人等级表现出政治性质的缺乏,活动本身不包含普遍性的目的。黑格尔想通过等级要素作为普遍性的政治等级实现真正的同一,实质上表现出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仅具有反思关系,无法改变国家的本质,这也反证私人等级是掩盖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的工具,并不具有政治性。
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方法论逻辑,认为黑格尔的论证方式是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的。黑格尔所言说的现实的关系并不是由现实本身决定的,而是由逻辑决定的,现实的政治演变历程是在逻辑中完成的。例如,黑格尔给行政权下的唯一哲学定义是使“单一”和“特殊”从属于“普遍”,但“黑格尔不问这种从属的形式是否合理,是否合适。他只是抓住这个范畴并满足于为它找到一种相应的存在”(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2页。。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神秘主义的论证方式是将观念看作脱离人的抽象思维,并且这种抽象思维是独立的主体。黑格尔通过概念的逻辑演绎作为动力,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现实关系转变成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因而陷入语言的诡辩和哲学的神秘主义中。“黑格尔总是把推理理解为中项,理解为一种混合物。可以说,在他关于理性推理的阐释中,表现了他的体系的全部超验性和神秘性的二元论。”(13)同上,第105页。黑格尔的普遍事务是一种独立的主体,通过运动分别到政府事务的官僚政治以及议会的等级要素中寻找它的现实形式,其实质是通过中项掩盖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对立,但无论是行政权所代表国家利益,还是立法权所代表的市民社会的利益,这些都是由现实的特殊利益和政治地位决定的,它们本身与其说是中介,还不如说是矛盾的体现,共同的本质都在于私有财产。黑格尔总是在矛盾与悖谬中赋予中介多种规定,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始终无法通过中介达到真正的统一,普遍性实则成为一种装饰。这种非批判性的、神秘主义的做法是将中间物即官僚政治看成是君主的政治抽象,等级要素看成是市民社会的政治抽象。马克思认为,无论是行政权还是立法权都不能体现中介作用,中介的虚幻性和形式性使马克思逐渐转向政治批判。
至此,马克思直接进入政治批判破解黑格尔伦理国家的秘密,“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14)同上,第39页。。黑格尔借用官僚政治和等级要素解决现代政治的难题,通过中介要素消解矛盾,实质上使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政治国家也成为土地贵族以及长子继承制的守护神,只有私有财产才是国家独立性的体现,这实则是一种现代政治的倒退。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视域,进而回应卢梭的民主观,认为“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15)同上,第40页。。民主制能够消除二元论,“人民国家”才是国家的真正形式,只有在真正的人民国家,议会才成为普遍利益的代表。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期望从更高的阶段恢复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统一,使国家成为人的最高现实,因此竭力使行政权复归于人民社会生活,人民成为中间等级直接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打破官僚政治和等级要素的垄断政治的权力,真正的普遍性只有适用于全体人民,而非某一特殊的阶级才有效。
二、哲学与无产阶级:超越抽象普遍性的初步成果
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基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裂的现实,马克思将化解二者矛盾、实现普遍性诉求的愿望置于市民社会之中,发现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解放并非是实现普遍解放的最后形式,人的解放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普遍性。那么,这种普遍性由谁来担当呢?“无产阶级”的概念呼之欲出。无产阶级作为实践的主体成为马克思化解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追求普遍性的中坚力量。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胜任此任务,是由于它作为整体的阶级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中遭受普遍的苦难。在此基础上,无产阶级代表的阶级利益即是普遍利益,其实现自身解放的过程能够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因此无产阶级阶级作为普遍的阶级在德国革命中具有现实性。
(一)无产阶级由何而来?
马克思为何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突然提出“无产阶级”的概念?无产阶级的蓝本在何处?(16)对于马克思从何处了解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并无确证的结论,目前学界对早期马克思了解无产阶级的途径存在多种解读。(参见[日]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66页;韩蒙:《法哲学批判的社会主义语境——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起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4期,第73—79页。)从逻辑理路看,马克思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转向激进的共产主义,在社会中寻找到解决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因素,逐渐形成“无产阶级”的概念。随着现代社会与国家分离,人与人的社会差别不再具有政治意义,阶级作为一种现代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应运而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看到市民社会中的人逐渐变为原子式的个人,社会按照财产、消费等形成不同的等级,而这样的等级逐渐丧失政治效能,市民社会仅仅显现出私人领域的差别。市民社会产生一个新的阶级,新的阶级丧失财产,依靠自身的劳动生活。马克思将这一阶级看作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同时,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进一步关注欧洲国家阶级的形成、阶级和等级的特权性质的问题。他发现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第三等级”跃迁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但“其中包括重大矛盾,一方面宣布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牺牲私有财产”(17)王旭东、姜海波:《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研究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29页。。在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摘录中,马克思关注到人始终是围绕财产关系展开活动,历史中任何阶级都是从自己的思想利益出发对待公共事务,即使在民主社会中个体意志与普遍意志也可能不相符合。马克思认为二者的平衡必须借助别的力量,这一力量能够把自身的利益看作是国家利益的阶层,依靠这一阶层的普遍意识使得个体意识过渡到共同意识,从而完成真正的历史任务。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受到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和法国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工业革命和政治变革中,英、法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入新阶段,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德意志民族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许多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德国,无论是魏特林、赫斯还是施泰因,这些学者都看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18)[德]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孙则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305页。,看到无产阶级主导社会运动所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整体形成自己独立的意识和阶级认同(19)[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I(1818-1844)》,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持平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479页。。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马克思辗转至工人运动的革命中心——巴黎。在巴黎,他与“正义者同盟”结交,看到法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激烈,感受到现实的无产阶级身上充满信心、勇气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德国的阶级力量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20)奥古斯特·科尔纽认为马克思到达巴黎后,抛弃卡贝的共产主义学说,重视布朗基的学说,布朗基在接受巴贝夫阶级斗争观点的基础上把无产阶级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手段。(参见[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I(1818-1844)》,第559页。)。在德法两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巴黎工人运动的影响下,马克思逐渐接触到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赋予无产阶级以新的内涵。
通过对于现实的德国制度的考察,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确立为解决市民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力量。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看到政治解放只是一种抽象的、局部的解放,国家与市民社会处于对立中,人实质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在政治国家中,人作为公民存在于政治共同体之中,具备自由、平等、安全等人权;而在市民社会中,任何一种人权都未能超出私有财产的原则,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二者分裂的结果是利己主义的人的出场。此种矛盾也存在于德国现实之中,在德国官僚阶级将垄断发展到极致,德国人民在市民社中依然处于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苦难关系中。对此,马克思认为,要推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必须回到人本身,“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人的解放必须通过彻底的革命推翻一切的特殊物,重新确立解决市民社会问题的普遍性力量,真正实现人的高度的革命。而德国要想进行彻底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必须在阶级中找到一个由于自己的现实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本身的强迫而形成的阶级来实现普遍解放,由此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马克思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的阶级力量。
(二)普遍的阶级——普遍地遭受苦难
马克思通过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运行机制必然导致工人的贫困。由于私有财产制引发阶级的利益斗争,因此,无产阶级的出场具有必然性,其历史使命并非是通过人为组织主观形成的,而是通过无产阶级所处的生活状况和资产阶级的整个社会结构导致的。
无产阶级自身的生活状况决定无产阶级自身代表普遍利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为,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任务是由无产阶级身处非人性的市民社会中决定的。19世纪40年代,由于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在城市中占有极大优势,德意志无产者生活较为悲惨。无产阶级除了承受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还有更为深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354页。。“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阶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17页。一方面,德国无产阶级成为被排除于市民社会之外的阶级,市民社会的原则并不适用于无产阶级。社会早已剥夺了无产阶级所有的特殊性,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得不到任何权利。工人只是付出自己的劳动,承担起整个社会的重担。从另一方面看,工人赤贫化的现象并非是局部的而是普遍的,这种普遍性的贫困表明一切补救的尝试都无法改变工人被奴役的现状。因此,无产阶级代表的利益必然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而非某个阶级的特殊利益。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所处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无产阶级必将作为普遍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承担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24)同上,第262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民经济学家提到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但事实上无产者通过机器参与劳动,他们在为资产者创造财富的同时却愈加贫困化,无产阶级和财富在其中处于对立关系中。马克思在无产阶级身上看到消灭私有制的否定性力量,面对资产者对无产者不断造成的伤害,无产阶级作为整体的否定性的一面,必然会进行抗争。在这场抗争博弈中,二者都表现出异化状态,但无产者在异化中感到自己的非人化,即精神和肉体都陷于贫困状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同于其他阶级,因为这些阶级一旦获得胜利,仍依赖于它们的对立阶级和辅助阶级的继续存在……只有无产阶级作为真正的‘普遍阶级’,才真正不需要自己的对立面来确保自身存在。”(25)[以]阿维纳瑞:《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张东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69页。因此,在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和社会结构中无产阶级并未获得任何私有财产,它作为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的阶级必然会产生摆脱这种异化状态的普遍性的需求。现实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决定无产阶级必然表现为市民社会的一种否定和革命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它所代表的普遍性不仅仅是一种合理化,而是具有哲学层面的必然性。
(三)普遍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即是普遍的解放
无产阶级受奴役的地位决定无产阶级必然站起来进行抗争,马克思看到任何争取解放前景的运动都必须以普遍目的为基础,那么具有普遍性的无产阶级如何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认为,德意志的社会阶级结构比法国更为保守和落后,19世纪的德国不可能像法国那样先进行政治解放再进行社会解放,德国资产阶级无力粉碎普鲁士集权主义,但无产阶级的力量却伴随工业化在不断增强。伴随着中间等级急剧解体,“自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的农奴也正在逐渐跨入无产阶级的行列”(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页。。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增大,其所积聚的力量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股力量的催化之下,无产阶级由于贫困必然将一切弊病归因于现实的社会制度,因此推翻这种被奴役的现状的全部补救办法就在于通过暴力推翻特定的政治制度,这才是无产阶级自身的真正目的。无产阶级在德国遭遇人的完全丧失,其运动带有自我毁灭的性质。无产阶级在实现解放的过程中,即使最后获得胜利,也绝不会成为社会的对立方面。因为无产阶级的扬弃不单是扬弃自身,更是扬弃所有阶级,自我灭亡的特性使得无产阶级能够消灭一切阶级的特殊利益。当无产阶级真正实现普遍解放时,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无产阶级的对立面——私有财产都会消失。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普遍性无需任何中介要素,其实现方式是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在批判宗教的基础上,马克思看到相较于走在时代前沿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学说,德国现实虽然还在“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但德国哲学是德国人未来的历史。1843年9月,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提到:“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对于自身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自己的行动。”(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一方面,意识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它可以充分暴露世界的混乱不明之物,使不自觉的历史趋势朝向一个更为自觉的历史趋势发展。而当意识以一种批判的哲学形式对当代的斗争做出自我阐明以后,哲学作为彻底的理论通过无产阶级就会要求现实世界实现彻底的哲学化,使得哲学理念不断在现实世界生成。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在奴役状态中通过哲学获得理性和智慧,作为哲学的物质武器对现实世界进行改造,并能够生发一种扬弃一切不自由的状态、超越市民社会私人利益的更高的追求。“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人。”(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页。德国革命是彻底的、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革命,无产阶级与哲学之间的结合能够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
因此,无产阶级体现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本质与存在的绝对对立,是观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的彻底表现。而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是观念与现实在现实的物质世界的历史中的和解,进而才能够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三、超越中介性因素的历史唯物主义回答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超越了黑格尔的中介性要素,无产阶级无需任何中介,通过自身的阶级意识就能从整体上把握历史任务,化解市民社会的矛盾。黑格尔只关注反思性的关系而无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鸿沟。在由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跨越中,黑格尔不论是借助封建贵族、等级要素还是其他中介性要素,都仅仅是一种带有历史限制的诉求,只能退回到保守的立场,与现代政治的发展不相符合。相反,马克思直面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非逐渐过渡,而是变体。因此,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超越黑格尔的中介性要素,发现无产阶级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所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运行机制必然导致工人现实的贫困,无产阶级不需要作为自己对立面的私有财产来确保自身存在,在阶级意识的引领下无需借助中介性要素直接同资产阶级进行抗争,消灭私有财产和一切阶级,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并非是经验层面的个体,而是作为整体的阶级,“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29)同上,第17页。。马克思这里从哲学思辨的层面赋予无产阶级普遍性,以实现“人就是人的世界”,同时他对无产阶级给予厚望,无产阶级是人类的总体性质,无产阶级遭受的奴役状态是整个社会对人类自由压抑的表现,工人能从整体层面反思自己的历史任务,对自身有一个自觉的把握,可以理性地认识推动革命的发展(30)唐文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第38—45页。。
当然,马克思在追求无产阶级普遍性过程中不断实现理论的自我超越,使无产阶级由一个宏大的概念逐渐转变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并成为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和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性力量。伴随着大工业时代的到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始关注到诸如分工、交换、劳动等概念,现实的人一开始就是社会化而非孤立的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分工和交换逐渐形成普遍交往。马克思从世界历史层面关注无产阶级的普遍性,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交通工具的完善,工人阶级的组织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在此条件下,共产主义早已突破地域性,无产阶级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由此,无产阶级不仅仅是充满激情的革命力量,而是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生成的历史主体,它要完成的使命是由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此外,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序言》中,恩格斯提到:“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4页。无产阶级的普遍性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中无法克服的矛盾,凸显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矛盾不断激化,矛盾的激化与斗争有助于无产阶级形成主体意识和革命性力量,劳动者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消灭雇佣劳动,使所有人免于异化劳动而获得真正的解放。
总之,阶级是马克思理解历史的关键性概念,同时马克思追求普遍性诉求体现了他对人的价值的关注,更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文关怀。德国的现状表明现有的社会状况是违反人性的,黑格尔的法哲学也无力改变这种现状,通过阶级概念,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的特征表现出自身的阶级意识,真正的普遍性追求由无产阶级来承担。“人”由此成为马克思政治批判的逻辑起点,马克思通过追求人的本质的现实性,通过扬弃宗教作出当代的批判哲学,将工人阶级作为现实的斗争工具,呼吁受压迫的阶级应当超越一切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的现实关系,以期通过与哲学结合改变现实人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现状。此外,从现实来看,无产阶级的本质属性和未来形象从未被固定,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将呈现出更新的样态。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言,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活动,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应围绕着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从无产阶级到群众的扩展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文关怀,更凸显人民作为无产阶级的主力军将会在历史发展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