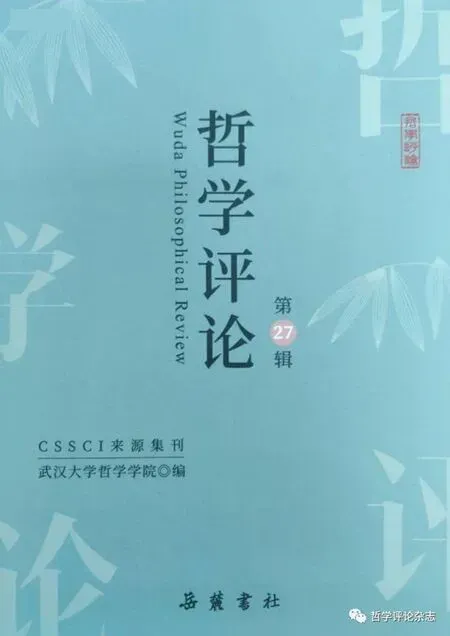功利主义与完整性是否相容?
——对西方功利主义式完整性辩护路径的述评
张继亮
人们通常从功利主义忽略正义以及要求过高(demanding)出发对它展开批评,[1]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4.Spencer Carr, “The Integrity of a Utilitarian” , Ethics, 1976 (86), p.241.在这些批评中,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它为实现功利最大化而忽略正义或权利以及为了实现功利最大化而对人们提出超出其本无须承担的义务的要求等这些问题,而很少关注它对完整性(integrity)的破坏。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首先从完整性的角度出发对功利主义提出了严厉的
批判。在威廉斯看来,完整性意味着“一个人深切且广泛地参与其中并深深认同的那些‘承诺’(commitments)”,或者一些“一个人在某些情形之下从内心最深处将之视为其生活意义之所在的计划和观点”[1]Bernard Williams, “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 , in 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J. J. C.Smart and Bernard Willia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16.。[2]威廉斯有时将这些体现一个人完整性的承诺、计划和观点称为与一个人的“存在密切相连,并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他的生活以意义”的“根本性计划”(ground project),参见Bernard Williams, Moral Luck: Philosophical Papers1973—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2.由于功利主义根据一个行为是否能带来功利最大化来判断其正确与否,所以,当一个行为不能实现功利最大化,那么这一行为也需要被舍弃,即使这一行为源自体现一个人完整性的承诺、计划、观点或“根本性计划”也是如此,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正是功利主义的功利最大化这一要求侵蚀了人们的完整性:个体的完整性在功利计算中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人变成了只是进行功利加总的机器,用威廉斯的话来说就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个人的行为和他的决定源自他最为深刻认同的计划和观点这一事实。因此,从最表面意义上来看,这构成了对他完整性的侵犯”。[3]Bernard Williams, “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 , in 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J. J. C.Smart and Bernard Willia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16—117.毋庸置疑,威廉斯对功利主义展开的完整性批判是奠基性的,然而,在其观点提出之后,西方很多学者对他的这一观点质疑,他们纷纷认为,功利主义者实际上可以消除功利主义与完整性之间的冲突或矛盾。[4]Sarah Conly, “Utilitarianism and Integrity” , The Monist, 1983 (66), p.299.然而,国内学术界却对这一重要的议题知之甚少,[5]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是毛兴贵在其文章中曾提到过本文涉及的两个重要视角并对其展开了分析,参见毛兴贵:《伯纳德·威廉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为了更好地展开对这一重要议题的述评,本文首先从威廉斯对完整性的界定出发开始讨论,然后分别介绍并评价“受以行为者为中心限制式功利主义”“精致式功利主义”“完整性式功利主义”以及“功利主义居优”等为功利主义进行完整性辩护的路径,最后,在总结部分中,我们需要说明这些路径总体来讲为什么是失败的。
一、完整性的概念
威廉斯将完整性界定为“一个人深切并广泛地参与其中并深深认同的那些‘承诺’(commitments)”,由于这一界定与“完整性”一词的词义相匹配——“完整性指的是一个事物的整全性(wholeness)、完整性(intactness)、纯洁性(purity)”[1]Damian Cox, Marguerite La Caze, and Michael P. Levine,“ Integrity” ,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integrity/.,因而它从直觉层面来看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很多学者也因此追随威廉斯将它界定为对观念与承诺的坚守。例如,弗拉纳甘(Owen Flanagan)就认为,“完整性指的是一个人坚守他最重要的观念和承诺并按照它们行事的特点”[2]Owen Flanagan, Varieties of Moral Personality: Ethics and Psychological Realism,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81.;布鲁斯坦(Jeffrey Blustein)也认为,“从直觉层面来看,完整性意味着人们忠于自己最重要的承诺,或忠于自己的根本计划”[3]Jeffrey Blustein, Care and Commitment: Taking the Personal Point of View,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80.。
将完整性看作是忠于自己的观念和承诺具有一定道理,因为它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说某人具有某方面的完整性时,[4]对完整性更为详尽的分类参见Damian Cox, Marguerite La Caze, and Michael P. Levine,Integrity and the Fragile Self,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101—138.他需要真正根据自己所奉行的信念、承诺去行动,而不只是具有行动的欲望或倾向,并且,更重要的是,在面对人性所能承受范围之内的危险、诱惑时能够坚守住相关的观念、承诺,[5]Mark S. Halfon, Integrity: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9, pp. 39—47.相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抵御上述危险和诱惑,那么,我们会说,他在某些方面并不具有完整性。从这一角度来说,完整性这一价值与本真性(authenticity)有所区别,虽然两者都指向真实的自我,但一个人虽然可以有很多本真性欲求、信念与承诺,或者说他具有按照这些欲求、信念与承诺的欲望与倾向,但他不一定真的按照它们去行动,更重要的是,在面对危险与诱惑时,它们可能会被舍弃掉。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将完整性只是定义为忠于自己的观念和承诺也存在问题。一方面,这些观念和承诺可能是“非道德的或甚至从道德层面来看是可鄙的”[1]Cheshire Calhoun,“ Standing for Something” ,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5(92),p.242.,而且,更有可能的是,它们并不是真实的,它们只是人们自我欺骗的结果,而如果一个人所忠于的信念或承诺是假的或不道德的,这就与人们忠于这些信念与承诺的做法相矛盾;[2]Elizabeth Ashford,“ Utilitarianism, Integrity, and Partiality” ,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2000(97), p.424.另一方面,这些观念和承诺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但它们绝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们在现实中遇到一些特别事件或随着自己经验的增多,他们可能会修改,甚至在个别情况下会放弃之前奉行的观念或承诺。所以,人们忠于自己的信念或承诺并不意味着完整性的实现,人们至少需要保证他们所信奉的信念或承诺是真实的,并且需要根据自己遇到的现实情况和经验的增多进行必要的调整。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调整自己的完整性过程中,人们可能会持有两种相互冲突的观念或承诺,例如,在欧美国家中的来自亚、非、拉三洲传统社会的同性恋移民一方面认同于同性恋身份,另一方面又认同于塑造他们身份认同的传统社会的观念,虽然这些传统观念是反同性恋的。而这就使得完整性与自主(autonomy)这一概念区别开来,因为,自主意味着二阶欲求支持一阶欲求,[3]Gerald Dwork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ut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0.然而,在上述例子中对同性恋的认同问题上,来自传统社会移民的二阶欲求之间出现冲突,因而,从自主的层面来看,他并不具有自主性,但这不妨碍他具有完整性。当然,除了这类特殊情况之外,完整性与自主之间具有共同的交集,毕竟完整性意味着一个人(的二阶欲求)对(作为一阶欲求的)观念与承诺的确认与支持。
另外,威廉斯、弗拉纳甘与布鲁斯坦等人没有指出的是,完整性意味着人们所信奉的观念和承诺必须是本源性的,即人们忠于它们必须是出于它们自身而去行动而不是出于更高层面的观念或承诺,或者说,构成完整性的信念或承诺必须具有足够的自主性或独立性。[4]Damian Cox, Marguerite La Caze, and Michael P. Levine, Integrity and the Fragile Self,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84—87.例如,一个法官持有公平断案的信念或承诺,而且在现实中的确也是这么做的,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说他具有职业完整性,他可能迫于上级命令或出自升职的想法而这么做,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就不能说这名法官具有真正的职业完整性,因为他公平断案的行为并非出自公平断案的信念或承诺,而是源自更高的命令的信念。
总体来说,完整性并不只是意味着忠于自己的信念与承诺,它意味着人们所秉持的信念是真实的并且有价值的,而且随着人们的经历与经验的增多,这些信念与承诺需要被修正甚至被放弃,最后,构成完整性的信念与承诺必须是本源性而不是外源性的。因此,从我们对完整性这一定义所作的这些修正来看,威廉斯等人的完整性定义存在很多漏洞。[1]对照Daniel D. Moseley,“ Revisiting Williams on Integrity” ,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2014(48), pp. 60—68.然而,即使如此,威廉斯可能会说他完全接受这些批评,并按照这些批评对完整性进行重新界定,那么,从新的完整性定义出发对功利主义的批判是否也存在很多漏洞?很多学者认为这一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从“受以行为者为中心限制式功利主义”“精致式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居优”以及“完整性式功利主义”等角度出发对威廉斯的功利主义完整性批判提出了反驳。
二、受以行为者为中心限制式功利主义
既然威廉斯对功利主义提出的完整性批评的核心在于功利主义的功利最大化要求会损害行为者的完整性,那么一个非常自然的应对方案就是在功利计算中提升人们完整性的重要性,使之在最大程度上不受功利计算最大化要求的影响,这样,人们的完整性就得到了保护,我们可以将这一方案称之为“受以行为者为中心限制式功利主义”(agent-centered restriction utilitarianism):“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对于一个行为者是否应被要求促进最好的整体结果这一问题来说,答案取决于他这么做所带来的益品的数量(或者他这么做所避免的坏的结果的数量),以及他为了实现最优的结果所做出的牺牲的规模。更具体地说,我认为,一个可行的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特权(a plausible agent-centered prerogative)允许每个行为者赋予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人的利益以更大的重要性。”[1]Samuel Scheffler, The Rejection of Consequent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p.20.对完整性这一议题来说,这种功利主义认为,是否采取促进功利最大化的行为取决于这一行为是否会危及他自己的完整性,经过行为者衡量之后,如果这一行为不会危及自己的完整性,那么他就可以实施这一实现功利最大化的行为,反之,他就可以不去实施这一行为,因为,毕竟“从心理层面来讲,一个行为者不可能放弃他自己的计划”[2]Ibid, p.59.,那么,按照“应该意味着能够”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能要求这个行为者因为要实现功利最大化而放弃自己的完整性。
受以行为者为中心限制式功利主义这一方案,据说一方面保存了行为者的完整性,同时又兼顾了其他人的利益从而没有陷入利己主义,因而实现了保存完整性与功利最大化两者之间的平衡。[3]Ibid, p.21.然而,事实上却是,这一方案既没能保存行为者的完整性,也没有尊重功利主义的基本要求。
从完整性这一层面来看,它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人们所奉行的相关观念或承诺必须是本源性的而不是外源性的,然而,在受以行为者为中心限制式功利主义这一路径之下,体现行为者的完整性的信念和承诺并不是本源性的,它们来源于外源性的功利计算,即,虽然某个行为会实现较优的目标,但由于它会危及甚至会牺牲他的完整性,而牺牲完整性对行为者来说基本是不可能的,那么,功利计算后的结果就是不去做这一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去做这种行为反而实现了功利最大化:“人们允许行为者去促进他所选择的非最优结果的实现,假如相比起他选择其他每个更优方案所带来结果,他这么做所带来结果的低劣(inferiority)程度按照具体的比例来说不超过他为了实现较优结果而所做出必要之牺牲的程度。如果行为者所有可以实现的非最优结果按照这个标准都被排除在外的话,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被要求实现最大化的整体结果。”[4]Ibid, p.20.因此,在受以行为者为中心限制式功利主义的视野之下,体现行为者完整性的信念与承诺并不具有自主性或独立性,它们并不体现出行为者的完整性。
从功利主义这一层面来看,由于功利主义要求人们在进行功利计算的过程中保持无偏私性(impartiality)——在“人与人之间完全做到不偏不倚”[1][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8页注释。,在此基础上找出能够实现功利最大化的方案。然而,在受以行为者为中心限制式功利主义的路径之中,行为者的利益/完整性却被赋予“特权”或者说赋予他自己的利益/计划比其他人的利益/计划更大的重要性,这实际上破坏了功利主义的无偏私性承诺,所以,在此基础上经过计算得出的结果严格来说并不为严格的功利主义者所接受。[2]Damian Cox, Marguerite La Caze, and Michael P. Levine, Integrity and the Fragile Self ,London: Routledge, 2003, p.92.总之,受以行为者为中心限制式功利主义虽然从表面上看既维护了行为者完整性又坚持了功利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三、精致式功利主义
由于威廉斯完整性批评的目标指向的是行为功利主义(actutilitarianism),而行为功利主义只是功利主义家族谱系中一员而已,[3]对功利主义更为详尽的分类参见David Lyons, Forms and Limits of Utilitarianism,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5, pp.1—29, 以及[美]茱莉亚·德莱夫:《后果主义》,余露译,华夏出版社,2016年。因此,很多功利主义的辩护者指出威廉斯的完整性批评并不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功利主义,例如间接功利主义或精致式功利主义(sophisticated utilitarianism)。从历史上来看,很多功利主义者意识到,人们如果直接追求幸福或功利,会导致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的结果,即,直接追求幸福反而无法获得幸福。例如,密尔在其《自传》中通过追溯自己青年时的经历指出:“生活的各种享受足以使生活成为乐事,但是必须不把享受当作主要目的,而把它们看作附带得到的东西。若是一旦把它们当作主要目的,就会立刻觉得它们不足以成为乐事。”[1][英]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吴良健、吴衡康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88页。
在此基础上,雷尔顿(Peter Railton)提出了“精致式功利主义”来说明完整性与功利主义可以相容。雷尔顿首先区分了主观功利主义(subjective utilitarianism)与客观功利主义(objective utilitarianism)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观功利主义指的是“一个人在行动中应该采取快乐主义式观点,即,他应该在任何可能的时刻尝试决定那个行为最可能有助于最优地实现他的幸福并根据这一决定采取行动”[2]Peter Railton,“ Alienation, Consequentialism, and the Demands of Morality” , Philosophy& Public Affairs, 1984(13), pp.142—143.,也就是说,主观快乐主义不仅规定何为正确的标准——幸福最大化,而且规定了取得正确结果的决策程序——直接进行快乐式计算;相比之下,客观功利主义指的是“一个人应该采取实际上最能实现个人幸福的行为,即使这在行为过程中并不采取快乐主义式观点”[3]Ibid., p.143.,这意味着,客观功利主义采取了判定行为正确性的标准,而在很多情况下舍弃了取得正确结果的直接式计算程序,相比起主观功利主义,客观功利主义更具有优势,因为,人们的计算能力有限,而且人们在计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偏私性,所以,人们最好在很多情况下放弃直接式的功利计算。在此基础上,雷尔顿提出了能够容纳完整性的精致式功利主义:“如果一个人试图过一种客观式快乐主义生活(即,在特定环境之下,他能实现的最快乐的生活)而且并没有持有一种主观式快乐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称这个人为精致式快乐主义者。”[4]Ibid.精致式功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间接功利主义,它将功利最大化规定为判断人们行为的最终标准,但没有将直接的快乐计算作为决策程序,因此,它允许人们发展出特定原则、信念、承诺,只要它们最终能够实现最大化幸福,而且重要的是,这些原则、信念、承诺可以免于直接功利计算,所以,从总体上看,这种形态的功利主义能容纳完整性。
为了更好地说明精致式功利主义能够容纳完整性,雷尔顿举了一个假想的关于胡安(Juan)和琳达(Linda)这对夫妻的例子。胡安和琳达是一对因工作原因分居两地的夫妇,胡安每隔两周与琳达聚会一次,最近一周,琳达似乎有点情绪低落,所以,胡安决定最近的每周都去看望琳达一次,但胡安也意识到,每次去看望琳达的路费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如果他仍按照每隔两周去看一次琳达的频率可以把一笔不小的费用省下来,他可以把它捐给乐施会(Oxfam),乐施会可以用它在非洲凿井来救济处在濒临渴死边缘的居民。但如果胡安是一个精致式功利主义者,而且他也明确知道将钱捐给乐施会而不去看望琳达从客观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讲是正确的选择,或者说,能够带来最大化的客观功利主义结果,虽然如此,他还是更注重培养对妻子琳达关心的承诺、倾向或性格,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承诺、倾向或性格从长远来看更能够促进世界的最大化幸福,而如果他不培养这样一种关爱琳达的承诺、倾向或性格的话,那么,“最终他对人类的幸福的贡献就不会获得最大化的结果,因为,他可能变得更愤世嫉俗和更以自我为中心”。[1]Peter Railton, “Alienation, Consequentialism, and the Demands of Morality” , Philosophy& Public Affairs, 1984 (13), pp.159—160.
雷尔顿的精致式功利主义方案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受以行为者为中心限制式功利主义的局限,更融贯地将完整性整合进功利主义之中。然而,这种路径的功利主义也面临着不小的难题。首先,胡安发展出来的对琳达的关心的承诺并不是本源性的,他是在经过功利计算后发现发展出这种承诺会有利于幸福最大化这一结果的出现,因而,即使他在现实中克服障碍一直在忠于这一承诺,他也不具有关心琳达的完整性。
其次,胡安明确知道他为了保持关心琳达的承诺是有代价的——付出他人生命的代价。虽然,他知道形成关心他人的承诺甚至形成关心他人的性格、倾向有助于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功利最大化,而且即使最后他成功了,他也需要背上沉重的负担——本来可以拯救他人的生命却放弃了这一机会。这样,他在反思这一选择过程中可能会对他发展这一关心承诺的正当性质疑,如果他质疑,那么,这种符合精致式功利主义原则的完整性就会遭到侵蚀。[1]Damian Cox, Marguerite La Caze, and Michael P. Levine, Integrity and the Fragile Self,London: Routledge, 2003, pp.96—97.当然,精致式功利主义者可以反驳说,他可以放弃这一反思活动,因为,毕竟坚守这一承诺或发展出相关的性格会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功利最大化,但这一反驳并不成立,因为完整性要求人们在面对新的经验或事件后进行反思,并对自己的承诺或计划做出修正,而如果胡安修正自己的关爱的承诺,容纳特定场合之下的功利计算的话,他就违反了精致式功利主义的限定——排除直接式功利计算,而且即使精致式功利主义能够允许这种修正,它也会带来“道德滑坡”的危险——慢慢滑向主观式功利主义的危险。总之,作为精致式功利主义者的胡安面临两个困境:反思自己之前的选择会侵蚀自己的符合精致式功利主义的完整性,甚至会完全颠覆自己对精致式功利主义的坚持;不反思之前的选择,那么他可能会冒着自欺而失去完整性的危险。
四、完整性式功利主义
既然人们对功利主义的承诺经常与其他非功利式承诺、计划相冲突,而且,据说这种冲突是“内在于行为功利主义之中的”[2]Peter S. Wenz,“ The Incompatibility of Act-Utilitarianism with Moral Integrity”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79(17), p.552.,那么,功利主义的拥护者或辩护者的一个“最具影响力”[3]Damian Cox, Marguerite La Caze, and Michael P. Levine, “Integrity” ,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integrity/.的回应就是人们都将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承诺或将功利最大化作为自己的承诺,而如果人们都将功利最大化作为自己的承诺的话,那么,原先的承诺都会从属于功利主义承诺,从而不会再出现非功利最大化的承诺与功利最大化的承诺相冲突的可能性,即,“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么按照行为功利主义的要求去思考和行事就至少会与一个承诺相一致”[4]Gregory W. Trianosky, “Moral Integrity and Moral Psychology: A Refutation of Two Accounts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Utilitarianism and Integrity” ,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1986 (20), p.280.,而这样就会消弭“据称是造成完整性被削弱的根源”[1]Spencer Carr“, The Integrity of A Utilitarianism” , Ethics, 1976(86), p.243.,完整性因此也就无法构成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了。我们可以将功利主义的这种应对方案称为“完整性式功利主义”(integrity-utilitarianism)方案。
完整性式功利主义这一应对完整性批评的方案虽然在直觉上具有吸引力,但它立刻会面临一个反驳:既然完整性意味着与其他人的承诺、观念、计划相比,人们认为属于自己的承诺、观念、计划具有首要性(primacy),即,人们具有更充分的理由首先要实现这些承诺、观念、计划,而功利主义的承诺为了实现功利最大化却要求人们保持无偏私性,或要求人们将自己与他人的承诺、观念、计划一视同仁,那么,我们从什么意义上来确认功利最大化式完整性是一种完整性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既然我们将功利最大化奉为自己的承诺或计划,那么,这就要求我们保持无偏私性,要求将自己与他人的承诺、观念、计划一视同仁,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并不只是因为某些承诺、观念、计划是他人的就因此对它们一视同仁,而是因为我们奉行功利最大化这一承诺才对他人的承诺、观念、计划一视同仁,简言之,功利最大化这一首要性承诺与平等对待其他人的承诺、观念、计划一视同仁相一致。[2]Jeffrey Blustein, Care and Commitment: Taking the Personal Point of View,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71.
另外,完整性式功利主义会面临高阶/低阶计划的困境。威廉斯曾指出,“作为一个功利主义者,他拥有一个实现最大化可欲性结果的总体性计划……然而,可欲性结果恰好不在于行为者执行那个计划;必须存在一些一个行为者和其他行为者共同持有的更基本或更低阶的计划,并且,这些可欲性结果部分在于最大化地、和谐地实现这些计划……除非这些一阶性的规划存在,一般性的功利性计划无法发生作用,因此会变得非常空洞”。[3]Bernard Williams“, 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 , in 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J. J. C.Smart and Bernard Willia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10.简言之,功利最大化式承诺的实现需要依赖于“更基本或更低阶的计划”,然而问题在于,功利最大化式承诺经常会破坏这些“更基本或更低阶的计划”的实现,所以,完整性式功利主义者最终会面对高阶/低阶计划的困境:高阶计划(功利最大化的承诺)的实现需要低阶计划(非功利最大化式承诺)的实现,但高阶计划(功利最大化的承诺)的实现却往往会破坏低阶计划(非功利最大化式承诺)的实现,高阶计划最终就无法实现,然而,如果放任低阶计划发展而不去进行干涉,那么,功利最大化的计划也可能无法得到实现。这种高阶/低阶困境式批评并没有力度,因为,完整性功利主义者完全可以通过引导欲求、希望、愿望而不是诉诸非功利最大化式的计划来实现功利最大化的计划。[1]Jeffrey Blustein, Care and Commitment: Taking the Personal Point of View,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74.
即使功利最大化这一首要性承诺与平等对待其他人的承诺、观念、计划一视同仁相一致,它还存在的缺陷在于它与人性不符。功利最大化式承诺要求人们的非功利最大化式承诺服从于它,但由于这些非功利最大化式承诺构成人生的意义之所在,人们可能会拒绝让功利最大化的要求挫败这些承诺与计划,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对于一个具有根本性计划的人来说,在特定的情形之下,将所有因果相关性的要素都考虑在内之后,如果那个计划所要求的行为与作为一个非个人性的功利最大化者的承诺相冲突,那么功利主义就会要求他放弃他的根本性计划所要求他做的事情,而这一要求是很荒谬的……以道德行为者所在世界的无偏私性式益品排序的名义让一个人放弃他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合理的”[2]Bernard Williams, Moral Luck: Philosophical Papers 1973—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4.,或者说,“当一个总数从部分由其他行为者决定的功利网络中得出以后,人们要求一个人绕过他自己的计划和决定并认可功利式计算所要求的决定这一做法是荒谬的”[3]Bernard Williams, “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 , in 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J. J. C.Smart and Bernard Willia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16.,而如果人们允许功利最大化的承诺压倒这些构成人生意义的承诺或计划,那么,人生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得贫乏。面对这一批评,完整式功利主义者可能会回复说,人性具有非常高的可塑性,[1]Gregory W. Trianosky, “Moral Integrity and Moral Psychology: A Refutation of Two Accounts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Utilitarianism and Integrity” ,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1986 (20), p.286.人们最终会将功利最大化式承诺作为自己的立身的根本,但按照目前人性的特点来看,功利最大化式承诺只能是非常少数人的首选,绝大部分人仍将它看作是分外的义务,而不是一种严格的道德义务,换言之,目前大部分人的人性仍然无法承担如此沉重的、要求如此严格的功利最大化式承诺,按照“应该意味着能够”的原则来看,对于绝大部分人无法承担的承诺不能确立为道德义务。
五、功利主义居优
威廉斯对功利主义(包括康德式道德哲学)的完整性批评暗含着一个三段式结构:W(1):一种道德理论具有合理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它不能牺牲完整性;W(2):作为一种道德理论的功利主义牺牲了完整性;W(3):所以,作为一种道德理论的功利主义不具有合理性,人们因而也就无须严肃对待它。
受以行为者为中心限制式功利主义、精致式功利主义与完整性式功利主义都试图从各个方面出发来证明功利主义给予完整性以足够的重视或尊重,即,它们都试图证明威廉斯对功利主义三段论式完整性批评中的W(2)是错误的,虽然它们由于存在很多缺陷而没有能证明W(2)是错误的,但它们基本都认可W(1)是正确的,即“一种道德理论具有合理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它不能牺牲完整性”。阿斯福德(Elizabeth Asford)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并没有试图证明W(2)是错误的,他试图证明W(1)是错误的,因为,事实表明以及很多道德理论家都认识到,构成个人完整性的根本性计划经常与道德责任相冲突,而如果W(1)是错误的,那么,威廉斯的结论就站不住脚,除此之外,他也试图表明W(2)也是不成立的。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结论说,功利主义不仅认识到现实之中构成个人的完整性的根本性计划与道德责任相冲突,而且还提出了协调这些冲突的程序,因此,它要比其他道德理论更具优势。[1]Elizabeth Ashford, “Utilitarianism, Integrity, and Partiality” ,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2000 (97), pp.421—439.
阿斯福德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包括两部分——“无偏私性的道德承诺”与“个人计划和承诺”,其中,“无偏私性的道德承诺”属于道德价值系统,而“个人计划和承诺”属于审慎性价值系统[2]Ibid., p.426.。如果构成个人生活的“无偏私性的道德承诺”与“个人计划和承诺”能够相互融贯地整合成一体,那么,这种生活就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之中,“无偏私性的道德承诺”与“个人计划和承诺”经常处于冲突之中,即,“构成良好生活的这两个成分处于根本性、无可挽回的冲突之中并因此难以整合进一个完整的良好生活之中”[3]Ibid., p.427.,简言之,在现实生活之中,个人的完整性经常受到道德承诺的挑战。
不仅现实之中的个人完整性经常受到道德承诺的挑战,有些强调完整性重要性的道德理论家实际上也默认了这一点,例如威廉斯自己。威廉斯虽然非常重视完整性对每个人生活的重要意义,但阿斯福德却指出,威廉斯的论述默认道德承诺对个人完整性提出了挑战这一事实。例如,威廉斯在《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一书中曾指出,道德义务“最终都基于一种理解: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要过。人们需要帮助,但并非(婴儿、极老迈者、严重残疾者除外)无时无刻需要帮助。他们无时无刻需要不遭杀害,不遭凌辱,不遭无端干涉”。[4][英]B. 威廉斯:《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陈嘉映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3页。按照威廉斯的论述,这意味着他承认,“鉴于很多人的根本性利益(vital interests)正遭受营养不良和疾病的威胁,帮助他们的义务经常与行为者将金钱与精力奉献于他们的根本性计划这一做法不相容”。[5]Elizabeth Ashford, “Utilitarianism, Integrity, and Partiality” ,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2000 (97), p.430.
基于上述人类生活现实以及道德哲学家的认识,阿斯福德认为个人的完整性与道德承诺或原则在很多情况下不相容不只是功利主义所独自面临的一个事实,然而,相比于其他道德理论,功利主义不仅认识到这一事实,而且提出了一个解决两者冲突的方案:如果一些根本性的道德要求,例如,保护人们的根本性利益不受伤害,即保证他们“不遭杀害,不遭凌辱,不遭无端干涉”,与人们的根本性计划或承诺相冲突,那么,人们就需要暂时牺牲自己的完整性去满足这些要求,因为,如果人们的根本性利益得不到保护,那么他们会遭受极大的痛苦;而如果其他人的根本性利益没遭受威胁,那么人们就不需要承担试图实现功利最大化的义务,因为,毕竟从心理上来讲,人们不可能同等对待所有人,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计划和承诺具有偏私性。[1]Elizabeth Ashford, “Utilitarianism, Integrity, and Partiality” ,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2000 (97), p.43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斯福德认为功利主义并不具有威廉斯等人所批评的那样具有要求过高的特点。
阿斯福德的功利主义居优式论点独辟蹊径,提出了一条为功利主义进行完整性辩护的新路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其他为功利主义进行完整性辩护的路径相比,他的论证更具进攻性,因为它表明,功利主义不仅意识到个人完整性受到道德原则的挑战,而且更是表明它能够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出路。然而,阿斯福德的两个论证存在漏洞。第一,阿斯福德并没有能证明W(1)是错误的,他只是表明现实之中的道德原则对人们的完整性提出了挑战,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毕竟在一个价值多元以及承诺多元的世界中,人们总会面对相互冲突的要求,面对这一局面,人们需要在不断反思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的根本性承诺或计划,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道德责任会对人们的完整性提出要求,但这一要求并不是一种无偏性的功利最大化式要求,或者说,一般性道德责任对完整性提出的要求并没有过高。同样,威廉斯也认识到道德原则会对人们的完整性提出挑战,但这一挑战并不是功利主义最大化式道德原则对完整性的挑战,即,他可能认为人们需要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但他们无须承担起为了实现功利最大化而牺牲完整性的责任。总之,阿斯福德只是表明道德原则会与个人完整性相冲突,但他没有能证明一般的道德原则会对个人完整性提出过高要求。第二,阿斯福德试图表明W(2)是没有根据的,他一方面试图通过限定功利最大化原则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试图通过人类的心理事实出发来确保个人的完整性免受过多的侵蚀,但这两个论证都存在问题。就前者而言,将功利最大化原则限定在维护人们的根本性利益并不能降低功利最大化原则去完整性的挑战;就后者而言,由于功利主义的目标在于实现功利最大化,这就需要依照无偏私性的功利计算来找到并执行实现功利最大化的方案,如果阿斯福德赋予个人完整性以更大价值,那么,这就从客观层面上使得功利最大化无法实现,从而也就失去了功利主义的独特价值。[1]对照毛兴贵:《伯纳德·威廉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44—45页。
六、结论
虽然威廉斯对完整性的界定存在一些问题,但他对功利主义的完整性批判是强有力的。即使人们从“受以行为者为中心限制式功利主义”“精致式功利主义”“完整性式功利主义”以及“功利主义居优”等角度出发为功利主义进行完整性辩护,但这些辩护都难以成立。功利主义之所以难以容纳完整性的关键在于,功利主义主张进行无偏私性的功利加总,而完整性恰恰重视偏私性,重视每个人自己的承诺与计划,同时,在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完整性拒绝加总,拒绝功利最大化。谢弗勒(Samuel Scheffler)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他认为威廉斯对功利主义进行的完整性批判是为了“回应下述不一致,即,一些关切与承诺自然地源自一个人的看法而不是依赖于这些关切在总体事态中的非个人性排序中的重要性的方式与功利主义要求行为者将来源于他自己看法的关切看作是完全依赖于它们在这种排序中的道德重要性的方式之间的不一致”。[2]Samuel Scheffler, The Rejection of Consequent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p.56.总之,通过系统地梳理西方学者围绕完整性批评所提出的四种功利主义式完整性证明路径,我们更加明确了目前西方学术界针对功利主义提出的完整性证明的研究现状,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提出更具有说服力的功利主义式完整性证明路径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