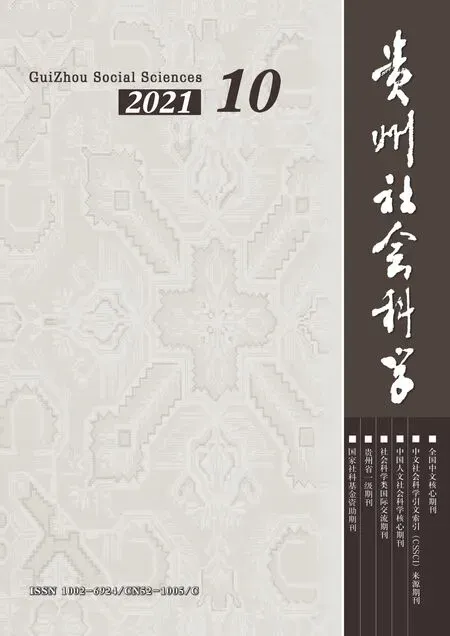民歌与淡怨:欧阳修文风的形成及美学意义
韩 伟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毋庸置疑,欧阳修是宋代文坛的领袖性人物,其经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是北宋时期审美风格、文学风格、学术风格的主要缔造者(1)本文所引欧阳修作品,悉据《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除转引“附录”部分他人文献外,不再单独出注。。作为政治家,他不仅身体力行支持改革、纠偏时弊,而且“奖引后进,如恐不及”[1]10381,曾巩、王安石、三苏等都曾受其扶掖。作为史学家,其《新唐书》《新五代史》去取精当,“简而有法”,堪称史家典范。作为文学家,“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1]10383,规约了有宋一代的基本诗学走向。顾随在《驼庵词话》中称“宋代之文、诗、词,皆奠自六一”[2],这种认知几乎代表了宋代以后研究者的共识。此种背景下讨论宋代学术自然无法绕开欧阳公。截至目前所见,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对欧阳修艺术风格的形成原因及过程还有深掘的空间。应该说,民间文化尤其是民歌因素在欧阳修诗学旨趣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扮演着潜在助推器的角色。
一、民歌情怀的早期驻留
天圣八年(1030),24岁的欧阳修以殿试甲科十四名的身份进士及第,紧接着便被授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等职,并任西京留守推官,自此开启了他四十余年的仕宦生涯。在西京洛阳,受到钱惟演的赏识,入其幕府,“钱文僖惟演守西都,梅圣俞(尧臣)、谢希深(绛)、尹师鲁(洙)、欧阳永叔(修)、杨子聪(愈)、张太素、张尧夫(汝士)、王几道(复)同在幕下,号为八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率常赋诗饮酒,间以谈戏,相得尤乐。洛中山水园庭塔庙佳处,莫不游览”[3]。可见,在与友人一咏一唱、寄情山水的过程中,除了以高雅诗赋彰显才能之外,亦不免掺杂“谈戏”的成分。按谢绛《游嵩山寄梅殿丞书》所载,欧阳修曾与友人同游嵩山,“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吕氏店。马上粗若疲厌,则有师鲁语怪,永叔、子聪歌俚调,几道吹洞箫,往往一笑绝倒,岂知道路之短长也”。其中明确提到欧阳修歌“俚调”一事,因缺少具体史料,现已无从考证其所歌俚调到底为何种歌曲,但将其定位为民间小调当大抵不错。此事发生在明道元年(1032)九月,正任河南府通判的谢绛奉命代皇帝祭祀中岳嵩山,欧阳修、杨愈、尹洙、王复四人陪同。《游嵩山寄梅殿丞书》便是五人游览结束之后,谢绛写给妹夫梅尧臣的书信。当时欧阳修26岁,正值意气风发之际,饮酒、狎妓、远足在其生活中占有相当比重,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他不无惭愧地说“仆知道晚,三十以前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知以为乐而不知其非也。及后少识圣人之道,而悔其往咎”(《答孙正之侔第二书》)。这一时期其“歌呼”的主要内容或者是艳词,或者是民间俗曲。事实上,两者又存在天然之联系。尽管历来很多研究者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或者认为“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4],或者臆断为“刘煇伪作”[5],但诸如《减字木兰花·楼台向晓》《减字木兰花·歌檀敛袂》《玉楼春·春葱指甲轻拢捻》《南歌子·凤髻金泥带》《南乡子·好个人人》《迎春乐·薄纱衫子裙腰匝》《宴瑶池·恋眼哝心终未改》等作品已确定出自欧阳修之手无疑。实际上,这些作品并非真正不堪入目,只不过较直白地描写了男女的自然情感而已,这在受温柔敦厚观念影响的传统文人眼中,自然有伤风化,似乎与欧阳修这位文坛领袖式人物极不相配,所以宁可相信非其亲作。实际上,艳词恰是民间俗曲的类型化和高雅化呈现,民歌中大量充斥着赤裸的爱恋、肉欲内容。欧阳修对民歌的态度虽然显露于少年轻狂时期,但却一直贯穿始终,在《崇文总目叙释·小说类》中称“俚言巷语,亦足取也”[6],甚至晚年退居汝阴(今安徽阜阳)时,提及韩愈时亦以“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六一诗话》)为据,高度赞扬其“曲尽其妙”的成就。这种评价便带有以民间通俗精神为旨归的色彩。
与这种倾向相一致,欧阳修的诗作中出现了很多民歌意象。“樵歌”“棹歌”“俚歌”等被多次提及,比如“林穷路已迷,但逐樵歌响”(《游龙门分题·上山》)、“樵歌杂梵响,共向松林归”(《游龙门分题·宿广化寺》)、“归路逐樵歌,落日寒川上”(《伊川独游》)、“行歌采樵去,荷锸刈田归”(《秋郊晓行》)、“向暮卷空罾,棹歌菱浦北”(《游龙门分题·鱼罾》)等,这些作品都为天圣至明道年间作品。此时作者还未经历仕途坎坷,充满了理想化气息,自然山水与民间歌谣在他生活中占有相当比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作中反复出现“逐樵歌”“行歌采樵”之类的表达,它们已经不单纯是字面意义上对林间歌声的追寻,更加代表了诗人的主观审美追求,俨然成了诗人审美倾向的投射。
经历了短暂的恬适时光之后,欧阳修进入了仕途的坎坷期。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直陈时弊,触怒权相吕夷简,很多文人以“朋党”之罪牵连其中。欧阳修上书指斥司谏官高若讷见风使舵,献媚失职,“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与高司谏书》),遂以“越级上书”之名遭到报复。谗言之下,仁宗下诏责其“妄形书牍,移责谏臣,恣陈讪上之言,显露朋奸之迹”[7],因此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令。夷陵属于历史上的“荆蛮”之地,民风原始,巫俗盛行,欧阳修虽仅在此一年有余,但却对楚谣俚歌印象深刻,获得了进一步接触民间歌舞的机会。在《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一诗中他说“时节同荆俗,民风载楚谣。俚歌成调笑,摖鬼聚喧嚣”,这是诗人初到夷陵写给好友苏舜钦的诗篇,介绍了荆楚之地的风土人情,其中提到的“楚谣”“俚歌”给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据《东湖县志》记载,此地百姓崇尚渔猎,其时往往“连歌彻夜”,婚丧习俗或者“鼓乐筵宾,喧阗屡日”,或者“鼓锣喧闹,足蹈手舞,尽夜而罢”[8]。这种情况在欧阳修其他诗作中亦有反映,《黄牛峡祠》称“大川虽有神,淫祀亦其俗。……潭潭村鼓隔溪闻,楚巫歌舞送迎神”,《夷陵书事寄谢三舍人》亦称“腊市渔盐朝暂合,淫祠箫鼓岁无休。……月出行歌闻调笑,花开啼鸟乱钩輈”,在耳濡目染过程中,欧阳修势必会产生情感的认同,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事实上,随着对当地文化了解的深入,欧阳修表现出了难得的推崇之情,针对很多人对此地的偏见,他在《夷陵县至喜堂记》一文中辩驳称:“然不知夷陵风俗朴野,少盗争,而令之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橘、柚、茶、笋四时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很显然,“风俗朴野”是他对夷陵的基本定位,他对这种原生态的生活状态非常推崇,而“楚谣”“俚歌”恰是这种朴野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夷陵世俗生活的浸染,不仅可以使诗人远离政治的纷扰,也逐渐净化了诗人的心灵,由此对自然之美也多了一份情愫。景祐四年(1037),欧阳修由许州还夷陵,途中作《自枝江山行至平陆驿五言二十四韵》,“山鸟啭成歌,寒蜩嘒如哽。”虽然全诗略带感伤情绪,但鸟声、鸡鸣、寒蝉、溪菊、田鴽却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立体画卷。景物相似,却身在旅途,不由得产生“梦先归”的急切之情,最终在想象中的“棹歌”声中寻找到了感情的慰藉。客观而言,无论早期放浪形骸的京洛生活,还是首次被贬夷陵的心灵放逐,这些都为欧阳修与民间文艺的深入接触提供了契机,前者是铺垫,后者是发酵。加上后来贬谪滁州、扬州、颍州的生活经历,这种情愫被不断升华,最终以类似盐溶于水的方式,渗透到了欧阳修的整体诗词创作之中。
二、民歌因素的深入渗透
总体上看,景祐三年(1036)至皇祐元年(1049)这段时间,欧阳修基本处于外任贬谪的状态。人生不幸诗家幸,也恰是在这段时间欧阳修才可以更充分、更多元地接触民间文化,吸收民间养料,在山林牧歌中实现人生境界的进一步提升,所谓“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间”(《游琅琊山》)、“援琴写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穷山间”(《奉答原甫见过宠示之作》)是也。此时欧阳修的文风渐趋由少年放纵变得“绝去刀尺,浑然天质”[9],进一步奠定了自己的诗美风格。市井生活的经历为欧阳修文学思想、文学创作的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民间艳乐、俗曲成了他后来诗词中驰骋想象、锻造语言的武库。否则,若纯以高雅的文士生活而入,则后来的作品很可能成为缺少生活气息的“掉书袋”之作。这无论是对诗词内容的提炼,还是对艺术表达的成熟而言都不是好事。欧阳修所反对的宋初西昆体、晚唐体的症结也恰在于此。
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中称欧阳修的诗词“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10],指出了欧阳修诗词取材广泛的特点。某种程度上,这与欧阳修对民间生活的吸纳不无关系。在欧阳修的很多作品中,往往含有大量关于民间节日(如人日、元宵、上巳、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以及冬至)、民俗活动(如祭祀、灯会、捕鱼、登高、采莲)等方面的描述,此类作品如《生查子·去年元夜时》《渔家傲·三月清明天婉娩》《采桑子·清明上巳西湖好》《越溪春·三月十三寒食日》《蝶恋花·越女采莲秋水畔》等等。与此相一致,欧阳修很多作品的语言风格也带有明显的俚俗色彩,试看一首《渔家傲》:

愁倚画楼无计奈。乱红飘过秋塘外。料得明年秋色在,香可爱,其如镜里花颜改。

在欧阳修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其民间性的应该是鼓子词。鼓子词之名始于宋人《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是一种以鼓为主要伴奏乐器的演唱伎艺,主要盛行于两宋之际,元明以后仍有少量文人创作。按照现有材料,最早进行鼓子词创作的应是欧阳修,代表作是《渔家傲》(正月斗杓初转势)十二章。该组词以联章体的形式,分别吟咏十二月的节令变化和景物特征,将十二月景色寓于《渔家傲》词牌之下。除此之外,还有归于欧阳修名下的《渔家傲》(正月新阳生翠管)十二章联章词,但对这组与《渔家傲》(正月斗杓初转势)高度相似的词作,出处颇有争议,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称“未知果公作否”[12]7。《渔家傲》(正月斗杓初转势)组词后附无名氏跋语曰“荆公尝对客诵永叔小阙云:‘五彩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凤。’曰:‘三十年前见其全篇,今才记三句,乃永叔在李太尉端愿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词。数问人求之,不可得’”[13],这段话一方面明确交代了这组词为“鼓子词”的性质,另一方面通过对王安石、李端愿生卒年的考察,可大概推测这组词应该作于庆历五年(1045)到嘉祐元年(1056)之间,“其时公年不满五十”[14]。
对于鼓子词的性质,郑振铎最早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指出“当为士大夫受到‘变文’影响之后的一种典雅的作品。……当是宴会的时候,供学士大夫们一宵之娱乐的”[15]。后来学者中刘永济继承此说,《宋代歌舞剧曲录要》认为鼓子词多为“文人遣兴之作”或宴会中“娱乐宾客之用者”[16]。上述观点自然不错,但却并未将问题推向深入,即这种文人“典雅”之作的源头是什么?我们认为,其源头必然可以追溯到民间歌诗。作为“最早出现”的鼓子词,欧阳修的《渔家傲》(正月斗杓初转势)取材于十二月。这种以时间为顺序的叙述方式,在民间或者按照一年四季、十二月的宏观样态体现,或者按照微观时辰的逻辑运行。前者最早如《豳风·七月》《子夜四时歌》,后来历朝历代,大江南北都流传有以十二月为叙事线索的大量民歌,其中当然包括欧阳修曾生活过的四川、湖北、江苏、安徽等地;后者则以“五更”题材最为普遍,按照吴立模、刘半农等人的考证,见于文献记载的五更调可以上溯到晚唐至宋代之前,且极有可能是由“五更转”发展而来(2)按:《歌谣周刊》1924年4月第51期刊载有吴立模《五更调与五更转》一文,考察五更调的产生时间及来源问题,并附有吴立模与当时在法国的刘半农关于这一问题的往来书信。刘半农为其提供了自己发现的《太子五更转》材料,吴立模据此更加坚定了五更调源自五更转的观点。现将《太子五更转》转录于此:“一更初,太子欲法坐心思:□知耶孃防守□,何时得度雪山□;二更深,五百个力士睡昏沈,遮取黄羊及车□,朱鬃白马同一心;三更满,太子腾空无人见,宫里传齐悉达无,耶孃肠肝寸寸断;四更长,太子苦行万里香,一乐菩提修佛道,不藉你分上作公王;五更晓,大地下众生行道了!忽见城头白马纵,则知太子成佛了!”后来民间流传的大量五更题材唱段有逐渐艳情化的趋势,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很显然,欧阳修的这组联章词属于宏观样态,只不过较之民间歌谣更加文雅化而已,但基本叙事逻辑存在明显的相似处。
用欧阳修自己的话说,这种建基于民间文体之上的雅化歌诗,产生的是一种“清欢”式审美效果。这在其《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十一首联章词中表现明显。虽然《采桑子》组词不像《渔家傲》组词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它们属于“鼓子词”,但从基本形态来看,众多研究者仍将它们归入鼓子词的行列(3)近代以来,首先提及欧阳修《采桑子》的是王国维,其在《宋元戏曲史》中指出该组词与普通词的区别在于“重叠此曲,以咏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于天池在《宋代文人说唱伎艺鼓子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一文中亦指出,《采桑子》“虽然没有明确标出是鼓子词,但从它的《西湖念语》来看,却是典型的鼓子词”,此外,马兴荣《中国词学大辞典》、李雪梅《中国鼓词文学发展史》等著作皆将《采桑子》归入鼓子词之列。。这组词是欧阳修晚年(65岁)退居颍州西湖所作,十一首词在基本叙事逻辑上将宏观时间、微观时间、人生际遇相结合,就宏观时间而言,几首词的首句分别是“春深雨过西湖好”(其二)、“群芳过后西湖好”(其四)、“清明上巳西湖好”(其六)、“荷花开后西湖好”(其七);就微观时间而言,几首词的首句分别为“轻舟短棹西湖好”(其一)、“画船载酒西湖好”(其三)、“天容水色西湖好”(其八)、“残霞夕照西湖好”(其九)。作者又将这些自然层面的宏观时间、微观时间与自己的人生际遇相互化合,所谓“何人解赏西湖好,佳景无时”(其五)、“平生为爱西湖好,来拥朱轮。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其十)。整体来看,这组词实现了景物与人生、时间与空间的深度统一。一般情况下,鼓子词并非单独出现,在宴饮场合往往会配以散体“致语”,构成念、唱结合的形式。《西湖念语》便属于这组词的“致语”,其中对这组词的性质进行了如下描述:“因翻旧阙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技,聊佐清欢。”明确指出此为“翻旧阙”而作的“新声”。“采桑子”词牌始于南唐,旧题“丑奴儿令”“丑奴儿”“罗敷令”等,李煜、冯延巳等人较早以此格式进行创作,到了宋代已经较为普及,欧阳修之前以晏殊的作品最具特色。因此,《西湖念语》中的“旧阙”当指已经成型的文人之作,而“新声之调”当是指“鼓子词式”的民间连珠体形式。这样,就使《采桑子》实现了通俗与高雅的融合。通俗体现了普通人的日常之“欢”,高雅则保持了文人阶层的精神之“清”。这应该也是欧阳修援民歌入诗词的深层目的所在。
三、民歌与“淡怨”旨趣的形成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多次提到梅尧臣,对其诗风评价极高,称梅尧臣“闲远古淡”“深远闲淡”。《六一诗话》属于欧阳修晚年“退居汝阴”之作,两人相识30余年,性趣相投,文风接近,对老友诗风的总结和高扬,又何尝不是自己诗美理想的折射?事实上,对“淡”的推崇,除了梅尧臣的影响之外,民间文学的自然取向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清人沈曾植评价欧阳修诗作“颇多通俗俚语,故往往与乐章相混”[12]3610,此处所言之“乐章”当更多是指民间乐歌,其诗作中所谓的“通俗俚语”便是其“尚淡”旨趣的具体呈现。民间因素的浸润,使得欧阳修诗风呈现出一种自然清淡的特征,叶梦得称“其言多平易疏畅”[17],苏轼亦称“其言简而明”[18]。欧阳修本人也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其曾通过曾巩转告王安石“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19],表达殷殷劝诫之情。在给徐无党的信中称“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与渑池徐宰书》之五)、“犹爱吾子辞意甚质”(《答徐无党第二书》),勉励之余也对徐无党质朴的文风予以称赞。在给张棐的信中谈及以文明道之意,认为六经之文“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与张秀才第二书》),鼓励取法六经文风进行实际创作。为了将崇尚自然、淡泊的旨趣表达得更充分,欧阳修专作《斲雕为朴赋》,文中他提出“素以为贵,将抱朴而是思;焕乎有文,俾运斤而悉去”,主张祛除文章华丽雕饰的外表,返归平易质朴的本质。
如果说“尚淡”仅是欧阳修诗风的外在呈现的话,那么对“怨刺”传统的皈依则是其内在精髓。其对民间歌诗的重视,绝不仅仅因为它们以自然的风貌为其带来感官愉悦这么简单,更为重要的是民歌具有“通下情”的作用。《毛诗大序》很早就指出“风,讽也”“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民众借助歌诗表达内心所想,统治者凭借民歌反思政治得失,于是“观风”成了正直之臣和贤明君主的重要活动。欧阳修对民歌的重视,恰恰是其文学家身份之外,政治家理性的折射,“诗可以怨”“诗可以观”传统在他这里获得了延续,这也是其重视民歌的深层动机所在。康定元年(1040)在《赠杜默》一诗中,欧阳修首先以凤凰起兴,称赞杜默“其音和且清”,并指出“杜默东土秀,能吟凤凰声”,但在他看来这样还不够,于是建议对方“子盍引其吭,发声通下情”,承担起歌者的责任。杜默的老师是宋初理学开创者石介,石介在《三豪诗送杜默师雄并序》中称有宋文坛“石曼卿之诗,欧阳永叔之文辞,杜师雄之歌篇,豪于一代矣”[20],据此,后人遂以“诗豪”“文豪”“歌豪”称呼三人。很显然,欧阳修希望杜默秉承风雅传统,为民间发声,歌之有物。
事实上,欧阳修对“怨刺”的认知与其对民歌的重视相互同步。明道元年(1032),时年26岁的欧阳修写就《书梅圣俞稿后》,文章主旨是在推扬梅尧臣的诗风,但大部分篇幅却是在讨论音乐。在他看来,音乐可以“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并指出春秋以前“诸侯之国亦各有诗,以道其风土性情”。很显然,他不仅看到了音乐和谐天地、和谐人心的形而上作用,亦重视民歌呈现风土人情的现实功能。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最终才得出“诗者,乐之苗裔”的结论。这一命题,不仅彰显了诗与乐在发生学上的同根性,更加规定了两者在功能论上的一致性。除此之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亦称赞梅圣俞“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这更充分地表明欧阳修眼中所谓的“闲淡”“纯粹”实际上乃是一种形式之自然与内容之兴寄的深度统一。宋祁在《授知制诰举欧阳修自代状》中评价欧阳修的文章时,称“措辞温雅,有汉唐余风”[21],此处之“温雅”与本文的“淡怨”意思相近,认为其秉承了汉唐以来自然平和而又言之有物的诗学传统。在《六一诗话》中,欧阳修认为白体之弊为“得于容易”,西昆体之弊为“语僻难晓”,晚唐体则单纯“以精意相高”,结合欧阳修对宋初文坛上述不良文风的否定,可以说他既反对单纯的形式浅白,也反对孤立的内容深奥,而是试图营造一种“谲讽淡泊”的审美氛围。
正因欧阳修对民歌的深度接受,才使其表现出与梅尧臣“同中有异”的审美追求。如这部分开头所言,欧阳修与梅尧臣“文风接近”。这主要表现为他们都有对“淡”的审美追求,但“接近”却不等同于“一致”。每个人的性格、际遇、生活环境绝不可能完全一致,这也必将导致不可能存在完全相同的创作风格和审美旨趣。事实上,梅尧臣在对“平淡”的追求中,也包含着怨刺的因子,比如在其《寄滁州欧阳永叔》中除了称赞欧阳修“君才比江海,浩浩观无涯”之外,还以“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22]330与欧阳修共勉。但坎坷的人生际遇,使其难于施展人生抱负,诗歌在“济世”层面所达到的高度也不免受到限制,朱自清先生就认为梅尧臣的平淡初为“闲肆平淡”,后来则“间亦雕琢”[23]。这种“平淡”与陶渊明、王维不同,也与欧阳修有所差异。相比之下,梅尧臣逐渐向纯艺术的层面深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成了其最终的诗美追求,而欧阳修却将梅尧臣《依韵和晏相公》中所期望的“文字出肝胆”[22]368真正付诸实践并发扬光大。所以,如果说梅尧臣所尚之“淡”,倾向于“无为”之淡的话,那么欧阳修所践行之“淡”,则可以说是“有为”之淡。或者说,梅尧臣的“淡”是“闲淡”,而欧阳修之“淡”属“雅淡”。
欧阳修没有将含有“怨刺”的文字,变成生硬的载道之文的原因恰在于对“淡”的深入理解。这种效果的实现与其深厚的民间文学底蕴密不可分。在《送杨寘序》中,欧阳修借讨论琴音,进一步诠释了自己的审美追求。在他看来,古琴之音“纯古淡泊,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从中不难看出,所谓的“纯古淡泊”绝不仅仅是形式层面的自然天成,更为主要的是内容层面的忧患、怨刺,这与其对文学的看法如出一辙。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才可能实现“滑稽嘲谑,形于风刺”的自由境界。由此可见,欧阳修所践行的“淡怨”实现了李白式的自由与杜甫式的沉郁的深度整合。尽管其文学成就无法与二人匹敌,但在风格建构层面的努力则值得肯定。艺术境界的日趋精纯,加上中年以后逐渐提升的政治地位,为其审美理想的普及提供了助力,有研究者指出,其“借助‘场屋’之权有效地推行起‘平易流畅’的文风诗风”[24]。欧阳修历任主考官,从长远来看,他的主观好恶必然在潜移默化之中左右举子们的创作倾向,从而形塑了有宋一代文学的整体审美追求。
综上所述,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坛巨匠,诗、词、文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尽管其词作中仍带有一丝花间词的影子,但他在词境拓展方面却做出了突出贡献,遂使宋词变成了“无事不可入”的文学正宗。在诗歌与散文创作方面,他一方面呈现出流畅自然的语言风格,另一方面则在流畅中寄予深厚,体现出文学家的艺术才能与政治家的经世胸怀的统一。欧阳修作品总体艺术风格的形成除了其自身超拔的文学天赋之外,民间文学尤其是民间俚曲的长久浸润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动力因素。本文所论之“淡”,绝不是一汪清水般的纯净无物,它更像是一杯醇厚可人的香茶,表面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其中却蕴蓄着对自然的提炼,更加含有令人精神振发的因子。民间歌谣自然随性的表现形式,为欧阳修的作品提供了“淡”的外衣,同时,其言志体俗的内在属性,则使其作品淡中有物、淡内含讽,两者水乳交融便形成了欧阳修独特的“淡怨”风格。如果从整个宋代文化史来看,以欧阳修为主导的文人式的“淡怨”追求与以周敦颐为代表的理学家的“淡和”旨趣,在宋代社会逐渐合流,前者在形而下层面实现了审美与社会的整合,后者则在形而上层面实现了天理与人间的勾连,这一过程中便完成了“淡”的全方位建构,也对宋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了立体性统摄,塑造了“宋型文化”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