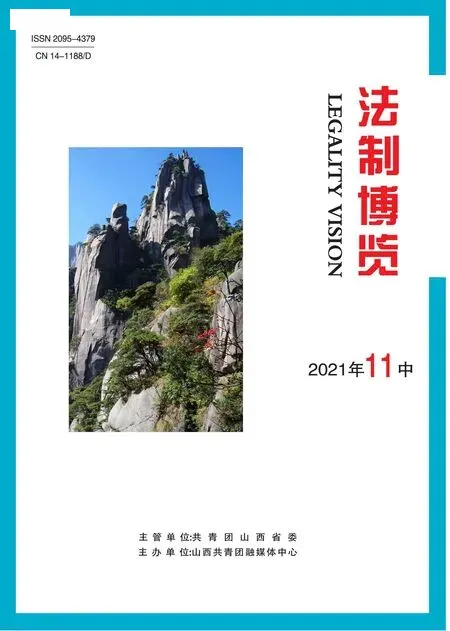刑罚的目的
毕祺祺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人民法院,河南 南阳 474250)
刑罚是指刑法所规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适用的,剥夺或限制犯罪人某种权益的制裁措施。而今所指刑罚目的,实际上指国家制定刑罚、量处刑罚和执行刑罚所希望其能产生的结果,刑罚的目的实现是一种主观要求,它以观念的形式在刑罚运行前已经形成,是国家对自身需要与犯罪作斗争的客观可能结果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反映。[1]
一、刑罚目的学说
在现代刑法理论体系中,一般认为关于刑罚目的的理论主要有:报应论、预防论。
(一)报应论
报应理论又称为绝对理论、正义理论,任何人均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基于此,国家对犯罪人施以刑罚,使犯罪人因自己给被害人带来的痛苦及给社会秩序带来的危害承受否定性的后果,在正义的方式下使犯罪人所造成的损害得以弥补,报应是刑罚公正性的要求。
康德坚持“人只能作为目的而不能作为手段”,认为刑罚是“一种与所有的目的性考虑无关的由正义提供的手段”,即刑罚只能惩戒行为人基于自由意志而选择犯罪的行为。黑格尔将犯罪看成是对法的否定,将刑罚看成是对犯罪的扬弃。黑格尔与康德都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报应。黑格尔还强调,如果适用刑罚是为了预防,那无疑会湮灭人之所以为人的荣光。而类比相互作用力,犯罪为第一性的强制,会出现相应的第二强制,这种强制与前者方向相反,力量相等。
黑格尔对康德理论进行了发展,提出了等量理论。等量理论所提倡的同态复仇,并不能涵盖所有情形,如:瞎子打瞎别人,无法通过打瞎瞎子来实现正义。而黑格尔提出等价理论:无论是犯罪还是刑罚,价值永远体现为侵害。基于犯罪与刑罚在价值上的等同,刑罚便摆脱了外在性状的限制,并获得以有限的刑罚对抗无限的犯罪。
(二)预防论
又称相对理论,通过对犯罪人的惩罚剥夺其再次犯罪的机会,同时向社会公众宣示此犯罪行为的后果,警示社会公众实施犯罪的不良后果承担,以减少、预防犯罪的发生,其强调一种社会功利效果。预防理论的观点大致可以追溯到刑法思想的起源时期。
费尔巴哈提出一般预防,即刑罚应当作用于一般公众,通过刑罚的威胁和执行,使公众不再犯罪。他认为,人们必须通过犯罪收获的喜悦和得到的痛苦进行权衡,并在痛苦大于喜悦的情形下,产生一种“心理强制”。一般预防追求立即广泛地预防犯罪,从社会政策方面亦具有重要的价值。李斯特主要发展了特殊预防的概念。
(三)报应刑与预防刑关系
报应论与预防论并不是排斥、对立的。它们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从根本上看,二者是相通的。报应论主张对个人实施的犯罪,要罚当其罪,罪刑相称,反对将惩治个人作为防卫社会的手段,强调刑罚的正义性。而预防论以社会为本位,强调维护社会利益,保护公共秩序,反对片面地为了刑罚的正义性,而不顾及刑罚的功利性效果。在刑罚执行的不同阶段可以实现在不违反刑罚正义性的同时,报应兼顾预防,在不违反刑罚功利性的时候,预防兼容报应。报应与预防虽有不同之处,可以通过具体案例采用不同的方法,使二者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既有利于罪犯改造,又有利于社会预防。
二、刑罚的目的
根据主体对象的不同,刑罚的目的分为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
(一)特殊预防
由李斯特倡导而发展起来的以重新社会化为核心的特殊预防理论,其特殊性表现在对象之特殊,其作用对象仅为犯罪人。
特殊预防实现的途径有:首先,通过适用限制自由等刑罚来剥夺犯罪人继续犯罪的能力和条件。其次,通过对其实行系统的教育,使其消除犯罪心理,确立守法意识,将犯罪人改造为守法的公民。根据功利主义,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国家根据人的这一本性使因犯罪而受到惩罚的人怯于再次受到惩罚而不敢再次犯罪。考虑到单纯的严酷惩罚有可能使罪犯产生对立情绪而不利于纠正其主观恶性,只有正确地把惩罚与教育结合起来,在惩罚的前提之下,实行感化教育,在思想上破除其犯罪心理,建立其守法心理,通过对犯罪人人格的重塑使其恢复非犯罪的心理状态。
特殊预防理论同样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首先,特殊预防的有效性难以获得证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再犯危险性无法通过任何科学手段准确测量。而累犯、再犯的实例在司法实践中却不少见,令社会大众不由得对特殊预防理论丧失信心。此外,特殊预防理论无法对于某些没有再犯可能性,或者不需要施加刑罚,以其他手段就可以防止犯罪人今后再犯罪时依然根据刑法判处相应刑罚的情况作出妥善的解释,比如对于身份犯只需要剥夺行为人的特定身份就可以避免他今后再犯该罪,特殊预防理论无法说明为何此时仍需要对其施以刑罚。
(二)一般预防
在特殊预防的基础之上,费尔巴哈在系统阐述心理强制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般预防。这种预防在作用对象上具有广泛性,通过对犯罪人实施惩罚对“潜在犯罪人”设立一种警告,“潜在犯罪人”会在内心进行利益的权衡。当然,这是消极的一般预防,刑罚通过对犯罪人的惩罚使其付出了违法成本,也保证了法律的权威,增强了法律的贯彻力和执行力,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更多的民众来维护法律、信仰法律。积极的一般预防主要思维出发点是认为法律规范是人类行为的指导标准,应当被遵守,并且是不容许被破坏的,而刑罚最重要的核心目的应在于“法秩序防卫”,刑罚的主要任务在对犯罪人施以再社会化与合规范人格化过程中,达到规范内化的目标。[2]
三、刑罚的终极目的——积极预防
笔者认为,所有刑罚的终极目的应是积极的特殊预防和积极的一般预防。在确保遵从规则方面,其他因素诸如信念、公正、信实感和归属感等因素远较强制力为重要,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必须植根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仅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它应该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3]通说认为刑罚只调整人的行为而不调整人的思想,从只惩罚有危害行为的人而不惩罚思想犯来说,这句话是合理的,但人的行为受思想的支配,只调整行为显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治标不治本,这又陷入了一个悖论。所以在此意义上,积极的一般预防与积极的特殊预防显得意义重大。
(一)积极的特殊预防
对于积极的特殊预防而言,刑罚是要治愈犯罪人道德上的缺陷,重塑法律权威与尊严,这样,犯罪人不仅是基于严酷的惩罚而感到恐惧、痛改前非,而是由于唤醒了内心的良知而改过自新。在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阿里斯瑞德有一段自白,“我没有一天不后悔,但并非受惩罚才后悔,我回首前尘往事,那个犯下重罪的小笨蛋,我想跟他沟通,我试图讲道理,让他明了,但我办不到,那个少年早就不见了,只剩下我垂老之躯。”这坦诚的道白也正是刑罚积极特殊预防的目的,用温情唤醒罪犯的良知,使他们真正回归社会。
犯罪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讲,罪犯也只是可以医治的生理(道德)病人,需要对症下药,用社会的疗法来治疗。当然,再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已经不再是刑罚,而是教化与治疗的方法,补充其社会价值认知的不足,增强其守法的动机,强化犯罪人对于刑罚的认知度与忠诚度。
(二)积极的一般预防
积极的一般预防同样侧重重塑法律的权威。预防不是预防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犯罪人以后的犯罪,而是稳定社会的规范,维持社会规范的同一性,同时建立公众对于法律的忠诚、信仰。
当今的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又是外发型的法制现代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多元化加剧,法律的权威性在民众心中并非牢固不催,所以更需要积极的一般预防来维护法律的规范性,在公众心中建立法律情感、法律意识,使公众建立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的忠诚,培养有效性认同。通过刑罚强化普通公民的守法意识,促成其对法律权威的信赖,培养法律意识,渐变为法律情感。
作为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刑罚的使用必须妥当,罪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用不同的治疗方法进行医治,犯罪祸患与其救治措施之间必须有效统一起来,着重于具体案件的解决而非搞“批量生产”。在刑罚的目的方面,应突出刑罚的积极预防——积极的特殊预防和积极的一般预防。通过积极特殊预防帮助犯罪人改过自新、重塑人格,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对于积极一般预防来说,则是重构法律秩序,树立法律的权威、培养民众的法律意识、法律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