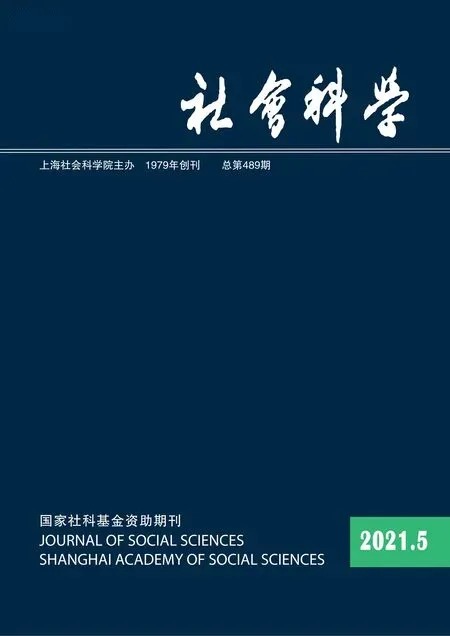破解“全球治理赤字”何以可能?*——兼论中国对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
赵 洋
全球治理的概念在冷战后受到广泛关注。这是因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人类的政治生活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报告》指出,冷战的结束使国际社会将围绕这样一个理想而联合起来,即“在广泛的领域内承担起集体责任。这些领域包括安全——不仅只是军事意义上的安全,也包括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安全,持续发展,促进民主、平等和人权,人道主义行动”(1)[瑞典]英瓦尔·卡尔松、[圭亚那]什里达特·兰法尔:《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节选)》,谢来辉译,载杨雪冬、王浩主编《全球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并且强调“消除暴力在政治、经济、社会或其他方面的一切起因,是治理方面的重要目标”(2)[瑞典]英瓦尔·卡尔松、[圭亚那]什里达特·兰法尔:《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节选)》,谢来辉译,载杨雪冬、王浩主编《全球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页。。这份报告指出了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所要追求的目标,认为各国人民应当以共同的价值为基础来管理全球事务,以维护全球安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推动全球法治化。但是,全球治理的现实并没有向着这份报告所预测的方向发展,报告所列举的治理目标也没有实现。有学者指出,当代世界政治呈现出失序状态,主要表现为军备竞赛加剧、“暴力文化”盛行、相对贫困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愈演愈烈、“文化同质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问题日益突出等。困扰着主权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各类问题并没有消失,相反在某些方面还显得更加突出。伴随着相互依赖、共同关注和共同命运,随之而来的是由军备竞赛、持久的贫困以及普遍暴力等现象所塑造的新的支配形式(3)Upendra Baxi,“‘Global Neighborhood’ and the ‘Universal Otherhood’: Notes on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21, No.4, 1996.。现有的全球治理模式在应对这些问题时软弱无力,甚至加剧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正如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表明的那样,全球金融市场的运作出现了体制性失效,经济决策核心也存在严重的缺陷。而且,伴随着金融危机,粮食、能源、气候变化等危机接踵而至,暴露了全球治理机制在面对这些挑战时存在的严重弱点(4)卢静:《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这表明存在严重的全球治理赤字现象。治理赤字在全球层面上是指在面临对全人类构成威胁的全球性挑战时,缺乏权威而有效的全球治理活动,有关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要么多样而混乱,要么不成熟、不完善,它意味着“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需要全球治理却严重缺少全球治理,目前的全球性机构没有发挥出全球治理的应有作用”(5)庞中英:《全球治理赤字及其解决——中国在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中的作用》,《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需要指出的是,破解治理赤字,不仅需要新的治理规则和治理机制,更需要新的治理理念。西方国家的治理理念无法克服治理规则非中性引发的治理赤字问题,而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则为破解治理赤字提供了一种可能,通过分析“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全球治理实践领域的具体运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可能将转化为现实。在探讨这种可能性之前,首先有必要厘清治理赤字何以产生的问题,这离不开对现有全球治理规则及其特征的剖析。
一、现有全球治理规则的非中性特征
全球治理本身依赖于各类规则而开展,规则构成了全球治理体系的主体。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指出,治理实质上就是一种规则体系,它依赖于主体间的意义而存在。主体间性意味着只有当绝大多数行为体接受它们的时候,这些规则才能够起作用。同时,治理也是一种目标导向的活动,而这些目标不是来自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责任,也不依赖于国家强制力来推行(6)James N.Rosenau, “Governance,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in James N.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和安东尼·麦克格雷(Anthony McGrew)也指出,全球治理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全球性的、地区性的或跨国性的权威性规则塑造和执行体系,它的主要关注点是不断进化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政治协调体系,包含了从本地到全球的多重层次,并且同时涵盖了寻求实现共同目标或解决共同问题的公共权威和私人机构(7)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Introduc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Power, Autho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p.9.。同政府发布指令不同,治理并不是一种等级制或权威性的命令,而是一种引导机制,它表明一个组织或社会引导自身的过程,而交往和控制则是这种过程的核心(8)James N.Rosenau,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 Governance,Vol.1, No.1, 1995.。这就将治理同政府正式的统治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通过国家强制力来推行自身目标的。由于有了全球治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就可以得到保障。治理和秩序本身就是紧密相连的两种现象,因为作为一种被人们有意识地设计来约束和管理世界事务的活动,治理本身就塑造了全球秩序(9)James N.Rosenau, “Governance,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in James N.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pp.7-8.。
但是,不依赖于国家强制力并不意味着治理规则就可以脱离国家权力影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展全球治理的目的是要在资本的控制下实现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因而需要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而建立一种畸形而非稳定的秩序,并利用这种秩序来参与全球治理(10)胡键:《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的全球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长期以来,受到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霸权的影响,全球治理规则的非中性问题体现得非常明显。所谓非中性,就是指同一种规则或制度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其含义是不同的,而那些从既定的制度当中,或者可能从未来的某种制度安排当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会极力争取或维护对他们有利的制度安排(11)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全球治理中的大多数规则可被理解为尼古拉斯·奥那夫(Nicholas Onuf)所说的“指令性规则”(directive rules),它具有约束性,表达了规则制定者希望他者做出某种行动的意图(12)Nicholas Greenwood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p.87.。借助这类规则,西方国家可以根据自身意志塑造全球治理的运作模式,并要求非西方国家在这些规则提供的框架下,按照西方国家设计的治理蓝图行事。这些治理规则以及这些规则所构成的各类国际制度,无论是肇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各种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制度安排,还是安全、政治、文化和环境等领域的制度安排,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其主要官员任命、“游戏规则”制定乃至具体事务性安排也由西方国家牢牢掌控。历史地看,这些规则或制度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各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时期的产物,因而反映了西方国家的偏好,同时也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于能够最大限度地为它们带来收益的世界秩序的追求,是西方国家的意志和霸权地位的体现。正如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W.Cox)所言,各种制度反映了它们最初产生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关系,并且鼓励不同的人群对于社会秩序所拥有的集体概念同这种权力关系保持一致(13)Robert W.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0, No.2, 1981.。对于那些弱小国家而言,是否加入制度就成为一个两难的选择。由于在制度外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较高,而在制度内又处于不利地位,因而弱小国家无论是否加入制度都无法有效维护其利益。制度中的规则实际上反映了制度内事实上的和潜在的成员国之间的相对权力地位,而这又制约了可能的讨价还价空间并且影响了交易成本(14)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2, No.4, 1988.。
自由主义学者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则指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一种由美国主导的,以西方民主国家为核心的,以开放、谈判和国际制度为主要基础的自由主义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美国是主要的安全和经济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同时也是国际规则和制度的主要制定者和政治互动过程的维护者(15)G.John Ikenberry, “Liberalism and Empire: Logics of Order in the American Unipolar A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0, No.4, 2004.。基于自身强大实力,美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稳定所需的大量公共产品,或者如“霸权稳定论”所言,美国充当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者”(stabilizer)角色,承担了为各类商品提供市场、促进资本的稳定流动等义务(16)Charles P.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Exploitation,Public Goods,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5, No.2, 1981.。客观地讲,美国的行为维护了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了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从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中迅速恢复。美国的主要作用在于推动建设了一批当前仍然在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国际制度,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但是,美国也是这些制度的最大受益者,非西方国家在这些制度中则处于不利地位。例如,世界银行对各国的贷款显著地受到美国利益的影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他国家贷款的条件也因为这些国家同美国的关系不同而有多寡之别(17)何帆、冯维江、徐进:《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条件下,很难达成一种有利于各方的协议。因此,即使是像伊肯伯里这样的自由主义学者也承认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一种交易,美国自愿在一种制度化的政治过程中接受某些约束,而其他国家则同意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承认并且尊重美国的领导地位(18)G.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3, 1998.。可以看出,美国建立一系列规则和制度的首要目标在于维护和增进自身利益,而非为了满足其他国家的需求,更不是为了推动世界秩序向着公平和公正的方向变革。二战后美国的决策者们决心要建立一种可以增进美国利益的世界秩序,使美国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财富和权势,而且可以将其价值观推广到世界的任何角落(19)[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四卷),王琛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通常而言,国际规则在利益分配上对于主导大国的偏向性可以通过例外条款、加权投票、否决权等方式来体现,这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中都体现得非常明显。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本身也包含了很多有利于美国的重要规则,并且美国与盟国的同盟条约也往往包含有不对等内容(20)周方银、何佩珊:《国际规则的弱化:特朗普政府如何改变国际规则》,《当代亚太》2020年第2期。。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后来的世界银行)的设立有助于防止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种国际经济无政府状态,但这些机构也都被美国的巨大经济力量所支配,被一些批评者贴上“美国经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载工具”的标签(21)[美]诺曼·里奇:《大国外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时殷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5页。。作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美国为这些机构提供所需的大量资金,而且对其活动保持与之相称的控制权,人们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服务美国长远利益的初衷已不再有任何疑问”(22)[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四卷),王琛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从理论上讲,任何国际组织或制度都有沦为国家谋求自身私利的工具的可能性,而这主要取决于制度内的运作机制。在一些较为悲观的学者看来,国际制度无法缓解无政府状态对于国家间合作的影响。这是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中,国家总是会关注自己的相对地位,因而会对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给予更多关注(23)Joseph M.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Charles W.Kegley, Jr.(ed.),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Belmont:Wadesworth, 1995, pp.151-152.。作为制度中的主导者,西方大国同样无法摆脱对相对收益的关注,因而会将制度用作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以确保自身可以通过制度获得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收益,这就体现为国家之间在制度内的竞争,即围绕着制度运行的规则而展开的竞争。规则是制度运作的基础,不同国家总会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下竞争规则设定的主导权(24)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国际制度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对制定规则的权力的争夺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同时制度也不是改善国家间福利的公共产品,而是一种私人产品,只能服务于个别或少数国家的利益(25)Shiping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12.。即使在特定条件下某些制度能够提供某些集体福祉,那也是制度内成员长期以来的权力斗争而非协商与对话的产物。
二、治理规则非中性引发的“全球治理赤字”
可以将现有的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以非中性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模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概括为治理赤字。治理赤字表明,现有的国际制度在面临各种或新或旧的全球性威胁或挑战时,要么其活动被个别或少数国家所主导,要么表现出效率低下或软弱无力。治理赤字背后反映的实质性问题是治理中的政治赤字或“民主赤字”,即在目前的全球治理机构当中,非西方国家代表性、发言权的缺失导致了这些机构的低效和失败(26)庞中英:《全球治理赤字及其解决——中国在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中的作用》,《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导致全球治理赤字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现有全球规则具有非中性特征。治理规则的非中性导致了全球治理制度的碎片化。所谓治理制度碎片化,是指具有不同价值观和功能的国际组织出现在治理体系当中,它反映出行为体在权力和偏好上的差异,导致并不存在一种具有显著优势的治理机制(27)王明国:《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与机制融合的前景》,《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 5期。。或者说,在许多政策领域当中都存在着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国际制度,这些制度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和规范、不同的支持者、不同的空间覆盖范围和不同的关注点(28)Fariborz Zelli and Harro van Asselt, “The Institutional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sponses-Introductio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13, No.3, 2013.。由于在非中性条件下规则总是有利于某些特定国家,从而所有有能力的国家都力图通过制定规则来为自身谋求更多利益,进而造成治理体系中各种规则充斥,而国家则会选择性地依靠那些对自身有利的规则。碎片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导致在某一问题领域当中存在着多种规范或制度,从而造成国家的无所适从。同时,某些国家可以利用自己在其中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来推动有利于己的治理规范的产生,而这往往并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意愿。以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为例,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联合国气候机制,而外围则包含了其他各式各样的国际环境制度和非环境制度(29)Fariborz Zelli and Harro van Asselt, “The Institutional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sponses-Introductio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13, No.3, 2013.。这些制度之间甚至会在议题主导权上相互竞争,推动了并不一致的规范的产生,从而对国家遵守规范造成障碍。
治理制度的碎片化扩大了那些拥有较强实力国家的选择范围,使它们可以在小范围内推动达成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协议,而这又增加了国际社会就某个问题达成总体协议的难度。在制度碎片化条件下,那些强大国家可以自行决定哪些规则应当被遵守,哪些协议是重要的,以及这些协议的内涵(30)Karen J.Alter and Sophie Meunier,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Complexit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7, No.1, 2009.。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发达国家通过操控各类规则来为自身攫取更多收益以及限制发展中国家追求自身正当利益的能力,因为这些国家可以凭借其经济和政治优势来自行设计和决定总体上对其有利的规则,彼此之间就涉及某些领域的规则达成交易,并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这种交易之外,同时也利用这些规则来约束发展中国家的行为。很显然,这种治理模式成为发达国家谋求自身利益和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工具,不能反映出国际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利益诉求,自然也无法有效解决当今越来越多的各类全球性问题。
全球治理本身是各国采取“国际集体行动”的领域,它表明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各类全球性危机与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大国或国家集团可以单独地成功解决这些问题(31)庞中英:《全球治理赤字及其解决——中国在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中的作用》,《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但是,全球治理规则非中性所导致的收益分配方面的非中性又使国家之间缺乏信任,进而导致国家之间难以通过有效合作开展集体行动。有效的全球治理依赖于全球信任文化的形成,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全球各区域之间的信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国际社会积累的信任存量或可提供的信任供给也不能满足全球信任需求(32)吴志成、李佳轩:《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中国视角》,《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6期。。在以主权国家和各类政府间国际组织为主体的治理模式中,多边合作是应对各类威胁的主要形式,而它本身就是一种对信任的表达。在一个缺乏信任的世界上,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往往盛行,国家之间不仅在安全等传统的“高级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贸易、金融、环境保护、恐怖主义、能源、传染病等“低级政治”领域都难以通过有效合作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信任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外溢”效应,可以从两个彼此进行合作的国家之间延伸到其他国家(33)Brian C.Rathbun, 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当国家之间缺乏信任的时候,它们就只能相互孤立,或者只同那些它们能够获得足够的可靠信息或拥有特殊友好关系的国家进行合作,这就导致了合作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是这种有限范围的合作,也只是国家在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基础上的权宜之计,而非为了解决国际社会所面对的共同问题而作出的长远规划。
在整体实力不断下降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仍然竭力通过各种手段维护对于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并且压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对于那些仍然可以从中获利的规则或制度,西方国家会竭力促使其保持现状,而对于那些被认为已经不能充分保护自身特权的规则或制度,这些国家则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它们进行改造,以保障自身优势可以长久维持下去。在国际金融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进展缓慢,作为一个整体,西方国家在各关键事项和核心利益方面并没有作出根本性让步。在国际贸易领域,西方国家则认为传统的贸易规则已经“过时”,并通过阻挠世界贸易组织正常运行、交替运用谈判和关税手段迫使他国让步、组建由西方国家构成的排他性的高标准自贸区等方式,极力争夺国际贸易竞争的制高点(34)刘世强:《应对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及其现实意义》,《理论月刊》2020年第3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极少甚至没有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反而要承担发达经济体采取抗疫措施后的负面效应。除去那些既有的、没有根据国际权力结构变化而进行相应调整的领域,气候、网络、海洋、太空、极地等新兴的议题领域则缺乏普遍适用的国际规则,从而导致了各个行为体之间的无序竞争,进而带来了严重的负外部性(35)刘世强:《应对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及其现实意义》,《理论月刊》2020年第3期。。
西方国家的治理理念决定了现有全球治理模式无法克服规则非中性所带来的治理赤字问题。“国家利益至上”是指导这些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扩大本国利益则是这些国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而应对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不过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和手段(36)卢静:《“逆全球化”凸显全球治理赤字》,《人民论坛》2018年第19期。。尽管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着日渐增多的跨越国家边界的问题与挑战,但各国仍然难以形成有效应对与解决这些问题的合力,更多是仅仅以本国利益作为行动参考标准。例如,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采取各种方式对威胁自身安全的恐怖主义严防死守,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在新疆开展的去极端化工作进行无端指责,以民族、宗教、人权等为借口大肆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反恐政策的蓄意抹黑行为,暴露了它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反映了这些国家将恐怖主义活动作为挑拨中国民族关系、遏制中国发展工具的图谋(37)《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发表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721307.shtml,2020-09-05。。再如,在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时,美国单方面强调“美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政策,采取贸易霸凌主义行为,背弃国际承诺,四处出击挑起贸易争端,动摇了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根基(38)《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s://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38292/1638292.htm,2020-09-12。。这些事实表明,主导现有全球治理模式的少数西方大国所奉行的治理理念是以工具主义动机为基础的,而这些国家的自身利益则是衡量治理是否“有效”与治理规则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非西方国家在现有治理体系中被边缘化,其合理利益诉求也没有得到关注。
三、“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的可能
要破解当前存在的全球治理赤字,需要的不仅是新的治理规则和治理机制,更需要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治理理念反映了治理主体的世界观,指导了治理实践活动,并且也影响了治理规则的制定和对于治理成效的评价。现有全球治理理念落后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导致全球治理实践不能满足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客观需求。实践活动需要以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因此理念创新是推动全球治理实践模式变革的基础。事实已经证明,单纯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依赖于非中性规则的治理理念无助于全球治理的完善,相反还会造成各类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导致全球治理日益陷入困境当中。随着中国等非西方国家不断进入全球治理体系当中,全球治理理念变革迎来了新的契机。这些非西方国家必然会将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实践模式、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对国际关系本质的认识等背景知识带入治理体系当中,从而丰富全球治理的内涵。与西方国家不同,非西方国家较少站在“既得利益者”的角度来认识和维护国际秩序,而是希望改造现有秩序中的不合理之处。同时,一种背景知识只有得到国际社会成员国的认可,或者说只有当其转变为国家间共有知识时,才能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观念性力量。共有或主体间知识是维持全球秩序的首要因素,它决定了人们感知、看待和理解各种事物得以安排的方式,并且包含了关于世界政治的运作方式的心理状态、信念体系和共享观念等内容(39)James N.Rosenau, “Governance,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in James N.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p.14.。离开了西方国家集团之外的其他行为体的赞同和参与,任何国际秩序都不可能转变为真正的世界秩序(40)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Global Order: Agenc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8.。
正是基于自身独特的历史经验、社会文化传统和对国际关系本质的认识,中国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41)党的十九大以来,围绕“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学界已经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可以参见王鸿刚《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新时代的机遇与方向》,《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蔡亮《试析国际秩序的转型与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树立》,《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5期;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吴志成、吴宇《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初探》,《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宋秀琚、余姣《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毛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与贡献》,《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6期;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念、进程与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姚璐、景璟《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2期。。这一理念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强调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不能由少数国家所垄断,而是要由世界各国所共享,同时指出各种规则和制度应当建立在世界各国协商共识的基础之上,不能成为少数大国、强国权力意志的体现。“共商”就是集思广益,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商量着办,不能搞“一言堂”;“共建”是指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和能动性,通过合作来应对全球挑战;“共享”则是要让全球治理成果惠及各国,实现多赢、共赢,特别是要让治理成果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42)刘世强:《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布局与能力建设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它反映了治理中所蕴含的关系性,也就是说治理在本质上是治理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模式,只能存在于主体间关系当中。关系性强调实体之间的互动,认为互动所产生的社会结果不能被还原到个体当中,而行动者则会在一种“互动参照框架”中解读行动、建立身份、界定关系、内化相互角色(43)金天栋:《理解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变化:以“关系范式”为研究进路》,《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9期。。它并不排斥规则治理,但也认为需要通过协商的过程来维持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的和谐模式。规则治理可以帮助治理主体塑造共同预期,推动制度性合作,维持秩序并且使治理制度更加有效运作。关系治理则强调治理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平等性,它的基础是国际间的共识,而不是一方强迫另一方接受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规则。具体而言,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它不强调对他者施加控制,而是强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商和谈判;第二,它将治理理解为一种达成协议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本质是动态而不是静态的;第三,被治理的对象不是某一个单一的行为体,而是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第四,与依靠正式规则来约束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行为体的规则治理不同,关系治理是以行为体之间的互信为基石的(44)Qin Yaqing, “Rule, Rules and Relations: Towards a Synthetic Approach to Governan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 No.2,2011.。在中国看来,国家不论大小、贫富或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都应当平等参与决策。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不能由少数国家所垄断,治理成果也不能被少数国家所独占。要破解治理赤字,就要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推动治理规则民主化(45)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3/26/c_1124286585.htm?agt=1887,2021-02-25。。“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强调要将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并重,从而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可能。它突出了治理的协商本质,强调各国在治理中的共同责任,同时又承认各国在发展程度和阶段方面的差异,尊重各国发展本国社会、经济、文化的权利,注重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
(一)突出全球治理的协商本质
如果说治理赤字最主要体现为西方国家垄断了对于各类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声音严重缺失,那么协商治理无疑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最有效途径。同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宗旨是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46)张宇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86页。。这也需要尊重各国参与全球性事务的权利,在全球治理中赋予各国平等话语权,突出治理中蕴含的协商本质,而“共商共建共享”无疑满足了这一条件。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经指出,有效的原则必须是通过在其中寻求达成协议的各方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协商来建立的(47)Andrew Linklater,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1, p.50.。在这种协商的过程当中,不存在一方试图说服另一方的问题,因为双方都准备接受对方的观点,也都可以被对方所说服。同时,协商的各方也需要认识到,他们的观点也可能是有缺陷的,反映了他们自身的个体或文化偏见,倾听对方的观点则可以使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更加透彻和全面。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协商各方的相对权力对比,而是“更好的论据的力量”(the force of the better argument),也就是那些可能受到规则或规范影响的人们之间的共识取代了命令和指令成为这些规则或规范具备有效性的决定性因素(48)Andrew Linklater,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1, p.51.。在达成这种共识的过程当中,每一方都被允许平等地参与对话,并且每一方都可以对他人的主张提出疑问,也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态度、欲望或需求(49)艾四林等:《民主、正义与全球化——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种制度是否具有合法性,在根本上取决于这种制度被普遍认同的背后所蕴藏的理由,而各种国际制度也不能例外。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讲,就是“一种或多或少以商谈的形式、在公开争论中产生的公共意见所具有的影响,当然是一种可以起举足轻重作用的经验变量。但只有当这种舆论政治影响通过民主的意见形式和意志形成过程的建制化程序的过滤,转化成交往权力、并进入合法的立法过程之后,才会从事实上普遍化的公共意见中产生出一种从利益普遍化的角度得到了检验、赋予政治决策以合法性的信念”(50)[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59页。。现有的全球治理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大国的价值观和利益观的体现,是这些国家凭借自身权力优势将自身理念强加给非西方国家的产物,因而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在治理理念上缺乏共识。如果不能以共识为基础,任何全球治理理念都不可能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普遍拥护和尊奉,也就难以发挥有效的影响力(51)卢静:《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因此,将协商引入全球治理当中,可以弥补现有的治理规则和制度的非中性缺陷。治理制度需要具备合法性才能有效运作,而民主商议则可以提供这种合法性,因为它表明制度所作出的决定是在追求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并且也建立了一种“话语责任”(discursive accountability)(52)Ben Thirkell-White, “Hard Choices in Global Deliberative System Reform: Functional Fragment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osmopolitan Republicanism”,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10, No.2, 2018.。同全球治理的整体性相一致,商议也具有一种整体性质,或者说它需要在公共领域中发生。公共领域一方面保证了公共政策可以得到公众的批评和审查,另一方面也将碎片化的利益集中在一起,并且通过拥有生活经验的具体人群来商议哪种利益是可以共享的(53)Ben Thirkell-White, “Hard Choices in Global Deliberative System Reform: Functional Fragment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osmopolitan Republicanism”,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10, No.2, 2018.。因此,在全球治理中,决策制定应当是以“争论”(argumentation)为基础的,它确保了所作出决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54)Erik O.Eriksen,“Getting to Agreement: Mechanisms of Deliberative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10, No.3, 2018.。具体而言,争论应当是一个“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的过程,它包含三个阶段:首先,需要提出一个主张,它表明某些事情是需要被做的;其次,需要在公共领域中向第三方证明这个主张的正当性;最后,如果可以证明该主张的正当性,那么就会导致公众的学习过程,也就是公众态度的变化(55)Erik O.Eriksen,“Getting to Agreement: Mechanisms of Deliberative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10, No.3, 2018.。也就是说,全球治理中的协商或争论的目标是在各国之间达成共识,而共识则涉及态度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推动国家态度变化的力量不是权力政治或经济利益,而是各国所提出主张的正当性和说服力。事实上,在世界政治领域总是涉及正当性——也就是集体层次上对于理性的管理——问题。正当性是达成协议的必要条件,它是通过主体之间的对话来实现的(56)Erik O.Eriksen,“Getting to Agreement: Mechanisms of Deliberative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10, No.3, 2018.。在全球治理中,争论是实现正当性的先决条件,它表明这种治理能够广泛代表国际社会成员的意志和利益。争论本质上就是一个协商和对话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个治理主体可以平等地交换论据,即每一方都可以提出自身论据并准备接受对方的合理论据,从而使就相关问题形成共识成为可能。
以“共商共建共享”中蕴含的协商本质为基础,中国积极参与周边地区和全球层次上各类治理活动。在地区层面上,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的外交方针,主张“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同周边国家协商解决各类问题,推动中国发展惠及周边。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积极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的新架构。中国认为安全应当具有普遍性、平等性和包容性,不能以自身安全为由来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不能由任何国家垄断地区安全事务,各国都平等地拥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并且应当尊重各国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合理照顾各方安全关切(57)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112页。。在全球层面上,中国主张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把握的基本取向是“平等协商,合作共赢”,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小或强弱,都应该得到尊重。这种共同体并不是大一统的体系,而是在尊重各国合理利益关切、尊重各方差异性的基础之上,促进各国家、各国际组织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加强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抵制相互敌视、相互排斥、相互取代(58)颜晓峰、常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建构与实践要求》,《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这些倡议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受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2017年2月,“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标志着这一理念进入联合国决议(59)《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211/c1002-29074217.html,2021-02-25。。同年11月,“人类命运共同体”又被写入“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联合国安全决议当中(60)《“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写入联合国决议》,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1103/c1002-29624208.html,2021-02-25。。中国在各类治理活动中遵循协商共议原则,不把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他国,尊重他国合理利益诉求,促进各国在治理中实现共赢。在协商基础上,中国已经同众多国家建立了以共同利益为准则,以促进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国际合作为路径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伙伴关系网络(61)门洪华:《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在伙伴关系中,国家无论大小或强弱都是平等的伙伴,中国尊重中小国家的独立自主性,尊重它们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充分照顾它们合理的利益关切,也不会把自身的意志强加给它们。这种网络关系对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实现各国的互利共赢具有重大意义。
(二)坚持正确义利观,强调大国提供公共产品的特殊责任
全球治理也是一个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治理赤字的主要表现之一即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严重短缺,无法涵盖不断宽泛和日益新生的问题领域。相对于国际公益而言,国家的优先考虑事项仍然为本国的私利(62)吴白乙、张一飞:《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学术月刊》2020年第1期。。约翰·鲁杰(John Gerard Ruggie)指出,纯粹的公共产品是可以由一个共同体当中的成员共享的,它的收益不能在这些成员之间进行分割,并且一个成员对它的消耗不会减少其他成员对它的消耗。具体而言,公共产品主要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一种“联合供给”(joint supply)的产物,也就是说它一旦被生产出来,就可以同时被所有的成员享用;第二,它不能排斥他者享用这种公共产品所带来的收益,也不可能要求他者支付享用这种收益的成本(63)John Gerard Ruggi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ohn Gerard Ruggie (ed.),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49-50.。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各国均有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但是,公共产品所具备的普惠性和收益共享性,使得那些即使没有为提供这些公共产品承担成本的国家也可以享受公共产品所带来的收益,从而导致国家之间经常陷入经济学家所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这是因为尽管一个集团的全体成员对于获得集体利益有着共同的兴趣,但是它们却对为获得这一集体利益而付出的成本没有共同兴趣,并且每一个成员都希望别人付出全部成本而自己可以分享收益(64)[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 16页。。在全球治理中,受到“集体行动的困境”的影响,国家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各自为战”的现象也很普遍,这就经常导致相关领域的治理陷入困境。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途径是大国首先承担起贡献公共产品的责任。一方面,相比于一般国家,大国拥有更多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因而有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能力基础;另一方面,大国通常也可以比一般国家从公共产品中获得更多收益,因而主动贡献公共产品对大国自身也是有利的。例如,所有国家都可以从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和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中获益,但是经济大国在这种金融秩序和贸易体制中显然比一般国家收获更多,因为它们对于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往往更深。国际关系学者也指出,当代全球秩序正在变得越来越多中心化,其中全球性霸权国家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减弱,而诸多地区大国则需要承担起更多责任以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具体而言,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意味着约束对武力的使用、尊重国家间协议、承认小国的权利与地位、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尊重主权和其他国际社会的基本原则等。在这种秩序中,所谓的“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即美国依赖其霸权国地位使自身免于遵守很多它希望其他国家遵守的规则——将不可能继续存在,而诸多大国则需要更加约束自身行为,并更多地参与到对共同问题的解决中(65)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p.300.。
作为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大国,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主动参与到对各类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中。中国在国际合作中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的合作模式,充分照顾对方利益,坚持“独行快,众行远”原则,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66)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53页。。中国主张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惠及他国人民,增进全球福祉,促进共同繁荣(67)徐进:《理念竞争、秩序构建与权力转移》,《当代亚太》2019年第4期。。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提出正确义利观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这一义利观的提出是为了破解当前全球治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方面,全球化的非均衡发展导致国家之间、特别是南北国家之间在人均收入、资源利用、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不断拉大,进而造成各国之间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平等。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奉行霸权主义,利用自身对国际规则的控制不对等地汲取外部资源以维护优势地位,并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挑起国际争端,摧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努力(68)刘世强:《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布局与能力建设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要缩小南北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使南方国家不再成为全球化所造成的各类负面后果的主要承担者,就需要改变这种现状,为发展中国家借助全球化促进自身发展创造条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自然需要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促进全球公益,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善治方向发展。第二,这一义利观也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在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中对于正义的追求。石之瑜(Chih-yu Shih)指出,中国文化强调“义”的重要性,它的内涵包括信任、真诚、正义和相互帮助等,其最高要义则是在帮助朋友或追求正义时不考虑自身利益,这也成为中国人协调人际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69)Chih-yu Shih, 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Psychological View,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0, p.50.。中国因而在全球治理中主张要特别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必要支持。为此,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使中国的发展可以带动沿线国家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一带一路”实质上是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中国智慧转化为新多边主义的世界智慧,将双赢、多赢上升到全方位开放的共赢主义,从而实现人类公平发展、和平发展、包容发展(70)王义桅:《“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的天下担当》,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这一倡议深刻体现了和平、合作、共赢的时代内涵,促进沿线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71)王志民、陈宗华:《“一带一路”建设的七年回顾与思考》,《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1期。。以“一带一路”为核心,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当中,在国际社会中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促进各国均衡发展、推动全球问题解决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主张以公平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破解治理赤字同样离不开公平,“共商共建共享”还突出了全球治理中的公平原则。所谓公平,就是要考虑到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强弱之分,承认这种差异是由不平衡发展规律决定的,因而也不可能完全消除(72)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同西方国家片面强调“平等”不同,中国更加注重协调强者与弱者、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关系,强调要消除由于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冲突。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由于能力不同而处于不同地位,片面强调平等原则就会使弱国陷入不利境地(73)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146.。全球治理依赖于各国提供公共产品,共担治理责任,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治理中所承担的责任是有区别的。从历史角度看,西方发达国家是造成当前各种全球性问题的主要“始作俑者”,理应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更大贡献。片面地强调所有国家都要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同样程度的贡献,无疑是忽视了这些问题的本质和导致它们产生的原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动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中心、边缘和半边缘地区,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扩大了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而中心国家的各种优势则一直在扩大(7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罗荣渠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464页。。西方国家同样是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等问题的主要推动者。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都出现过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西方大国出于利己主义动机对中东、西亚、北非等地区局势的介入,也是导致这些国家难民涌现的主要原因之一。从现实角度来看,同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不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本国社会经济、减少贫困、增进国民福祉。在这种前提下,要求发展中国家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同西方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责任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
中国坚持全球治理应当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基础,也即在坚持各国均应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的同时,进一步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各类全球性问题上应承担的不同历史责任,承认二者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以及所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这一原则的现实意义在于国际社会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大国有时存在某些不切合现实的预期,这就对这些国家参与全球治理造成困扰,因而需要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更鲜明地维护自身合理利益。以中国为例,中国自我坚持为发展中国家,却又被某些国家认为是“大国”,因而具有“双重身份”(75)李少军:《论中国双重身份的困境与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4期。。这种双重身份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带来的困扰在于,全球大国身份要求它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多贡献,承担更多责任,而发展中国家身份又要求中国从自身条件出发,避免承担“过多”责任(76)Il Hyun Cho, “Dual Identity and Issue Localization: East Asia in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Vol.19, No.4, 2013.。事实上,西方国家提出所谓“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动机是非常自私的,其意图是迫使中国接受由它们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和秩序,以免损害它们的既得利益,同时帮助它们分担维护现有秩序的成本,甚至暗中借“国际责任”的名义抑制中国经济发展(77)程国花:《负责任大国:世界的期待与中国认知》,《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自然不能接受发达国家这种承担“无限责任”的要求。
在全球治理的诸多领域,中国都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基础,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合理利益发出声音。在气候治理领域,中国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利益,特别是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中国主张各方要共同维护《巴黎协定》成果,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其道义性话语权不断提升(78)李强:《“后巴黎时代”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构建: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国际论坛》2019年第6期。。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反对发达国家集团为维护自身优势而质疑某些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主张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充分参与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解决世贸组织内部关于不同国家地位的争议(79)彭德雷、周围欢、屠新泉:《多边贸易体制下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研究——基于历史、现实与规范的多维考察》,《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1期。。2019年,中国同印度、南非、委内瑞拉、巴基斯坦等国联合向世贸组织提交了《惠及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对于促进发展和确保包容的持续相关性》文件,反驳了发达国家某些无理要求(80)彭德雷、周围欢、屠新泉:《多边贸易体制下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研究——基于历史、现实与规范的多维考察》,《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1期。。同时,中国也从不回避自身责任,在世贸组织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让利,主动放弃某些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中国还积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价值链,增强类似“中国项目”(China Programme)的技术援助的针对性和具体性(81)徐清军、高波:《WTO改革的发展议题之争及解决之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2期。。中国主张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奉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多边主义为基础,尊重各国发展差异,将全球治理的宏观目标同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相结合,根据本国国情参与全球治理,承担自身责任。
四、“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运用
在前述可能性的基础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对于全球治理实践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积极致力于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运用于全球治理实践之中,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贡献公共产品。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较为独特的角色。这也要求中国去维护和争取自身合理权益,仅仅将希望寄托于其他国家在制定规则时考虑中国的情况,或者只谈学习、遵守规则,不谈修正、制定规则都是不现实的(82)赵龙跃:《制度性权力:国际规则重构与中国策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当然,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面对西方大国的挑战。那些西方大国一方面希望中国承担更大责任,为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进程作出更大贡献;另一方面限制中国在各种治理制度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以维护自身主导性(83)庞中英:《重建世界秩序:关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因此,中国需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治理中的合理利益,促进全球治理模式向着更加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基础上构建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关切并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实践模式,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公共产品就是至关重要的。
(一) 借助“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化的过程,并非一直由经济主导,政治、文化因素有时也扮演主导角色。”(84)[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黄中宪、吴莉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85-486页。但是,不可否认,经济领域仍然是当前全球治理当中最为活跃,也是各国参与度最高的领域。中国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促进各国在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开展互利合作,另一方面也要推动新的国际多边合作模式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打造新的国际制度。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中国为克服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谷所作出的贡献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在金融危机后的历次20国集团会议上,中国都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强调世界各国要加强协调、密切合作、共渡难关,强调20国集团的制度化建设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85)蔡拓:《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中国也为推动金砖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协作作出了重大努力,并促成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顺利开业。该机构旨在支持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和前沿技术发展,其核心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为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财政援助,以实现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86)参见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网站,https://www.ndb.int/about-us/essence/mission-values/,2020-09-20。。这一多边金融银行的开业,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投融资便利,改善全球金融治理模式,降低成员国对外贸易中的汇率风险以及环保和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一带一路”则是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付诸实践的核心平台,它倡导“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商量着办”(87)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629/c1024-25213364.html,2020-09-20。。在一定意义上,“一带一路”是一种“根本制度”(fundamental institution),即国家用来解决与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共存相关的协调和协作问题的根本实践规则(88)Christian Reus-Smit, “The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Nature of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4, 1997.。它不同于世界贸易组织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类由某些国家出于特定目的而建立的具体制度或机制,而是寻求从更加宏观的层次上解决无政府状态下在国际社会中的共存与合作问题。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中,中国从不谋求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计划和发展战略强加于别国,而是寻求将本国政策同他国政策对接,尊重各国现有的发展计划和政策,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从本质上讲,“一带一路”要求互联互通。只有实现了互联互通,才能形成各国共同发展的态势。从理念上讲,“一带一路”反映了国家间的共生而非排斥关系。共生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长期以来所倡导的理念,正是在共生的基础上,中国才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谐世界”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所谓共生,是指共生单元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照一定的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而“一带一路”中的合作问题实质上则是区域合作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结合,是在合作过程中关注合作主体的协调性和互利性(89)衣保中、张洁妍:《东北亚地区“一带一路”合作共生系统研究》,《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3期。。它关注国家间的协调互补关系,认为不同国家的发展战略、发展计划不应当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社会发展程度有所不同,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但是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以获得共同收益、建立国家间协调机制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等方面拥有共同愿望,因此可以通过政策协调与对接形成相互补充的共生关系。
从实践角度来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构建的地区互联互通模式也初具形态。当前,“一带一路”已经完成总体布局和机制规范等方面的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大写意”,正在设施联通、产业融合等方面绘制精谨细腻、高质量发展的“工笔画”,已经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新平台(90)王志民、陈宗华:《“一带一路”建设的七年回顾与思考》,《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1期。。中国同沿线国家通过产业合作、建设工业园区等方式,推动了相互间的互利共赢。其中,赞比亚的蒙内铁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区、白俄罗斯的“巨石”工业园区和墨西哥华富山工业园区等成为中外合作成功的典型案例(91)《“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行稳致远 砥砺前行》,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8/09/c_1123246444.htm,2020-10-25。。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一带一路”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世界也将从快速发展的“一带一路”中获益,因为这一倡议可以推动“能够产生包容的、可持续的和持久的社会和环境收益的经济增长”(92)《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帮助缩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巨大资金缺口》,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zh/news/sustainable/china-belt-and-road-forum.html,2020-09-26。。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向纵深发展,如提出建立“冰上丝绸之路”倡议等。可以说,“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担当。它不是中国利用经济手段干涉他国发展模式或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势力范围”的工具,而是借助中国自身的发展来带动沿线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发展,使各国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二)立足周边,积极推动区域治理发展
无论是推动全球治理变革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都应当是基本立足点,周边地区的安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直接影响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在当代世界政治中,伴随着全球化的一个平行趋势是“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它一方面承认地区大国可以在本地区发挥特殊影响力,另一方面认为一个地区也应当保留自身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多元化国际合作(93)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02.。对于中国而言,为地区发展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让本地区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成果,也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重要途径。
同全球层次相比,中国可以更深入地参与到地区治理当中。在全球层次上,中国主要参与经济治理,而在地区层次上,则可以进一步参与到安全治理等具有较高敏感性的领域当中。中国处理周边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突出“亲、诚、惠、荣”方针,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强调要按照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使周边国家可以受惠于中国的发展,同时也强调包容的思想,以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94)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6页。。除积极推动建立自贸区等经济领域活动之外,中国还积极为地区安全提供公共产品。例如,结合恐怖主义活动新动向,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积极推动反恐和禁毒双管齐下的系统性工程,以应对恐怖主义和贩毒相互勾结的趋势(95)张宇燕主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5页。。自2006年起,中国还连续举办香山论坛,使之成为一个各国军方人员和学者共同参与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平台。中国建立香山论坛的目标是以对话促合作、以合作促和平、以和平保发展,维护亚太地区持久安宁,它体现了各国在安全领域中的责任共担,也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96)《国防部:北京香山论坛已成具国际影响力高端安全对话平台》,人民网,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9/1031/c1011-31431325.html,2020-09-30。。在东南亚地区,中国积极推动“10+3”机制发展,促进该机制向东亚峰会转变。中国尊重东盟在东亚峰会的主导地位,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筑牢经济、安全和人文这三大东亚峰会支柱,以推动区域合作全面协调发展(97)张清敏、李秀铎:《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1978-2018)》,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338页。。总体上看,在处理同周边中小型国家的关系时,中国注重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互利甚至是适当向他国“让利”,以推动地区治理深入发展。
当然,立足于周边和地区的治理模式并非中国首创,部分西方国家也同样重视地区的作用。例如,作为南欧国家的意大利长期将参与全球治理的重点放在地中海沿岸,并试图利用欧盟创始成员国身份和特殊的战略区位,推动欧盟和北约的集体决策向该地区倾斜(98)韩笑、吴志成:《意大利的全球治理理念与战略》,《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4期。。同意大利类似,德国也充分利用自身经济优势,将推动地区一体化作为自身全球治理战略的核心,积极承担地区责任,并为此采取了诸多行动,包括为欧元建设提供核心支持、在金融危机期间积极维护欧元稳定以及承担最大份额援助欧元区重债国家等(99)吴志成、王亚琪:《德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作为一个整体,欧盟的全球治理理念也是以区域治理为基础的,积极推动区域治理同多边主义有机结合,将欧盟内部的多边主义同整个欧洲乃至全球层次上的多边主义连接起来,加强跨区域多边合作,促进自身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100)杨娜、吴志成:《欧盟与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比较》,《欧洲研究》2016年第6期。。但是,当前欧洲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时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一方面,欧盟国家长期以来未能摆脱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发展缓慢,同时又面临诸多内部问题,欧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正在下降。另一方面,欧盟内部的民粹主义势力也在发展壮大,从而增加了欧盟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除英国选择退出欧盟之外,在法德等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倡导国内部,民粹主义思潮也得到越来越多支持。在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利用国内对全球化的悲观情绪,积极宣扬“法国优先”主张。在德国,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旗帜,也受到越来越多支持(101)王瑞平:《对当前西方“反全球化”浪潮的分析:表现、成因及中国的应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6期。。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欧盟在参与全球治理时过于强调欧盟经验和欧盟标准的普世意义,主张按照欧盟模式制定全球治理规则。例如,在环保领域,欧盟积极在全球层次上推行欧盟标准,并将环保标准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先决条件,迫使发展中国家采取较为严苛的环保政策(102)杨娜、吴志成:《欧盟与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比较》,《欧洲研究》2016年第6期。。从本质上讲,这仍然是以西方国家所偏爱的规则为基础的治理模式,忽视了其他国家的发展现状和客观需求。相比之下,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基础的治理模式给予其他国家充分尊重,不为合作预设人为障碍,不干涉其他国家国内政策,因而是一种以地区国家为中心而非以自身为中心的治理模式。
(三)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作为负责任大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中国应当并且事实上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自2019年起,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分摊比例已经上升至12%,维和摊款比例也上升至15.2%,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联合国会费出资国和维和摊款国,而中国也将其作为应尽的财政义务(103)《外交部就中国将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等答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gov.cn/xinwen/2018-12/24/content_5351756.htm,2020-10-02。。在安全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还为维和事业提供了大量资金和技术援助,积极派遣工程、运输、医疗人员参与维和行动。中国主张全面恪守维和基本原则,完整贯彻执行安理会决议,并将维和行动同预防性外交、和平建设、政治斡旋、民族和解、民生改善等相互配合(104)《习近平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并发表讲话》,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5308.htm,2020-10-02。。
在经济发展和减贫领域,中国一方面大力发展国内扶贫事业,使国内贫困人口大量减少,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为此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并倡导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105)张清敏、李秀铎:《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1978-2018),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333页。。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尽管自身面临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压力,中国仍旧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治理,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基础,中国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到45%(106)《中国愿意、可以也有能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ex.cssn.cn/jjx/xk/jjx_yyjjx/csqyhjjjx/201801/t20180118_3820422.shtml,2020-10-05。。中国还主动开展气候外交,同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先后发表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107)张清敏、李秀铎:《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1978-2018)》,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334页。。中国一方面在国内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另一方面主张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事业,要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实现更高水平的全球可持续发展(108)《习近平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2/01/c_1117309626.htm,2020-10-06。。
在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方面,中国致力于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同中国类似,欧盟也强调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对于中国为联合国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鼓励中国支持联合国的改革和改善全球治理框架(109)洪邮生、李峰:《变局中的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的重塑——新形势下中欧合作的机遇和挑战》,《欧洲研究》2018年第1期。。同美国相比,欧盟对待中国的态度相对积极,愿意同中国保持对话和接触,而不是将中国视为威胁,也不认为强大的中国将会同西方国家的全球利益发生直接冲突(110)杨娜、吴志成:《欧盟与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比较》,《欧洲研究》2016年第6期。。对此,习近平也指出,中欧在支持联合国积极发挥作用、推进全球治理完善、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多边主义等方面拥有广泛政治共识和坚实合作基础(111)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3/26/c_1124286585.htm,2020-10-09。。此外,诸多发展中国家也重视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因而也同中国在多个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
结 论
20世纪80年代,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等人曾经将“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定义为“一个国家群体,它们不仅仅在一方的行动是另一方需要加以考虑的因素的意义上构成了一个体系,而且通过对话建立了约束它们相互间关系的规则和制度,并且就这些规则和制度达成共识,同时承认它们在维护这些制度性安排方面拥有共同利益”(112)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1.。在当代,随着全球化在各个领域不断深入推进和国家间相互依赖不断增强,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比布尔为“国际社会”下定义时更广泛、更重要。由于各种跨国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当前的国家间关系已经超越了“社会”维度而体现出了“命运共同体”的特征。
当前,国际社会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效果仍不尽如人意,也尚未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合力。这是由于现有治理模式以西方大国主导的规则为主,治理规则又具有非中性,这就导致治理赤字问题的产生。要解决这一困境,推动治理体系变革,首先需要创新治理理念。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施动者,其对世界事务的参与不仅对于它自身,而且对于国际共同体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离开了中国,任何国际制度的有效性都会大打折扣(113)Pichamon Yeophantong, “Governing the World: China’s Evolving Conceptions of Responsibili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6, No.3, 2013.。正是基于这一事实,中国需要提出既能充分反映自身价值诉求,同时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利益,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治理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全球治理模式变革。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是具有创新性的理念,可以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观念性力量,它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可能,反映了全球治理中所蕴含的关系性,强调相互尊重、协商、互信、互助等因素在治理中的重要性。这一理念体现了全球治理的实质特征和内在价值,突出了各国在治理中的共同命运、共同责任与共同利益。通过将这一理念运用于实践之中,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