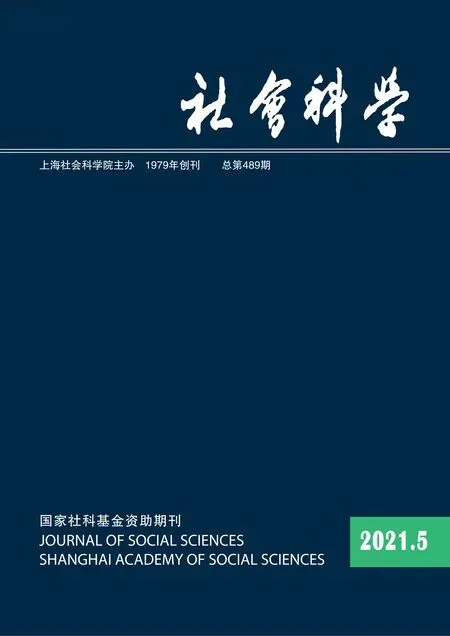大国竞争时代美国科技创新战略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以国家安全创新基地为中心
刘国柱 史博伟
近代以来,科技实力一直都是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近几十年来,随着人口数量、国土面积等传统国力组成变量的重要性相对衰减,以及技术迭代的时间间隔变短、速率加快,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实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科技创新方面的竞争已成为当代大国竞争中最为关键的领域,更加有效创新的一方无疑将占据大国竞争的优势地位。在2017年推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美国政府推出了“国家安全创新基地”(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的概念。此后,围绕这一概念,美国战略界相继发布了系列研究报告,美国立法机构也围绕这一概念推出了系列相关立法。拜登更是将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视为他担任总统的基石。可见,这一理念已经成为美国战略界的共识。被美国视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对美国的新国家安全观应有全面的认识,对大变局下美国政府主导的科技创新战略发展趋势更要有敏锐的感知。
一、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内涵及产生背景
国家安全创新基地不是具象的物理性存在,而是一种新的大安全概念,主要涉及科学与技术的创新以及相关的理念创新和方式创新。它的着眼点不是微观的战术设计,不是某一关键科学领域或技术领域的创新安排,而是致力于制定宏观的战略规划,是将影响当今时代的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都囊括在内的全方位创新提升计划。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提出了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概念,指出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是“美国的知识、能力和人员的联动网络,包括学术界、国家实验室和私营领域在内,它将创意转化为创新,将发现转化为成功的商业产品和企业,保护并提高美国的生活方式”(1)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December, 2017。根据该文件中关于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解释,里根研究所认为,该基地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包括资金、研究、知识、能力、政策、刺激因素、人才,其更详细的组成部分包括国家安全机构和组织、国家实验室、联邦资助的研发中心、大学附属的研发中心、高等学术机构、传统的国防承包商、商业部门、风险基金、美国盟友与伙伴国的创新体系。。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概要》认为,“保持国防部的技术优势,需要工业文化改革、投资资源以及保护,而这一切须通过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来实现”。因此,该战略谋求的一个重要国防目标即“建立一个无可匹敌的、能够有效支持国防部行动、能够获取安全和偿付能力的二十一世纪国家安全创新基地”(2)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January, 2018.。这两份政府文件基本勾勒出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主要内涵和重要目标。
科学、技术与创新是人类无止境的研究事业。1945年,美国著名科技管理学家、时任白宫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主任万内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呈递给杜鲁门总统一篇名为《科学:无限的边疆》(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的报告中,将美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形容为在“无限边疆”上的开拓。布什在报告中谏言,随着传统边疆的消失,美国必须在科学这一富含无穷创造力的新边疆上,加快开拓的步伐(3)“Endless Frontier”一词首次出现在这份报告中。该报告的中译本将其翻译为“没有止境的前沿”,但本文认为,该词更为合适的译法为“无限的边疆”,因为布什显然参照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于美国学术界并被政界广为接受的边疆理论。参见[美] V.布什等《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关于战后科学研究计划提交给总统的报告》,范岱年、解道华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Vannevar Bush,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5。。借2020年布什报告发布75周年之际,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重温并宣布继承布什报告的精神,将美国未来75年的科学研究事业同样视为在无限边疆上的征程(4)Steve Olson, The Endless Frontier: The Next 75 Years in Science,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20.。从另一方面来看,开拓无限边疆含有抢占科技制高点、侵噬他国创新优势、控制世界所有关键技术领域的意味。在当前大国竞争回潮的背景下,借助布什报告和2020年5月美国参议院推出的旨在提升美国科技实力的《无限边疆法案》(The Endless Frontier Act),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表述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是美国意图开拓科学、技术、创新领域的“无限边疆”,将美国打造成全世界的创新中心,保证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虽然该基地并不是指具体的基地,但其概念却是对具象性基地的抽象化理解,是将美国几乎所有科技创新领域的资源视为一个源源不断产出创新果实的基地。它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战略历史上早已存在的诸多基地概念。美国之所以下定决心制定动员其科技创新全部力量的宏大战略,源自它对现代技术发展趋势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环境的危机认知。
(一)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渊源
“Base”一词易被中文译者视为“基础”之意,但它更精确的汉语译法应为“基地”,带有科技创新源泉之地以及竞争性、防护性堡垒的含义。基地概念自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在美国战略界被频繁探讨、论证和强调,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的专家安德鲁·亨特(Andrew Hunter)甚至将2018年视为“工业基地之年”(The Year of the Industrial Base)(5)Andrew Hunter, “The Year of the Industrial Bas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1,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year-industrial-base.。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概念的产生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在美国工业产业的历史上,存在着大量“含基地之名、有相似含义”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的内涵丰富程度和触及领域的广度,都不及国家安全创新基地。但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概念内涵,部分是美国战略界整合各类基地概念形成的结果,因此,这些基地概念可以为透视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本质提供独到的视角。
美国国防工业领域就常提出诸多技术基地概念,其中最为有名、同时也是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意涵重要来源之一的是“国防工业基地”(Defense Industrial Base)。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曾详细阐述过美国国防工业基地的历史演变(从独立到当代):美国独立后各州的弹药库与海军建设园构成了美国国防工业基地的第一批元素;一战前后,以塞缪尔·莫尔斯、亚历山大·贝尔、托马斯·爱迪生、古列尔莫·马可尼、亨利·福特为代表的发明家使用的新技术,用以支援盟国和供给美国远征军的大规模军事生产设施组成了国防工业基地的主要部分;二战期间的美国军工厂、海军基地、临时生产军事物资的私营企业等是国防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单元;冷战时期的战术武器生产、战略武器生产、核工业、太空项目、新国防科技等,在更大程度上丰富了国防工业基地的内涵(6)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U.S.Defense Industrial Base”, Defense Manufacturing in 2010 and Beyond: Meeting the Changing Needs of National Defens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1999, pp.87-94.。已经立法50余次的《国防生产法案》(Defense Production Act)都会直接点名,或以间接的方式谈及国防工业基地,强调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1993年,美国政府问责局(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国防工业基地是“人员、机构、技术专业知识、设施设备的集合”,负责设计、发展、制造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事业所需的武器和辅助性国防设备。该基地大致分为三个功能性组成部分:研发、生产、维护与修缮,每个部分都包含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雇员与设备(7)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An Overview of an Emerging Issue”, March, 1993, 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uiug.30112033980506&view=1up&seq=1&q1=national%20technology%20and%20industrial%20base.。每一时期对国防工业基地的阐释都不尽相同,但国防工业基地作为国防产业联合体的本质未曾改变。美国国防工业协会(National Defense Industrial Association)自2020年1月起每年发布报告,专门评估美国国防工业基地将美国及其盟友武装起来应对可预见挑战的能力。该协会近几年频繁表示,国防工业基地面临史无前例的危机,其2020年关于国防工业基地的首份报告,将该基地各项指标的综合评级定为C级(差),并担心它有继续向下滑落的趋势(8)National Defense Industrial Association, “Vital Signs 2020: The Health and Readiness of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January, 2020, https://www.ndia.org/-/media/vital-signs/vital-signs_screen_v3.ashx?la=en.。
国防工业基地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专有名词,“国防技术与工业基地”(The Defense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Base)、“国家安全工业基地”(National Security Industrial Base)(9)U.S.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Building Future Security: Strategies for Restructuring the Defense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Base”,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une, 1992, https://www.princeton.edu/~ota/disk1/1992/9205/9205.PDF.其中,可以明显看到国防科技与工业基地与国防工业基地两词的交替使用情况。Defense Science Board, “Creating an Eff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Industrial Base for the 21st Century: An Action Plan to Address the Coming Crisis”, July, 2008, https://apps.dtic.mil/dtic/tr/fulltext/u2/a485198.pdf; Michael O’Hanlon, “National Security Industrial Base: A Crucial Asse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se Future may be in Jeopardy”, Brookings Institute, February, 2011,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the-national-security-industrial-base-a-crucial-asset-of-the-united-states-whose-future-may-be-in-jeopardy/.在国防部与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两篇报告中,可以观察到国家安全工业基地与国防工业基地两词频繁的交替使用。等用词,也会出现在政府或智库的报告文件中,用来指代国防工业基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9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为应对冷战结束对国防工业基地的影响,提出“国家技术与工业基地”(N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Base,NTIB)。该基地被《美国法典》明确定义,目前是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后者意涵的重要来源。它由活动于国家安全、军民两用技术研发、生产、维护以及相关领域的人员和组织构成(具体包括政府部门、大学、非盈利研究实体、非传统的商业项目承包商、进行商业研究、军事研究与商业生产的私营承包商等),其目的是为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目标提供助力,包括:为军事行动供给技术;进行高级研发和先进系统研发,确保美国军事力量的技术领先优势;争取可靠的关键物质资源;为战时和国家紧急状态时的行动做好工业准备。在诞生之时,国家技术与工业基地就被设计成一个国际间合作概念,包括美国与加拿大。近年来,该基地的参与国数量已经被国会拓展,英国和澳大利亚被笼络加入进来(10)Heidi M.Peters, “Defense Primer: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Bas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31, 2020, https://fas.org/sgp/crs/natsec/IF11311.pdf,国会研究服务局采用的这一概念取自《美国法典》;Rhys McCormick, Samantha Cohen, Andrew P.Hunter, etc., “N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Base Integration: How to Overcome Barriers and Capitalize on Cooperati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2018,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180307_McCormick_NationalTechnologyAndIndustrialBaseIntegration_Web.pdf;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7”, December 23, 2016, https://www.congress.gov/114/plaws/publ328/PLAW-114publ328.pdf。。自成立至今,国家技术与工业基地一直都在有效地发挥作用。美国法律规定,国防部长每年3月1日前必须向国会两院的军事委员会递交关于国家技术与工业基地的评估报告。
除了上述较为宏观的工业基地之外,在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概念创建之前,还有一些与某种产业领域相联系的工业基地概念已经活跃在美国战略界话语体系中,如航空航天工业基地、空间交通工业基地、海军工业基地等。这些基地都为国家安全创新基地作出了概念内涵方面的贡献,目前也是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双重认知压力驱动下的国家安全创新基地
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概念是美国历史上十分罕见的,将所有能牵涉到的新兴技术和关键技术领域都囊括在内的超级战略构想,体现了美国的强烈反应。在该战略制定的背后,起助推作用的不仅有美国对当前技术发展潮流的趋势认知,还有在大国竞争日渐白热化、亟需科技创新领域提供战略支持的情境下,美国对其科技创新能力及全球地位的危机认知。
在技术认知层面:第一,这一概念是美国在理解当今世界科技创新领域演化趋势或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之后,必然做出的回应。科技革命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不言而喻,对某一国家的前途命运更是起决定性作用。美国著名决策科学公司戈维尼(Govini)认为,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就是对“以物理、数字和生物三大类科技领域新发展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投资计划(11)Govini,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 Investments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 2018, https://es.ndu.edu/Portals/75/Govini_NationalSecurity_4IR.pdf?ver=2018-05-29-113355-597.。在本轮科技革命的时代条件下,美国国防部认为兼具破坏性与革命性(Disruptive and Revolutionary)的新兴技术“将会改变社会,并且最终改变战争性质”(12)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January, 2018,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导致整个战略环境发生根本变化。美国不愿也无法承受在科技“竞技场”落后的沉重代价,打造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既是一种应时之举,又是技术发展趋势的倒逼之举。第二,该概念还源自美国对新兴技术本身自带的不确定性的担忧。例如,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Defense Science Board)在一篇关于自主系统技术的报告中,坦承自主技术是把双刃剑:自主技术作为一种应用广泛的基础技术,使大部分军事领域、任务和保障活动更加有效率,并因此快速在整个国家和全球扩展开来,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很多系统都可能面临新的风险和弹性问题,包括动能损伤、传感器干扰、数据污染、网络干扰等灰色地带性质的威胁(13)Defense Science Board, “Counter Autonomy: Executive Summary”, September, 2020, https://dsb.cto.mil/reports/2020s/CA_ExecutiveSummary.pdf.。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在名为《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报告中也承认,尽管人工智能有可能在军事环境中带来诸多优势,但也有可能带来挑战,比如,它的技术结果有可能难以预测,或者容易被特殊形式的操纵所控制(14)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November 10, 2020, https://fas.org/sgp/crs/natsec/R45178.pdf.。
在自身科技创新实力和世界地位的认知层面:美国的基本理解是当前其科技实力出现相对衰退,代际规模的技术差距逐渐被磨平,引以为傲的科技引领者的角色被弱化。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吉姆·英霍夫(Jim Inhofe)在美国《国防新闻周刊》(DefenseNews)上撰文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人民一直坚信我们的军队拥有所有最先进的技术,但是使我们领先对手20年的技术优势已迅速消失。在一些方面,我们已经落后。在2030年之前,如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将军所言,除非我们‘采取大规模的急剧改革’,否则美国很有可能要面对一个拥有超强武器、超强设备、超强能力的敌人”,据此,英霍夫疾呼,“我们必须按照国防战略所要求的那样,建设国家安全创新基地”(15)Jim Inhofe, “SASC Chairman: We must Build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Our Defense Strategy Requires”, December 2, 2019, https://www.defensenews.com/outlook/2019/12/02/sasc-chairman-we-must-build-the-national-security-innovation-base-our-defense-strategy-requires/.。当前,美国战略界充斥着对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自满态度和停滞局面的批判。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2020年发布的报告批评道: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沉湎于美国在以往取得的科技成就,骄傲自满,因循守旧地依赖冷战模式,不思将其改进和现代化;国家用于研发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数十年间几乎未见增长;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成果——尤其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尽管花费糜耗,但已经停滞不前;美国的领导地位已经处于极其险恶的境地(16)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rpening America’s Innovation Edge”, October 16, 2020,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1015_GoodmanGerstel_AmericasInnovativeEdge_Report%20%28002%29.pdf.。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和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Rice University 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联合发布的报告认为,美国的科学和工程事业正处于自阿波罗登月50余年以来的一个临界点,面临着因自满而带来的危险。该报告不无忧心地指出,即便在科技研发领域仅仅落后少许年份,都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就业、生活水平和国家安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17)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nd Rice University 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The Perils of Complacency: America at a Tipping Point in Science & Engineering”, September, 2020, https://www.amacad.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resources/Perils-of-Complacency_Full-Report_3.pdf.。奥巴马政府公布的《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科学、技术与创新战略》认为,美国很多攸关现代国家安全的科学和技术事业,都是数十年前为应对冷战威胁而建立的,如今,新兴技术在诸如网络安全、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自主系统、气候变化等领域,有潜力地创造新的、非对称的、难以预判的威胁(18)White House, “A 21st Centur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for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May,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NSTC/national_security_s_and_t_strategy.pdf.。具体在军事科技方面,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CSBA)在2020年发布的报告认为,国防部为取得冷战胜利而开发的技术能力,包括隐形战机、精准制导武器、远程通信网路等,都已经扩散至其它国家的军队中,潜在的敌人也已经仔细观察到美国在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等冷战后冲突中的军备行为,并照此改变他们各自的行为理念,因此,美国的军事高层都承认,未来美军在这些背景下取得的任何领先优势很可能会非常狭小,且稍纵即逝(19)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Mosaic Warfare: Exploi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utonomous Systems to Implement Decision-centric Operations”, February 11, 2020, https://csbaonline.org/uploads/documents/Mosaic_Warfare.pdf.。
在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对中国等竞争对手科技进步的担忧弥漫整个美国战略界和产业界,甚至到了危言耸听、妄自菲薄和故意夸大威胁的地步。里根研究所(Ronald Reagan Institute)2019年的一篇报告认为,“重要的创新正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发生,即使是国内创新,也往往伴随着外国投资和供应链而发生,易受外国影响”(20)Ronald Reagan Institute, “The Contest for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 in an Era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December, 2019, https://www.reaganfoundation.org/media/355297/the_contest_for_innovation_report.pdf.。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每年,竞争对手从美国窃取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知识产权。窃取专利技术和早期创意,使竞争者不公正地挖掘自由社会进行的创新。多年来,竞争对手已经在网络经济战争和其它恶意活动中使用复杂的手段来削弱我们的商业和经济。除这些非法手段之外,一些行为者还使用基本合理、合法的转移和关系来获取某些领域、专家和可信赖的工厂的访问权限,以填补他们的能力差距并侵蚀美国的长期竞争优势”(21)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2018年,美国国土安全部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联合发布的报告认为,“对手们(主要是中国)正在雄心勃勃地投入,不仅要缩短同美国的技术差距,而且志在颠覆这种差距关系”(22)2018 Analytic Exchange Program,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U.S.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July 26, 2018,https://www.dhs.gov/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2018_AEP_Emerging_Technology_and_National_Security.pdf.。由顶尖的美国公司和商业组织、研究型大学、科学界联合成立的“美国创新工作组”,2019年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与美国在科技创新各个要素层面的能力进行了详细比较,其发布的报告难掩忧虑地指出,美国难道要屈居“第二名”了吗(23)The Task Force on American Innovation, “Second Place America? Increasing Challenges to U.S.Scientific Leadership”, May, 2019, http://www.innovationtaskforc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Benchmarks-2019-SPA-Final4.pdf.?当时,竞选总统的拜登在这一问题上态度鲜明,他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他的目标就是要让“美国引领创新”(24)Joseph R.Biden, Jr., “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2, 2020, p.68.。在这种意义上,与中国的科技战略竞争可被视为促动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概念产生的最重要因素。
二、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内容要旨与战略底色
根据美国政府相关战略文件以及科技战略研究界的相关建言,可以归纳出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拥有三项重要的内容要旨,包括关涉领域、主导角色和机制模式。这些内容要旨连同大国竞争的战略环境,决定了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具有特殊的战略底色。
(一)新兴技术和关键技术是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核心关切
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内容要旨之一在于,其关涉的具体技术领域都是影响时代进程、奠定未来工业基础、攸关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2020年,白宫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赋予关键技术与新兴技术一个具体范围层面的定义——“被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评定为,对保持美国国家安全优势(包括军事、情报和经济优势)至关重要、或有潜力变得至关重要的技术领域”,并且详细列出了20项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清单,分别为高级计算,先进常规武器技术,高级工程材料,先进制造,先进传感技术,航空发动机技术,农业技术,人工智能,自主系统,生物技术,化学的、生物的、放射学的与核的缓解技术,通讯和网络技术,数据科学与储存,分布式分类账技术,能源技术,人机界面,医疗和公共卫生技术,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和微电子学,空间技术。该战略文件还表示,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负责协调的各部门联动机制下,这一名单将会被审核,并且每年都会更新(25)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October,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10/National-Strategy-for-CET.pdf.。2020年,《无限边疆法案》列出的联邦政府需要着力提升的技术清单与上述白宫公布的清单大体相当,包括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高效能计算,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硬件、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机器人学,自主系统和先进制造业、自然或人为灾害预防、先进通讯技术、生物技术,基因组学与合成生物学、网络安全,数据储存和数据管理技术、先进能源、材料科学与工程(26)Charles E.Schumer, “Endless Frontier Act”, May 21, 2020,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3832/text.。2020年9月,由国会民主党重量级议员提出的《美国领导法案》(America LEADS Act,全称《美国劳工、经济竞争力、联盟、民主与安全法案》)列出的技术清单与《无限边疆法案》几乎完全重合,另附加了一项“同其它关键技术相关的金属与材料生产”。与《关键技术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一致,《美国领导法案》也强调清单更新的重要性,明确这一清单只是“初始清单”(Initial List),并为其设定一个“更新流程”(Updating Process),即以四年为周期,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主任应在四年后(以及随后每四年)重新审校关键技术清单,如果对美国的竞争性威胁发生了改变,可以增加或删减具体技术条目(27)Robert Menendez, “America LEADS Act”, September 17, 2020,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4629/text.。
(二)强调政府在战略制定和基础研究中的主导性地位
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内容要旨之二是强调美国政府的重要作用,即由政府布局宏观战略、统筹协调各方合作、加大研究投入。决策公司戈维尼认为,第四次科技革命与之前任何一次都不相同,正是促使数字、物理和生物领域之间界限模糊化的数据和新兴技术引燃了此次革命,而政府是受本轮革命冲击最大的一方,政府必须进行投资来弥补能力缺口,使新技术充分发挥潜能(28)Govini,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 Investments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 2018, https://es.ndu.edu/Portals/75/Govini_NationalSecurity_4IR.pdf?ver=2018-05-29-113355-597.。自21世纪初中国科技实力显著进步以来,美国科技战略研究界一直都在表达对中国举国体制的担忧,而尤以近期为甚,美国认定中国科技进步的动力根源是国家支持。一方面,美国攻击中国举国体制的意识形态劣势,认为中国采取的是“创新重商主义”(Innovation Mercantilism);但另一方面,美国过激的忧虑实际上间接承认了中国模式持续的高效率优势。据此,各大智库建议制定美国版本的政府支持计划。由“法律战学会”(Lawfare Institute)和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创设的“法律战网站”(Lawfare)2020年3月发布文章,强调政府介入科技发展的必要性——“政府处于评估国家安全风险的最佳位置……在一些情况下,仅仅依靠市场或许不能解决问题,正如我们在5G技术上看到的那样。因此,政府投资在一些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此类倡议对于信奉市场决定力量的美国而言,是一种根本价值观意义上的挑战。为此,法律战学会认为,“此类分析不应当从‘政府干预市场本质上是错误或者是失当’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正是这种立场,使得美国(曾拥有世界上人人艳羡的电信技术)到了这般田地——它必须苦苦哀求满腹疑虑的盟友们不要购买中国的电信设备……我们坚持认为美国应当毫无畏惧地使用全部可能的政策手段来提升经济竞争力,即使这需要使用类似‘工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之类的肮脏词汇,也在所不惜”。基于此种逻辑,法律战学会建议美国政府制定积极有为的战略,如在5G技术领域,建议美国借鉴其在对抗日本半导体行业冲击中大获成功的“Sematech”(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联合体)方案,制定名为“Sematech 2.0”的5G方案。为维持美国在该领域的供应链安全,法律战学会甚至提议美国直接入股海外的5G技术生产商,以替代中国生产商(29)David Forscey and Herb Lin, “‘Just Say No’ is not a Strategy for Supply Chain Security”, Lawfare, March 25, 2020, https://www.lawfareblog.com/just-say-no-not-strategy-supply-chain-security.。
拜登政府国防部长特别助理、时任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副总裁和研究项目总监的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在国会听证会上也强调,为应对来自中国竞争的压力,联邦政府应该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国会应该建立应对中国挑战的两党共识,并“通过继续支持增加基础研究资金、制定战略性移民和签证政策以及投资于教育等优先事项,重点提高美国的竞争力,确保美国持续的经济实力和技术领导对于维持美国竞争力的至关重要性。因此,美国政府应该继续保持其为重大技术突破提供种子资金的悠久传统,更多侧重于提高美国竞争力的国内政策,这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至关重要,包括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战略移民和签证政策……对工人进行技能再培训、强调改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大学科门类)教育”(30)Ely Ratner, “Blunting China’s Illiberal Order: The Vital Role of Congress in U.S.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January 29, 2019,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Ratner_01-29-19.pdf.等措施。
2021年3月3日,拜登政府颁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性文件——《过渡性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明确表示新一届政府将加大对“研究和开发、基础计算技术和国内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确保美国的创新优势;通过投资STEM教育,扩大美国科技队伍;调整移民政策,“激励世界上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在美国学习、工作和停留”;为新兴技术制定技术标准,以“提升美国的安全、经济竞争力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和吸引力”(31)Joseph R.Biden, Jr.,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的民主党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更加强调政府的主导性。
(三)多方协同合作是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机制模式
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要旨之三在于,其基本实施方式是多方协同合作。此合作事业包含众多利益攸关方和广泛的牵涉面,包括公共部门之间的合作、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公私两部门与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美国政府与盟友及伙伴国之间的合作等。例如,目前在美国国会两院均获通过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国防部通过与学术界、国防工业、商业界、政府机构以及风险基金的合作,扩展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涵盖范围(32)“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1”, December, 2020, https://docs.house.gov/billsthisweek/20201207/CRPT-116hrpt617.pdf.。由于政府在国家安全创新基地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美国战略界对政府各机构间的合作尤其重视。自“9·11”事件后被美国政府逐步接纳的“全政府战略”(Whole-of-Government Strategy),在近两年进入鼎盛时期,频繁见诸于战略界的科技战略建议中。全政府主张汇集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资源,通过各组织间的协调、合作及联合行动,共同应对公共政策领域的复杂问题(33)张帆:《一加一大于二?——试析“全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体制中的应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8期。。2018财年到2021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都提及美国应制定全政府战略或方法。2019年1月,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共和党籍)以及副主席马克·华纳(Mark Warner,民主党籍)联名推出议案,呼吁在白宫设立“关键技术和安全办公室”(Office of Critical Technologies and Security),协调部门间的合作,培育一个长期的、全政府的战略来应对技术挑战。马克·华纳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全政府的技术战略来保护美国在新兴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上的竞争优势,通过阻止技术从美国流出以应对中国威胁”(34)Marco Rubio and Mark Warner, “Rubio, Warner Introduce Bipartisan Legislation to Combat Technology Threats from China”, January 4, 2019, https://www.rubio.senate.gov/public/index.cfm/2019/1/rubio-warner-introduce-bipartisan-legislation-to-combat-technology-threats-from-china.。2020年,由来自美国太空部队、空军研究实验室、国防创新小组的四位专家联名撰写的报告,在对美国太空工业基地(Space Industrial Base)的现状进行评估后,也呼吁采用全政府战略来应对美国在空间技术领域面临的挑战:通过制定跨部门间的整合政策,美国可以合并组成一个广阔和多样化的技术基地,确保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35)Steven J.Butow, Thomas Cooley, Eric Felt, etc., “State of the Space Industrial Base 2020: A Time for Action to Sustain US Economic & Military Leadership in Space”, July, 2020, http://aerospace.csis.org/wp-content/uploads/2020/07/State-of-the-Space-Industrial-Base-2020-Report_July-2020_FINAL.pdf.。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2020年的一份报告认为,全球经济的高度互联性,意味着存在诸多敏感技术和数据流向敌手的渠道,并据此建议提升全政府的技术控制政策,维持美国的长期创新优势(36)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rpening America’s Innovation Edge”, October 16, 2020,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1015_GoodmanGerstel_AmericasInnovativeEdge_Report%20%28002%29.pdf.。全政府组织原则的一个重要外延是美国政府与盟国及伙伴国政府的相关机构进行合作,所涉及的部门不仅在科技创新政策方面开展交流,而且在安全政策方面探讨组建技术管控联盟的可能性。
鉴于当前私营部门在美国创新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几乎所有的官方文件和智库报告都将政府机构与私营部门的合作视为一种必需的机制。而且,考虑到目前事关国家安全的许多新兴技术主要来自商业部门(37)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January, 2018,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防范私营企业的关键技术向中国输出,更加深化了当前公私合作的必要性(38)参见志在沟通政界和技术界的美国公共利益组织“第二战线体系”(Second Front Systems)的报告,“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erspectives from the 2019 Offset Symposium”, July, 2019, https://secondfront.com/wp-content/uploads/2019/07/Offset-Symposium-Whitepaper-6-5-19.pdf。。以大学、国家实验室为代表的学术机构是传统的科技创新重要源生地之一,鼓励联邦政府、私营部门与之合作也是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意图延续这一经典方式的表现。
(四)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战略底色
本质上,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概念体系是科技创新方面的一种“举国体制”(Whole-of-Nation),因为其核心内容就是动员美国全社会的力量(39)刘国柱:《特朗普政府要打造怎样的“国家安全创新基地”》,《世界知识》2020年第10期。。在中文的语境下,举国体制常被认为独属于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存在。但这是一种思维二分法式的误解。尽管并不频繁,但举国体制在美国政府文件中时有出现,如美国国防部2010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曾提及举国体制(40)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10, https://archive.defense.gov/qdr/QDR%20as%20of%2029JAN10%201600.pdf.;公共管理学家薛澜将1980年代美国为应对日本半导体威胁而开展的“Sematech”(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联合体)计划视为美国的举国体制(41)薛澜:《薛澜谈新型举国体制:真正卡住我们脖子的是什么?》,http://zhishifenzi.com/innovation/multiple/10286.html,2020-10-28。将“Sematech”视为举国体制的一种,实际上与许多人的认知相反,主流的意见几乎否认美国存在这种体制。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薛澜观察到,“Sematech”将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大部分力量集中起来,统一制定政策、统一管理、统一研究,符合举国体制的标准。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联合体的成员包括AT&T、IBM、Intel等11家半导体相关企业,全部产量占全美总产量的75%。作为政府与产业界合作的典范,“Sematech”每年两亿美元的研发经费由成立时的11家公司与美国国防部平摊。该联合体的管理模式是由一个中心管理机构统一管理,研究人员来自各成员公司,管理人员全部来自产业界。美国国防先进技术开发署也参与顶层指导协调,虽不作为联盟成员,但派出人员参与“Sematech”董事会和技术顾问委员会,引导制定时间计划表和规划图,协调国防部所属机构资助相关研究。该联合体与上述设备供应企业联合体深度合作,并将成果及时向生产制造商辐射。;科技战略研究学者樊春良认为,二战时期美国为建造原子核武器而实施的曼哈顿计划也是科技举国体制的一种表现形式(42)樊春良:《科技举国体制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发展趋势》,《国家治理》2020年第42期。;美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者在建言献策时,也会提及举国体制,并无避讳。宏观经济学者黄寿峰认为,“举国体制就是国家利用各种行政手段和政策法规,举全国、全社会之人力、财力、物力和各种社会资源去达成某一特定目标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43)黄寿峰:《准确把握新型举国体制的六个本质特征》,《国家治理》2020年第42期。。但本质上,举国体制的定义性特征是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全社会参与,其聚焦的要点是“效率问题”,即所有的利益攸关者能否就特定目标展开有效合作,能否在战略规划设定的时间内达成共同目的。至于“公共权力或国家行政权力的凝聚作用”,则并非是举国体制的定义性特征,而只是某种类型举国体制的特点,如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以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为代表的传统举国体制。当前中国强调的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更加强调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44)唐任伍:《赋能更具活力的新型举国体制》,《国家治理》2020年第42期。,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些特点都间接弱化了有“计划和强制”色彩的行政权力的作用力,也佐证了举国体制的关键点不是政府的强制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举国体制不需要一个统御全局的指引协调中心,相反,该中心对于举国体制的成败尤为关键。
在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理想概念中,提升和巩固美国在科技创新层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已经上升至一种无可置疑的国家意志。政府制定宏观战略,加大研发投入,吸引和挽留人才,与私营领域保持合作,且外联盟友,组建科技创新和安全的国际联盟。私营企业界充分理解科创实力对国家安全的深刻影响,增加研发投入。以大学、国家实验室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充分利用包括人才在内的研究优势,努力攻关克难。上述三方几乎代表了美国科创领域的全部力量,囊括了创新进步所需的全部要素机构(理论上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所需的要素机构包括企业家、公司、产业、大学、研究实验室和政府机构(45)Phil Budden and Fiona Murray, “Defense Innovation Report: Applying MIT’s Innovation Ecosystem & Stakeholder Approach to Innovation in Defense on a Country-by-Country Basis”, MIT Lab for Innovation Science and Policy, May, 2019, https://innovation.mit.edu/assets/Defense-Innovation-Report.pdf.),政府就扮演着协调中心和重要投资者的角色,企业界和学术研究机构扮演着创新主体角色,它们之间通力合作,提升美国科创实力,这些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典型表现,符合举国体制的判断标准。但与20世纪80年代同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竞争而采取的举国体制相异,国家安全创新基地采取的发展模式,并没有那么严格周密的组织程序,因为该基地不是某一具体技术领域的发展战略,而是囊括诸多新兴技术和关键技术的极为宏观的战略规划,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有特别精细、具体的管理策略。
技术安全化和技术民族主义是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另一重要特质。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全部关切是关键技术与新兴技术的研发以及防扩散,它从战略角度来看待技术和制造业的发展,认为在高度竞争的世界中,技术是一种关键的、排他性的国家资产,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这种将技术安全化的战略观,一方面由新兴技术的破坏性和革命性本质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大国博弈“落后即出局”的严酷性所决定。与技术安全化相伴而生的是附着在国家安全创新基地上的技术民族主义倾向。在一个践行技术民族主义的国家,其“对内政策就是壮大本国技术创新能力,为本国的技术研发创造有利条件;对外则是技术保护,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保障本国在海外的技术市场优势,从而促进本国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46)关于技术民族主义概念,参见Robert Reich, “The Rise of Techno-nationalism”, The Atlantic, Vol.259, Issue 5, May, 1987, p.66;刘国柱《特朗普政府技术民族主义论析》,《美国研究》2020年第4期。。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无疑符合技术民族主义的定义特征。
将中国预设为美国的首要战略对手和防范对象,是该基地技术民族主义倾向的典型体现。所有的智库报告在述及美国的科技竞争对手时,无一例外地都指向中国。2020年9月,参议院提出的一项旨在提高美国竞争力的重磅议案——《美国领导法案》,在长达六百余页案文的首页顶端,旗帜鲜明地指出该法案的目的是“应对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该法案规定,相关部门必须向国会两院提交关于中国技术发展态势的报告,比如:规定国务卿在与商务部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的合作下,向国会中该法案规定的委员会提交关于中国政府军民两用技术发展与应用情况的报告;规定商务部长在与美国贸易代表的磋商下,向参议院和众议院提交关于中国政府反竞争行为的报告;规定商务部长向国会中该法案规定的委员会提交报告,论述工业领域的美国私营实体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资源和使用由中国操作的全球分销网络;等等(47)Robert Menendez, “America LEADS Act”, September 17, 2020,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4629/text.。2020年5月,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尔斯·舒默(Charles E.Schumer)推出的《无限边疆法案》全文未提及“中国”一词,但文中控诉的拥有种种所谓卑劣行径的“外国竞争者”显然意指中国。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旗下的顶尖期刊《科学》称,“领先中国法案”(Stay Ahead of China Act)或许是这部法案更准确的称呼(48)Jeffrey Mervis, “U.S.Lawmakers Unveil Bold $100 Billion Plan to Remake NSF”, May 26, 2020,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5/us-lawmakers-unveil-bold-100-billion-plan-remake-nsf.。
三、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战略举措
怎样建设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是近四年美国战略界激烈讨论的议题。与新兴技术和关键技术相关的产业协会几乎都在倡议联邦政府加大投资力度。保持一定程度独立的智库和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几乎无一例外地倡议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一同增加研发投入,提升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且强调美国与盟友在科技创新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在充分吸收这些建议的基础上,作为基地建设主导方的美国政府,出台了诸多措施方案。其中,首次提出该基地概念的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2020年10月白宫发布的《关键技术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为外界观察基地建设提供了最佳视点,两者基本囊括了所有战略研究界的建议以及有可能付诸实施的举措。
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是“防建”结合的基地概念,既形成一个防止技术扩散的堡垒,又建设一个创新源泉之所。在“防”的层面,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了一个极其简易的方案,其中,计划采取的优先事项包括理解遇到的挑战、保护知识产权、收紧签证程序、保护数据和底层基础设施。2020年《关键技术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详细述及了“防”的战略措施,具体包括:确保竞争对手不能使用非法手段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研究、发展或技术;要求在技术发展早期阶段就进行安全设计,并同盟友及伙伴国合作采取同样的措施;通过促进学术机构、实验室和工业界的研究安全来保证研发事业的诚实度(49)原文中的“Integrity”常被中国国内的译介文章翻译为“完整性”。但此为误译,“Integrity”在这里指代“诚信”“诚实”,与偷窃相对立;确保研发事业的诚实度,意为防止所谓的“中国学术间谍”在美国及其盟国的主要学术机构窃取知识产权。,同时也兼顾外国研究者的有益贡献;确保关键技术与新兴技术的适当方面处在出口法、出口规章以及多边出口机制的控制之下;鼓动盟友与伙伴国效仿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CFIUS)的做法,开发他们自己的管制程序;与私营部门密切互动,掌握私营部门对“与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相关的未来战略弱点”的理解,以及它们对关键技术与新兴技术的理解,并从中获益;了解世界各地的科技政策、能力和演化趋势,理解它们可能如何影响、损害美国的战略与项目;确保安全的供给链,鼓励盟友与伙伴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告知关键的利益攸关者保护技术优势的重要性,并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提供实际帮助。
在“建”的层面,《关键技术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囊括了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关于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建设的所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更加细化了具体的建设方案,旨在强化美国作为世界科技创新主要源泉的地位。两份战略文件的建设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技创新人才梯队建设
在人才政策方面,白宫强调,“要培育世界上最高质量的科学与技术人才力量,吸引和留住发明者和创造者”。
之所以采取这一举措,不仅仅因为人才竞争是科技创新竞争的本质,更因为当前美国面临着科技人才流失的严峻状态。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联合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经过调研发现,美国的年轻一代对STEM学科兴趣不足,大学前的STEM学科教育水平不高,美国在STEM学科方面的学术研究严重依赖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外国出生人才(50)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nd Rice University 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The Perils of Complacency: America at a Tipping Point in Science & Engineering”, September, 2020, https://www.amacad.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resources/Perils-of-Complacency_Full-Report_3.pdf.。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根据多方数据,也不无忧虑地指出,尽管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在教育花费上保持较高的水平,但美国STEM学科的教育成果却比较平庸,而且在性别、种族和社会经济上存在鸿沟。2018年,美国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每位学生上的投入,在35个发达经济体中排名第四,但在科学和学术评价中仅仅取得平均水平。美国STEM学科教育因高水平海外留学生的注入,才变得极有活力(51)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rpening America’s Innovation Edge”, October 16, 2020,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1015_GoodmanGerstel_AmericasInnovativeEdge_Report%20%28002%29.pdf.。可以说,美国的科技发展严重依赖原国籍为非美国的研究者和人才。以人工智能为例,根据保尔森基金会(Paulson Institute)下辖的马可波罗智库的数据显示,美国境内的高端人工智能人才,原国籍为美国的仅占31%,原国籍为中国的占27%,原国籍为印度和欧洲的人才各占11%(52)Macro Polo, “The Global AI Talent Tracker”, https://macropolo.org/digital-projects/the-global-ai-talent-tracker/.。据非营利组织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2017年的调查,2015年美国的STEM从业人员中外国出生的比例高达24.3%(53)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 “Foreign-born STEM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June 14, 2017, https://www.americanimmigrationcouncil.org/research/foreign-born-stem-workers-united-states.。
里根研究所发现,近十余年来出现的一个严峻趋势是大多数的外国留学生从美国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选择返回母国,而非加入美国的工作队伍(54)Ronald Reagan Institute, “The Contest for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 in an Era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December, 2019, https://www.reaganfoundation.org/media/355297/the_contest_for_innovation_report.pdf.。而且,由于近期美国在移民政策上设置的障碍,海外人才很难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政府许可进行国家安全项目工作的外国人才出现流失的情况,同美国政府合作的私营企业面临着此类人才短缺的窘境。近年来,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适用于外籍工作者留在美国工作的H-1B签证的拒签率陡然升高,2020年前两个季度的拒签率接近30%(根据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的数据,2015年的拒签率仅为6%)(55)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merican Policy, “H-1B Denial Rates through the Second Quarter of FY 2020”, https://nfap.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H-1B-Denial-Rates-Analysis-Through-The-Second-Quarter-Of-FY-2020.NFAP-Policy-Brief.August-2020.pdf.。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警告称,排斥广大外籍研究者的行为,对美国科学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56)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rpening America’s Innovation Edge”, October 16, 2020,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1015_GoodmanGerstel_AmericasInnovativeEdge_Report%20%28002%29.pdf.。因此,对于美国来讲,吸引和留住人才不再是口号式的宣传,而是当务之急。针对这种紧急状态,美国国会正在考虑加强措施吸引人才,如2020年6月众议员詹姆斯·兰格文(James R.Langevin)提出了《国家安全创新通道法案》(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Pathway Act),要求国土安全部为关键技术领域顶尖的外国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进入美国提供“特别移民签证”(即绿色通道),从而提升和保护国家安全创新基地(57)James R.Langevin, “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Pathway Act”, June 18, 2020,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7256/text.。在更宏观的人才战略上,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甚至提议白宫、国会和学术界效仿具有重大意义的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制定一项21世纪的《国防教育法案》,以纾此困(58)James Manyika, William H.McRaven and Adam Segal,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Keeping Our Edg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eptember, 2019, https://www.cfr.org/report/keeping-our-edge/.。
(二)政府与以私营部门为代表的其它部门的合作
在公共部门与其它利益攸关方的关系方面,白宫强调,“利用私人的资本和专业力量去建设、创新;在政府内部发展和采纳高端技术应用,提升政府作为私营部门客户的可取性;鼓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与私营部门一道,创造积极的信息传递,提升公众对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的接受度。支持强有力的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发展,将学术机构、实验室、辅助性的基础设施、风险基金、辅助性的商业和工业,都包括在该基地内;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国建立强大且长久的技术合作关系,促进民主价值和原则”。下面抽取“利用私营部门的创新力量”“政府采购私营部门技术”“与盟国合作”三个重要方面作具体的逻辑阐述。
第一,关于利用私营部门的创新力量。无论怎样强调联邦政府对科技事业投入的重要性,都必须看到,美国私营部门在研发投入中始终占据着美国研发总体投入的大部分。在高度强调市场作用的美国,科技事业的进步离不开商业资本和私营部门人才。如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认为,私营产业拥有政府在完成关键国家安全任务方面所依赖的许多技术(59)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或者说,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苏联解体后美国面临的竞争形势、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发生的变化,共同促使美国更为依靠私营企业来开展创新。尤其是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时代,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不再主要由传统的国防承包商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通用动力等贡献,而是更多依赖商业部门的技术产出。据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2018年的调查,从1980年到2016年,美国商业资本的研发投入一直呈现大幅度上升的趋势。1980年代,商业资本占总体研发投入的50%,这一数据在1990年代、21世纪第一个十年、21世纪第二个十年,都超过了60%(第二个十年约65%)。私人资本的研发投入在198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1.1%,这一数据在2016年超过了1.8%。但该基金会认为,美国私营部门在研发方面的表现并不如表面数据显示得那样强大,近期的经济研究都显示研发投入的生产效率在近几年持续走低,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与总体投入近数十年显著增加的趋势并不同步,私人资本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增长乏善可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占企业全部研发投入的比重在1980年代接近30%,此后一直呈现下跌态势,2010年代仅刚过20%),总量投入的大部分进入到商业产品的发展领域。而且,在主要对手和世界各国加大研发投入的情况下,美国企业研发投入增长的绝对量仍不足以使美国保持长久的领先地位。该基金会认为,“实际上,与美国经济福利最大化所需资金量相比,私营部门的研发投入仍缺口目前体量的2至4倍”(60)J.John Wu, “Why U.S.Business R&D is not as Strong as It Appea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June, 2018, http://www2.itif.org/2018-us-business-rd.pdf.。
第二,关于政府采购私营企业的技术,促进创新发展。该论说不仅有理论根据,而且有实践支撑,美国有诸多成功的先例。军工公司“安都瑞尔工业”(Anduril Industries)的战略主管、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克里斯丁·布洛斯(Christian Brose)在2020年2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提振美国国防创新基地的方式十分简洁,那就是更多地购买这一创新基地正在建造的东西。这事关供应和需求。美国政府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创造更多的需求”(61)Christian Brose, “Hearing of the Future of Defense Task Force ‘Supercharging the Innovation Base’”, February 5, 2020, https://www.congress.gov/116/meeting/house/110475/witnesses/HMTG-116-AS00-Wstate-BroseC-20200205.pdf.。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认为,“一般情况下,与补贴相比,政府采购是更为有效的工具。它应当用于支持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技术种类,而不是支持具体的公司或某种具体技术……尽管人们对于政府干预私营市场深恶痛绝,但华盛顿拥有支持关键产业发展的成功历史。自二战以来,政府已经利用采购和大规模的研发预算来驾驭市场力量,促进尖端技术的发展……1950年代和1960年代,联邦政府的初始投资以及与斯坦福大学签订的研究订单合同帮助了硅谷的建立。阿波罗项目和民兵洲际导弹项目促进了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62)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rpening America’s Innovation Edge”, October 16, 2020,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1015_GoodmanGerstel_AmericasInnovativeEdge_Report%20%28002%29.pdf.。这些都是显著的例子,而且政府作为购买方,本身就是市场交易的一部分,不会触及当前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的底线。
第三,关于盟友在国家安全创新基地中的作用。几乎所有美国国会提出的相关法案以及美国智库公布的报告,都强调与盟友合作的重要性,目的不仅是建立防护性联盟、阻止关键技术流向中国,而且包括通过与其它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促进美国技术发展。新美国安全中心2020年发布的报告甚至断言,美国使胜利的天平偏向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加强与盟友的创新合作。为此,该中心建议美国打造一个“联盟创新基地”(Alliance Innovation Base),具体举措包括:第一,强化美国技术参与的工具包,如国防创新小组(Defense Innovation Unit,一个总部位于硅谷、旨在快速利用商业技术的国防部部门)应尽全力走向全球化,从“在盟国进行巡回展示”起步,直至建立永久性海外基地等;第二,发布新的合作平台,如建立双边国家安全创新基金、组成军事测试设备联盟、建设跨国平台孵化新公司;第三,降低盟国投资美国的障碍;等等(63)Daniel Kliman, Ben FitzGerald, Kristine Lee, etc., “Forging an Alliance Innovation Bas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rch 29, 2020,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forging-an-alliance-innovation-base.。
(三)政府研发投入
白宫在该文件并不显著的位置提及了战略界最为关心的问题,即“在设计美国政府预算时,提升研发的优先权”。对于新兴技术和关键技术而言,联邦政府的研发投入极为重要,而当前的局面也令美国各界极为担忧。2018年,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与国土安全部联合发布报告指出,从2015年到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劲步伐助推私营部门在技术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持续增长,与之相反,美国政府的研发投入却在逐渐降低。从1962年到2017年,联邦研发投入占联邦预算的比重已经下降了68%。一个更为骇人的数字是截至2017年,联邦国防部分的研发支出相比于2007年下降了43%(64)2018 Analytic Exchange Program,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U.S.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July 26, 2018, https://www.dhs.gov/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2018_AEP_Emerging_Technology_and_National_Security.pdf.。实际上,1964年至今,政府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基本处于大幅下降的态势(尽管一些时段偶有小幅提升)。里根研究所认为,近20年美国政府的研发预算之所以减少,是因为政府投入模式逐渐让位于商业投资模式(65)Ronald Reagan Institute, “The Contest for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 in an Era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December, 2019, https://www.reaganfoundation.org/media/355297/the_contest_for_innovation_report.pdf.。但商业投资模式存在专注于短期效益,忽视长远安全效益,同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动力不足等缺点,无法抵消联邦资金缺位引发的后果,无法替代联邦研发支出的重要作用。
面临这一状况,几乎每个产业界以及战略界都在呼吁联邦政府增加科技研发投入。例如,曾获得巨大成功的半导体业界,目前又遇到了新半导体时代技术更迭带来的挑战。2020年,美国半导体研究公司(Semiconductor Research Corporation)和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联合发布报告,制定半导体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并宣称在新半导体时代,为维持和加强美国在信息与通信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需要在未来十年中,每年持续增加34亿美元的联邦投入,以进行大规模的、与产业相关的、基础性半导体研究(66)Semiconductor Research Corporation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Interim Report for the Decadal Plan for Semiconductors”, October, 2020, 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wp-content/uploads/2020/10/Decadal-Plan_Interim-Report.pdf.。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和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认为,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应以每年至少4%的增长率持续增加,确保联邦基础研究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0.2%提升至0.3%(67)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and Rice University 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The Perils of Complacency: America at a Tipping Point in Science & Engineering”, September, 2020, https://www.amacad.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resources/Perils-of-Complacency_Full-Report_3.pdf.。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建议联邦政府在未来5至10年内,将用于研发方面的投入恢复至二战后的平均水准1%,并且每年连续增加1000亿美元。《美国领导法案》规定在该法案生效之后的四年内,联邦政府应倾注额外的3000亿美元资金到科学与技术的研发领域(该3000亿美元是附加资金,作为对正常计划内研发投入的补充),而且还规定在上述四年的投资期后,每一财年的总体研发投入额要比上一个财年增加3%(68)Robert Menendez, “America LEADS Act”, September 17, 2020,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4629/text.。
联邦政府的资金投入集中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这两个领域具有风险等级高、研究周期长、直接收益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等特点。也正是这些特点致使企业资本不愿涉入,这要求政府必须为此进行兜底,因为基础研究是任何创新发生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决定了某一国家科技创新实力的广度、深度和等级。包括先进材料、电子学、半导体、空间技术、科学仪器学、试验设备、机器人学、水资源净化、计算基础设施、能源等领域的基础研究,都符合这种高风险、回报慢的类别,它们又基本都是事关科技竞争成败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但公共资金的作用却不仅仅局限于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它同样可以促进企业资本更多地涉入这些“费时费力、油水稀少”的领域。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图尔(Andrew Toole)曾专门就制药产业做过一番调查,研究发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每增加1美元的基础研究投入,就会导致制药行业的研发经费在8年后增加8.38美元;国家卫生研究院在临床研究的投入增加1美元,就会导致私人制药行业的研发投入在3年后增加2.35美元(69)Andrew Toole, “Does Public Scientific Research Complement Private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50, Issue 1, 2007, p.83.。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报告也认为,政府投资可作为工业投资的催化剂,刺激私营资本增加额外的研发支出;在一些情况下,政府的支持会致使那些原本不可能实现的项目得以开展;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政府的研发投入可以促进或拓展在原来条件下只能缓慢发展或小规模推进的项目(70)Matt Hourihan, “If Government Scales Back Technology Research, Should We Expect Industry to Step in”,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October 16, 2017, https://www.aaas.org/sites/default/files/AAAS%20Public%20%26%20Private%20R%26D.pdf?AYBSf.tHhNcjLd1ZMW2RSRpJgve.tbQ1.。
(四)立法与制度性保障
在政府立法与制度性保障方面,白宫强调,“迅速应对发明与创造,引领世界范围内技术规范、标准和体现民主价值和利益的治理模式的发展,减少既繁琐又阻碍创新和工业进步的管制、政策和官僚化程序,鼓励各州和地方政府也采纳同样的行动”。下面抽出“政府如何应对发明与创造”“减少阻碍创新的政策和官僚化程序”两个最重要方面来阐述政府规划,解释其各自的必要性逻辑。
第一,与创新有关的重要国会法案及行政部门的重要创新文件。面对第四次科技革命汹涌而出的新科技领域和创新需求,美国政府内部人士深知迅速抢占先机的重要性。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尔斯·舒默于2020年5月提出惹人注目且广受美国各界赞誉的《无限边疆法案》,力图通过改革联邦政府的研发支持机制,促进美国科技创新事业的全面进步。这一整体框架涉及的内容是对《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ct of 1950)和《1980年斯蒂文森-惠德勒技术创新法案》(Stevenson-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 of 1980)在具体条款和措辞方面的修正建议。该法案认为,联邦政府必须促进美国的创新事业,通过提升聚焦于发现、创造、商业化和生产新技术等方面的基础性研发投资,确保美国在未来工业中的领先地位。
该法案重点提出三项建议:其一,将国家科学基金会改组为“国家科学与技术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dation),在改组后的基金会内部新设立“技术局”(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并增设一名基金会副主任,负责该部门的具体事务,包括为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提供合同与合作协议、为基金会其它部门和其它联邦研究机构提供资金、进行跨部门合作、提供奖学金、将技术推广至市场等。法案规定,国会在接下来的五年内(从2021财年到2025财年)向“技术局”批准1000亿美元预算资金来维持其运转。其二,建设一个关于“区域性技术中心”(Regional Technology Hub)的项目,规定在该法案成立后的五年内,在全美设立10-15个区域性技术中心(每个技术中心包含高等教育机构、地方政府、州政府、聚焦科技创新创业的经济发展组织、风险发展组织、金融机构、人才培训组织、关键技术企业、联邦实验室等要素机构,地点选在那些有巨大潜力和相关资产、但尚未成为技术中心的地方),目的是将创新能力扩展至美国各地,在关键技术领域促进更高质量的、有广泛基础的增长和竞争力,确保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其三,要求联邦政府制定关于经济安全、科学、研究、创新的战略和报告,规定国家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协同国家经济办公室主任、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其它相关的联邦机构领导人,在2021年以及随后的每年都要审核与科学、研究、创新有关的国家安全战略,并为联邦政府制定相关战略,此外,还要向国会各对口委员会提交关于科技创新的报告,并阐述制定的战略(71)Charles E.Schumer, “Endless Frontier Act”, May 21, 2020,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3832/text.。
该法案的提出是美国政府内部忧心人士对联邦政府研发投入不力的强烈反应。考虑到1945年布什的无限边疆报告关于政府与科学关系的阐述对美国科技政策的重大意义(联邦政府由此创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72)Steve Olson, The Endless Frontier: The Next 75 Years in Science,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20.,2020年《无限边疆法案》的题名取自布什报告,不仅显示出一种传承,更传递出一种象征意义——该法案可能在美国科技政策的发展演化史上,成为一个如同布什报告那样的重大节点,预示着美国新科技政策的到来。
继《无限边疆法案》推出之后,前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嫩德斯(Robert Menendez)又推出了影响重大的《美国领导法案》。该法案最重要部分是美国投资其竞争力的宏大计划,可被称为美国版本的“制造2025”战略,其声明的目的是保持对中国的领先地位。它事无巨细地制定了从2021财年到2025财年期间,美国在包括基础设施、数字、制造业、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大规模提升方案。在提振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研发、防止技术向中国转移、促进美国科技教育等方面,该法案都制定了明确的计划,作出了详细的预算安排。此外,在宏观科技政策领域,与《无限边疆法案》《美国领导法案》有类似抱负的重要法案还有众议院2020年1月推出的《确保美国科学与技术领先地位法案》(Secu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 of 2020)等。
第二,减少制约创新的政策和官僚化程序。减少官僚化程序的必要性,仅以当前国防部的技术研发程序为例便可管中窥豹。未来的战斗系统以软件为中心,而速度和迭代是软件管理的最重要标准。但美国国防创新委员会(Defense Innovation Board)2019年3月的一份报告认为,国防部现在进行软件开发的方式暴露出诸多软肋,如“耗时太长,成本高昂,延缓作战人员获取确保任务胜利所必需的工具,从而使作战人员暴露在危险之中”(73)Defense Innovation Board, “Software is Never Done: Refactoring the Acquisition Code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March 21, 20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Mar/26/2002105909/-1/-1/0/SWAP.REPORT_MAIN.BODY.3.21.19.PDF.。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在该份报告的基础上总结道:大多数国防部软件项目采用“瀑布式”开发过程,依次为形成需求、投标、选择承包商、最后执行程序以满足所列要求,整个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以至于当软件最终部署时,它不再符合操作需求(74)James Manyika, William H.McRaven and Adam Segal,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Keeping Our Edg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eptember, 2019, https://www.cfr.org/report/keeping-our-edge/.。这种阻碍研发的低效管理方式和官僚化程序还以不同形式见于其它政府部门,构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种内部威胁。
四、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对中国的挑战
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是大国竞争战略的产物。在技术民族主义的鼓噪之下,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意图举全国全社会之力建立一个“创新在此产生、创新在此发扬,不依赖外界、不向对手输出”的创新堡垒,其最终目的是促使美国在科技创新的“无限边疆”里不断开拓,获得“第三次抵消”(The Third Offset)的能力(75)“第一次抵消”是指依赖核武器来对抗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军力的数量优势,“第二次抵消”是指“依赖全球定位系统、精准制导武器、隐形传送平台来应对与潜在敌人在数量上的劣势”。参见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U.S.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reparing Military Leadership for the Future”, February 22, 2017,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170222_DuBois_ScienceTechnologyNationalSecurity_Web.pdf。,即用新兴技术和关键技术的高质量创新,抵消竞争对手的数量优势或其它优势。考虑到中美竞争的长期性和科技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在科学、技术、创新领域制定宏观战略,提升美国整体科技实力,保持该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已成为包括两党在内的美国社会各界的共识。以国家安全创新基地为核心内容的美国科技创新战略,将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带来新的风险与挑战。
第一,中国很有可能面对一个在科技创新领域“跑得更快”的美国。据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ck Sullivan)阐述,拜登强烈地认为,“在与中国的任何竞争中,如果我们跑得更快,我们将是最有效的”(76)Walter Russell Mead, “ Dialogue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World Affairs: Discussing the Future of U.S.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with Jack Sullivan”,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6024-transcript-dialogues-on-american-foreign-policy-and-world-affairs-discussing-the-future-of-u-s-foreign-policy-and-national-security-with-jake-sullivan.。所以,美国应少关注怎么让中国减速,多关注怎么让自己跑得更快。与共和党政府相比,民主党政府的施政理念更加倾向于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更为积极地参与到美国科技创新与发展之中。正如拜登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所宣称的,“对于5G和人工智能等未来技术……美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77)Joseph R.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2, 2020, p.75.。美国国防部负责审查和制定对华战略的工作组组长拉特纳也认为,要保持美国的创新优势,必须加强美国的创新引擎,增加对新兴技术如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微电子等领域的联邦投资。可以确信,掌握着白宫和参众两院多数席位的民主党政府,在未来四年,将围绕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在科技创新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源。再加上美国高度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及雄厚的科技创新基础,中国将很有可能面对一个在科技创新领域发展得比以往更快的美国。
第二,中国有很大的可能会面对一个美国主导的、遏制中国科技创新和发展的“科技联盟”。《临时性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明确宣布,美国“将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一道,发展和捍卫可信的关键供应链和技术基础设施”。不仅多家美国智库提出了组建西方10国(T-10)或12国(T-12)技术联盟的设想,拉特纳领衔的“新美国安全中心”更是对此进行过系统研究。拉特纳在研究报告中建议创建一个由主要民主国家组成的国家集团,协调彼此的技术政策,共同制定新兴技术的新国际规则、规范和标准。组建技术联盟是美国两大政党最有共识的领域之一。新一届国会两党重量级议员如查尔斯·舒默、梅内德斯等发起了名为《民主技术伙伴法案》的联合提案,要求“世界上主要的自由民主国家必须在技术伙伴关系中共同合作,以确保这些技术促进民主制度、规范和价值观”(78)“Bipartisan Senators Introduce Legislation to Reassert Democratic Leadership in Technology Strategy & Development”, https://www.warner.senate.gov/public/index.cfm/pressreleases?ID=3C5C0D90-479F-4657-A66D-93A1120B938E.。这样一个科技联盟,将给中国未来在国际社会正常的文化交流、科技交流和技术产品交流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即使不会出现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巴统”组织,“瓦森纳协定”(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将在美国主导的技术联盟的基础上得到强化。
第三,在新兴技术治理的名义下,美国将抓紧抢夺新兴技术规则的制定权。《临时性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强调,世界领先的大国正在竞相开发和部署诸如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这将打破大国间的地缘经济和军事平衡,甚至全面重塑国际社会的未来。拜登政府认为,“技术革命的方向和后果仍不确定。新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受法律或规范的支配,这些法律和规范旨在强调权利和民主价值观、促进合作、防止滥用或恶意行动、减少不确定性和管理导致冲突风险的竞争”。有鉴于此,美国将“制定新兴技术标准,以提高我们的安全、经济竞争力和价值观”,并力求避免“由中国和俄罗斯编写数字时代竞争的规则”(79)Joseph R.Biden, Jr.,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第四,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名义下,拜登政府将推动精准化对华技术脱钩。拜登认为,“如果中国有办法,它将继续抢夺美国和美国公司的技术和知识产权”(80)Joseph R.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2, 2020, p.70.。为避免美国新兴技术流失,拉特纳提出,“在重振国内创新基地的同时,美国将必须更加警惕地保护关键的美国技术”(81)Ely Ratner, etc.,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CNAS-Report-NDAA-final-6.pdf?mtime=20200116130752&focal=none.,认为美国需要继续加强投资筛选和出口管制的立法努力,还需要作出更全面的努力来解决强迫技术转让、学术和商业间谍活动以及知识产权盗窃方面的非法行为。
然而,拜登政府不会执行特朗普政府在科技领域对华全面脱钩的政策,而是选择性的脱钩。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印太事务协调员库特·坎贝尔(Kurt M.Campbell)2019年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主张“有选择地”加强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两用技术的投资和贸易限制”,而非彻底截断美国或其盟友与中国的科技合作,因为“对技术限制的过度推广可能会将其他国家推向中国”(82)Kurt M.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98, No.5, 2019,p.106.。为此,美国智库为拜登政府提出了在技术领域精准脱钩的“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战略。这一战略最初由美国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的高级研究员萨姆·萨克斯(Samm Sacks)在2018年提出。根据这个战略,政府需要确定与美国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即“小院”),并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即“高墙”)。对“小院”内的核心技术,政府应采取更严密、更大力度的封锁,“小院”之外的其他高科技领域,则可以重新对华开放。
2021年1月26日,前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导的中国战略组(CSG)发布的《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Asymmetric Competition: A Strategy for China & Technology Actionable Insights for American Leadership)研究报告,为拜登政府筛选“小院”内的核心技术领域提供了分析框架:(1)卡脖子技术(Choke Point):该单项技术的失败可能会导致更大经济领域的失败;(2)重要竞争护城河(Competitive Moats):在该特定领域的领先能够为美国提供强大的防御优势;(3)战争安全风险:该技术在特殊情况下可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4)增速技术:该技术有助于提高美国整体创新速度(83)Eric Schmidt, “ Asymmetric Competition: A Strategy for China & Technology Actionable Insights for American Leadership”, China Strategy Group, Fall, 2020, https://assets.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20463382/final-memo-china-strategy-group-axios-1.pdf.。报告建议政府在科技领域针对中国开展“非对称竞争”,在科技领域实施“分岔”(Bifurcation)战略,即选择性脱钩。
此外,拜登政府根据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已经针对中国采取限制投资和出口管制的措施,并开始对美国关键供应链如半导体和稀土两大行业进行审查,以保证关键产品的供应链由美国及其盟友来提供。这对于目前供应链上的中国企业及其技术产品——无论是为美国企业提供技术产品或依赖美国技术产品的中国企业,都将构成直接和持久的挑战。
结 语
76年前,万内瓦尔·布什提出《科学:无限的边疆》研究报告,阐述了科学技术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并导致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建立,科技创新逐渐被纳入到美国国家安全体制之中。在万内瓦尔·布什时代,美国大国竞争的主要对手是苏联。美国凭借强大的科研基础和政府各种方式的科研投入,在科技创新领域奠定了对竞争对手的优势,并依靠科技优势,最终在经济、军事等领域取得了对苏联大国竞争的胜利。
今天,美国故伎重演,推出了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概念。围绕国家安全创新基地这一国家创新战略的核心,自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政府聚焦新兴技术领域的创新与发展,从政府到智库、从立法机构到行政部门、从公共部门到私立部门,推出了一系列在美国发展新兴技术的战略和政策,强化了科技创新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美国政府推出了系统性的在美国发展新兴技术的战略和政策。另一方面,利用投资审查对外国投资美国企业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以增强保护美国尖端科技的能力;利用技术产品出口审查,加大了对竞争对手的限制和打压。同时,在国际社会筹组“民主科技联盟”,一方面试图将联盟成员绑架在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中;另一方面利用盟友体系遏制竞争对手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表现出浓厚的技术民族主义特征。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主要表现就是方兴未艾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纵观前三次科技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国际格局的巨大变化。第四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变化,无论规模、范围还是复杂性,都将超过以往历次科技革命。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主要领域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新一代移动通讯技术等未来科技领域,美国与竞争对手的差距明显在缩小。对优势逐渐丧失的焦虑是美国推出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主要原因。
现在,中美两国普遍认识到,在目前的大国竞争中,更有效创新的一方将占据大国竞争的优势。美国围绕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来强化自己的科技创新战略,中国政府则是将科技创新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对中国而言,作为后发国家,基础相对薄弱、技术积累不足。我们应该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为科技创新创造更为优良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从而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在科技创新之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