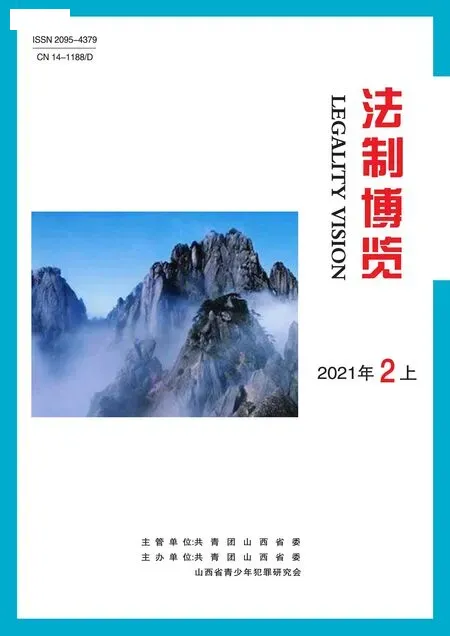污染环境罪之“处置”行为的认定
——基于法益保护的视角
张小丽
(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一、引言
2020年10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对污染环境罪进行了五处修改,将条文中量刑部分“后果严重的”修改为“情节严重的”,并增设了罚金刑;对条文的第一款增设了“依法确定的国家重点生态保护区域”;对条文的第三款基本农田保护部分,增设了“永久”的限定性规定;对条文的第四款增设了“致使多人重伤、严重疾病,或者致人严重残疾”的规定。我国将严重污染环境并且使公私财产遭受损失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并且可处刑罚的最早规定是1997年刑法,1997年刑法新增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体现了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渐显现和我国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罪名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将入罪的构成要件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标志着刑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的理念。2020年的《刑法修正案(十一)》继续延续了这一理念,注重生态恢复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打造绿水青山。从此次对污染环境罪的修改来看,对法律条文做出了进一步的增设和释明,对污染环境罪行为指向的对象更为广泛,污染环境罪的入罪范围扩大,如条文第一款增设的“国家重点生态保护区域”,体现了法律的制定及时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体现出所保护的法益更加明确,但是对污染环境的行为规定依然不够明确具体,尤其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一直存有争议的“处置”行为,这种模糊规定在司法实务中仍会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二、“处置”行为解释之争议
(一)学界关于“处置”行为解释之争议
污染环境罪是环境污染犯罪的基本罪名,入罪要件为“严重污染环境”。其对危害行为规定了三种形式,即“排放”“倾倒”和“处置”,从立法技术上来看,立法者对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模式作了穷尽式列举。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关于“排放”和“倾倒”的解释是清晰的,“排放是指将有害物质直接排入环境的行为;倾倒是指将有害物质通过运载工具等转移至他处排入环境的行为”。[1]由于“处置”的含义比较模糊,其射程涵盖范围广,学界对“处置”含义的解释存有不同观点:一种是根据体系解释方法,认为“处置”行为是污染环境罪的兜底性规定,将等同于或相近于“排放”和“倾倒”的危害行为囊括进污染环境罪的罪名之内。另一种学说则认为“处置”行为的违法程度应低于“排放”“倾倒”。从上文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排放”“倾倒”是将危险物质直接排入环境中造成污染,由于“处置”行为对环境产生的损害后果并不像直接“排放”“倾倒”那样直观,且与污染产生的结果之间存在多种因果关系,因此,应当将“处置”与“排放”“倾倒”的违法程度加以区分,否则将会缩小“处置”行为入罪的范围。[2]
(二)司法解释对“处置”行为的界定
在我国,司法解释发挥着维护立法的稳定性与社会发展多样性之间弥合的重要作用,具有指引司法认定的功能。根据2016年11月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涉及“处置”行为的有8个条文,如第一条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涉及第1项、第2项;第三条认定“后果特别严重”的,如第2项;第四条认定“从重处罚”情节的;第七条认定“共同犯罪的”,其他条款不一一列举。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观点,下列“处置”行为会产生“严重污染环境”的法律后果:非法处置“有害物质发生在特定地点或达到一定数量;二年内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后又非法处置有害物质;非法处置有害物质违法所得达到一定数额”。[3]从这个角度去看待2016年《解释》对污染环境罪“处置”行为之认定,其对行为的次数、行为达到的排放量、违法所得的数额、行政处罚次数等进行了量化,一定程度上讲,似乎使法条更加明确具体,易于在实践中操作,从而得出统一的裁判结果。实则不然,司法实践和立法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事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果单纯依据数据而不结合具体事实和立法目的进行裁判,如在认定的过程中,“处置”行为达到了解释中所规定的排放规模,但未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又如,“处置”行为样态本身是对危险物进行消解,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环境的结果等等。如果对“处置”行为的认定不结合立法目的,不从环境法益保护的立场出发,则会使案件的裁判结果不为公众所接受,从而降低司法公信力。
三、“处置”行为之认定——从刑法保护的法益出发
笔者通过对上述观点的分析认为,对污染环境罪“处置”行为的解释,应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出发,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合理的法益衡量,可以使刑事司法避免形式化,避免损害大众利益。[4]可见,在对污染环境罪进行认定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对何为污染环境进行明确定义,这是对环境污染行为和造成的结果进行罪与非罪评价的重要标准。根据赵秉志教授的观点,污染环境是指“人类直接或者间接地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者能量,从而使环境的质量降低,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系统和财产造成不利影响的现象”。[5]通过上述概念的引入,可以看出,环境污染的构成要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排放的废弃物或有害物质超过环境自身的自净能力,并且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人类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危害。由此推之,污染环境罪应是实害犯,而不是行为犯,在司法实践中,对“处置”行为的认定,不能仅仅从形式上进行判定,将形式上达到一定数量额或者违法所得达到一定数额便认定为污染环境罪,应充分考虑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所保护的法益,从实质上进行认定。申言之,从法益保护的视角出发对“处置”进行解释,更加符合立法的目的。诚然,环境犯罪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危害性,目前部分学者倡导应当将污染环境罪设定为危险犯,只要有对环境造成危害的紧迫危险,便应对其行为加以处罚,通过这种强化处罚的方式以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定罪量刑时强调充分考虑代际利益的考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该从实质上进行认定,立足于刑法处罚的必要性和环境法益的正当性,避免机械适用法条或者司法解释而导致刑罚畸重的情形。从这个角度出发,显然,对“处置”行为进行同类解释方法,即“处置”行为须达到和“排放”“倾倒”同等危害程度的法益侵害,才能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实害犯。相反,对“处置”行为进行扩张解释,认为“处置”行为的违法程度应低于“排放”和“倾倒”,会将一些形式上符合污染环境,但未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程度的危害行为入罪,一如司法解释中所存在的问题,只要“处置”行为达到一定数量、违法所得达到一定数额便认定为污染环境罪,这样的认定方式将会和刑法的本质相违背。
综上所述,对严重污染环境行为进行非难和谴责,是维护好绿水青山、追求代际效益的公正选择,但由于环境责任相比其他责任而言,有其主体、行为和责任实现方式上的特殊性,据此,规范我国的环境刑事责任的认定,是刑罚规范“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双重体现,[6]既有利于环境的修复和保护,又有利于维护个人利益不受超出法规范和法本质的处罚。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决定了部分条文的含义具有模糊性,这就决定了法律的明确性程度,即法条的内涵和外延依赖于学者从立法的目的出发进行解释,同时要求法官释法也要从法的本质出发,唯有如此,才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作出合法、合理、合情的裁判,提升司法公信力。一如学者所言:“法益不仅具有作为犯罪分类标准和构成要件目标解释之机能”,[7]而且还具有“刑事立法和司法政策的机能”,[8]推而及之,对于污染环境罪中“处置”行为之认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应合乎立法目的和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并且结合司法实践,从环境法益的视角出发,作出符合刑法本质的解释和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