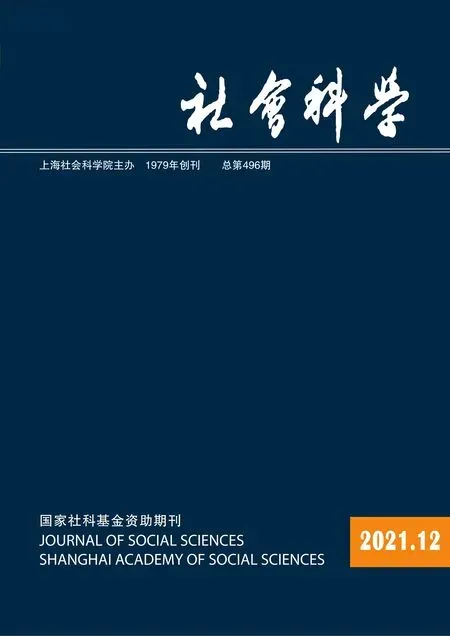多元与融合:风险社会中的危机致贫及治理框架建构
林 茂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我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一方面,这是经济与社会成功转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市场、社会良性互动所致。然而,贫困治理绝对不是一劳永逸的事。贫困,从有形财富比较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既有的收入低下、温饱问题突出的社会事实。(1)孙德超、周媛媛、胡灿美:《70年“中国式减贫”的基本经验、面临挑战及前景展望——基于主体-内容-方式的三维视角》,《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但贫困问题不仅涉及绝对意义上、纵向维度(时间阶段)最为基本的需求无法满足,更涉及横向维度(社会空间)基于先赋性社会资源存在状况的差异比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资源占有的不均衡。贫困也从来都不只是个体生活困境问题,更是与之相关的环境、制度以及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
在社会的复杂转型中,贫困个体所面临的往往是个体困境与社会危机叠加,尤其是在前现代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现代性的风险和突发性危机导致的贫困或“返贫”是值得关注与预警的。举例来说,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近些年来,全球各国在解决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自2019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使这一进展倒退8至10年。(2)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是一种着眼于超越收入的指标,包括安全饮用水、教育、电力、食品和其他六项指标。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新冠疫情或使世界解决多维贫困进展倒退8至10年》,联合国新闻网,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7/1062381,2020-07-16。突发性的公共危机,不仅带来对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同时也促进政治体制的完善和社会群体的博弈,创造出规则重组的机会。与传统社会个体由于脆弱与饥饿而导致的贫困有所不同,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由突发性公共危机所导致的贫困,和不可抗力相联系,呈现出一种不确定的、流动的与无边界的状态。
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是正在经历第二次现代化的“风险社会”,是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其所面临的“不可抗力贫困”却伴随着风险与危机无处不在。迅速的、激烈的、突发的社会危机,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剧了对现代社会稳定性的冲击。(3)林茂:《危机社会治理中的“法律”及其属性》,《求索》2021年第1期。一方面,长效稳定的分配制度在应对危机事件时,其滞后性显而易见。改善分配制度的程序合法性的建立以及新制度的实施,滞后于应对突发性危机所需的时效。另一方面,个体精神领域的贫困,无法简单地通过科技进步与制度完善来解决。
精神领域贫困所导致的社会成员个体之间互动关系模式的改变、社会信任机制的破坏,以及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侵占,都促使既往累积的社会问题在突发公共危机中进一步强化,展现出社会个体精神与能力的双重贫困状态。如何在物质资源丰富的情况下,解决风险社会中的危机致贫问题?这一问题不仅与社会整体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分配制度高度相关,更与个体能力、权利维度高度相关。
危机致贫呈现出不确定性与流动的状态,个体困境演化早已超越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幼年期、老年期、哺乳期等弱势阶段)。基于多元融合视角,对危机致贫治理框架的建构,其前提就在于承认贫困的不确定性和多元化,承认彼此冲突的判断贫困的价值原则的存在,如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定义与判断。价值原则的多元化使我们在认识贫困产生的机制及其后果上产生不同的“优先性”(priorities)排序。本文试图超越个体-社会两极对立的格局,从人类共同体视角出发,探寻和总结社会危机引发的贫困问题的内涵、特征及其治理框架。只有聚焦于现实视角,才能促使我们更容易阻止真实存在的非正义,从而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二、危机致贫:不确定性、流动性与无边界性
现代社会面临着动荡 (Volatility)、不确定 (Uncertainty)、复杂 (Complexity) 与模糊 (Ambiguity) 的风险。(4)应验:《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危机治理》,《中国治理评论》2021年第1期。“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所招致的匮乏状态与以往研究所发现的由物质需求导致的贫困有所不同。(5)[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 2 页。在风险社会中,与公共危机相伴,贫困作为一种生活状态,具有不确定性、流动性与无边界性的特征,且往往是两种维度贫困混合的产物。(6)Robert Walker, The Shame of Prop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第一维度的贫困,即维持生存需要的最低物质需求。这一维度的贫困高度同质化且可量化,如贫困区域和低保收入的划分多着眼于此。第二维度的贫困(多维贫困),则是精神、文化、法律、权利方面的贫困。(7)参见Sabina Alkire, Suman Seth,“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Reduction in India between 1999 and 2006: Where and How?”, World Development, Vol.72, 2015, pp.93-108。
危机致贫同样涉及上述两个维度,具体是指受制于现代性的整体风险而产生的公共危机,进而由这一危机所引发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匮乏。这种匮乏或“阙如”的状态,伴随着相对剥夺而产生,与社会正义高度相关。既往的研究中,多数反贫困研究以探寻完美正义的应然性为目标而建构理论框架,将抵抗贫困的结果正义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并试图确立一种先验性的完美正义制度的框架,从而实现按照“社会的基本结构分配某些基本物品”。(8)[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页。这样的理论框架对现实背景下个体或群体危机困境的判断难有突破。原因在于,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以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加剧了基于制度的贫困,与社会选择条件下对权利的剥夺有一定的相关性。
以被征地或拆迁的农民为例,第一维度的贫困多是征地赔偿款低于市场价格而导致的物质贫困——农民不能再购买住房,既往社会关系受到破坏而没有得到补偿等。这一维度的物质贫困通过行动实现补偿平等即可以解决。事实上,自2010年后,我国因被征地或拆迁引发的物质贫困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二维度的贫困却更加常态化。一些被征地或者被拆迁的农民从事保安、清洁工等职业,从农民变成市民,部分人无业,依靠房租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财富而言,或许已然丰裕,但其在能力及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等领域的匮乏状态却更加突出。换言之,解决民生问题,不等于获取民生权利。在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这一群体的部分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面对突发性的公共危机,如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依靠租房、从事底层体力劳动的“市民化农民”群体,其贫困的不确定性集中体现为抵御农业生产活动中的自然风险的能力不足以抵御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不断累积就可能成为一种整体性社会危机。当疫情导致人口流动减少、生产经营活动萎缩进而引发退租、失业等社会风险时,刚刚成为“食利者”的“市民化农民”既有的生活经验中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和技巧失去了应有价值。(9)张康之:《论风险社会中的危机意识》,《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
究其原因,“农民市民化”后所拥有的重要权利仍是基于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但源自农业生产经验的劳动力并不被城市社会需要,无法用于交换。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丧失了主体性能力,是“被制度化安排的市民”。(10)文军:《“被市民化”及其问题——对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再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这一社会现象伴随着现代社会的推进而涌现,并非新生事物。在工业革命发展初期,农民由于土地有限而脱离土地,四处谋生,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11)[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将这一群体纳入,为他们提供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避免他们因劳动力无法在城市市场交换而沦为赤贫,但这仅仅是在常态稳定的现代社会中的状况。随着公共危机与整体性风险的出现,叠加在这部分群体身上的则是:禀赋权利不能充分发挥的贫困,(12)Yan-Yan Chen, Liu Hong and Robert Walker, “Reconstructing Poverty-Related Shame Among Urban Seniors in China: An Exploration of Their Narrated Experiences and a Reflection on Anti-Poverty Interventions”,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Vol.12, 2020, pp.1-21.且交换权利由于公共危机无法得到满足,进而导致突发性的、不确定性的穷困或“返贫”。这种贫困伴随着公共危机而不断流动、扩张,又呈现出无边界性的特点。全球经济与社会的一体化,使得一国以内的危机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地理位置或空间,如全国各地的“三和青年”们,(13)参见田丰、林凯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海豚出版社2020年版。流动性促使危机致贫不断叠加与放大,由此所造就的贫困也成为全球范围内流动的贫困。
(一)相互叠加的匮乏状态
风险社会中的危机致贫,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种社会关系,(14)李小云:《消除贫困:中国扶贫新实践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更加准确地说是一种分配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冲突在危机境况中,以叠加的方式呈现出的资源匮乏的状态。因此我们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有效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15)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 25 页。针对叠加的匮乏,解决的办法是提供底线保护,聚焦于不同群体对食物的支配/控制能力的权利差别关系。这样一种叠加的匮乏状态,表现在权利领域,是象征职业群体能力的技术资格证及“禀赋权利”(土地、自身的劳动力)不再有价值,其“交换权利” (从事生产并与他人交换以获得商品)不能实现。在现代社会中,当一个人基于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而处于贫困状态时,这一状态呈现出权利和能力被剥夺的局面是客观存在而不可控的。(16)[美]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8页。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行业萧条与失业潮,进而引发的“房贷”“车贷”等各种借贷体系的崩溃,在美国的“次级债危机”中得到深刻的展现。叠加的匮乏状态不仅体现在导致匮乏的负面原因层层叠加,在呈现的后果上,其匮乏的类型与程度更是一场深刻的危机,即物质、精神与权利的多重溃败。其多重性表现在物质领域,是基本物品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特殊需要”更是不被满足,如自我实现的需要、爱与尊重的需要。这种多重性表现在权利-能力领域,则是个体无法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
面对这一多重匮乏的状态,古典的治理框架对基本物品的概念化与一般化,使得传统的贫困治理成为一个同质化的过程,难以解决这一贫困问题。根据对基本物品的获得来判断制度的优劣以及正义的实现效果,只是考虑到贫困的单一中心发展模式中某一阶段的物质匮乏状态。实际上,在风险社会中,一种复合的能力(capabilities)、权利与功能,及其所带来的自由选择,使得个体有可能实现各种功能n元组合, 其“复数能力”的自由建构才是解决匮乏状态的关键。(17)[印] 阿玛蒂亚·森:《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应奇、刘训练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从多元整合的角度来看,基于自由选择发展自身能力的权利与保障多重能力,皆需法律与政策层面的支持,尤以底线保护为重。底线保护更为深刻的内涵在于,底线所蕴含的物质、精神与权利的基础性资源平台,表现在个体身上,则是通过选择各种可能的能力与功能的组合,(18)[印] 阿玛蒂亚·森:《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第215页。这是个体解决现代性不确定风险所导致的贫困问题的主要路径。
就此而言,社会关系中的信任、人的自主性、人际间差异性,还包括受教育、医疗卫生、福利制度等保障人的权利与能力,可用于理解危机与贫困之间的关联。因此,在哲学层面增强个体“人”的情感、文化、道德等对规范和规则的作用,在社会学的层面将集体、行动看作建构以软法/活法为代表的法律体系的重要元素,从多元主体参与的视角出发理解规则的形成和现代国家管理的转型,是对危机致贫问题作为社会关系的最为基础性的回应。
基于社会群体的异质性,我们可将贫困进一步类型化,将其分作先赋性贫困、自致性贫困、制度性贫困等。但基于社会危机而引发的贫困,涵盖且不限于上述类型。在多元整合发展的模式下,要将贫困的常态化与非常态化加以区分,因此,将需求决定论置于贫困研究之前就显得尤为重要。面对风险社会的来临及其挑战,强化危机意识,理解贫困问题中的多重叠加状态,或许将催生出风险国家 (risk state) 这样一种新型的后行政国家的治理体系,(19)刘鹏:《风险社会与行政国家再造:一个行政学的阐释框架》,《学海》2017 年第 3 期。从而从根本上提升个体的复合能力及其能力所蕴藏的社会功能。
(二)选择及多重需求难以满足的困境
上述所言“复数能力”的缺乏,与角色集的概念类似,并不是彼此互斥的缺乏状态,而是表现为整体性的多重能力及功能的缺乏。“复数能力”的缺乏并非简单的各种单一能力所具有功能的无法实现或不完全实现的总和状态,而是对多重能力的选择、重组与整合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表现出的自由,以及日常生活实践的逻辑与智慧的缺乏。这种缺乏首先是能力种类不足——做选择的前提在于有多种选择存在。其次,缺乏平等地进行多种选择的机会。最后,在机会平等与选择自由之间,个体即使拥有多重能力,仍缺乏实现多重能力所需的选择的智识与自由。
现代社会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但并不意味着工业社会比农业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减少。事实上,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返贫风险,每一次都激发出社会学意义上对确定的、农耕社会的怀念。这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宏观社会结构的认识高度一致,即“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对贫困的定义,多是就同一类资源和实物占有的比例多少而言的。(20)梁树广、黄继忠:《基于贫困含义及测定的演进视角看我国的贫困》,《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单一的、简单的需求所带来的稳定性,在现代风险社会之下,已然改变。
风险社会中危机致贫的突发性、客观性与边界不可控紧密结合。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基于满足生存的需要而对农民与乡土的珍视,呈现出单一的资源占主导的美好生活。然而,现代性的危机致贫,所要满足的则是多重的需求与资源占有。所要求的能力-功能重组所创造的美好生活,是难以通过简单的物质需求满足就可以实现的。这一重组打破了既往的对于贫困群体的简单想象。
单一需求的贫困群体想象源于劳动分工所造就的专业化发展。长时间以来,专业化被认作现代社会稳定的构成基础,职业群体之间所具有的异质性知识和能力,本不具有统一量化评比的可能性,因此也不具有基于评比结果而产生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和普遍意义上某一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的贫困。然而,流行于各学科的马斯洛需求等级所体现出的从物质到精神的排序理论呈现出中心主义的霸权,忽视了贫困的整体性,即物质需求的满足所对应的能力,及这种能力所获得的社会认同在常态社会中低于满足精神追求的能力所获得的社会认同。
农民所掌握的四季生产的知识与制造芯片的科学家所掌握的微电子技术知识并无优劣之分。从微观的个体角度来看,阅读识字的能力,与烹饪料理家务的能力皆是生活所必需,在风险社会中,面对存活和发展的需求,烹饪和家务能力的必要性甚至更强,但阅读识字等作为满足前者之后的“奢侈品”与“富余的爱好”则变为必需品。突发性危机促使我们正视物质、精神与权利的多重贫困和剥夺的匮乏状态。
在此意义上,风险社会所带来的危机致贫所呈现出来的对能力的需求打破了从物质(低级)到精神(高级)这一中心主义的理论路线。风险社会的系统性,不同风险之间暗藏着的丰富内在联系,(21)[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使得现代社会公共危机,通常以专业分工链条上某一环节的平衡被打破而呈现,进而导致社会面临全面的风险与多重需求无法同时满足的状态。
三、危机致贫的发生机制:分配与能力
现代社会中风险的非边界性突出,全球化使得一国以内的风险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地理位置或空间,风险的流动性促使基于突发性的公共危机也不断叠加与放大,由此所造就的贫困也成为全球范围内流动的贫困。这一流动性使得现代危机致贫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还是受制于空间发展的社会关系集合。现代性危机使每个人都难以置身事外,整个社会乃至全球成为共同体。基于常态性的、全面性的风险而导致的突发性危机,也促使共同体内资源发生变化。不同的社会和国家,在应对现代性的风险的过程中,基于危机而产生的贫困深受分配不均衡的影响。
对现代风险的控制需要整体思维,更需要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合作通常建立在两种方式之上:通过暴力或通过自愿、自发。(22)[英]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严复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88页。局限于传统行政区划和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风险控制难以应对流动的外生性风险。因此,个体的社会成员或国家居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中,常态化的分配方式,即基于既有禀赋差异的分配将进一步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无论处境最差的群体是否应该为自己的不利境地承担责任,在资源共享层面,面对“无知之幕”,作为共同体的社会,富有者是否应当为禀赋差异负责而救济贫困者都成为一个难题。(23)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Revisited”, Ethics, Vol.113, No.1, 2002, p.122.
事实上,在共同体之中,区分“选择(分配)”和“环境”,排除由环境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个体应当为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贫困承担责任。在一个社会内部,如何解决由天赋不平等所导致的贫困?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旨在缓和自然资产的分配对贫困的影响。但是在寻找与确定处境最差者(最为贫困者)的指标时,这一特殊性的建构,暗含了主观价值评判。(24)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74.从分配的角度来看,自然资源与天赋不应该被用来为个人谋利,而应该为社会全体成员所共享。共同的财富必须属于共同的主体,将差别原则建立在共同体观念的基础上是一种路径,而个人对其天赋是不应得的和不应拥有的,是否意味着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对它们是应得的和应拥有的?依照对所拥有的天赋的不同看法,个体与其所对应的天赋之间,是所有权意义上的天赋的“拥有者”(独占者与绝对支配者)还是为共同体所有的天赋的“监护者”(使用者)?(25)Michael Sandel,Liberalism and the Limit of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99.因此,在危机状态下,由于分配而导致的贫困,这一问题本身与资源的先天分布不平等类似,是环境作用于个体或人类社会的结果。
(一)分配与再分配:总体性风险打破分配平衡
社会世界基于人的总体性智慧并通过征服自然所获得的财富,却在总体性的风险出现并成为危机后产生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不平衡。面对共同性的危机致贫,财富、权力的分配与贫穷之间的关系在亚洲文化中已经建立起因果的认知。(26)张清:《贫困与自由:基于印度“不平等”的宪政分析》,《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2期。在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避免分配不均而产生的危机成为常态化社会条件下生产关系变革的动机。(27)孙永平:《自然资源与经济増长关系的历史考察——三次“中心-外围”格局的形成及其转换》,《经济评论》2011年第2期。在风险社会中,由社会本身运行规律所导致的全面风险,基于专业化的分工与科层制的发展,在一国内部无法依托单一部门进行防范和控制。面对突发性的经济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环境危机,既有的分配格局与资源供需平衡被打破,调整既有的分配制度所需要的统筹管理与时效,常常使得再分配的平衡具有滞后性。由此而产生的危机致贫深受分配制度影响,如“中产阶级陷阱”,以一种突发事件出现在个体日常生活之中。
社会内部的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贫富分化是稳定社会的常态,但现代性框架下的危机加剧了这一分配制度的不完美。如果我们运用斯宾塞的人格化的理论,将会发现不同国家先赋性资源的多少源自于对自然的掠夺,这本身存在贫困危机。但在整体性风险引发的突发性危机中,对风险的认知增强了所有行动主体的危机意识,这会导致这种资源占有量的分化更为明显。因此,危机致贫,在相对意义上而言,还源自既有分配的静态与惯性,无法满足危机之下需求的增加。借由危机而必须进行的再分配,对既有的分配框架的改变,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对既有分配框架的习惯和安全感或再分配制度建立的滞后性,都可能产生新的贫困或加剧贫富分化。
既有的分配制度对处于弱势地区和国家的资源掠夺,将进一步导致这部分群体处于全面危机与贫困之中。然而,不管是先赋性的差距(对自然的掠夺)还是分配的掠夺,两条掠夺的路径,从未有心甘情愿的臣服者。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危机中,对新冠疫苗的争夺,超越了原有的市场经济下商品交换的属性,演变成为强势国家与贫困国家的生存竞争,欧洲各国对美国疫苗预定的争夺即属此例。
在全球化过程中,多中心之间的经济、人口、商业的流动,让一国内部的危机在各大陆之间传播“变异”,在认知领域强化了个体对风险与危机的认识。“人人自危”与对贫困者的放弃、掠夺,这是社会在战胜贫困的道路上不得不面对的“自造的囚笼”。这一危机所带来的贫困均基于进化论思维与中心化/同化逻辑,排除多样性与多中心,这将可能导致全球陷入普遍性的危机致贫。
换言之,作为差异性存在方式的传统贫困,对于阻隔危机(如新冠疫情)的公共性传播或许反而是有积极意义的。如那些基于低需求而独立于全球化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缺乏流动性,也减少了对全球化的依赖,由此避免社会系统因过度满足“偏颇性供给”的需求而发生危机致贫。类似前现代社会中,粮食自足而不依赖进出口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避免共同危机致贫。但一种以单一中心或单边主义为主的社会发展模式,制造绝对的富有与绝对的贫困本身就是违背多元中心发展的垄断模式,全球化危机致贫背后更深刻的却是本身固有的特定区别,(2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7页。在文明与非文明种族之间如此,在生命体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在对抗危机致贫的过程中,基于差异而产生的整合分配再平衡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个体能力无法通过常规分工与社会交换实现
在全球化进程中,突发性公共危机防控取得成效的核心技术往往成为治理危机问题的关键。如同前现代社会中农耕制度作为核心因素可以缓解物质贫困一样,现代社会中人的能力和基于此而产生的技术是解决贫困的重要因素。技术为解决社会贫困问题提供了工具,而技术功能的实现则依赖于社会内部成员间权利与社会整体权利的分配。
如前所述,基于危机的突发性与不确定性,在整体性危机到来的时刻,个体全面发展的权利难以通过常规的社会运转链条和交换行为实现。个体多重能力不仅包含一个人利用各种能够获得的法定渠道以及所获得的可供选择的商品束的集合——对事物的所有权是现代社会中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29)Amartya Sen, “Development: Which Way Now?”,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93, No.372, 1983, pp.745-762.——同时也包括对其所拥有的能力进行自由交换的权利。受制于突发性的社会危机,对贫困的定义不再是数字标准,而是具体的情景以及情景之下的行动限制。只有给予人们在行动上更大的自由、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机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将危机致贫消除。(30)Amartya Sen, “Development: Which Way Now?”,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93, No.372, 1983, pp.745-762.不仅如此,危机致贫也不再是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每一个国家,是整个人类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权利视角”(Entitlement approach)下,造成饥荒的真正原因并不是食物短缺,而是由于个人所拥有的交换权利不断下降。(31)[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4页。在面对公共危机时,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数量紧缺,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社会治理在危机环境中不仅应当提供基本的食物供应和保障,更应该制定可保护人民权利、发展可行性能力(capability)的措施,从而建构人们进行选择和行动的“实质性自由”。(32)[美]玛莎·C.纳斯鲍姆:《寻求有尊严的生活》,田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基于能力而产生的贫困的焦点不在于一个人事实上最后做了什么,而在于他实际能够做什么,即能力所产生的功能实现,而无论他们是否会选择使用该机会。(33)[印]阿玛蒂亚·森:《资源、价值与发展》(下) ,杨茂林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 271 页。通过自由的选择和发展,个体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同的功能与特性,利用这些功能和特性获得成就、福利以及人的主体性,从而真正摆脱贫困。这是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先赋性资源依赖降低后,人对自身自决性的体现。
在现代社会中,公共危机所导致的贫困状态,其内涵和意义都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向,在既有框架下定义贫困群体,不但要面临本身所既有的能力、权利的缺陷以及功能的不可实现,还必须承认面对“具体性的事物和问题,只有在其出现了某种端倪的时候,才能作出应对的选择”(34)张康之:《论风险社会中的危机意识》,《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的无能。危机致贫的突发性、流动性与无边界性,让身处危机致贫中的行动主体无法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当风险以危机事件的形式出现的时候立即作出反应。
四、迈向多元融合的危机致贫治理模式
个体与整个社会皆有危机致贫的风险。回顾人类社会多线发展的艰难历史、认识困境与应对困境,可以发现人类对贫困的认知体系的探索经历了差别化-多元化-一体化的不同阶段。差别化阶段,主张尊重主观先赋性因素的异质性与个人选择的自由;多元化阶段则强调在差别中去中心化发展,通过分配制度上减小贫富差距,尊重多样化发展,避免霸权主义与同质化;一体化阶段,在保留多元的基础上,强调实现以人类共同体为基础的“共同善”以对抗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不是铲除过去的先天性的差异性。这里的一元概念指的是同质性、单一中心的贫困(治理)模式;多元则指的是异质性、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模式。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面临一元和多元并存,强调多元一体、多元融合,而不是单边主义或同质化,其目的在于回应和尊重多样性与人类总体价值。
我国的多元化发展不仅包含兼容并蓄的不同民族和地域的统一协调发展,还包括在生产技术领域中不同技术间打破壁垒与界限,相互融合,提高生产力从而走向繁荣和富强。相比于海洋文化与殖民者开拓精神,我国本土的有关利益的、宗教的、对生命本身的理解等多种状态综合成一种对世界整体干预状态。我国在发展路径与治理模式上多中心、多元融合的发展模式,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兼容并蓄与相互转化的辩证思维,历久弥新,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相对于西方二元且对立的发展模式,在社会理论层面,我国社会治理的多元化特征与优越性,值得学界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的讨论。
建构多元化的发展路径本身在于通过多元化消解不同单元的界限和排斥,从而减少面对整体性危机时的机会不平等。“强调以多样和统一辩证的观念观察世界,既强调世界多样、道路多样、文明多样,具有多样性,也注重共同性,它反对‘西方中心论’‘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是主张国家平等、文明互鉴、包容发展、互利普惠的文明”。(35)韩庆祥:《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丰富内涵》,《学习时报》2021年8月30日。只有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多元之间的融合,才能让那些原本有可能凭借自身的智慧和能力改变经济状况的群体平等地获得重要的对抗危机致贫的机会。
(一)个体基于自由发展的可行能力塑造与实现
可行能力的多元化是亟须被正视的解决危机致贫的重要因素。通常而言,个体受教育越多、知识水平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小。基于个体差异性,贫困问题面临现代性的转向,对贫困的认识更多聚焦于交换权利的不可实现,而非禀赋权利的不可获得。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中,我们可能将面对更多多元化发展带来的挑战与不确定性。其结果必然是: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就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的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36)[奥]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页。面对疫情叠加衰退,社会呼唤多边反危机协调新模式以建立底线保护。(37)雷达、武京闽:《疫情叠加衰退:呼唤多边反危机-协调新模式》,《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4期。
从整体论意义上看,解决危机致贫,能力、权利与自由均涉及个体内在的自主性,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同义反复。在能力与功能实现之间,受到三组“转换因素”(conversion factors)的影响。第一,个人转换因素(如新陈代谢、身体状况、性别、阅读能力、智力),影响一个人怎样将商品的特性转换为一项功能。第二,社会转换因素(如公共政策、社会规范、歧视性行动、性别角色、社会阶级、权力关系)。 第三,环境转换因素(如气候、地理位置),在从物品特性转换为个人功能的过程中产生影响。(38)Ingrid Robeyns,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A Theoretical Survey”,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Vol.6, No.1, 2005, pp.93-114.从能力-功能的角度解决贫困问题,超越了个体层面的能力建构,强调应当更多地着力于公共政策层面能力的获得与基本需求相结合,使基本能力(basic capacity)在解决危机致贫问题时更具效力。(39)郑智航:《全球正义视角下免于贫困权利的实现》,《法商研究》2015 年第1期。即,在单一中心模式下,极端的贫困问题的解决只需要通过获得相应的基本能力,进而占有维持生命活动必需的食物和住所。在其他语境下,包括经济发展的更为一般的问题,这个基本能力的构成清单可能很长而且更不相同,(40)[印] 阿玛蒂亚·森、[美] 玛莎·努斯鲍姆主编:《生活质量》,龚群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7 页。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言,人的功能是获得幸福生活(Eudaminia)的能力。自由和主体性成为能力的本质体现,这一观点如前所述,深受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影响。(41)[印]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页。解决危机致贫问题,从个人优势视角来看,对能力的研究探求的结果归结为“自由”,一个人能否自由地做他有理由珍视的事情,这一情形比拥有“基本善”更能体现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优势。(42)[印] 阿玛蒂亚·森、[美] 玛莎·努斯鲍姆主编:《生活质量》,龚群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1页。
发展多重能力的自由、自主选择并整合能力,成为应对风险叠加的现代社会中危机致贫的一种设想。如对于贫困村与乡村贫困家庭,我们国家扶贫的思路也发生了从“为生存而生产”向“为市场而生产”的转型。(43)王春光、单丽卿:《农村产业发展中的“小农境地”与国家困局——基于西部某贫困村产业扶贫实践的社会学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扶贫政策也聚焦“服务转向”,通过建构自下而上的农民赋权的维度,呈现出基于农民主体的差异性为主的多元化的扶贫方式。(44)李小云、徐进:《消除贫困:中国扶贫新实践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危机致贫是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产物,减少或消除贫困必然涉及到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减少或消除贫困的机制也表现在扶贫政策与社会系统的互动上。(45)王浦劬、汤彬:《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 9 期。从社会学角度看,复合型治理结构决定了政治与行政之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46)王春光《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主体性——以 40 年农村发展和减贫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 11 期。
同时,个体自由发展可行能力在现实领域,得到一定的实现。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应确保个人在所拥有的交换权利不断下降时,能使用合法的分配方式掌控事物所有权的能力,这一权利再分配的体系与国家权力高度相关。国家应提供再教育和培训资源,提供就业机会,使得农民能力复合化、多元化以应对现代化专业分工所带来的生存危机,从而实现在城市中再就业。促成社会群体能力多元化的过程,在群体性结果的层面,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即专业化的多中心、个体的多重能力、地理空间的多中心发展。这一发展模式,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在运转,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征。
(二)国家-社会系统内部:差别化原则与多元融合
上述个体能力的建设,是从微观行动角度出发,建构危机致贫的治理框架。从宏观结构角度看,在多元中心模式下,如何在一国内部应对危机、建设个体成员多重能力?差别原则应用于现代化过程中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似乎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这一行为本身在方法论上的可能性讨论并不是重点,面对突发性危机,基于分配方式而造成的贫困及非正义讨论才是争议的焦点。富裕地区的居民是否有基于正义帮助危机致贫地区的义务?基于先验主义视角既定的自然资源分布不均的现实与建设多重能力而选择的资源再分配原则,实现正义的过程和以正义为目的的行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分离,“每一个人对总体可利用资源的一份都有一种平等的显见要求权”。(47)[美]查尔斯·贝兹:《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丛占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如果能够践行资源再分配原则,资源较为贫乏地区的居民获得发展能力所需要的经济条件保障就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这一合法性从人类整体的利益来看,常常导致以正义为目的的行动产生非正义的行动过程,如为抢夺疫苗而忽视既有贫困地区群体的生存状况。为解决先赋性因素的不平等采取再分配行动而实现结果平等,是不能忽略过程平等的。
基于分配制度而引起的贫困受制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一个国家经历、进展如何的关键因素是其政治文化”。(48)[美]约翰·罗尔斯:《万民法》,陈肖生译,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157页。即使我们承认基于自然资源的分布而导致的传统贫困是一个事实,但是分配制度对自然资源分布的处理方式,就关涉到国际制度的正义与否。(49)高景柱:《评约翰·罗尔斯与查尔斯·贝兹的国际正义之争》,《世界哲学》2014年第4期。
因此,在制度体系框架下谈论贫困以及非正义的解决方法,多元中心的模式除了考虑到自然资源的分布属于先赋性的既定因素,还应考虑到基于道德上的任意性与人的自由选择等因素。正是由于这两个因素,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50)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承认贫困的先赋性与客观性,由此而实行的公共行为与制度建设应该维持多重能力建设的目标,避免公共危机加剧传统贫困群体的贫困,进而实现人类共同体意义上的协同发展。在多中心发展模式下,为了减少危机致贫,基于系统外部力量的援助义务致力于满足需求,使个体成为一个合乎情理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是再分配性援助义务的目标。(51)[美]约翰·罗尔斯:《万民法》,第160页。
(三)协同合作框架下打造多中心人类共同体
除多中心下的差别化发展以外,多元融合的模式建构还应考虑差别化所带来的分歧如何解决。基于社会选择以及社会分层的结果所展现出的等级与区隔,应将贫困治理的目标缩减为减小差距与去“等级化”,由此而衍生出针对贫困治理的备选方案。如果将相关群体实际生活评估体系的价值原则进行排序,我们会发现,贫困治理在执行层面以实现统一标准的需求满足为基础,将会忽略价值多元与利用局部排序的整合过程。(52)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Penguin Books, 2009, pp.2-7.正是基于更高层次的预防和消除危机致贫,贫困治理模式可能发展出多元融合的方案。
在理论建构层面,用社群主义来对抗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53)姚大志:《评桑德尔的分配正义观》,《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建立起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公共危机最有力的武器。(54)习近平: 《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人民网,http://hi.people.com.cn/n2/2020/0416/c231187-33952040.html,2020-04-16。尊重差别原则,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实现团结合作,对解决危机致贫问题的结果有个体化与整体化之分,从多元一体的角度来看旨在建立以社群主义为核心的联合的善,或者说共同的善。(55)[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第170-172页。这有别于单个的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善,即一个国家/民族根据审慎的合理性而乐于从最高级的计划中选的那项合理生活计划所决定。”(56)[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426页。相对于整体性的危机致贫,联合的善、基本善或者“天赋权利”意味着一个不能以任何其他善的目标来换取的前提性价值。(57)李伟:《正义与公共善孰为优先——论桑德尔与罗尔斯政治观的分歧》,《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共同的善是对人类共同体共有价值的追求,表现在危机致贫问题上,它要求限制个人选择与追逐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基于共同善进行援助与再分配。在多元中心模式下,强调社会有机体整体建设与个体成员发展并重。将贫困看作全人类共同的困境——不仅看作某一个体基于先赋性或自致性因素的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待贫困、弱者以及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的态度。
对抗危机中的困境,中国本土化中的文化自觉与多元包容,将客观与主观结合,实现了授人以渔、助人自助的解决贫困问题,其最基本的前提是承认人际间差异性,进而在差异的基础上实现资源整合。危机致贫的多维度衡量所产生的解决贫困的能力也是复数的。应对贫困多元一体化的态度,体现在我们国家当前,则是重视贫困的多样性并采取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路径。面对不确定性,具有理解风险、接受风险和采取措施的意愿和能力,解决自身危机致贫问题,并进一步确认多中心的秩序,强调参与者的互动过程和能动地创立治理规则、治理形态,这也是我国战胜社会整体性风险与危机致贫的挑战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五、讨论与反思
多元融合下的危机与贫困,不仅需要判断既有的制度和规则的完善情况,更需要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二元互动的角度判断社会本身所处的时代及其转型。在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所造就的社会公共危机中,我国脱贫攻坚仍能够取得全面的胜利,并经历了资源分配的不同模式的转换与融合。从管理向治理、服务的发展,这是国家应对危机致贫问题与现代化建设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危机致贫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的社会关系,但以家庭为单位的,以血缘、地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未消失。相反,随着人口迁徙,这样的社会关系在危机致贫的背景下,在大都市社区治理中日渐发挥作用。
多元融合作为更为深层次的文化结构,在政府主导的脱贫工作中表现为不断吸纳符合现代化专业分工的伦理要素,构成了家庭、国家和社会同向性的互动模式,从而使得个体层面与社会整体层面得到统一稳定的发展。治理危机致贫的主题并不仅是试图建构完美的正义社会或制度,而是建构现实可行的多元化的分配方式,以减少导致非正义产生的条件,在个体层面发展多元复合能力。同时,进一步赋权个体,强化通识教育,促进选择自由将复合能力转化为功能,实现多元到整合的过程,进而阻止人类共同体意义上的贫困及非正义。
强调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与社会的共同富裕,正是对抗危机致贫所带来的异质性与不确定性的重要路径。在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利益基础上,建立起发展个体的多重复合能力的社会分配制度,以激励人们根据自己的选择、依从那些决定着其日常行为的动机而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其他人的需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58)[匈]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面对个体与社会、一元与多元、同质性与异质性、本土化与全球化,身处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中,不抛弃对立,但调和对立、解除对立,建构多元融合的知识体系,在认识危机致贫的理论道路上,才能避免通往被奴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