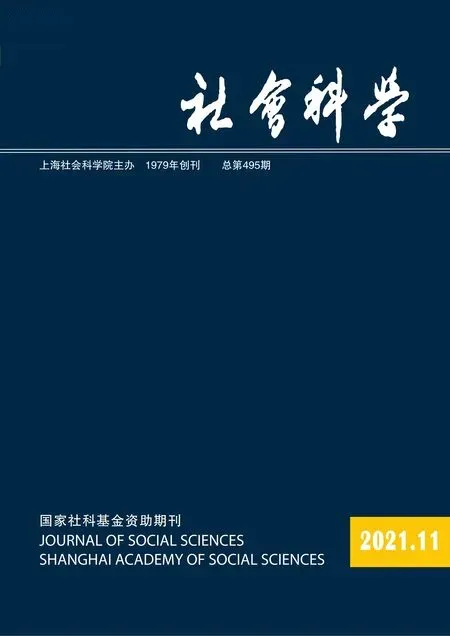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批判及中立性地缘议程建构的可能*
于海洋 张微微
地缘政治学诞生之初就与权力政治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地缘政治理论长期饱受质疑。二战中德国地缘政治思想与纳粹主义的结合,更使该理论一度陷入绝境。但是,地理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当前,中西方学者都在尝试建构新型理论模式,解释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政治与空间关系所发生的新挑战、新问题。初现轮廓的新地缘政治议程不可能与旧的传统完全决裂,但又必须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提供新的可能性。如何实现传承与创新,需要从重新梳理地缘政治理论的传统假设开始。
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错误推论及合理忧虑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包含坚固的权力政治内核,这种关联性使地缘政治受到长期批判。二者的绑定固然限制了地缘政治理论的与时俱进,但这种绑定所揭示的忧虑同样具有学术和政治层面的双重合理性。
(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错误推论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所构筑的体系结构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取向,以海陆两极对峙的全球结构和毗邻者为敌的区域结构为基础,展开自己的分析。德国学者C.施米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部海权对抗陆权、陆权对抗海权的斗争史”。(1)[德]C.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林国基、周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让地缘政治理论化系统化的麦金德则认为,“海员对抗大陆人”(2)[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构成了国际关系史的永恒主题。这种分析经常陷入僵化,并产生四个失之偏颇的推论。
推论一:海陆对峙是全球地缘传统的核心内容。无论是陆权说、海权说还是边缘地带理论,都建立在海陆冲突的原点之上。海陆对峙学说用海陆二分法,对国家间关系进行了不恰当的简化,把复杂的地缘政治冲突归结为海陆冲突,海洋和陆上大国之间的关系具有悲剧性的宿命论色彩。但是,国际关系史上存在着大量陆权国家间以及海权国家间的冲突。在复杂的国际冲突中,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竞争是存在的,但是,海权国家间的竞争、陆权国家间的竞争,甚至海陆国家联合对抗第三国(可能是海权,也可能是陆权)的情况,同样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高度冲突化的古代和近现代国际体系中,联盟与对抗的逻辑是复杂的,海权和陆权并非最重要和唯一的干预变量,有时甚至不起重要作用。
推论二:权力政治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全部理由。马汉认为,“地缘政治是指国家政治权力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3)[美]阿尔弗雷德·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4 页。杰弗里·帕克也认为,地缘政治“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4)[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认为地缘政治需要权力、服务于权力。这使传统地缘政治学说对世界的看法趋于悲观,地缘政治理论总体而言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更加关注国家间冲突和竞争。但是,正如现实主义并不只是权力政治一样,地缘政治冲突也并非都由权力因素产生。合理的安全忧虑及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包括资源稀缺、疾病、非法移民、武器及毒品走私等)也可以经由地理路线传递,或受地理因素的影响而诱发重大的政治变化。(5)M. Coleman, “Immigration Geopolitics beyond the Mexico-US Border”, Antipode, Vol.39, No.1, 2007, p.60.
推论三:空间的控制和占领是地缘政治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格拉鲍弗斯基在阐述地缘政治学的产生时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使地缘政治学产生”,对“空间的欲求”成为国家研究地缘政治的理由。(6)参见国玉奇、[俄]В. П. 丘德诺夫:《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占领或者控制,以及防止地缘政治竞争者的占领和控制,成为地缘政治的终极追求。拉采尔认为,大国都有扩大领域的倾向。豪斯霍弗强调德国对泛欧区的占领控制。麦金德提出由控制东欧到控制心脏地带,再到统治世界岛、统治世界的三段论。马汉则强调对具有战略意义的狭长海上通道的控制。总之,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假定存在着一片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土地或海洋,发现它和占有它才能实现国家的持久强盛。传统地缘政治学说忽略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空间控制权的争夺是所有冲突中旷日持久和难以和解的,尤其当不同国家都声称对同一空间存在巨大需要时,空间的价值经常被控制所带来的成本与代价抵消;第二,空间的占领控制和有效使用并非同一概念,国家对空间的利用能力存在巨大差异,受到时代背景、生产力水平、国家治理能力等要素的影响。
推论四:将国际政治简化为大国政治。经典的地缘政治逻辑认为,陆权大国和海权大国充分利用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优势的地理环境,争夺全球主导地位。它们之间的冲突会产生全球性后果。小国可能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充当棋手控制的棋子或“支轴”等角色,但它们的角色依附大国而存在,不是独立的。事实上,地缘政治的基本假定在于空间会对政治行为体和政治关系产生普遍性影响。除全球大国外,其他政治行为体也受到地缘政治规律的制约,一般国家间关系不仅是大国地缘政治的简单附庸,它们在特定空间结构中的互动也会对区域和全球体系产生重要影响。那种把国际冲突与合作的所有根源和影响都归结于大国的逻辑,忽视了普遍存在于更广阔世界中的多元主体、冲突因素、利益需要及潜在的解决方案。
(二)传统地缘政治的合理忧虑
总体而言,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霸权主义及帝国扩张深刻影响了传统地缘政治研究。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固然有着将强权国家侵略行为正当化、暗示冲突必然发生等弊端,但其所反映的地缘冲突现象也是存在的,国家基于地理考量而产生安全忧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正当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合理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地理因素在国际冲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国家间冲突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邻国间的斗争以及海洋国家、边缘地带国家、陆地国家间的斗争既长期存在,又显然与地理因素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意味着地理的毗邻和地理类型的差异容易产生国家间冲突。正是基于将地理因素视为国家冲突而非合作的诱因,詹姆斯·多尔蒂等学者才会得出相邻国家是天然敌人的观点。地理毗邻增加了国家间交往的密度,使冲突发生的概率激增;同时,还降低了国家权力投送的难度,使国家以战争或威慑的方式进行对外交往更为容易。地理类型的差异则造成国家某些至关重要的资源和能力的稀缺,相对稀缺鼓励了海陆竞争,通过控制重要地带弥补地理缺陷造成的国家弱点。传统地缘政治海陆对峙经典命题产生的客观原因在于:陆权国家的优势在于占据大量的领土空间与自然资源,缺陷在于地理封闭,国家权力投放的机动性受制于地理屏障;海权国家的优势在于海洋赋予的机动性与灵活性,却经常陷入领土空间有限与资源缺乏的困境。因此,俄罗斯对不冻港的追求,英国对低地国家免受欧洲陆权国家控制的需要,都具有可理解的客观缘由。
第二,可能造成冲突的各种因素通过重要的交通路线或毗邻区域传递,使各国存在着对空间进行跨境管辖的客观需要。在帝国主义时代和霸权逻辑下,这种管辖经常表现为军事占领及干预。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在观察世界经济的历史发展后指出,世界经济的驱动使各国都被纳入相互关联的关系当中,这一过程既包括融入也包括边缘化,(7)Immanuel Wallerstein, Geopolitica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65.它造成了一种高度变化的国家无法单独掌控的局面。边界既无法拦住来自全球化的经济波动、战争与冲突等传统安全风险,也无法阻挡毒品、非法移民、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特殊的地区环境和通道,加速或延缓某些危机的传递速度及程度;有效控制某些地区,则会给国家提供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案。地理空间为各种冲突因素的传递限定了一个比较活跃的范围,这个范围往往与国家边境不相重叠,这意味着强有力的跨境管理是必要的。真正需要批判的是权力政治时代强权国家解决跨境管辖的方式,它们用弱肉强食的方式并吞、殖民,或干预解决,或转嫁麻烦。
二、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批判学说的观点及缺陷
传统地缘政治向来不乏尖锐的批判者。从早期地缘政治理论内部孕育出来的法国学派、美国地理理想主义,到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的反思,传统地缘政治的批判者在“去冲突化”“去国家化”“去地理化”的学术逻辑中找到了共同点。对传统地缘政治的理论批判存在合理性,但无法在地理因素与政治选择之间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简约解释,地缘政治理论因此呈现碎片化趋势。
(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批判学说的发展脉络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由于过度强调权力、冲突,具有明显的宿命论色彩,因此,其发展一直伴随着严厉的批判。
早期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并非完全被现实主义的呼声所独占,法国联合地缘政治思想、美国理想主义倾向的研究一直存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激励学者们对传统地缘政治进行彻底的反思,从法国学派到美国地理理想主义,批评者对改造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充满信心,试图在地理空间与和平之间建立简约的逻辑关系,以提供替代性全球地缘政治选择为主要目标。兴起于法国的白兰士学派主张以互谅互让和联合来挽救欧洲,其代表人物阿尔伯特·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激烈地批判了德国地缘政治传统,指出“虽然双方(法德)都看到了新世界体系即将产生的种种迹象,但是法国人认为,这个世界体系应建立在某些国际主义的原则之上,而德国人则认为这个体系不过是大陆帝国主义的一种新形式罢了”。(8)参见[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以德芒戎为代表的很多学者希望以基于主体间的国际主义代替基于霸权的帝国主义。二战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福利增长,国际关系学者再次思索区域共同体的可行性。美国地理理想主义代表人物埃德蒙·沃尔什(Edmund Walsh)认为,“地理政治学可褒可贬,它可以在两者间选择——要么是权力的价值要么是价值的权力”。(9)参见[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他认为,新地缘政治学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相比,差别就在于其崇高的理想主义。沃尔什主张热带被动民族和温带进取民族、东洋和西洋之间建立新的关系,设计出由全球性国际组织到全球性联邦的全球地缘政治联合之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imore)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已经彻底结束,反帝国主义将促使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融合。他和魏格特把推动欧亚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普遍的自由民主制度视为理想主义地缘政治学的实现路径。(10)参见张微微:《对地缘政治观念的反思与重塑》,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
冷战的延续割裂了世界,法国学派和美国理想主义建立一个全球性地理联合空间的热情逐渐消退。全球化带来的多元化和差异化使有志于修正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学者不再追求全球性地缘政治图景,转而研究特定空间内发生的有利于和平的政治地理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约翰·阿格纽(John Agnew)、格兰特·奥图瓦塞尔(Gearóidó Tuathail)、赛门·达尔比(Simon Dalby)为代表的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成为批判传统地缘政治学说的主力。批判地缘政治借助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权力论观点,把地缘政治空间视为政治活动的载体,用特定场域内发生的叙事与表达区分地缘政治空间的边界。(11)Gearóid Tuathail,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57-60.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对空间的概念进行了复杂化处理,在它们看来,地理空间不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视野下完全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社会实践、政治互动、知识互构以及历史叙事在空间内的聚合。历史情境与记忆、共同体的意向及预期,形成了对地理空间的社会建构。在福柯的叙事产生权力的逻辑下,知识与空间的结合方式产生了若干话语性权力,不同类型的话语性权力存在相互替代的可能性。某些空间因此具备了走向政治地理合作的条件。
(二)批判性见解的共同特征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存在明显的解释力瓶颈,对国际体系所发生的很多重大变化视而不见。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批判各有侧重,其主要观点集中于三个方面:
第一,认识论层面的去冲突化。法国学派、美国理想主义及批判地缘政治学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地缘政治传统理论,要求在认识论层面实现国际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替代。批判地缘政治集中批判了传统地缘政治描述蕴含的权力政治逻辑,认为其建构的有关权力与空间关系的知识隐藏着霸权正当化的企图。(12)胡志丁、陆大道:《基于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解读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地理学报》2015年第6期。但是,理想主义的地缘政治学和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在去冲突化的程度方面存在着分歧。法国学派和美国地理理想主义认为,权力政治和霸权主义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应该被铲除,新的联合性地缘政治观通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批判地缘政治学则审慎地认为,地理空间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具有多元性。约翰·阿格纽、克劳斯·多兹等认为,地缘政治研究者不可能超然于国家、民族、阶级、种族和性别立场之上。基于地缘政治实践的情境性和区域性,他们谨慎地认为,部分区域存在着地缘政治话语和文本转化的可能,新的权力关系使建立共同体成为可能。换言之,去冲突化在一部分地区可行,在另一部分地区则不可行。
第二,地缘政治主体的去国家化。在很多学者看来,地缘政治的冲突性、悲剧性和权力政治导向,来自其固有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法国地理政治学本质上是国际主义的,德芒戎等人期望替代帝国主义的国际合作,等同于对国家身份进行再造。当意识到依靠国家实现这一目标难度太大后,白兰士学派转向借助欧洲共同文明和和平愿景的力量,这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地区概念的引入。美国理想主义地理政治学派则把目光投向全球性政治组织(如国联和联合国),期望它们能够协助热带国家与温带国家实现共同和平。受益于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的迅猛发展,批判地缘政治学对其他行为体所发挥作用的认识更为充分。批判地缘政治学观察到,很多跨国和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到国际治理、国际机制及区域化实践当中,改造了特定地缘环境的运行逻辑和区域文化,造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地缘政治的结果,使边界由地理区隔变成文化与社会因素整合的产物。(13)N. Parker, N. Vaughan-Williams, et al., “Lines in the Sand? Towards an Agenda for Critical Border Studies”, Geopolitics, Vol.14, No.3, 2009, p.584.例如,边界概念的弱化使区域成为最有价值的新地缘政治主体。这种区域化的地理空间建构与传统地缘政治基于国家互动而形成的政治空间截然不同。它带来的地缘政治效果就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区域概念逐渐具备了独立的政治身份和利益诉求,而不再仅仅是国家活动的地理空间。
第三,地缘政治客体的去地理化。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批判理论非常关注那些能够降低国家对地理环境依赖的因素,把这些因素视为地缘政治理论发生改变的决定性因素。传统地缘政治理论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地理决定论倾向,它们相信政治一定会受制于自然条件“长期趋势性感应”,(14)程洪:《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载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并对不同的空间形态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作出一系列假定。传统理论的批评者对地理决定论作出了抨击。法国学派、理想主义关注欧洲历史、文化与传统习俗中的国际主义,批判地缘政治学则更关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以及制度与观念的全球组合。批判者要么相信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力极大降低,要么相信空间可以被新的要素改造或干预。(15)J. Hyndman, “Towards A Feminist Geopolitics”, Canadian Geographer, Vol.45, No.2, 2001, pp.210-222.去地理化意味着空间的价值是可变的,能源、文明、宗教、族群、身份、流行文化、叙事方式等多种因素作为干预变量,影响人类或国家与地理空间的互动,使地缘政治实践具备了情景性和非中立性特征。通过这些因素的改造,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所能起到的作用不再是固定的。非地理因素尤其是那些鼓励国家走向合作的因素,赋予了地理因素新的价值,降低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限制了权力竞争的规模和方式。总体而言,地缘政治的去地理化是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地理决定论”的反思,用人地互动论的思维解构传统地缘政治坚硬的现实主义内核。
(三)传统地缘政治学批判理论的缺陷
杰弗里·帕克曾经把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批判性学说概括为非战主义概念的地缘政治学(A Pacifist Conception of Geopolitics)。这些学者深受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的鼓舞,相信传统地缘政治的基本假定、价值偏好和行动方案都是错误的,并希望对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区域化和国际社会的发展进行解释。(16)B. Doherty, T. Doyle, “Beyond Borders: Transnational Politics, Social Movements and Modern Environmentalism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15, No.5, 2006, p.705.应该说,这些学者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批评是强有力的,但传统地缘政治并未因此消亡。悲剧性宿命论式地理政治观依然反复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当中。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在于,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存在巨大的解释力缺陷。
第一,批判理论最严重的缺陷在于“去地理化”瓦解了地缘政治理论的内核。传统地缘政治基本都相信“地理因素本身就是冲突的根源”,(17)Paul F. Diehl, “Geography and War: A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17, No.1, 1991, pp.16-23.这种观点的谬误十分明显。问题是批判者在去地理化层面走得太远,引入了太多其他变量解释国际冲突或合作,使其丧失了政治地理学独特的理论视角和价值。在偏离了“空间”与“政治”的基本逻辑主线后,(18)R. Pain, “Globalized Fear? Towards An Emotional Geopolitic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33, No.4, 2009, pp.466-486.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所关注的内容的社会性已经远超地理性,它虽然仍具有理论解释力,但这种解释力已经和地缘政治范畴无关,也无法用以解释或批判政治地理现象。事实上,割裂或者干脆否定地理与政治选择之间的逻辑关系,无助于解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因为地缘政治从未否认除地理因素外其他变量可以对国际关系造成的影响,传统地缘政治的力量在于它们在地理因素与悲剧性国际关系之间建立了普遍性且有说服力的简约逻辑。批判者为了实现“逻辑的替代”,也需要在地理结构与政治选择之间建立一种简单有力的逻辑,说明地理因素如何促进非战的合作。如果只是借助知识性、社会性因素(如叙事方式、制度、共识、情感等)对地理空间进行改造,才能实现合作的效果,反而反证了“地理导致冲突”的假定是合理的。简而言之,批判地缘政治不能绝对否定地理决定论,而应该坚持地理因素产生和平的那种地理决定论。从这一意义上讲,区域化和相互依赖概念对于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批判学说在“去冲突化”问题上的乐观态度使其观点丧失了平衡性。无论是法国学派、理想主义地缘政治学还是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它们都认识到权力政治和地缘冲突的普遍性,但是,它们把去冲突化视为一定能够实现的先验目标,因此,存在着一种将地理空间所发生的政治变化理想化的趋势。法国和美国地缘政治学坚信国家经过残酷的世界大战,必然会形成对战争的理性反思能力,拉考斯特因此认为,地缘政治理论摆脱沙文主义的关键是实现地缘政治学与国家战略的分离。(19)参见Michel Foucher, Fronts et Frontiers, Paris: Fayard, 1988, p.439。因此,在论述国家转向国际主义立场时,只寄希望于民族自决、民众和平意识的觉醒和民主制度的成熟,这种逻辑过于简单和缺乏说服力,而且暗含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一样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批判地缘政治学在理论层面看似更为平衡,认为地缘政治理论应该具有情境性和非中立性,空间叙事的复杂性使国际冲突与合作都有可能。但在具体的研究当中,很多学者实际上没能坚持平衡的立场,福柯思想中政治叙事改变的“可能性”被很多学者有意无意地演绎成地缘政治由冲突性转向联合性的“必然性”。在去冲突化愿景的引领下,政治地理的情境性给很多研究者造成了一种“冲突一定可以克服”的幻象,他们更加注重区域化、共识等有利于合作的因素对地理空间的改造,忽视了地区内的固有矛盾及民族主义的深刻影响。
第三,批判理论在构建全球分析框架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传统地缘政治所建立的海陆对峙范式是粗糙的,但也曾经被国际关系史反复验证。批判者没能建立一个替代性全球政治地理分析框架,这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缺陷。二战及冷战时期的部分地缘政治学者试图建立一个国际主义解释框架,但是,他们过度借鉴传统地缘政治的理论范式,除了国际主义外没能提出新的东西,因此很快被世界遗忘。批判地缘政治学则转向了有限地理空间的描述。哈特向强调要避免把地缘政治和某种“法则”联系起来,约翰·阿格纽则关注地缘政治实践中的具体情境,他们都相信地缘政治不存在一个体系层面统一的简约逻辑,更倾向于采用后现代主义“解构”研究的范式,探讨地区一隅所发生的特殊政治现象。这种情境化和非中立化的地缘政治解读,更贴近地理空间所发生的现实情况,也更容易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假定做出经验性反证。但是,福柯系谱学基础上的地缘政治分析过度强调话语实践及其隐含权力关系的自主性,带来了两个严重影响地缘政治理论解释力的问题:第一,基于特殊文化、族群、技术和其他要素形成的话语实践变成了支配客观地理环境的力量,地缘政治由“存在叙事权力”变成“地缘政治等同于叙事权力”。话语主导使相似地理空间内发生的政治现象无须遵循客观的法则或逻辑,地理类型的归纳(如陆权和海权)也没有意义,客观的地理要素还有什么意义变成一个问题。第二,叙事的情境性和非中立性取代了主流社会知识的支配性,使建构一个全球性且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变得没有必要。空间与政治的客观法则被视为压制自主性话语和知识的总体叙事。(20)Hubert L. Dreyfus,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84-92.历史的偶然性很大程度上成为地缘政治实践和战略产生的基础,这使地缘政治理论不再具有强的因果性阐释和解释能力。
三、地缘政治议程中立化的倡议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在地理因素和权力之间架构了简约而有力的逻辑,并据此得出了地缘政治冲突的结论。批判学说则将理想主义价值观或批判性权力叙事引入地缘政治分析,强调地缘政治合作的可能。两种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歧和辩论,无法以某一方的彻底退出终结。总体而言,一个兼顾两者特点的中立性分析框架有利于我们建立对地理空间内政治现象的总体理解。
(一)中立性地缘政治议程的基本判断
地缘政治议程中立化的本质是对地理因素与国家选择间的联系进行客观描述。一个中立化的地缘政治议程需要在五个方面整合传统地缘政治及其批判者的观点。
第一,分析框架的全球性和普适性。与批判地缘政治学批评超越文本的研究相反,一个简约的全球性地缘政治分析框架依然是必要的。地理空间内叙事文本的情境性,不是否定全球主导性知识结构的理由。通过地缘政治主体的历史性互构,作为叙事存在的地缘政治知识形成了超越文本的全球性共有知识(Common Knowledge)是极为正常的。包括拉格在内的建构主义者都相信,虽然实践的(再)建构产生了规范,但规范和规则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仍然是稳定的和支配的。很难想象一个全球化的国际体系存在体系结构与体系共识,却不存在全球性地缘政治理解。地理空间存在差异性,但也存在着地理因素的同质性,相同的地理环境会鼓励特定的政治选择,诸如海权国家倾向于谋求对边缘地带进行控制。当这种政治选择超越情境差异而成为普遍选择的时候,全球性地缘政治分析框架就产生了。一个全球性地缘政治议程才是完整的,符合知识和实践两方面的需要。
第二,地缘政治哲学的中立化。地缘政治哲学的形成既包含地理空间内历史记忆的沉积,也包含一种地缘空间的共同想象。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和区域间反复发生的冲突,会让地缘政治冲突看似成为“历史的必然”。一定规模的共同经济和社会生活也会在地理层面形成共同体的愿景,使空间成为共同体的载体。将任何一种可能性上升为宿命的做法,会把大量国际关系现实排除在外。罗伯特·卡普兰认为,“地理可以预知,而不是确定,因此它不是宿命论的代名词。它和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分布一样,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制约和推动因素”。(21)[美]罗伯特·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涵朴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地缘政治理论维持必要的客观性,意味着它需要同时与冲突的地缘哲学、合作的地缘哲学保持距离。
地缘政治冲突固然会带来战争和动荡,但国家基于维护自身安全而实施的自卫性举措在地缘政治层面带有某种必然性。在地理资源稀缺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地缘冲突很多时候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而非价值层面令人厌恶的政治疾病,更不能因为价值偏好就认为地缘联合一定能够替代冲突。同样,渴望国际合作与地缘联合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望,但地缘政治联合所带来的地理空间的高度开放,同样会带来威胁和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全球性非法移民、族裔冲突及恐怖主义威胁,都引发了人们关于重新控制边界、进行有效地缘政治管理的讨论。一个科学的地缘政治理论认为,具体的地缘政治叙事是非中立性的,但在对地缘政治叙事的分析和概括中,则应严格遵循中立性原则。“空间”与“政治”的关系不应存在预设立场,而应被视为一个存在若干可能性的客观进程。地缘政治战略是无法保持中立性的,但地缘政治科学需要中立的立场以维持学术的严谨性。
第三,人地互动诱发的政治选择。地缘政治理论的逻辑主线在于地理因素与政治选择之间的关系。对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无论是海权说、陆权说、空权说还是边缘地带说,都习惯于强调某种空间类型会特别稀缺,拥有某种资源或某种特殊的物质精神优势,(22)孟德斯鸠在阐述地理环境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时认为,“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生活的人更遵守道德规范,而在温和气候条件下生活的人道德操守不稳定……炎热的气候则使人们性格变得软弱”,载国玉奇、[俄]В. П. 丘德诺夫《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地理空间与固定化的行为模式相互关联。例如,重要航线和交通要道更具战略意义,大陆国家更具领土欲望,海洋国家产生重商主义等。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则更强调社会性因素对国家政策选择造成的影响,强调地理因素蕴含的差异性及权力的话语性。总体而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带有地理决定论的倾向,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则带有更为明显的地理改造论倾向。前者强调地理因素影响政治选择,后者则相反。我们需要看到,这两种倾向都只能反映地缘政治的某一侧面。新的地缘政治议程应该跳出简单的决定论或改造论思维,立足于人地互动的具体进程及其带来的权力关系,进行不预设立场的研究。人地互动的过程具有情境性,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一方面,地理环境会形成特定的政策惯性。这是不争的事实。“地理磨损”使国家军事战略选择“远交近攻”,海洋国家会选择控制边缘地带,弥补自己控制欧亚大陆腹心地带的困难,这都是典型的例证。因此,国家会把地理因素作为政策选择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地缘因素对权力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又不是绝对的。例如,邻国必敌就与海陆对峙学说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之处,海权国之间的冲突和陆权国之间的冲突不一定比海陆对峙更为稀少。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人类对地理空间的改造成为第三种日益重要的地缘政治现象,地理空间成为一种兼具客观性和实践性的复合概念。我们需要正视人类对地理环境的改造开发及其政治影响。
一个中立的地缘政治议程的核心就是对人地互动所造成的政治效应进行准确描述和分析。国家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又通过利用或改造地理环境推动政策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关键在于地理因素的约束作用是否能够被改造地理因素的实践所抵消。地理因素所发出的信号并不是单一的,地理毗邻会导致摩擦、竞争和冲突行为,但地理空间同样会带来贸易的便利性。重要的是国家间政治选择是在加强冲突的地理便利性还是合作的地理便利性。例如,英法海底隧道的开通,则与拿破仑试图建造平底船队来登陆英格兰的意义完全不同,使英法间地缘空间的联合便利化。有时候地理空间的改变带有复杂的特性,跨境交通的发展既有利于跨国经济合作,也使军事冲突或跨国非法移民等危机因素的传导更为方便,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对地理环境的改变可能产生新的联合前景,也可能造成新的冲突,其地缘政治影响无法用单一倾向来描述。人地互动的地缘政治框架为国家外交政策创造了一个基础性框架,其他干预变量在该框架之上与地缘因素共同解释国家行为。地理因素带来了强烈的倾向性,但决定国家如何选择不是地理环境本身。阿尔萨斯和洛林提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煤钢联盟时期,德法两国的价值绝不相同,但德法间的地理格局从未改变。国家的政策选择有复杂的动机形成机制,政治体制、联盟关系、战略文化等多种因素都可能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我们需要意识到地缘政治理论存在着解释力的边界,对地理环境的研究不能替代对其他干预变量的研究,地理因素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可能存在多个可以彼此替代的理论范式。
第四,权力的工具化。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服务于权力,以维护和扩张权力为目的,因此被指控为权力政治的附庸。理想主义地缘政治学则因为完全去权力化的诉求,被认为无法解释国际政治现实。批判地缘政治学叙事性权力的观点,给地缘政治新的权力分析带来了有益的启示,但它更多局限于地理叙事为权力服务这一侧面,而没有考虑权力为空间服务的一面。在当代地缘政治环境下,权力与空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权力关系隐含于复杂的话语叙事当中。帝国主义式直接占领和完全控制太过敏感,权力作用于空间的方式更为间接化和隐蔽化。同时,空间带给权力的效应更为复杂,空间不仅能服务于权力,也可能是权力的陷阱和负担。国家的地缘战略不可能与权力绝缘,但是,国家经营地理空间不能以权力为唯一目的,权力则成为服务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之一,与其他手段共同发挥作用。
首先,维护霸权和制约霸权应该成为地缘政治议程“硬币”的两面。传统地缘政治学说为海洋和陆地强国攫取霸权提供了简单有效的道路,这是地缘政治理论的成功,也成为地缘政治理论的局限。地理空间不仅是霸权的玩具,包含霸权与服从的关系,也可以是制约霸权的绝佳武器。地区的非军事化、边缘地带的政治中立、防御性区域安全同盟以及国家寻求成为永久中立国或捍卫天然边疆的抉择,都是国际关系史上固有的并在当代成为更为常见的地缘政治现象。权力的工具化需要地缘政治把研究视角转向非霸权国家利用地理因素自卫的各种举措,并把这些现象视为地缘战略研究的核心议题。例如,伊朗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优势对抗美国的军事压力。
其次,权力作用于空间的方式更加间接和隐蔽。亚非拉掀起民族独立浪潮及新兴国家崛起后,霸权国对空间“施以直接控制是否可行”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存疑的问题。(23)J. Agnew, “The Territorial Trap: Th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 No.1, 1994, pp.62-63.美国在阿富汗的狼狈撤离再次验证了一个古老的政治法则,强权政治的直接干预成本太过高昂。因此,虽然空间对于权力而言仍然具有很大的价值,但大国的权力政治行为普遍不愿引起占有土地或空间方面的联想,转而更愿意通过联盟、国际机制、区域一体化、双边或多边协定等中介机制,对空间施加隐性控制,权力政治出现了隐蔽化和间接化趋势。批判地缘政治学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著述。可以看到,大国与地区代理人合作的过程还没有脱离权力政治和大国竞争的窠臼,但它必然伴随着权力转移和分享。权力叙事的多元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各国更注重权力的诱导性而非强制性一面,也确实淡化了权力政治零和博弈的一面,增加了空间共商、共建、共享的可能。
再次,空间对权力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空间与叙事性权力的关系不是批判地缘政治学所理解的依附性,而是各自独立的。空间有时可以成为重要的权力资源,但“空间必定带来权力”的逻辑则未必总是成立。空间对权力的削弱作用是当代地缘政治需要回应的命题。地缘竞争和地缘联合都可能带来消极的效果。一方面,传统地缘竞争并不总会带来收益,海陆两极的对峙与心脏-边缘地带的二分,再加上民族国家人口与土地凝聚力的增强,地缘竞争也趋于长期化,最终制造了若干深陷地缘竞争而无法自拔的地区,导致很多国家有意识地与这些制造麻烦的地区做出隔离。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的联合趋势带来了国境的开放,跨国交流产生了财富,也制造了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危机。流行疾病、毒品、武器、人口买卖与各种危机要素的跨国流动,冲击了国家制度结构,在削弱国家权力方面的作用不亚于传统地缘政治竞争的失败。此外,国家对空间的消化利用能力存在巨大落差,不同空间出现了权力资源单向的“虹吸效应”。与强势一方毗邻的国家和地区,不但无法利用空间增加权力,反而因为“虹吸效应”导致在毗邻地区形成无法愈合的伤口。墨西哥与美国的毗邻就成为墨西哥悲剧命运的地理注脚。
第五,国家主导下的行为体多元化。倾向于国家还是倾向于超国家或次国家行为体,成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及其批判者的重要分野之一。传统地缘政治研究过于强调西方中心论及大国中心论,但是,包括新兴国家、地区在内的其他行为体,深刻介入到地理空间塑造的过程当中,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地缘政治主体多元化意味着支配性海陆大国对地缘政治的垄断被打破,更多国家主动参与到对地区和全球地缘格局的塑造当中。这必然会带来权力的分散化以及次区域和区域影响力的增加。另一方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家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不是完全对立的。地缘政治行为体的多元化不是国家的退场,而是国家影响力的扩大。全球和地区大国依然具有明显的优势,其他行为体和主导性大国的合作使地缘政治版图的变化更加隐蔽。在这一意义上,国家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权力没有根本改变,发生改变的是大国处理与其他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模式。大国优势不再是那种对其他行为体的绝对支配,而更多体现在规划、协调和诱导各国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上,批判地缘政治学把这种能力表达为建构地缘政治主流叙事的权力。
在支配性大国改变了空间控制的方式后,其他地缘政治主体尤其是活跃的地区性强国,在权力与空间结合方面已经体现出更多的优势。它们利用自己特殊的地缘优势,在分享支配性海陆强国权力上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区域强国与次一级地区内国家的关系也遵循类似的逻辑。总体而言,地缘政治行为体的多元化使地缘政治战略陷入一种更复杂的关系当中,空间的分割与联合形式也更加多元。
地缘政治行为体多元化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区域和次区域的独立性增强,区域性海陆联合的局面成为可能。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改造是相当困难的,次区域和区域的地缘政治环境塑造则相对可行。开放而活跃的地区成为拥有自我意志的地缘政治参与者之后,会进一步制约全球性海陆大国的选择。区域一旦建立了可持续的合作制度,就会从整体的而非二分的、合作的而非对峙的视角,思考地区成员的共同命运,抵制区域外力量的干预,遏制内部的分离趋势。区域和次区域的发展没有达到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宣称的乐观程度,区域一体化缺乏足够管理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但是,区域和次区域确实创造了一个更具问题导向而非权力导向的地缘议程。国家会把权力让渡给地区性制度安排,但这种制度安排本身要解决地区面临的共同挑战。以制度安排为载体的区域和次区域,也必须表现出更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有可能赢得区域成员的支持。这就创造出一个更具联合前景的地缘政治格局。
(二)中立性地缘政治实践的优先议题
一个中立化的地缘政治分析框架承认地理因素会造成政治影响,但拒绝承认这种影响的宿命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共同地理空间的前景受到了严峻挑战,传统地缘政治实践出现了回潮的趋势,中立性地缘政治观在实践领域需要回应两个问题:
第一是开放地理空间的管理问题。传统海陆二分法背后的争议焦点在于,海权和陆权是否向对方开放及开放后的控制权争夺。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地理空间的封闭已经难以做到,那么,目前的焦点就变成如何把地理空间权力导向的控制转变为问题导向的管理。控制强调占有,管理则强调绩效。地理空间的开放总体而言是不均衡的,它可能是某一方对另一方的不对等开放,也可能是双向的对等开放;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强制的。无论是那种类型的开放,只要毗邻、区域和跨区域的经济社会交往存在,由此带来的安全需要就必然存在。共同管理在本质上兼顾约束和保障。防范导致危机的要素自由流动,保障开放所需各种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是各国地缘战略的底线共识。依据要素流动的密度及安全性,中立性地缘政治议程需要对地理区块或交通路线的价值做出政治判断。
很显然,如果共同管理缺位,则强权控制或地理空间割裂必然回流。在某种意义上,极端情况下重新封闭地理空间也是共同管理的办法。但在更多情况下,各国寻求的其实是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妥协。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协同大国及区域组织发挥跨国流动管控机制的重要作用;全球经济增长的停滞,又需要各国打开国门,冒着疫情扩散的风险重启包括“一带一路”等合作框架在内的全球合作议程。在一个霸权主义和权力失衡仍然存在的国际体系中,权力控制与有效管理的界限经常是模糊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危机在跨国空间内的自由流动缺乏管理,而本来承担最大管理职责的各国政府已经被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不均衡开放严重削弱了。中立的地缘政治观承认共同管理的困难,但认为地缘政治理论最低限度需要重新认识“边境”的价值,重拾国家对国土尤其是边界的保护和管制职能。国家需要在恢复自身主权能力、实现开放和共同管辖之间保持平衡。与此同时,因开放而联合在一起的地理空间也必须证明自己可以建立强有力的共同管理机制,这种地缘联合才是可靠和可控的。
第二是地理空间的共同体化问题。在海权、陆权及边缘地带之间的地理壁垒业已打开的大背景下,共同管辖权力的政治分割能够解决最基本的秩序问题,却无法解决发展问题。在一个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地理空间的和平利用和改造是维系地缘安全最好的办法。不解决发展问题,则绝无可能解决和平问题。在共同发展缺位的情况下,共同管辖可能被单向的剥削僭越。地理空间的共同体化存在两重内涵:一是充分的地缘经济合作,二是共同体在地区内的建构。就地缘经济合作而言,地理空间的共同开发和改造,是稳定的和平地理空间存在的基础。但是,帝国主义时代权力政治留下的政治阴影,使任何共同空间的改造都变得敏感而困难。单纯的经济合作只能使空间控制权竞争的烈度降低,只有辅之以共同体建构才能达到理想中地缘政治联合的结果。国家克制权力竞争的冲动,以长远眼光看待地缘经济合作议程,就地理空间的共享达成共识、建立规制,本质上都是一个地区或全球的共同体化进程。国家对自身疆域和外部空间建立一种合作而非对立的叙事,会造成一种抑制权力政治的地理认同,使权力叙事成为地理空间内成员的共同知识。
余 论
中立性地缘政治承认空间与政治行为存在强的因果关系,但不使之绝对化。地理环境会限定国家政治行为的选择范围,赋予国家特定的政策动机,这种影响是普遍的和全球性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应该聚焦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对国家身份与行为的塑造及影响,描述人地互动的客观过程,预测地理空间及国家政治行为在这种互动中产生的变化。在现实层面,有效的地缘战略既无法否认西方国家的权力优势,也不能通过抑制非西方国家的发展空间而获得成功。很多国家的地缘战略无法摆脱权力竞争和冲突的历史惯性,但是,新的地缘政治想象已经具有了更大的空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都在践行令人振奋的新空间愿景。中立的地缘政治议程需要同时考虑干涉与防御、开放与隔离并存的现实,并基于此对国家地缘战略的多元性特征加以认识。总而言之,中立性地缘政治议程愿意承认地理空间与政治活动之间的互构关系,并基于这样的逻辑,考虑国家在地缘战略方面的多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