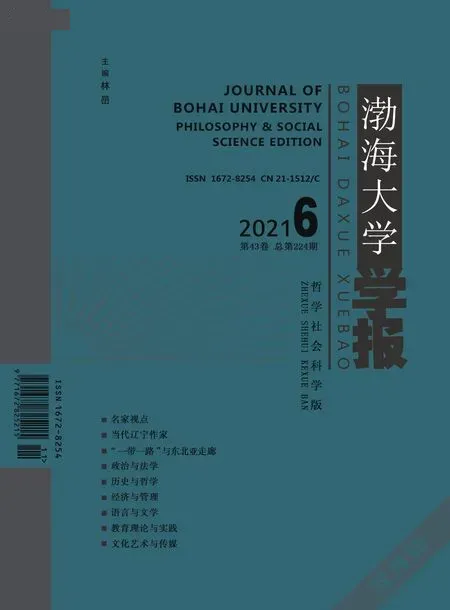试分析《邯郸记》的荒诞色彩
张睿文(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北京100073)
一、何谓“荒诞”
“荒诞”是一种对人或事物状态的描述。
在中国,“荒诞”与“荒唐”可以作为同义词,《辞海》中对其解释为“虚妄不可信”①。在西方,“荒诞”(absurd)一词由拉丁文(sardus)(耳聋)演变而来,可以理解为“离奇”“不合情理”“虚妄”“虚假”,即与“真实”不相符合,所以要了解“荒诞”,就要先了解“真实”。真实的本质在于合乎客观世界和符合现实规律,那么荒诞的本质就是事物与客观世界和现实秩序的分离②。“荒诞”一词在古代文学中首先要追溯到唐朝李白的《大猎赋》:“哂穆王之荒诞,歌《白云》於西母。”[1]这时,“荒”“诞”最早合成为一词。但“荒诞”一词所蕴含的美学思维却早在先秦《庄子》一书中有所流露。在庄子作品中通过“畸人”“庄周梦蝶”“混沌”“支离疏”等例揭示了人生,世界具有“荒诞性”,庄子虽没有明确提出“荒诞”一词,但在《庄子·天下篇》提出了“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作为他思想与风格的概括。因此《庄子》也成为中国古代荒诞美学的开端。
二、从“梦”管窥《邯郸记》中“虚”与“实”的荒诞色彩
(一)《邯郸记》中的梦与荒诞
“荒诞”本就是人类理性发展自然产生的意识心理,而“梦”也是人类心理的产物,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认为:“梦不是偶然形成的联想,而是压抑的欲望(潜意识的情欲伪装的满足),可能是某种心理产生的原因,梦是通往潜意识的桥梁。”[2]汤显祖也曾说“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由此可见,汤显祖笔下关注的“梦”是立足于人的意识心理层次上的,《邯郸记》中的黄粱美梦便是卢生内心对酒色财气的欲望投射。
在临川四梦中,《邯郸记》相比《牡丹亭》和《紫钗记》,不再仅仅把“梦”作为一个重要情节在个别场次里出现,而是全本三十出,有二十六出都发生在卢生的梦里。
如果用梦去划分《邯郸记》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从第一出《标引》到第三出《度世》是第一部分——“入梦前”,从第四出《入梦》到第二十九出《生寤》是第二部分——“入梦中”,从第二十九出《生寤》后半部分到第三十出《合仙》则是第三部分——“梦醒后”。梦里的世界是虚假的世界,并非是人真实生活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的本质是违背客观世界与现实秩序的。
本文开头即明确了“荒诞”的定义,单从词语本意可以得知它与“真实”相对,本质上是事物与客观世界和现实秩序的分离。
上文已提到西方从哲学高度对“荒诞”做了阐述,即“荒诞”在西方荒诞哲学范畴中,认为世界是荒诞的。而汤显祖构建了“梦境”这一非真实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荒诞世界”,由此可以看出《邯郸记》是具备“荒诞性”的。
(二)《邯郸记》中的“虚幻世界”与“真实世界”
若从“梦”的角度来分析《邯郸记》的荒诞色彩,《入梦》一折则具有较强的“可分析性”。《入梦》一折把卢生在《邯郸记》中分成“梦中人”和“醒中人”,卢生所在的世界也在这一折变成了“虚幻世界”与“真实世界”。
《入梦》一折前半部分是现实,后半部分是梦境,恰如许中翰所评“离合悲欢,倏而如此,倏而如彼,绝无头绪,次都描画梦境也”[3]。卢生跳入枕中,酣睡入梦,开始进入这个与真实、客观相悖的虚幻世界,也展现了一幅荒诞绝伦的世界图景。
虚幻世界是卢生“入梦”所处的世界。而卢生来到这里,就误闯有着“红粉高墙”的崔府宅院,崔家并非寻常人家而是朱门大户,亲戚多是朝廷显贵。但这样一个“世代荣华”的富贵人家,家中却只有三位妇人,分别是老母、待字闺中的女儿和丫鬟梅香。更为可笑的是,她们在看到误闯进来的穷酸秀才卢生时,居然在对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准备让他入赘崔家,与崔氏结为夫妇。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更是不符合人类客观世界的现实秩序的。
在这个“荒诞世界”中,因为它的非真实性,其世界的秩序同真实世界相比也是荒谬且反常的。在《入梦》一折中,卢生刚误闯崔府,不消片刻就从跪在地上有可能受到严重惩罚的贼,变成了坐在红帐里即将与崔氏结为夫妇的男主人,人物的经历极为戏剧化。婚姻如同儿戏,看似可笑荒谬,但却是大多凡夫俗子“飞上枝头变凤凰”轻松达到阶层跨越这一隐秘幻想的外化。从婚姻一事,纵观卢生的成功经历,都是被一种超现实力量推动,而这一超自然力量正是卢生心底关于酒色财气的欲望,即在梦中世界,人的真实欲望可以得到显化。
“妄想游魂,参成世界”,梦是人的内心映射。在人与真实世界发生冲突时,梦中世界更应该赤裸地展现梦中人的欲望,发生的事情则是欲望的具象化,并且是理想的、美好的,与残酷的真实世界形成对立。但是《邯郸记》中的“荒诞世界”却似梦非梦,似真非真。汤显祖笔下的梦都源于“至情”,主人公都是“因情成梦”。但是《邯郸记》的梦不同于《牡丹亭》的梦,《牡丹亭》的情是“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汤显祖借丽娘的情与梦,肯定了人类对天然情欲的渴望,所以梦中是美好的一晌贪欢,春情荡漾,并着笔于象征美好爱情的花神。而《邯郸记》的情是“生小误痴情,情痴误小生”。卢生的情是“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汤显祖已对人生的终极追求有了自己的答案,他借助卢生的情与梦,揭示了酒色财气都是凡夫俗子的一场虚妄,所以在卢生的梦里,梦不再是与残酷现实对立的美好,而是残酷本身。
真实世界是卢生出梦后的现实生活。世界荒诞,命运无常。世界的荒诞性在《邯郸记》中体现得尤为残酷直接。而汤显祖将人物置身于非真实的“荒诞世界”,更是对真实世界的质疑与揭露。
虽然梦中的“荒诞世界”光怪陆离,卢生一生中的“成功经历”都如玩笑一般,典型案例恰如《入梦》中的婚姻。但是他这一生却并非一帆风顺,一直经历着起起落落、大喜大悲。官场瞬息万变,他时而受宠,位极人臣;时而落难,绑缚刑场。在《入梦》一折中,通过婚姻奇诡已经预兆了官场沉浮,他从阶下囚跃身堂上客正是他一生忽而落魄,忽而辉煌的缩影。而这些事件让卢生深刻体验到的正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两者更是真实世界的本质与人间真相。
而在虚实两个世界中,梦中的虚拟世界又非纯粹的“虚”,荒诞中又折射了许多现实世界的情况,非梦的现实世界又不是纯粹的“真”。因为在《邯郸记》中现实世界同样不具备“理性”与“正常”,反而充斥了荒诞滑稽的色彩。
从《邯郸记》的“梦”出发,从它“虚与实”的关系中足以体现《邯郸记》的荒诞色彩。
三、从“戏谑”管窥《邯郸记》中的荒诞色彩
何谓“戏谑”?“戏谑”一词在中国古代汉语体系下,最早见于《诗经·卫风·淇奥》:“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戏谑”之事不易,以“不为虐兮”为准则。“戏谑”如果作为一个作品笔法风格的修饰,则含义较为广义,含着嘲笑与讽刺、游戏与玩笑、幽默与情调、迷狂与想象,更偏向于自由和不拘泥的状态。
戏剧中戏谑则是一种典型的喜剧形式。通过戏谑,可以将严肃的主题赋予可笑滑稽的外壳,同时强化讽刺意味,作为强化“荒诞表现”的手段,使艺术中的“荒诞性”更显深刻。
在明代戏曲创作中,徐渭使用了戏谑的笔法进行杂剧创作。在他的代表作《歌代啸》中,荒诞中透着滑稽,滑稽中透着讽刺,讽刺中透着愤怒,愤怒中透着悲哀;剧中的州官在审理李和尚与吴氏奸情一案时,颠倒黑白,张冠李戴,具有强烈的讽刺批判特征。徐文长寓歌于哭,以歌代啸,掀天揭地,用滑稽、讽刺、戏谑嘲弄的手法揭露了种种黑白颠倒的社会怪现象,达到了讽刺与鞭挞封建官僚昏庸和无能的效果。
徐渭和汤显祖作为同时期名噪文坛的剧作家,汤显祖对徐渭尤为欣赏,而这份嬉笑怒骂中的荒诞也被汤显祖学习运用到他的传奇创作中,在《邯郸记》的多处得以呈现。
(一)《邯郸记》中的“戏谑”运用
纵观《邯郸记》全剧,“戏谑”可以作为其风格之一。全剧伊始,在《邯郸记》第一出标引中通过上下句无逻辑的唱词“乌兔天边才打照,仙翁海上驴儿叫”,以及“犹难道”“凭谁”“回头笑”“俏”“蠢”就体现了汤显祖在创作时选择了戏谑的态度与手段作为讽刺的表现手法,奠定了全剧的戏谑与荒诞的基调。
汤显祖在全剧中用讽刺戏谑的手法道出了官场沉浮和人生际遇的滑稽与荒诞。如在第七出《夺元》里,卢生以一介草民,凭借妻子崔氏的“孔方兄”金钱打点,竟然做到了“非万岁爷一人主裁,他与满朝勋贵相知,都保他文才第一”。就连司礼监的太监都说“也看他字字端楷哩”。可见他打点了满朝权贵甚至上到皇上,下至太监。由此可以看出官场过于黑暗,并且只靠金钱的打点,过于夸张荒诞。
而崔氏封得诰命夫人更是荒诞。在《外补》一折中卢生回家后第一时间告诉了崔氏她现在是诰命夫人,而原因居然是“你不知,小生因掌制诰,偷写下了夫人诰命一通,混在众人诰命内,朦胧进呈,侥幸圣旨都准行了。小生星夜亲手捧着五花封诰,送上贤妻,瞒过了圣上来也”[4]。
(二)滑稽与荒诞
戏谑是中国古代的戏曲传统,从参军戏开始,戏曲便善于利用“滑稽”的戏剧表达,达到深刻的艺术效果。《邯郸记》中多个场次运用了大量戏谑的手法,来表现其滑稽的风格。
在《入梦》一折中“戏谑”成分较为明显,在卢生误闯崔府被抓以后,崔家老夫人、卢生、崔氏的关系是紧张的,但是她们三人的唱词最后一句却巧用重复,分别是“敢来行踏,敢来行踏!”“感行调达,感行调达。”“再来回话,再来回话。”“男儿膝下,男儿膝下。”通过唱词造成滑稽的效果。如果说大户人家在婚姻之事上如此“玩闹”,轻易随便就将闯入府内的穷酸书生召入府中,已在人物行为上足够戏谑又荒诞了,那么母女之间戏谑性的对话,更是荒诞不经。在卢生沐浴更衣前来拜见崔老夫人与崔氏时,崔氏听到“尽风华,衣冠尽楚多文雅”时低声问“内才怎的?”但是崔老夫人竟然回复“便是那话儿郎当”直接调侃女儿与准女婿,一个高门大户的老夫人对着自己女儿开生殖玩笑,并且调侃对象还是刚认识就要招入府内的准女婿,语言与人物身份严重不符。而借由戏谑荒唐的对话,对人物关系进行戏谑调侃,进而达到讽刺的作用,体现了《入梦》一折充分采用了喜剧形式。如此戏谑,不仅人物行为语言令人感到荒诞可笑,同时更明显体现出喜剧形式在剧中的运用。
《邯郸记·入梦》一折入梦出梦,可笑可啼。滑稽与戏谑贯穿全折,同时体现出荒诞派戏剧的风格特点,即“采用荒诞的手法直接表现荒诞的存在”与“轻松的喜剧形式”。通过充斥戏谑的、不符合人物身份的对白,表现荒诞的母女关系状态。崔氏母女的人物行为与戏谑性语言之所以荒唐,正是汤显祖为了表现荒诞的梦中世界而特殊设定,以达到讽刺与荒诞的效果。
用戏谑的态度书写一枕黄粱美梦,荒诞入梦,荒诞出梦,终究是丰世悲欢成一笑,晨钟动处月光寒。道尽了汤显祖对人生意义的理解。
四、从“人生追求”窥测《邯郸记》中“意义”与“无意”的荒诞色彩
人生追求是中国文人始终关注的命题,老庄之道作为中国早期哲学,在《庄子》庄周梦蝶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通过梦蝶,以梦境与现实的对照,真实与荒诞或即或离的状态,思考现实与人生状态与人的主体的实在性。由此产生了“人生如梦”这一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哲学思考。从此形成了通过梦境与现实的对比,来反映荒诞的现实。庄周梦蝶是对人生荒诞的思考,“人生如梦”是对人类追求的回答,更是人类心理产生荒诞思想的根本原因。
《邯郸记》给出了两种人生追求,一个是酒色财气,一个是功名身外事。卢生之所以会经历一场黄粱美梦,就是去悟人生追求是什么,人生有什么意义?
在《度世》中,一众岳阳楼的宾客是酒色财气的众生相,在卢生的梦里,他自己经历的人生更是道尽了人对酒色财气的追求。在《生寤》一折中,卢生惊奇地发现这经历的一生居然竟是一场黄粱美梦,过眼繁华相,都是这枕头里去。恰似〔簇御林〕所唱“风流账,难算场。死生情,空跳浪,埋头午梦人胡撞。刚等得花阴过窗,鸡声过墙,说甚么张灯吃饭才停当?罢了,功名身外事,俺都不去料理他,只拜了师父罢。〔拜介〕似黄粱。浮生稊米,都付与滚锅汤。”[4](189)在《合仙》一折,汤显祖通过八个仙人的数说敷衍,也道尽了人生如梦,功名身外事的人生意义。
其实在《邯郸记》前部分《入梦》一折中通过吕洞宾对《岳阳楼记》的背诵,暗示了理想的人生状态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奈卢生尚执着于功名利禄。为了深刻清晰地揭示现实世界中人生的追求是无意义的,酒色财气,人生成败都如梦虚幻,吕洞宾才引卢生入梦。“卢生,你待要一生得意,我解囊中赠君一枕。”追逐功名利禄化为黄粱一梦,一枕空幻,暗示了人生的追求是无意义的,把“人生如梦”当作对人生追求什么的回答。
在《外补》一折,卢生中了状元以后,因“单掌制诰”三年后再回家,夫妻二人正在庆祝团聚,与崔氏得到封号时,圣旨传来,卢生被贬官到陕州凿石开河,而且要“走马上任,不许停留”。剧情一波三折,人生如戏,这种“朝承恩,暮赐死”政治斗争的变化莫测,也是人生如梦般的变化莫测。
因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的探索追求都是徒劳无益的,这时候“荒诞的世界”是导致“人生如梦”的原因。而因为生活在世界的人一生的追求都没有意义,世界便是荒诞的。这时候“人生如梦”是导致“荒诞的世界”的原因。
《邯郸记》的荒诞色彩体现在多个方面,不仅在其剧情安排、唱词设计,也在其思想内涵。本文试从梦、戏谑、人生意义出发,分析《邯郸记》中“真实与虚幻”“严肃与滑稽”“意义与无意”体现的荒诞性。
纵观中国古典传奇、神道题材剧目较多,乏善可陈,创作风格难逃窠臼。但是汤显祖的《邯郸记》却因其别具一格的荒诞色彩为神仙道化剧增添了一抹亮色,后人观之,赞叹不已。
①https://baike.baidu.com/item/荒诞/2957215 fr=aladdin。
②https://www.douban.com/note/801909403/ from=auth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