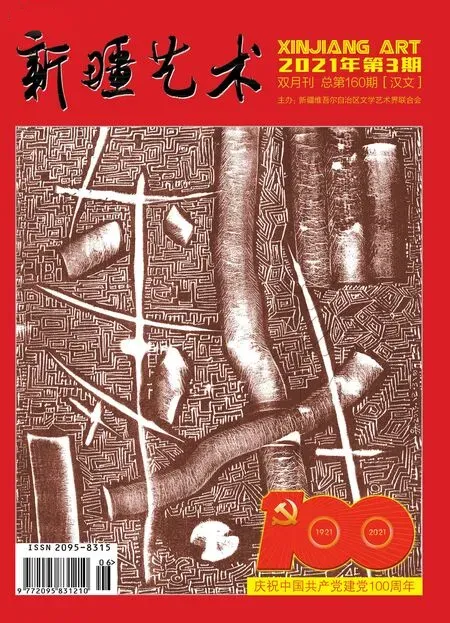艾青诗歌中的“文字绘画”之美
□ 荆利霞

艾青早年学的是美术,他的艺术生涯是从绘画开始的;1928 年就读于当时全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国立两湖艺术专科学校,开始了他系统的绘画学习之路;1929-1932 年在法国巴黎留学,这一时期正是印象主义盛行之时。前期印象派注重瞬间光和色的变化,而后期印象派画家更关注画家的内心感受、主观感情和情绪,表现“主观化的客观世界”,在艺术表现上更加注重形体、线条、色彩等。身为画家的艾青接触了印象主义并深受其影响。黎央先生曾评价艾青诗歌时说:“艾青写诗像‘印象派在作画’”。艾青自己也说:“同样都是为真、善、美在劳动。绘画应该是彩色的诗,诗应该是文学的绘画。”
显然,艾青早年的绘画经历,加之法国印象派绘画艺术对他的深刻影响,使他的人生与绘画结下不解之缘,这段经历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画家的眼光去观察和捕捉生活中的事物,以画家的敏感去感知生活、书写诗歌,这也为他之后的诗歌创作实践增添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一、构图之美
艾青在《诗论》中说:“诗人应该有和镜子一样迅速而确定的感觉能力,而且更应该有如画家一样渗合自己情感的构图。”这种“情感的构图”的创作方式,体现在艾青的诗歌中,一般带有印象画派的印记,即用表示线条、形状的词语和散点透视法的方式在诗歌中勾勒和布置画面,并由此形成独具艺术特色的具有绘画美的诗歌。
其构图之美,首先表现为线条和形状的运用。线条和形状是属于绘画中最基本的要素,同时也是造型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线条又是最高级的语汇,因为线条能表达画家精微的感觉和细腻的情感。”因而对于有着画家身份的诗人艾青来说,在诗歌中运用线条和形状的绘画因素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他的诗歌中有一些是直接运用线条、形状来体现诗歌画面的构图之美的句子。
比如他笔下的《公路》:绵长的公路/沿着山的形体/弯曲地,伏贴地向上伸引。运用一些像“绵长”、“山的形体”、“弯曲”、“向上”、“伸引”等表示线条性的词语,将公路的走势与形态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再比如《浮桥》:“一只船并挨着一只船/……/从江的这一边/到江的那一边/浮桥浮搭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用“从……这一边”、“到……那一边”、“搭”、“在……之间”将一幅富有诗意的画面用这些表示平行、垂直关系的线性词勾勒出来;再比如《西伯利亚》:“从山坡到山坡/电线架和电线/一直向天边伸引……”用“从……到……”,“伸引”等,给我们视觉上以由近及远的审美体验;又比如《低洼地》:“岩石砌上岩石砌上岩石砌成山/山下是杂色的树杂色的树排列成树林/林间是长长的长长的石板铺的路/石板铺的路通过石桥一直伸引到乡间……”以表示叠加的线性词语“砌上……砌上……砌成……”与表示延伸的线条词语“……排列成……”、“长长的”、“伸引”等,在诗歌的空间布局上给我们营造出一种近大远小、近低远高、近实远虚、近宽远窄的视觉美感。在《会合》和《太阳》中,用“团团的”、“烟圈”、“长发的”、“卷烟”和“圆体”等描述物体形状的词,给读者呈现了一幅形象逼真的画面。在上述这些诗中,诗人艾青以画家的眼光去选景写景,以画家的敏感发掘画面潜在的线条结构和形状,进而用语言艺术创造出极具构图之美的诗歌意境。同时还在体现构图之美的细节之中,艾青将自己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与真挚细腻的情感体现了出来。
其次,表现为散点透视法的运用。透视法是画家绘画时常用的技法,一般分为散点透视和焦点透视两种方式。西方古典绘画大多采用焦点透视的画法,但后期印象派更注重画家自身的主观情感,因而在作品中更多地采用散点透视的画法。所谓“散点透视”,即观察者的视点通常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也不受视域的限制,而是用移步换景的方式来选取自己需要的景物。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使诗歌的空间画面更丰富,而且还有利于作者“融情于景”。受后期印象派绘画影响的艾青在其诗歌作品中,也运用过散点透视法。
比如《秋日游》:“草原的低洼处/星散着白色的山羊/它们各自啮啃着青草/没有一个人去看管/新筑的黄土公路沿着小溪/弯进了杂色的树林/又出现在远方的/照着阳光的山坡上……”再如《西伯利亚》:“早晨的草原上/朝着初升的太阳/站着一个/花裙迎风摆动的/年轻的农妇/叠木的小屋的/玻璃橱里面/盆花红得像火焰一样/从那菜园里/向日葵探出了头/看着牛犊在吃草……”又如《透明的夜》:“……阔笑从田堤上煽起……一群酒徒,望/沉睡的山村,哗然地走去……村/狗的吠声,叫颤了/满天的疏星”在这几首诗歌中都没有要着重表现的主体画面,也没有固定的视点,画面的空间布局也没有在固定的视域内,而是凭借移步取景的方式来实现。艾青在诗歌中以这种散点透视的方法,不仅细致地写出了诗中景物的空间位置与整体布局,展示了其诗歌的构图之美,而且也在景物的转换间将自己心中向往静谧和谐的感情(《秋日游》),闲适恬淡的情趣(《西伯利亚》),迷惘郁愤的愁苦(《透明的夜》)也一并糅入到景物之中,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审美体验。
二、色彩之美
塞尚曾说:“色彩是伟大的本质的东西。”梵高也认为色彩具有“暗示力量”:“画里面的色彩,就是生活里的热情。”“绘画,像现时的,将趋向更精微更多的音乐,较少的雕塑。最后它许诺提供色彩,而这是和情感结合着的色彩,像音乐和激动结合着的。”艾青也说:“一首诗里面……没有色调,没有光彩,没有形象,艺术的生命力在那里呢?”可以说在印象派绘画和艾青的诗歌中,色彩是不可替代的存在。在印象派绘画色彩艺术的影响之下,艾青在自己的诗歌中对色彩进行了巧妙的运用,并根据色彩的明暗、冷暖赋予了这些色彩词语以特定的象征寓意与思想情感。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随类赋彩、以彩寓象。艾青常常在自己的诗歌中,利用这种方式来达到表情达意的目的。在艾青的诗歌中,某些色彩逐渐被赋予了一定的隐含意义,有些看似简单朴素的色彩词语,用在具有象征意味的诗歌之中却表达了特定的含义。比如在《那边》《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中用黑色表示黑暗、灾难、不公;在《生命》《吹号者》《冬天的沼泽》中用灰白色表示忧伤、难过、低沉;在《他死在第二次》《红旗》中用红色表示光明、热情、活力、希望;在《手推车》《风陵渡》中用黄色表示荒凉、失落、哀怨;在《呼喊》《北方》《绿色》中用绿色来表示生命、活力、朝气;在《向太阳》《小蓝花》《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用紫色表示悲痛、深沉、高贵等。

其次是原色的并列与堆叠。印象派画家受色彩混合理论的影响,采用了色彩并置的表现手法,并通过原色并置、堆叠的方式在诗歌中形成富有力度、有节奏、有情感的韵律。比如《当黎明穿上了白衣》:“紫蓝的林子与林子之间/由青灰的山坡到青灰的山坡/绿的草原,绿的草原,草原上流着……”再如《绿》:“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到处是绿的……/到哪儿去找这么多的绿:/墨绿、浅绿、嫩绿、翠绿、淡绿、粉绿……/绿得发黑、绿得出奇/刮的风是绿的/下的雨是绿的/流的水是绿的/阳光也是绿的”又如《那边》:“黑的河流,黑的天/在黑与黑之间……”通过各种不同的颜色将那些抽象化的事物转化成具象化的东西,可视可感可触。又凭借着原色的并列以及不同颜色之间的堆叠往复,不仅勾勒出一幅极具审美享受的诗歌画面,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体验,而且在这些色彩词语的并置与堆砌之中,作者赋予这些色彩词之上的象征意义与附加情感被更加强烈地表达了出来。比如在《绿》中用绿色的并列与堆叠,强调了诗人内心对于勃勃生机的渴望之情;在《那边》中用黑色的往复循环强调了社会的黑暗和诗人的忧国忧民之情。
再者是色彩的补色对比。印象派画家在对原色的运用中发现两种不同的颜色放在一起时,会将一色推向自己的补色,比如白色与黑色,红色与绿色同时出现在画面上,一种颜色会因另一种颜色的补色对比而显得更为鲜艳。正如德劳奈说:“红与绿,在中央对抗着,产生极快的振动。”达·芬奇在谈色彩的对比关系时也说到:“色彩在与其对比色相邻时会表现出最佳形式,也更为鲜明。”在艾青的笔下,更是不乏运用这种手法来对比强调内心情感的诗歌。如在《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中:“一个是那样黑/黑得像紫檀木/一个是那样白/白得像棉絮”,用黑白两个人种来作比,鲜明而又强烈地表达出作者对于不平等社会的感慨与对黑人姑娘的同情;在《黎明》中:“希望在铁黑的天与地之间/会裂出一丝白线”,在天地笼罩的黑暗的衬托下,更显现出对于黎明的白昼的向往与希冀;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用“黄土下紫色的灵魂”的对比,让我们透过厚重的黄土之下更看到乳母高贵的紫色灵魂;在《生命》中“也将要自己的悲惨的灰白/去衬映出/新生的跃动的鲜红”,用表示自我悲惨的“灰白”去映衬代表新生活力的“红”,在强烈色彩对比中突出表达作者对于新生的向往;在《雪里钻》:“雪的平原/突然看见鲜红的血迹/淋漓在净白的雪堆上”,在红色与白色的鲜明对比中,体现出作者对革命战士勇敢奉献精神的赞颂以及对消逝生命的叹惋之情。
三、笔触的表现力之美——动词在诗中的巧妙运用
印象派绘画在作画时因受到时间因素和光线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因而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绘画。这也使得画家为了更好地表现画面的整体效果而有意忽视了对细节的刻画,在绘画时选择用奔放的笔触直接描绘事物,也更注重笔触的表现力。尤其是后印象派绘画,更加强调笔触的表现力。这派画家在凸显笔触的表现力之美时注重“写”的精神,这种方式使得绘画富有激情与遒劲奔放之感。而且在绘画过程中还强调用色彩的“点彩”与“分色”来实现笔触的表现力,以更好地表达新鲜、颤动的画面效果。

艾青在《母鸡为什么下鸭蛋》一文中提到:“诗比起绘画,诗它的容量更大。画只能描画一个固定的东西;诗却可以写一些流动的、变化着的事物。”艾青为使自己的诗歌展示出笔触的表现力,不仅借用印象派的“写”的精神(线条的运用)和色彩对比、并列之法,还在诗画结合的过程中,巧妙地使用了动词来使诗歌更具笔触的表现力之美。比如在《湖心》中用“荡碎”、“映着”、“飘”等动态词语,将镜面似的湖面的寂静打破,恰似诗人“颤震的心灵”一般的不平静;又比如在《透明的夜》里,用“煽起”、“望”、“哗然”、“叫颤了”、“冲进了”、“醉了”、“笑”、“走”、“去”这些动词,将夜晚本该是宁静的状态打破,而使“透明的夜”变得热闹又喧哗;再比如在《会合》中使用大量描写细节动作的动词,如:“转在”、“摇动”、“沸腾着”、“戴”、“点”、“读”、“看”、“思索”、“苦恼”、“兴奋”、“沉默”、“飞”、“散”、“喊”、“恨”、“捶”等,在诗歌中渲染出一种“动态”、“张扬”的氛围。艾青在诗中使用这种极具表现力的动词,一方面使诗歌呈现“颤动”的画面效果和动态之美;另一方面,又使得诗歌勾勒出的和谐画面出现激烈冲撞与矛盾冲突,以此表达诗人当时内心的复杂情感,在情感上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艾青在论诗时说过:“存在于诗里的美,是通过诗人的情感所表达出来的、人类向上精神的闪烁。”“不要成了摄影师:诗人必须是一个能把对于外界的感受与自己的情感思想融合起来的艺术家。”艾青虽然在诗歌创作中以画家的眼光描绘了“文字绘画”的美,但绝没有以一个画家的身份单纯地去表现“绘画美”,而是在展示“文字绘画”之美的艺术实践中,融入了时代情感与个人思考。艾青笔下所写的“文字绘画”的这类诗,做到了他对诗歌的要求,即“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
结语
艾青在巴黎的绘画学习经历,让他的诗歌创作与绘画艺术融为一体,因而在其诗歌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展示出了“文字绘画”之美。但艾青在创造诗歌“文字绘画”之美的过程中,没有仅仅停留在诗歌的审美层面上,而是融绘画审美艺术与诗人的个人情感、时代关注于一体,使诗歌既具有审美体验,又具有更深的探索和研究价值。可以说艾青在“诗画”相结合的诗歌艺术实践中,创造了一条属于自己独特的诗歌艺术之路,其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诗歌的“文字绘画”之美,还有诗人对于家国的深厚感情与对时代命运的切身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