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汪”情深
——从毕亮《如看草花:读汪曾祺》说起
□ 张家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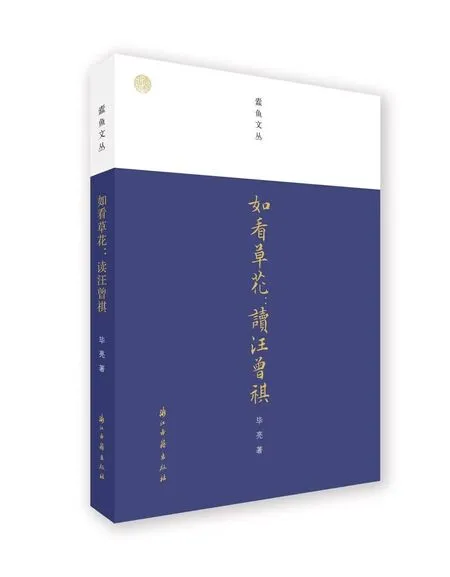
从2009 年开始接触汪曾祺的文学作品到现在,毕亮一直悠哉悠哉地沉浸在汪曾祺的世界里,关于某本书的版次、印数、某一封信的意义、某一篇文章的内容遗漏,皆被他津津乐道地讲述着。他把读汪后的诸多感受、体验、领悟书写成文,结集成《如看草花:读汪曾祺》。草花本为凡俗之物,汪曾祺的文字正是人间日常的书写。
这样的见解在两位当代文坛名家那里得到真切的呼应。
贾平凹于二零零六年至高邮时,对汪曾祺的评价极高。“这一类作家生前不一定很红火,他们不一定得了许多奖,不一定做什么官,偏偏是只有这一类作品很长久。”很长久的是作家笔下关乎世道人心的作品。突然造访高邮的铁凝不以北头街上众多的摊子为意,笑意盈盈地对东道主说:“没关系,生活本来就是这样。这种环境是人的生活气息浓的表现呀。”很显然,汪曾祺当初对铁凝、贾平凹等人的提携与鼓励,在后来是得到对等回应的。不是说他们彼此之间的鼓励与夸赞是对等的,而是对文学本质的理解殊途同归。
写汪曾祺的朋友圈,对毕亮来讲既是勾勒作家的交游史,也是寻求知音之举。不难想见的是,毕亮在读到铁凝、王安忆、贾平凹等人对汪曾祺的高度评价后,心中的那份欣喜。此番欣喜不是源于初遇的惊艳,而是得到鼓励与鞭策后往后读书生涯里的甘之如饴。他对汪曾祺的想念与敬意、与年纪长于他的人言说着。这种不断被填充、丰富、积攒着的美好,为他的新疆岁月增添了千金难买的幸福指数。
如果说阅读汪曾祺是一场接力赛的话,毕亮的书写是第二棒,接续传递第一棒的热度。在分享自我快乐的同时,让汪曾祺其人其文为更多读者熟知,是阅读带来的意外之喜,是阅读独特的魅力所致。然而,毕亮并不是汪曾祺研究学者,他所做更多的是梳理,梳理自家视野中汪曾祺作品及其研究著作的编撰史与传播史。
金实秋的《泡在酒里的老头儿:汪曾祺酒事广记》可让读者一窥汪曾祺“饮酒史”的全貌。王干习惯于夜间读汪,这样的习惯持续长达四十多年。夜读时感觉“如秋月当空,明净如水,一尘不染,读罢,心灵如洗”。《夜读汪曾祺》正是他读后体会的部分成果结集。凸凹喜欢汪曾祺,人生不顺时,常从汪的文字里寻求一剂解药。如从老朋友那里寻得宽慰。诚如他所说:“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苏北在认识汪曾祺之前就痴迷其文,在结识汪曾祺之后既痴迷其文更喜爱其人,并且写出一本又一本汪曾祺研究专著,被人称为“天下第一汪迷”。话说回来,《如看草花》的出版何尝不是编撰史与传播史中的一环?尽管这些总结虽不免片面,却有其存在的意义。至少,读者想要了解汪曾祺的某些侧面,可以以书籍或文章为路径,潜心读下去。
毕亮是地道的汪迷,这无疑是令人羡慕的。若无专注,则没有自称为“迷”的资格。让自己的生活与汪曾祺的作品互相交融、难解难分的他,每每打开书籍则爱不释手、乐不思归。翻读《汪曾祺:文与画》,他时而冲着文,时而冲着画,文与画交替品读。“好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去年出版了《四时佳兴》、故宫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书画》,弥补了些许遗憾。它们被我请进了书房,从而解放了《汪曾祺:文与画》。”“请”字好,透着按捺不住的窃喜甚至兴奋。“解放”一词也好,不自禁地流露出他的爱不释手,他的痴迷至极。
居家读,外出读。住村时躺宿舍床上就着台灯翻几页汪曾祺的小说,雨夜时听雨打铁皮声想起汪曾祺的《星期天》,按照汪曾祺四处走走的提醒学着观察生活,学着汪的笔触了解记录闹市中的“活庄子”,看着无处不在的晚饭花想起小说家笔下的李小龙、王玉英,学着汪曾祺拌菠菜一样拌了一盘蝎子草。毕亮读汪曾祺绝不止于书籍,还在于日常的诸多片段中。他说:“我读汪曾祺,常被他细微之处的人间情怀打动。”情怀濡染人心,毕亮的情不自禁跃然纸上。汪氏笔下汉字的奇妙与鬼斧神工,固然是其不必多言的魅力。然而,他更多的魅力早已超越文学的局限,蔓延在广阔的天地里。亦如贾平凹所评价的,“偏偏是只有这一类作品很长久”。在品读王干《夜读汪曾祺》的文章末尾,毕亮颇为肯定地自许道:“我读汪曾祺近十年,越读越喜欢,今后大概也会随着汪曾祺老去吧。”
既是编撰史、传播史,也是毕亮梳理自家关于汪曾祺著作的阅读史与成长史,或者说是他与与汪著的“恋爱史”。这是一种痴迷更是一种福分。毕亮并不专作考据、求证之事,若有也只是偶尔为之。正如他在《立体的汪曾祺》中所言说的,“我并不是研究者,只是汪曾祺众多作品的读者。我之所以一遍遍地翻看这本书,看重这本书,只是想更多地了解作品之外的汪曾祺,试图通过这本书走近那个可爱的老头儿。”研究者只是少数,如毕亮这样的读者才是大多数。如此,则《如看草花》是不设门槛的,拥有走近许多人心里的可能。读汪曾祺的文,亦是在品汪曾祺的人,这种注定相伴一生的际遇,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正因为得不到,才有了阅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