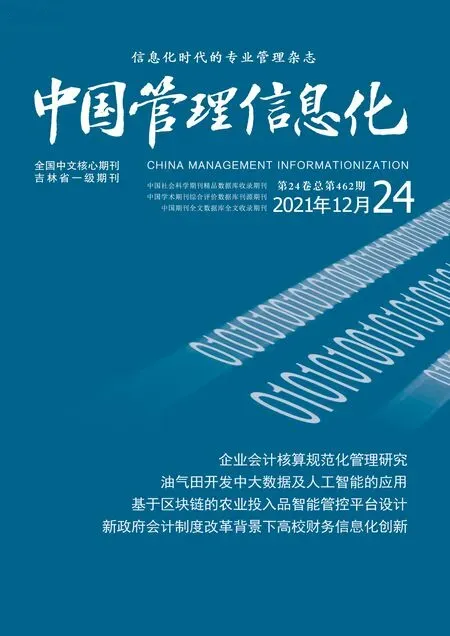社会资本视角下提升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幸福感的路径探析
郝蔓嘉
(南京邮电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南京 210023)
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社会数字化程度日渐加深,老龄化现象也愈发突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面临着“数字鸿沟”导致的数字化生存困境。据调查,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会上网的人数占比仅为1/5[1]。由此可知,数字化时代仍有大量老年人陷入无法享用数字社会便利的现实困境。针对日益凸显的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困境,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指出让老年人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自我控制失败导致的时间效能感降低,会进一步削弱主观幸福感[2]。因此,探究提升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幸福感的路径对于构建智慧老年社会、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社会资本:构建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幸福感路径的理论框架
对于有关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学术界存在多元分析视角与理论框架,其中社会资本于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种系统的学术概念。1916年利达·汉尼范在《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学术年鉴》上首次使用“社会资本”这一专属称谓,并将人们生活中与传统资本具有同等价值地位的实在物质如伙伴关系、往来互动等纳入了社会资本。在这一概念雏形的影响下,诸多学者对其内涵进行了研究与阐释:布迪厄最早将社会资本系统化,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较强稳定性的社会关系网络;科尔曼则从社会资本的功能视角出发,强调其社会结构特征;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其中,普特南的理论解释框架成为众多学者理解社会资本的重要逻辑,其内涵主要体现在认知、结构与制度三大层面。
2.1 社会信任:提升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幸福感的基本前提
社会信任是一种柔性契约,是构建人际关系与社会联结的基础条件。它能够将其蕴藏的文化价值与伦理道德等柔性要素融入硬性的制度设计中,这为提升幸福感路径的可行性与实效性提供了隐形保护层。一方面,要提升老年人对社会的信任程度。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生活满意度也越高[3]。因此,提升老年人社会信任度有助于提升其数字化生存幸福感。另一方面,要提升社会各界对老年人的接纳程度。倘若社会各方对老年人的数字能力持不信任的态度,直接忽略或放弃对老年人数字设备与技能的帮扶,则意味着对老年人的数字化自主能力进行了“抛弃”。因此,社会信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老年人的良性数字化生存需要老年群体与社会各界相互信任,只有实现双边信任才能构建出真正有效的幸福路径。
2.2 社会网络:提升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幸福感的主要载体
社会网络是社会成员之间交流互动的纽带,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呈现多元化,数字化应用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生命历程长期处于无网、少网状态的老年人来说,其在短时间内融入数字化社会是困难且不切实际的。对此,社会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合力,提供全面的数字化适应服务,为老年人增能赋权,提升老年人数字化生存的自主能力。唯有构建起良性的社会网络,老年群体才能在数字化生活中有资源可依、有技术可循,为生活幸福感的提升创造契机。
2.3 社会规范:提升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幸福感的重要保障
社会规范作为在社会期望与公众利益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具有较强稳定性与可靠性的制度机制,为社会成员的行动提供了基本保障。对老年人来说,融入数字化社会意味着突破基础性数字瓶颈。然而,这一过程是复杂多变的,不能仅依靠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等能动性支持而缺乏强有力保障。这就需要充分发挥顶层设计的作用,在制度设计与管理条例等方面进行有力保护。这不仅可以为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提供个性化社会服务等保障,激发与增强老年人适应数字化生存的信心,还可以起到引领社会服务方向,提升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帮扶力量的作用。
3 社会资本式微:老年人数字化生存的现实困境
3.1 双边信任不足
受到传统观念与文化水平等的影响,老年人对于无血缘或亲缘关系的陌生群体易产生排斥与隔阂,因此来自社会力量的善意帮助可能会面临无人接受、屡遭拒绝的尴尬局面,这不仅会打击社会群体对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帮扶的积极性,还可能进一步降低老年人主动学习数字技能的能动性。与此同时,社会刻板印象情结浓烈,充斥着老年人过于羸弱、迟钝等偏激的言论与认知,对老年人积极健康地融入数字化社会持有不信任与不重视的态度,这对于老年人学习数字技能、获取数字信息、适应数字化生存等具有负面影响。双边信任不足,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构建社会支持网络、落实社会制度保障的基础。信任缺失成为老年人提升数字化生存能力和主观幸福感的重 要阻力。
3.2 社会支持网络尚未形成
老年人数字化生存适应与否,有赖于众多社会力量携手合作的成效。现如今,代际关系松散化、社区服务项目单一化、社会组织服务零散化等现象屡见不鲜,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尚未形成,支持发展迟缓状态也未能良好改善。在代际层面,部分子女对于老年人的数字操作技能、数字信息识别等方面的帮助普遍缺乏足够的耐心与精力。在社会层面,难以寻找到对应的精准服务。社会支持网络不健全,意味着老年人即便有积极融入数字化社会的意愿,可寻求的社会资源也是有限的,甚至无路可循。
3.3 制度设计不完善
目前,我国关于老年人数字化生存的管理与服务存在制度规范体系不完善、基层制度个性化欠缺等问题。政府根据法律与公共服务管理的需要为老年人提供外力驱动型规范,然而这种规范大多是纲领性、指导性的,离真正落实还有一定差距。内生性规范存在于社会各个组织、团体中,如社区或社会服务组织针对老年人数字化生存自行设定的一种规范,对于真正落实帮助老年人融入数字化社会具有关键作用,也是可指标化、实践化的社会规范。然而,当前针对老年人数字化生存方面的制度设计明显空缺,且外力驱动型规范与内生性规范难以结合,导致现有的制度保障与服务规范对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缺少切实效用,难以满足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需求。
4 增量社会资本: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幸福感的提升路径
4.1 加强社会参与,提升社会信任度,加强双边信任联结
要提升老年人数字意愿,打破公众刻板印象,为老年人打好数字化生存基础。老年人对新兴事物的态度常受到身边群体行为的影响[4],提高老年人与社会参与度高的朋辈群体的接触频率不仅可以提升其对外界的信任度,促进其社会交互行为,还有利于提升老年人以数字通信方式进行交流的数字意愿。除此之外,老年人数字化生存的关怀与支持应聚合社会各方力量。然而,受到传媒舆论等的影响,老年人羸弱、记忆退化等形象深入人心,这导致很多人持有老年人不必融入数字化社会的消极观念,并且质疑老年人融入数字化社会的能力。在此观念影响下,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面临被轻视或无视的局面,给老年人带去了难以言明的痛苦与无奈。对此,大众传媒等应正向引导社会氛围,拒绝老年“无用论”;社会各界应积极投身于助老行动,加强双边信任联结。
4.2 营造养老氛围,构建助老社会网络
要加强代际反哺,完善精准服务,为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提供多元支持。受到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经济地位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家庭“共同体”趋于分裂,代际关系也随之呈现出松散化态势。为充分发挥子女反哺作用,应合理利用社会舆论效应,营造以家庭为核心的养老助老文化氛围,增强子女赡养意识,使其合理规划自身时间,积极履行赡养义务,助力老年人更加便捷、舒适地融入数字生活。此外,有研究表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关系[5],社会支持力度越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因此,各大社会主体都应积极发挥自身作用,以达到多元共治的为老服务效果。社区、社会团体等服务组织应树立正确的年龄意识,将自身服务与老年人数字化生存的现实困境相结合,在传统养老服务的基础上开辟新的服务领域,提高个性化服务供给能力,构建助老社 会网络。
4.3 加强制度设计,提供韧性政策保障
要实现政策个性化保护,为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提供根本保障。社会公平的实现离不开顶层设计的支持,科学制度的制定也需要加入人文关怀。老年人受时代局限与生理机能退化等影响,在数字化社会中属于相对弱势群体,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符合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老年人数字化生存的相关政策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完善的个性化保护与帮扶政策尚有缺失。因此,制定老年人数字化生存方面的政策保护与服务规范,对于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具有重 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