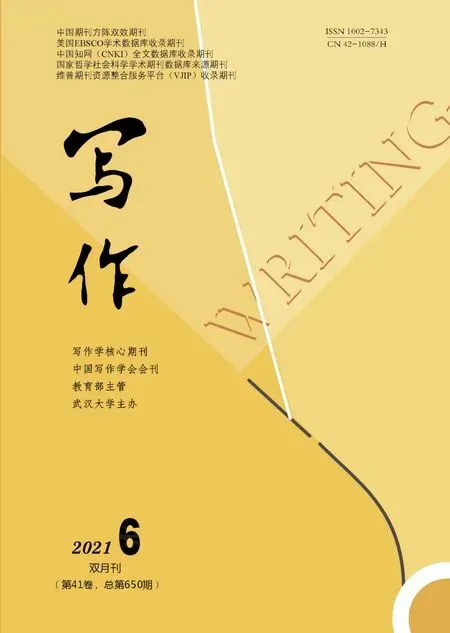电视剧改编的文本整合策略
陈爱国
文本整合策略是作品创作时对相同或相近题材的文本进行整理、综合的策略。它是叙事类型化与大数据时代产生的有关题材的类型版本与全景版本。叙事型文艺到了艺术规范高度成熟的阶段,到了原创能力被耗尽的阶段,文本整合策略便应运而生。当前,电视剧创作界的一些名著改编剧、翻拍剧,面临同一题材、同一类型、关联较大的多种版本的竞争,若要脱颖而出,吸引社会注意,似乎往往需要采取这一策略,通过“新的综合”产生“新的文化”。对于这一策略,业界至今缺乏系统性的梳理与探讨。
众所周知,“任何一部文学或艺术的经典名作之常新,不仅在于有着‘永恒’的审美价值,其常新刚好在于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的一再重读,或再阐释。”①戴锦华:《文学与电影·序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名著改编剧从语言叙事转到影像叙事,或从短篇叙事转到长篇叙事,“必然要兼顾自身媒介的本体特征,必然会融入导演对原著的创造性阐释和新的文化内涵”②毛凌滢:《从文字到影像:小说的电视剧改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其实,还存在更具有结构性的变化,即改编者对原著重新阐释,大多运用一定的整合理念,类似时下流行的“市场整合营销传播”,引领名著改编翻拍的风尚。如今,几乎所有电视剧都是改编剧,源自文学名著、历史名著、戏剧名著、网络文学等,其初始版本一般忠实于原著;一旦改编翻拍版本陆续增多,势必会另辟蹊径,采取文本整合策略,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翻新,出奇制胜,与其他版本区别开来。这正是新创版本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之所在。
一、文本整合策略的艺术动机
1980—1990年代,中国内地电视剧对文学名著的第一轮改编,基本忠实于原著,“向经典致敬”,采取“一文一剧”或者“一文多剧”的策略,推出了《红楼梦》《人物志水浒传》等一批经典改编剧,努力再现文学原著的内容与结构,但较少考虑电视剧本身的叙事特点与文化特质。1994年央视第一次全景拍摄《水浒传》时,拟邀请香港演员梁家辉出演林冲。他提出要以林冲为主角贯穿全剧,这是当时境外早已流行的传记式改编策略。这一要将原著弄得“面目全非”的改编思路被影视观念正统的央视谢绝,梁家辉也因此无缘参演。
21世纪以后,在文化产业、资本运营的推动下,内地古典文学名著进入重拍期,如何超越旧版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受1990年代《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等港台影视剧改编策略的影响,内地的一些电视剧编导不再拘泥于原著再现,改编思路逐渐“野”起来,艺术观念逐渐放开,倾向于现代翻新、文本整合等新型改编策略,体现出新历史主义、消费主义的艺术倾向。“多文一剧”的文本整合改编策略的艺术动机主要有三个。
(一)故事加长的需要
人类创造的各种故事文本大体呈现为“滚雪球”的模式,越来越长。将长篇叙事发挥至极致的叙事性文艺是电视剧,篇幅多则成千上万集,可以无限加长。这里包括两种艺术原动力的需要:
一是文化整合与文化增殖的需要。这是文化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不断文化积累与文化创新的结果,而“文化的再生的基本原因在于文化的创造”①梅新林、赵光育:《现代文化学》,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电视剧改编与翻拍,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创造、文化增殖,而不是简单的文化复制、文化传承。文本整合策略是文化增殖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文本整合、文化叠加而生产出具有新质要素、新型样式的文化产品,促进文化的再生、增殖、繁衍,其体量相应会有所增加,篇幅越来越长。
如台湾省《新白娘子传奇》,是经过明清以来许多同题作品的不断累积整合而成的,前有明清冯梦龙、黄图珌的基础性创作,后有方成培、田汉等人的一系列改编作品。该剧的前30集,大体根据当代田汉的京剧《白蛇传》以及清代方成培的传奇《雷峰塔》、玉山主人的小说《雷峰塔传奇》改编,其中有些唱词源自京剧版本里的唱词。该剧的后20集,大体根据清代梦花馆主的小说《白蛇全传》改编,增加许士林的成长故事,与李碧莲、胡媚娘的爱情,以及中状元、祭塔、大团圆等情节。该剧第一次全面贯通、完整展现了白蛇的神话故事,成功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有效表达了人妖有别、慈悲为怀等思想主题,并运用歌舞剧的形式,建构了诙谐、欢快的大众文化品格,因而得到大众的文化认同。
二是长篇叙事与故事消费的需要。电视连续剧、系列剧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主要形态,属于长篇叙事型的文艺作品,能够满足观众的日常审美消费的需要,因此容易滚动式地扩展剧情,呈现线性延伸的发展趋势。鉴于内地的电视剧生产体系与播出体系大多是分离的,生产单位为建构史诗作品,追求最大利润,往往不断加长剧集篇幅,动辄达到70集以上。
为了达到长篇叙事、增加集数的目的,“大IP”策略、文本整合策略、编剧团队策略的运用就在所难免。一些编导者、策划人往往抓住多个“大IP”作为故事资源,搜罗古今中外的一些历史记载、传说故事、文学作品,以及它们的各种版本,积极运用文本整合策略进行“孵化”,组织编剧团队进行创作。在理论意义上,这些被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大IP”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叙事策略,而叙事策略则决定拍摄集数。只要制作人、投资人具有某种需要,编导者、策划人就可以临时增加某些人物、情节、线索、主题,从而人为地加长了电视剧的篇幅。
这两种艺术原动力是互为表里的。原型故事在不断加长、不断增容的过程中,必然会进行文化整合,实现文化增殖。
(二)叙事突破的需要
同一文本、同一故事的影像化改编,不会停留于一个版本。鉴于前有初始版本、经典改编,此后的改编、翻拍往往就要走突破创新的道路,在人物、关系、情节、线索、主题上,极尽腾挪变化之能事。对于长篇叙事而言,“做加法运算”尤其重要。相比于1992年版的《新白娘子传奇》,此后香港电影《青蛇》、内地电影《白蛇传说》、内地话剧《青蛇》、动画版《白蛇:缘起》,都在《新白娘子传奇》的基础上,做加减法运算、伦理主体逆转、叙事视角更新,各显特色。为避开《新白娘子传奇》的“光环”,2018年版的《天乩之白蛇传说》在京剧《白蛇传》的基础上,融合电影《青蛇》、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以及骊山圣母等许多其他神话传说。这是迄今为止白蛇故事改编力度最大的电视剧版本,走的是当前流行的古装玄幻剧的创作路数。
举一个恪守原著、拒绝突破的案例。相比于1987年版的《红楼梦》,2010年版的《新红楼梦》《黛玉传》,除了在音乐、服饰上略显新意外,在人物、关系、剧情与题旨上,都拘泥于原著《红楼梦》或旧版《红楼梦》,缺少突破、创新。在《新红楼梦》的策划、创作过程中,某些红学家过度干预剧情,要求原封不动地照搬原著故事,大量增加画外音以再现原著文字,造成声音和画面严重错位,形同“鬼片”。即使《黛玉传》试图用人物传记模式改编原著,强化“宝二奶奶之争”的冲突,也还是沿袭旧版的总体框架,缺乏总体意义上的叙事突破。
有一些改编剧的叙事突破,是暂时找不到确切的历史文本来源的,只能算作“合理想象”,或者算作“虚构文本”,不同程度地体现某种“集体无意识”。荣格认为:“人生中有多少种典型情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无穷无尽的重复已经把这些经验刻进了我们的精神结构中。”①[瑞士]荣格:《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荣格文集》,冯川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如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作为平行主线的孙少安的某些情节,是临时增加的。电视剧《红高粱》中增设为平行主线的朱豪三的一些情节与关系,以及戴凤莲与父母、与情人张俊杰的一些情节,也是临时增加的。从故事原型、故事衍生的角度而言,“合理想象”“虚构文本”大多应该是有所依据的,至少运用了原型思维,如果编导在有关的创作陈述中不予明言,一时之间往往很难让人查证。
(三)文本还原的需要
以往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历史作品,因为各种原因,在处理历史事实、生活事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时,大多增加了很多传奇、神秘、正统、伪造的色彩使得历史和生活变形了,走样了。电视剧改编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是进行“现象学还原”,将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回来。在文本学意义上,“历史”概念可指涉历史事实、历史源本、原初文本。历史还原、文本还原是一项高深而复杂的学术工作,一时很难讲清。简单地说,它们是将人物、情节、主题置于最初的历史环境、故事情境,客观地、辩证地予以对待。电视剧改编的历史还原、文本还原,一般是兼顾、复原多个历史文本乃至学术文本,尽量避免文艺文本中的虚构成分、伪造成分,做到客观公正、符合本原面目。
内地电视剧中,最早进行“文本还原”尝试的,可能是1987年版的《红楼梦》。其80回之后的故事蓝本主要是依托于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的学术成果,少有高鹗的续书内容,尽量“还原”小说原著的原初文本。该版本在华人圈广受好评,却也引起一些支持高鹗续书的红学家的不满与抵制。再加上其他原因,80回之后的拍摄内容遭到大量删节,原来应有15集,最后被压缩成7集播出,草草收场②参看矮木:《揭秘87版红楼幕后的大师们》,网易号2017年6月24日。据摄像师李耀宗说,体现后四十回内容的15集的底片其实已经拍完,全部底片上交电视台,但2007年它们惊现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摊主开价颇高,他无力购买。若是收回,或许可以再现44集的全本面貌。。与政治问题无关的文本还原工作理应是容易被接受的,但在激烈的学术争议的氛围下也难免充满历史吊诡。
最耀眼夺目的历史还原、文本还原,是一些历史传奇剧纷纷升格为历史正剧。价值观念的普世化与历史资料的普及化,促使一些传奇英雄的“加冕”或“失圣”。电视剧《成吉思汗》在电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基础上,糅合了《蒙古秘史》《多桑蒙古史》等历史文献,尽量再现丰富复杂的历史文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呈现出粗犷原始的史诗风格。电视剧《三国》《大军师司马懿》都极力摆脱小说《三国演义》的束缚,最大限度地糅合《三国志》《后汉书》等历史文献,对曹操、司马懿等一些“反面人物”以及刘备、关羽等正面人物的评价,都比较客观。电视剧《精忠岳飞》在传统小说、评书《岳飞传》的基础上,糅合了《宋史》《金史》《鄂国金佗稡编》等历史文献,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做了真相还原,对岳飞、宋高宗、秦桧的特定心理给予了较多揭示。
相反,21世纪以后的《杨门女将》《杨门虎将》,仍然改编自传统小说、评书《杨家将》,仍然保留穆桂英、杨宗保等虚构人物,依然将北宋名臣潘美丑化为“潘仁美”,没有结合《宋史》《辽史》《九国志》等历史文献,没有还原杨家将的历史面目,走的是传统历史传奇剧的路数。究其原因,杨家将的真实故事不及虚构故事精彩,而忠君爱国的主题思想是无法被替换的。历史还原、文本还原是电视剧改编目标中最难处理的一项,因为它们跟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的创作思潮有关,而意欲颠覆既定的“历史文本”,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二、文本整合策略的整合模式
电视剧改编需要遵循一定的叙事模式与艺术理念。如内地1986年版《西游记》的改编,运用幽默喜剧模式,去掉血腥暴力的内容;香港2001年版《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改编,运用爱情历劫模式,剧情大框架是三角恋;内地2011年版《新西游记》的改编,运用人生历练模式,近似情感励志剧。与之相应,名著的文本整合改编,会根据一定的文本整合模式,对题材、情节、人物有所增减,对线索、时空、主题有所调整,其间还会进行“合理想象”“现代阐释”“创造性转换”。总体上看,其整合模式主要有三种。
(一)人物传记模式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大多是头绪复杂、人物众多、内容庞杂、片段连缀的。将某个重要人物确立为主人公并贯通原著中的某些人物、线索、情节,使之成为主人公发展史的传记电视剧,或者在某个历史人物的戏份里叠加另一历史人物的故事,使之成为典型性更强的传记电视剧,这是当前电视剧改编中常见的人物传记模式。一般需要确立主人公的形象意义、“CP组合”及其可贯穿性,并运用增删、转移的方法去处理原著的人物、线索,适当合并同类人物。这种被赋予比原初人物更多内涵与外延的新人物传记,可以被称为“大传”。
小说《水浒传》改编力度较大的最早电视剧版本,是1973年日本电视台(NTV)推出的《水浒传》(舛田利雄导演)。该剧以林冲为主角,让他成为梁山的精神领袖、贯穿线索。扈三娘开头就登场,高俅放走妖魔,吴用和公孙胜合并成一人,武松被删除。内地2013年版的《武松》,糅合《水浒传》和《金瓶梅》及某些野史传说,是内地《水浒传》中改编力度最大的版本,变成了“武松传”。它删减《水浒传》的开头,增加武松幼年情节,以及与孙二娘的情感关系(由同门情谊到男女爱情),增加《金瓶梅》中西门庆、应伯爵等人的情节,转移史进、鲁智深等人的情节,将武松变成诸多梁山故事的参与者、见证者、连缀者、行动者。它还融合江南民间流传的“武松单臂擒方腊”的故事。武松先与方腊结交,后放走方腊,不满于宋江的招安路线,使得该剧的英雄主题得到突出。
TVB《齐天大圣孙悟空》是小说《西游记》改编力度最大的版本,运用的是“孙悟空传”的改编模式。它整合了原著《西游记》和电影《大话西游》两个源本。在这里,原著中其他人物的戏份被大大压缩。除了西天取经的事业线,孙悟空的爱情“CP”体现于他跟紫兰仙子、白骨精的纠缠关系,贯穿始终。他与紫兰仙子的三生爱情故事,又借鉴小说《红楼梦》中的“木石前盟”。该剧主题之一是爱情劫难,因此剧中其他人物的感情戏份也得到丰富,如哪吒、红孩儿、唐三藏、猪八戒、沙僧、白龙马等,大多改编于其他多种源本。如哪吒的戏份部分改编自《封神演义》,绝情丹、被蛊惑等情节又改编自别的文本。
这类人物传记模式的改编剧很多,其中的优秀作品也很多。TVB《封神榜》是所有《封神榜》改编剧中改编力度最大的版本,变成了“哪吒传”“杨戬传”与“妲己传”的综合体。《大军师司马懿》承接《三国》的改编经验,也即将《三国演义》的蜀汉正统改为曹魏正统,更进一步,将《三国演义》变成了“司马懿传”。为此,该剧增加司马懿年轻时代的情节以及感情三角关系,将其他谋士的戏份进行了重叠组合。
人物传记剧的另一整合模式,是在某个历史人物的戏份里叠加另一历史人物的故事,使之更典型,更有代表性、可看性。如电视剧《苏东坡》将苏东坡的人生故事跟王阳明等人的人生故事进行糅合,使其兼具文治武功,成为“三立完人”,同时在文章、政治、军事上都有所作为,以此树立标杆人物形象。
改编剧为人物立传,还原、展现其心路历程,让人理解、产生共鸣,一般是具有一定的叙事目的的。比如以上作品中的“妲己传”“司马懿传”之类的主要目的是“翻案”,“苏东坡传”之类的主要目的是“歌颂”。这可以被理解为时代思潮、文化风尚作用下的“现代阐释”。
(二)情节综合模式
情节综合模式是故事情节层面的“杂烩”,即对相关题材、情节进行集中、综合,组成一部内部有机联系、风格较为统一的作品。这是比原初文本更丰富、更庞大的“大文本”。这种类型情节的集合模式并非情节的并置、拼贴,而是对相关题材、情节进行组装、融化与整合。这种改编模式是情节加长、叙事突破的不二法宝。
情节综合模式的主要方式是“合并同类项”。内地2007年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延续经典越剧文本的基础上,参考了浙江宁波鄞县(即今海曙区和鄞州区)关于梁山伯的传说,增加梁山伯出任县令、勤政爱民、有勇有谋的内容。改编者还合理想象历史背景,插入陶渊明、谢道韫、王凝之等东晋历史人物的情感故事,为梁祝的爱情诉求增加浓郁的魏晋风度。“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①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这些人的思想观念影响着梁祝。陶渊明的桃花源表达美好的社会理想,而剧中移植的十里桃花是梁祝爱情理想的诗意象征。
TVB江华版《西游记》在原著《西游记》的基础上,综合了电影《大话西游》的情节内容,还综合了《西游记》的续书《西游补》以及《东游记》等其他神话小说的情节内容。澳大利亚的《美猴王传奇》,根据中国名著《西游记》以及电影《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篇》进行综合化改编,形成了一个新的故事版本。这种兴起于1970年代的世界电视剧改编潮流,至今方兴未艾。如美国的系列剧《童话镇》,改编了德国《格林童话》及世界各国童话、神话、少儿文学,将所有的童话故事情节集中于主人公艾玛·斯旺在缅因州童话镇的冒险奇遇记之中。在多种故事文本的情节综合中实现文化累积与增殖,是最常见的改编目标之一。
情节借鉴也是一种常用的情节综合方式,俗称“融梗”。剧中被综合、融合的情节内容,往往并非同一题材、同一类型,甚至并非同一时代,而只是故事情节的模仿性借鉴与转换性化用。TVB《封神榜》中,哪吒与杨莲花的故事,明显融合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某些故事,一起读书、相爱,莲花变成蝴蝶追随哪吒;杨戬与黄颜的故事,明显借鉴了薛仁贵与柳金花的故事,佣工爱上小姐,投军立功,全家团聚;苏妲己的故事,比原著小说中已有的故事要多,应该是糅合了武则天、慈禧、杨玉环等“后宫”影视形象的某些典型情节。对于这种情节移植,改编者一般不会予以说明。一般受众可以识别出这些故事原型。
情节戏仿、恶搞也应属于情节综合模式,属于“超文本”的范畴。戏仿即戏谑式模仿,以达到对源本和仿本进行双重恶搞的目的。台湾省1987年版的电视剧《倩女幽魂》,就有恶搞小倩、小翠的故事,跟源本差异较大。此后的电视剧《武林外传》《爱情公寓》等,对某些影视桥段,现代飞碟、机械怪兽、网恋、比赛、电视广告等“噱头”进行大量戏仿、植入,表达戏谑、反讽的主题。这种颠覆性的情节综合模式一般适合青年观众的审美趣味,需要谨慎使用。此外,“社会话题文本”的楔入也属于戏仿式情节综合模式。《戏说乾隆》《武林外传》中,一些时事新闻、社会问题被巧妙植入剧情,借用古装戏进行呈现、评议,喜剧性较强,往往令观众会心一笑。
(三)互文并置模式
互文并置是指将两个在内容或形式上具有关联的文本并置于作品中,相互渗透、对照,达到互文见义的目的。改编剧的互文并置,是将某些再表演性、非情节性的其他文本强行插入故事文本,一般运用片头、片尾、片中插播、片中评述、戏中戏等形式。这种“有意味”的文本嵌套,能够发挥对照、反讽、交代、评价等作用。1998年版《水浒传》的片尾尝试插入戴敦邦的国画长卷《水浒人物一百零八图》,以增添英雄色彩和民族风格。1999年版《大明宫词》运用戏中戏的形式,植入皮影戏《采桑女》、角抵戏《东海黄公》、古琴《长相守》、昆仑奴面具游戏,且贯穿全剧,借以表达感情、塑造人物、推动剧情。
21世纪以后,改编剧的互文并置模式得到大量运用。《王贵与安娜》是中国当代婚恋剧,而其片头曲是朴树翻唱的苏联民歌《白桦林》,借以隐喻婚恋战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题材和人物都是虚构的,与李清照无关,而其片头曲是李清照的《如梦令》,借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爱情故事以表达一种婚恋理想。《精忠岳飞》在情节演进中,多次插播说书人讲述评书《岳飞传》的场景,与历史文本进行价值对照,甚至出现秦桧与说书人的对话,显示一种思想深度。《都挺好》在片头曲中插入苏州评弹曲调和江南世情漫画,在重要场景中插入苏州评弹中《三国演义》《白蛇传》等题材的传统曲目唱词,都具有对照、评价的叙事功能。因其故事发生地是苏州,这种文本插入还能营造地域文化氛围。
此外,有些改编剧在台词内容和风格上模仿了其他名著文本的经典语言范式,属于经典台词的“碰瓷”,因其商业性强、原创性弱,不值得提倡。《甄嬛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对古典小说《红楼梦》的一些话语进行借鉴、模仿,形成内地古装剧的“红楼体”“红楼风”。这种典雅的古代文白体成为古装剧最受追捧的台词风格,但原样照搬、雷同较多会造成观众的反感。
三、文本整合策略的价值评估
文本整合的改编策略给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带来一些生机:
(一)解决“剧本荒”的问题,提供文本生产的可能性
文化产业被视为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甚至被视为最有潜力的投资领域之一。大批量、日常化的电视剧需求量,已经使得中国几乎所有重要历史、已有的文学经典,都快要通过影像化的方式被讲述殆尽,有些还经历多次改编、翻拍,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文本整合改编策略。各种改编模式被探索出来,来势汹汹。剧本是“一剧之本”,而“剧本荒”“题材荒”一直在威胁着影视产业链的所有人。受各种“限剧令”“限娱令”等影视政策的影响,近年国产电视剧兴起一股新的翻拍风、改编风。此前的版本得到政策认可,成为经典,因而翻拍剧、改编剧、衍生剧具有政策与市场的双重保障性。据国家广电总局统计,2018年翻拍剧有23部,2019年翻拍剧有90部,但数据来源据一般观众反映,九成翻拍剧不如原版剧。新版改编剧如果沿用旧的套路,势必会与原版剧差别不大,从而失去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文本整合改编的策略,势必会成为新版改编剧的一种创作策略。
(二)丰富原著的人物与情节,推动文化整合与增殖
这可能是文本整合策略得以存在的最大价值,有利于中国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各种文学名著、历史名著以及新兴“大IP”的改编、翻拍,不断发掘亮点,增加新质,革新形态,可以促进文化产品及其文化价值的多元化、现代化。受时代语境的影响,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西游记》备受追捧,催生出了多个优质改编版本。小说《三国演义》与史书《三国志》在改编剧中的多次结合,不断更新了观众们的历史观与价值观。香港“西游记”题材的系列影视剧的改编,总是富于想象、创意,灵活运用多种资源文本,加入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各种片段,令国人大开眼界。改编剧《三国》《精忠岳飞》《成吉思汗》充分吸收了有关历史著作,高度还原了历史面目,从而超出了一般英雄传奇故事,超出了一般人的历史认知模式。在这里,面向大众的“影视史学”、面向历史的“官方史学”和面向知识的“精英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整合、统一,革新了一些观众的历史观、价值观。
(三)形成新的叙事模式,促进类型电视剧的发展
各种文本整合的改编模式,使得一些改编剧在人物、情节、主题、风格上逐渐趋同或不断翻新,促进了一些新的叙事模式和类型模式的形成。2002年,TVB《洛神》在《三国演义》《三国志》《洛神赋》有关文本的基础上,增加甄宓与“三曹”感情纠葛的故事内核,以及法国荒诞派戏剧《女仆》式的身份互换的结尾,促进了华语古装宅斗剧的形成。2017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化用《山海经》《封神榜》《桃花源记》的某些资源,还借鉴TVB《齐天大圣孙悟空》中的故事支架,如三生三世、天庭规矩、翼君封印、同归于尽、历劫重生等,促成了内地玄幻神话剧的高度成熟。《甄嬛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对古典名著《红楼梦》《金瓶梅》的某些情节的借鉴,促进了内地古装宫斗剧、宅斗剧的成熟。新的类型电视剧总是在不断兼容、杂交、重组、裂变中产生的。
当然,文本整合的改编策略有时会让电视剧误入歧途:
(一)东拼西凑,涉嫌抄袭
改编剧的文本整合策略,包含借鉴、戏仿的方式。借鉴、戏仿名义上是艺术传承,可以自由运用,可一旦涉及版权,尤其涉及今人的版权,就必须慎重对待。如电视剧《金粉世家》《大宅门》《甄嬛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在改编各自的原著小说的基础上,都对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某些人物、关系、情节、语言有所借鉴,片头可以不标明出处,属于“合理借鉴”,因为《红楼梦》属于“公共版权”作品。但是,对今人作品进行多方拿来,东拼西凑,明里暗里借鉴模仿,容易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涉嫌侵权。如《甄嬛传》《武媚娘传奇》《如懿传》《延禧攻略》等电视剧,被一些受众指责涉嫌“借鉴”多个其他作品。诉诸法律而得到确认的,是《宫锁连城》对琼瑶小说《梅花烙》构成侵权,片头并未提示改编字样,也未征得原作者的同意、给予原作者相应的版权费。琼瑶宣称前者在故事主线、角色、人物关系等层面,都与后者如出一辙。这涉及大陆影视剧界的版权意识的问题,还有原创意识的问题。琼瑶对大陆电视剧原创意识的不足提出强烈批评,这让大陆业内人士深感汗颜。
(二)胡编乱造,枝蔓丛生
部分改编剧追求全方位、全息化的改编模式,集合所有相关人物与故事,造成主线模糊,喧宾夺主。陈晓版《神雕侠侣》在原著小说基础上,结合《射雕英雄传》乃至香港版《九阴真经》《南帝北丐》《中神通王重阳》等“射雕”系列衍生剧的内容,让剧中的所有老少侠士都忙于三角恋爱。原著中有的与没有的恋情,被讲述的与被呈现的恋情,都被充分挖掘出来。林朝英与王重阳的,李莫愁与陆展元、何沅君的,小龙女与杨过、甄志丙(即尹志平)的,杨过与陆无双、程英、郭芙、公孙绿萼、郭襄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独孤求败的,诸多恋情在剧中被一一展现。过于复杂的线头将该剧弄得主线丧失、面目全非,而杨过的英雄成长主题被置换为爱情成长主题。在这种“玫瑰江湖”中,所有大侠都输给了一个“情”字。由此可见,文本综合的改编策略需要确立叙事主线、主要关系、主导行动、主题思想,离开了这个创作规律,肆意攫取素材和文本,只会出现“经脉错乱”“消化不良”的症状。
(三)创新过度,亵渎原著
有的改编剧追求新奇、震撼与逆袭的效果,故意恶搞原著的基本设定,因改编尺度较大,有亵渎原著之嫌,陷入了接受困境。TVB《齐天大圣孙悟空》中,“叛逆儿童”红孩儿变成“思春少年”,暗恋紫兰仙子,仿佛是当代初中校园剧里虐心的姐弟恋,令人感到不适。霍建华版《笑傲江湖》中,“自宫怪侠”东方不败变成“不老女神”,与后辈令狐冲演绎了一场虐心的旷世恋情,最后沉入冰湖,眨眼微笑,都让很多观众感到费解。这里融合了一些影视剧里的换心情节的“梗”,但做法难免有些粗暴。韩国根据《西游记》改编的现代版《花游记》,也让中国观众难以接受。这是创新,还是恶搞?如果恶搞是一种改编,那么改编、重写的最低尺度是什么?按照这种乱改、恶搞的模式,小说《红楼梦》可以被改编成贾宝玉与刘姥姥的虐恋故事,或者改编成林黛玉与焦大的虐恋故事,而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文本狂欢,无疑是对原著的严重亵渎,使得改编剧陷入娱乐至死、文化自戕的怪圈。
结语
改编剧的文本整合改编策略是时代文化思潮演变的结果,也是电视剧产业自身发展的产物。当同类题材达到饱和状态而故事原创力不足时,文本综合、文化增殖的创作策略就势在必行了。它的形成具有故事加长、叙事突破、文本还原等艺术动机,并存在着人物传记、情节综合、互文并置等三种主要改编模式。它在促进当前中国类型电视剧的成熟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存在着东拼西凑、胡编乱造、创新过度等问题和弊端,不利于中国电视剧创作的健康发展。
文本整合策略是当前电视剧界无法阻挡的艺术手段,愈演愈烈。可以说,只要有原著文本的改编、翻拍,就会有各种文本整合策略的“幽灵”的入侵。从艺术创作与创新的角度讲,作为“IP”的文学名著本身具有不同的阐释视角,改编剧难免会做加减法运算,融合其他“IP”,多方综合借鉴,产生一些整合性、综合性的新文本。与此同时,改编剧的文本整合策略必须尊重艺术创作与创新的一般规律与规则,建立并健全科学合理的艺术创作机制与方法,有利于中国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
2010年代以来,各种文学名著进入第三次改编期,在资本、观念与政策的多重影响下,新一拨的改编剧乱象丛生,弊多利少。国家广电总局曾经发文,要求“古装历史剧不能捏造戏说”,甚至要求不得“歪曲、恶搞、丑化经典文艺作品”,并对“改编热”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改编尺度的把握问题依然是最受关注的,既要传达新鲜价值,又要具有接受基础,还要体现底线意识、版权意识。那些浑水摸鱼、胡编乱造的改编行为,迟早会付出惨痛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