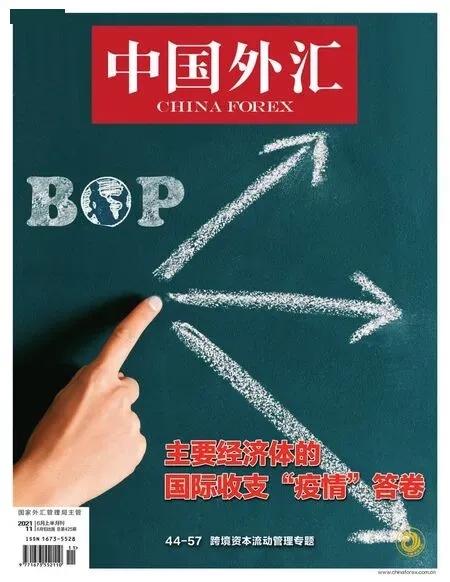引导内保外贷合规发展
文/翟相如 许侃 解光明 编辑/章蔓菁
当前,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推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企业跨境融资意愿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内保外贷业务风险值得关注:其在便利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容易被用作跨境资金异常流动渠道,加剧跨境资金流动的顺周期性。有鉴于此,进一步完善内保外贷管理,不仅有助于在微观上引导企业内保外贷业务的良性发展,也有助于防范跨境资本的流动风险。
内保外贷下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近年来,内保外贷成为境内主体开展跨境资金融通的重要渠道。实践中,内保外贷业务结构复杂多样,部分市场主体通过业务结构的叠加和嵌套来达到规避监管的目的,加大了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一是小额境外投资叠加大额内保外贷。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发布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地方企业作为投资主体所开展的、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下的非敏感类项目,在投资主体注册地的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备案,3亿美元以上的则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实践中,部分企业往往采取“股权+债权”的替代策略,即压低境外投资规模,剩余资金以内保外贷方式在境外融入。通过这种“小规模股权投资+大规模内保外贷支持”的架构,规避境外投资备案要求和境外放款额度管理。该类业务结构的潜在风险在于,一些财务状况较差的境外企业一旦通过此类方式借入大量资金,后续往往需要通过境内主体担保履约偿还融资,加大了跨境资金流出风险。
二是内保外贷叠加返程投资。实践中,为规避外债额度、资格方面的限制,部分境内企业先作为担保人,通过内保外贷方式让境外主体获得融资,其后再将融资资金以外商直接投资方式汇入境内企业(即担保人),境内企业再将该笔资金通过关联借款借予境内其他关联企业使用。这类业务结构的潜在风险在于,境外借款人往往没有开展实质经营,而是被用作融资通道,后续担保履约风险较大。同时,这类业务结构往往因嵌套境外上市业务,资金来源多由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境外债务人往往需承担远高于一般跨境融资成本的借款成本,从而会进一步加剧境外债务人的偿付压力和跨境资金潜在流出规模。
三是跨国企业集团通过内保外贷实现“短债长用”。跨国企业集团具有业务种类多、组织架构关联性高、跨市场跨领域经营等特点。实践中,部分跨国集团下属企业通过内保外贷在境外融资并相互拆借。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一方面,多方拆借会造成资金划转路径复杂,难以“穿透”监测资金的最终用途;另一方面,同一集团内企业的相互拆借也增加了集团自身的财务杠杆和风险。此外,一些企业境外项目投资规模大、周期长,为规避长期限融资带来的成本,利用内保外贷举借一年期以内的融资实现短债长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境外投资项目出现亏损或某关联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很容易造成风险的跨境传染。
内保外贷异化之因
尽管内保外贷业务形式复杂多样,但在被用作跨境资金异常流动渠道时,其共性特点都是因境外借款人主观或客观上无力偿还贷款,需要由境内担保人履约偿还内保外贷项下的融资而引发跨境资金流出。笔者结合实际工作体会,将实践中内保外贷异化为跨境资金异常流动渠道的成因,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部分企业利用不同业务的管理口径差异打政策“擦边球”。内保外贷现行管理重点聚焦于审核主体资格、基础业务的合规性以及还款来源的充足性等方面。其中,主体资格、基础业务合规性的审核可通过相关登记文件等客观事实来判定,但对还款来源充足性的判定大多依据境外资金用途、项目收益测算等,有赖于债务人营业收入、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流动资产等财务数据。而这些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往往难以判定,加之各行业财务指标所适用的标准并不统一,客观上会加大还款来源充足性判定的主观性。而一些企业正是利用这一缺陷,通过内保外贷规避境外投资、境外放款和外债相关管理政策,加大了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二是集团企业内部循环担保模式不利于对资金用途的穿透式监管。近年来,内保外贷业务日趋复杂化、多元化,单一集团内部关联企业互相循环担保开展内保外贷、交叉偿还境外融资款的现象逐渐增多,部分企业通过这一方式模糊资金脉络,加大了对资金用途实施穿透式监管的难度,埋下了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和传染隐患。此外,实践中有时会出现身处不同地区的集团与境内子公司联合为境外子公司跨地区申请担保业务的情形,加上关联企业之间股权关联关系较为复杂,进一步加大了审核签约环节主体资格、审查内保外贷历史开展情况以及在担保履约环节办理对外债权登记的难度;同时,由于内保外贷业务涉及多个监管部门,企业跨区域办理内保外贷业务也加大了监管协调成本。
三是对企业作为担保人的内保外贷业务缺乏后续追踪手段。对于以银行作为担保人的内保外贷业务,其多为境内银行与海外分/支行或合作行联动办理,因此境内银行在开展贷后管理、追踪款项境外资金用途上具有显著优势。而对于担保人为非银行金融机构或企业的,外汇管理部门在追踪资金境外用途上有一定难度。根据现行规定,担保人为非银行金融机构或企业的,应在签订担保合同后15个工作日内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内保外贷签约登记手续,外汇局按照真实、合规原则对非银行机构担保人的登记申请进行程序性审核并办理登记手续。实践中,由于企业在外汇局办理内保外贷签约登记的时间一般早于境外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放款,因此外汇管理部门在签约登记环节难以通过银行流水等凭证确定资金路径,把控资金最终用途的合规性;后续如直接要求企业补充资金划拨凭证,则缺少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只有在境外债权人或被担保人积极配合的情况下才能跟踪境外资金的最终去向。
引导内保外贷规范发展
内保外贷业务的推出,有效改善了我国企业境外投融资环境,丰富了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为支持真实、合规和合法的内保外贷业务,同时切实防范内保外贷被部分企业异化为跨境资金异常流动渠道,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内保外贷管理。
一是明确内保外贷对外或有债权属性,实现与境外放款协同监管。内保外贷业务的复杂性在于其兼具对外债务和对外债权属性,即担保人在履约前形成对境外债权人的或有负债,履约后则形成对境外被担保人的债权;但从最终效果来看,内保外贷、境外放款、境外投资异曲同工,均是使境外主体通过债权融资或股权融资获得资金支持。针对部分企业利用内保外贷方式规避境外投资、境外放款相关管理要求的行为,建议将内保外贷定义为或有债权,与境外放款实现协同监管。
二是引入数量型管理工具,适时将内保外贷纳入对外债权统筹管理范围。在明确内保外贷对外或有债权属性的基础上,可引入企业对外债权余额上限、企业对外债权风险加权余额等数量型约束指标,实现对企业对外债权的统筹管理。其具体按以下公式计算:
企业对外债权余额上限=企业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暂定为0.5)
企业对外债权风险加权余额=本外币境外放款余额×类别风险转换因子(暂定为1)+本外币内保外贷余额×类别风险转换因子(暂定为0.5)
在指标口径上,建议企业内保外贷余额的管理口径包括其作为担保人所提供的担保余额,以及其作为反担保人通过金融机构提供的内保外贷余额。集团企业在计算风险加权余额时应使用母公司(集团本部)的所有者权益,避免集团公司多次计算额度。
之所以设定上述公式,主要有两方面考量:其一,通过将境外放款和内保外贷的系数分别设定为1和0.5,体现直接债权和或有债权的区别管理,即风险更小的或有债权可适当增加“杠杆”。其二,引导企业通过正规渠道开展跨境业务,压缩政策替代空间。对于以担保履约实现资金出境为目的所开展的内保外贷业务,虽然其初始系数低、上限额度高,但履约后所形成的境外放款金额可能超过境外放款额度,以此引导企业内保外贷业务回归本源,减少“构造”交易的动机。
三是完善系统对内保外贷数据信息的采集和分析功能,为穿透式监管提供大数据支持。目前,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中的“银行自身-内保外贷查询”提供辖内法人银行的全口径数据查询以及总部在外省的辖内分支行数据查询。鉴于银行跨地区营销较为普遍,为掌握企业内保外贷业务办理“全貌”,笔者建议,可在内保外贷签约登记环节将数据查询权限扩大至企业在辖外银行所开展的内保外贷业务。同时,在事后核查环节,笔者认为可采用“事前备案+事后信息报送”的机制,引导担保人在系统中自主上传与该笔担保项下境外贷款资金的用途、流向相关的银行流水信息,以便外汇管理部门能更好地掌握资金境外流向情况,落实“穿透式”监管。
四是加大政策培训力度,加强系统内交流和对银行展业的指导。鉴于实践中内保外贷交易结构千变万化,建议加强对特殊业务案例,特别是交易结构复杂、潜在风险高的业务案例的收集,通过政策培训、典型案例汇编等形式进行系统内交流,以便各地外汇管理部门能准确理解政策内涵,督促金融机构做好展业。
——基于《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13条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