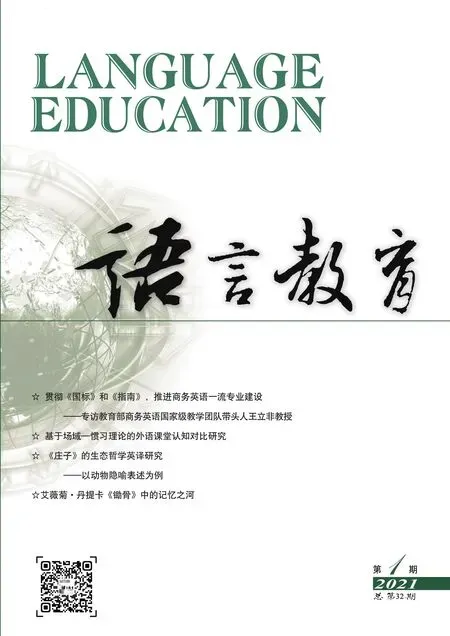艾薇菊·丹提卡《锄骨》中的记忆之河
舒进艳
(1.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2.喀什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喀什)
1.引言
河流在兰斯顿·休斯的诗中是繁衍生命与孕育文明的摇篮;在托妮·莫里森的小说中是黑人挣脱束缚与搏取自由的战场。流动的河水带给人们的是生存与希望、安全与自由,但黑人与河流的故事并未止于此。当代海地裔美国女作家艾薇菊·丹提卡传承了休斯与莫里森书写黑人与河流的历史传统,在她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历史题材小说《锄骨》(1998)中,河流既是开放的地理空间,又是兼具文化和历史底蕴的记忆空间。海地甘蔗工与大屠杀河的故事不仅续写着生存与迁徙的话题,而且还观照着海地的当下与未来。该河位于加勒比地区海地与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是两国间一道天然的地理屏障。小说中,丹提卡借助大屠杀河这道物理边界具备的记忆功能来铺陈小说的故事背景、塑造人物形象、进而打开海地传统文化、往昔历史的记忆之门,从而揭橥历史事实的真相。本文突破以往河流书写常规,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将地方与记忆理论结合来论证大屠杀河作为移民往返迁徙的地方,携有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功能,它在帮助海地人实现自我、建构民族自信的同时,也在引领海地人积极反思、展望未来。
大屠杀河既是海地甘蔗工人往返于故乡与异乡的必经要道,也是海地甘蔗工谋求生存的重要通途,蕴示着海地劳工阶层生生不息,寻求自由与实现自我的伟大抱负,正如华裔学者段义孚所言:“水只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候才有生命”(段义孚,2006:4)。河流作为一个特殊的地方,代表的是记忆的储存和希望的延续,人文地理学家克雷斯韦尔也曾指出:地方与记忆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Cresswell,2015: 85)。《锄骨》中大屠杀河贯穿故事始末,是唤起海地人对个人过往、民族文化及历史记忆的地理空间,这种对地方的深刻体验被段义孚称为“感受价值”(段义孚,2006)。海地砍蔗工不畏艰险、逾越大屠杀河来到多米尼加种植园,或成为季节性砍蔗工人,或在多米尼加边境内安定下来,河流始终伴随着甘蔗工们的生存与迁徙,成为维系情感和生命的纽带。在梦想与希冀的召唤下,海地劳工却忽视了跨越大屠杀河潜存的暗流与危险。1937年西芹大砍杀给大屠杀河烙上了无法抹去的记忆印迹,由此,大屠杀河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故乡与异乡的空间隔离而且还有海地人与多米尼加人的心理隔阂;大屠杀河既成为海地人的精神寄托,又成为羁绊他们的枷锁。那么,作者是如何将海地人对大屠杀河的情感体验书写进河流的记忆功能里呢?
根据段义孚对地方的阐释:“地方是一个独特的实体,有历史和意义”(Tuan,1974: 213)。《锄骨》中的大屠杀河恰具备以上特点,丹提卡在创作小说前多次来到大屠杀河畔:“我一到那儿,就能感受到历史,我会看到它就好像在屏幕上延展开来”(Johnson,2003: 80)。小说始终以大屠杀河为轴线,河带给人们的是希望与失望、安全与危险并存的复杂迁徙体验。该河作为海地甘蔗工们前往异乡与返回故乡的空间通道,在往返流动的过程中,海地甘蔗工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传承在无意识中流淌。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大屠杀河既是一个开放的地理空间,又因其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凝结而成一个特殊的记忆空间,那么,这一空间的记忆功能是如何凸显的呢?论文将围绕此展开论述,试图证明:这条“记忆之河”并未始终将海地人封锁于历史的桎梏之下,而是将其置于未来的曙光之中,河流蕴含的海地文化的包容与多元性特质亦将成为海地拓步前行、面向世界的不竭动力。
2. 融汇文化记忆的地理空间
克雷斯韦尔指出:“一个地方的重要性意味着,记忆不会被抛弃在变幻莫测的心理过程中,而是作为公共记忆被铭刻在景观中”(Cresswell,2015: 85)。大屠杀河作为一道自然景观,见证着过去与未来;作为记忆的载体,承载着海地作为美洲第二个独立国家的深厚文化底蕴。有学者认为是非洲文化构成了海地人性格的基石,但是它被深埋在潜意识之中(雷古勒斯,2010)。不过,奈特却明确表达海地将非洲遗产视为新国家的骄傲、同质化的象征(Knight,1978)。丹提卡从小随父母移民到美国,她对故土海地的思念和文化的记忆常映射在她的著作中,无论是在精神还是物质层面她对无数移民或散居在外的海地人都给予格外的关注。丹提卡自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息·望·忆》(1994)后,海地就位于美国托管期间(1995-2010),面对强势文化来袭,丹提卡在她的小说中通过一些特别的意象如神话传说、民俗、海地方言等来唤起对海地几近失传的古老传统文化的记忆,丹提卡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如她在小说《锄骨》中塑造的人物罗曼神父,在他对海地山谷教众的布道中,他经常提醒每个人共同的联系:语言、食物、历史、狂欢节、歌曲、故事和祈祷,他的信条是记忆。于是,丹提卡借助海地人生命中的河流之母——大屠杀河来开启对海地的文化记忆,重现往昔图景,一些特别的形式或符号如传统技艺、仪式、海地方言等都在丹提卡的笔下娓娓道来。
小说的故事是以美国统治海地近20年,海地传统文化日渐式微、面临美国与多米尼加特鲁西略独裁的霸权文化侵蚀为背景,丹提卡借助文学的力量向海地人发出保存民族传统、传承文化记忆来对抗强势文化的呐喊。书中的复杂记忆网络交织于大屠杀河,大屠杀河成为叙事背景及聚焦点。德国哲学家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包括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时间必不可少且反复使用的文本、图画、仪式等内容,其核心是所有成员分享的有关政治身份的传统,相关的人群借助它确定和确立自我形象,基于它,该集体的成员们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属性和与众不同之处”(转引自金寿福,2017: 37)。因此,丹提卡怀着对海地文化的古朴情愫,在《锄骨》中通过大屠杀河隐喻海地甘蔗工代表的精湛缝制技艺、丰富的药草知识、庄重的沐浴仪式来回应对海地悠久的传统文化记忆,将个人与民族的经历融合在一起,这些记忆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而且是对现实的有力回击。
阿玛贝乐对父母的深刻记忆始于大屠杀河畔,虽然此段记忆较为凌乱,却常呈现出美好的图景,母亲缝制的洋娃娃、父亲做的灯笼均成为阿玛贝乐儿时的陪伴。阿玛贝乐对妈妈给自己做洋娃娃的场景记忆犹新“一串红丝带缝在皮肤上,两块玉米芯做腿,一粒干芒果籽做身体框架。肉用羽毛,眼睛用木炭,头发用可可棕色绣花线”(Danticat,1998:55)。丹提卡虽未用过多笔墨来展现阿玛贝乐母亲独特的手工技艺,但看得出她的别具匠心,不仅为后来阿玛贝乐拿起缝纫篮做铺垫,而且以缝纫篮作为一个隐喻来暗示源于非洲的传统缝纫文化,“缝制衣物可以帮助人们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对于家庭关系也是如此”(Tavormina,1986:221)。丹提卡不仅视缝制技艺传承是对家庭亲密关系的维护,而且再现了源于非洲“百纳被”工序中的缝合、拼接手法。此外,小说多处对主人公阿玛贝乐的缝纫场景进行描述,并借阿玛贝乐之口表达到:“我视缝纫为财富”(Danticat,1998:266)。主人公阿玛贝乐从母亲那里习得的缝制技艺既是对海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留存也体现了家族作为一个世代延续而又相对封闭的基本生活单位,总是积淀着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记忆(诺拉,2015)。
作为家族记忆的一部分,阿玛贝乐用父母传授的生产知识帮助女主伴巴伦西亚顺利诞下双胞胎,由此,她从一名卑微的女仆变为一名助产师,全得益于生前作为海地与多米尼加两国边界的助产师兼药草医师的父母,他们凭借药草治愈了河边界许多的甘蔗工人和多米尼加人。西芹是海地民间常用的一种药草,它既可以内服又可以外用。作为食物,“咀嚼时无味而苦涩,但嘴里留下甜甜的余味,叶子和茎有不同的味道,我们把它当作食物和茶尽情享受”(Danticat,1998:60),作为一种常见的药草,它“可被用来治病、疗伤、助产,但它同时也可以使人愚笨、中毒”(Wcirsolcy,2006:168)。民间药草师们根据药草的不同疗效来对症治病。此外,海地人用它来沐浴,以“清洁身体内在和外表的痛楚与伤痕,把过去一年的灰尘作为一个新的黎明,用它和煮过的橘子叶来给新出生的婴儿洗发,给逝者清洗遗骸”(Danticat,1998:60)。在海地民间文化中,人们相信可以通过草药这种特殊力量改变一些理论上无法改变的状况。甘蔗工刚果的儿子鸠不幸遇难后,他矗立在河水中央,用一把新鲜的西芹慢慢地搓洗着宽阔的肩膀,他扭动着身子,“让西芹涮洗着他脊背上的一道道伤疤”(Danticat,1998:60)。西芹与河水的糅合不仅帮助刚果与儿子通灵、对话,而且借此以抚慰他内心的极度悲恸与困惑。儿子的意外身亡令刚果怆痛不已,借着水与西芹的“沐浴”,他在不停地拷问着自己的内心,或自责于未充当好儿子的保护伞,或无力于寻求事情的真相。他慢慢地重复着一个动作,试以西芹作为化悲痛为力量的武器,弥合身体与心灵的创伤,同时也表明他作为一名精神领袖的存在力、承受力和个人感召力在河水与西芹的治愈下即将复原。小说中多处出现的西芹,即是对海地民间文化的再现和承续。阿斯曼曾提道:“文化记忆始终拥有专职承载者负责其传承”(阿斯曼, 2015: 48),丹提卡塑造的主人公阿玛贝乐与甘蔗工刚果均承担着这样的责任与使命,他们不仅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文化传统,而且凝聚着他们周边人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
在悼念鸠的场景中,甘蔗工们挤进河水中央,没有隆重的告别仪式,只是在黎明前“对鸠的集体守灵——静默的告别”(Danticat,1998:61)。水在海地人传统文化中代表着与神和神灵联系在一起。在阿玛贝乐对集体沐浴仪式的回忆中,河流是剥离于世俗空间的神圣空间。海地甘蔗工把这一特别的空间形塑成了他们在精神上能够净化自我、与群体再结合、对逝者表示敬意、不忘记初心的地方。刚果在水中用西芹不断搓洗自己的身体,他相信儿子的灵魂将与他合为一体。水对海地人来说是神圣而重要的,意味着再生。在佐拉·尼尔·赫斯顿的民间故事集《告诉我的马》中,水亦被视作是“浸润身体的圣物”(Wcirsolcy,2006:174)。河中的瀑布是海地甘蔗工们劳作完一天沐浴的场所,在这里他们可以祛除身体的污垢和疲乏,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泽与乐趣。在海地的民俗学和民族志研究中,关于瀑布作为精神朝圣和疗愈场所的提法比比皆是。此外,河水还是甘蔗工们庆祝甘蔗丰收的场所,“这是新甘蔗收获的第一天,水里非常拥挤,满是男人和女人”(Danticat,1998:57)。丹提卡试以这种方式证实海地人身份不能只拘囿在甘蔗园或多米尼加雇主的私宅,特别是当阿玛贝乐把失去双亲与爱人的地方同故土海地缀联了起来,正体现了“地方是一个充满人类经验和意义的场所,同时让人类对自身和地方产生认同” (李燕,2015:11)。海地甘蔗工们将自己的过往与喜怒哀乐都投射在水里,对大屠杀河这个地方的深深依附之情尽显读者眼前。集体沐浴成为海地甘蔗工生命中重要的仪式之一,不论是喜庆丰收、接纳新生,还是疗伤治痛、悼念亡者,沐浴都能带给人身体和精神上的洗礼。在那种场合下人们可以记忆起他们在家乡的一切:包括他们使用的语言、重要事件、历史、狂欢节、歌声、民间故事和祈祷等,恰证明了记忆是“表现空间和地方意涵的一个积极要素,在明晰社会意义和认同方面起到重要作用”(Withers,2005:29)。大屠杀河正是这样一个能帮助群体恢复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增强集体感、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地方。然而,多年后阿玛贝乐重返旧地,曾经的瀑布再也不是她记忆中的神圣空间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现代化气息的世俗空间。丹提卡通过阿玛贝乐对瀑布的重新审视,也传达了她本人对海地文化的忧虑与反思,固步自封、流连过往显然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鸠的车祸身亡其实早就暗示着现代性对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种植园的猛烈冲撞。
阿玛贝乐以大屠杀河作为对传统文化记忆与反观现实的重要场域,表明河流是“承载过去记忆和未来想象”的一个地方(李燕, 2015:11)。丹提卡视大屠杀河为海地人文化记忆的标志性场所,不仅助海地人重拾了个体自我,而且建构了民族与文化自信。小说以躺在河水中的阿玛贝乐收尾,在她看来,河水是记忆、愈合与重生的象征,传达了作者本人积极思考,对未来秉持希望的正能量态度,也是河水所表征的海地文化的精神要旨。克雷斯韦尔说:“地方既简单(这也是其吸引力的一部分),也是复杂的”(Cresswell,2015:85),大屠杀河作为聚合海地甘蔗工集体经历的重要场地,它在帮助丹提卡传递古朴情愫与精神理念的同时,又融入了作者对海地文化的忧思;它在助力海地人通过文化记忆找到自我的同时,又在时刻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过去。由此,丹提卡借河流所显现的文化记忆不仅是对历史存在意义的揭露与阐发,而且是她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考证与挖掘。
3.铭刻历史的记忆空间
海地悠久的历史对其人多地少产量低的国情并无裨益,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流毒使得许多海地人四散飘零,海地甘蔗工们以成功跨越大屠杀河,来到多米尼加种植园为荣。然而随着海地甘蔗工移民的不断涌入,多米尼加政府却公然视其为一种威胁,该国的白色空间在特鲁西略独裁的阴影笼罩下,对海地这一外来有色民族布满了恐怖,特鲁西略政府暗中策划血统大清洗的砍杀阴谋使得大屠杀河成了海地与多米尼加之间的一个“血色空间”。丹提卡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解答到“1937年大砍杀是作为海地人历史的一部分,但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写它本身就是一种回忆”(Mallay,1998: 43)。然而,在没有具体的纪念标志和仪式的情况下,记忆成为凝聚海地人集体意识的绝佳方式。丹提卡通过对时代背景、社会状况进行深度考量,充分搜集与大屠杀河相关的记忆与证词来揭示海地人这段被选择性遗忘的历史,并将其移植于自己的小说《锄骨》中。
哈布瓦赫提出:“每段集体记忆都是在一个空间框架内展开的,记忆社区的成员不仅共享地理信息、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而且还共享物质以外的其他集体空间:法律、经济和宗教”(Halbwachs,1992: 140)。因此,丹提卡在《锄骨》中以大屠杀河为背景,塑造了身为女仆兼幸存者的主人公阿玛贝乐成为记忆的代理人。阿玛贝乐是丹提卡在写作时多次前往海地搜集的一个关于大砍杀遇难者的真实故事而建构的人物,阿玛贝乐的幸存者身份亦足以让她作为叙述者并承担起记忆大砍杀的重任。丹提卡通过阿玛贝乐的经历表明了记忆是建立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并改变了她对周围世界和所处阶层的认知态度。作为女仆,她的佣人身份和地位显然无法与女主巴伦西亚比拟,但她与甘蔗工塞巴斯蒂安的关系为她开辟了一个新的社交空间,也促使她与甘蔗园工人达成了一种身份共识。虽然小说始于阿玛贝乐从梦境中记忆有关大屠杀河的一切,不免让人感到虚幻,但丹提卡恰是借助虚实结合的创作手法将1937年大砍杀这一史料真实化、具象化;虽然1937年大砍杀成为历史,但历史离不开记忆,记忆可以成为帮助人们从创伤中得到释放和救赎的工具(彭刚,2014: 4)。
历史事实的再现与主人公阿玛贝乐的回忆紧密相关,丹提卡对大砍杀的记忆是始于主人公阿玛贝乐从别处听说的传闻:“我认为是谣言,总是有谣言,关于战争的谣言,关于土地争端的谣言......这和像我、伊夫思、塞巴斯蒂安和刚果这样在种植园劳作的人无关”(Danticat,1998:138)。在阿马贝乐看来,“劳作”意味着她和甘蔗工们关于土地的自然权利,她并未意识到在大砍杀中,个人经历会与阶级、种族、国籍和她的个人生活与身份有关。当医生加瓦用克里奥尔语告诫阿玛贝乐离开多米尼加时,阿玛贝乐还在暗忖:我想得到更多的警告。我需要确切地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一切都很奇怪(Danticat,1998: 139)。与此同时,她的爱人塞巴斯蒂安也很质疑加瓦的用意。丹提卡以悬念的方式逐渐将读者置于大砍杀历史的记忆背景中。在逃亡途中,阿玛贝乐一行遭遇到多米尼加士兵的严厉审讯与盘查,年轻的硬汉们在他们面前挥舞着西芹(用西芹的读音来判断是不是海地人),还未等到他们张口回答,伊夫思和阿玛贝乐即被推倒在地,他们每个人的下巴都被强行撬开,士兵们抓起一把把西芹硬生生塞进他们的嘴里,“我的眼里充满泪水,我快速地咀嚼和吞咽着,但却不及他们往我嘴里塞西芹的速度”(Danticat,1998:191)。字里行间渗透的西芹恐怖是灾难性悲剧的前兆,极具讽刺的是西芹由海地人可以服用与治病的药草变成了定夺生死的标尺,对大部分说克里奥尔语的海地人而言成了一种致命的毒药,因为他们无法发出西芹(parsley)中的这个“r”音,只能发出perejil中的“j”音。不仅如此,阿玛贝乐还遭到士兵们猛烈地拳打脚踢,“疼痛就像刀子或冰锥上的利刃袭来,我蜷缩成一团,尖叫着,感觉快要死了”(Danticat,1998: 191)。丹提卡将士兵们的野蛮与残忍行径充分暴露于读者眼前,阿玛贝乐身边的逃亡者伊夫思、提本、奥迪特纷纷遭到毒打、滥砍,提本死了,伊夫思从河里托回奄奄一息的奥迪特,临终前她还用克里奥尔语叨咕着“pesi”(西芹的发音)。砍杀结束的几日里,伊夫思、牧师、医生以及其他人沿着河岸打捞遇难者尸体并进行掩埋,丹提卡通过阿玛贝乐身边人物的不幸遭遇还原了大砍杀的真实景象与那段血迹斑斑的历史。阿玛贝乐与塞巴斯蒂安及其妹妹因逃遁而失散,也因此,她对大屠杀河这一地方的难以舍离之情经久不散,为日后的寻亲之路埋下了伏笔,这不仅拉近了幸存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而且也让读者对历史真相的记忆更为深刻。时隔许久阿玛贝乐的脑际还常浮现大砍杀的情景:每当在大街上看到畸形人时——不管是残缺的鼻子还是瘸腿——我就想他们是不是也历经过大砍杀?1937年大砍杀让阿玛贝乐无法克制自己内心的畏惧与恐慌,大砍杀给她造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创伤,并使她固着在这种记忆里或者身处于幻觉中,以至于日后她的脑海中不断重现这样的场景,无法自拔。在她的这段记忆中,伊夫思、罗曼神父、医生加瓦、塞巴斯蒂安等都参与了历史,罗曼神父的疯癫就是被这段历史改变的真实写照。
当伊夫思告诉阿玛贝乐“现有的国家官员,治安官,他们在倾听并记录那些在砍杀中的幸存者的故事”,然而特鲁西略却试图抹黑这一历史事实,但“他同意给那些受影响的人一些钱”(Danticat,1998: 229)。两国政府对待大砍杀事件的不同态度让阿玛贝乐既欣喜又失望,幸存者或受害人家属本以为他们的申诉能够得到海地政府的怜悯和正义声讨,但“他把你的名字写在书上,他说他会把你的故事交给文森特总统,这样你就能拿到你的钱了。他让你说话,让你哭,他问你是否有文件证明所有这些人都死了”(Danticat,1998: 232)。种种托辞却彰显了海地政府的懦弱无能,海地幸存者最终明白历史的固化逻辑:如果一件事被写下来,记录在案,载于一本书中,那才是真的,作为书面记录的一部分,他们的证词才将成为真实。虽然个人与集体记忆的表达与言说对海地人的历史至关重要,但当时处于二战前期,美军与特鲁西略暗通款曲,遂导致特鲁西略主体欲望与极权膨胀,并“使自己成为他者遵从的标准”(胡振明 徐婵娟,2020:85)。在他统治期间,多米尼加与海地均弥漫着恐怖的硝烟。为此,多米尼加裔作家阿尔瓦雷斯在《蝴蝶飞舞时》(1994)中,选择发生在大屠杀河另一端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西略专制作为故事背景,对这段怵目惊心的历史也有记录:“佩罗索一家的男人都被杀光了。马丁内斯·雷那和他的妻子在自家的床上被谋杀,还有成千上万的海地人在边界被屠杀了,他们说,这些海地人的血使得那条河的水至今还是红的”(阿尔瓦雷斯,2014:61)。此外,丹提卡在短篇小说集《克里克?克拉克!》的《1937》中也追述了海地人于砍杀前仓惶逃离并不幸遇难的情景给幸存者留下的创伤性记忆,大屠杀河成了令人望而生畏、肃然起敬的地方,著名地理学家戴维·洛文塔尔(David Lowenthal)曾言“记忆不仅保存过去,而且根据当前的需要调整重新适用,我们没有确切地记住过去,而是使过去变得清晰易懂”(Lowenthal,1975: 27)。丹提卡用河水的意象来映衬许多像阿玛贝乐这样的海地人的具身感受,大屠杀河触发了人们的强烈情感与历史记忆。
谈及1937年大砍杀事件时,有研究者表示“没有任何事情能证实发生了什么,没有纪念牌,没有道歉,生活在继续,那时我意识到记忆是多么脆弱。如果我们让它消失在空气中,它就会消失”(Shea,1999: 21)。而阿尔瓦雷斯《蝴蝶飞舞时》中纪念米拉尔瓦姐妹的博物馆就落座在她们的家庭空间,这就迫使海地人不得不思考如何将1937年大砍杀事件融入他们的国家和集体记忆中,以记惦那段选择性失忆的历史。在阿尔瓦雷斯和美国作家米歇尔·瓦克、艺术家谢雷扎德·加西亚、剧作家内汉德拉·洛伊塞亚等的组织与策划下,纪念1937大砍杀的活动如“烛光边界”“独白之夜”和“西芹记忆”等陆续举行,2012年在大屠杀河畔举行的用烛光照亮边界的75周年纪念活动得到了境内外多米尼加人和海地人的拥趸。“烛光边界”不仅促进了多米尼加和海地两国人民在边界内外的情感联络,同时也烛照了两国之间的转折性关系:海地与多米尼加不能囿于历史而应精诚合作,正如洛文塔尔所述:“通过对过去的认识,我们学会了重塑自己。通过对自己经验的认识,我们也重新思考过去,取代一直被改变和失去的东西”(Lowenthal,1975:24)。“独白之夜”是在美国第一次以公开方式纪念1937年大砍杀,该活动初衷是征集来自全国各地关于大砍杀的独白;“西芹记忆”则是通过讲述故事和分享记忆的形式来治愈创伤。这些活动的举办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凭吊与释然,而是透过历史面对当下、思索未来。
4.结语
大屠杀河不仅仅是个开放的地理空间,它所承载的文化和历史底蕴还使其成为一个独特的记忆空间。这一记忆空间装盛着不同时期的文化与历史信息,把记录和体现人们印迹的活动植入历史文本。在丹提卡的精心安排下,大屠杀河是人们迁徙体验与情感依附的地方,经由这里,海地的民族文化得以赓续传承,海地的民族历史得以镌刻与铭记,海地的民族创伤得以弥合与治愈。丹提卡在《锄骨》中以史实为依据,虽书写的是海地人过往的一段经历,但观照的却是海地的当下与未来。海地与多米尼加的关系亦正如丹提卡在《锄骨》中塑造的异卵双胎,两国虽隔河相望,但唇齿相依、休戚与共。《锄骨》开放式的结局也意蕴深远,卧于河水中的主人公不是沉湎过去、逃避现实,而是对未来满怀期待,一如小说标题的名字不仅涵盖了作者对劳工精神的肯定与嘉赞,而且丹提卡坚信历史并不能阻碍海地人前往多米尼加的步伐,边界迁徙会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海地文化的包容与多元性促使海地在接纳多米尼加这个肤色迥异的胞妹、与其携手构建加勒比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也在积极思索与探寻民族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