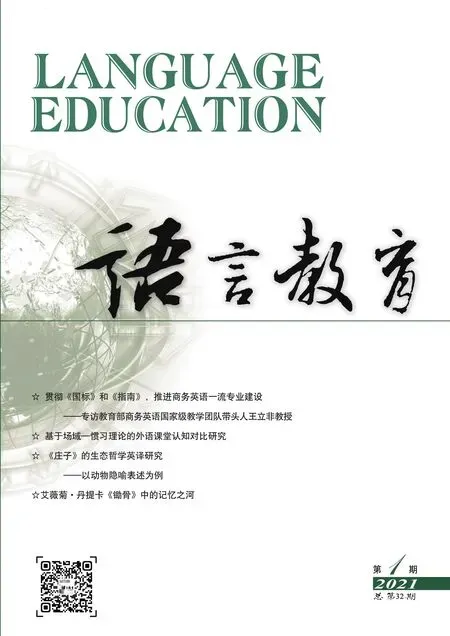信息时代“肉体神胎”的命运
——小说《果壳》中的后人类困境
陈 莉 吕万英
(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
1.引言
伊恩·麦克尤恩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在英国当代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麦克尤恩共有17部小说,均在文学领域产生不小的影响。他获奖频频,1976年因处女座《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获毛姆奖,1998年《阿姆斯特丹》获得布克奖,更凭借代表作《赎罪》一举拿下史密斯文学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奖和圣地亚哥欧洲小说奖。之后的三年内,他分别获得莎士比亚奖、耶路撒冷文学奖,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这些成就奠定了他在英国当代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美国《华盛顿邮报》资深书评人说:“现如今用英文写小说,没有人比得上麦克尤恩”(Yardley,2007)。其写作风格具有阶段性,早期作品关注人类内心的阴暗面并借此表现社会中的暴力、乱伦、性等给人们带来的苦痛。麦克尤恩的作品具有极大的语言魅力和引人深思的人生哲理,不仅涉及儿童成长主题、女性主义,还蕴含复杂的人物心理、社会伦理。他的作品曾经一度被冠名为“震荡文学”(literature of shock),麦克尤恩也被评论界戏称为“伊恩·恐怖”(王密卿 韩杰,2014)。麦克尤恩的后期作品面向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空间,其作品《时间的孩子》是他写作风格的分水岭。
《果壳》是伊恩·麦克尤恩的第十七部小说,于2016年11月出版,通过一个独特的全知视角——胎儿一步步引出一场谋杀案的前因后果。这部作品共20个章节,描述了“我”在母亲特蒂子宫中第三个月到出生整个时期,借助“我”描绘了母亲特蒂,叔父克劳德以及父亲约翰三个角色之间复杂的关系,并讲述了母亲和叔父谋杀父亲,最终因为“我”的出生耽误逃走时间而被捕的故事。《果壳》无疑是麦克尤恩的另一杰作,自出版以来各评论家纷纷就其发表自己的见解。《卫报》评论家凯特·克兰奇认为,《果壳》书名虽然听起来不够令人神往,“说话的胎儿不够令人信服,或者至少是受到限制的叙述者,而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更新使缝合线绷得过紧”(Clanchy,2016)。《金融时报》泰勒评论道,《果壳》的“主要噱头在于,小说叙事者来自类似葛特露形象的人物的子宫里,她那即将临产的喋喋不休的儿子……他能感受到全球暖化、堕落的启蒙价值和加剧竞争的民族主义,叙述者听见了这些”(Tayler,2016)。在《果壳》中,说话的胎儿既是整个小说出彩的地方,又是争议最大的地方,不管评论家如何定位这一肉体神胎,他们都无法否认胎儿“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后人类。“我”蜷缩于母亲子宫,被困于家庭利益之争、阴谋事件,又无法摆脱世界整体格局下人的价值观和伦理扭曲的命运。他所面临的后人类困境正是麦克尤恩想要让我们所有人去反思的东西。
2.后人类定义及研究
什么是后人类?后人类主义代表人Haraway(1991:149-81)将后人类定义为“赛博格”,一个“自动化控制机体,机器和有机体的杂糅体,现实和虚构的混合体”。后人类先驱代表人Katherine Hayles (1999)探究了赛博格中的虚拟身体并就一系列科幻作品探究了后人类主体。Neil Badmington(2004:109)在他的作品Alien Chic:Posthumanism and the Other Within中指出“后人类可以是与当代西方文化无关的任何事物”。Brent Waters(2006)简要介绍了从变形人到后人类的转变,并指出人类改变天生和潜在的能力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借助变形来突破界限,其中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延长寿命。Toffoletti(2007:10-11)在Cyborgs and Barbie Dolls:Feminism,Popular Culture and the Posthuman Body中对后人类研究做了一系列总结,“许多作家清楚地阐明了其对于后人类未来的观点,质问了科技时代背景下的身体状态和自我。大部分人批判地探索了后人类存在的可能性,同时一些人表明对于向后人类转变的焦虑”。Pepperell(2003:170-171)在The Posthuman Condition中对后人类下了清楚的定义,“后人类是人脑之外的意识,后人类将会是那些拥有史无前例的生理、智力和心理能力的人类,能够自我编码和自定义、潜在不朽的,没有限制的个体”。罗西·布拉伊多蒂(2015:07)在其作品《后人类》一书中指出,“后人类作为一个概念,可以用来探讨积极地联系当下现实的方法,以经验为基础解释其若干特征”。凯瑟琳·海勒(2017:07)认为“后人类的主体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一个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构建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在小说《精神漫游者》中,叙述者把后人类的身体描述为“数据做成的躯体”。凯瑟琳·海勒提到,“变成后人类不仅仅意味着给人的身体安装假体设备,它更意味着要将人类想象成信息处理机器”(2017:331)。
目前国内学者也将视线投向后人类,孙绍谊(2011)就一系列科幻电影探究了当代西方后人类主义思潮,并指出电影中涌现的后人类景观有助于后人类思潮的普及;信慧敏(2012)探究了文学作品《千万别丢下我》中的后人类,从后人类主义语境分析人类与作为后人类的克隆人相互转化和关照的关系,探讨了人类与后人类的伦理沦丧和困境。
不难发现,随着基因工程、机器人学、假体技术、电脑技术、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后人类”(posthuman)一词频繁出现在人们面前,它被看作是人类的未来存在形式,无论是拥有人类思想的机器人,还是植入信息技术的人类,拥有超能力的变形人,甚至文学作品中能够表达信息的动物、植物等都可以被称为“后人类”。当人类与机器人、动物、克隆人的界限随着科技变得越来越模糊,身体已经不再是成为人的必要条件,人类也不该以自我为中心,陷入可怕的控制论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要突破人类界限,就要走向后人类未来,而后人类的重心则是信息。
3.《果壳》中的“我”——后人类胎儿
如果说科幻小说中《千万别丢下我》中的克隆人是后人类,那么在小说《果壳》中的那个凝结所有故事情节,并担当着所有信息的叙述的“我”,一个未出世的胎儿,无疑是另一个后人类。格林曾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已经成为赛博格:医学移植进我们的身体,机械工具唾手可得,来自全世界的商品遍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Gilbert, 2008:141)。在《果壳》中,无所不知的胎儿“我”孕育于信息时代,“我将继承一个现代身份并着落在地球的一个享有特权的角落——丰衣足食的,没有瘟疫的西欧”(McEwan, 2016:03)。在小说中,现代科技的商品无处不在,如播客、耳塞、黑比诺葡萄酒、基因、波音飞机、电冰箱、止痛片、冷冻剂、安眠药、埃菲尔铁塔、DNA等等。“我”的后人类特征贯穿整个文本。首先“我”是信息的独立实体,整个故事是从“我”的视角出发的,是“我”一步步揭开母亲、叔叔和父亲的关系的。再者“我”是异源成分的集合,是科技和人类的结合,来自全世界的商品充斥着“我”的生活,“我”和母亲一起听广播,一起看播客,听父亲谈论诗歌,“我”有非凡预知能力,在“我”还不知道蓝色和绿色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我”的将来是不幸的,“我从一开始便知晓,当我打开我那被金布包裹的意识天赋时,我知道我会在一个非常错误的时间里诞生在一个错误的地方”(McEwan, 2016:03)。“我”能区分不同的酒,“但是,啊,一杯使人高兴的又让人脸颊泛红的黑比诺葡萄酒,又或是一杯醋栗酿造的白索维农酒,可以让我在秘密海洋里旋转和翻跟头”(McEwan, 2016:07)。“我”十分了解诗歌,“我父亲知道的诗歌大多都很长,就像那些银行职员的著名创作《萨姆·马吉的火葬》和《荒原》一样”(McEwan, 2016:13);“大多数现代诗让我感到十分寒冷。有太多关于自己,对待他人的时候就像玻璃一样的冰冷,那么短的诗行却表现了那么多的埋怨。但是约翰·济慈和维尔浮斯莱德·欧文的诗歌却像兄弟的拥抱一样的温暖”(McEwan, 2016:14)。“我”甚至对当今社会的环境了如指掌,“说的话飘浮在空中,就像北京的雾霾一样”(McEwan, 2016:72)。“我”可以脱离身体束缚,“我的化身耸了耸肩,靠近他的外套,以他的方式低语,那光荣的杀戮没有一丝现代的优雅”(McEwan, 2016:52-53)。不得不说,这样一个能透视未来,随意谈论葡萄酒,对经典诗歌作家脱口而出,又了解世界环境气候和政治局势的胎儿,正是后人类的一员。
4.《果壳》中“我”的后人类困境
近年来,后人类个体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电影《千万别丢下我》中的机器人后人类和童话书《爱丽丝漫游记》中会说话的动物后人类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后人类困境。后人类不知如何面对和人类的情感,忽略身体和信息的重要联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往往处于奉献者的地位。在《果壳》中,麦克尤恩刻画了“我”的三重困境:身体之困、爱恨之困以及命运之困。借此来诠释了被科技信息包裹着伦敦城市里人们感情的疏远、伦理的背离、价值观的背离,母亲特蒂和叔叔克劳德分别代表了物欲横流的社会背景下人们迷失在美丽外表和金钱财产的欲望之中。他们忽略文学和感情忠诚对人类的重要性,更忘却了道徳迷失和谋害生命只会自食恶果并殃及后代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接下来,本文分别就文本一一阐释“我”的后人类困境。
4.1 后人类的身体与信息——“我”的身体之困
凯瑟琳·海勒在讨论人工生命的叙事时,表明了身体对于后人类的重要性,“关于人工生命的叙事表明,如果我们承认观察者必须成为画面的一部分,身体就永远不可能只由信息构成”(凯瑟琳·海勒,2017:331)。在小说《果壳》中,胎儿“我”身体处于三层困境之中:作为未出生的胎儿困于母亲特蒂子宫之内,作为独立的生命困于全球环境之中,作为后人类意识困于身体之中。
“我”局限于母亲特蒂子宫那一狭小的空间,无论母亲做什么,“我”都要身不由己做同样的事情。在小说第一章的开头,作者就描述了胎儿的身体困境,“现在,完全反了过来,没有一寸空间属于我自己,我的膝盖挤着肚皮,我的头和思想都被占据。我别无他选,我的耳朵日日夜夜都贴着血色的墙。我听着谈话,并记下来,我感到困扰”(McEwan, 2016:01)。继而,胎儿用“内在困境”来形容自己待在母亲子宫内的状态,“总体上已经清晰了,同我内在困境相比,或者应该是不值一提的”(McEwan, 2016:03)。“我卡在这里,除了生长发育外什么也不做,我吸收一切事物,就连这里为数不少的琐事也是如此”(McEwan, 2016:05)。“我”的处境是十分痛苦的,“我”的生命要依赖母亲体内由食物转化而来的营养提供,“我”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她喝酒,“我”也会醉;她和自己丈夫的兄弟通奸,“我”也不得不一起承受;她谋杀丈夫,“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走向死亡。
小说全文多处夹叙了后人类状况,以昭示后人类“我”所处的时代背景。在第一章节,“我”清楚地发表了自己对于所处时代的意见,“有太多去庆祝的东西。我将继承现代条件(卫生、假日、麻醉学、读书台灯、冬天里的橘子),并住在地球上优越的一角——富饶的、没有瘟疫的西欧”(McEwan, 2016:07)。正是“我”出生于这里,经济富裕、科技发达的西欧,“我”才会成为后人类,才会在母亲和父亲之间左右为难。社会政治的整体不和谐,“欧洲,就她所言,处于危机之中,就像自恋的民族主义一样易怒和弱小,啜着同样有品位的茶。价值的迷茫、反犹太主义细菌的发展、移民人口的沮丧、愤怒和厌恶。其他地方,任何地方,新奇的财富的不平等,统治民族分离的富有”(McEwan, 2016:25)。科技时代背景下,政治将世界分割成了国家,个体的平等因财富和权力而崩塌,价值观曲解、人们对金钱欲望的膨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如世界政治一般表面和平,背后却暗流涌动。喜爱文学、从一而终的父亲因财富失利而显得懦弱,无处容身,而行为粗鄙、谈吐恶俗的叔叔却因拥有金钱虏获了母亲的心。科技时代背景下,人们对金钱欲望的膨胀疏远了夫妻之间、兄弟之间的亲情,背叛、谋杀成了微不足道的事情,父亲的死亡无可笔描,而“我”作为生命的开端,一个胎儿的人生价值观是慢慢树立的。在整个事件中,“我”徘徊于法制和暴力之间——“我”既尝试过幻想用轮胎击打叔叔的头颅来阻止他谋害父亲,也无数次想通过报警、写信、叫救护车等方式拯救父亲。然而“我”无法改变世界,无法改变父亲的命运,“我”只有屈身社会整体环境之中。
后人类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探究身体与信息的关系。后人类的身体在不断抽象,信息的地位在上升,但这不意味着后人类可以完全脱离身体,也不代表身体是可以被丢弃不顾的。恰恰相反,后人类仍然需要身体来作为信息的载体,信息的传达不能脱离身体的存在。在小说之中,虽然“我”的思想可以脱离身体去监视叔叔和母亲、去亲近父亲。如“我的化身耸了耸肩,靠近他的外套,以他的方式低语,那光荣的杀戮没有一丝现代的优雅”(McEwan, 2016:52-53)。然而这种“脱离”十分局限,后人类仍然无法真正脱离身体,一旦身体失去活力,意识失去载体,后人类将很快死去。小说中多次提及“化身”离开身体去监视叔叔,不管“化身”每次去哪里,它最终都会回归身体这个唯一的目的地。而且,一旦身体失去活力,“我”也将死去。“我仍然爱她,我想让她知道,但如果她往后滑落,我就会死”(McEwan, 2016:74)。正是这样的相对的自由束缚了“我”,将“我”囚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也正是这种未出生前的种种牢狱般的日子才使“我”整日担忧将来是否会被关入监狱,再次失去享有幸福和自由的权利,而结局是不言而喻的,“我”也很清楚这一点。
4.2 后人类伦理与情感——“我”的爱憎之困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对人的本质和价值的尊崇随着时代的变迁渐渐被人文主义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取代,这一观念是后人类主义强烈反对的。毫不夸张地说,西方后人类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防止人类再次落入人文主义的控制论。不论是后人类机器,后人类动物,还是后人类文学,都离不开后人类的情感。如果后人类仅仅把机器人看成工具,那么后人类就会很容易丢失掉自己的人性,变得像石黑一雄《千万别丢下我》中的人类一样,在利用完克隆人后将他们残忍的杀戮、抛弃。同样,如果后人类对于自然没有一个崇敬、热爱之情,那么他们就会忘记生命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企图征服自然,而最终只会自食恶果。
在小说《果壳》之中,作为后人类的“我”处于比没有情感更为可怕的境地,“我”一方面爱憎分明,一方面又处于左右为难、无可奈何的境地。其中胎儿与母亲的联系最为紧密,“我”对母亲的情感最深,也最摇摆不定,“我”在爱恨之间左右为难。处于这样一场乱伦之中的“我”逃脱不了对母爱的肯定和否定,“我”不知如何面对这份情感,“我”对母亲的情感处于困境之中,正如文中第十六章所写“‘我’命中注定的母亲,‘我’注定深爱和厌恶的母亲”(McEwan, 2016:157)。“我”是没有安全感的,极度忧虑的。
在小说的第一、二、四、五、六、八、十一、十七、二十这九个章节中,共有12处写到“我”对母亲的告白——“我”爱她。在整个过程中,“我”逐渐长大,逐渐有了自己的意识,了解了“我”的处境,父母感情的破裂,母亲和叔叔的阴谋,这一系列的事情构成了“我”情感波动的前因后果。“我”的情感过程经过了从爱恋——质疑——肯定——厌恶——憎恨——再次肯定这一系列的变化。她的一切“我”都想了解,她的内在,她的外表,就如文中那频繁出现的、直言不讳的爱的宣言:“而且‘我’爱她——‘我’怎能不爱呢?‘我’尚未谋面的母亲,那个‘我’仅仅了解她身体里面的人。这可不够!‘我’渴望她的外在”(McEwan, 2016:3)。极度的不安感使“我”格外珍惜母亲的爱,不论她做错了什么,哪怕是出轨,“我”都爱她。“我”因她做的平常小事而格外欢喜,宽容她所有常人不能忍之事。母亲晒晒太阳就是爱,上楼时握紧栏杆的举动是爱,这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仍然爱她”(McEwan, 2016:74)。她按时吃饭于“我”都是疼爱和关心。看似孩童般幼稚的想法,实则并非自恋,而是知足和珍惜。这样的知足和珍惜,现代人类是极少能做到。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使得人们惜时如金,就像谚语说的“浪费时间就是谋财害命”。所以人们着急赶时间,交通摩擦、工作摩擦、利益摩擦,人们变得暴躁,人们的满足感被金钱压制得局限在一个很小空间里。而后人类“我”是不一样的,“我”珍惜母亲的爱,不会觉得那是理所当然。当“我”因为恼怒而辱骂她时,“我”也会立马收回前言,“等等,我爱她啊,她是我的神,‘我’需要她。‘我’收回刚才的话!”(McEwan, 2016:15),这是许多成年人类都做不到的事情,父母于其而言负有养育的责任,是理所应当。
但后人类有强烈的伦理道德观,这使得“我”憎恨母亲,爱憎分明的天性使得“我”无法释怀母亲的背叛,尤其是谋杀。当母亲听着收音机晒太阳的时候,“我”认为她是为了让我摄入维生素D而欣喜,而后又因母亲的入迷报以怀疑,让“‘我’无法确定她是否爱‘我’”(McEwan, 2016:32)。在傍晚“我”听到了生物学家的争论,这种过度侧重客观事实忽略情感的信息让不安的“我”更加害怕。“怀孕的母亲必须和她子宫的占有者做斗争。自然,一个母亲,注定要为孕育‘我’将来的兄弟姐妹所需要的资源而斗争”(McEwan, 2016:32-33)。在人类世界,即便母亲孕育孩子这样一件伟大而富有爱意的事情都变得冰冷,“斗争”无处不在,甚至始于子宫。面对父亲死亡的消息,母亲感到伤心但却装得好像不是她亲手所为,这样的冷血是后人类不解和厌恶的,在那时候后人类的恨意涌现出来,“‘我’恨她和她的懊悔”(McEwan, 2016:115)。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难以摆脱母亲和胎儿之间天然的亲密和情感依恋,但又无法屈服于这样的不正常的关系,这促使“我”没有安全感,不断质疑“我”对母亲特蒂的情感,对母亲的反复告白恰恰证明了“我”安全感的缺失。这种情感上的困境使得“我”产生了一系列暴力的想法。“我”仇恨叔叔,是他偷走了亲兄弟的妻子,欺骗自己侄子的父亲,下流地冒犯了自己嫂嫂的儿子。“我”不止一次有杀死叔叔的想法,“当‘我’出生后并最终可以独自一人的时候,会有那么一刻‘我’想拿起厨房的刀。但是拿刀的人也可能是我的叔叔,那个给我四分之一基因组的人”(McEwan, 2016:32)。第二次,“我”想要杀死叔叔来拯救父亲,“放一个武器在他手中,一个轮胎扳手,一根冻羊腿,让他站在叔叔的椅子后面,那个能看到冷冻剂并被煽动的地方。问一问自己,他能——我能——干这个,砍掉那个骨头上长着毛发的圆丘,让他那灰色的脑浆溅出来撒在桌子的肮脏上”(McEwan, 2016:52)。对于深爱的母亲,“我”同样有残暴的报复想法,“‘我’将用这黏糊糊的绳子捆住她,在我生日那天用那眩晕的,新生儿的凝视将她强征入伍,一个孤寂的海鸥痛哭着将渔叉戳进她的心脏”(McEwan, 2016:43)。原本积极、拥有包容心又深爱母亲的那个后人类随着这种情感困惑的波动也失去理性,企图使用暴力手段——杀死叔叔、母亲甚至自杀——来解决矛盾。透过这样的情节,麦克尤恩预示了人类暴力的源头,不论本质多么好的人,如果一味接受负面消极的环境,失去情感寄托,那么将不可避免会产生难以预料的悲剧。
4.3 后人类的未来——“我”的命运之困
小说《果壳》的每一章都穿插着暗示“我”命运的字眼,“我”置身于亲人的矛盾之间,变得怀疑母亲的爱,胡思乱想又无可奈何,“我”被困在命运的枷锁之中,母亲的子宫是一堵墙,隔绝了“我”与父亲,“我”被无故卷入家庭纷争,只能接受父亲被谋杀,母亲坐牢的悲惨命运。在小说的第一章中,就对“我”的降生做了一个铺垫,“从一开始我便知道,当我将包裹我意识的礼物的金色织物解开之时,我便知晓我会在一个不当的时间降生在一个错误的地点”(McEwan, 2016:3)。母亲特蒂是那么的美丽动人,尽管有孕,但于父亲而言依旧是完美的。在小说结尾,作者借胎儿之口描绘了特蒂的美丽,“父亲说得没错,那是一张可爱的脸。她的头发比‘我’想的更黑,眼睛是灰绿色的,双颊由于刚刚的使力仍然泛红着,鼻子的确很小巧。‘我’觉得在这张脸上看到了整个世界”(McEwan, 2016:197)。父亲喜欢诗歌,并常常为母亲写诗读诗,这样一件浪漫的事情,母亲却只是厌烦,以自己困了为理由打发父亲离开,看似简单的描写实则印证父母之间感情的破裂和不可调和的现状,为母亲下决心毒害父亲埋下伏笔。正如小说中所写,“无论什么时候,当她和我听诗的时候,我感受到她那减缓的心跳,视网膜里透露着乏味,她对这个宽大慷慨男人毫无希望的辩解,以不流行的十四行诗的形式,熟视无睹”(McEwan, 2016:13)。小说的第四章结尾提到了这场谋杀的方式——“下毒”,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胎儿说的第一个词,一个让人瑟瑟发抖的词语,从而解释了后面章节之中“我”为什么时常怀疑母亲不爱自己,幻想自己未来悲惨生活,想尽办法阻止父亲被杀,这种种看似啰唆没有逻辑的描绘,恰好突显了“我”的不安与惶恐。
此外,“墙”一词共出现22次,其中有4次指“死亡之墙”,1次指“生命之墙”,7次指“子宫墙”,8次指“房间墙”,2次指“监狱墙”。这些形形色色的墙分隔了“我”与外界,暗示了父亲死亡和母亲坐牢的必然性。小说以果壳为名,与墙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是父母爱情的果实,所以“我”必然会破壳而出,就像父亲被谋杀的真相必定水落石出一样,“我”这个生命的降临意味着阴谋的破解。“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诠释“我”的困境,“我”的苦痛,揭示“我”情感和生理的成熟过程。“我”不仅要亲眼见证母亲和自己的叔叔乱伦这一让人愤怒的背叛,还不得不参与之中,“没有人知道你父亲的情敌的性器官从你鼻子上缓缓滑过是什么样的”(McEwan,2016:20),而“我”却要有如此经历,然而母亲的子宫壁像一堵墙限制了“我”的自由,好像牢笼网住了鸟儿。“我闭上双眼,咬紧牙关,准备冲击子宫壁。这场动荡足以折断波音飞机的双翼”(McEwan, 2016:20)。此后书中又紧接着出现了“死亡之墙”这一词,此处的墙指的是“我”的恐惧,“我”害怕在母亲和叔叔性交过于激烈而会伤及“我”的头骨,更害怕自己将来会像叔叔那样思考和说话,假如事情演变至此,那么对于“我”而言就同死亡没有区别了。作为后人类的“我”是正义的,以积极的方式去反抗命运,“‘我’用脚踝而不是脚趾急剧又形状完整地击打这墙壁。‘我’感觉这像是一次孤独的,为了听到涉及自己事情的击打”(McEwan, 2016:92)。在十一章节,文中描绘到“在街道上人类排泄物的气味就如同房屋的墙壁一般牢固”(McEwan, 2016:104),在此处墙壁给人的是一种消极负面的形象,让人感到冰冷和难以推倒,就好似命运般难以逆转,离开了母亲的子宫,面对破裂家庭的“我”又将处于冰冷的牢笼。
5.结语
伊恩·麦克尤恩用他不拘一格的行文方式全方位的书写了信息时代背景下后人类胎儿的身体困境、伦理和情感困境以及命运困境。这些困境穿插于故事情节之间,环环相扣,用假象的故事反映了真实的社会问题。其中,叔叔克劳徳代表了金钱,母亲代表美丽,父亲约翰代表淳朴,“我”代表了后人类的未来。《果壳》揭示当代社会中人类自身的罪恶对后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我”是无辜的,却最为不幸。后人类视角为分析小说《果壳》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并启迪我们深思人类将来命运。我们处于科技信息的时代,势必要走向后人类未来,金钱欲望的膨胀和外表的追逐、伦理的歪曲等社会问题只有得以改善,后人类才能避免面临《果壳》中的胎儿困境。但如果淳朴的本质被抹杀,人类不能及时悬崖勒马,那么其自身和后代只能陷入不幸,难以改变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