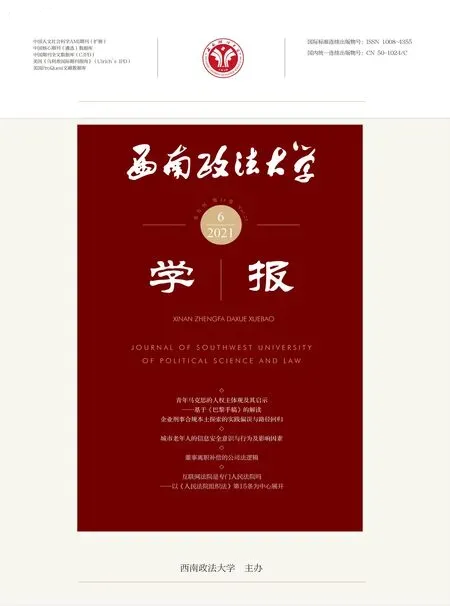董事离职补偿的公司法逻辑
曹兴权,王婷婷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重庆 401120)
一、问题的提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适用劳动法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值得关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3条对此有所回应。该条第1款确定了公司无理由解聘董事的权利:“董事任期届满前被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有效决议解除职务,其主张解除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第2款涉及董事被公司无理由解除职务后的补偿问题:“董事职务被解除后,因补偿与公司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综合考虑解除的原因、剩余任期、董事薪酬等因素,确定是否补偿以及补偿的合理数额。”司法解释主动提及离职补偿的做法或有“吹皱一池春水”之效果。毕竟,董事会处于公司治理之“震中”,是公司治理的关键一环,与其相关的任何一项治理改革都有可能引发一些连锁反应。(1)参见薛前强:《论股东资助和补偿董事选举的法律规制——兼议我国防范董事选任利益输送的前置性变革》,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9期,第105页。对比《公司法》并未对董事离职补偿问题作明文规定的立法立场以及此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多采劳动法逻辑的做法,司法解释的适用可能存在一些疑问:第一,司法解释为何表达出对董事离职补偿的限制立场?第二,如何理解适用司法解释对董事离职补偿的限制规则?诸如,公司章程或者合同未涉及补偿而董事主张补偿之时,能否以未约定等于不补偿为由直接否定其主张?解除原因、董事薪酬等因素又如何影响是否补偿以及补偿数额之评判?
抛开司法解释,首要问题在于,董事离职补偿与劳动者离职补偿的关系。如果说对普通劳动者的离职补偿是保护性的,那么针对董事的离职补偿理应是限制性的。因此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是,为何要限制董事离职补偿以及如何限制董事离职补偿?关于为何限制董事离职补偿,需要思考的问题有:《民法典》总则部分所提出的一系列法律原则对解决董事离职补偿问题是否有所启示?对离职董事赋予同普通劳动者一样的经济补偿权利,甚至高于一般离职经济补偿的金额是否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公序良俗原则又是否允许对因违反忠实义务被罢免职务的董事给予离职补偿?尽管我国《公司法》条文中没有明文规定董事离职补偿的内容,但基于法律整体性和关联性的观念,能否从《公司法》的其他条文以及其他法律中解读出对董事离职补偿应当采取限制性立场之意?比如,《公司法》第147条关于公司董事负有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规定是否意味着,董事离职补偿必然区别于劳动者补偿,对离职董事进行补偿是否会背离董事信义义务?关于如何限制董事离职补偿亦有两个维度需要考量。从程序正义维度看,公司补偿决定之作出,是基于章程还是股东(大)会决议?能否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作出补偿决定?从实质正义维度看,除《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3条提到的可参考因素外,还有哪些需要考量的因素?
可以认为,对于公司董事离职补偿的司法难题,司法解释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路径,很多基础性问题以及操作问题还有待探讨。本文拟在尊重现行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所体现的限制董事离职补偿的价值理念之基础上,从程序限制和实质限制的双重维度考察我国董事离职补偿审查机制。
二、董事离职补偿限制之缘由
(一)董事身份的特殊性
董事是公司主要管理者,也是公司的员工、劳动者。身份的模糊性是造成董事离职补偿纠纷法律适用困难的根源。为了规避此种困境,一些国家明文禁止董事在任职期间成为公司雇员,以防止因董事二元身份产生的矛盾。比如,英国、(2)参见[荷]阿德里安·德瑞斯丹等:《欧洲公司法》,费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页。法国、(3)《法国商法典》第L225-44条。比利时(4)参见[荷]阿德里安·德瑞斯丹等:《欧洲公司法》,费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页。公司法明确指出董事本身不是雇员、不得成为公司雇员。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立法与商业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董事身份的模糊性。实践中,董事兼任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之外其他主要职位的情况较为普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下简称《破产法》)中,董事被当成一种特殊的员工和劳动者。该法第113条第3款规定:“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那么,在离职补偿场合下,究竟应当如何定位董事身份?
虽然董事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曾引发公司法学界的争论,但委托关系说已然成通说。(5)参见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依法保护股东权益 服务保障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相关负责人就《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答记者问”(以下简称《答记者问》),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55282.html.2021年2月2日访问。《答记者问》中指出,我国现行公司法对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确实没有非常明确的陈述,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践都逐渐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视阈下公司与董事之间成立委托关系。不过,在董事离职补偿纠纷的裁判中,公司法学界的立场并未完全被司法实践所接受,法院适用《劳动合同法》或者《劳动法》审理董事离职补偿案件较为普遍。例如,在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严泽祺与广东伦教汽车玻璃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严泽祺既具备公司董事身份,同时也是公司的员工,其合法权益受劳动法相关规定的保护,故而支持了严泽祺的离职经济补偿金的请求。(6)详见(2006)佛中法民四终字第174号判决书。无独有偶,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徐怡琳与上海迈伊兹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7)详见(2015)徐民五(民)初字第456号判决书。以及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莫树浩、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8)详见(2018)粤01民终23124号判决书。中均有相类似的表述。
问题是,董事与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劳动关系?如果成立,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委任关系与劳动关系是否可以并存?或换言之,二者是否为排斥关系?
首先,关于董事与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劳动关系,即董事是否是劳动者?我国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5年颁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劳动关系的建立有具体的解释,其中第1条规定了建立劳动关系应同时具备几个条件:第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均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主体资格;第二,劳动者须遵循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接受其管理并享有报酬;第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属于用人单位的一部分业务。据此分析,可得出以下简单结论:其一,从《公司法》第146条关于董事主体资格的规定看,董事的主体资格甚至比普通劳动者的主体资格更严格,而公司通常都享有用人单位资格,因此二者均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其二,董事虽为公司的管理者,但并非意味着董事不必接受任何的管理,公司章程等公司内部自治文件对董事同样具有约束力,而董事履行董事职责享有相应的报酬自是不必多说;其三,董事负责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其所提供的劳动当然属于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因此,当董事实际向公司履行董事职责之日起,就应当认定董事与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即董事具备劳动者身份。
其次,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委任关系是否可以与劳动关系同时存在?二者是否互相排斥?最高人民法院在“孙起祥与吉林麦达斯轻合金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再审案”(下简称孙起祥案)中指出:“公司与董事之间的委任关系并不排斥劳动合同关系的存在,即公司与董事之间在符合特定条件时还可以同时构成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关系。”(9)详见(2020)最高法民再50号判决书。换言之,公司与董事之间既存在委任关系亦存在劳动关系,且二者之间并非水火不容的相斥关系,而可以同时存在。按照这一说法,相较于普通劳动者,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特殊性可见端倪——不同于普通劳动者纯粹的劳动关系,董事与公司之间还同时并存有委任关系。
问题在于,当董事职务被解除时,是否意味着公司与董事之间的委任关系与劳动关系一并解除?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孙起祥案中的意见是:如果公司解除了董事的职务且没有为其安排其他工作,此时该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就随着委任关系的解除而一并被解除。也就是说,存在仅解除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委任关系而保留劳动关系的可能,这一特殊性在董事同时兼任公司其他职务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委任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基本逻辑是有所区别的,相关法律展开的基本逻辑也完全不同。在劳动关系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并非处于对等地位,劳动法的基本政策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施以倾斜性保护;而在委任关系下,委托方与受委托方均有缔结和解除契约的自由,双方处于平等地位,法律并未给予任何一方特殊的保护。具体到离职补偿问题上,劳动者被无因解雇享有的是法定的、强制的离职经济补偿,其目的在于救济和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而委托方任意解除委托关系却不负有当然给予受委托方补偿的义务,而是看是否存在补偿的约定以及受委托方是否因此遭受损失。当董事与公司的劳动关系随着委任关系的解除而一并解除时,这样的差异性表现并不突出,而当仅仅解除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委任关系时,董事若想要获得离职补偿,须首先证明合同中存在离职补偿的特别约定或因公司任意解除受到了实际损失。可见,鉴于董事和公司之间同时存在劳动关系和委任关系这样一种特殊性,董事离职补偿纠纷并不当然适用《劳动合同法》予以解决,将董事离职补偿问题区别于普通劳动者离职补偿问题对待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补偿影响之特殊性
对离职董事予以补偿应当采取何种立场,是否应当予以限制,需要关注两组重要的利益冲突:经营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1.董事违背信义义务的风险
董事在离职时获得离职补偿是否会影响其与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评判的关键因素在于离职补偿是否会诱发董事违背信义义务的风险。按现行法律通说,董事对公司负有的信义义务可分为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10)根据美国法律研究院(ALI)在《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中的界定,董事的积极义务具体表现为“注意义务(Duty of care)”或“勤勉义务(Duty of diligence)”,鉴于我国公司法条文表述的是“勤勉义务”,本文对二者暂不区分,统一使用“勤勉义务”的表述。前者关乎个人品德问题,后者则是关乎个人能力问题。(11)参见王艳梅、祝雅柠:《论董事违反信义义务赔偿责任范围的界定——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董事责任程度”为切入点》,载《北方法学》2019第2期,第49-50页。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忠实义务是对作为受托人的董事之道德底线要求。一般来说,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判断标准相对比较客观,违反后将赔偿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并且一般不得随意被豁免。例如,我国公司法采取的是对公司损失全面恢复原则,(12)参见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64页。也未规定公司决议豁免董事责任的规则;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虽然引入了豁免规则,但该规则在2000年之后才被明文规定;(13)参见Gabriel v. Rauterberg, Eric L.Talley, Contracting Out of the Fiduciary Duty of Loyalty: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rporate Opportunity Waivers,Columbia Law Review, August 12, 2016, p.1147.英国2006年公司法引入了协议免除机制,但仅仅限于一些优先的特定情形。(14)《英国2006公司法》第233-236条。可见各国对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容忍度都是很低的。这意味着,关涉利益冲突的忠实义务的违反较之勤勉义务的违反更不易为司法所容忍。(15)参见[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尔、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罗培新、张建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可以推测,公司基于理性的决策一般不会给予因违反忠实义务被解除职务的董事离职补偿。换言之,董事若想获得离职补偿就不能有违反忠实义务的记录。坚持此种立场的根源在于,离职补偿可能诱发董事违背忠实义务。
勤勉义务则有所不同。勤勉义务本身内涵的模糊性和违反该义务的界定标准的模糊性或给董事留下了可利用和可操作的空间。一个倾向于理性保守的董事,为了避免因违反勤勉义务而承担不利后果,必然要选择保守的经营策略,尽可能减少有风险的经营行为。因此,法律允许对董事离职进行补偿,尤其在事先对此有所约定的情况下。当然,在股东明明认为离职董事违背了自己的期待利益、信赖利益的情况下仍被要求按约定对离职董事进行补偿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法律也应当对董事离职补偿设置适当限制。
2.控股股东利益输送的风险
当公司内部存在控股股东时,如何评判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之间的利益争夺战是公司法的一个重要任务。(16)参见邓峰:《代议制的公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4-95页。控股股东不仅可以控制股东(大)会的决议机制,也可借助于多数决规则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从而控制董事会决议机制。现实中,控股股东选出的这些董事与控股股东合谋损害公司长远发展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屡禁不止。(17)参见王伟:《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页。这种侵害行为,亦可能发生在董事离职补偿的场合。基于公平原则的考量,必须对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而侵害其他非控股股东正当利益的行为进行限制,引入“多数不得欺诈少数”的法定原则,要求控股股东对其他非控股股东承担一定的“信义义务”。鉴于控股股东可能利用其股权的优势地位在董事离职补偿过程中完成利益输送,应当满足中小股东对董事离职补偿实施限制的需求。
三、董事离职补偿限制之理念
基于对董事离职补偿采取限制性立场构建董事离职补偿机制,还需要先解决一个前提问题,即限制的基本理念是从严还是从宽。
(一)相关规定之检视
1.《公司法》
基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逻辑,如果将离职补偿确认为董事所享有的一项权利,那么董事的对等义务又是什么?在实践中,一些公司在其章程中规定董事离职后仍对公司和股东承担一定的忠实义务。也即,董事任期的结束不当然意味着董事忠实义务的自动免除,而是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约束力。(18)参见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9年版):第106条,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http://www.sse.com.cn/aboutus/mediacenter/ceremony/flashback/c/c_20200106_4979744.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2月2日。从这个角度来看,董事离职补偿可以看作是董事离职后仍承担忠实义务的“报酬”。《公司法》虽然没有直接明确规定董事离职补偿的内容,但关于董事报酬是有明确规定的。(19)其一,《公司法》第37条和第99条规定,董事报酬事项由股东(大)会决定;其二,《公司法》第116条规定,公司应当定期向股东披露董事从公司获得报酬的情况。鉴于董事在职期间的报酬是最容易产生利益冲突的领域,(20)参见高海:《国外董事报酬决定法律制度比较与借鉴》,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8年第3期,第98页。《公司法》对此进行了严格限制,不仅决定权在股东(大)会手中,且属于公司应当定期披露的事项。既然《公司法》对董事在职期间的报酬给予了关注并施以严格限制,那么没理由对同属于这一范畴的董事离职补偿不予以严格限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董事离职补偿采取严格限制的理念是理所当然暗含在《公司法》规则之中的。
当然,如果将在职期间的报酬与离职补偿作为董事与公司之间关系的一种综合性商务安排,则可以将离职补偿当作董事报酬的构成要素来对待。就此而言,《公司法》对董事报酬的限制逻辑当然适用于离职补偿。
2.《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董事离职补偿问题有所规定。(21)《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第61条:“上市公司章程或者相关合同中涉及提前解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的补偿内容应当符合公平原则,不得损害上市公司合法权益,不得进行利益输送。”该文件第61条表达了对董事离职补偿进行限制的立场。根据该条规定,上市公司章程或者相关合同中有关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补偿的条款或者约定,若要得到法院支持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补偿内容应当符合公平原则;第二,不得损害上市公司合法权益;第三,不得构成利益输送。作为反收购措施的离职补偿协议或者条款,并不一定有效或者可执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利用这些条款向关联董事转移公司财产之时,即构成不当的关联利益输送,损害了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可以认为,《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提出了以公平原则作为限制董事离职补偿的基本要求,表达了对董事离职补偿采取严格限制的理念。
3.《公司法司法解释五》
《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3条第2款虽列举了法院在处理公司与董事之间的离职补偿纠纷时需要考量的因素,但具体是否遵循严格限制理念,仅从文本尚难以看出清晰的立场。不过,根据《答记者问》,《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的出台首先要实现的目标是维护公司的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正当利益。具体到第3条董事职务的无故解除及与之相关的补偿规则,其目的在于厘定公司与董事之间的关系,防范代理冲突,增强对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当然,允许股东(大)会无因解除董事职务并不意味着不考虑董事的合法利益。换言之,公司不得借此损害董事的合法权益,公司无理由解聘董事应给予董事合理的补偿以保护董事的正当利益。可以说,《答记者问》所表达的立场已然非常明确——自我交易的本质、作为核心要件的公平、对合理补偿的强调,无不传达出对董事离职补偿应采取限制性立场且要求严格限制的讯息。(22)参见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依法保护股东权益 服务保障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相关负责人就《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答记者问”(以下简称《答记者问》),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55282.html.2021年2月2日访问。《答记者问》中指出,我国现行公司法对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确实没有非常明确的陈述,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践都逐渐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视阈下公司与董事之间成立委托关系。
(二)公平性审查与公序良俗审查
从《公司法》以及与公司法相关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内容的检视来看,针对董事离职补偿问题,坚持限制性立场并遵循严格限制理念是基本的价值导向。或许有人会问,对董事而言,如此严格限制是公平的吗?事实上,股东基于科学理智的决策,绝不会轻易“无故”解除公司董事职务。(23)参见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董事真正被无因解职的概率或许并不高,诚实、清白的董事被无故解除职务的可能性小之又小,即便真的发生了,也可以在具体的程序设计中以某种方式加以消解,对董事离职补偿总体坚持严格限制理念并不成为问题。问题是,这样的严格限制理念落实到立法的具体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的具体裁判路径上应当如何表达?换言之,董事离职补偿限制路径的设计应当如何回应这一严格限制理念?
诚如前文所述,董事离职补偿的本质与普通劳动者离职补偿的本质大相径庭。在我国,公司股权结构上存在控股股东,且控股股东与其所委任的董事之间或为同一主体,或具有实质利益联系。董事离职补偿,一方面可以视为是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另一方面也可直接看作是控股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的实质特性在于控制权人借助其影响决策的优势地位同时影响有关公司乃至其交易对方,而控股股东与董事主体重合的可能性使该关联交易实际沦为“基本自我交易”或“自我交易”。董事离职补偿本就容易受到责难与非议,其自我交易的本质更是可能会异化董事离职补偿约定。既然对关联交易施行公平性审查、实质审查是难以回避的,(24)《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1条表达了对关联交易公平性进行实质审查的立场。那么对董事离职补偿同样应当适用公平性审查、实质审查,甚至应更为严格。但从本文开篇所举案例来看,法院的立场并非如此,不仅未进行公平性审查,更不涉及适用自我交易的严格公平性审查标准。换言之,司法审查中对董事离职补偿本应当适用的公平性审查、实质审查已严重缺位。董事离职之原因,还可能是故意违法。如果在此刻仍然对董事进行补偿,则可能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因此,对董事离职补偿的限制,公平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都应当作为判断标准。
四、董事离职补偿限制之路径
鉴于董事和公司之间可能同时存在劳动关系和委任关系,并且,董事与公司之间委任关系的解除并不当然意味着劳动关系的解除,董事离职可进一步区分为仅解除委任关系而保留劳动关系以及劳动关系同委任关系一并解除两种情形。考虑到这些特殊情况,应当区别董事与公司之间对离职补偿事项有无约定,为董事离职补偿的限制提供精巧的制度安排。权利的文字规定并不保证其充分实践,法律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其所在社会的实际需求,而不只是为了指明某个确定的方向。(25)参见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如果董事与公司之间对离职补偿事项无约定,离职仅解除委任关系而保留劳动关系的,离职董事最多可主张赔偿解除委任关系而引发的损失,而无合同特别约定的事实则可解读为离职不补偿,除非该离职董事能够证明公司之解职行为导致自己遭受了严重不合理损失以至于违背公平原则。此刻,适用的法律依据应当是《民法典》第933条。如果董事与公司之间对离职补偿事项无约定,劳动关系同委任关系一并解除的,董事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6条、第47条等有关离职经济补偿金的内容请求离职补偿。当然,关于离职补偿的争议,更多地发生在董事与公司之间对离职补偿事项有约定或者无事先约定而由公司单独决策的场合。其实,无事先约定而由公司单独决策的,事实上也会产生董事与公司之间就离职补偿事项进行约定的效果。因此,本部分聚焦于董事离职补偿约定,从程序限制与实质限制两个方面讨论限制机制的构建。
(一)董事离职补偿的程序限制
诚如富勒教授所言,在涉及利益冲突的场合,应该通过正当程序来约束决策。(26)参见[美]朗·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8页。为防止董事被任意给予离职补偿,制定程序标准以确保董事离职补偿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对达到限制董事离职补偿之目的是不可或缺的。出于对公司自治的尊重,对董事离职补偿的程序限制一般不首先考虑外部而是应从内部着手。故本部分将重点关注公司作出董事离职补偿的程序以及董事是否能够参与到这些程序中的问题,包括可以参与时参与的程度如何等内容。
1.公司内部机关决策权的配置
(1)以股东(大)会决策为原则
股东(大)会作出的决策一般分为章程和决议两种。从防范控股股东利益输送风险的角度而言,对离职董事补偿事项采取特别多数决的表决方式显然是对非控股股东更为有利的。换言之,应当在公司章程中直接规定董事可以获得离职补偿的情形以及具体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或者在章程中约定有关董事离职补偿事项的内容由股东以特别多数决的表决方式做出决议。但是,即便在表决方式上予以了限制,由章程直接规定董事离职补偿事项和由决议来规定董事离职补偿事项仍然是有所区别的。股东(大)会决议一般并不对外公开,章程对离职补偿的规定则因为公司章程的登记备案机制而具有一定的透明性。从保护非股东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角度考虑,公司以章程的形式规定董事离职补偿事项无疑是最佳选择。
公司章程的记载内容,有必要记载事项与任意记载事项之区分。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的规定,董事离职补偿既可以在公司章程中规定,亦可以由董事与公司以签订合同的方式约定。据此可以推测,董事离职补偿事项并非公司章程的必要记载事项,而是任意记载事项。从董事离职补偿的限制性立场出发,将董事离职补偿事项列入公司章程必要记载事项固然可以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但是风险防范并不是公司治理的唯一目标。一味地强调风险防范会忽略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一方面其与现行的法律规定的基本要义并不相符,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公司对效率的追求。更何况,风险防范亦不仅仅限于事前措施,事后救济也能够消解不利并且重新达到利益冲突的平衡。思及这些因素,建议采取下列做法:将董事离职补偿作为公司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公司可以在章程中直接规定董事离职补偿的相关事项,如直接规定某一离职董事是否可以获得补偿以及获得何种补偿;或者在章程中规定股东(大)会表决具体补偿决议的特别多数决规则。当然,公司与董事以合同方式来约定离职补偿事项的,该补偿约定应当交由股东(大)会适用特别多数决规则进行表决。
(2)董事会决策的一般性排除
董事选举等事项是公司基本事务决策之一,不仅关乎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安排,更是对股东的核心地位及其最终控制权的直接反映,(27)参见曹兴权、黄超颖:《股东会授权董事会的底线:权利配置基础结构维持原则》,载《财经法学》2017年第3期,第98页。因此,董事的选举和更换被视为是股东的基础性权利,原则上不允许被授权给董事会来作出决定。那么董事离职补偿呢?作为董事更换的延伸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允许股东(大)会将离职董事是否获得补偿以及对其如何补偿的决定权授予给董事会呢?
美国特拉华州一直容许由公司董事会对离职的高管施以高额的奖赏,甚至于超过合同原本确定的数额,但前提是不得存在利益冲突。(28)参见Blish v. Thompson Automatic Arms Corporation,Del.Supr.,64 A.2d 581(1948).该裁决认为,如果隐含的合同表明存在这种约定,或者就高管提供的服务来看,这种奖励的金额并无不合理之处,则不能认为这种回溯性的薪酬安排缺乏对价。日本公司法亦有关于董事责任的减免由董事会决议决定的规定,但其具体适用情形十分复杂。(29)参见蔡元庆:《董事的经营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在我国,亦有案例显示存在由董事会决定董事离职的情形。(30)在该案中,被告公司伦教汽车玻璃公司的董事会以经营状况不佳为由,解除与所有员工的劳动关系,包括被告公司的董事严泽祺。详见(2006)佛中法民四终字第174号判决书。这至少证明,即便是涉及董事自身利益的事情,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决定也是可能存在的。问题在于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做法必然会引致不利的后果,而这些不利后果是可以消解的吗?如果不能消解,或者消解不利后果的成本过高,那么这种授权就应当被禁止。股东授权董事作出决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董事的专业才能与知识,以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但这一期待不可避免地会有落空的时候。因为,董事为公司和股东谋求利益的同时,也会谋求私利,权利的滥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代理成本正由此产生。对离职董事的补偿,是直接关涉董事自身利益的事项,客观存在的利益冲突必然会影响董事会决策的理性程度。尽管董事作为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人员,相较于股东更熟悉公司的事务,对于一位董事是否坚守了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是否做到了为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尽职尽责,其他董事或许比股东更为了解,在判断一位董事是否应当获得离职补偿的时候,董事会决策可能要比股东(大)会决策更有效率。但是,我国仍然应一般性排除董事会对董事离职补偿的决策权。理由在于:其一,如果董事之间为了获取离职补偿达成合谋,董事违反信义义务的风险将被进一步扩大。其二,董事离职补偿在本质上属于自我交易,依据《公司法》第148条规定应由股东(大)会批准。其三,我国也不适宜引入董事自我交易的董事会决策规则。一方面,我国《公司法》事实上坚持着“股东会中心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公司存在控股股东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离职补偿交由董事会决策更容易引发控股股东利益输送风险。
(3)监事会的辅助性监督
在我国,监事会是《公司法》明确规定的常设机构,其基本角色定位或功能定位是监督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活动以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31)参见李建伟:《公司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页;赵振华:《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153页。关于监事会职权,《公司法》第53条、第54条、第118条有详细列举。具体而言,这些职权包括对“人”的监督权和对“财”的监督权。前者体现为对董事等人运营公司行为的监督;后者体现为对公司财务情况的监督。在董事离职问题上,我国监事会的主要职能可体现在监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行为,提出罢免行为不当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建议。一方面,监事可以通过列席股东(大)会掌握董事离职补偿决策信息,对行为不当的离职董事提出不得予以补偿的建议;另一方面,监事通过日常列席董事会会议以及对董事履行董事义务的其他行为的监督,了解董事的职务履行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就某一董事离职补偿的具体事务向股东(大)会提出是否补偿以及怎样补偿的建议。
2.离职董事的参与限制
鉴于我国对“股东中心主义”的坚持和贯彻,董事事实上只是股东(大)会决策的执行者,即便是关涉董事自身利益的离职补偿决策,亦没有强制董事参与到这些决策中的必要。不过,如果公司内部自治文件如公司章程规定离职董事可以参与到董事离职补偿之决策并赋予了离职董事一定的权利,这些规定是否背离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
(1)离职董事的知情权
离职董事可以列席公司作出离职补偿决策的股东(大)会,从而知晓公司不予以离职补偿的具体原因或者予以离职补偿时,补偿金额的具体确定之过程。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董事会负责召集股东(大)会,董事长负责主持股东(大)会,即董事列席股东(大)会应当属于一种常态。当股东(大)会所要决策的事项与董事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比如决定董事的报酬、决定董事的离职补偿等,该董事需要回避吗?也即,该董事是否不得列席该次股东(大)会?
其一,《公司法》规定的回避规则有一个共同前提,即需要回避者对该利益冲突事项享有表决权,为防止其表决权的行使影响公司决策的理性,故不允许其就该事项行使表决权。董事列席股东(大)会,可以准备会议、主持会议、记录会议,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对股东(大)会的决策事项享有表决权。因此,董事并不能成为股东(大)会的回避主体。其二,即便是就回避本身而言,《公司法》所提及的回避方式仅仅是表决权的限制行使,而非禁止利益冲突主体出席会议。因此,从离职董事知情权的行使角度而言,其仅仅是列席股东(大)会,根本没有表决权,遑论表决权的限制行使,而《公司法》也并没有规定董事需要回避股东(大)会的情形。因此,没有必要限制董事列席股东(大)会,即便股东(大)会决策事项为该董事的离职补偿,该离职董事的列席并不违反程序正义。
坚持董事离职补偿的限制性立场与允许离职董事事先知晓补偿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势不两立的;相反,知情权体现的是经营管理者与股东利益冲突的平衡与折中。对于一个诚实善良的董事来说,知情权的行使使得其可就离职风险提前准备,以分散提前被股东(大)会解聘的风险。尽管董事通常扮演着一个相对强势的角色,但强势地位总是相对的,当董事被解除职务时,虽不至于达到同普通劳动者一般需要法律倾斜保护的弱者地位,但其离职所引致的风险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董事作为公司重要的管理人员,在公司中浸淫日深,为更好地履行董事职责需要不断获取专用于任职公司的专业技能,离职再就业意味着他们必须另行投入,以获得其他公司所需要的专业技能。(32)参见[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尔、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罗培新、张建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7页。就像找不出两片模样相同的叶子,完全相同的公司亦不存在,适用于某一公司的管理方式不见得适合另一个公司,毕竟“南橘北枳”的悲剧时有发生。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并购市场等带来的市场压力,也会不断压制董事的选择。所有的投入都需要成本,理性的人总会试图避免这些成本,因此理性的董事不会轻易地选择离职,但是在公司股东(大)会可以无故解聘董事的前提背景下,董事被解除职务的风险提高,再理性的董事也会不得不面临这些风险和成本。(33)尽管基于同样的理性,股东(大)会也不应当随意地无故解聘董事,毕竟董事的选任也是需要成本投入的,但不理智的决策总是时有发生。就此而言,对离职董事给予补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基于公平原则的要求,是对董事离职后再就业所投入成本的一种补偿。因此,离职董事可通过列席公司作出离职补偿决策的股东(大)会了解公司不予以离职补偿的具体原因或者予以离职补偿时补偿金额的具体确定过程等,从而预估自己即将面临的风险和成本以做出合理的安排。
(2)离职董事的陈述权
不管是从限制离职董事参与董事补偿决策程序的角度,还是从公平尊重离职董事利益的角度,离职董事列席公司作出离职补偿决策的股东(大)会而拥有的知情权都不是最关键的。真正有意义的法律问题是,离职董事在列席股东(大)会的基础上能否进一步享有陈述权。股东(大)会认为,董事在某一项目经营上没有完全尽到勤勉义务,导致项目没有实现利益最大化,故而减少对该董事的离职补偿甚至决定不予以离职补偿,此时是否能够允许该董事就自己对该项目有无尽到完全的勤勉义务作出陈述,以期说服或打动享有决策权的股东,从而努力争取自己的补偿利益?而这样的陈述权又是否有招来不利风险的可能,而与董事离职补偿的限制性立场相悖?比起离职董事知情权,陈述权的行使更具有实质意义,如果说前者仅仅是一个列席的“旁观者”,(34)在决定董事离职补偿的股东(大)会上,直接关涉的离职董事显然不愿置身事外,但是囿于股东与董事权力的划分,仅仅列席的董事事实上无法左右股东(大)会的决策,只能做一个听取会议的“旁观者”。后者的参与感则要强得多,因此有必要对其单独予以讨论。
从域外法的实践来看,离职董事享有陈述权不是个例。《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168条、第169条规定,即使董事与公司之间存在不得提前解除职务的协议或约定,股东会仍然享有在董事任期届满前罢免董事的权利,但是董事拥有向股东会就离职决定作出陈述的权利。《德国股份公司法》第84条规定,在正式任期结束以前,如果有重大的原因,监事会可以撤销对董事的聘任,对于是否存在解聘的重大原因,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尤其是应当考虑相关董事的解释说明再作出相应的决定。在我国,虽然《公司法》条文中并没有类似的规定,但是实践中确有类似操作。比如,《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提前解除董事职务应当说明解除董事职务的理由,且被解聘的董事有权向股东大会作出回应。(35)详见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A股发行后适用)第111条,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20-02-25/601696_20200225_2.pdf,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2月2日。从董事离职补偿限制性立场出发,离职董事的陈述权有无违背公平原则或者公序良俗原则之处?换言之,是否会不利于董事违背信义义务等风险的防范而必须要予以限制?
从公平原则的角度看,虽然陈述权的行使对股东决策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对该董事离职补偿的最终决定权仍掌握在股东手中。因此,无论是对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还是对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离职董事的陈述权均不会有实质性改变之效果。相反,如果允许离职董事对离职补偿事项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展现自己诚实善良的董事形象,哪怕具有谋求更高离职补偿之企图,该陈述也具有使得股东获得更多的信息、帮助股东作出科学决策的效果。当然,我们无法排除存在控股股东与董事合谋作出虚假陈述的可能,但是这样的不利风险仍然是可控的。毕竟,离职董事的陈述不是一锤定音式的,可以配合其他的证据予以佐证。总之,离职董事的陈述权不仅不会背离公平原则的要求,反而具有保护诚实善良的董事、促进公平的效果。
离职董事的陈述权也不会背离公序良俗原则。正如前文所述,离职董事的陈述本身有影响股东(大)会决策的可能,但是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正面效用。
(3)离职董事的议价权
董事离职补偿,可通过合同的方式加以约定。此刻,离职董事事实上可以获得与公司就离职补偿事项讨价还价的权利,此为议价权。不同于离职董事的知情权和陈述权,议价权的本质是改变了董事和公司在离职补偿事项上的地位格局。在离职董事行使知情权和陈述权时,他们仅仅享有知晓和表达意见的权利,是在配合公司行使最终决策权。虽然陈述权在一定意义上可能影响公司决策,但绝未达到撼动公司主导地位的境地。而议价权则不同。陈述权表现为“你问我答”,而议价权则表现为“主动出击”。基于合同双方主体平等地位的特性,行使议价权时董事至少在形式上与公司达到了对等的地位。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董事利用可能的强势地位谋取自身利益本无可厚非,但这其中还是存在董事违背信义义务的风险,尤其是他们可能串通控股股东获取高额离职补偿。正如《答记者问》明确指出的,董事离职补偿的实质体现为董事与公司之间的自我交易,董事议价即意味着董事自定补偿、自我激励。个体具有趋利性,存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本能。在签订离职补偿协议过程中,董事可能出于自利逻辑而放弃公司利益以保证自身的既得利益。同时,当不能和公司就离职补偿达成一致意见时,董事也可能因失去激励而在最后任期内消极怠工。特别是,当董事和控股股东沆瀣一气欺骗小股东时,小股东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这显然不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的要求。因此,应当限制离职董事个人在签订合同中的议价权。当然,董事议价权隐含着董事对个人能力的自我价值判断。从尊重个体人格的角度看,任何个人的自我价值判断都不应当被无情地彻底抹杀,即便是出于追求集体利益的正当目的,个人利益也应当得到合理的尊重。就此而言,对待离职董事的议价权,可以基于风险防范的目的予以限制,但尚不至于赶尽杀绝。
针对离职董事的议价权,可考量从以下角度进行限制:其一,允许离职董事就离职补偿提出申请。当公司对董事离职补偿事项尚无明确规定时,离职董事可以通过向股东(大)会提出补偿申请,说明要求补偿的理由以及补偿金额的计算依据。其二,赋予离职董事对股东(大)会补偿决议的异议权。当离职董事对公司股东(大)会做出的补偿决定有异议时,有权向股东(大)会提交异议申请,说明异议的原因。股东(大)会收到申请后应当及时处理离职董事的申请并给予答复。离职董事无论是提出补偿申请还是针对补偿决议进行质疑,虽然事实上具有影响股东和公司在离职补偿事项上权力分配的效果,但只要股东(大)会牢牢掌控董事离职补偿事项的决策权,此种影响就不会脱离公平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的基本要求。
(4)公司法对董事离职补偿陈述权与议价权的表达
如何在公司法中表达董事离职补偿的陈述权与议价权需要精细的考量。离职董事对陈述权的行使,发生在股东(大)会的决策程序中,并且是相对被动的。而离职董事对议价权的行使,其补偿申请在股东(大)会决策前,异议申请在股东(大)会决策后;并且,不论是补偿申请还是异议申请,董事都处于主动地位。从这些权利行使对离职补偿协议以及对公平与公序良俗的影响看,对陈述权的肯定应强于议价权。因此,《公司法》修订时,可以考虑引进离职董事的陈述权以促进公司决策理性,却没有必要对离职董事的议价权作专门表述;至于对议价权的限制,可交由法院在个案裁判中予以考量。
(二)董事离职补偿的实体限制
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是正义的两种表现,二者相得益彰并缺一不可。对董事离职补偿予以严格限制,除了考虑公司内部机关决策权的配置以及离职董事在参与程序上的限制以外,还要考虑许多其他的实质影响因素。《公司法司法解释五》明确指出要综合考虑的董事离职原因、董事剩余任期、董事薪酬水平等因素,就是实体性限制。
1.董事离职原因
董事离职的原因,除无理由被公司解职外,还涉及其他情形,比如董事主动离职、因违反勤勉义务被罢免、因违法或者违反忠实义务被罢免等。不同离职原因所涉利益冲突不同,限制方式或限制程度也应当有所区分。结合《公司法》对董事任免事项的规定,董事离职原因可以区分为董事任期届满的情形、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辞职的情形、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被解除职务的情形。如何在坚持严格限制董事离职补偿的基础上,分别针对这三种情形构建实体性限制规则呢?
(1)任期届满
《公司法》第45条和第108条规定了公司董事的任期。(36)《公司法》第45条:“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第108条第3款:“本法第四十五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任期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一般来说,公司董事的任期在公司章程中予以具体规定,履行期间届满,即董事任期届满。董事任期届满,委托事项完成,委托合同即履行完毕,除非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而必须留任或者履职事项很特殊而要求该董事完成该事项。依据《民法典》第928条第1款,委托合同履行完毕后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受托人支付报酬。根据文义解释,委托人没有额外向受委托人支付补偿的义务。因此在董事与公司之间没有约定的情形下,离职董事很难要求公司支付补偿。或许,离职董事可能基于离职后仍然承担一定忠实义务的逻辑去主张。的确,许多公司章程都设置了要求董事在离职后仍承担一定忠实义务的条款。不过,章程的这些规定很难作为董事与公司之间没有约定时离职董事主张离职补偿的正当性基础。关于章程有关董事在离职后仍承担一定忠实义务的条款,本身可以看作是董事与公司之间委托合同的内容。离职董事履行该义务,本身是在履行委托合同。即使不作此种解释,该义务也可被解释为后合同义务。
倘使公司与董事对此种情形下的离职补偿事项事先或事后有约定,情况将有所不同。问题转化为是否允许公司与董事约定,在董事任期届满后由公司支付董事一笔离职补偿金?从合同自由的角度考察,当事人有约定的应当从其约定;但是从公司法逻辑考察,则应当关注这些约定可能诱发的董事信义义务违背之风险。在限制其决策程序的基础上,任期届满这一离职原因是否需要被限制在约定补偿范围之外呢?
鉴于董事因任期届满而离职是董事离职的常态,公司给予董事离职补偿可出于以下几个目的:其一,用于激励,许之以额外的酬劳激励董事在任职期间全心全意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其二,表达感谢,对董事在任职期间的辛苦付出表示肯定;其三,表示期待,希望董事离职后可以诚实履行后合同义务,减少因此产生纠纷的几率。从目的正当性来看,这三种目的无疑都符合人之常情,当然符合公序良俗原则的要求。因此,因任期届满给予董事离职补偿的约定是可以被容许的。问题还在于,容许的程度有多高?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为避免对公司其他利益主体造成不公平对待,有必要为董事离职补偿金额的约定设置一个最高限额,以限制不合理的天价补偿。该最高限额的设置,既可以由法律、行政法规等直接予以明确,亦可以由公司章程具体表达;但是一旦法律、行政法规等对此有所约束,章程所表达的最高限额便不得超过法律、行政法规等设置的最高限额。该最高限额,可以具体表现为不得超过该董事的平均年薪、不得超过同行业董事平均补偿数额等。不过,对于具体标准,则应当结合董事剩余任期、董事薪酬水平以及个案中的具体情况予以确定。
(2)任期届满前辞职
在任期届满之前,董事可基于自身原因主动向公司提出离职。(37)本文所讨论的离职原因不局限于离职的表现形式,而是追究其本质。因此自身原因不包括董事违反忠实义务或勤勉义务之类的情形。因违反忠实义务或勤勉义务而引咎辞职的,其表现形式上虽然是董事辞职,但其本质仍归为有因解除。作为受托人的董事,当然可以行使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解除自己与公司的委托合同关系。但是,自由不仅意味着拥有选择的机会,更意味着必须承担行为之后果。(38)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3页。董事有离职的自由,但在其做出辞职的选择时应当对由此产生的风险做好应对的准备,不得以此为由要求获得离职补偿。不仅如此,根据《民法典》第933条的规定,作为受托人的董事享有随时解除委托关系之权利,但同时负有赔偿因其行使合同任意解除权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之义务。根据该条,在主动离职时,董事不但不享有向公司请求补偿的法定权利,反而可能承担赔偿因其离职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之义务。此外,由于董事职位特殊,董事离职带给公司的风险可能高于普通劳动者离职带给公司的风险。此时要求公司进行补偿无异于要求可能遭受损失的人为造成风险的人提供补偿。在劳动关系与委任关系一并解除的情形下,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辞职亦可视为是董事主动要求解除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而《劳动合同法》第46条亦规定了主动离职的劳动者一般不享有离职经济补偿金。
但是,主动离职的董事可否依据与公司的约定享有离职补偿呢?理论上,公司不太可能愿意向在任期届满前辞职的董事支付额外的离职补偿。毕竟,在提前辞职的情况下,董事尚未完成公司的全部委托事项,作为委托人的公司之期待利益尚未得到完全实现。但是实践生活总是复杂得多,我们也无法排除公司愿意向辞职董事支付补偿的情形。如果确实经由股东(大)会作出这样的补偿决定,即可视为是公司愿意自行承担董事辞职后的风险。因此公司对主动离职的董事支付离职补偿可以被容许;但同理,该约定补偿的金额也要受到合理限制。
(3)任期届满前被解除职务
首先是无因解除情形。公司在董事任期届满前无因解除董事职务,属于委托人单方行使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行为。根据《民法典》第933条的规定,作为委托人的公司在解除委托关系时,应当赔偿作为受托人的董事因此直接受到的损失以及合同履行后可能获得的利益。这或许可以成为被无因解除职务的董事要求获得离职补偿的请求权基础。即无论公司与董事之间是否有所约定,如果离职董事可以证明公司的无因解除行为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就可以要求公司给予赔偿。也就是说,《民法典》第933条不仅确定了离职补偿的条件,亦确定了离职补偿的范围。这样的离职补偿本质上是损失的弥补,这显然是符合公平原则要求的。从域外的法律规定来看,大多有相似的表述。例如,《法国商法典》规定,股东有任意罢免董事的权利,且不需要证明罢免董事的特别决议具有科学性,公司的章程亦不得通过任何条款对股东罢免董事的权利进行约束,被罢免董事可以要求补偿,但前提是其证明因股东的任意罢免遭受损失。(39)《法国商法典》第L225-18条第2款,L225-45条,L225-46条。《波兰商事公司法》规定,在章程未作特别说明的情况下,股东会有任意罢免董事的权利,但罢免不影响董事就损害要求赔偿的权利。(40)《波兰商事公司法》第203条。德国公司法中亦有类似规定。(41)《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8条规定,股东通过股东会议可以在任何时间罢免董事,除非章程做出限制。但这种罢免将不影响已有的任何服务协议,该协议通常包括一次性支付一定金额以终止协议等。可见,公司无因解职中的赔偿损失式离职补偿是比较通行的。而在劳动关系同委任关系一并解除的情形下,董事被无因解除职务相当于作为用人单位的公司主动要求解除劳动关系,董事亦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6条及第47条的规定享受有限的法定离职经济补偿金。
当然,在董事被无因解除职务的情况下,公司完全可以就此与董事另行达成约定。不过,此种约定是否当然有效?如果是,它与上述法定补偿的关系如何?其一,被无因解除职务的董事本身是没有过错的,且因为被无因解除而被动地承担了离职之后的风险,公司若就此与董事做出补偿的约定,该补偿显然具备正当性基础、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其二,基于约定优先于法定的民商事基本原理,应首先考虑董事与公司之间的离职补偿约定。但是基于对严格限制董事离职补偿理念的坚持,对约定的补偿金额仍然要予以限制。鉴于此种类型下的补偿金额有明确法律规定,约定的补偿金额不应当过分高于董事的实际损失或者《劳动合同法》上规定的离职经济补偿金,即不得超过最高补偿限额。倘若约定的金额明显低于法定补偿以至若按约定的补偿金额履行将显失公平,离职董事可诉至法院要求调整。
其次是有因解除情形。需要区别违反忠实义务还是违反勤勉义务。就忠实义务而言,我国公司法仍然坚持董事必须全面赔偿的严格责任立场,尚未引入域外公司法关于允许公司通过协议的形式排除或限制某些情形下责任的规则,因此现实中几乎不存在公司通过约定减免董事违反忠实义务赔偿责任的情形,故对违反忠实义务的董事支付离职补偿的约定应当被禁止。就勤勉义务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勤勉义务与董事的个人能力有关,董事依据个人专业知识和技能做出的商业决定是否正确在决策作出之时是很难判断的,即便事后我们可以发现公司的某项商业决定效果甚差,也并不能表明其自始即犯了错误。(42)参见[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尔、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罗培新、张建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页。另一方面,对董事勤勉义务设置过高的赔偿风险,会压制董事经营的积极性。因此,各国公司法普遍对违反勤勉义务的董事之容忍度高于对违反忠实义务的董事之容忍度。因此,一个违反勤勉义务的董事应当有获得约定离职补偿的机会。在董事因违反勤勉义务被解除职务时,若公司基于上述原因的考虑,通过章程、公司决议或者在委托合同中约定离职补偿,应当得到法院的认可和支持。但同样地,基于严格限制董事离职补偿的立场,约定的补偿金额不得超过合理的限制。
再次是金色降落伞条款。公司解除董事职务的情形下,还存在一种比较特殊的董事离职补偿情形,即金色降落伞条款。以反收购为目的的金色降落伞条款具体是指目标公司章程约定,董事等管理层可在公司实质控制权发生转移时获得一笔费用以弥补其因此受到的损失。(43)参见林国彬:《敌意并购防御措施之研究——黄金降落伞》,载《万国法律》2007年第152期,第10页。为达到反收购之目的,金色降落伞条款下约定的支付给董事等管理层的费用通常较高。与前文所述的董事离职原因不同,金色降落伞条款下董事离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触发点,即公司面临被收购,公司内部控制权将产生变化。在实践中,公司在其章程中规定金色降落伞条款下的董事离职补偿内容的不是个例,因此有必要对该情形单独予以讨论。首先,作为一种市场行为,收购和反收购行为没有明确的好坏之分,二者之弊端都不应当被过分夸大,公司收购的效果只能依据潜在的利益与弊端具体判断。(44)参见宋永泉:《论上市公司公开收购的法律问题》,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第83页。但对董事而言,成功的收购不仅代表其经营者职位的丧失,还可能要承受随之而来的名誉受损。(45)参见王伟:《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页。因此,目标公司的董事很可能成为恶意收购的利益受损者。基于这样的考虑,应当允许采取适当的反收购措施。(46)参见张舫:《公司收购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虽然金色降落伞条款下的董事离职补偿约定可以被容许,但问题在于如何限制?首先,按照前述程序限制机制,决策权应当牢牢把握在股东(大)会手中。(47)参见关家涛:《我国证券法中上市公司收购法律规定之检讨》,载《中国商法学精粹》,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页;王伟:《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其次,金色降落伞条款的特殊触发点是否使得董事离职补偿金额所受到的限制区别于其他情况下的董事离职补偿?在实践中,一些公司为了吸引或者激励有才能的董事,在金色降落伞条款中制定了非常高额的离职补偿。比如,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海印集团)在其章程中约定的离职补偿金额高达离职董事前1年所有薪酬福利总和的10倍。(48)《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7年11月版)中规定:“当发生公司被并购接管的情形时,在公司董事、监事、总裁和其他高级人员任期未届满前如确需终止或解除职务,必须得到本人的认可,且公司须一次性支付其相当于前一年年薪及福利待遇总和十倍以上的经济补偿。”再比如,《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6年1月修订版)中规定:“当发生公司被收购接管的情形时,在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期未届满前,非本人原因需终止或解除职务的,公司须一次性支付其相当于前一年年薪总额十倍的经济补偿金。”我们假定一家公司董事的年薪约为50万~100万,那么按照海印集团章程中的规定,离职董事将可以获得高达500万~1000万的补偿金,如果不对其予以限制,其不利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公司控制权是董事行为的外部监督力量之一,而金色降落伞条款有减弱控制权监督的风险。董事基于金色降落伞的保护可能放松对公司业绩的重视程度。已有证据表明,金色降落伞的保护或影响董事决策的审慎性。(49)参见Lynn A. Grisham and Doug Rake, Future Executive Bail Outs: Will Golden Parachutes Fill the American Business Skies? 14 Texas Tech Law Review615(1983):615-616.毕竟,即便公司因业绩不佳被收购了,董事也可以获得一大笔的补偿金,这样的负面激励实则有违公平原则,因而必须对其加以限制。但此种限制与上文中的限制应当有所差异。金色降落伞条款需要考虑到抵御“外部野蛮人”之目的,如果补偿数额定得过低,不利于反收购目的的实现,故可适当提高最高限额。比如,如果董事任期届满后离职可获得的补偿金为其任职年限内平均税前薪酬总额的一半,那么在金色降落伞条款中可放宽至其任职年限内平均税前薪酬总额的2至3倍。
2.董事剩余任期
相较于公司的存续时间,董事的任期总是相当有限。因此,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公司法都会面临一个董事任期的有限性与股东持股期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而该矛盾所带来的弊端将在董事任期届满前变得尤为严重。譬如,董事此时更偏向于投资成本较低但见效较快的项目,而放弃更具获利性但是见效期间更长的项目。(50)参见于东智:《论代理成本的控制——兼议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302页。董事如此决策的目的在于,避免在最后的任期内因出错而丧失获得离职补偿的机会。但另一方面,董事离职时剩余任期越短,意味着董事至少在量的维度上对董事职责的完成度越高,为公司创造的利益越多。如果公司出于激励等目的要支付离职补偿,合理的补偿金额应当随着董事实际任职期限的延长而增加。即,董事离职时剩余任期越短,离职补偿数额反而应当随着实际任职期限的延长而增加。当然,董事剩余任期对董事离职补偿的实质影响需要根据董事离职的原因予以区分。
3.董事薪酬水平
较之于普通劳动者,董事薪酬通常不菲。董事高薪,已然是现下公司治理制度中的重要奖赏机制之一。(51)参见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64-365页。几乎所有情形的约定补偿都或多或少地暗含乃至明显有激励意图,董事离职补偿事实上可能成为薪酬激励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如,在美国特拉华州法院审理的一起有关迪斯尼公司的案件中,公司董事因批准向迪斯尼公司的总裁支付高达1.4亿美元的离职补偿金而被起诉。由于存在解职约定条款,董事会基于约定条款而决定对离职董事进行补偿关涉的到底是薪酬方案还是离职补偿,成为该案的争议焦点。(52)参见In re Walt Disney Co. Derivative Litigation,906 A.2d 27(Del.2006).法院认为,董事会的自由裁量权仅仅限于前者。不过,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一直容许由公司董事会对离职的高管支付高额的、甚至超过合同原本确定数额的奖赏。(53)参见Zupnick v. Goizueta, 698A.2d 384 (Del.Ch.1997).该案中,法院支持针对管理人员以往的服务在其任期结束后赋予期权激励。如此处理的逻辑在于,离职补偿实际上被视为是薪酬激励的组成部分,是董事在任时薪酬在离职后的一种延伸体现。
不过,董事的高薪激励机制可能被异化,离职补偿亦如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多家金融机构陷入严重经营危机,或破产、或被并购、或被国有化。在这些公司中出现了受到社会各界挞伐的显著不公现象,大量人员失业但高级主管等人却可以领到一笔丰厚的离职补偿金。这些现象表明,薪酬激励的正面效用有限,无法取代或者部分取代股东以及市场的密切监督。(54)参见Lucian Bebchuk, Jesse Fried and David Walker, Managerial Power and Rent Extraction in the Design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69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751(2002).为此,必须建立适当的控制机制来控制董事薪酬以及离职补偿。其中,美国的危机应对法《多德-弗兰克法》引入了股东对董事薪酬决定的主导权、扩大公司董事薪酬信息的透明度等措施。前文关于股东(大)会牢牢掌控董事离职补偿的决策权、将董事离职补偿事项纳入公司应当披露事项的建议,一方面符合中国公司治理现实需要以及《公司法》规定的既有逻辑,另一方面也源于美国公司法发展的启示。
对董事离职补偿的约定数额设定最高限制,也是限制董事薪酬的一种选择。为此,可将董事任职期限内的董事薪酬作为参考因素。首先,可借鉴《劳动合同法》与《破产法》的做法。根据《劳动合同法》,高薪劳动者离职补偿金按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支付且支付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根据《破产法》,企业破产后董监高劳动债权的优先受偿额按职工工资的平均值确定。《劳动合同法》与《破产法》的规定,已经暗含了高薪劳动者以及董监高等人原享有的报酬可能不甚合理的意味。鉴于这种限制思维正好契合适当限制董事离职补偿的公司法逻辑,可以参考《劳动合同法》与《破产法》的做法,按“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确定董事薪酬的合理基数,以此为基础综合考量其他因素,嵌入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的容忍度,以最终确定离职补偿的额度。
五、结语
虽然不能与《公司法》的规定相提并论,但《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3条在明晰公司治理规则上表现出了两大价值:第一,正面回应了公司是否有权无理由罢免董事职务的疑问,进一步肯定了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10号的立场;(55)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0号:李建军诉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该案中,最高法指出:“公司法尊重公司自治,司法机关原则上不介入公司内部事务……公司的章程中未对董事会解聘公司经理的职权做出限制,并未规定董事会解聘公司经理必须要有一定原因……可以做出解聘公司经理的决定。”第二,正式提及董事离职补偿问题并引入了实质限制的理念。虽然公司如何处理董事离职补偿在本质上属于公司自治的事务,法律一般不加干预,但董事获得高额离职补偿可能损害公司利益、背离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的内在要求,公权力对此不能完全坐视不管,必须在司法甚至立法的层面有所回应。从检索到的国内司法案例来看,司法干预主要坚持劳动法逻辑,忽略了董事与公司之间的特殊委托关系以及董事作为公司管理人员的特殊身份。司法裁判的思维有必要从劳动法转向合同法,并且借助公司法的自我交易限制机制来处理董事离职补偿纠纷。不过,仅仅依靠司法的努力是不够的。通过司法适用或者解释而供给的规则对于社会大众的指引效应显然没有立法供给的规则作用大,就像阿列克西反复强调的一样:“司法判决的绝对合理以立法的合理性为前提条件。”(56)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355页等。在总结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域外公司法关于董事离职补偿的规定以完善董事补偿的相关制度,应是本轮公司法修订的一个重要任务。特别是,司法解释尚未涉及高级管理人员、监事的离职补偿,更亟待公司法的直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