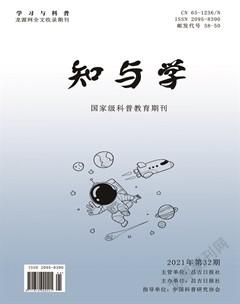激动与喜悦 挣扎和彷徨
秦荣
摘要:作为陶渊明辞赋精品的《归去来兮辞并序》,为我们读者尽情展示了作者真诚质朴的人格魅力,然而身逢乱世的他要表达的情感又是委婉含蓄的。只有把握作者真实的心路历程,才能帮助我们准确理解该作品所蕴含的真实情感。
关键词:陶渊明;作品;情感
作为中国第一隐士,陶渊明一直享受着后人的膜拜,何况还有他那些清新质朴的田园诗,发乎心传于世的辞赋,和引人入胜的桃源,所以他应受之无愧的。《归去来兮辞并序》算是陶渊明散文和辞赋的精品了,给高中生读,显然是有启蒙和引导的作用,特别在官本位的中国,在世俗化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人们浮躁的心灵被外物所累,灵魂没有安放之处。质朴真诚的诗人在这篇辞赋里算是用心了,他勤勉为文,用心构思,将自己一番委曲难诉的复杂情感真诚地表达了出来。诗人是真诚的,他忠实于自己的情感,然而他的感情是复杂的,他身处的时代是复杂的。于是我们读到了这样一篇看似风平浪静实则蕴藏着惊涛骇浪般情感变化的文字。
我愿意称他为诗人,而不是隐士,至少在他写作这篇辞赋的时候。因为诗人的情怀是率真而感性的,坦荡而激情的。在古文里我们几乎没有读到辞赋和序文一起并传的文字。诗人已经准备好用辞赋表情达意,却丝毫没放弃倾注于序文的力量,这大概也是诗人真诚为文的实在吧。
梳理完序文,我让学生思考一个问题:序文写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做官的原因,一个是辞官的原因。从常见的序文作用看,他不厌其烦地从做官的原因诉起,“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这些是否罗嗦?学生们大多只能想到铺垫。当然这是为了铺垫,正因为诗人自己没有多加思考的“脱然有怀”,才会有着“心为形役”的“惆怅而独悲”;正因为迫不得已的为谋生而去做官,才会有连夜归去的可能。这是正面的铺垫。如果认真研读序文,也可以发现,其实这段叙说还有强烈的反衬作用,越是强调做官是迫于生计,越是彰显了诗人归去的决心。那么这里的做官原因也恰是辞官的原因了。这样从文章的表达上来说仍然是丝丝入扣紧紧围绕中心的。当然在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也是纠葛。这种超越于物质之上的精神追求是当下许多中学生很难理解的价值观。今天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物化”了。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正在成型的高中生来说,物质主义社会对其精神生活的裹挟导致他们精神生活的世俗化和功利化特别明显。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成为当代中学生生活中的缺失性存在。所以有很多学生在讨论时都说,陶渊明只可以仰视,甚至将我们的诗人世俗化,认为他是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这其实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滑坡现象。我们无须唱高调,现实确实如此。为此,我们有责任用经典作品去陶冶青年学生的情操,引导青年学生做个有精神追求的人。
于是将陶渊明从神圣的祭坛上请下来,把握他的真实的心路历程是我们准确理解《归去来兮辞》的思想内容、把握诗人内心情感的最好途径。我不喜欢用那些概念术语去固定诗人的形象,学生们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一个理想受挫的诗人内心的苦闷与烦恼,或者洒脱和坦然。所以学生不难理解诗人吟唱的田园之乐总或多或少带有某种虚幻主观。因为诗人将要逆时逆己而行,诗人将要决绝归去,他是需要充足的理由说服他人、更是说服自己。诗人是真诚的。在这篇辞赋中,诗人一面极力歌唱着归去的激动和喜悦,似樊鸟脱笼,如池鱼入渊;一面也丝毫不回避自己的犹豫和矛盾、惆怅与失意。别看诗人在篇首就那么自信地说“觉今是而昨非”,篇中又极写归家的喜悦,再写村居生活的自在,可贯穿诗文始终有一条伤感的线在忽明忽暗地飘动着。除了在第一节“惆怅而独悲”、第二节“抚孤松而盘桓”、第三节“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些隐约的伤感外,至第四节一开篇“已矣乎”,诗人伤感的情怀已经不再是那么犹抱琵琶了。这是一声多么沉重的叹息。行文至此,是读者理解上的一个难点。诗人忠实于自己的情感,决不肤浅地一路高唱下去。家庭的和美,村居的悠闲,这些归去的田园之乐也只是表象的快乐,还不能从根本上排解诗人的忧郁和不安,若不能从生命的高度真正地释放心灵,那即便回归也依然会像在庸俗的世界里一样比长短,争是非的,恰如诗人这一句“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的叹息。所以我以为诗辞的最后一节应是诗人思想感情又一次质的飞跃,为他的回归提供了最有力量的措辞。“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 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寓形宇内”,在自然山水之间寄寓自己的身心。“委心”,顺应自己的本心,也就是随心逐愿之意。“去留”, 指生与死。“帝乡”,仙乡。《庄子·天地》:“乘彼白云,至于帝乡。”“植杖”,把手杖插在一旁。“耘”,除草。“耔”,培土。“皋”,水边高地。“啸”,即口撮起来发出又亮又长的声音。吹啸之举可能是魏晋名士的一种雅好,一种风度吧。据《世说新语》记载:谢安隐居东山时,曾携友人临海观潮,风起潮涌之际,友人们兴奋地唱歌吟咏,而谢安则“吟啸不言”,用一段长“长啸”表达内心的欣喜愉悦。《晋书》记载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听闻吴中一士人家有一片好竹林,便专程驱车前往观赏,进入竹林,先是一番吟咏,继而就长啸不止。陶渊明在《饮酒·其七》也写道:“啸傲东林下,聊复得此生。”“长啸当歌”,正是魏晋名士孤傲清高、超凡脱俗心态的生动的彰显。“乘化”,顺随大自然的运转变化。“尽”,生命的尽头。诗人终于醒悟:生命在世上又能有多长时间呢?何不遵从真实的内心,听任其自然地生死?为什么还心神不宁,又要去往何处?世俗的富贵荣华不是我所追求的,那虚无飘渺的仙界幻境我又无法企及。既然这样,那就不要辜负大自然的美好,尽情地流连欣赏吧;田园到了该耕作的时候,还是要去除除草,松松土,培培苗。登上东边的高冈,眺望四方,心旷神怡,放声长啸;徜徉于清澈的溪水边,诗兴不可遏制。姑且順随着生命的自然变化终了余生吧,乐天知命,又有什么还值得顾虑犹豫呢?在诗歌最后一小节中,诗人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憧憬,上升到对生命的自觉关照与反思。
有人喜欢把这篇辞赋看作诗人归去的宣言,其实诗人的文字没有那么铿锵有力。诗人在复杂纠缠的情绪里归去,这显然是有着深深的无奈和矛盾的。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不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诗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经过艰辛的挣扎和苦苦的彷徨,诗人的思想境界因此得以提升,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将生命放归自然之中。
这篇辞赋构思极其精巧,到了我们都怀疑这是否是诗人刻意为之的地步:诗人是故意要从感性到理性地诉说自己的艰难归去,还是我们的诗人就是自然而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这是怎样的鬼神功夫,才会有着这样天然自成的抒情?从表象的归去快乐,到理性的生命认知,从外在的叙事想象,到内在的真情抒发,激动与喜悦,挣扎和彷徨的情绪贯穿始终,就这样天衣无缝,水到渠成融合为一篇精妙的文字。而事实上此文更多的只是凭借它的思想深度震撼和征服着一代代的读者们。
参考文献:
[1]杨丽伟执教. 在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间痛苦挣扎——《归去来兮辞并序》课例研究[J]. 语文教学通讯:高中(A), 2012, 000(003):15-17.
[2]张玉平. 试论古文教学中情景交融之探究与迁移——以陶渊明辞赋《归去来兮辞并序》为例[J]. 当代教育论坛, 2010, 000(009):6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