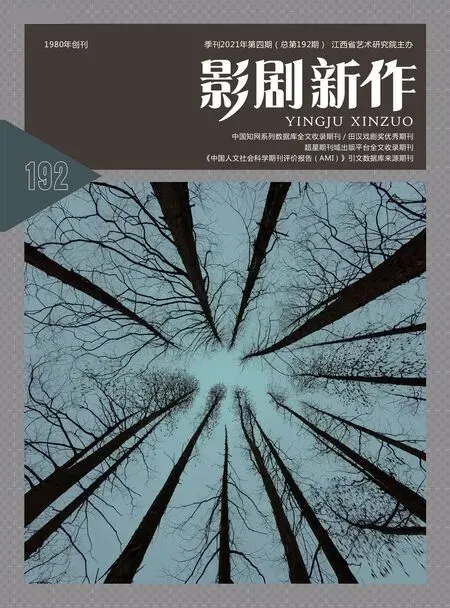主角立得住 配角有妙用
——评小剧场京剧《一蓑烟雨》
邢欣欣
小剧场京剧《一蓑烟雨》(编剧、导演白爱莲)作为第七届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佳作之一,于北京繁星戏剧村上演。该戏侧重表现苏轼的思想转变,成功塑造了一位由儒向佛、进而向道的苏东坡。无论从历史还是艺术的角度看,苏轼这一形象都立得住。该戏的另一亮点便是小配角有大妙用——巧用丑、旦配角以增添戏的趣味性、推动戏剧情节发展、增强舞台表现力等。作为一部新编戏,小剧场京剧《一蓑烟雨》主角立得住、配角有妙用,对当代小剧场与文人戏的创作具有借鉴意义。
苏轼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少负盛名,意气风发,名动公卿。后因“乌台诗案”落狱,命悬一线。劫后余生被贬黄州,入不敷出,便开垦荒地亲自耕耘补贴家用,自称“东坡居士”。后被起用又两次被贬。苏轼曾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正是他三次被贬发配之地,苏轼将三地戏称为自己的平生功业,个中滋味,三分戏谑,三分凄凉,四分洒脱,耐人寻味。苏轼颇具戏剧性的坎坷生平被搬演到戏曲舞台。元杂剧“东坡戏”有《花间四友东坡梦》《苏子瞻风雪贬黄州》《苏子瞻醉写赤壁赋》《苏东坡夜宴西湖梦》《佛印烧猪待子瞻》《苏东坡误入佛寺游》。遗憾的是,在当代戏曲舞台上,“东坡戏”不常见了。小剧场京剧《一蓑烟雨》从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东坡戏”的舞台空白,上演后便受到关注。
“东坡戏”的创作有一定难度。苏东坡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生平事迹多有史可据,但他的知名度也使创作变得棘手,戏说比史实多一分便不够庄重,少一分则显得沉闷,观众都不会买账。且作为文人戏,“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小剧场京剧《一蓑烟雨》如何把握虚与实之间的微妙平衡,如何规避文人戏的沉闷迂腐,如何做到“深入情思,文质互见”?观众带着上述疑问和审美期待进入剧场。值得欣慰的是,小剧场京剧《一蓑烟雨》巧妙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关于苏东坡的重要戏剧情节取自史书记载,唱词多化用苏东坡诗词歌赋,此为实;将戏聚焦于苏东坡的内心层面,想象其生平留白部分,合理加工史实的细节,此为虚;而戏的趣味性则借助配角实现,既中和了文人戏的乏味,又不会亵渎苏东坡的文人形象。
该戏立足于苏轼真实生平经历,遥想了苏轼“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的三个夜晚。这三个夜晚,有酒、有诗、有朋友,还有不期而遇的自己。一直平步青云的苏轼突然遭此横祸,身处坎坷之中,思想受到巨大冲击而发生变化。戏中没有突出外化的戏剧冲突,而是聚焦于苏轼心境的变化和思想的嬗变。对于苏轼心境、思想的表现,三场戏各有侧重,分别以借酒买醉、假死戏人、对话过去和未来的自己等,表现出苏轼由儒家仕途失意的苦闷转向佛家笑看生死的释然、再转向道家恣意行吟的洒脱,向观众展现了一个鲜活立体的苏轼。
第一场《藏》,苏轼因“乌台诗案”受挫,便将心事深藏于内,要求自己不念不言。听到酒馆说书先生讲述自己被贬遭遇,往事钩沉,悲从中来,难以自持,遂在酒馆买醉。“酒楼买醉”±一段戏,显见对京剧《问樵闹府》程式动作的化用,表现了苏东坡遭陷害被贬谪的落拓失意、忠君爱民却报国无门的困苦无奈。此处的苏轼沉浸在儒家思想中难以排遣。
苏轼生平与高僧佛印过往甚密,也常与僧人一起参禅悟道,佛家思想在其思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二场《嬉》,苏轼一出场便表明自己无聊困顿之际打坐念佛参悟生死,“洒扫拂尘理书案,闭阁关窗别有天。一念清净学陶潜,稳坐蒲团我把生死参。”之后一段唱词流露心境,“此时间虽暂得安稳,到底心意难平。为求自新,焚香打坐,深自省察,以求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所谓一念清净,烈焰成池也。”最后甚至“问佛祖该如何换骨脱胎”。参禅未罢,朝云前来,苏东坡突发奇想,与侍妾朝云串通以假死戏人,嬉笑生死,最后因朋友侍妾一句话而顿悟——“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儒家不参生死,不事鬼神;道家潇洒恣意,不念生死;只有佛家参生死,讲因果,信来世。苏轼“此心安处,便是吾乡”的顿悟,也正是佛教禅宗的法门。
第三场《行》,苏轼面对人生的困境,该何去何从?纵酒避世吗?“纵酒避世,不失自在。然,非我之道,我酒量不行。”仿效陶渊明避世?“我实在无有辞官之心呀!”学李白清高吗?“太白乃谪仙,而我在人间。”黄庭坚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戏中苏东坡一一否定了上述三种选择,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蓑烟雨任平生。最后,老、中、少三位苏轼不期而遇,同行场上,且行且歌,不悲不喜,超然物外,尽显道家无为逍遥姿态。正如词中所写“人间有味是清欢” “一蓑烟雨任平生”,至此,苏轼的思想、心境完成转变,苏轼也成为了苏东坡。
小剧场京剧《一蓑烟雨》的成功,不仅在于塑造的主角苏东坡人物形象立得住,还在于配角亦蕴巧思,亦有妙用。鉴于小剧场的灵活性,小剧场戏曲可以实现与观众的良好互动。酒保、朝云分别以丑角和花旦应工,两个角色包揽了戏中的插科打诨、嬉笑怒骂,偶尔打背躬蹦出几句流行语、俏皮话,极大地避免了整部戏偏向文人气的沉闷压抑,又不至于使舞台向观众过度开放,带给了观众极好的观感体验。与大剧场戏曲相比,小剧场戏曲一般时长较短,行当角色较少。囿于小剧场戏曲的规制,在处理戏中众多人物时,该戏另辟蹊径,以工丑行的焦敬阁一人分饰多角和花旦应工的朝云为吊唁宾客代言的方式来实现。丑角焦敬阁分别扮演酒馆酒保、说书人和老年之身的苏轼,并且说书人还要表演皇帝、大臣、阎王、酒鬼等书中人。侍妾朝云是苏轼“活出殡”的重要助手,也是吊唁宾客的代言人。不需吊唁宾客一一现身,只借朝云之口,观众脑海中便浮现众人悲戚状。亦可知,吊唁者少有达官显贵,多是平民百姓,有平日里与苏东坡有交集的田西老伯、渔翁、砍柴老丈、放羊倌,还有苏东坡救助的育婴堂孩子。前来吊唁的百姓对苏轼敬重爱戴,侧面表现了苏轼的勤政爱民。
丑行的设置丰富了该戏行当,推动故事的发展。戏中,青年苏轼、中年苏东坡分别是生行的小生、老生,侍妾朝云是旦行的花旦,焦敬阁扮演的酒保、说书人、老年苏轼等则是丑行。同时,焦敬阁以丑行应工的众多角色也推动戏剧情节发展。说书人讲演苏轼乌台诗案,勾起苏轼的心酸往事,直接促使苏轼饮酒买醉,进而有后续剧情;身后之身的老年苏轼间接促进了苏东坡在心态上的转变。老年苏轼来到苏东坡身边,并告知其身后之事:“你过世后,蔡京当道,皇上昏庸,一纸禁令,你的文章书稿,都要焚毁,你的丹青书画,也都要烧掉。你写下的碑文,砸了。你题写的匾额,烧了。换了上那蔡京蔡大人的……但凡民间私藏苏学士诗词文章刻印书稿的,一律问罪。”既知后事如此,苏东坡的情绪由悲愤转为释然,并称“身后之事如何管得,只求生前无愧”,并表示坚信“公道自在人心”,由此,苏轼方实现由儒向佛、进而向道的进一步转变,才成就了后面剧情中三人偕行吟唱《定风波》的潇洒恣意。
该戏也有美中不足之处。最后一场,三个风格迥异的苏轼同行于台上,虽然新颖别致的形式凝聚了主创团队的巧思深意,但是,于苏东坡人物形象塑造和主旨立意表达而言,似乎并不是加分项。纵使苏轼在不同年龄段、不同际遇下,外在容貌体态与内在精神气度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形体样貌、精神状态等相去甚远的三人同行于场上,仍有碍于苏东坡的人物形象的统一性,甚至产生割裂之感。实际上,这场戏由苏东坡一人在舞台上且行且吟,也可达到同等表达效果,且独角戏更能展示演员实力,为该戏加分。另外,利用检场人舞扇表现宋朝文雅气质,构思虽巧妙,但过于抽象,于一般观众而言,未必能明白其中奥义。当然,瑕不掩瑜,小剧场京剧《一蓑烟雨》仍不失为一部成功的小剧场戏曲作品,彰显出当代小剧场戏曲的风采,为当代小剧场创作和文人戏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应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小剧场京剧《一蓑烟雨》第一场《藏》哀而不伤,第二场《嬉》乐而不淫,第三场《行》不悲不喜。悲喜之间,尽显悲喜交加的人生况味,处处体现苏东坡的处世哲学。于当今社会,这套处世哲学也有积极意义。小剧场京剧《一蓑烟雨》就像一抹月光,照进时人缺乏诗意的生活;似一捧清泉,流进今人浮躁意难平的内心。观戏后,不免驻足审视自己的内心,此心安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