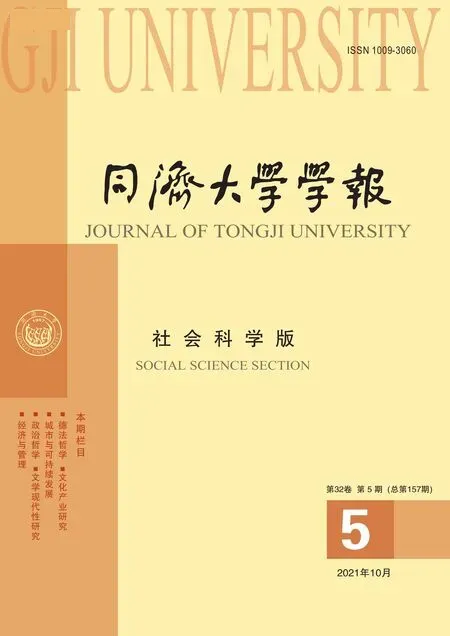“爱邻如己”是可能的吗?
——拉康视角下的邻人问题与主体的伦理
李 锋
(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文理学部, 上海 201209)
耶稣将旧约的诫命归纳为爱上帝与爱邻人(1)参见《圣经》中文标准译本 (CSBS),《马太福音》第22章第36-40节,第7章第12节。,“爱邻如己”作为基督徒奉行的道德金律,在西方传统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影响波及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对它的怀疑也从未停息过,我们在尼采和弗洛伊德这两位现代思想的怀疑大师那里就遇到了对“爱邻如己”的强烈质疑。
尼采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讲道:“你们忙着交好你们的邻人,你们为着这个使用美丽的词句。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爱邻,只是你们的错误的自爱。”“你们不能忍受自己,你们不十分疼爱自己:所以你们想用爱去诱惑邻人,而以他的错误自饰。”(2)尼采: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尹溟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第63页。
尼采在这里谈到了对邻人的爱是“错误的自爱”导致的,人由于不能忍受自己,所以要逃避到邻人之爱中。尼采这一洞见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看到“爱邻如己”这一伦理律令和人的主体性的构成密切相关,爱邻人有可能是一种“症状”,是由于错误的自爱导致的。
同样,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面对这一律令也表现出“无法抑制的惊讶和困惑”:“这怎么可能呢? 我的爱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东西,我无法不假思索地把它抛弃。……经过更为细致的考察,我还发现了更多的困难。这个陌生人不仅在总体上不值得我的爱,我必须坦承,他更值得我对他抱有更多的敌意,甚至仇恨。他对我没有丝毫爱的迹象,对我丝毫不予考虑。假如伤害我的行为能给他带来什么利益,他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他越是觉得安全,我越是觉得无助,那么我就越肯定地预料他会对我采取这样的行为。”(3)弗洛伊德: 《一种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 严志军、张沫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第96 页。
对“爱邻如己”这一伦理律令的质疑,我们可以看到在尼采那里质疑的焦点是自我,在弗洛伊德那里则是邻人,是邻人的可能的邪恶使得“爱邻如己”难以实行,于是对这一伦理律令的质疑可以追溯到以下基本的问题:如何理解人的自我? 谁是“我”的邻人? 两者之间的爱是如何可能的?
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一伦理命令的深入理解需要重新思考主体与彼者的关系的原初经验,以及通过参考一种有足够解释力的主体理论来反思这一伦理律令在不同的主体与彼者的关系模式中的具体内涵,否则对这一伦理命令的讨论就会流于空洞而变成单纯的赞同或否定的教条之争,无法挖掘出它真正的伦理意义。在我看来,拉康基于他的精神分析的临床经验所建构的主体理论恰恰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视角,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基督教这一伦理命令的意义及其可能的盲点。
一、 作为相似者的邻人与自恋的快乐
《马太福音》对这一伦理律令解释道: “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4)参见《圣经》中文标准译本 (CSBS),《马太福音》第22章第36-40节,第7章第12节。我们看到这一伦理命令的核心在于一种对称关系——你要别人怎么对待你,你也要怎么对待别人。精神分析对爱的思考是从对象关系出发的,也即是从主体与对象的力比多(libido)(5)力比多(Libido)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是心理性欲能量的代表。投注关系来思考人的爱的经验。对于主体和彼者之间的这种基于对称关系的爱,拉康用想象界的镜像关系来加以解释,因为这种爱的经验一直可以追溯到幼儿镜子阶段的自我形成的时刻。
我们都知道,拉康的镜像阶段的概念最初来自法国心理学家亨利·瓦隆(Henri Wallon)关于幼儿心理学研究中的“镜像实验” 。瓦隆观察到:大约从六个月起,人类的幼儿和大猩猩都可以认出镜子中反射的图像,但是大猩猩很快就丧失兴趣去干别的了,但人类的幼儿则不同,他会被这个图像深深吸引,以至于会有某种欢呼雀跃的狂喜的情感表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根本的差异呢?
拉康认为,这是由于人类个体在出生时带有根本的未成熟性,从一开始就存在与环境原初的不一致、不和谐,正是这种不一致的缺口才是图像的功能要去填补的。也就是说,当幼儿身体各个部分的运动机能并不能很好地协调一致的时候,在镜子中的一个外在于他的图像恰恰提供了一个整合的图式来帮助他达到某种统一感,进而形成他最初的自我。幼儿对镜像作为一个彼者的再认过程,正是他的“我”形成的时刻,也是他克服身体的支离破碎感,获得统一感的欢呼雀跃、狂喜的时刻。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人的主体就和彼者纠缠在一起,没有那个镜子中作为相似者的“彼”,也就没有主体的“我”,而且“我”对自己的镜像深深地迷恋,“我”爱这个具有相似性的“彼者”,这个最初的“邻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的“爱邻如己”的律令可以在人的自我形成的最初时刻找到它的心理学基础,这一伦理命令之所以对人类得以可能有它的心理学层面的根源。
孩子不但和镜子里自己的图像构成镜像关系,他和自己的母亲依然构成一种镜像关系。母亲是孩子理解这个世界的窗口,是他经验这个世界的一面镜子。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弗洛伊德的自恋理论的发展。在《自恋导论》中,弗洛伊德已经提出,“人只有两个原初对象:他自己和照顾他的女人”(6)S. Freud, “Pour introduire le narcissisme”, La vie sexuelle, PUF, 1997, p.94.。也就是说,从利比多投注的角度来说,人最初的对象关系也就是投注对象的选择带有自恋的性质,孩子被母亲作为自己身体的延伸,而孩子也认为母亲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母亲和孩子之间是一个融合的关系,而并没有清楚地区别开来。这个阶段的母子关系被人们赋予了很多理想化的色彩,比如母亲对孩子忘我的爱、孩子对母亲无条件的信赖,这似乎突破了人与人关系中常见的自我主义和利己倾向。
但拉康恰恰在镜像关系中看到了利他主义和同情心的起源(7)J. Lacan,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9—1960), Seuil, 1986, p.230.:“事实上,所有那些基于相似者的他人的图像,那些和我们的自我具有相似性的以及所有把我们置于想象界的事物,都与我们密切相关。我在这里作为问题提出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爱邻如己这一伦理律令的基础?”(8)J. Lacan,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9—1960), Seuil, 1986, p.230.
我们看到,在拉康那里,“爱邻如己”中的邻人首先指的就是“我”的相似者,只有相似者才能在镜像关系中维持一个利比多的投注,因为“我”在彼者身上发现了自我的理想,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发展出一种理想认同的关系,也就是一种爱的关系。这个意义上的爱,拉康在他的L图式中用镜像轴来加以解释,我们下面会进一步加以讨论。事实上,从反面来说,我们从历史上基督教对异教的不宽容、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的迫害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正是这个提倡“爱邻如己”的宗教表现出对异教徒极端地不宽容,这恰恰是因为异教徒作为不相似者并没有被作为邻人,从而也不需要被爱。
二、 作为陌生者的邻人与大彼者的享乐
邻人不只是相似者,我们在弗洛伊德对基督教的“爱邻如己”的律令的质疑中已经看到,这个邻人更可能对“我”充满敌意甚至恶意,“对我丝毫没有爱的迹象”,“如果他能从中满足任何欲望,他就会无所顾忌地嘲笑我、侮辱我、诽谤我,显示他的优势”。在此我们面对的恰恰是邻人根本的异质性、陌生性,而这一点在思考“爱邻如己”的伦理命令时是不能忽略的。
事实上,弗洛伊德在1895年《科学心理学大纲》讨论孩子的知觉经验时,已经讨论了邻人的陌生性的问题。孩子来到世界,知觉到的第一个邻人是他的母亲,但对她的知觉经验已经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那些能被归于自身的身体经验的信息,也就是依据我自身的经验的图像,能够在他人身上认出和再认的元素; 另一部分则是物(la Chose)本身,也即是说未知的、不能被表象的、一个无法进入的空洞,它由一个恒定的结构所强加,作为物本身而被保留。”(9)P. Julien, L’étrange jouissance du prochain, Seuil, 1995, p.147.
我们可以说,孩子此时经验到的母亲不再只是作为相似者的母亲,而是作为“物”本身,作为具有根本相异性(altérité )的母亲,也就是说母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的镜像关系,即便孩子很小,他依然可以感觉到在母亲那里有某种未知的、神秘的东西是超出他的理解范围的。
关于“我”与“彼者”的关系, 拉康在L图(见图1)中有更清晰的思考,这个图式(10)J. Lacan, Le Moi dans la théorie de Freud et la technique de la psychanalyse, Seuil, 1978, p.284.拉康在他的第二个讨论班也就是《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与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中首次提出,是为了思考“自我与彼者、语言与话语所提出的问题”(11)J. Lacan, Le Moi dans la théorie de Freud et la technique de la psychanalyse, Seuil, 1978, p.284.。

图1 L图式
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维度的存在对“我”与“彼者”的关系的影响。我们看到拉康在这个图式中区分了主体与自我、小彼者(autre)与大彼者(Autre)的不同,“我”可以分别占据主体和自我的位置,“彼者”也可以分别处于小彼者和大彼者的位置,于是原先的母子二元关系现在变成了由四个元素构成的结构。也即是孩子和母亲的关系现在被放置在由四个元素构成的结构中加以思考,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母子的镜像关系要放在自我(moi)—小彼者(autre)的镜像关系的维度中加以思考,母亲这个时候是作为小彼者出现的,对于这种镜像关系,拉康在上述图式中用a—a’加以描述,因为“这种形式的彼者与自我有最紧密的关系,是可以叠加的,所以我们就用a’表示”(12)J. Lacan, Le Moi dans la théorie de Freud et la technique de la psychanalyse, Seuil, 1978, p.285., “于是就有了镜子的平面,以及自我和相似的彼者构成的对称世界”(13)J. Lacan, Le Moi dans la théorie de Freud et la technique de la psychanalyse, Seuil, 1978, p.285.。
但这种镜像关系并不是母子关系的全部,因为母亲不单单是母亲,她更是一个女人,当她朝向父亲而离开孩子时,她的欲望对孩子来说就变成了不可理解的。孩子会问一个问题:她到底想要什么?母亲这个时候就以大彼者的形象出现,她对孩子所代表的就是一种相异性、具有根本陌生性的存在,拉康把这种关系放在主体(Sujet)—大彼者(Autre)维度加以思考。
正是在这个维度上,精神分析破除了母爱的神秘化,而看到了母子关系中潜藏的危险,特别是当一个母亲完全把孩子当成自己的身体的延伸,从而以一种倒错的态度对待孩子时,这里面牵涉到的就不再是自恋的享乐,而是一种享乐的意志(volonté de jouissance)。这时的母亲对孩子有可怕的权力,面对一个无助的、完全依赖于她的孩子,母亲代表的是一种可怕的令人窒息的力量,拉康把这样的母亲形象地描述为“鳄鱼母亲”(la mère crocodile),他强调了母亲欲望的有害维度:“母亲的角色,这就是母亲的欲望。这一点是很关键的。母亲的欲望不是某种与你无关的东西一样可以被人们所承受。 它总是带来有害的后果。一个巨大的鳄鱼,你就在它的嘴巴里,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母亲的形象。人们不知道谁可以突然抓住它,把它的嘴巴关上。母亲的欲望就是这个。”(14)J. Lacan, L’envers de la psychanalyse, Seuil, 1991, p.129.
如果母亲把孩子作为她对菲勒斯(Phallus)欲望的换喻对象,而孩子也填补了母亲的缺失,这样的话,孩子就完全被捕获在母亲的欲望之网中,成为母亲的享乐客体,就像一个鳄鱼张开嘴巴把孩子吞下去一样。它带来的后果是孩子会出现各种心理症状,甚至有导向精神病的可能。
同样关于邻人以大彼者的形象出现的问题,拉康在第七个讨论班《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提到了基督教的圣马丁(Saint Martin)的例子。当圣马丁在街上遇到一个赤身的乞丐时,他把自己的衣服一分为二,给那个乞丐遮体,这在基督教传统中被认为是邻人之爱的经典例子,但是拉康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当涉及物质需要时,没有问题,我们和他人是一样的。 圣马丁和别人分享了他的衣服,人们从中得到了很多。但是这只是一个供应的问题,衣物被做出来就是为了使用的,无论给他人还是给自己都是类似的。无疑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一个需要被满足的原始需要,因为乞丐是裸体的。但是很可能,乞丐除了需要穿衣服之外,他还乞求别的东西,比如让圣马丁杀了他或者和他做爱。这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一个和邻人的相遇中,行善的回应和爱的回应是完全不同的。”(15)J. Lacan,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9—1960), Seuil, 1986, p.219.
拉康无疑在这里对圣马丁的行善之举做了非常另类的解读。他要让我们看到的是:邻人对我们所要的,并不是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提供的。“我”与邻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称关系,用拉康的L图来解释的话,就不是自我(moi)—小彼者(autre)的想象关系。特别是在爱欲关系中,人们碰到的更可能是具有根本相异性,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具有“深深的恶意”的邻人,也就是处于L图中大彼者的位置的邻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邻人之爱意味着什么呢? 在拉康解释的圣马丁的例子中,是要满足乞丐的“乞求”而陷入一种暴力或者色情的关系中吗? 当陷入一种大彼者享乐的关系中时,任何可能的人性关系还存在吗?
通过上述两个邻人作为大彼者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们面对的是超越镜像关系,超越相似性原则,进而超越了快乐原则所能解释的范围,而进入到拉康称为享乐(jouissance)(16)享乐在拉康那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首先要区别于快乐,享乐是对快乐原则的违反,它所涉及的是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以死冲动概念所描述的大量的临床现象,其中表现出享乐的悖论特征:一方面它是一种满足,另一方面正如拉康所说,“享乐是一种痛苦”。的领域。在此我们面对的是邻人根本的相异性,在这个维度,基督教的“爱邻如己”律令遇到了根本的困境:当这个邻人对“我”要求的不是“善”而是“恶”,不是“快乐”而是“享乐”,不是可以分享的利益,而是完全的剥夺时,“爱邻如己”还是可能的吗? 这种“爱”意味着什么,它又是真正可欲的吗? 所有这些都成了问题。
三、 主体构成的外在性——谁是最近的邻人?
由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对基督教“爱邻如己”的伦理命令的质疑,拉康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一伦理命令本身的否定。拉康进一步提出“谁是‘我’最近的邻人”这一问题,将我们的目光从对外在的他者的思考转向对主体性构成本身的思考。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打开了对“爱邻如己”这一伦理命令进行全新的阐释的可能性。
由上述的L图我们能看到,主体和彼者是深度关联的。从人作为主体诞生在这个世界起,由于人诞生时的未成熟性,他不得不依赖于一个彼者,通常情况下是母亲扮演了这个史前大彼者(Autre préhistoire)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拓扑图形来描述主体的构成,就不能是一个球形,虽然球形在希腊哲学中代表的是完备、完满的最高形式,但是精神分析视角下的主体离这样的图式是最远的。拉康在他后期理论中,借助于拓扑学的工具,用两个交叉的环面(17)Jo⊇l Dor, 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Lacan, Tome II, Deno⊇l, 1985, p.152.(见图2)来代表主体与彼者:

图2 交叉的环面
在这个图中,我们能看到,左边代表主体的环面,其中心是空的,同时这个中空部分是被大彼者代表的环面所占据的。如何理解这个拓扑图式,我们可以从两个简单的问题出发略做讨论。
首先,为什么代表主体的环面中心是空的呢?
我们可以说,环面中心的空,代表的是“物”(la Chose)与主体的分离。主体的诞生是和语言的介入以及词对“物”的谋杀相联系的,自此“物”变成了一个被禁止的、一个不可接触的对象,用拉康的术语来说就是一个不可能的对象。由于它无法被表象,拉康就用空(vide)来代表,而主体的精神系统的建构是围绕着这个最初的缺失、围绕这个空来进行的,这是拉康对主体构成性的思考的一个基本观点。人的存在也因此被拉康界定为“缺在”(manque à être),而人的欲望作为不断追寻欲望对象而不可能真正得到满足的过程,正是这种“缺在”的换喻表达形式。
这个“空”的地点,这个代表原“物”的地点,也可以说是代表“我”自身享乐的地点。但是这种享乐不但对自身而且对于他人都是有害的,所以人通常都是通过各种防御机制远离这个“空”的点,完全靠近这个点正意味着主体自身的死亡。然而拉康却同时告诉我们,这一享乐的部分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每当弗洛伊德在爱邻如己的伦理律令的后果前停下并被震惊到时,他所看到的是在邻人那里出现的深深的恶意。但是那样的话,这种恶意同样也会存在于‘我’自己身上。还有什么是比‘我’自己身上的享乐的部分更为邻近的呢?对这种享乐,‘我’也害怕靠近。因为只要‘我’靠近它时——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的意义显现出来,一种可怕的攻击性呈现出来,在它面前,‘我’不得不后退,并将这种攻击性导向自己,正是在律法消失的位置上,它显示了自身的力量,特别是在于阻止‘我’逾越限制抵达‘物’的边界上表现出来。”(18)J. Lacan,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9—1960), Seuil, 1986, p.219.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上述图式中两个环面要交叉呢?
拉康借此想表明,彼者在主体自身的构成中占有核心的位置,也即是构成主体核心的最内在的部分,恰恰是外在的,依靠于彼者的。我们都知道拉康的名言,“人的欲望是大彼者的欲望”,在人那里并没有一种独立的、只属于主体自身的欲望,所有的欲望分析到最后都是彼者的欲望。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拉康关于主体思考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视角——主体的外在的亲密性(extimité),也就是说恰恰是在主体最内在(intimité)的部分,我们看到了它根本的外在性。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地点已经不能清楚分辨彼与此了,正如拉康所说,“比‘自我’本身更是自己的部分,构成了‘自我’的核心,并且超越了‘自我’……而这个内在,这种空,我已经不知道它是‘我’的还是他人的”(19)J. Lacan,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9—1960), Seuil, 1986, p.233; p.85; p.217.。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问的是:如果在“我”身上同样存在着一个彼者,这样一个彼者难道不是最近的邻人吗?“爱邻如己”的伦理律令难道不应该同样适用于它吗? 但是现在问题就变成了:当面对“我”自己身上这样一个彼者时,这样一个离我最近的“邻人”时,“爱邻如己”是否还是可能的?更进一步它是否是可欲的呢? 难道不正是因为它所包含的巨大的危险,人们才退却的吗,就像拉康在上文中分析的那样?
四、 面对邻人的陌生,一种伦理是如何可能的?
无疑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去避开这个每个主体身上都存在的具有根本异质性的部分,这一部分对人性而言是难以承受的。事实上神经症的各种症状也可以看作是对它的防御反应,弗洛伊德讲的压抑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文明社会得以可能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一我们身上最近的“邻人”——主体自身的无意识——也是精神分析意义上构成主体的享乐的地点,对于这一地点,人们害怕靠近它,因为它不仅对主体自身有害,而且也对周围人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正如我们上面所讨论过的,在此人们进入的是超越快乐原则、超越镜像关系的领域,人们必然会碰到弗洛伊德在1919年的文章中用“异样的陌生”(unheimlich)的概念(20)Sigmund Freud, L’inquiétante étrangeté et autres essais, Folio essais, 1985.加以描写的现象:人们会碰到存在于每个主体身上的这一既熟悉又陌生的部分,或者说恰恰在原本熟悉的领域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陌生性,而这是每个主体的精神系统为了维持自身的平衡而不得不加以防御的。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人只能对我们身上最近的“邻人”——无意识——加以防御,从而通过压抑来解决冲突,或者换句话说,某种形式的神经症是不是每个主体不得不经历的命运呢?
主体构成的中心是“空”的,这意味着每个主体的诞生必然要经历与原初的“物”的分离,必然要经历原初压抑的过程。这也意味着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主体必然是无意识的主体、分裂的主体(sujet divisé)。完全没有压抑意味着这个环面的“空”不再存在,而主体也就不再存在了。恰恰由这个图式我们能看到的是,主体的精神构成不能够脱离这个处于核心中的“空”。这个“空”的位置,这个最初的“物”占据的位置对于主体来说具有最大的价值,就像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样,主体的精神机构也是围绕这个“物”构建的,完全远离“物”同样意味着主体的死亡。
应该说,我们在此碰到的是一个具有悖论性质的情景,主体构成的悖论情景,而这一悖论与“物”本身的暧昧状态密切相关。正如拉康在第七个讨论班《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分析亚里士多德的至善概念时所说的那样,在精神分析的视角下,原初的“物”代表了主体真正的至善(le Souverain Bien )(21)J. Lacan,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9—1960), Seuil, 1986, p.233; p.85; p.217.;但另一方面,拉康也明确地说,享乐是一种恶(22)J. Lacan,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9—1960), Seuil, 1986, p.233; p.85; p.217.,而“物”所在的位置对主体而言则意味着绝对的享乐,因而是根本的恶(le mal radical)。拉康在此是否自相矛盾呢? 当然不是。拉康在这个讨论班中围绕“物”讨论主体的构成,进而讨论精神分析的伦理时,他让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在这个主体身上具有根本异质性的部分,在这最近的“邻人”——无意识——那里,我们既碰到了真正的善的可能,也碰到了真正的恶的可能,也正是在这里,伦理的问题对主体而言才成为存在维度的根本问题。
神经症可以被看作对这一主体存在的困境的某种妥协的解决方式。也就是说,当神经症回避这一具有根本异质性的“邻人”——无意识时,他所采取的压抑机制虽然避免了自身的享乐可能造成的对他人的恶的发生,但与此同时,他也回避了可能的真正的善的展开。所有的心理症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心理能量的无用的耗费,神经症从而陷入某种心理冲突的内耗,陷入弗洛伊德所说的在爱与工作上的无能状态。
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一主体身上最近的“邻人”——无意识——恰恰构成了主体的存在最内在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是生命动力的源泉。如果采取神经症的策略,对此源泉采取压抑的态度,那么只能导致生命的枯萎。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神经症回避了“爱邻如己”的伦理命令,他不能去爱这样一个具有根本异质性的“邻人”。换句话说,神经症表达的不单单是症状维度的心理不适,而是存在论维度的伦理选择的失败。
“爱邻如己”这一伦理命令的真正意义,在拉康看来,恰恰在弗洛伊德的格言“它我所在之处,自我也要抵达”(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第31讲结束的部分讲道:“精神分析的治疗目的在于增强自我,使之更加独立于超我,拓宽它的知觉领域,扩大它的组织,以使它能够占有本我(23)“本我”这一翻译有使人以为存在一个原初的真我的倾向,建议翻译为“它我”,以突出这一心理装置的根本相异性。的新领域。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这是一种矫正性的工作——就像苏伊德海的排水一样。”(24)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3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第532页。
“它我”正是我们身上最近的邻人,它是我们的无意识,正是在这个领域,人们会碰到由于各自的人生经历的不同而标定了每个主体独特命运的能指链。在此,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见证了人的命运的无意识重复,无意识的本质就是重复,特别是当主体对自身的邻人——无意识——保持无知(ignorance)时,这种症状意义上的有害的重复就是不可避免的。
同样,精神分析的实践也见证了在治疗的框架下,借助与分析家(analyst)的移情关系,分析者(analysant)与自身的无意识这一最近的邻人重新接触得以成为可能。治疗的空间就代表了转化的空间,从而使得人摆脱重复并创造一种新的关系成为可能。在此,精神分析所理解的伦理才获得了它根本的意义:认识你自己,不要“向你的欲望屈服”(céder sur son désir)(25)J. Lacan,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9—1960), Seuil, 1986, p.368.。
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无意识构成了每个人身上的陌生部分,这非但不意味着对人的主体责任的豁免,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无意识的存在,主体才有责任去面对这种根本的相异性、根本的无知的维度。“爱邻如己”这一伦理命令的意义,在拉康看来就是面对主体身上这一最近的“邻人”,真正对自己的无意识负责。正如兰波所说,“我是一个彼者”,要去爱的,恰恰是这个具有相异性的“我”。“爱邻如己”促成的是这个作为彼者的、尚未到来的“我”的创造。
另一方面,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特别在爱情关系中,“爱邻如己”这一伦理命令的意义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拉康在第七个讨论班《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用骑士之爱(l’amour courtois)的例子描述了这一点。我们会看到,这一西方历史上非常特别的、被拉康称为出于诗歌的创造的爱情关系,是如何突破了在爱情关系中常见的自恋维度,而进入了一种与“物”的升华的关系中。
在爱情关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主体对于他人的爱,常常掩藏着对于自身的爱。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这是一种自恋型的对象选择的方式。也就是说,爱情关系中的“爱邻如己”在此表现为:一个恋人爱上一个彼者,只是因为在彼者那里找到了比他自身更理想的、更值得被爱的形象。
这是一种处于自恋维度的爱,“爱邻如己”意味着爱的是一个相似者,是另一个自己。但是由于自恋关系中必然内含一种攻击性,这种爱也常常会转变为一种恨,这也是人们常常在爱情关系中发现矛盾情感(ambivalence)的原因——人们深深爱的人和同样强烈恨的人常常是同一个人。
但拉康在中世纪骑士之爱的文化中发现了另一种爱情关系的形式。在西欧的封建时代,女性常常被作为婚姻经济的交换对象,结婚是为了财产、生育以及家族的延续。但是在骑士之爱中,贵妇却从被男性主导的对象,变成了一个主导男性的对象,成了他的女主人。骑士要对她真诚、专一、炽烈,并且他首先应该让自己值得他的女主人的爱,他有责任马上完成她的各种任意的愿望和命令,以此用全身心的奉献换取女主人点滴的馈赠。但这一爱情的追求并不导向婚姻,也不以导向性满足为目标,而是“把女人抬到一个纯洁无瑕的境界, 从而把一切肉欲的污点从她们的爱情中清除出去, 让爱情自由地翱翔, 上达精神领域”(26)但娜希尔:《历史中的性》, 光明日报出版社,童仁译,1989年, 第281页。。
骑士对于贵妇的爱被认为是一种强烈的欲望和最大的克制的结合,这一骑士之爱的特点恰恰在于它赋予了梦想中的女人一个不可能接近的位置。
在拉康看来,贵妇在骑士之爱中被置于“物”的位置上,占据着我们上面讨论过的环面的中空的位置,围绕她的诗歌、吟唱以及骑士之爱的各种仪式,则可以被看作是环绕这一中空的能指链。拉康强调能指(signifiant)出于无的创造力量(création ex nihilo)(27)J. Lacan,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9—1960), Seuil, 1986, p.147; p.133; p.134.在此显现了出来。在这个意义上,骑士之爱是一种诗性的创造,贵妇此时成了美的代表,她遮盖了“物”的不可表象性。她一方面构成了对骑士的强烈的吸引,另一方面则是如同“物”一般不可穿透、无法接近,只能作为远处的诗意存在而被向往。
关于升华,拉康在第七个讨论班《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定义:“它把一个对象提高到……‘物’的尊严的高度。”(28)J. Lacan,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9—1960), Seuil, 1986, p.147; p.133; p.134.升华在这个意义上重建了主体与原初的丧失的“物”的关系,打开并维持了一个欲望的空间,主体从而避免了神经症的压抑的命运。骑士之爱作为“升华的范例”,也代表了对自恋之爱的突破。女性从被欲望的想象的对象,来到了大彼者的空的位置上。在拉康看来,爱就是去爱那超越了显现的存在(un être au-delà de ce qu’il parat être)(29)Ricœur, Jean-Paul. “Lacan, l’amour”, Psychanalyse, 2007, 10(3), pp. 5-32.。在此意义上的爱,朝向的是彼者的存在(son être),而不是她的某种具体特质。
在这一视角下,“爱邻如己”的伦理命令就获得了新的意义。不是他人作为相似者才值得被爱,恰恰是他人身上的那个相异者,那个标定了主体的独特性的部分的“空”值得人们去爱,这种爱突破了自恋关系,进入一种升华的领域。
通过骑士之爱的例子,拉康让我们看到,骑士仰慕的并不是一个日常的女性对象、一个相似者,相反却是占据“物”的位置的大写的“女人”(La femme),后者在这个意义上处于具有根本相异性的大彼者的位置上,而恰恰在与这种彼者的相遇中,骑士放弃了简单的对象满足,与此同时一种独特的、更加丰富的爱情关系被创造了出来。虽然这一诞生于十二世纪法国南部行吟诗人传统的典雅爱情文化在历史上早已消失了,但拉康认为,“骑士之爱仍然在无意识中留下了痕迹,这一无意识被我们仍然栖身其中的一种文学、一种想象所支撑,特别在我们与女性的关系方面”(30)J. Lacan,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9—1960), Seuil, 1986, p.147; p.133; p.134.。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拉康这里探讨的伦理学是一种创造的伦理学,升华在他的伦理思考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因为恰恰是升华的途径才能面对“邻人”的陌生性与根本的相异性。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这种相异性不单表现在主体与他人的关系中,更表现在主体与自身的关系中。面对着这种相异性、陌生性不退却,而去创造一种与“邻人”的相处方式,去爱那无论在自己身上还是在彼者身上“超越了显现的存在”,这是“爱邻如己”这一基督教的伦理律令在精神分析伦理视角下呈现的基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