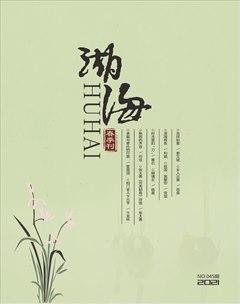承载与寄托的行旅
管国颂
阿根廷作家、批评家博尔赫斯不止一次和友人谈及诗歌的美好与价值,他认为,“诗就是人的一种永恒的需要”。诗作为精神层面的载体,凡有人的地方就有诗、凡有人群活动的场所就有歌吟。欢乐时,诗是兴奋的旋律,悲情时,诗是感伤的疗药。诗在我们前行的生活中,如同一场没有开始,也永远不会结束,承载故乡与寄托情怀的行旅,如痴如醉,如凌云之上穷尽想象的《月亮邮局》。
《月亮邮局》是张大勇的新作诗集,从草木盐蒿、季节春夏写到歌哭逝水、行游八方,最终,诗人还是把笔墨落到了故乡的家园。一个人一生能走多远,完全不在于他的双脚,比双脚更得力的应该是承载他思想情怀的灵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前辈诗人艾青如诗感叹,《月亮邮局》亦在探索中践行。“我有两个的自己/自从走进黄海森林公园/就像一座木屋之于我惊喜的眼睛/我对自己,有着/心旌摇曳的发现……我从一朵星光里找到谜底/我从一颗露珠打开履历/我在黄海森林公园里/自己打量自己,自己陪伴/自己/我的祖国,搂抱着黄海滩涂/黄海滩涂搂抱着一座森林/一座森林搂抱着木屋/一座木屋搂抱着我/我搂抱着另一个的自己……”两个自己,一小一大,家园和祖国构成了小我向大我跳跃的升华。诗歌的思想性,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为的排斥,或者说被一些人有意亦或无意间忽略不提了,似乎一强调诗歌的思想性就会弱化诗歌的艺术审美,这样的结果其实很可笑。老杜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耳熟能详,白居易同情《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诗句那样急迫,“诗言志”传统自古有之,丝毫也没有影响到流传的价值。当然,对于文学艺术,我们要的“诗言志”,绝不是空泛的说教,而是寓于文学形象的自然流露。“我是你两千余年的孩子,我是盐城/我的乳名叫盐渎啊/晶莹的盐粒是我的胎记你的图腾/我的母亲,我的黄海/在你海浪的摇篮里,我慢慢地成长/向东,向东,向着仙鹤丹顶一样上升的朝墩/你的慈爱在上升/我的心羽在上升……”其中表达的对故乡的情怀和承载的思想当然不言而喻。
张大勇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我把这样一个标签加到他身上似乎很容易,但要真正挖掘他,一个诗人身上与生俱来的气质及才情,不深入走进他的作品,注定还是虚无。在我认识的为数众多的诗人中,张大勇算是最少张扬的一个。多少年来,他默默地写、默默地发表,他给我的印象,似乎在任何场合,他大多属于一个“静”态的人。也惟其“静”,构成了他诗歌独有的“三维空间”。他写《平原上的树》:“我站着/平原无山无岳/一道道年轮,旋转着/大地的鼻息,运送到枝杪/观日出看霓彩/鸟巢留住白云,还有更高的风声/月光灌满天籁/传输下来,地气开始发发酵/描绿烟,擎花香/更多的道路从我身边走向远方……”体验平原上一棵树的感觉,站着,是一种静态,而在原点承受自然,祝福“更多的道路从我身边走向远方”,则是在静的空间装进了动的能量,诗意的升华顿时立显。他写《听雨亭》:“今夜,一座木亭只剩下听觉/只剩下我//长一声叫的是前世/短一声,按住微微上翘的飞檐/有若干古人路过/中空的剑鞘丢弃一地//有时,雨声是肉做的/有时,雨声是木质的/上阕不知有多远//就用一群烈马去追,左右挥鞭/三十里河东,三十里河西//九千根雨声织一袭蓑衣/我把自己扶上一声喷嚏/一座木亭带着根须迁徙”。诗人的想象力如此丰富,新旧今昔交错演绎的空间如此逼真,让本是静静听雨的木亭经历了历史的穿越后,有了新生的可能。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和人、人和事、人和时间与空间永远分割不开。空间和时间存在于现实世界,也决定了诗歌的空灵与隽美,可以说,没有空间的诗歌是僵直呆板的,没有时间的诗歌,亦如一潭死水,无从去谈论清新。同样,诗人在《静观》里让“街道上的行人,各行其事/世相在日光的花枝上兀自舒展//他的身影把时间拉成悠缓的小溪/一位妇人一根手绳一只宠物狗/排成了线性又有点奢大的队形/白头发的老奶奶在垃圾桶里翻捡//一位小男孩逮住了我的注视/他冲着我,也冲着生活/扮了一个鬼脸”,这些画面的依次呈现,让一些事物出现又消失,诗歌所以能以鲜活的方式记录某个瞬间,完全取决于诗人自身的体验与情感的容量,归根结底,也是衡量一个诗人独到的发现能力,它与技巧无关。
英国作家毛姆曾经说过,“为艺术而艺术不会比为喝酒而喝酒更有意义。”可以说,多年的诗歌写作,让大勇有了突破为诗歌而诗歌的能力,读他《月亮邮局》,在他更多隐忍角力的背后,任何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的诗歌,因为表达的强大,所以诗的张力在诗行中就有了极大的释放空间。他“用洁白的白说话/用芬芳的芳说话/《诗经》的音质/民歌的腔调/五月的耳朵 苏北的耳朵/我的平原張开一副俏丽的嘴巴”,洁白的白、《诗经》的音质、民歌的腔调,最直白的用语,最大气的语境,表达起来干净利索却意境隽永。真的诗和真的人一样,以一颗率真的心拥抱生活,高举思想的火炬,把梦照进现实,以激情燃烧未来之路,那样的《回忆》才至真、至美!“烟花,是灰烬长出的树/灰烬的余生抱着烟花的余温”,回忆以烟花开题,有“怔楞与张皇”,但更多的还是需要“打开一坛封存的酒,舀一勺子的沸腾”,人生匆匆,只要敢于面对,回忆就有了温暖。”让所有的翅膀/都开成铲子的形状/在虚无举起的半空中/我们的鸽子正在翻炒着阳光//阳光越来越熟/带着桔黄色的馥郁/在精神与物质的交界处漫漶/斟满一个又一个仰望//飞升的鸽群/翅翼粘着的阳光油亮油亮/一闪一闪的,像神祇的眸子/阅看低低的烟气和人间//时光咕咕地说着箴言/平民的鸽子,娴熟地/在自己的能动之中飞翔”。没有任何的华丽装饰,一切在不急不缓中进行,思考隐在深处, 感觉读着这样的诗就等于读着诗人深藏于心的梦境与现实,我们知道了,人世间有很多错综的纠结需要破解,因为惜字如金,所以我们才选择了以诗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心中的灯盏、吟唱与萤火虫,我们在诗歌中充分表达的修辞和意象,也许同故乡的风一样,普遍湿润温和、质朴平实,即使那些欲言又止的沉默、迷茫和忧愁,也散发着月亮的清辉,执念于自己与内心世界的和解。
合上这本张大勇的《月亮邮局》诗集,我想起,在我所有的诗歌评论中,我曾经无数次设想过经典诗歌的写作样式,并想以此为借鉴做个系统性梳理,这一次依然没有成功,可能根本就没有成功的胜算。诗歌多样化的写作,以及诗人“这一个”个体对于世界、对于人生的体验,永远不会是一种范式,这一点,在张大勇的《月亮邮局》诗集里,再一次得到印证。
还是要感谢狄金森的诗句:“为我的夜晚骄傲,因为你用月亮使夜平缓……”《月亮邮局》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