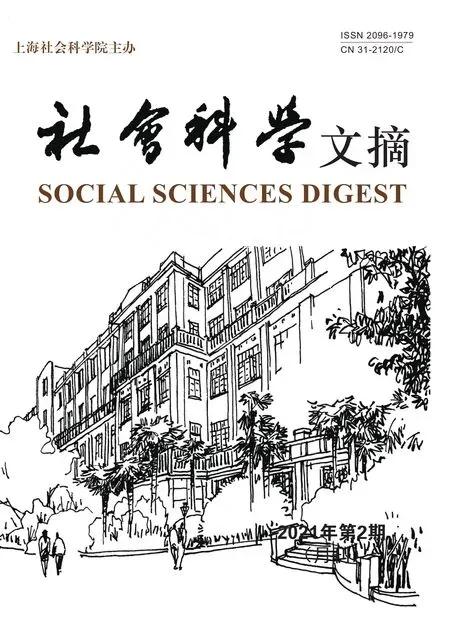增设新罪的原则
文/张明楷
当今社会发展变化迅速,“日常生活的浪潮(Wellen)将新的犯罪现象冲刷到了立法者脚前”;“我们的社会不得不比以前更加依赖于刑罚”。试图以各种理由阻止犯罪化进程的观点,显然不合时宜,因而不可能被立法机关采纳。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立法机关已经通过了10个《刑法修正案》,这些修正案都以增设新罪为主要内容。《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也是如此。但是,增设新罪必须贯彻必要性、类型性、明确性、协调性的原则。
必要性原则的贯彻
如果某种行为完全能够按照现有刑法规定处理,或者这种行为极为罕见,就没有必要增设新罪。反过来说,只有当某种法益侵害行为具有一般预防的必要性,而且根据现行刑法不能以犯罪论处时,才需要增设新罪。
(一)已有规定的情形
首先,既然某种行为按现行刑法能够得到处理,就表明这种行为已经是犯罪行为。如果现行刑法对这种行为的处罚过重或者过轻,就只需要修改法定刑,而不需要增设新罪。其中的所谓按现行刑法能够得到处理,不只是按现行刑法分则能够得到处理,而且包括按现行刑法总则能够得到处理。《草案》增设的部分条款并无必要性。例如,《草案》第8条第1款修改了《刑法》第160条第1款,同时增设了第2款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实施前款行为的,处……”但是,本款的增设完全缺乏必要性。
第一,《刑法》第160条第1款并没有将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规定为身份犯,即没有限定行为主体的范围,既然如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当然也能成为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的行为主体。所以,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来说,没有必要增设第2款。
第二,组织、指使行为虽然不是《刑法》第160条第1款规定的实行(正犯)行为,但根据《刑法》第26条、第29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组织、指使行为不仅可能成为教唆行为,而且完全可能成为共同正犯行为。
第三,《刑法》第26条第4款规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本款规定表明,对于组织、指使实施欺诈发行股票、债券行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也应当按其组织、指使的全部罪行处罚。既然如此,《草案》第8条第2款的规定就没有必要性。
第四,《草案》第8条第2款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规定的主刑与第1款完全相同,只是罚金刑不同。第2款有罚金刑最高额的限制,而第1款却没有最高额的限制,这就表明第1款的罚金刑较重。由此可见,增设第2款的规定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导致第1款与第2款不协调。
综上所述,《草案》第8条增设的第2款缺乏必要性。不仅如此,增设第2款的规定,反而会导致共同犯罪认定的混乱,即导致在没有增设类似规定的法条中,司法机关对相关人员的组织、指使行为不以犯罪论处。这是因为,在《草案》第8条第2款的规定事实上只有一种提示作用,但司法人员习惯于将提示性、注意性的规定理解为基本规定或者法律拟制。
(二)极为罕见的情形
对于极为稀罕的行为,即使法益侵害较为严重,也没有必要规定为犯罪。其一,刑法是普遍适用的规范,不得以稀罕之事为据制定法律。刑法过多地规定极为稀罕的行为,就会导致许多法条的不适用,从而影响刑法的效力。其二,极为罕见的行为缺乏蔓延的可能性,因而缺乏一般预防的必要性,没有必要将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
《草案》的某些规定事实上将极为罕见的行为增设为独立的新罪,不符合必要性原则。例如,《草案》第2条第1款规定:“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夺驾驶操纵装置,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处……”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的驾驶人员与他人互殴,危及公共安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如果说本条第1款的规定具有必要性,是容易被人接受的,那么,本条第2款的规定则缺乏必要性。
首先,与第1款规定的案件相比,驾驶人员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的过程中与他人互殴的案件极为罕见。如上所述,将极为罕见的行为增设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完全没有必要。其次,即使发生了这种案件,对驾驶人员的行为也完全可以按相关犯罪处理。如致人伤亡的,可能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即使没有致人伤亡,没有造成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的,也有可能认定为寻衅滋事等罪。
类型性原则的贯彻
刑事立法的重要任务便是描述各种犯罪类型。根据类型性原则,刑法分则条文对各种犯罪应当作类型性的描述,既不能按照现实发生的个别案件详尽描述构成要件,也不能单纯使用抽象的概念,而是将构成要件描述为可以与具体案件相比较的类型。如果构成要件的描述类型性,必然形成处罚漏洞;发现处罚漏洞后,为了保留原有的法条,不得不增设新的具体犯罪,于是,刑法分则的类型性越来越差。这是值得立法机关工作人员反思的现象。
《草案》也存在缺乏类型性的现象。例如,《草案》第22条增设了以人类遗传资源为对象的犯罪,具体描述了三种行为:“……(三)未经安全审查,将国家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向境外组织、个人及其设立或实际控制的机构提供或者开放使用的。”从构成要件的描述来看,将合法采集的国家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在境内公开就是无罪的。然而,在网络时代,只要在境内公开,就必然会被境外组织、个人使用,而行为人并没有向境外组织、个人提供和开放使用。笔者认为其中存在处罚漏洞。其实,只要将第(三)项简单地表述为“未经安全审查,提供或者公开国家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就可以使构成要件更加类型化,从而避免处罚漏洞。
《草案》对个别犯罪的加重构成要件的描述也缺乏类型性。例如,《草案》第16条规定的加重构成要件限定为三个领域。然而,并非只有这三个领域的虚假证件文件值得科处较重的刑罚。这是因为,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随时可能产生新的生产、经营领域,新的生产、经营领域也可能存在未知的重大风险。所以,依据当下的有限事实过于具体的描述,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处罚的不均衡。
就法定刑升格的条件而言,采取例示法最为合适。例示法是概括条款与个案列举法的有机结合,既能保障刑法的安定性,也赋予法官对此类或类似的案件作出同样处理的任务,既能对应社会生活事实,也能限制法官权力。
此外要顺便指出的是,在发现新的犯罪现象时,不一定要用法条增设新的犯罪,完全可以仅修改原有的法条,使原有的法条更为类型化,就可以使刑事立法更为完善。
明确性原则的贯彻
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明确性是对刑事立法的要求,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可以肯定的是,任何部门法理论都没有像刑法理论这样强调法律的明确性。
明确性的最起码要求是,一个法条的表述不得使司法人员可以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去理解和适用,至少要做到使司法人员朝着一个方向去理解和适用。此外,如果法条表述不明确,也不可能通过解释使之明确的,也不符合明确性原则。《草案》中存在不符合明确性原则的条文。例如,《草案》第17条规定,在《刑法》第246条之后增加第246条之一:“侮辱、诽谤英雄烈士,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
其一,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行为性质是什么?从法条的位置来看,本罪属于对个人法益的犯罪;而从法条表述来看,本罪又属于对社会法益的犯罪。其二,英雄烈士是什么含义?从对象本身来说,存在朝着完全相反方向的理解和适用,同样也不可能有可以消除不明确性的解释路径与方法。在本文看来,为了确保法益的明确性以及保护的平等性,只需要增设毁损死者名誉罪。
协调性原则的贯彻
刑法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刑法本身也是一个体系。根据协调性原则的要求,增设的新罪与已有的犯罪之间,增设的各项新罪之间,以及增设的新罪与其他法律之间,必须保持协调关系,既不能产生冲突与矛盾,也要避免罪刑不均衡。就此而言,《草案》还有值得修改之处。
(一)法条内部的协调
法条内部的协调,是指一个法条内部必须和谐一致。就此而言,《草案》的某些规定值得商榷。例如,《草案》第1条规定,在《刑法》第114条中增加两款作为第2款、第3款:“从高空抛掷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在本文看来,增加高空抛物罪也未尝不可,但将高空抛物罪安排在《刑法》第114条之后,明显不协调。
其一,《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是危害公共安全罪最严重的犯罪,其重要特点是,一旦危险现实化,实害结果就无法控制。但是,在高空抛物的场合,即使行为人在楼下人员密集的地方抛物较多,也不可能造成实害结果的范围无法控制的局面。所以,将高空抛物罪规定在《刑法》第114条之中,必然造成条文内部的不协调。
其二,《刑法》第114条第1款中的“危害公共安全”是对具体的公共危险犯的表述。但《草案》第1条对高空抛物罪却出现了“危及公共安全”的表述。于是产生了以下问题:这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否相同?如果相同,为什么在同一法条内采取不同的表述?如果不同,法定内部的两款之间如何协调?
其三,根据《草案》第1条的规定,高空抛物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如若造成多人死亡,按照司法实践的通行观点,就要适用《刑法》第115条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是,第115条与第114条原本就具有对应关系,将高空抛物罪规定在第114条之中后,第115条与第114条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被破坏了。
其四,将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同时要求危及公共安全,只能逼着下级司法机关违反刑法规定认定犯罪。这种有损刑法权威性的刑事立法并不可取。
所以本文的建议是,倘若要增设高空抛物罪,就应当将其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一节中。具体而言,可以作为《刑法》第293条之一第1款规定如下:“从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法条之间的协调
刑法是一个整体,法条之间必须保护协调。既不能将轻罪规定在重罪法条之中,也不能将重罪规定在轻罪法条之中,否则,就必然导致处罚的不公平。例如,《草案》第7条增加的第142条之一第1款规定:“违反药品管理法规,有下列情形之一,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生产、销售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禁止使用的药品的;(二)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进口药品或者明知是上述药品而销售的;(三)依法应当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药品的;(四)药品申请注册中提供虚假的证明、数据、资料、样品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的;(五)编造生产、检验记录的。”这一规定存在两方面的不协调之处:
其一,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场合,《草案》第7条第1款规定的法定刑却明显轻于生产、销售劣药罪,这便极不协调。亦即,原本《草案》第7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基本犯比生产、销售劣药罪更为严重,所以,只需要产生具体危险就成立犯罪,然而,就结果加重犯与情节加重犯而言,《草案》第7条第1款规定的法定刑却又轻于生产、销售劣药罪,这便明显不协调。
其二,《草案》第7条第1款第2项与第3项规定的行为,明确侵犯了药品管理秩序,不应当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作为构成要件要素。例如,擅自进口治疗白血病的药品销售给白血病患者的,不可能具备“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要件,因而不能按照《草案》第7条的规定定罪量刑。但是,未经批准擅自进口药品并销售给他人,则侵犯了药品管理秩序,需要作为行政犯处罚。再如,行为人销售未经检验药品的行为,同样侵犯了药品管理秩序,即使事后查明并不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也应当以犯罪论处。
本文建议将《草案》第7条分解为两个犯罪:一是不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作为前提的行政犯,二是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作为前提的具体危险犯(同时规定加重犯),对二者分别规定不同的法定刑。
(三)刑法与其他法律的协调
法律体系是一个协调的整体,刑法在增设新罪时,不能与其他法律的合理规定相矛盾,而应当与之相协调,对此不必赘述。就此而言,《草案》的个别法条的规定还存在疑问。例如,《草案》第20条第1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催收高利放贷产生的债务或者其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并以此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情节较轻的;(三)恐吓、跟踪、骚扰他人,情节严重的。”这一规定明显与民法不协调。
既然高利贷产生的债务不受民法保护,就意味着被害人没有债务,行为人以此为由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催收的,理当成立抢劫罪或者敲诈勒索罪,而不应当按《草案》第20条的规定处罚。同样,既然是其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就意味着被害人没有债务,行为人以此为由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催收的,当然成立抢劫罪或者敲诈勒索罪。可是,《草案》20条的规定事实上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虽然民法不保护这种债务,但刑法要保护这种债务。这就是在保护民法不保护的债务,造成刑法与民法的不协调。
其实,在发放高利贷行为已经作为非法经营罪处理的当下,上述为催收高利贷所实施的行为,完全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共犯。既然如此,规定本罪就缺乏必要性。倘若承认以暴力、胁迫手段催收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构成较重的犯罪,《草案》第20条的规定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性。所以,建议删除该条的规定,否则,必将是刑事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瑕疵。
在当今社会,频繁修改刑法典已经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任何一次修改都要谨慎,尤其是增设新罪时,要贯彻必要性、类型性、明确性与协调性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