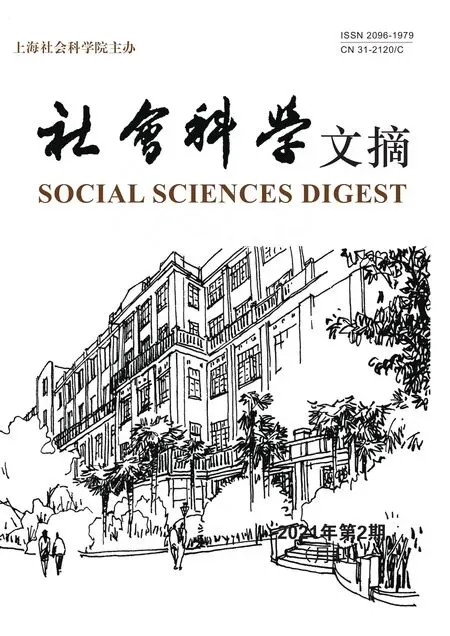《塞浦路斯大道》中的“北爱尔兰病”
文/李元
1968年,北爱尔兰著名摇滚音乐人凡·莫里森(Van Morrison)创作出名曲《塞浦路斯大道》。歌中人物站在贝尔法斯特富庶的中产阶级街区塞浦路斯大道上,仰望小山坡上的一所大宅,无限神往,沉迷其中,甚至感觉快要发疯。时隔近半个世纪,北爱当代剧作家戴维·爱尔兰德的《塞浦路斯大道》(Cyprus Avenue,2016,以下简称《塞》剧)问世,讲述居住在这条街区大宅里的一名60岁新教联合派男子如何因为遭遇身份危机而渐至疯狂。该剧于2016年由英国皇家剧院与爱尔兰阿贝剧院联合制作,聚焦北爱尔兰在《贝尔法斯特和平协议》(1998)签署之后出现的社会心理问题。男主角埃里克·米勒是中产阶级新教徒,如同不少从小受到忠英教育的联合派一样,面对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他无所适从,竭力维护他所坚信的民族身份,对变化的世界充满愤怒、焦虑和挫败感,日渐失去理智,产生妄想,认为刚出生不久的外孙女是敌对党——共和派新芬党——前领袖杰瑞·亚当斯的化身。在剧尾,埃里克终因精神分裂而犯下对家人的暴行。
书写后协议时期的北爱尔兰问题
北爱尔兰在历史上一直被派系冲突所撕裂,新教联合派与天主教共和派纷争不断。自20世纪60年代起,爱尔兰共和军(IRA)制造的暴力事件以及天主教徒与英国警察、军队的冲突频频发生,直到20世纪90年代开启和平进程后才逐渐平息,这30多年的不堪历史被称为北爱问题时期。1994年,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停火,开启北爱和平进程。1998年,北爱和平协议《贝尔法斯特和平协议》被签署。尽管北爱和平协议结束了武装冲突,但派系隔离和仇恨仍然存在,亲英联合派(新教徒)与共和独立派(天主教徒)这两种民族主义仍然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方面进行角力。受到各方力量的牵制,和平协议的某些条款也迟迟得不到落实,使得民众感到焦虑、失望。自21世纪初起,在北爱议会选举获胜的是两大激进党派,即新教徒的民主统一党和天主教徒的新芬党。《塞》剧中的男主角埃里克所支持的政党就是由伊恩·佩斯利所创建的民主统一党,该党派与新芬党并列对峙,同为当今北爱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民主统一党和新芬党的不少成员都曾经是北爱问题时期的激进分子,亲自参与过暗杀、汽车爆炸等恐怖主义活动。除去政治的割裂,有学者提到后协议时期北爱尔兰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区分社会和平进程与政治和平进程。和平协议的达成标志着政治和平进程告一段落,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和平进程一帆风顺,更不意味着人们的创伤就此终止。社会和平进程是一个长期过程,其中涉及多种因素,包括敌对双方的宽容与和解、公民社会建设、社群关系修补、对历史的纪念和回忆策略、新的文化符号的确立以及对身份的再评价和考量等。而这些在北爱都相当缺乏,社会共识并没有达成,各界对过去避而不谈,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人民对未来又充满不确定。历史学家约翰·布兰尼根在描述后协议时期的北爱尔兰时,指出该地区“被悬置在臭名昭著的过去和岌岌可危的未来之间”。
爱尔兰德于1976年出生于贝尔法斯特南部的新教徒街区,该街区是强硬联合派的聚集地,每年都举行大规模的奥兰治游行。特殊的成长经历对其创作产生了影响。2012年,他开始构思和写作《塞》剧时,还觉得这个题材太本地化,不会引起广泛关注,然而到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时,有关北爱的议题突显出来。多重不确定因素使北爱政治危机重现,令亲英的联合派尤为恐惧不安。
北爱版“愤怒的白男”
《塞》剧反映了北爱联合派的焦虑,全剧以男主角的身份危机为起点展开。正如英国著名剧评家迈克尔·比林顿所言:“埃里克的身份危机代表忠诚派的困境,他坚持自己的英国特性,但又经常陷入恐惧中:他恐惧的是,如果在其笃信的英国特性背后是爱尔兰人呢?”事实上,在英国越来越拥抱多元文化主义的今天,大多数英国人根本不在乎北爱尔兰人对身份的纠结,更不会去区分共和派和联合派。北爱联合派如此强调自己的英国身份,对英国人来说不过是个笑话,这也令埃里克从困惑变得愤怒。
爱尔兰因其人种一致、语言相同、地理位置相近而成为英帝国的一个特殊殖民地,也使其成为后殖民研究的一个特殊案例,经常令研究者感到迷惑。学者维杰·米什拉和伯格·霍杰进一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后殖民主义,即“反对”与“共谋”,并将二者与不同意识形态取向结合在一起,特别指出共谋型后殖民主义适用于对英国白种人殖民地的研究。尽管米什拉和霍杰主要分析的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英联邦国家,但在北爱尔兰语境中,这两种类型同样非常适用:反对型后殖民主义指共和派开展的一系列针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抵抗活动;而共谋型后殖民主义是指被殖民者愿意参与殖民活动,以期从帝国获利,这当然是像剧中埃里克那样的联合派所作出的选择。自英国殖民伊始,北爱尔兰便开始分裂:“同时是西方的又是被殖民的,既是白人又是种族上的他者,既是帝国的又是被征服的,在双重经验的存在中变得边缘化。”因此,北爱很难建立明晰统一的身份,其分裂的殖民历史并不能如其他的后殖民表述那样明确分清自我与他者,甚至殖民与后殖民的两分也模糊不清。
在北爱的民族身份形成过程中,既有共和派的反抗也有忠诚派的共谋,双方互为敌对关系,每一方都以对方的对立面来定义自己,以偏见和高度选择性的叙事将自己呈现为受害者,每一方都有一套讲述人民如何受苦、怎么反抗的故事。在这样一个互相指责的游戏中,双方阵营也都发展出一套话语以再现过去,以“我们”和“他们”来描述各自对历史和国家疆域的占领,在两种文化之间划下清晰的认知界限。
《塞》剧描写的就是在其中一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下长大的个体,他以仇恨对立和敌我两分来确定个人身份。这种褊狭的身份定义是所有派系划分地区的常见思维模式。将自我身份与民族话语、政治偏见绑定的思维,在民粹主义盛行的今天,可引起很多共鸣。《纽约时报》有剧评认为,埃里克是民粹主义的一个经典类型——“愤怒的白男”。“愤怒的白男”这一说法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特指美国政治保守的中老年白人男性,他们反对平权法案,对年轻人、女性、少数群体怀有敌意,已成为小说和电影、戏剧中的一个类型。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在研究这一特殊群体的专著中指出,许多白人男性在美国社会越来越流行多元文化价值这一背景下,对自己逐渐丧失社会特权和经济优势感到愤怒,有被时代抛弃的挫败感。在特朗普时代,这一群体愈发受到关注,他们也是当年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的重要票仓。值得注意的是,“愤怒的白男”不仅限于美国,他们在欧洲、大洋洲国家也大量存在。《塞》剧中的埃里克便可以被视为“愤怒的白男”的北爱版本,尽管文化内涵和政治语境不同,但愤怒是他们共同的底色。
民族主义与现代精神疾病:从“英格兰病”到“爱尔兰病”
有剧评家谈到观看《塞》剧最大的感受是,观看者被困于埃里克疯狂的头脑中,体会他的各种情感和思维。如果该剧是描写埃里克偏执的头脑如何逐渐疯狂,他的世界如何因偏见、仇恨而扭曲,那么剧中其他人物则可被看作其心理的投射。第一幕戏就是埃里克在看心理医生。很显然,他的精神已经出了问题,需要寻求治疗;也或许心理医生是他妄想的开始,他与想象中的医生的对话反映出了他不正常的心态。埃里克疯狂心理投射的中心则是他刚出生不久的外孙女,第一眼看到她,埃里克立刻表现出恐惧和愤怒:“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婴儿……特别是现在,我在她脸上画了胡子……你会发现有问题……她是……是芬尼亚恩人,在我们家里……那个婴儿是芬尼亚恩人……我们不能让芬尼亚恩人在家里,我不能容忍他们在我家里。我们……不管是家庭、人民、还是民族,我们被包围……我们必须保护我们拥有的东西……必须有人叫这个芬尼亚恩小杂种从我们家滚蛋!这就是我们说不的时候。”
埃里克这段语无伦次的台词显示出了精神分裂的症候。精神分裂的临床定义是患者在行为、认知、情绪、心理和言语上的不正常,一般先起于多疑、被害妄想,然后出现幻觉或幻视、幻听,语言组织混乱。研究爱尔兰戏剧的著名学者昂德雷·皮尔尼指出,该剧“巧妙地模糊了民族主义与精神疾病的界限”。的确,埃里克从愤怒、抑郁到精神分裂、产生妄想,最后犯下暴行,整个过程都有统一的主题,即个人身份的危机和对假想敌“芬尼亚恩人”的恐惧与仇恨。关于民族主义与现代精神疾病的关系,美国学者莉亚·格林菲尔德有很独到的研究,她着重分析现代化进程对人的心理影响,尤其关注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指出人的精神疾病是文化产物,而不是由生理决定的。
在她看来,民族主义对个体身份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社会变得世俗化,超验世界萎缩,人类生活变得越来越重要;其二,民族意识与宗教和等级意识完全不同,其平等原则既指国家内部人人平等,也指民族独立,不被外族统治。这种平等观念改变了个人身份性质,赋予个人身份以尊严。世俗主义与平等这两个方面看似积极进步,却隐藏着危机,因为民族主义强调个体进行自我管理,赋予个人选择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权利与自由,但尽管这种自由赋予个体力量,却使得身份的形成变得复杂。对于具有宗教意识和处于严格社会秩序下的个体而言,其地位和行为在出生时就被等级制度或神的天命所定;相比之下,民族国家的个体则需自己选择和评判,因此往往无所适从,陷入悬而未决的境地。如果说个体身份的确定和清晰是保证其精神健全的重要条件,那么身份的模糊和悬置则会导致精神疾病。
格林菲尔德认为现代文化的失范带来新型精神病症,并将其追溯到16世纪的英格兰,以“英格兰病”(English Malady)来指称。该病症在英格兰传播迅速,到16世纪末,已成为英格兰社会的一个特别标志。
英国精神病理学先驱乔治·切恩首次描述了“英格兰病”的流行。此后,该病症被不同学者分析,不断增加新的阐释维度。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总结前人的观点,对“英格兰病”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将其与政治意识形态和现代社会个人自由等原则联系起来。福柯的分析显然为格林菲尔德所吸纳,但格林菲尔德更强调民族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由于民族主义的特征不再被传统文化价值(主要是宗教价值观和等级制度)所定义,而是取决于对一种社群(国家)的无比忠诚,因此,民族主义极易催生激情和野心,导致精神疾病。16世纪英格兰民族主义的时代开启,与此同时,一种特殊类型的精神疾病出现,一个新的术语——“疯病”——应运而生,由此也产生了病理专业(最终叫“精神病学”),还有了与疯病相关的立法。格林菲尔德同时也观察到,当“英格兰病”随着民族主义在英国的兴起而出现后,它逐渐向帝国的殖民地传播,其中最易感的当属距离最近的爱尔兰,在那里,“英格兰病”很快演变为“爱尔兰病”。
疯病从英国蔓延到爱尔兰,跟爱尔兰民族意识的发展直接相关。1798年民族主义起义之后的10年间,爱尔兰的疯病病例陡增,增长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可以想象,当疯病在英国、爱尔兰流行时,处于两种民族主义撕扯之中的北爱尔兰更是不可能幸免。步入21世纪,在遭遇长达数百年的派系撕裂、暴力冲突后,并没有太多媒体和官方叙事谈及情绪管理问题,讨论应该如何应对社会变化产生的恐惧、仇恨和愤怒等。
可以说,《塞》剧对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北爱尔兰病”病例。埃里克的“北爱尔兰病”也是源于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因为北爱派系斗争而加剧。正如格林菲尔德所指出的那样,政治意识形态走到极致,容易演变为非理性的激情,往往被某些狂热的政治目的所驱使,而这些政治目的在大部分情况下与参与者的个人经验无关,只是参与者用来解释自我在社会环境中感到不适的理由,因此就其本质来说,它们不可避免地隐藏着精神分裂的妄想:缺乏对社会现实的了解,混淆符号与所指的关系,将符号看作客观现实。例如,在埃里克的头脑中,共和派“芬尼亚恩人”是个流动的所指,除了爱尔兰天主教徒,还包括他憎恨的所有人,如罗马教皇、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美国歌手丽莎·明尼里等。他认为这些芬尼亚恩人无所不在,随时密谋消灭他的族群。埃里克向自己外孙女痛下杀手,认为她是共和派领袖的化身,他的暴力行为完全是非理性的,其内在逻辑等同于现代社会的恐怖主义袭击:恐怖主义者混淆了符号与所指的关系,他们袭击平民,不是因为被袭击者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被袭击者所代表的东西。
格林菲尔德在分析美国当代的恐怖主义事件时特别指出,民族主义制造了新的精神疾病,且往往以自杀或非理性暴力来表达。个体将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问题和不适归罪于外部因素,或通过建构一个故事,使自己的不适得到解释,以为这意味着自己受到某种邪恶的威胁。带着这样的思维,这类人可能会参加某个组织,致力于与那种假想的邪恶作斗争,或者自己行动起来,毫不犹豫地去杀戮。如此一来,暴力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格林菲尔德比较了民族主义产生前后的暴力行为,认为在前民族主义时期,暴力在总体上是工具理性的,谋杀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无论是抢劫还是政治胜利。然而,自16世纪起,英国疯病患者的暴力行为并不符合上述规则。疯狂改变了暴力犯罪的性质,极大增加了非理性因素,暴力行为不再是工具性的,而是表达性的。现代的连环杀人、校园枪击、政治暗杀、恐怖袭击等案件大都具有意识形态动机,将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视为邪恶的化身,凶手感到有责任去消灭它,这样的意识形态动机是妄想性的。埃里克的杀戮行为符合这一分析,他将自己的焦虑和恐惧转移到外孙女身上,进而延伸至妻女。在其疯狂的逻辑下,他将自己对家庭成员的谋杀看成是对“芬尼亚恩人”的战斗。
《塞》剧以黑色幽默开场,随着埃里克的疯狂而走向恐怖血腥,最后的杀戮令人战栗。有观众称观看该剧的感觉仿佛是得了“弹震症”(Shell shock)。埃里克的暴力源于疯狂的“北爱尔兰病”,是恐怖主义行为,正如皮尔尼所评论的,埃里克杀戮的暴行是疯子所为,是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推演到极致的结果。2016年4月,《塞》剧在伦敦首演时,正值英国脱欧公投前夕;2019年该剧再度被制作上演,愈发贴近现实。英国政府在2017年大选后,执政的保守党完全依靠北爱新教激进党民主统一党来维护其在众议院的大多数席位,也正是这一强硬的忠英党派对英国脱欧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他们的民粹主义言论时常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埃里克则代表这一政治氛围下的“愤怒的白男”,当他的整个世界都被民族身份、政治意识、派系仇恨所左右时,一切理性、科学、逻辑都被置之脑后,他也最终因褊狭、极端、激进而陷入疯狂。比林顿称《塞》剧是近年来在伦敦上演的“最令人震惊、最具颠覆性和最暴力的一部剧”,并且“与现实极其相关”:“正如所有优秀的剧作一样,《塞浦路斯大道》引起隐喻式共鸣……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派系划分,那么这种角度就值得去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