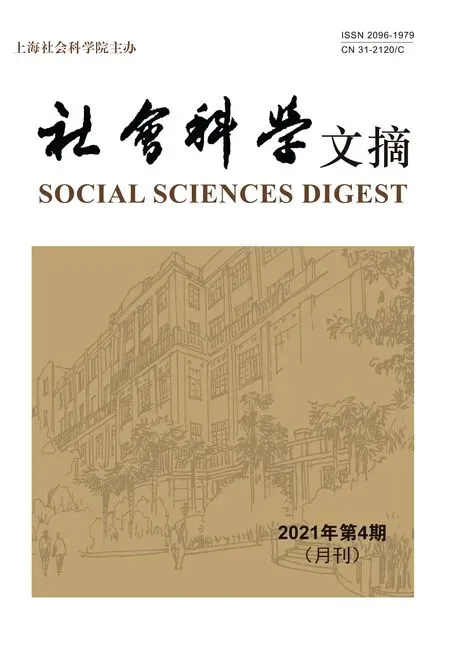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研究:学科边界与学科交叉的探索
文/严飞 祝宇清
近年来,历史社会学研究在中国学界日益得到重视,对于学科边界、学科概念、研究方法以及发展脉络的学理性讨论也随之增多。对于历史社会学的一个普通共识,就是历史社会学不仅仅只是社会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且是社会学固有的内在属性,“是一种具有总体性、本源性的研究趋向”。在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之下,有关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异同也在最近几年开始重新回归学术视野,其延伸讨论指向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深层次关系,也是对所谓“学科交叉”的可行性探索。围绕着“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关系”这一议题,社会学家的观点与历史学家的观点微妙地呈现出学科边界思维的差异,对于两者关系的论述也不尽相同,但又最终同归于一个方向,即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范式、方法、材料,以达成完善本学科体系的目标。
与此同时,在社会学学科内部,无论是带有历史维度的社会学研究抑或是针对特定历史事件/现象的社会学分析,到底应该归属于历史社会学的范畴,还是社会史的范畴,迄今都未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划界。对此,本文以《社会学研究》《社会》这两本社会学代表性期刊为样本,从中抽取了2010—2020年间所有涉及历史维度/历史事件的论文共46篇,并对这些论文进行深度解剖,以期就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边界与学科交叉问题进行深度检视,从而探寻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
在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的关系议题下,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其差异点,例如学术目标、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方法、指向结论等。学者们普遍认为,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的差别根源在于学科范式的差别。在对本学科边界的确立中,学者们通过反复辨析学科概念、强调学科使命,达成了区分于其他学科、明确边界的需要,也隐隐提供了借鉴其他学科优势的合理性。
就国内学界情况而言,有关社会史学科范畴的探讨远早于历史社会学,主要集中在社会史研究复兴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86年举行的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标志着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复兴,而复兴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社会史的概念之争”。具体而言,社会史概念的界定主要包含三大问题,分别为“社会史是专门史还是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在周晓虹的分析中,社会史的特殊之处在于,由于“社会”范围的复杂性,社会作为一类范畴、一种研究对象,其边界性常常是模糊的。因此,历史/时间的维度与社会/关系的维度下产生的各类研究问题,必然是学科当中不能回避的基础性、普遍性问题。而在赵世瑜的分析中,社会史是一种崭新的研究范式,而非一门分支学科或者一种综合史,社会学对于社会史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借鉴意义,但与此同时,“社会学可能是主要的,但绝不是唯一的社会史的依靠对象”。
20世纪90年代,历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领域,在国内的发展力量还较为弱小,成果也非常鲜见。这一时期的社会学研究者在强调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差异时,虽然认为不能忽视研究目的和特点所导致的学科“分工”,但对其与社会史的关系并没有进行深度挖掘。此后,伴随着历史人类学、区域史、新社会史等研究领域的兴起,社会学对如何看待与历史学关系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最近10年里,历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愈发受到国内学者们的重视,并将“历史想象力”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必备素质。目前,历史社会学在国内早已不再被视为单纯的分支学科,而更多强调其对社会学整体发展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比较研究方法、历史因果机制的应用上,展现出了清晰的学科定位和范式革新。
整体而言,历史社会学对社会史、对历史学的态度是相当清晰的,所要利用的是“历史取向的研究路径”。而在近年来的理论浪潮中,更多学者强调,历史社会学研究同样需要坚实的第一手档案史料,需要加深对于“历史”的在场理解。例如,李里峰将历史社会学的范畴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认为历史/时间维度的上入对于历史社会学而言至关重要;同时,历史学的历史感和复杂性是难以替代的,社会学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能力也独具优势,二者可以尝试取长补短,探寻“美美与共”。而在学科边界上,历史社会学将重点落在社会学学科内部,强调历史社会学如何与政治社会学等其他分支学科表现出不同,即历史/时间的维度可以切入其他分支学科,使之也成为历史社会学主题下的一部分。
纵观学科史的发展历程,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在学科内部的处境是相似的,既有作为分支学科的一面,保存着本学科的某个重要侧面,也始终存在着作为学科固有范式的可能,指向对抽象整体和本质的追求,并时刻见证着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兴衰交替,试图上入其他学科作为“方法”,借此提升本学科的厚度与宽度。同样面对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关系这一问题,阐明二者区别的必要性始终是服务于本学科功能性的。这种对“异同”的阐发与其说是对学科边界的再确认,不如说是对学科核心主旨的绝对拥护。边界勾勒出学科的疆域,时刻上入新兴议题;核心则始终保持着学科本身的自觉性,使之呈现出独特性与独立性,提供学科交叉或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
近10年来国内研究综述
随着历史社会学本身在社会学学科中日益得到重视,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学科分野也不再意味着天堑与鸿沟,而是更为温和地走向交织与融合,并从单一学科向多元视角转变。本部分通过对近10年来发表在《社会学研究》《社会》这两本社会学期刊上涉及历史维度的相关论文进行综述,概括各类研究表现出的理论与方法趋向,以及与历史学的结合与嫁接,从而加深对于学科边界和学科交叉的认知。
(一)明清之前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基本趋势
在本文所取样的两本社会学期刊中,专门针对明清之前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目前还相对较少。除谢宇等人对东汉时期中华帝国治理能力与地方官员责任的讨论外,大部分论述都集中在对儒家伦理思想与礼乐教义的探讨中。其中,一类研究逐渐转向对儒家思想传统中的部分概念、制度、实践进行考察,在完善中国社会学史的意义层面进行学术史刻画,强调延续费孝通、梁漱溟、潘光旦等学者的部分研究主题,将服制等古代伦理制度的合法性投射进现代生活之中。这在目前已经呈现出相对一致的研究脉络。
另一类研究则出现了对深层历史机制的积累性讨论,在对儒家经典文本、作品、史料进行再解读的过程中,既对接西方社会学理论,同时又尝试为本土化的社会学搭建学科传统,从而形成对方法合理性的反思。例如,围绕“差序格局”这一中国社会学的基础性概念,学者们试图将古代儒家传统中的基本原理和当代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进行联结,将“人情”“关系”“社会正义观”等现象上溯至宗法、礼乐等制度当中,试图以概念史的方式剖析儒家思想,透视历史脉络中的伦理关系变迁。杭苏红在家国同构这一逻辑框架下,利用《汉书》等史料对西汉时期外戚为官的人数与具体职位进行统计,将之解释为家话关系中的“义”这一伦理法则对皇帝行为的影响。吴柳财则与韦伯、高延、葛兰言等外国学者的中国宗教礼仪研究开展对话,论述了文本解释这一研究路径的合理性,以《礼记·曲礼》为基础探讨了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意义。
这一类型的研究所表现出的张力不仅是现代社会下对于儒家制度的思考与再解读,也是现代性生活中对于儒家伦理思想的某种复兴,其结果既可能是将历史视野带回中国社会学,也可能是将历史简化为一种单一的理想模型。
(二)明清史研究的基本趋势
在近年发表的相关社会学研究成果当中,明清史研究与近现代史研究成为两个主要的时间段,并在叙述结构上呈现出一定差异:明清史研究往往需要用更多的篇幅来充分描述朝代、地点与基础等时间线索,而近现代史研究则更偏向于将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带入到历史叙述当中。当然,这种差异并非是绝对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的路径差别。
根据研究思路的不同,针对中国明清史特定社会现象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以个案作为核心,倾向于描摹一定时期下特定地区特定现象的出现、发展与嬗变,重点关注从史料中发掘新材料、填补原有的空白,其进展多得益于历史学和考古学方面的突破,在研究路径上也更偏向于社会史。
帝国统治下的国家与地方关系通常是此类研究关注的重点,而这种关系又需要通过地方制度展现出来。例如,麦思杰以清代广西昭平县黄姚街作为案例,基于时间与地理空间,对该地“风水”的演变进行分析,探讨社会权力的构建如何重塑风水走向,最终将话题上入帝国构建与地方社会关系演变。陈志刚则结合区域社会史的思路,考察了明代上川南地区佛教的传播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将佛教的地方传播拆分为宏观意义上的统治实用主义和微观意义上的社会互动的结果,并探究了儒家与佛教的思想矛盾如何在地方实践中得以化解的整个过程,进而认为义和善的共同道德观念为之提供了求同存异的可能。
部分研究则将“地方”进一步细化为边疆地区与少数民话地区,以区分地方的特殊性对于历史事件的影响。例如,杜树海通过对广西靖西县村庄的墓碑、石刻资料的探索,描绘出清代边疆民话地区功名人士在地方文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胡冬雯利用人类学田野调查,并尝试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还原清代乾隆年间金川改土设屯的具体过程和最终结果,探究嘉绒藏人的内婚制与家话发展等日常生活如何受到国家政策影响。马健雄关注清朝滇缅边疆地区的地方发展历史,其对政治格局的细致描述更像是政治史的叙述方式,核心问题则围绕着地方新制度与国家体制、边疆地区的国家治理展开讨论。张江华考察了清代广西土司地区科举制度的推行过程,分析清政府、当地土官、地区社会成员三个主体间的角力互动,及其背后所展现出的当地商业与社会群体地位、科举政策发展的关系。
部分研究将家话史、交游史中的微观内容作为研究的基础,在个案中充分展现出特定制度的发展情况。例如,侯俊丹考察了同光时期温州永嘉学派的地方社会重建工作,立足于19世纪60年代温州地方史,探索以孙氏家话为代表的传统士人如何应对社会危机并为变迁中的小氏话构造宗话认同。蒋勤则挖掘石仓契约科举账簿的第一手资料,研究以石仓阙氏为代表的小商人阶层如何在科举制的大背景下自主选择政治参与策略,以期获得学轨制中的最优解。
综上所述,此类研究通常基于区域社会史或者家话史的材料,着重于在时间序列上展开对于个案的详尽叙事分析,同时与民话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进行交叉,并在此基础上为国家—地方关系、民话—宗教关系等宏大议题寻找答案。
第二类则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下,将明清的社会现象与当代议题连接起来,并尝试提炼出历史事件中的机制与规律,展现出更为明显的历史社会学风格。例如,付伟选择对清代公文系统进行分析,利用官箴书、会典例则、官员日记、书信、文集等材料,系统检视了儒家理念如何“文以明道”,在公文系统中兼顾传递感情与信息,从而呈现出传统治理体制中“反官僚制”的特征。侯俊丹将晚清时期温州的军事化运动作为案例,分析“任侠之气”这一精神伦理如何在地方社会当中表达出来,概述精神原则如何对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地方社会组织产生影响,进而将之融入政治治理的理论框架当中。张佩国将中国历史情境下的福利实践与社会学概念下的西方福利制度进行对比,强调传统观念在中国福利实践中发挥的串联作用,通过长时段分析将之融入对象征支配的讨论当中,重新与西方社会学理论进行比照。傅春晖延续市镇研究的理论传统,将目光投向明清时期的中国市镇发展,从市场发展、社会构成、政治局面等角度对城镇化的历史意义进行讨论,更多体现出对国家—社会关系这一命题的深入探索,最终将结论指向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
与前一类研究相比,这类研究强调将历史维度中的特定现象或制度与当代现实情况进行对比,以加深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解,也将研究的责任指向反思的层面,为社会学经典理论的延伸或转向提供了可能。
(三)近现代史研究的基本趋势
和上述明清史研究相比,针对近现代史进行的研究往往更能形成集中性主题,也更有可能在研究方法上应用口述史等方法。
在面向近现代这一时间跨度相对有限的范畴时,一类研究将目光投向了现代化制度的发展与变迁,其研究内容更接近于广义的社会史,与经济史、政治史的视角相勾连,并尝试在此基础上透视国家权力如何延伸至各个领域。例如,黄素娟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下梳理了广州城市土地产权变迁的过程,认为这种产权变迁是政府应对不同时期、不同问题的策略结果,从中可以观察到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互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等。杜丽红针对近代北京公共卫生制度的变迁展开研究,将这一主题视为个案研究,对制度变迁进行了阶段划分和成因探讨,综合分析变迁过程中行动者、制度逻辑、制度环境各自发挥的作用。毛丹利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档案对当时城市基层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描述,详尽展现了政策层面中的居委会建设、知识分子培养的过程与问题以及各个主体相对应的职责,认为在国家主导、社区配合、社区自我维持的三种机制下,基层社会得以迅速扩张并发展成为后期建设新型社区的基础。
另一类研究则将研究场域集中于农村、工厂、社区(生产队)等场所,重点关注国家治理与群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探究历史运行中具体案例的制度逻辑。在这部分研究中,“如何处理史料”不再是核心议题,“如何与理论对话”成了基本出发点。这一类研究的方法取向又可以总结为三大特点。
首先,更重视梳理事件的内部逻辑,将论点控制在相对具象的范畴之中,注重研究问题本身的承上启下关系与“精耕细作”。例如,林超超承接对新中国“工人阶级”如何形成的已有研究,以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作为案例,将民主改革运动视为新国家改造旧工人的一种尝试,并分析运动中采用的各类技术策略。此研究重视新策略如何作用于群众,群众如何在运动中逐渐发生改变,更多是从城市层面入手,与农村研究形成对照,补充了城市民主改革的视角。林超超围绕1957年上海“工潮”所做的另一项研究同样呈现出这一特点。除了工人研究以外,中国共产党史下的诸多议题(乡村治理、工厂建设、政策与组织结构)也同样重在关注具象的个案,包括历史中的人物、事件或政策。例如,孟庆延对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算账派”代表人物王观澜以及该时期政策的研究,应星等人对曾天宇与万安暴动及该时期党组织形态的研究,不仅体现出个人生命史如何与历史事件相互勾连,也对中国革命的组织制度与政策变迁作出了机制性分析。
其次,突出社会学范式,注重与经典理论形成有效对话,试图在梳理事件逻辑与制度成效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验证、修正或丰富。例如,胡悦晗以1945—1949年间的武汉工会作为具体案例,在法团主义理论的视角下对工会中的基本制度与日常活动进行考察,最终认为工会不能达到法团主义整合方案的基本条件。阿拉坦在内蒙古东部某旗县的卫生档案和相关当事人访谈资料的基础上,针对该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防疫运动进行了历史民话志的书写,着重探索其中的秩序操练与社会展演,与福柯在权力分析方面所讨论的规训机制与治理技艺进行对话。杨可以天津东亚毛纺公司和重庆民生公司作为案例,在劳工研究的理论体系下,承接现代化转型背景下人如何转变的核心问题,利用已有调查报告、档案馆材料、公司内部刊物及访谈和回忆录,对民国劳工宿舍的建设进行考察,认为这一体系下的劳工教育、群体关系、劳工发展等议题使得宿舍成为了实现现代文明教化的重要空间。
再次,通过个案丰富已有理论的层次,或为学科上入新理论、提出新概念。例如,孟庆延关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倒欠户”现象背后的制度与伦理成因,主要依托华北某地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资料,集中讨论制度规划与历史效果之间的关系。该研究一方面是对口述史材料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倒欠户”具体情况与内部逻辑进行挖掘,另一方面持续与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等经典理论路径进行对话。此类研究既是对斯科特已有理论的回应,将问题落回“简单化规划”为何失败,也是对该理论的丰富,表现出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之间更为细微的张力。陈映芳借鉴政策学和行政学中的“政策群”概念,剖析云南知青回城运动及其三封公开信如何体现出国家政策趋向的变迁,而在此过程中,知青返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建祠堂等社会现象与政策现象都表现出“家庭化”的取向,表现出历史转折时期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张力。此研究一方面试图将综合政策理论及方法上入社会学研究当中,一方面提出“家庭化”的概念,简明地呈现出当时个人—家庭—国家之间关系的转化。
上述研究切实地提醒学者们,对于理论的运用既需要敏锐的目光,将之作为工具分析个案,也需要反思的精神,避免将历史现象沉入宏大的理论蓝图当中,时刻审视个案研究如何作为经验现象,如何将具体案例中的问题、机制、逻辑作为宏观机制下的特定历史面向进行社会学的剖析。
(四)有关研究差异度的讨论
对于社会学研究来说,一旦涉及对于历史事件与历史维度的讨论,在研究方法上就必然需要对史料与档案进行深入挖掘;同样,当研究触及对事件的“结论”时,又需要在理论基础上归纳出一定机制或趋势,试图厘清各主体之间的关系,这又构成了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探讨。
从对两本社会学期刊涉及历史题材的文献梳理来看,明清史研究较多偏向于社会史路径(19.6%),而近现代史研究则更多采用历史社会学的路径(39.1%);同时,近现代史相关研究总量更多,这可能与这部分研究已经形成积累性议题、档案资料相对丰富的特点有关。而从文献的发表时间来看,2014年以来,历史社会学路径下的相关研究数量趋于稳定,在一定意义上也能呈现出历史社会学在学科内部地位的提升。
讨论与总结
本文延续过往学界对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异同的重要讨论,并通过选取近10年来《社会学研究》《社会》两本社会学代表性期刊上所刊发的共46篇关涉历史维度/历史事件的论文进行评述,概括梳理不同类型的研究所展现出的理论取向与方法脉络,并以性别研究作为具体案例,分析了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学科范式对这一领域产生的影响。
本文认为,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确实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是,其学术发展历程则呈现出了较强的相似性。首先,对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史而言,历史与社会都是其中不能剥离的基础要素。也正因为此,历史与社会的观念变化,都会随时反映在两个学科的路径取向上。特别是近年来,科学化、文化转向、叙事学转向等成为新的关注点,这也使得学科潮流的转变往往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例如,从追求科学化转向叙事与“说故事”,并力图成为“说故事的人”。其次,两者都试图从分支领域的狭窄范畴中突围,着力将自身研究方法与逻辑推入社会学或历史学的根本属性当中,以证明本领域所追求的历史维度或社会维度对学科的基础性作用,进而完成对所在学科的丰富与拓展。
从这一层意义出发,对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异同的讨论,恰恰是对学科边界与学科交叉的探索。事实上,对于历史社会学而言,由此产生的问题正在于“与哪一领域对接”,一旦某一研究呈现出跨领域的特质,就无法摆脱对其基本学术立场的选择,例如历史社会学对于规律与机制的追求,社会史对于通史或综合史的追求。这种学科交叉既是“美美与共”式的,能够借鉴利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或理论,扩展本学科的疆界;同时也是“以人为鉴”式的,通过学习理解其他学科的方法与范式,从而对本学科的研究路径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