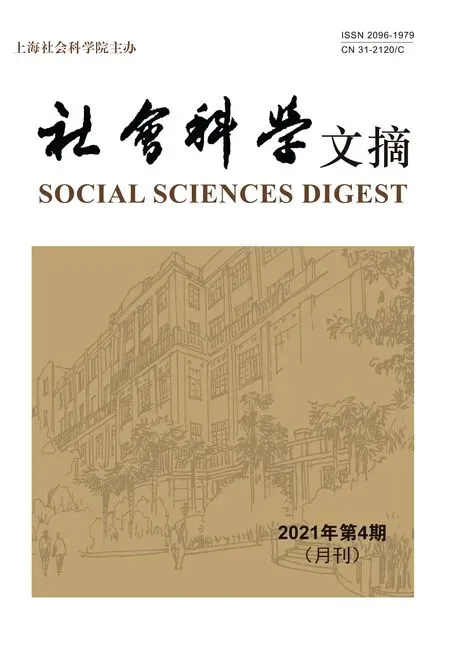特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治理的观念重构与行动选择
——一个基于“文化治理”视域的分析框架
文/胡范铸 张虹倩 周萍
知识决定行动,行动生产知识。新冠疫情的暴发和控制,暴露了当代社会尤其是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个重大问题:信息的生产与管理问题。而信息的生产与管理,不仅仅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治理的过程。
疫情管控:既是“公共卫生的政策过程”也是“文化治理”过程
对于“文化”的理解,今天与上古、中国与西方并非风马牛不相及。受到泰勒定义的影响,今天学界一般都将“文化”看成是一种“名词”。其实,在先哲那里,无论是《周易》的“人文化成”观还是古罗马的“灵魂培育”观,强调的都是“变化”和“过程”。这蕴含着“文化不仅是结构性的,更是建构性的,是一种过程”的思想可能;也蕴含了“文化最根本的在于价值追求”的思想动力。也就是说,文化就是由一个共同体基于历史、面向未来、协同开展的,由器物、制度、观念体系所体现的,感觉、意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疫情的防控离不开信息,通常认为,疫情的治理就是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信息的制定、发布与落实的过程,其实不然,它更是一种“文化治理”过程,是“感觉、意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
“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动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当各自所“依据”的旧的文化规范互相冲突时,意味着社会成员的行动很难协调;反之,当社会成员的行动终于能够协调时,则意味着某种意义的新的“文化共识”已经形成。因此,这里既需要“依据文化加以治理”,同时也需要“对文化加以治理”。文化的构成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等不同层次,其中最根本的是观念文化。人类每一次重大危机,往往都意味着一系列观念的助推;而每一次对危机的克服,又往往意味着新观念的生长。公元前430年—前427年的雅典大瘟疫既导致了雅典“古典”财税体制的瓦解,也催生了以火消毒防疫的观念——“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发现,雅典城中有一类人几乎不染疫情,那就是每天和火打交道的铁匠,由此他联想到也许火可以防疫,于是在全城各处燃起火堆来扑灭瘟疫。这个简单易行的方式,成为其后上千年西方防疫的重要手段之一。没有对于积极性观念的发扬,没有对于陈腐性观念的批判,便很难形成疫情防控的有效共识,也很难形成长效稳定的疫情防控机制,更遑论推进文化的涅槃。
由此可见,无论是“依据文化加以治理”,抑或是“对文化加以治理”,其核心都是对观念文化的“扬弃”过程。这一“扬弃”贯穿了危机预防、应对与善后的全过程。
流言未必一定有害:危机预防中的观念重构与先机把握
在危机预防阶段,信息治理的关键是有效把握先机,既维护正常舆论秩序,又不能干扰社会信息预警,由此就带来两个侧面的工作:一是如何在正常行政系统信息传递之外,及时体察本地危机的社会预警信息;二是如何控制各种“谣言”的传播,防止无谓的社会恐慌。为此,就需要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流言”,什么是“谎言”,什么是“谣言”。
在信息管理中,经常可以看到“打击网络流言”“防止流言蜚语”之类的管理话语。其实,混淆“流言”“谎言”“谣言”之间的区别是信息治理中的常见弊端。
流言就是“没有得到证实而又无法反驳的信息”,与是否“有害”并无必然关联。
谎言就是不合乎事实的话。其实,言语交际中的信息可分五类,即:客观事实;说话人认可的事实与信息;语言形式在客观上荷载的信息;说话人希望听话人接收到的信息;听话人实际理解的信息。谎言的本质不在于一个人说的话是否合乎事实,而在于说自己不相信的话。如果一个人以为已经暴发了疫情,于是告诉了大家,哪怕疫情其实并没有暴发,也不能断定其“撒谎”;反之,如果一个人以为疫情已经暴发,却告诉大家没有暴发,哪怕疫情真的还没有暴发,他依然属于“撒谎”。
在上古,“谣”最初是人类传承知识最基本的手段。两千多年来,“谣”经历了一个由“语言社群记录、传播、传承最重要的共同体知识的主要手段”—“传播民间的认识,尤其民间的批评性意见的主要方式”—“(民间流传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的转折。今天,从信息治理出发,“谣言”应该严格界定为“在公共空间故意传播的已被确证的不实陈述”。这就意味着所谓“谣言”,至少包括这样几个要素:一是“不实陈述”;二是该陈述已被足够证据证伪;三是故意的;四是在公共空间获得传播。
“流言”与“谣言”虽然都不是“真实陈述”,但二者的最大区别就是与“事实”的关系:“流言”内容的真伪是尚未确定的,可能是“不合乎事实”的,也可能是“合乎事实”的;而“谣言”则意味着已经被证明属于虚假的,肯定“不合乎事实”。“谣言”也与“谎言”有关。“谎言”与“谣言”都是“掩盖事实所指”的言说,但“谎言”的生产是“对话性”的,即“生产+消费”;而“谣言”的生产则是“大众传播性”的,即“生产+传播+消费”。只对某一个人撒谎,其意图并不在于广泛传播,不能称之为“造谣”。而对某个人撒谎,并推动这一谎言广泛传播,便构成“造谣”。正因为“谣言”的生产过程离不开“传播”,“谣言”行为的责任主体也就分为两类:“生产者”和“传播者”,“谣言”需要“传谣”者的合作。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造谣”的“原述行为”就是“撒谎”,但“传谣”的“转述行为”却未必属于“撒谎”,他可能是因为相信而“传谣”。
社会需要的是打击“造谣”,对于“传谣”则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信息的生产”是一个生态化的过程。只有充分的信息竞争才能有效地制止谣言。在正常的思想竞争、信息竞争中,市场固然会不乏谣言,但这些谣言通常都不足以危害社会,而一旦试图抑制大部分主体的信息生产,信息的竞争机制失效,真正灾难性的谣言才更容易产生。对于牵涉公共利益的流言,需要的是及时作出说明,而不是简单“封堵”,这意味着不但不能简单采用“封号”的方法,更不能轻易动用司法力量。既要有效“管控网络谣言”,也要有效“保护社会自发性预警信息”。
同时,需要构建多渠道全方位的公共信息流通机制。第一,从“屏蔽”到“发现”。网信管理机构不能满足于“屏蔽不良信息”以“控制舆情”,更要善于借助“舆情”发现潜在的危机。第二,从“发布”到“互动”。政府政务新媒体平台应改变以往单向的“发布”行为,完善社会公众“报告”和“叩问”机制,使得公众的问题发现、心理焦虑都能及时传达到管理和决策部门。第三,从“本地”到“全球”。21世纪是人口全球流动的世纪,也是疫情全球流动的世纪,更是信息全球流动的世纪。特大城市治理,不仅要关注本地的疫情信息,同时还必须对全球的疫情信息保持足够的敏感。在本次疫情初发时,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经验就是,在武汉发出明晰的预警之前就已经捕捉到了危机的动向。第四,从“闭环”到“竞争”。社会治理需要构建成为一个“太极结构”,即各个层面各个角度都能够互动的结构。语言是一种生态,在正常的思想、信息竞争的语境中,世界上可能充满流言,但这些流言一般并不足以危害社会。正如我们不能老是依赖抗生素去杀身体里面存在的各种微生物,在非常时期才可以使用抗生素来抑制某一部分的微生物,正常情况下微生物自己会产生和谐状态。如果每个人都能自主地、如实地、没有恐惧地表达对世界的理解,不但所谓流言的负面影响将被极大地缩小到可接受的范围,而且那些建设性的力量更容易获得流通。
信息发布不只是政府责任:危机应对中的观念重构与社会动员
危机一旦发生,信息治理的关键是有效进行社会动员,既能及时全面采集疫情、民情等各种重要信息,又能使政府信息发布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由此便需要明确“何为信息责任”。
公共安全危机管理,尤其是疫情危机管理首先是一种“社会动员”行为,需要动员全社会每一个人参与。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的发布与接收”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社会的每一方都需要确立“信息责任”的观念。
第一,主管机构的信息责任是“以民为本,实话实说”。这要求城市主官要有“预案意识”“危机意识”“行动意识”“担当意识”“数据意识”“法治意识”“情感意识”“战略意识”。
第二,新闻机构的信息责任是紧紧盯住那些直接关乎全社会根本利益的事件。这包括越是重大问题越是要主动说、越是重大的问题越是要及时说、越是重大问题越是要全面地说、“不说”也可能属于“造谣”。
第三,执法机构的信息责任是保护而非遏制信息的自由流通。如果执法部门在疫情初发、信息明显供给不足时,对于发布事态发展传闻的市民盲目“依法处理”,显然有违保护信息自由流通和自由竞争的信息责任。
第四,疑似感染者的信息责任是主动告知、及早就医。疫情不仅是个人身体健康问题,更是公共安全问题,因此,一旦发生疫情,任何疑似患者及其家属都有义务将自己可能牵涉疫情的信息如实地向有关机构报告,争取进行及时的隔离与治疗。
第五,社会公众的信息责任是推动危机解决而非制造危机。就社会公众而言,其信息责任首先就是认真监督:监督有关方面的信息发布是否合乎事实,监督有关公权力的运用是否合乎人民利益。公众所发布的各种相关信息,只要不是自己恶意瞎编,哪怕是传闻不确,也是在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当有关公权力信息供给明显不足的时候,公民把自己所目睹的、所知晓的有关现象,把自己的内心诉求和紧张直接发布出来,与其他社会成员共享,形成一个有关该重大事件的“信息拼图”,这也是一种公民的“信息责任”,有利于促进危机的化解。
“正能量”应避免幸存者误差:危机善后中的观念重构与疫后恢复
在危机善后阶段,信息治理的关键是化危为机,重构社会信任和政府认同,推动国家形象提升和社会发展,由此便需要重新认识“何为正能量”。
首先,要完善疫情信息的认知框架。特大疫情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也造成全社会生活生产节奏的紊乱,由此导致社会情绪甚至社会价值观的紊乱。因此,疫情一旦受控,最重要的首先是纾解恐惧,推动社会生产生活的有序恢复。为此,在疫情信息发布上要继续注意:
第一,完善“健康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框架。这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1)已经形成的全球疫情播报必须坚持到全球疫情完全受控为止;(2)国内新发疫情必须及时加以充分说明;(3)报道其他国家疫情必须坚持同理心;(4)报道全球疫苗研发与接种进程必须客观准确;(5)报道全球疫情致病率、重病率、死亡率、医护压力时应该注意空间变化和时间变化。
第二,完善国内疫情信息认知框架。任何疫情的应对行为都需要支付相应的社会成本,而疫情的强度有高有低,为了有效降低社会成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改变空间分割的认知习惯,完善以市、区、小区为单位的疫情分区管理模式,无须因一两个病例影响过大面积,一碰就导致“全省战时状态”“全市进入高风险”;(2)改变不分强度的认知习惯,完善口岸、医院、学校、地铁和其他公共空间的分级管理模式,有序解除过度的管控措施,适当鼓励公共生活;(3)改变传统公共卫生的认知习惯,实行就医戴口罩、公共场合设消毒洗手液、就餐使用公筷等防疫卫生措施,并将之制度化,使之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习惯变革的一个契机。
其次,要重建社会的情感认同。在疫情的防控过程中,群体情感冲突高发,而社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最核心的其实就是情感共同体。而疫后的奖罚分明,无疑是重建社会情感认同的重要路径。
第一,恰当表彰有功人员。(1)所有在疫情中殉职的医护人员都应被授予“烈士”称号;(2)建立“医护纪念牌”,弘扬为公众牺牲精神;(3)设立医护特别后援基金,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对所有在本次抗击疫情中因公死亡的医生护士,对今后所有在各种救灾中因公死亡的医生护士,乃至今后所有在医疗岗位上被医闹杀害的医生护士,都考虑由这一基金给予数倍于普通工伤的抚恤;(4)医护奖励应该“论功行赏”,政府可以用自己的无形资源或有形资源奖励医护人员,但用其他群体的利益“转移支付”给另一个群体的做法必须慎重。诸如“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加分”的政策,其用心虽好,但效果有明显缺陷。教育是社会的基础性领域,教育政策必须保持前瞻性和稳定性,不能简单当作临时的救济措施。为此,可以采取的方法是:其一,鼓励医护子女报考医学类学校;其二,医学专业学费全免,鼓励贫困学生报考。
第二,严厉处置过错人员。对于在疫情中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员,必须及时加以处罚。对疫情负有重大过错的人员如长时间得不到处理,也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的情感认同。
最后,要深刻反思,避免一味地简单庆功。疫情管控成功,自然得益于全民的努力,该表彰的必须表彰,幸存者也都可以大大松一口气。但在整个事件的处理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那些遭遇不幸的家庭。这时最需要的是总结教训,不宜过度庆功,更不可把整个事件“悲剧”当成“喜剧”。
总之,特大疫情中的信息治理,既是一场剧烈冲击文化观念、文化秩序的危机,又未尝不是一种促进文化自省、文化更新的机缘。疫情防控和疫情信息治理,不仅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治理的过程。这里,既要“依据文化加以治理”,也要“对文化加以治理”。这意味着,在危机预防阶段,信息治理的关键是有效把握先机,既维护正常舆论秩序,又不能干扰社会信息预警,由此便需要重新认识“何为流言”;危机一旦发生,信息治理的关键是有效实施社会动员,既及时全面采集疫情、民情等各种重要信息,又能使政府信息发布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由此便需要明确“何为信息责任”;危机善后阶段,信息治理的关键是化危为机,重构社会信任和政府认同,推动国家形象提升和社会发展,由此便需要重新认识“何为正能量”。没有对于积极性观念的发扬,没有对于陈腐性观念的批判,便很难形成疫情防控的文化共识,也很难形成长效稳定的疫情防控机制,更遑论化危为机、推进文化的“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