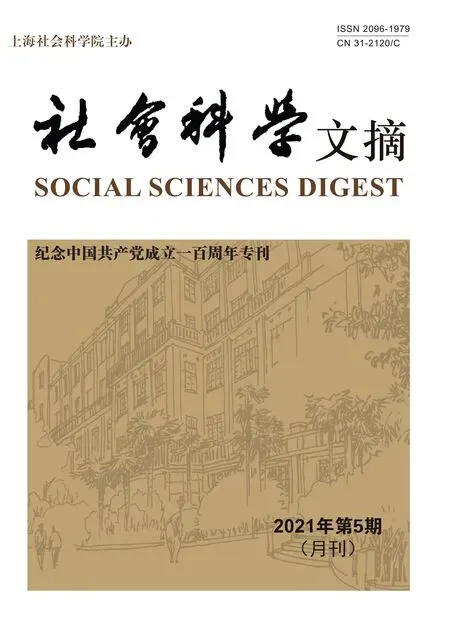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文/周良书
“范式”这一术语,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入的学术概念。它是学术共同体成员在开展科学研究中所共享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或集合。在库恩看来,当科学发展到某一阶段,总会出现一种主导性的研究范式,并形成关于某一问题研究的主流观点;而当这种主导范式不能解释的“异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产生范式的更替和转换问题。这一情况将促使关于某一问题的研究重新进入“百家争鸣”的状态。其实,在百年党史的研究中,研究范式也常处在不断更替和转换中。也正是这种更替和转换,推动了党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者认识的不断深化。
“革命史”与“现代化”
在党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新生产力和旧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革命虽然是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但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只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一指导性的线索,才能在充满矛盾的迷离混沌的阶级社会中,把握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洞察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业已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既然如此,那么研究者就应当以此作为历史评判的标准和参照系。
这一研究范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史学界,早在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就明确指出:“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单纯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按自身的发展过程划分阶段)。”与此同时,胡绳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而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时限内的一部专史——中共党史,自然也应当以革命史为基本线索,分析和评判党史上的人物与事件。
“现代化”范式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它试图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一的“革命史”叙事结构,从另一个角度开辟历史研究的新路径。按照这一分析框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在党史学界,张静如先生是这一研究范式的首倡者。他提出“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衡量历史人物、政党及各种群体的作用”,并强调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核心,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
但这两个范式也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它们还在各自的解释体系中为对方保留一席之地。一些主张“革命史”范式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复杂,丰富多彩,从任何一个侧面或角度为视角去观察、研究它,都将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因此并不一味反对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考察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而主张“现代化”范式的研究者,则认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这一“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它有利于对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作多角度观察,有利于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多方位思考。
因此,从这个思路分析,运用“现代化”研究范式,就可以拓宽党史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弥补“革命史”研究范式的某些不足。正如胡乔木指出的:“革命者在很长时间内是人民中间的少数。柔石写《二月》,鲁迅写《阿Q正传》,写《呐喊》《彷徨》的时代,虽然有共产党,但他们没有写共产党,不能因此说鲁迅就是反革命。”但倘若使用单一的“革命史”研究范式,就无法对柔石和鲁迅予以合理的分析和评价。
又比如,对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评价是一个难题。因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他们不仅一直处于校内派系斗争的中心,而且还被迫应对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他们夹在政府与学生之间,处境十分尴尬。在北京大学,蔡元培以其地位与个人魅力,可以用不断辞职作为武器。不过,这一点并不是每个大学校长都能够做到的。然而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我们以是否支持革命运动作为评判人物或事件的唯一标准。这既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也不能准确体现中国共产党在高校的政策。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并不希望一味地革学校的命,把学校都办成像“抗大”“陕公”一个样,而只是在承认和利用现行学校制度的前提下,来组织和发展自己的力量。
“单线史”与“复线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采用的都是线性的、进化论的、目的论的叙事方法,它们均根据现时的需要,来诠释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并以此建构各自的历史表述。这种叙事策略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拷问。因为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非中心、多样性等观念,与现代观念所主张的有中心、线性发展等观念完全不同。其接受的是米歇尔·福柯的观点,认为历史在行进中不断会有“散失”。后来杜赞奇继承并发展福柯的这一历史观,在中国史研究中提出“复线史”的叙事方式。他试图以此打捞散失在历史缝隙和裂纹中的不同声音,用多样性来替代单一体的演化,从而打破“线性历史”的封闭叙事。这对于我们党史研究也有极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首先,在复线的历史中,客观的历史被视为一种“同时兼具散失与传承的二元性或复线性的运动”。它要求我们必须努力收集线性历史中的已有记录,同时还要善于打捞那些被线性历史压制或遗弃的过去。也就是说,在历史叙事中,我们“不能以为会吵会嚷的演员才是真正的演员,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其他演员,只是保持沉默而已”。其实,历史主体从来不是历史中单一性的身份认同,我们所表述的研究对象也仅仅是相对的、暂时的,它只能算是众多身份认同当中的某一种。因此,必须打破这种单一化的历史叙事,将目光投射于线性历史之外,关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并恢复其历史主体的身份和地位。
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应当关注和重视这一点。胡乔木说:“党的历史是群众的历史,也是共产党员群众的历史,不仅仅是党中央某几个人的历史”;要“有意识地多写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在各个革命时期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虽然不可能详细地写,但是应该提到。也要选择一些普通的党员加以描写。这样,党的历史就不是一条线的历史,也不是一个面的历史,而是立体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保持沉默”的人民群众,对此我们也需要照顾到。
其次,在复线的历史中,现在与过去之间存在一种交易关系,现在通过打捞和利用业已散失的意义来重构过去。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的意义逐渐散失,而嫁接以相应的新的历史意义。在通常情况下,新意义指示着重心的转换或转喻性地与更早的意义联系起来。它赋予历史主体一种创造既作为过去又作为未来的历史的能力,并促使未来的历史向着此种叙事结构的内在方向或目标发展。杜赞奇提出“复线历史”,其目的就在于发掘历史意义的这种替代或转换的方式,收集那些被主流话语所压抑或利用的叙事结构。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党观念的改造和利用,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党”是受人摈弃的东西,中国士人向以君子为名,当然不肯与党有涉。正因为此,维新派试图用“政党”与“朋党”作区分,认为“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而遂行其志意,故联合同人为一党也”,而“朋党者,本小人之事,每以阴险为手段,在牵制君主之肘,以营利于其间”;鉴于国人以结党足以乱政,他们又强调其与“革命党”之不同,认为“偶有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逼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这种创造性的阐释,虽极大地缓解了国人对“党”的疑惧心理,但其对“政党”与“革命党”的刻意区分,也迫使“革命党”人极力与之拉开距离,以防玷污其革命的精神。比如,1905年在同盟会的预备会上,孙中山就宣布“本党系世界上最新之革命党”。而十月革命后,他又迅速把目光转向俄国,认为“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楷模。这恰好与中国共产党创立者的思路相契合。因此,我们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君子不党”这个中国文人所坚守的古老教条何以在十月革命后的1920年代会被彻底打破。
总之,“复线史”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为历史展现了更多分立并存的叙事结构,但它并非有意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当然也无法颠覆“单线史”所揭示的中国人民选择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其实,它是要借此使历史摆脱大家所熟知的叙事结构,以展示历史认同的能动性和多样化,以及各种历史表述之间的竞争性和替代性。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找回未被污染的、原始的中国史,而是为了确定一个场所,在那里,多层次的叙述结构或是在摄取历史之真或是在同历史之真挣扎,而历史之真除了通过叙述象征以外是不可得知的”。
“大历史”与“小历史”
“大历史”,即“大写历史”,它着重系统分析或整体研究,致力于历史事实的全面陈述与宏观把握;“小历史”,即“小写历史”,它着重个案研究乃至细节研究,致力于历史事实的钩沉拾遗与精审考订。近些年来,后者在中国史学界异军突起,大有超越和取代前者的发展趋势。在研究范式上,它也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从另一侧面反抗和瓦解现代主义的叙事结构。它主张研究单个的个人而不是社会或阶级,所描述的时空范围,甚至是几天而不是一个时代或长时段的发展,是一个小群体或小村庄而不是一个政党或国家。
在党史学界,这一研究范式也是方兴未艾。它通过对党史宏观叙事中的某个事件、村庄或学校等诸如此类的个案进行历史分析,把微观层面作为党史研究的着力点。其主要特征是“目光向下”,由以往偏重上层的政治事件与人物,转向下层社会和普通民众。这样,一方面可以拓宽党史研究的领域,改变过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方式,以防止大家都挤在某一条狭窄的道路上。另一方面,“小历史”也是“大历史”的始基。吕思勉说:“小事似无关系,然大事实合小事而成。一节模糊,则全体皆误。”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小历史”还可借助显微镜式的微观探头,将历史中枝蔓缠绕的复杂情态呈现出来,使之变得“有血有肉”,因而更加贴近真实的生活。正如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指出的:我们对宫廷和宫廷生活的了解是事无巨细,但却不知道鲜鱼怎样装在水箱里被运到市场,在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种野味的贩卖,我们从中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
其实,在党史研究中,人们过去习惯于处理“宏大叙事”,而忽视对历史细节的深刻分析,这样的确使我们的研究失去了许多鲜活的质感。比如,在高校党建史研究中,我就发现了一些在“大历史”中所见不到的内容。1928年12月厦门大学学生与校工的冲突,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原来厦大学生向水房要水洗澡,但水房已经关门歇业。“学生乃用力攻打水房门,因水房工人(是同志)系在室内睡觉。后门被攻开,水房工人乃与学生发生口角,继而相互殴打。”天之骄子受人殴打,自然怒不可遏,于是向学校提出交涉,要求开除肇事工人,签名者计有一百余人。“我们的同志——工人,始不敢向团体报告,及到签名纸张到我们的学生同志时,学生同志去问他,他才将情形详细说出来。当时支部会决定我们这次斗争的目标要设法转到学校当局方面去,由水房工人发一告全体学生及各界书,内容将此次与学生冲突的经过和工友平日生活的痛苦细述出来,驳斥学生的无理欺侮工人,及要求学校当局改良工人待遇。”但结果没有成功,工友“大概寒假时一定会被当局开除出去”。这表明校园也是一个由校长、教职工和学生组成的小社会,只有将党置于这个特殊“社会”中来观察,才能揭示出党在高校发展的真实状况。
但是,研究“小历史”,其目的还是为了写好“大历史”。倘若一味地追随后现代主义,主张“历史学必须放弃宏观综合,改为关注零碎的知识”,不应再描述历史的演变、进步与连续性,只需“发掘众多不连贯的瞬间”;这样长此以往,“历史学将逐渐失去自我”,“也将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只要我们检讨当下党史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失语,对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研究甚至陷入“节日学术”或“纪念史学”的困境,就会发现这种“危机”绝非危言耸听。
当然,要写好“大历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众所周知,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曾以书写“大历史”闻名于世,在《黄河青山》一书中,他说:
在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任教时,我们“赖以维生的课程”是“亚洲文明导读”。在这门课程中,中国历史仅安排四节课,所以在四个五十分钟内,必须讲完中国文明从天上到人间、从孔子到毛泽东的全部内容。……讲课中还不能遗漏重点,只会丢出一长串历史事件名单也是不行的,散乱的事件必须彼此相连,以便让一个个独立的故事形成整体,描述要求既翔实又生动,时刻抓住初学者的注意力。我的方法是先写下所有初步的念头,而后再慢慢充实内容。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我被训练成以大历史的方式来思考。
由此可见,“大历史”是由无数个“小历史”所累积而成的。所不同的是,“小历史”主要关乎“学”,“大历史”主要关乎“识”。“学”要扎实细致,“识”要远大通透。就党史研究而言,无论是整个学术界,还是治学者本人,都需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总体上的平衡。梁启超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解剖”和“鸟瞰”两种治史方法,来说明它们在具体研究中的互补性。前者“在知底细,令读者于一章书或一件事能得一个彻始彻终的了解。好像用显微镜细察苍蝇,把苍蝇的五脏六腑看得丝丝见骨”;后者“在知大概,令读者于全部书或全盘事能得一个明了简单的概念,好像乘飞机飞空腾跃,在半天中俯视一切,看物摄影都极其清楚不过”。因此,治学者“一面做显微镜式的工作,不要忘了做飞机式的工作。一面做飞机式的工作,亦不要忘了做显微镜式的工作。实际上,单有鸟瞰,没有解剖,不能有圆满的结果。单有解剖,没有鸟瞰,亦不能得良好的路径。二者不可偏废”。因此,我们都要把它们搜罗来,作为治史的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