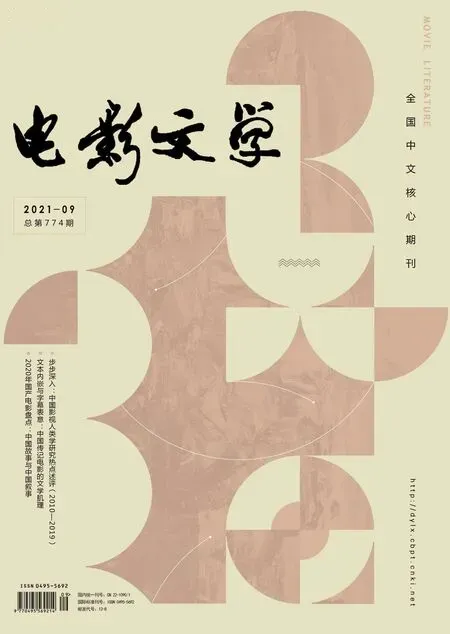中国形象:跨文化改编视角下的新移民电影
马阿婷(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发展,跨文化传播对于中国形象的建构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跨文化传播路径当中,电影的作用日益凸显,因为随着人们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对视觉的效果有了更高的追求,电影的震撼效果与高大上的观影体验无疑是提升生活品质的绝佳选择。出于对观众心理的分析与观众口味的迎合,电影题材从家庭伦理片、好莱坞大片、纪录片、都市言情片到系列动画片、系列贺岁片等类型电影占据了各大影院的各个档期。而近年来,新移民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越来越受到各大导演的青睐,笔者以北美华裔女性作家严歌苓创作的《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芳华》《妈阁是座城》等文学作品为例,深入分析其成功改编为电影脚本,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票房收益的原因不难发现,这些文学作品拥有了大量的读者粉丝,文字的力量使得读者怀着猎奇的心理想一探其视觉上的奥秘,进而读者演化为观影者,而作家也随之成为编剧。虽然身份的转变凭借一张电影票就可以完成,但文字转化为镜像确需一定的功力。
一、文化折扣:光与影的留白
以严歌苓为代表的新移民文学已经形成具有一定基础的文学产业链,形成了一定的品牌规模,由于其文字充满画面感,饱满的色彩似乎在银幕上呼之欲出,文学作品受到许多知名导演的青睐,获得不错票房业绩的改编电影同时也反哺文学作品的流传。著名导演冯小刚曾经说过,严歌苓的《芳华》是他电影心愿清单的最后一部。从严苛地挑选演员,努力还原历史背景,光影的流动,富有时代特点的色调,到或高昂或温婉,或澎湃或温情的配乐,使观众不无感知冯小刚导演对此部影片倾注了太多的情感,而这份情感足以跨越时代的限制,无论是否熟悉那个时代背景的观众都会被深深打动。曾经读过严歌苓的原著的读者也不难发现,看过书再去看改编的电影会变得更为苛刻。但是冯小刚导演的《芳华》对人性的剖析更多地运用了留白的手法,隐晦了很多,让观众运用各自的认知与心境,进而产生不同的观影体验。尤其是文工团的男兵和女兵对刘峰前后态度的转变,由先前的同情理解到后来的集体批判,然后萧穗子在多年后回首这段历史时的独白。这些都是原著《芳华》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但电影导演无意呈现,抑或是文学与电影毕竟是不同的艺术介质,文学作品以文字的形式引领读者,而电影需要观众加入自己的想象来呈现立体的艺术,个性化的艺术,光与影的加持才使得观众在艺术的留白中努力寻找黑暗中的那个自己,这也是文化折扣的魅力。
二、后殖民书写:新移民电影的美学价值
随着二战的结束,西方殖民主义的土崩瓦解,全球经济逐渐进入一体化发展进程,但西方文化依然以高语境文化姿态自居,后殖民倾向也渗透到对电影美学的评判中。国产影片鲜少涉及的“文革”题材却由移民作家严歌苓将她的文学作品《陆犯焉识》改编为电影《归来》,将人物的命运与国家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在黑白颠倒的“文化大革命”背景下,导演张艺谋对电影灰、黄色调的把握充分彰显了对“那个年代”的理解与感悟;主演陈道明深邃沧桑的眼神,在“红色风暴”中挣扎的“臭老九”形象,呈现出时代的印记;国际巨星巩俐饰演的冯婉喻对爱情不懈的等待,等待陆焉识的归来,冯婉瑜一辈子都在等待,但是她一辈子都等不来,因为她的失忆。为什么严歌苓让冯婉喻等了一辈子等到“失忆”了?因为这段历史太痛苦,记忆太痛苦。怎么办呢?失忆,只能把这个记忆失掉,抹去。这是痛到极限的一种痛苦,不仅表现出东方女性的隐忍与执着,也是民族记忆中的一段缺失。虽然电影《归来》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爱情片,但影片将特有的时代背景,知名导演对改编剧本的理解,一流演员的演绎杂糅在一起,便丰富了荧屏上的电影创作题材,也迎合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窥探心理,展示他者文化的神秘正是移民作家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脚本的创作源泉之一。在后殖民主义视角下反思中国电影的传承与发展,不能否定的是新移民电影大胆地拓宽了电影主题的选择,提升了电影的民族趣味性,呈现了独特的美学价值。
三、性别话语:新移民电影的女性主义
在移民题材的电影中,性别书写一向是永恒的主题,因为人,无论是男人或女人,构成移民经历的主体,移民电影一定是把这种母国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双向体验作为电影的主旋律,或呈现时代特色,或展现文化的交融,所以性别话语是移民电影的主要表征。而在新移民电影中,男性角色一般处于失语的状态,女性占据着主要的话语权。尤其是极具女性魅力的移民作家严歌苓,她所创作及改编的电影剧本,更多地把移民问题与女性、族裔、时代、人性这些普世性的话题结合起来,如扶桑,如小姨多鹤,如少女小渔,都是把中国女性置于感性地位,以感性拯救理性,以女性拯救男性,以弱势求生存的态势演绎“地母”形象的善与美,不争和不反抗有着甘地的精神。东方母性情怀或是天生的雌性使得移民电影中的女性多与自我牺牲和自我救赎联系到一起,温良谦恭,至善至美的母性形象代表了东方文化的包容性、宽恕性,体现了天人合一,尊崇自然的生命法则。无论是经典的移民电影《少女小渔》《妈阁是座城》,还是坊间流传即将开机拍摄的《扶桑》,其中的女性形象都以不善言语,经历坎坷,却以传统的“仁义”美德宽容男权的束缚,宽恕她们所遭遇的种种不平。严歌苓在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剧本的过程中并没有一味地迎合西方价值体系,也没有固守东方传统文化,而是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努力寻找相似文化基因,寻求东方文明的文化内核,赋予新移民电影跨越文化障碍的内生动力,通过新移民电影打破文化壁垒,实现跨文化平等交流的目的。
四、中国形象重塑:新移民电影的文化传播价值
中国形象包括中国文化,即物态文化,行为、制度、精神文化;景观文化,即城市景观与自然景观;华人形象,包括外在形象和内在形象。通过媒体艺术传播中国文化有利于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在文化外宣过程中,电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传播媒介的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建构无疑有重要的作用,除了主流政治大片如《建党伟业》《八佰》,纪实纪录片如《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等对中国形象的宣传有主导作用,为数不多的新移民电影则从华裔导演或编剧的视角为世界展现出别样的中国,正是华裔导演如李安、王家卫用跨越文化的独特审美视角,创作出了多部脍炙人口的电影佳作,提升了国产电影在世界电影的地位,进而提升了中国形象。新移民电影尤其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化呈现效果,对于物态的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刻画可以在导演王家卫的影片中找到答案,如电影《花样年华》中氤氤氲氲的大上海气息,别致的旗袍造型,暗哑的光效都是物态化的中国形象,从而形成对旧上海的刻板印象。而华裔导演李安的电影作品更多地注重华人形象的塑造。李安的三部电影被称为“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中以一位华人父亲形象为主线,所以又被称为“父亲三部曲”。华人父亲与美国文化之间冲突与碰撞也代表着新老移民在跨文化沟通中的困惑与迷茫。
而作为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后,对于中国形象的重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导演张艺谋与严歌苓联手打造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入围第62届柏林电影节展映,获得华表奖、美国金卷轴奖、亚洲电影传媒奖等多项大奖,严歌苓一向以军旅题材、移民题材、知青题材、女性题材为主要创作来源,《金陵十三钗》是她唯一一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剧本,通过战争表现人性,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中国女性的侠义血性是对中华民族这段苦难伤痕的特殊记忆。这种“悲惨的绚丽”构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群体意识,即相对于西方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表现战争题材的新移民电影没有可歌可泣的典型英雄人物,没有枪林弹雨的浴血奋战,但是新移民电影的创作者却能从西方文化可接受的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群体记忆,“善于记住苦难和展示苦难的民族一定是伟大的民族”。新移民电影对于中国形象的重塑有着重要的意义。
结 语
关于新移民文学与电影脚本的良性互动是本着两条腿走路的原则。一方面必须以尊重文学原著精神内核为原则,坚守艺术的独创性,回归艺术的本真,剔除功利的色彩,最大限度地尊重原作,忠实于原作才能把固有的读者群变成电影的粉丝群,才能博得观众更好的口碑,文本与剧本之间的转换,并非是文字与影像之间的切换,也并非是作家与编剧、读者与观众之间身份的变换,而是作者、编剧与观众三个主体之间共通共融,美美与共的结果。
另一方面,文学是电影的精神家园,在新移民文学影视化的过程中一定程度的扬弃也是在所难免的。由韩国导演许秦豪执导的电影《危险关系》的成片对严歌苓的剧本改动很大,最终只用了其中的两句台词。但是原创编剧严歌苓还是尊重导演的选择,尊重电影的影视化效果。所以说,在传承与蜕变中可以依据影片的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增加对影片的文化折扣和文化增值的预判,坚持对文学文本的合理转化,避免文字符号化,情节场景化才能赋予文学作品艺术形态上的华丽变身。
关于电影作品对中国形象的影响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国外大片还是本土的国产影片,任何品类的电影只要在中国的银屏上展映,对于中国国家形象、中国人形象的建构都有一定的影响,而处于边缘小众的早期移民电影,通常都是展现淘金生活、唐人街生活等苦难历程,而新移民电影则从全球性的文化视角打破了西方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既摆脱了自我东方主义,又重塑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尤其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一带一路”政策的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成果更是向世人展示了日渐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相信通过越来越多的新移民电影,搭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传递异质文化中相似性的文化基因,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精神、重塑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