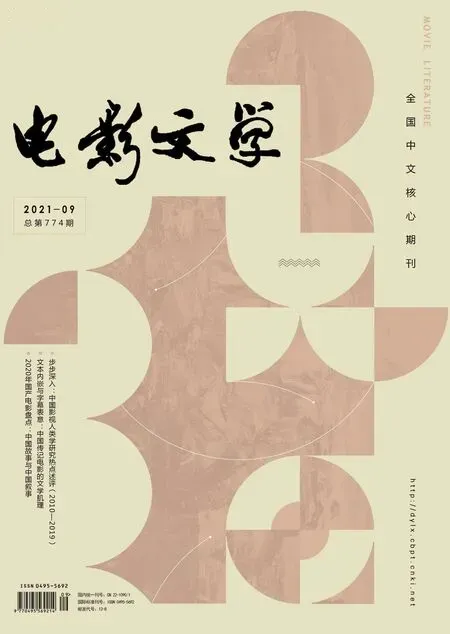主旋律仪式下的集体记忆建构
李 强 刘泽溪(.新华通讯社,北京 0003;.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0087)
一、互动仪式链与集体认同
(一)互动仪式
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仪式”也在不同领域分化出多样种类,其定义范围和概念边界也不断外延。一般来说,仪式是群体建立内部认同和维系群体间关系纽带的组织方式,能够“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成员的心理状态”。
从历史学范畴考察“仪式”的内涵,可以将其拆分为“仪”和“式”,所谓“仪”者,《说文解字》记载,仪者,度也,从人。“仪”的本初含义是法制、标准,“仪”是贴合人性、自然、社会规范的法规制度。
在《汉语大词典》中,“仪”既可以作为名词理解为“礼仪”“典范”“规范”,也可以作为动词解释为“取法”“适宜,匹配”。而仪式指按照既定程序进行的集体化行为。仪式的举办服务于特定的目的,譬如纪念重大社会事件、构建集体记忆、建立集体认同,在呈现方式上具有稳定性、重复性和程式化特征。
作为人类最久远的群体性活动之一,仪式活动可追溯至人类部落时期甚至更早,随着人类生存方式的演化,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祭祀占卜等古老仪式形态,逐渐分化出宗教仪式、生命仪式、政治仪式和娱乐互动仪式等多种样态。
作为一种特定的现象,仪式不仅意味着时空场景、物质摆放和行为活动,在仪式符号表象之下还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秩序、观念信仰与价值追求。国家仪式作为一种宏大的集体仪式,不仅承载着国家主体的意识形态,也是国家凝聚国民价值观、强化自身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而国家视角下的仪式叙事,呈现出价值信仰符号化、仪式流程重复化等特征,使之成为国家共同体身份构建的重要途径。
(二)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
无论是作为生物主体、社会主体、政治主体还是理性主体,人类相比于一般动物都存在其特殊性。关于人类本质的探讨,无数学者曾为此皓首穷经,却都无法给出完美定义。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化,“人”处于动态变化的概念中。
人类除了对基本生存需求的追逐外,还有对情感、意义、价值实现的追求。人类文明的推进以及现代社会的演化,人类集中力量去建立一个思维和情感的共同世界。对意义确定性的追求,也就是对“认同”的追逐。
亨廷顿将认同意识定义为“自我意识的产物,是一个人活在一个群体的自我认知”,是人类追求一种身份、存在意义与心理安全,也是人们通过构建身份、生产意义以确定自我存在和价值实现的过程,按照认同有机联系的分类,认同可以划分为“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所谓个体认同,即主体寻求相对固定的心理状态,并在自我认知、自我定位中寻求的“身份的确定”。而较宽范围的集体认同,指的是特定群体在特定文化语境、社会背景和意义建构中所构建的群体性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作为个体自我认知的坐标,身份标签的淡化带来了个体的迷失及群体性认同危机。甚至导致共同体的松散。尤其是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既有的行为主体以及群体划分边界逐渐模糊,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各种社会实力的聚集化和多元化,社会团体的聚合、分化、解体与重建不断加速,集体认同面临外部力量抽离以及内部力量撕裂的双方冲击。
除了基本的生物属性、追求底层的生存需求条件外,人类还是兼具群居属性的社会存在,集体是个体的集合,而个体也是集体的部分。个体安全感与认知的不确定性直接相关。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可以看作不断消除不确定性的过程。
不管是自我认同还是集体认同,都需要保持自我人格与身份的连续性。身份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综合产物,让个体获得并肯定某项身份标签的同时,也就将自身置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集体认同通过对集体成员进行分类而实现,在这种机制中不断调整认同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通常来说,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紧密相关,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
仪式作为一种惯例,其意义生产体现为对传统的崇敬。仪式维系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连续性,并给予参与者心理慰藉和本体性安全。
(三)集体记忆
任何机制要想维持良好状态,就必须控制其成员的记忆。个体记忆直接关乎对过去叙事和个体的历史认知。人们可以借助记忆不断穿梭于过去与现实,并根据自身经历不断建构生成全新记忆。
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一个流动的、碎片化社会,个体身份更加不稳定,其身份标签的建构与瓦解也呈现流动化。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身份结构部分依赖于社会框架和关系结构,当个体缺失心理群体归属时,其自我认知也会陷入缺位、迷失、焦虑。
哈布瓦赫最早使用“集体记忆”来定义记忆的社会框架以及记忆与特定社会群体的关系。所谓“记忆”,指个体对过去发生事件的印象,涵盖着在社会文化情境下将过去和现在乃至未来关联起来的生物性、媒介性或社会性的过程。而“集体记忆”并非是个体对过去发生事件的精准记忆,而是群体对共同经历的润饰、完善与重复。在对集体记忆进行反复构建的过程中,个体会不断形成全新的自我认知并消除分歧,在支配主体的引导下达成认同。
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其表达与实现离不开社会仪式和个人实践这两种方式。一方面,基于共同经历而累积的记忆片段在仪式重复上演中得到确认;另一方面,集体也会基于既有共识和认同不断创造新的记忆。
不同的集体记忆形成过程具有共性。集体怀旧意识的形成过程以符号载体的意义建构为基础。
一般来说,集体记忆的建构需要依赖视听结合的表意符号系统,凝结了内容生产者的审美、经历和精神。影像符号比起单一的文字符号、图片符号更生动逼真,且具有多异性,也蕴含着更加深刻的文化内涵。
二、仪式传播视角下的能量聚集
根据互动仪式链理论,人媒互动所产生的记忆积累和仪式认同,可以视为一种情感的动态变化过程,从初期加入并亲身参与再到情感聚焦,整个过程会产生包括道德、愤怒、快感等情感。这种情感能量通过互动仪式产生,经仪式链传播,促成社会成员之间情感资本的交换。通过互动形成产生的短期情感体验会伴随着互动程度的加剧持续积累和转化。
作为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核心概念,“情感能量”可以解释为互动参与者所受到的情感刺激,即仪式参与过程中共享的情感体验。尽管这种情感只是瞬时性的,但经过互动仪式的重复、累积和强化,可能转化为群体间共有的集体兴奋,进而产生其他类型的情感。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短期情感,互动仪式产生的情感能量长期保持稳定状态,为群体成员参与集体仪式提供心理动力、执行力和自主决策能力。
情感能量也是一个递进的连续统,高度的情感能量可以提供高度价值实现与自我满足,中间程度则表现出平淡的情感状态,而低度情感状态可能表现为意志消沉。在互动仪式中,情感能量往往作为无形的资源流动于社会成员之间。当个体越来越密切地关注到彼此共同行为时,也越能体验到情感共享,继而形成瞬时集体兴奋,将此前储备的情感能量转化为长期记忆和参与动力。
互动仪式同时也是一种群体间相互关注的情感机制。当粉丝群体建立集体行为和集体记忆后,说明互动仪式已经建立起情感协调。此前积累的情感能量在作用于群体后,游离于群体成员获得归属感并形成群体团结。在这种共同情绪的驱动下,对符号的崇拜会转化为对群体身份的认同以及维护意向,并自觉尊重和维护群体符号。对于不尊重群体符号的他者及其言论行为,也会进行集体抵制。
人是悬挂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而个体身处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共同构建了意义之网的宏观背景。仪式营造了一个意义生产的场域。如果将现代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不断消除不确定性的过程,那么仪式就是人类消解生理、心理不确定性的渠道。
仪式将程序构建的等级秩序投射到社会秩序中,赋予其一定的权威性和合理性。按照涂尔干的观点,真正的宗教信仰总是某个特定集体的共同信仰,这个集体不仅宣称效忠于这些信仰,而且还要奉行与这些信仰有关的各种仪式。这些仪式不仅为所有集体成员逐一接受;而且完全属于该群体本身,从而使这个集体成为一个统一体。
对于特定的群体而言,仪式能够整合群体成员以确保集体的存在和运转,通过秩序维持机制,确立某种基本社会价值。即便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不断削弱仪式的根基,但仪式依然满足着人们生存背景和面对现代化风险寻求慰藉的诉求。
仪式作为一种符号聚集体,不论承载何种样态的符号,都充满着象征性意义,仪式赋予感情神圣统一的表现形式,从而修正、补充和加强了社会稳固所依赖的情感体系。
作为人体最活跃的感觉器官,视觉感官承载着日常传播中最多的信息量。影像文本通过呈现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场景和情节,将观众带入到文本设置的时空场景中。作为承载记忆的媒介载体,影像文本将流动的光阴定格在胶片或数字上。
当视觉符号和文本承担起意义生产和记忆建构的职能时,便开启了关于公共话语的叙事,从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从虚拟社群到仪式链聚合,沟通了现代社会多元群体记忆发生、构建和维护的场景,也延伸出多样的操作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动态影像符号以具象化传播特征在集体记忆的塑造中占据优势地位。
影像文本带入性地构建了一个体验式的虚拟场景,同时诉诸受众视觉感官和听觉感官,以特定的情境还原和叙事逻辑完成一段关于回忆的再现。影像符号及其构建的影视文本可以视为一种强烈情感的具象投射,其功能在于唤醒受众内心的情绪力量,引导观众将媒介呈现的故事转化为记忆媒介,看作集体记忆中的优先载体。视觉符号与视觉文本很早就成为人类记忆留存的重要文本,记忆的能力作为修辞学的子系统,发展出一套视觉记忆编码。
影像符号既是记忆的隐喻也是记忆媒介,不论是静态的绘画、照片,还是动态的胶片、视频,都从外部支撑着集体记忆。当记忆建构成为集体行动时,这个共同体中的个体就会参与到对过去的以集体取代个体的具象回忆。
记忆本身是流动的,影像文本为公众经历记忆事件的文化意义提供了一个修辞环境,从场景设置、事件演绎和情境还原等方式形成关于集体记忆的叙事,并可以对集体记忆本质、个体与集体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见解。
三、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与商业
1987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主旋律电影”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其创作基调与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流价值观紧密贴合,承担着国家意志形态性质的教化功能。在20世纪90年代主旋律电影的浪潮中,主旋律电影的题材主要集中于革命历史题材和英雄人物题材,通常以政治宣传为目的,对时代主旋律进行形象化的演绎。
随着大众审美的变迁,主旋律电影也追求话语转向,在故事题材、叙事策略、话语视角等方面寻求突破,立足于观众的现实情感进行艺术化、商业化创作,以多种故事题材、多元叙事视角和多样人物形象来承载时代主旋律精神价值。当代主旋律电影跳出了模式化叙事和脸谱化人物形象,通过伦理感悟来包装政治主题或者说完成政治主题,使政治意义自然地通过伦理情感得到传达。
在宏观层面,主旋律电影正改变以往“国家资助、市场专供”生产模式,逐渐走向类型化、商业化的市场格局。传统主旋律电影多以宏大历史视野和史诗性特质记录国家民族的命运走向,将个体命运融入国家利益的英模叙事传达政治理念。进入21世纪后,主旋律电影尝试按照大众文化逻辑和市场资本逻辑作为文本创作基础,以受众的内心情感和精神需求为导向,舍弃了传统电影文本中宏大严肃的叙事论调,依靠灵活的叙事策略满足观众审美体验和视野期待。
随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也更加注重创新性和多元性,原有的政治属性边界不断被调整,一批电影人将主旋律电影承载的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意识形态与电影民族性、现代性、伦理性等美学形态融合,建构起与当代受众审美体验高度契合的电影文本话语体系。在电影题材呈现上,主旋律电影更加关注现实题材,走向多元领域;在叙事上,采用类型化、多线性、个人化等多元方式,迸发出新的审美趣味和美学结构;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则摆脱人物脸谱化带给受众扁平化的审美感受。
21世纪以来,主旋律电影在电影美学结构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甚至成为一种显性社会文化景观。一方面,主旋律电影借鉴商业电影的制片方式和叙事策略,采用多线叙事和群像式人物塑造方法;另一方面,商业类型电影在主体内容上自觉靠拢社会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徐克对红色经典《智取威虎山》的好莱坞式演绎、博纳影业基于“湄公河案件”拍摄的《湄公河行动》,为主旋律类型片的商业化开辟了道路,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商业价值和类型规则的平衡。
四、当代主旋律电影的文本创新
(一)故事题材:从“家国情怀”到“生活场景”
“主旋律电影”概念的提出已经有32年,在此期间主旋律电影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21世纪初的衰落和如今的再度崛起。一代代电影人不断探索主旋律电影的表达方式,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价值的完美结合。
主旋律电影兼具政治属性、艺术属性、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等特征。一方面,作为国家意志的承载者,主旋律电影承担着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职责,需要通过电影文本感染观众来传递正向价值观;另一方面,主旋律电影又要面临市场化竞争,必须随着受众审美取向的变化而调整表述方式。从《张思德》中的烧炭战士到《烈火英雄》中的消防员,从《中国机长》中的冷峻机长到《我和我的祖国》中满嘴跑火车的出租车司机……主旋律电影的叙事切口越来越细微。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以及电影人的努力,主旋律电影已经成功规避了叙事生硬、内容空洞、人物脸谱化的弊病。《张思德》导演尹力曾提出“用一滴小水珠折射阳光”,尖端特效打造出的视觉奇观虽然能满足瞬时的感官愉悦,但真正打动观众的还是最有质感的生活情怀,越是贴近大众生活的故事,越能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与以往军旅题材电影相比,《战狼》将刚硬严肃的国家意志与民族主义情绪完美融合。面对境外武装的越境挑衅、国际犯罪集团的基因战阴谋,影片并没有进行长篇幅煽情,而是借旅长“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掷地有声来传递“国土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意志。
《我和我的祖国》作为献礼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主旋律电影,对七大历史事件进行拆解,每段故事都采用平民化视角,聚焦于事件背后的平凡个体。《前夜》中送来红色绸缎和金属制品的街坊、《夺冠》中紧盯屏幕的弄堂邻居、《回归》中热泪盈眶的香港市民、《北京你好》中不知姓名的出租车司机、《白昼流星》中灰头土脸的顽劣少年……这些生活在社会角角落落的平凡个体,恰恰成为中国社会的镜像,他们的故事拉近了观众的心灵,其时空背景也能令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产生时空共鸣,激发代入感,形成一种心灵和故事情节的契合,宏观上也能展现中华民族的人文根脉和现代性反思。
(二)叙事视角:从“宏大叙事”到“个体命运”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聚焦于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的主旋律电影成为时代主流,这一时期电影文本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烙印,故事情节充满了浪漫的英雄主义情绪和庄严的历史感,以充满历史威严感的创作方式强化新生政权的合法地位。以《大决战》《大转折》《开国大典》为代表的经典作品在革命框架内建构革命记忆,按照时空记忆交汇搭建“走向伟大胜利”的叙事结构,文本按照一体化历史观开展人物故事和情感体验,强调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必然。
面对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和市场格局剧变,一些导演尝试改变创作观念,开始从“国家命运”到“个体生活”的转向,生活化的场景、大众化的角色还有鲜明的个性取代了传统的标杆化、脸谱化叙事,传统主旋律电影中的政治属性也因为情感包装实现柔性传递。《张思德》塑造了一个朴实憨厚、无私奉献甚至带有喜剧色彩的青年战士形象,通过细节呈现和情感表达,突出了宏大历史下的微观视角,表现了革命年代的人性朴实,也为主旋律电影的突破开创了道路。自《战狼》以后,主旋律电影在题材上不断突破传统革命历史的叙事框架,不再将政治性、艺术性和商业性三者割裂开来。
《战狼》中的解放军官兵、《湄公河行动》中的专案组、《烈火英雄》中的消防官兵、《中国机长》中的川航乘务组、《攀登者》中的中国登山队,这些人只是存在于社会各个岗位、和你我一样的平凡个体,按照岗位要求执行工作内容。
虽然电影情节为角色设置了故事高潮和情绪迸发,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都会展现出作为社会个体的人性一面。铁血战士冷锋在遇到冷艳上司时也会心生悸动,专案组执行境外抓捕任务时也不忘相互调侃,中队长江立伟会因为没有陪伴儿子而心生亏欠,冷峻机长在起飞之前也会思念女儿……这些温馨的生活桥段,搭建起平凡个体生存样态的叙事空间,为故事脉络的铺展提供了张力。
这些人群不仅是维护国家机器平稳运转的静默个体,也是社会秩序中的结构动能,他们的生活经历共同编织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前行轨迹,他们在严峻考验面前做出的生死抉择,也引发大众对社会生存模式的深度思考。
(三)人物形象:从“服从集体”到“有血有肉”
传统主旋律电影中的正面人物常常具有浓厚的使命化倾向,英雄的奉献牺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伴随着情节递进,人物形象被不断赋予“神格”,产生了由“平民”向“英模”的意义置换。
当代主旋律电影尝试改变传统叙事的严肃基调,从个体视角出发生产符合大众审美情趣的内容,令主旋律电影迸发出新的审美趣味,成为商业电影市场的新宠。在人物形象上不再一味烘托“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而是追求真情流露,对正面人物的性格缺陷和负面情绪也没有刻意规避。在展现对“信仰”思辨时,深入挖掘了人类共同性,即在现实与信念、私利与公利产生冲突时会表现出两难与决绝。
《北京你好》既赞扬了无名司机的爽朗与无私,也突出了他爱吹牛爱嘚瑟的小市民特质;《白昼流星》既致敬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发展,也通过沃德乐和哈扎布的偷窃行径,真实反映祖国边陲的贫困面貌;《护航》中吕潇然在作为备飞飞行员之前,也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和思想挣扎……彰显主流价值观和道德品质,不一定非要赋予神格、树立榜样,也能从普适层面来引导观众,通过展现人性的复杂、思想的争斗宣扬正向价值。
为了实现与观众的情感亲近,当代主旋律电影在烘托正面人物时亦不忘呈现作为血肉之躯的感性一面。《战狼》中冷锋的叛逆和痞性、《湄公河行动》中方新武因儿女情长而感情用事、《烈火英雄》中江立伟疏于陪伴家人的愧怍……对正面人物的世俗化处理已经成为主旋律电影的共识。这种降维处理令人物具有了差异性和生活质感,同时起到欲扬先抑的作用,强化后期在剧情高潮时带给观众的情感冲击。
五、基于集体记忆建构价值认同
(一)平凡个体塑造身份认同
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叙事,虽然情节有起有落、故事逻辑严谨,但故事文本中意识形态符号过于明显,通常在预设结局、塑造人物形象时因过于追求正面形象而导致人物脸谱化,容易产生背离真实生活的程式化叙事,令观众产生扁平化体验。当代主旋律电影则打破这种叙事框架,更加注重微观历史真实,追求平凡人物地位主体化以及大人物平民化。
对平凡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的重现与刻画,将人物情感转化为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体现出当代主旋律电影对人主体性的尊重。《战狼》中的特种兵、《湄公河行动》中的专案组成员、《烈火英雄》中的消防官兵、《中国机长》中的乘务组以及《我和我的祖国》中的普通民众,虽然没有站在历史舞台中央,却是保障国家机器稳定运转的必要部件。他们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紧密交织,其人性流露亦能传达丰富的历史个性。
电影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以明喻或隐喻投射特定时空的社会结构,其主题意蕴和审美特征结构构成对时代精神的呈现。主旋律电影中对集体记忆的重组和加工,实际上也是特定受众群体主体意识的投射,表现出个体的内心需求:对自我认同的渴望。当电影的故事内容与观众的经历产生情感共鸣时,自然就能感染受众的心理倾向和价值观念。
认同是建立在集体记忆之上,记忆不仅是对过往的铭记,也是个体建立身份认同、确定存在合法性的工具。《我和我的祖国》由不同年代符号构建起的时代标签,令当代主旋律电影聚焦的普通民众,涵盖警察、军人、科学家、消防员、扶贫干部等多元职业群体,他们不仅是阶层意义上的静态群体,也是社会运转能动结构中的基础力量,其个体形象虽不完美却更具生活质感。
相比追求唯美华丽的恢宏场面,平凡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生存经验提供了不同于精英视角、历史人物的特殊影像,也丰富了电影的叙事表达,主旋律基调下的基层叙事让社会多元场域的细节呈现日益丰富。通过还原平凡个体在历史事件中的参与过程,以及对个体在重大历史节点中的地位的讴歌,电影在个体记忆和国家命运间架起了一座情感桥梁,在进行宏大叙事的同时,令微观个体触摸到时代心跳,不仅满足了人们对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向往,也展现了电影文本的文学审美张力。
(二)平常生活建立时代认同
电影市场不仅是影片制作水准和内容质量的竞争舞台,也是电影背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角斗场。好莱坞电影中蕴含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伴随着电影输出影响着世界各地。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主旋律电影更需要承担起政治职能,但是在画面呈现中,不光要展现出坚定的国家意志,更要突出人文情怀。
《我和我的祖国》按照时间序列依次叙述七段故事,七段故事以开国大典、原子弹爆炸、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开幕、神舟升天和九三阅兵等历史性事件为背景,但文本内容并没有花费太多笔墨强调事件的历史意义,而是以平凡个体的平常生活来呈现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的鲜活个体。通过讲述这些个体的微观故事,间接折射出国家的点滴发展,缓缓铺开共和国七十年辉煌画卷。
相比宏大叙事,从小切口出发更加能体现国家整体的多元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作为开国大典电动升旗的设计师,林治远在开国大典前夜攻克了一系列困难,确保了开国大典上的红旗飘扬;因核辐射而罹患绝症的高远,在公交车上偶遇女友,然而为了保密更为了隐瞒病情,高远只能以沉默回应爱人的诉说;中国女排的决赛战况被全国人民牵挂,石库门整条街的居民都指望冬冬保障赛事转播,但冬冬的心上人即将移居海外,阳台之上,冬冬陷入纠结;为了保证五星红旗在零点零分零秒准点升起,已经分离了一百五十四年的中华儿女在谈判桌、训练场和钟表店里分秒必争;一个不知姓名的的哥,在幸运地抽到奥运门票后,本想借此与家人共聚天伦,却因为一位特殊的乘客以及乘客的特殊经历,做出了艰难的抉择;茫茫草原,白昼流星的传说成为贫困牧民心中的希望,自然无法出现的景观,因为中国现代科技而实现,其实,真正带来希望的不是缥缈传说,而是国家的富强和个体的奋斗;九三阅兵,所有的飞行员都竭力备战,渴望以最高水准一展雄姿,然而,作为团队最优秀的成员,吕潇然必须备飞以成为飞行表演的最大保障。
不同时空下不同人物的经历,因为“中国”二字串联在了一起。虽然故事置于重大历史性事件中,但《我和我的祖国》不仅致敬了“祖国”,更致敬了每一段历史横截面下的“我”。历史不仅存在于史册,更蛰伏在平民的日常生活中,《我和我的祖国》用微观具象的“我”来塑造宏大抽象的“祖国”,用具象化、平民化的叙事逻辑传递人文情怀,用充满真挚情感的生活细节引发观众的共鸣。
电影艺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形成具体感受,一方面,它是感性的;另一方面却基本上是诉诸心灵,心灵受到感动,也就得到某种满足。因此,主旋律电影首先需要确立精神内核,将抽象宏大的国家意志提炼为人类共通价值观。当普适性的价值观唤起受众情感共鸣时,自然就能引导观众的情感倾向和行动准则。
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生物,人文主义也是基于对文明进程和社会形态的深刻反思。当创作者为电影注入人文情怀时,就需要关注作品对个体所处社会情境的刻画。《我和我的祖国》就采用了大众化、平民化的艺术表达方式来传递人文主义精神。
当观众以人文视角审视影片,也会随着情节递进看到一些现实剪影,从而对现实发出种种疑问。开国大典上飘扬的国旗凝聚着多少人的付出?除了邓稼先,中国国防事业有多少位无名英雄的无声奉献?香港回归经历了多少阻挠,才能保证国旗的尊严不受挑战?已经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繁盛中国,却有一批为温饱苦恼的贫困个体,他们又该去何处寻找希望? 这些社会现实问题通过电影艺术连接观影主体,透过情绪酝酿、情感宣泄影响观影主体的思想和判断。
(三)平实记录催化仪式认同
对特定时期时空情景的再现,形成了一条通向当代大众情感结构的象征之路。当代主旋律电影用影像符号构建象征仪式性的隐喻,通过生产内涵构建记忆社会框架并唤醒集体记忆,在观众中主导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文化共享和仪式表演。
从电影自身形态来看,承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电影也是一种典型的仪式,在电影文本创新、故事情节编排的实践中,都不能脱离对价值内涵的热衷,故事化叙事推崇基于特定时空背景构建的画面有助于唤醒个体的集体记忆或记忆的社会框架。
集体记忆需要社会仪式的操练与表达。基于特定年代构建的整套生活方式构建了一种标准化的象征性仪式,这套仪式伴随着岁月流淌逐渐与个体的生活融为一体,无形中起到人伦教化和价值传承的作用。电影作为一种开放的艺术作品,将本属于私人的情感记忆转化为公共空间中对集体记忆的缅怀与回味,形成一种仪式化情绪狂欢。
主旋律电影对于集体记忆的建构则是一种基于共同认知的象征性虚拟文化仪式。《我和我的祖国》还原了七十年沧海桑田的历史性事件,剧情没有拘囿于对共和国宏大建设成就的亦步亦趋,而是透过平凡个体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直接进入微观人物的历史心态和心路历程,进而突出传承于民族血脉中的价值精神。
在《相遇》中,方敏为相认与否挣扎再三,通过回忆两人相处点滴推动高远眼神的温柔转化,诀别之际,方敏指着报纸上的喜讯,而高远则用看似云淡风轻的眼神轻微额首,带着一丝对爱人的亏欠以及被理解的感激,缓缓倒在欢庆的人群中。而这一幕,也将影片的悲剧性推向极致,在国防事业建设的紧要关头,创作者将恢宏的家国情怀包裹在儿女情长的浪漫主义中,让悲情大象无形地浸润于自我牺牲的陈述中。
基于重大历史事件构建的集体仪式感,有一种天然的身份和时空划分,唯有拥有特定身份和时空记忆的群体才能参与到情绪互动的集体狂欢中。《回归》将“国家”与“圣时事件”紧密联系,通过仪式再现将观众带回22年前那段岁月情境,以集体记忆为内容定位凝聚内地与香港的血脉之情。
仪式的建构需要符号的表征,电影在对集体记忆进行建构时也进入了影像符号表征的世界。电影通过符号的差异性构建整体秩序,为人们精神超越现实秩序提供无限可能,视觉符号的感官冲击、语言符号的情绪渲染从不同方向冲击着感官形成仪式认同。
主旋律电影通常采用线性追溯式的符号来营造时空认同感。不同年代符号的同屏相遇和特定年代中生活经历的共同体验,经过蒙太奇的逻辑编排催生出怀旧情绪。《前夜》中的老式留声机、铜烟嘴、《相遇》中主人公乘坐的斯柯达客车、《夺冠》中的黑白电视机和天线,还有《回归》中的怀表,这些老物件的出场缔造了整部影片的共时性联想,也彰显出故事的历史纵深感。
六、情境的回归:场景引导下的意义诉求
电影艺术通过一系列声像符号的剪辑加工来阐释影片背后的意义。在主旋律电影的话题体系编排中,可见的画面与无声的诉说共同构成对国家的敬畏、认同和传承。无论是字幕标注还是故事文本,都将影像符号和承载的集体记忆定格为记忆框架,这种创作策略将观影活动上升为一种充满敬畏感的文化仪式。
这种仪式以当下的体验置换历史情境中的真实事件,令观众产生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向往,进而对历史产生敬畏和憧憬,也让特定群体获得记忆空缺的补偿。《夺冠》没有直接讲述1984年女排夺冠的激烈赛事,而是采用“离场叙事”的方式,将镜头对准上海弄堂里的小男孩,为了调试天线、保障整条街的正常收看,冬冬无奈错过和小伙伴的告别。弄堂里的修车师傅、聚拢整条街邻居的黑白电视机、不断长鸣的蛐蛐令观众重回那段纯真质朴的岁月。
撇开宏大叙事中的正面歌颂,平实叙事构建的集体记忆更加平易近人。从1949年天安门广场上民族自信的树立、1968年为国家奋斗牺牲的质朴,到1984年自我意识的觉醒、1997年国家尊严的捍卫,再到21世纪每个人都能成为主人翁的信念,主旋律电影在为公众提供集体记忆和仪式认同的过程中,实现着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的传承。
集体记忆和即时认同的意义在于激发了用户的情感参与,将影像中的虚拟场景升级为观众的经历与感悟。创作者和观众通过意义互动生产着意义和快感。在对集体记忆的构建中,观众不再是屏幕前的旁观者,而是节目剧情中的时空背景、人物关系和情感纽带,在获得心灵慰藉的同时也认同接纳了文本蕴含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聚焦个体命运的主旋律电影的兴盛,不仅得益于观众审美标准的提升,更是创作者结合时代背景与受众心理需求而精心雕琢的结果。这种精雕细琢不只是简单地玩弄辞藻、刻意煽情,而是在集体记忆中构建集体认同。在这场记忆回味之旅中,主旋律电影借助影像符号回归历史时空,在记忆分享中传承民族精神与时代特质,进而转化为个体对民族国家主义的身份认知,凝聚并强化对集体的价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