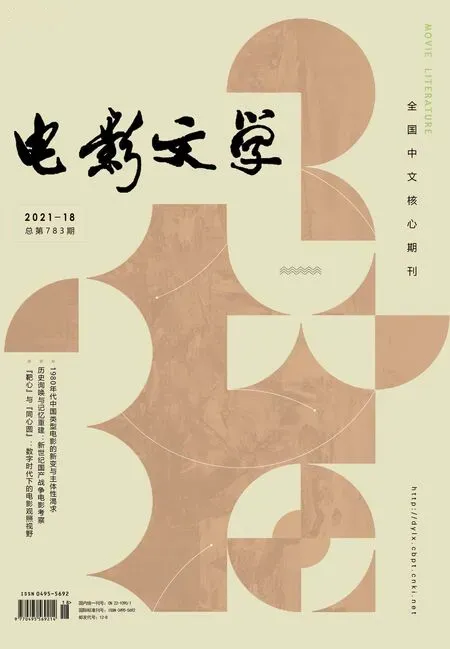《我的姐姐》女性主体的受损与贬抑解读
韩志刚 朱 宁
(天津大学,天津 300072)
随着女性女权主义运动的不断高涨与先进性别文化的不断发展,与女性有关或者是以女性作为主体的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等艺术作品的不断涌现,通过搭建的一个个还原、折射或者隐喻的艺术世界,将目光聚焦于女性群体的生存环境、权利义务、地位权威、情感世界与精神生活,在批判、呼吁声中强调平等生活中的女性独立性与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被传统具有优先性、主导性与权威性的男性群体所压迫、控制、物化的女性群体,以追求自由、平等、尊重的姿态在艺术作品中不断出现,塑造出许多不依附于男性、与男权抗争、争取权利的独立女性主体形象,并借此脱离男权建构的语言、符号、意义与权力世界。这一女性主义的意识内容也与电影作品有所结合,形成了特有的女性主义电影类别。
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电影以学术理论研究的形式进入中国社会,与此同时女性主义电影作品也大量涌现,并与中国社会现状结合,将范围泛化为:女导演创作的电影,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电影以及以女性形象作为主体的电影。大批优秀的女性电影人,从几十年对男性电影创作的跟随与模仿中寻求突破,展示女性所特有的情感、志趣与追求,创造好出许多佳作,如《夏日的期待》《青春祭》《沙鸥》等,在女性所独有的人生故事中塑造出许多生动饱满的女性形象。这不仅丰富了我国电影的类型、叙事视角,从社会性别文化视角进行多维的社会关照与思考,也进一步推动我国电影事业在先进性别文化构建方向上的发展。电影《我的姐姐》作为一部女性主义电影,还原女性群体受损与贬抑的真实社会环境,并在女性追求主体独立性的故事叙述中,塑造了一个坚强不屈的女性角色,借此来实现对女性平等权益的呼吁。
一、在场与不在场的主体控制
“在场性”源自德国哲学,意为显现的存在,直观被认识理解的存在,“面向事物本身”存在意义的展现。后被法国后现代学者德里达用以表示一切形而上学的根源或者本体,如果以人作为主体,可以通过语言、话语的形式进行扩散,从而搭建起一个“被听见—说话”的在场结构。从“在场性”维度,可以从浅层的时间空间深化到场内各个主体的相互作用、主体间性等关系和结构,是分析人的重要哲学理论支撑,同样也可以作为一个挖掘社会关系与深层内涵的重要哲学角度。
在以人物作为主要角色,社会环境作为主要空间背景的电影作品中,会经常性地涉及在场性的问题,即在某一特殊场景内的情节,所展现的人物关系、相互作用与权力关系不仅限于在场的人物,而是具有更为广阔的不在场网络。在场与不在场交织搭建起完整的电影叙事的人物关系与权力关系,并进一步成为叙事的基础性权力变化主导,影响故事的走向、人物变化甚至整个电影的主要内涵与意义表达。如电影《晚安,母亲》中主要情节围绕母亲塞尔玛和女儿杰茜展开,母女两人围绕着女儿自杀进行在场的讨论,但是母亲塞尔玛的丈夫作为不在场的角色,却对整个家庭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其威压一直悬浮在家庭场域内,将妻子与女儿置于被压迫与被控制的位置,并进一步左右着人物关系和行为变化。
电影《我的姐姐》在描绘女性主体性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在场与不在场的主体控制。女主角安然从电影开始便面临着扶养六岁弟弟的问题,父母车祸身亡,弟弟年纪尚小无法独立生活,一家人在葬礼之后围绕这一问题召开家庭会议。逼仄的客厅里面坐满了人,大伯、姑妈、舅舅、表哥、表姐等人商量着安然现在有了护士这份工作保障经济来源,能够将弟弟扶养成人。大伯以命令式的口吻将这一任务直接安排给安然,在遭到安然的强烈反对后甚至想要大打出手。在场的亲人,将姐姐安然和弟弟安子恒置于被操控和被指挥的位置,试图在三言两语的商讨后决定姐姐必须扶养弟弟,并不断强调这就是作为姐姐必须对弟弟付出的义务。
除了在场的亲人对安然进行主体控制以外,作为已经在车祸中死亡的父母,也以不在场身份对安然进行主体控制。安然小时候,父母为了再生一个儿子向相关部门谎报安然是一个瘸子,在残疾申请败露后,气急败坏的父亲对安然一顿暴打。重男轻女的父母还以“女孩早点挣钱养家是对她好”的名义修改安然的高考志愿,并在生了儿子之后对女儿一直不闻不问。父母的偏心与暴力影响着安然的性格成长,成为她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为了自保不得不将自己伪装起来,强硬到不近人情,厌恶父母的一切。但是车祸的意外使得安然不得不面对现实,父母只需要面对死亡,而安然则被父母以亲生姐弟的名义,将她和安子恒紧紧地绑在一起,以不在场的心理阴影和血脉联系控制着安然让她无法轻易挣脱。
二、男权对女权的主体与独立压制
在女性主义电影作品中,虽然围绕着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意识的表达与女性权力的强调而展开,但是同样作为社会基本构成的男性群体是在展现女性主义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一般而言,对女性主义的表达,多是从女性已有的生存环境、不公平待遇、不平等的权利、低下的社会地位、刻板化的社会认识中出发,描绘女性如何走向觉醒、反抗、崛起,并获得主体性与独立性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对男权压制女权的刻画,则成为女性主义电影的基础,在对比与突破中为女性主义的表达提供支撑。
在男权占据社会优势地位的社会中,女性群体多被放置于与优势相对应的被支配与被控制地位,甚至是被男性物化、凝视的对象,在社会关系中被看作是男性价值与意义的附属品,这种男性与女性的权力关系也体现在小说、话剧、电影等艺术作品之中。在传统以男性为主导的电影中,多围绕男性的高大形象与优秀品质展开,男性掌握话语权力与语言构建权力,而“女性作为女性没有得到适当的表达”,缺少对女性群体的聚焦,也更加疏于对男权与女权关系的进一步的探讨。女性主义电影由于关注女性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因而在电影中会将男权与女权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作为重点的表现对象,尤其是善于在男权对女权的主体与独立压制的叙事中,描绘受损且被贬抑的女性形象如何觉醒且崛起。
电影《我的姐姐》中的姐姐安然,从儿童时期开始便不断地遭到来自男权的压制,其主体被不断地贬损。儿童时期,安然父母想要再生一个儿子,不管安然的自尊要求安然对外装残疾;安然高考后父母偷偷修改安然的志愿,强行将安然留在本市大学;在父母去世后,她不得不面对父亲留给她的弟弟扶养问题。除了来自父亲男权压制以外,还有大伯、舅舅对安然轮番的游说、斥责、怒骂与暴力威胁,试图将安然与弟弟强制捆绑在一起,还有男朋友劝诫安然向医院的关系户服软,委婉地表示对她去北京考研的拒绝,并以结婚后一起生活的未来描绘将安然留在本市不去追求梦想。在这一系列男性对安然的要求、安排与规划中,安然作为一个女性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并未得到重视,反而是在对安然的道德、梦想与未来的贬损中要求她向男权屈服。
影片中饱受男权压制与贬损的女性不仅是安然,还有安然的姑妈安蓉蓉。安蓉蓉是一个典型的屈服于男权的女性形象。儿童时期因为自己的姐姐身份,需要将家中有限的资源让给弟弟,并且作为姐姐在生活中需要不断照顾弟弟;家中只有一个读书名额的时候,已经考上西南师范俄语系的安蓉蓉不得不把机会让给弟弟;弟弟的孩子出生了,远在俄国做生意的安蓉蓉也不得不回国帮助弟弟照看。此外,还要事无巨细地照顾瘫痪的丈夫、叛逆的儿子、年幼的侄儿……安蓉蓉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其一生都被男权所压制,个体意义受到多维度的贬损,成为男性的附属。
三、社会掠夺下的主体权力维护
电影作为一种立足于社会现实,以现实的真实性力量作为依托,经过艺术化加工与处理后能够反作用于社会现实的艺术作品,并不局限于对表层的现象的描绘和记录,而是善于透过表层深入社会内里,探讨社会权力结构、政治框架、文化伦理等背后的关系变动与特征表现。导演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重新搭建,在各种场景搭建、人物塑造、情节策划的排列组合中,构建一个能够有效折射现实表象与内里的影像世界,从而实现意志与意识表达。
在女性主义电影中,除了从男权与女权的关系、相互作用来展开以外,还善于从整个社会视角出发,由社会的表层认识中透视女性所处的位置,尤其是社会偏见、社会普遍性认识下女性被掠夺后的受损与贬抑主体性展示。但这种展示并不是女性主义电影的主要内容,而是以一种铺垫的形式为女性抗争社会的各种威压存在。将女性面对掠夺、压迫、控制后意识觉醒并奋起反抗重新夺回主体性地位与权力作为电影表现的真正内容。
电影《我的姐姐》中,原来打算与男友一起辞职,前往北京脱产考研,然后逃离现有生活的姐姐安然,在遭遇父母去世的重大变故后,一切的计划都被打乱了,她不得不面对扶养年幼弟弟的问题。周围所有的亲人觉得这个责任理所应当地由姐姐来承担,无视她的反抗与愤怒。社会上其他陌生人也将安然送养弟弟的决定视作“没良心”“歹毒”,没有履行姐姐的义务,有的甚至直接站出来无理指责。安然的行为与社会中所存在的普遍性认识相违背,而社会整体与社会构成个体为了维护已有的稳定,联合绞杀安然的反叛。
在来自社会铺天盖地的认识压制下,安然处于一种失去道德、未能履行责任的位置,甚至无法获得亲人、男友的理解与支持,只能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安然并不退怯,咬着牙和欺负她的人争执、厮打,不掩饰委屈与不甘时的眼泪,勇敢向前,毅然辞掉稳定的护士工作,与志向相悖的男友分手,卖掉房子,给弟弟找到一户富裕的领养家庭,将一切安排妥当。以一种逆反者、反叛者的形象独自踏上追求梦想与未来的道路。安然不畏世俗的眼光,勇于反抗这一切,维护自己的权利,在追逐过程中获得了同样身为姐姐、长时间被社会普遍认识所统治与压迫的姑妈的理解。
电影结尾处,安然去看望弟弟时,不禁想起与弟弟相处时的幸福时光,给予长时间缺乏亲情的安然珍贵的温暖,安然也因此忍不住将弟弟带回家,承担起照顾和扶养弟弟的责任。安然并非屈服于社会的控制与压制,畏惧社会的贬损,而是已经成功夺回女性主体权力后,面对亲情自主选择、维护主体权力的表现。
电影《我的姐姐》紧贴社会现实,反映“全面两孩”政策推进后高龄产子家庭增多,同胞年龄差较大等现象下所隐含的遗产分配、孩子抚养等社会问题,从女性视角出发,揭示身为女性在身陷这一系列问题时主体面临的受损与贬抑,以及展现面对压迫与控制的女性如何做出抉择。作为女性主义电影,《我的姐姐》还原了男权与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描绘女性个体发展过程中可能遭受的困难,一定程度上以女性的力量重构中国电影的性别话语结构,丰富电影的类别与内容,并且拥有反作用于社会现实的力量,促进现实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鼓励女性摆脱男权与社会的权力或者话语遮蔽,积极追求主体性与独立性,实现自我价值。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