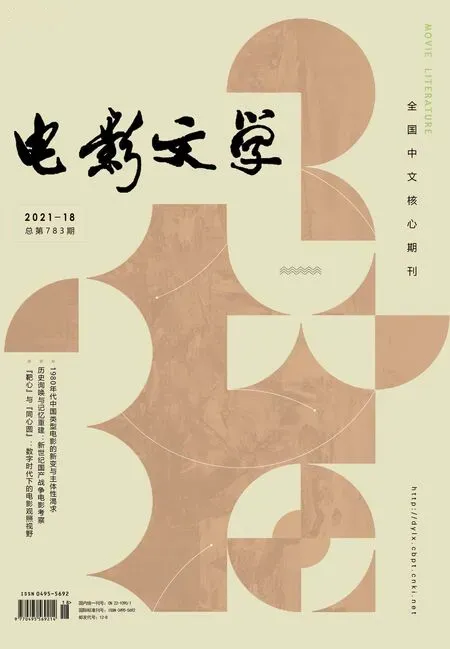电影叙事中动物隐喻的美学阐释
——以管虎电影为例
周 营 辛 赫
(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1)
隐喻是一种修辞方式,也是一种认知途径。隐喻是在多种事物相互对比、暗示、影响下产生的具体行为,如:感知行为、语言行为、心理行为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隐喻是发现跨界限、跨物种的事物之间相似性联系的引申方式。而对这种相似性的发现必以形象、意向为中介。电影是一种拥有传递多种语义功能的媒介,能够以影像为载体,把极其富有深度和美学价值的语义信息传递给观众,借助视听语言把语义内涵浅藏于影像之中,表现出电影的隐喻性特征。
一、动物隐喻的美学阐释
随着电影的不断深入研究和语义认识的快速发展,人们跻身于一个感受语义信息的新纪元。把两种貌似没有联系的人和物放在一起,找出他们之间相似的因素并加以对比、分析,使其产生一种隐匿的关联性,从而探索事物的深层内涵。在电影叙事中,以动物表现喻指人物角色,深化电影主旨立意,阐释人生哲理。然而,动物隐喻的实现和发展,离不开文化语境。动物隐喻作为文化现象的一种,将表象信息投射到文化内核中,文化内核又通过隐喻表象传达,文化作为动物隐喻的认知基础,同时也促进其发展。在电影叙事中,动物隐喻的方法早有应用,影片常以动物命名,或蕴藏于重要情节之中。
(一)理想主义——“孔雀”的隐喻
电影《孔雀》运用三段式的回顾结构,以展现20世纪80年代安阳小城中最平凡、普通的一家五口为内容,以兄妹三人迥异的性格与命运、青春与梦想、亲情与成长为线索,讲述了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故事,抒写了追求理想道路上的自我毁灭与涅槃重生。影片的名字叫《孔雀》,但孔雀作为意象只在影片末尾才出现,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地去逗弄它,但孔雀并不理会。
孔雀在这部影片中被赋予了特殊的隐喻意义——理想。理想仿佛瞬间开屏的孔雀,美丽而令人向往。然而在满怀希望期待的时候,却总是静默无为,这种事与愿违的无奈,恰似生活中人们对理想求之而不得的精准诠释。电影中兄妹三人的人生各有差别,但都对理想充满渴望与期许,导演巧妙地借助孔雀开屏来隐喻人生境遇,展现小人物的挣扎与无奈。
(二)同性之爱——“蝴蝶”的隐喻
在众多文艺作品中,蝴蝶是极具代表性的动物隐喻形象之一。蝴蝶的象征语义在东方特有的文化背景下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庄周梦蝶”“梁祝化蝶”,都象征着美丽和自由。在影视作品《梁祝》中,蝴蝶作为贯穿影片的关键性线索,共出现了四次,巧妙地传达出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发挥了隐喻功能,显现出独特的意蕴。其中“化蝶”片段,呈现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化作蝴蝶比翼双飞的幸福画面,除了象征自由恋爱,这里也暗藏着蝴蝶的另一隐喻内涵,即“同性间的爱恋”。早在祝英台女扮男装进入书院与梁山伯一同求学的时日里,两人朝夕相处、暗生情愫,以为英台与自己同为男儿身,但又难免心动欢愉,于是有了梁山伯“从此不敢见观音”的经典台词。“化蝶”也象征了一种打破封建束缚的新观念、新精神、新追求、新境界,蝴蝶隐喻得到了升华和体现。
香港影片《蝴蝶》,展现了一个不被世俗认可的同性之爱的故事。女主人公阿蝶,在高中时期喜欢女同学真真,被父亲发现后遭到阻拦,毕业后遵从父亲的要求结婚生子,走入正常的情感路径,过着别人眼中阖家欢乐的温馨生活。直到偶然间在便利店遇见另一个女孩小叶,她的勇敢追求唤起了阿蝶内心深处的情感和爱恋,最终阿蝶挣脱了男权束缚,拥抱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蝴蝶》是以阿蝶的成长经历和情感轨迹为线索,这部影片的社会背景处于香港学生示威游行、争取平等人权的时期,被当时的政治力量所限制,暗示了女同性恋者丧失了基本的人权,就像高中时期阿蝶被强制阻拦,明确指向了同性的爱恋是不被世俗接受和允许的。影片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意象——蝴蝶,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喻示着女同性恋之间脆弱、美丽、忠贞的爱情。
(三)情欲化身——“蛇”和“马”的隐喻
蛇和马作为动物隐喻的形象常出现在经典电影作品中。关于蛇的隐喻认知源自《圣经》,是蛇诱导亚当和夏娃吃下禁果,打破了伊甸园中单纯而快乐的平静,这里的蛇是欲望和魔鬼的化身。电影《青蛇》以音乐开场,一群纵情声色的男女在舞动腰肢,肆意享受欢愉。女人的舞姿就像缠绕摆动着的蛇,为影片夯实了情欲基调。随后,青蛇和白蛇以真身出场,盘绕在女人身上尽情撩逗,弥漫着浓郁的性暗示气息,这里揭示了蛇就是性欲的符号,是欲望的化身。
白蛇的故事流传已久,而影片《青蛇》一改常态,将视角转置到青蛇身上,以第一人称的身份讲述不同的故事。与已经修成人性的白蛇不同,青蛇身上固化了动物本性,堂而皇之地展示欲念,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她的心中没有伦理道德和世俗规矩,只受自己的本心驱使。在与法海斗法的片段中,小青的愉快和放纵是女性纯真、欲念的化身,法海则是男性克己制欲的道德楷模,两者的对峙恰似弗洛伊德提及的人格中本我与自我的对抗。虽然法海与世俗男性不同,但在《青蛇》这部影片中,“沉迷女色就会身败名裂”的封建成见在法海身上仍有所体现。在父权文化下,女性形象长期处于缺席、遮蔽和被扭曲的状态。而在影片的最后,法海作为父权文化的代表,他的观念已被颠覆,暗示了导演强烈的人文关怀,即女性与男性的地位应当平等,呼吁观众正确看待欲望。
在电影《东邪西毒》中,“马”的隐喻意义被细致地刻画呈现。影片的开始,由刘嘉玲扮演的女性角色桃花,在水潭中与马亲密接触的片段,隐晦地表达着情欲。桃花不停地抚触马的皮肤,身体趴在马背上,感受马的温度,借此宣泄自己的寂寞和欲望。马是桃花爱人的隐性化身,也是情欲的显性符号。
以动物隐喻作为叙事方法的案例不胜枚举,无论是在影视作品、文学作品,还是寓言故事中,从古至今不变的是作者都借动物之名传递着某种人性特质,戏剧化地呈现出关于人性这一永恒的思考命题,揭示生命的本质。
二、管虎电影的动物隐喻分析
管虎作为“第六代导演”之一,被称为导戏“鬼才”。他的影视作品极具个人风格,动物隐喻是管虎电影中视听语言的创新之一,也是他最常用的叙事手法。电影作为一门综合多种艺术元素的视听艺术,最大的魅力在于提供给观众一种沉浸式的造梦空间,观他人所观,想自己所想。在影视作品中,动物常作为重要角色出场,并且赋予了它们特殊的隐喻功能,在影片《斗牛》《杀生》《老炮儿》和《八佰》中,管虎大量使用动物隐喻,而这种认知之所以能够被观众所接收,正是因为这种叙事方式的生动、鲜活,以及在动物性与人性的拐点之间引发的深度思考。
(一)展现生存与关怀——《斗牛》中奶牛的隐喻
这部讲述生存与大爱的电影是一部战争喜剧片。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沂蒙山区为背景,故事讲述的是国际友人为给中国八路军提供援助捐赠了一头奶牛,在日军来袭时八路军将不易转移的奶牛交给村民代为保管,双方互留字据、盖章画押。经过阴差阳错的抓阄,奶牛和小寡妇九儿都被牛二带回了家。经历过日军“扫荡”后的村子,只剩下一人一牛,为了完成保护“八路牛”的承诺,牛二与多方周旋,幽默与悲情的矛盾情绪中也透露着作为农民的牛二在战争中挣扎求生的境遇,以及不屈不挠、朴实诚信的品行。有趣的是,《斗牛》中的奶牛以“主角”身份登上了片尾的字幕,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更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自古以来牛与农民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牛是农耕文明的象征,是老实、忠诚、憨厚形象的代表。虽然《斗牛》中的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耕地的黄牛,而是一头荷兰奶牛,但它仍扮演“拯救者”的角色,对众人有着非同一般的生存意义。不论是对八路军伤员,还是受难的流民,以及日军伤员,它都承担着一个“母亲”的职责,奉献自己的乳汁来保障他人的生命。
奶牛是农村妇女的隐喻,弱势且没有话语权,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在电影最初,由牛二和其他人共同关注着奶牛乳房这一剧情中可以察觉,奶牛丰满的乳房,使牛二和村里的其他男性都对奶牛产生了单方面的性幻想。奶牛的“妇女”隐喻,也使奶牛与九儿产生了许多共通点。奶牛有一纸协议,九儿有一纸婚约;奶牛桀骜不驯,九儿泼辣勇敢;奶牛被匪贼强行拉去和其他牛配种,九儿被村长作为利益互换赠送给牛二。两者都是人性中“求存”路上的牺牲品。在九儿死后,牛二的精神依靠只剩下奶牛,给它起名为“九儿”,负担起自己的责任和承诺,牛二对奶牛的守护也象征了守护中国农民的未来和希望。
在相对封闭的中国内陆乡村,奶牛作为外来物种代表着“新”的文化,当奶牛初来乍到却被毒哑时,也隐喻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产生对抗,外来文化在不可抗力作用下不得不“失声”。在影片最后,经历了多次的冲突与和解,最终一人一牛温暖相伴,这里暗示了传统思想与“新”文化的关系最终将兼容并蓄、万众一心,随着影片结束,奶牛的最后一重隐喻完美落幕。
在《斗牛》中管虎运用略带黑色幽默的叙事方式将人赋予了动物的特征,以动物隐喻的叙事方法对比了人性与动物性不同的呈现,赞扬重诺、有责任感,批判重利、无情冷漠,带给观众关于人性更多的探究和思考。
(二)表达禁锢与自由——《杀生》中“鱼”的隐喻
《杀生》源于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西南部的一个“世外桃源”式的长寿镇里,四面环山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封闭、保守、落后的思想状态和生存空间,也是当时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封闭中国的隐喻象征。在长寿镇,不管使用什么手段,“长寿”就是唯一的目的和标准,哪怕生活毫无意义,也依旧努力遵守传统风俗,有序地生活在“祖训七十二条”的规矩之下。牛结实的出现打破了小镇长久的平静,他是稳定秩序的破坏者,村民们一次次的驱逐都未能将牛结实赶出小镇,毫无收敛的“作恶”触动了村民们的底线,一场密谋杀害牛结实的故事就此展开。
影片使用了多种隐喻来揭示“杀与生”和“自由与束缚”之间的矛盾冲突。长寿村的村民都姓牛,但实际上牛结实的父亲姓马,是一个过路的商人,让人联想到“风马牛不相及”,意思是说两个事物之间没有丝毫的关联,预示着牛结实本质上并不属于这个充满束缚和禁锢的家园。牛结实代表着自由、反传统、反封建,他的存在是一种颠覆式的打破,在他身上也始终体现着这种隐喻的反叛精神。电影中,牛结实有三把钥匙,一把挂在胸前能够打开镇上佛庙的大门,另外两把用来打开傻子的脚铐,这里预示着牛结实就是打破封建家园的关键钥匙。
影片中多次出现“鱼形锁”“放着生日快乐歌的小鱼八音盒”是阻隔自由、文明落后的象征。“鱼”的符号在电影中呈现了两次,一次是佛庙大门上的鱼形锁,另外一次是牛结实卧在棺木中,宛如在大海中畅游的鱼儿,周围还有许多小鱼围绕,是一个充满自由和美好的新世界。正如鱼离开水就失去了生命和自由,牛结实也是一样,为了能拯救儿子的性命,只好放弃追逐自由选择自杀。他是一个敬畏生命、自由、快乐,不畏惧死亡和禁锢的人,这里的“鱼形锁”和“八音盒内游着的小鱼”就是牛结实的化身,是试图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信念与力量。
以长寿为荣的镇子却对牛结实施行了杀生,导演借此探讨了自由与束缚、开放与封闭、杀与生,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对立关系,显示了时代背景下的繁复人性。
(三)对照传统与现实——《老炮儿》中“八哥与鸵鸟”的隐喻
在电影《老炮儿》中出现了八哥和鸵鸟两种动物,赋予了他们不同的隐喻意义。八哥是一种会学话的鸟类动物,电影中的八哥却有着另一个名字叫“晓波”,是张学军儿子的名字。将会学话的八哥与不和自己说话的儿子进行类比,这里暗示了张学军和晓波之间疏离的父子关系。其次,在张学军溜冰、理发、遛弯儿的时候都会带着八哥,可以说是形影不离,象征着八哥以亲人的身份,替代实际生活中儿子的缺席,也表达了张学军牵挂儿子,渴望父慈子孝的生活。然而,每当张学军需要情感互动的时候,八哥都会应景地叫一声“六爷”,而这声“六爷”是张学军多年时间里唯一教会八哥的一句话,暗示了张学军的内心,渴望儿子晓波对自己父亲角色和江湖道义的认可。
在影片后半段中,由于仇家几次三番地围堵上门,八哥“晓波”被摔死在地上,儿子“晓波”被对方打进医院昏迷不醒,张学军的情感牵挂和寄托被生生割裂,剧情由此推向高潮。在影片的结尾彩蛋中,晓波开了家名叫聚义堂的酒吧,买了一只新的八哥并成功地教会了它叫“爸”,这里暗示了晓波最终对父亲的认可,也隐喻了父子关系的重新修复。
被禁锢在四合院中的鸵鸟,原本代表着顽强生命力,现在却成为畸形消费观下的富商宠物,隐喻了主人公脱离现代社会的倔强。在影片的最后,鸵鸟冲破牢笼奔跑在大街上,其本质是表现了一种原始冲动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格格不入。骑着自行车单刀赴会的张学军和肆意奔跑着的鸵鸟,抱着同样的决心,朝着相同的方向,在某种意义上鸵鸟是张学军形象的转化,也是他高傲性格的体现。预示着像张学军这样纵然心中有自己的道义与规矩,但在面对新时代来临时仍选择坚守“传统”、拒绝“现实”变化的这样一群人的命运,结局也终将被时代所淘汰。
管虎以一种“献祭生命”的方式来批判金钱当道、缺失人情味的社会现象,以一种英雄主义壮烈牺牲的色彩,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怀念与哀叹,描绘出一场时代变迁下的盛大悲剧,揭示着传统与现代、老炮儿与新一代人之间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
(四)传递信仰与希望——《八佰》中“白马、老鼠与孔雀”的隐喻
在《八佰》中除了先导预告片中将三种士兵的精神面貌分别用狼、狗和猫来喻指,整部电影最鲜明的一处动物隐喻是在战火中肆意奔驰的白马。它是中华民族不屈服、抗争到底的力量象征,是希望、自由和奇迹的化身。
白色,也称为无色,但同时,白色又是所有色光的集合。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统一的特质,使白色在自然界色彩中拥有绝无仅有的美学魅力,人们往往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电影《八佰》中白马的纯洁与战争的血腥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首次出场就叫醒了一些瘫软在地、事不关己的闲兵散将,随后在枪火四射的战场中冲出仓库,消失在街景中。战场上人人小心翼翼、步步为营,防止被暗枪狙击,唯独它自由地奔跑着。马是生命力的表现,尤其是奔跑中的马展现了雄性的力量,有一种原始冲动,是士兵们英勇男儿血性的表征意义。在影片的最后,白马从战壕里走出来,代表纯洁、高贵与和平,寓意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它奔跑到更远的地方,象征着光明的未来。白马出现在战乱的环境下是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处理,这是管虎的一贯影像风格,是一种柔软且坚毅的力量,也是这座孤城中残留部队的责任与荣誉。
在《八佰》中最先出场的不是白马,而是老鼠。探头探脑的老鼠,因为受惊飞快地返回洞穴,紧接着出现的就是一群逃兵,让人联想到逃兵“胆小如鼠”,“人人喊打”。老鼠以往的形象给人苟且偷生的感觉,它的出现反映了战争的残酷与生活的艰辛。与此同时,在场景处理中老鼠的出现也透露着死亡的味道。在抵抗了日军的第一拨进攻之后,四行仓库外出现了乌鸦,靠吃腐肉为生,能第一时间发现尸体,预示着经历过战争的四行仓库此时此刻就像地狱一样可怕,也可以说是一座活的坟墓。
第三个具有隐喻价值的动物是赌场老板的宠物——孔雀,象征了租界住民隔岸观火的冷漠、拥有被保护权的高傲,以及战士们对和平反战的向往。
在极端的环境下逼出人的动物本性——求生;抱着守卫国家领土完整,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坚守信仰和理想——求死。从最开始的“鼠性”逃窜到后来带着自由和生命力肆意奔腾的白马,在求生与求死之间,在动物性与人性之间,巧妙地出现了拐点,展现了从人性低谷升华到人性光辉的转换过程。
无论是在《斗牛》《杀生》《老炮儿》还是《八佰》中,在动物隐喻下阐释的人性,是具有动物性但高于动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人活着不可缺失的信仰和追求。电影中的动物隐喻,通过把人与动物之间的某种共性联动,把动物的特征投射到人的身上,借动物性与人性形成对比,更加巧妙地展现人性的复杂,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叙事策略。管虎借助动物隐喻的方式,形成一种新的叙事张力,引导观众深入思考:透过导演的认知审视时代变迁、生命本源,看到剧中人物的坚持与突破,重燃心中的追求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