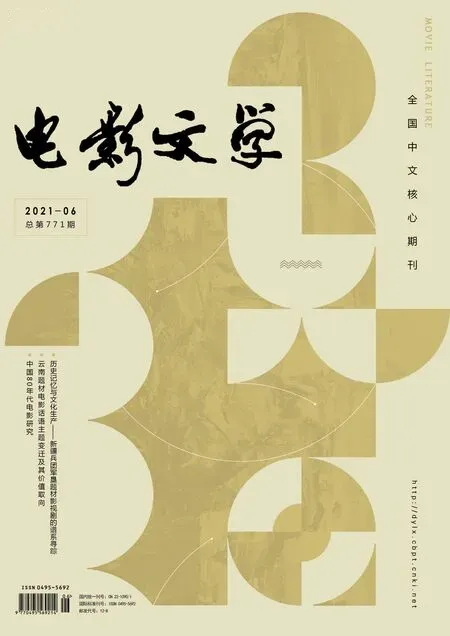《真相》中刘宇昆科幻戏中戏的叙事功能论
刘玉杰(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是枝裕和如此评价自己执导的家庭题材电影《真相》:“这部片可能真的是我的集大成。”《真相》既是导演家庭题材电影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导演作者性的集中展现之作。是枝裕和最引人注目的作者性就是缘于他多年电视纪录片创作经验的纪录片手法,但人们容易忽略他另一层面的作者性,即他对幻想类电影的熟稔。一方面,他执导过《下一站,天国》(1998)和《空气人偶》(2009)两部幻想类电影;另一方面,尽管他从没执导过科幻电影,但自幼对科幻电影十分热爱,无论是日本本土科幻影视(比如奥特曼系列),还是国外科幻影视(比如《科学怪人》《人猿星球》等)都耳熟能详。为了拍摄科幻戏中戏《关于母亲的记忆》,还专门观看了《阿尔法城》《别让我走》《前目的地》等科幻电影。因此,从类型片的角度来看,有了执导2016年《比海更深》家庭加侦探、2018年《小偷家族》家庭加犯罪等复合类型片的经验后,《真相》这样的家庭加科幻复合类型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作为典型的多线叙事影片,《真相》同时存在着友情叙事线、母女关系叙事线以及跨文化叙事线三条叙事线,科幻戏中戏的加入又为影片增加了元电影的叙事复杂性。在叙事功能上,科幻戏中戏《关于母亲的记忆》对于整部影片的重要性在于:它促成了《真相》三条叙事线的彼此融合与推进,在完成三重叙事功能的同时,赋予整部影片以连贯性和统一性。
一、科幻戏中戏的友情叙事功能
《真相》的署名编剧除了是枝裕和,还有美国华裔科幻小说家刘宇昆,因为电影中的科幻戏中戏源自刘宇昆2012年发表的同名短篇科幻小说《关于母亲的记忆》。然而,《真相》最初选用的戏中戏并不是《关于母亲的记忆》,而《关于母亲的记忆》的主题是母女关系,也与友情无关。两个关键问题随之而来:是枝裕和为何会选择《关于母亲的记忆》做戏中戏呢?《关于母亲的记忆》又是如何完成友情叙事功能呢?
首先,我们来考察《真相》的戏中戏替换成《关于母亲的记忆》的原因。原因之一是故事文本层面的,《真相》的前身《在这样的雨天》(初名《寄物》)是友情主题的单线叙事文本,情节相对简单,立意未见新颖,思想也难说深厚,而科幻戏中戏增加了叙事的复杂性。《在这样的雨天》最初选择了雷蒙德·卡佛的《大教堂》作为戏中戏。全剧唯一的冲突在于:女演员要演友情主题的舞台剧《大教堂》,却一个知心朋友也没有,根本无法理解细腻微妙的友情。终场演出后,戏迷老太太带着反馈信来访,两人之间的友谊由此生发。懂得了友谊微妙性的女演员心想,如果还有一场演出的话,她就可以演得更好一些了。
原因之二是现实层面的,《在这样的雨天》与电影《鸟人》高度重复。2014年上映的《鸟人》,核心剧情是饰演过超级英雄的过气男影星要在舞台演出卡佛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因与《在这样的雨天》有诸多重复,促使是枝裕和放弃了原本的戏中戏《大教堂》。而《关于母亲的记忆》日译版收录于2017年出版的同名小说集《母の記憶に》中,为是枝裕和于2017年11月10日考虑改作科幻戏中戏提供了文本基础。
其次,再来考察并不涉及友情主题的《关于母亲的记忆》是如何实现友情叙事功能的。《真相》并非大制作电影,甚至经费也面临不足,影视大腕法比安最终接拍了这样的电影,管家卢克向路米尔透露了原因:主演玛侬·雷诺尔被人称为小莎拉·莫丹瓦,而莎拉正是母女关系紧张之症结的关键。科幻戏中戏正是通过玛侬饰演母亲角色而又与莎拉十分相像这一戏外现实,实现其友情叙事功能。
莎拉虽未出镜,但在电影叙事上非常重要,是友情叙事线的核心人物。一方面,莎拉是法比安、路米尔母女共同的朋友。对法比安而言,莎拉既是好友,又是双重竞争对手。第一重竞争关系体现在表演事业上,莎拉的表演境界是法比安无法达到的(当然这只是皮埃尔、路米尔的看法,卢克的看法则完全相反),法比安通过与导演的暧昧关系抢夺了本属莎拉的角色,从而获得了恺撒奖。莎拉却因醉酒下海意外而死。第二重竞争关系体现在对女儿的吸引力上,莎拉因体贴温柔而获得了路米尔的喜爱,而母亲却因忙于事业疏远了女儿。对于路米尔来说,莎拉反而更像她的母亲,在她需要情感安抚时,陪伴她、安慰她的是莎拉而非母亲法比安。
另一方面,莎拉是法比安与玛侬友情的沟通人物。法比安与玛侬之所以能够化敌为友,就在于她们有着共同需要克服的心魔——莎拉。对法比安来讲,玛侬就是莎拉的现实镜像,与她形成了演艺事业上的竞争关系,她需要再度化解这种紧张关系。对玛侬来讲,她需要克服“小莎拉”这一名号所带来的影响焦虑,同时与前辈演员法比安达成和解。而和解依赖的是法比安对玛侬表演观的认同,具体来说是玛侬的两种表演观:其一是细节的连贯性,玛侬建议饰演38岁艾米的演员在撒谎时,可以像饰演17岁时艾米的演员撒谎时一样,表演出撩头发的动作细节;其二是现实与表演的共情,演戏时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类似情感体验。这两点都被法比安接受并运用到《关于母亲的记忆》的表演中去。
二、科幻戏中戏的母女关系叙事功能
电影《真相》构筑了三个世界中的母女关系:法比安自传《真相》中的母女关系、电影《真相》中的母女关系、科幻戏中戏《关于母亲的记忆》中的母女关系。这三种母女关系相互影响,环环相扣,构成了完整而复杂的叙事链条。
首先,自传《真相》中的母女关系遭到了法比安的美化,原本充满矛盾、误解的母女关系被虚构成和谐的亲情关系。古今中外的母亲形象大多是正面的、积极的,因而质疑母亲就成为文化禁忌,但正如《母爱创伤》所提醒我们的,应该正视无爱母亲、问题母亲的存在:“我们总相信母亲的定义就是能爱孩子、保护孩子,而且永远慈爱亲善。这种迷思为许多无爱母亲提供了掩护,因为丈夫、其他家庭成员和社会通常不愿直接批评或仔细检视这些母亲。”法比安就是典型的无爱母亲,她人格独立、经济自主、事业有成,是现代女性独立价值观念塑造的新女性。但在家庭关系方面,却与前夫、女儿、管家等人关系紧张,按照传统家庭观念又是不称职的。自传反映出法比安两种深层心理。一方面是以演员为第一要务的显性心理,在路米尔指出法比安身为人母的失职之处后,她并没有表现出歉意,反而为自己篡改事实的行为辩护说:“我是演员,我不能说出赤裸裸的真相。真相不能打动人。”另一方面是渴求和睦母女关系的隐性心理,自传《真相》就是法比安的白日梦,是她内心深处渴望亲密无间母女关系的文学表征。
其次,自传中不实的母女关系成为现实层面母女关系冲突的引爆点。路米尔的女儿夏洛特将外祖母的房子看作是一座城堡,路米尔却不无深意地提醒女儿:那是一座后面带有监狱的城堡。路米尔必然受到过家庭创伤,才将家庭看作是禁锢之地。“通常女孩在成年的过程中,是借由与妈妈建立认同及情感连接,定义自身的女性特质。但当母亲有虐待、尖酸、令人窒息的对待、抑郁、怠忽或疏远的倾向,导致这段过程无法顺畅进行,他们会被迫独自奋战,努力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坚实定位。”因此才有了她后来的远嫁纽约。路米尔从美返法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真相》修复母女关系,寻回长期处于缺失状态的母爱。
最后,与现实层面缺失型的母女关系不同,科幻戏中戏中的母女关系是补偿型的:身患绝症的母亲时日不多,为了能够维系与女儿的母女关系,以太空飞行来骗取时间,每隔七年与女儿见一面,女儿对母亲的缺失虽时有不解,但最终得以和解。戏中戏的母女关系贯穿《真相》始终,是促成法比安和路米尔母女关系和解的关键。是枝裕和曾说:“长期以来,我讲述的都是‘缺失’和‘死者’,总给人一种消极的印象。”《真相》延续了是枝裕和电影“缺失”的传统主题,却又因《关于母亲的记忆》具有了弥补缺失的新主题。
症结的解开靠的是颠转视角。《关于母亲的记忆》提供了最为重要的颠转视角——母女外貌与身份的颠转。既有外貌层面母女关系对身份层面母女关系的首次颠转,比如38岁时的女儿面对26岁的母亲如是想:“我脸上的皱纹比妈妈的还多,我觉得我需要保护她。”也有心理层面母女关系对外貌层面母女关系的二次颠转,比如小说最后,年轻的母亲与年迈的女儿均迎来了生命的大限,女儿靠在母亲身上睡着时重拾小女孩的感觉:“她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我身旁,我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逐渐睡去,仿佛回到小时候,而且知道,醒来时她一定会在我身边。”《真相》里母亲法比安扮演的是女儿艾米,她最开始无法演好年迈女儿的角色,甚至错说了年轻母亲的台词。一天早晨,法比安拿着坏掉的录音笔(里面有前夫《关于母亲的记忆》的台词录音)无助地闯进女儿的房间,法比安女强人的形象在这一刻被损坏了,路米尔由此开始注意到母亲的孤独与脆弱。
而法比安也因出演科幻戏中戏而注意到女儿的心理创伤,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称路米尔演出《绿野仙踪》时她有在场,只是为了回避对路米尔的糟糕表演进行评价而未露面。和解后母女相拥,然而就在这令人感动的崇高时刻,法比安心中所系的仍旧是演戏:“太浪费了,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些情绪留在片场用?!”母女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深情,瞬间又出现了“裂隙”。这一“裂隙”揭示出母女关系和解的微妙之处:只有在实现自我的基础上,才能与他者达成和解。正如是枝裕和所说:“戏名的‘真实’就有了双重意义,或是隐含一种讽刺的余韵。”刘宇昆原著小说中的母女和解并没有这种讽刺性,微妙性或者说讽刺性是枝裕和对原著小说的创造性改编。
《真相》里科幻与现实两种场景的互动,体现的就是母女关系和解的微妙性或者说讽刺性。一方面,科幻戏中戏对母女关系的和解有直接促成作用;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母女关系反过来又对科幻戏中戏的表演产生了反作用。母亲法比安从母女和解中获得了表演的灵感,要求重新拍摄科幻戏中戏。而女儿路米尔惊讶之余,也终于学会了将表演运用到生活中去,她让自己的女儿去欺骗外婆说:“我希望你能去一艘太空船上,这样我成为演员的时候你就能看见我了。”听到女儿关于外婆听后很高兴的反馈,路米尔露出了成功的喜悦表情,这是她作为“导演”的成功处女作,而且其中内含着导演凌驾于演员的权力。所谓母女关系的和解,本质在于母女双方看待母女关系的视角有所变化。女儿的视角变化在于:越来越理解表演,从而越来越理解以表演为重的母亲。母亲的变化在于变得越来越重视家庭,进而越来越理解渴求母爱的女儿。
三、科幻戏中戏的跨文化叙事功能
刘宇昆的科幻小说被刘慈欣称为“诗意的科幻”,向来不以未来科技为噱头,而着力展示未来科技影响下的人性、人心、人情,具有十分鲜明的东方思维特征与美学风格。刘宇昆而非卡佛,置于法语电影《真相》中,无疑具有了沟通东西方文明的跨文化叙事意义。
是枝裕和何以要赋予《真相》强烈的法国性呢?一方面,《真相》的法国性是字面意义的法国特性,传达出是枝裕和对尊崇艺术性的法国电影、法国演员、法国电影节的致敬;另一方面,《真相》的法国性隐含着世界性的含义。以日本视之,法国性最凸显的含义其实就是非日本的外国性,而外国性又可转义为世界性。日本性恰恰是是枝裕和最不想让国外观众所注目的。是枝裕和的电影大多亲自编剧、导演、剪辑,因此,电影的作者性非常强烈,日本属性就是作者性的重要要素。经过跨文化放大镜的放大之后,国外观众对他电影的日本属性感受尤其强烈。但他更希望国外观众在自己的电影中感受到超越国度的世界性。侯孝贤的天地有情观就是世界性的体现,是枝裕和受侯孝贤影响非常大:“我非常认可侯导‘天地有情’这样看待世界的态度。这是一种如何来凝视这个世界的视角,同时也是一种包容世界的胸襟。电影中的风景并不属于作者,而是属于这个世界。”
与是枝裕和对世界性的追求相契合,电影《真相》蕴含着非常多的跨文化属性。跨文化叙事既是《真相》的外在叙事,也是其内在叙事。所谓外在跨文化叙事,体现在电影创作者的跨文化身份上。导演自身具有强烈的跨文化背景。从家庭人缘关系来讲,是枝裕和的父亲是中国台湾人,这使他对中国文化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中国台湾导演侯孝贤对他影响深远,他曾将侯孝贤视作自己电影创作上的父亲:“如果我没有和侯导相遇相知,就不会用现在这样的手法拍电影了。在台湾的时候,我经常和侯导一起吃饭,一直保持联系。对我来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侯导就像一个父亲一样。”而戏中戏《关于母亲的记忆》原作者刘宇昆,是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其科幻作品十分注重中美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印证了张龙海、张武的如下观点:“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包括美国华裔作家在内的全体海外华人对于中华民族(包括文化)的认同感越来越强。”正是因为电影创作者的跨文化身份,才使得电影中充满了《关于母亲的记忆》、中餐馆等东方文化元素。出生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刘宇昆,用英语创作了《关于母亲的记忆》,随后被翻译成日语,从而进入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视野,最终成为法语片《真相》的科幻戏中戏。因此可以说,《真相》融汇了日、法、中、美四种主要的国别文化属性。
《真相》的内在跨文化叙事体现在电影内容上,尤其是科幻戏中戏与电影主线故事间的互通上。从科幻文学这一类型文学来看,本身就是现实与幻想的颠转视角。颠转视角与电影所需要的和解在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而跨文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同文化间的跨视角,与科幻文学具有内在一致性。在此意义上,跨文化叙事为友情叙事、母女关系叙事建构了基本的文化语境、逻辑语境,而友情叙事、母女关系叙事都可以看作是跨文化隐喻。友情叙事与母女关系叙事是个人间的微观叙事,而跨文化叙事是民族间的宏观叙事,但它们都是关于自我与他者的沟通交流的叙事。前者由最初的紧张、冲突走向了和谐,有赖共情心理机制的建立,后者则由最初的互不了解、对立冲突走向了交流、理解。自我与他者的有效沟通与彼此理解,离不开颠转视角。
总之,电影《真相》构筑了一系列镜像关系:电影《真相》与传记《真相》、戏中戏——《关于母亲的记忆》与戏外戏(戏外小说)《关于母亲的记忆》、外公皮埃尔与乌龟皮埃尔、现实中的母女关系与戏中戏中的母女关系、莎拉与小莎拉(玛侬)……这些蕴含着张力和差异性的镜像关系,既促使剧情向前发展,又容纳了视角主义的哲学方法论。收束了三种叙事功能的科幻戏中戏《关于母亲的记忆》,为是枝裕和提供了多维视角,体现出他电影叙事、电影思维、电影方法论上的视角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