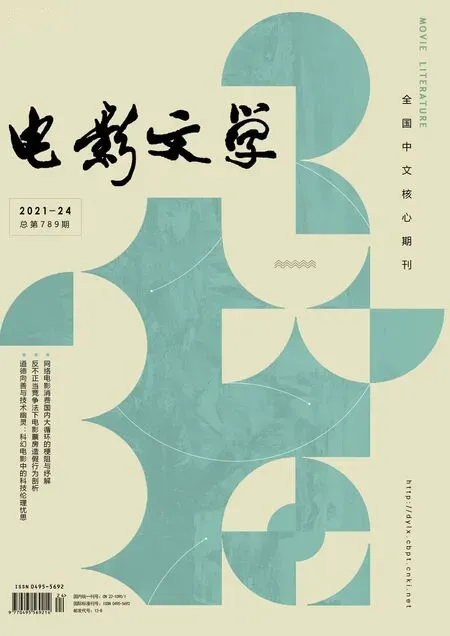地缘学视阈下战争题材电影中的厦门形象研究
黄诗娴 肖家豪
(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
在中国近现代战争史上,厦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地缘存在。厦门地处环太平洋西岸中心点,是我国东南沿海以及台湾海峡西岸的门户,东西交会、南北贯通。背靠大陆、面向太平洋的地缘属性,决定了其成为国际化口岸城市的先天条件。作为侨民移居海外的重要出发港以及返乡的重要登陆港口,厦门与海外华侨华人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作为对台工作“前线”,两岸尚未完全统一的政治现状决定了其战略要地地位。厦门特殊的地缘属性,也通过电影呈现,尤其是战争历史题材电影。《英雄小八路》(1961)、《海囚》(1981)、《小城春秋》(1981)三部电影,分别以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厦金炮战为题材背景,勾勒了近现代革命战争史上厦门的城市影像。
以往中国电影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时间范畴,空间维度的缺失导致研究者对中国地缘电影认知空白。中国电影百年长河中呈现出了具有不同地缘文化意义上的诸多作品,它们共同地讲述着不同地缘文化中的历史主题。地缘文化研究可以提供一种理论视野,特别是在中国电影学派与中国地域电影研究方面,借助地缘文化与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式,为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提供可操作性的科学工具。以空间视角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电影,有早年开始的对海派电影、京派电影、西部电影的研究,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江南电影、东北电影、粤港澳电影及部分民族地区电影概念的提出。就区域电影研究的现状而言,由于福建电影工业不发达、缺乏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代表作等,以福建为背景的“区域电影”相较于其他地区一直极少被关注。对于“福建电影”尤其是“厦门电影”的研究,伴随着中国电影金鸡奖长期落户厦门、厦门与电影的情缘进一步深化而凸显出其必要性;同时,作为尚未被关注到的中国电影的一个“区域电影”,对于“厦门电影”的研究也有助于丰富中国电影地缘文化研究的内涵与外延,验证并充实中国地缘文化电影研究的理论建构。
“地缘”指因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地质条件而形成的特定国家或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地缘政治“指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情况的地理因素的相互结合,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在特定历史时期,各方政治势力围绕权力利益进行战略规划与博弈,这是地缘政治学的理论要义。地缘文化则指“同一空间区域内的社会群体因受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影响而形成的具有共同内容和特征的文化系统”,而文化是隐藏于地缘格局下的深层动因。本文将从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两个地缘学要义,以三部厦门为背景的战争历史题材电影为研究文本展开论述:电影中的厦门,在鸦片战争时期,既是混杂的通商口岸,又是屈辱囚闭的“孤岛”;在抗日战争时期,既是华侨群起抗日的中继站,又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革命斗争的风暴眼;在厦金炮战时期,既是两岸对峙的战地前线,又是坚韧御敌的英雄之城。三部电影共构了作为中国战争记忆一端的“厦门”城市形象,完成了地缘特殊的厦门在中国城市中独一无二的再现。
一、《海囚》:混杂的通商口岸与屈辱囚闭的“孤岛”
电影《海囚》改编自厦门籍作家洪永宏的同名小说。1980年应北京电影制片厂之邀,《海囚》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1981年8月由曾导演《泪痕》并荣获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李文化出任导演。电影基本遵循了原著小说的创作思路,重现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主谋“卖猪崽”(华工贸易)的历史,讲述华工暴动反抗以彰显民族气节,最终却又被清政府绞杀的悲情故事。
鸦片战争后,随着军事进攻而来的还有殖民者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多层次的侵略,在地缘上作为中国东南沿海门户并拥有良港优势的厦门被侵占为通商口岸。一方面,殖民者纷纷在厦门设立使馆、划定租界、开办洋行;另一方面,在殖民者残酷的经济掠夺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产生大批破产农民及手工业者,传统农业无以为继的他们纷纷流入厦门城市以出卖劳动力为生。集聚在厦门的劳动力正好对接了殖民者这一时期在北美洲西部及澳大利亚南部进行矿业开发的劳动力需求,因而殖民者纷纷干起买卖、拐骗华工的罪恶勾当。电影《海囚》讲述的故事正是建立在《闽南革命史》记载的这一史实上:“从1845年—1850年,西方殖民者先后在厦门设立了合记、德记、瑞记、怡和等多家卖人行,它们都设有专门囚禁华工的地窖或暗室,称为‘猪崽馆’……他们以3~10元买一个华工,再以100~400或500元卖出,利润高达十至数十倍。”
影片中,厦门的地缘特性在殖民地社会特有的“洋行”空间中得到展现:琉璃窗棂上挂着精致的布艺窗帘,中式茶柜、博物架上摆放着红酒与威士忌,在东西方元素混杂的房间里,居中的是一幅维多利亚女王像,周围还摆放了鹿角、狮像、鹰像等物件,指代侵略中国的殖民者以及作为“猎物”的厦门。这一空间隐喻的是异质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侵入,这种文化混杂感正是来源于厦门在地缘上作为本土文化之原生地及异质文化之入口的想象。在领事馆、洋行空间里,主谋华工贸易“卖猪崽”的驻厦领事、拥有武装力量的洋船长、内外勾结的买办汉奸、腐败昏庸的清政府官员,共坐一桌商讨如何填补澳大利亚的劳动力需求、拐骗厦地百姓出洋为奴。驻厦领事、洋船长、买办汉奸这些社会身份是由厦门的特殊地缘所确认的,这些立场不同、种族各异的人物因在厦门得到了金钱利益上的共同点而得以联结,组成了影片故事核心矛盾中的“压迫者”一端——通过特殊地缘生发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高度集中”这一“在地经验”来强调厦门的特殊性,厦门便作为“前提”而催生了后续华工贸易的悲剧。
影片中的厦门空间对应“海囚”这一题名,依托“囚牢”“囚徒”蕴含的“封闭”与“狭小”进行空间塑造。影片以近岸的平静海面开幕,此时共同活动于海面这一空间的是唐姓宗族的小渔舟以及西方殖民者先进、庞大的商船。唐姓宗族的青年发现了漂浮在海面上的受难同胞,准备营救之时却遭到了西方殖民者的戏弄和侮辱,面对殖民者急速驶来的庞大船只,只好弃船泅回岸边。这一幕中,殖民者的大航船对厦地百姓小渔舟的撞击,是对外族战争入侵导致本族生存空间坍缩的空间表达,靠海为生的厦门人民此时只占有广阔海洋空间的一星半点儿,只能退缩回受到多重剥削的陆上。然而,如同牢笼般囚禁着厦地人民的不仅是浩瀚海洋与殖民者的飞鲨号商船,还有陆上封建王权施以的排挤与迫害。影片中,殖民者为逼迫华工签下出洋为奴的卖身契而剪断华工的“发辫”,被剪掉辫子的华工面对前路是暗无天日的矿山奴隶,后路是国与家对失去了辫发的自己将施以的排挤与迫害,在这“出洋为奴,归家亦为奴”的夹缝中,劳工纷纷失了魂似的跳下船只,葬身茫茫大海。
唐氏宗族与潘氏宗族之间的血腥械斗开展于对宗族祠堂的进攻中。械斗发生前,唐氏宗族子弟严守在由门楼及上厅分置前后两落,并围成一个天井组成的祠堂空间。镜头随着三个建筑实体各有高低、升降、进退的布局移动,扫过祠堂内的回廊、屏门、照壁等构件,展现这一空间“封闭性”“等级性”“团结性”的建筑意蕴,暗合了宗族械斗发生的荒谬原因——本来只是唐金龙与潘火狮两名“分属两个宗族的个体”之间的一场误会,在宗族观念、宗族制度的发酵下,同一宗族内毫不相关的其他个体也被卷入误会中,最终演变成为两个宗族之间大规模的血腥械斗。械斗发生时,潘氏宗族的子弟用木桩攻破了唐氏祠堂的大门,在两个宗族缠斗的过程中,殖民者雇用的“拐子手”在外部将祠堂大门封闭,械斗由此变成了一场无路可退的“死局”。两个宗族的青壮年也在缠斗力竭后被殖民者及“拐子手”轻而易举地拿下,沦为囚徒运送出洋。祠堂本是作为祖先认同与荣耀象征的“家园”,此时变成了殖民者得以将华工一网打尽的“囚笼”。
与华工封闭狭小的生存空间以及始终无法摆脱的“囚徒”命运相对应的,是厦门作为“伤城”的战争记忆与地理位置上的海中“孤岛”。“影像不是现实的摹写,而是艺术家的创造物,是经过文化‘过滤’的符号。影像的组合方式,是具有纯语言的约定性的重新结构的符号系统……为的是增添文化的属性。”无论是为了谋生谋财而主动走入的华工,还是因拐卖、抢夺而被囚禁上船的华工,再或是选择暴动反抗殖民者最终却被处刑的唐金龙与潘火狮,人物始终笼罩在“拯救、囚禁,自我拯救、再被囚禁”命运之下,影片将人物的心理活动与镜头对准的浩瀚大海进行组接,海洋意象在此绝不只是为了表现自然,而是以海洋与岛屿在空间上的包围关系,赋予海洋“牢笼”隐喻。在电影中,厦门人民是被殖民者囚禁的海上囚徒,厦门在地缘上亦是被战争围困的海上囚徒。
独特的宗族文化与神灵信仰为闽南一隅的地缘文化烙下了深刻的印记,《海囚》对厦门的宗族关系及神灵信仰的影像叙事,既拓展了观众对厦门民风民俗纵深的感知,也为影片增添了批判反思的思想价值。对宗族关系的强调与恪守是厦门乃至闽南民生的独特风貌,闽南宗族关系的基质在于血缘性,宗族成员以姓氏为表征的相同血缘关系出发,联结其宗族的其他亲属关系,构成了宗族所聚居的地区的基本组织形态。这一宗族关系的组织形态在民间对榕树的崇拜中可以洞见,榕树往往是枝干繁茂、盘根错节的,闽地人民理想的宗族形态即如同榕树一般主干扎根,新的枝条不断繁衍开拓,最后历经百年形成“独木成林”之大势。《海囚》中的唐氏宗亲与潘氏宗亲就是盘踞在厦门的两个大族,两个宗族的成员都在以姓氏符号为标志的秩序约束下,对宗族内部荒谬的权力配置深深认同并恪守,这一权力配置的荒谬尤其体现在潘姓宗族——潘汝非的一个身份是与殖民者勾结谋划“卖猪崽”的洋行买办,如此一个唯利是图、可以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全族人生死的汉奸,却因为辈分居于宗族首要,而成为潘姓宗族的族长。潘汝非利用宗族制度赋予族长无上的权威与号召力,号令宗族的青壮子弟进攻唐姓宗祠,挑起两族间的血腥械斗,亲手将自己的族人送进了殖民者的牢笼中。
“神灵信仰”作为闽南民间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有机地融入了电影故事的发展中。《海囚》中的破产农民张天乙是被洋行雇用的头号“拐子手”,闽地民间的神灵信仰是促使他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尚未泯灭的真、善、美而完成“英雄转变”的最大动因。随着影片故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华工被抓捕、囚禁,张天乙前往跪拜神灵以求减轻内心的负罪感,特写镜头多次在庄严的神像与张天乙紧张的面部表情之间切换,并通过人物与神像之间悬殊的大小关系、俯仰交替的视角转换来表现张天乙内心的道德焦虑。然而这些没有直接触动张天乙“迷途知返”,他反而在跪拜神像时以“家中老小需要养育”为说辞更加坚定了要“干最后一票”的决心。这里透露出闽地民生对于神灵信仰的实用性与变通性心态,以及神灵信仰在战争年代对人性向善框范的无力感。然而令张天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恶因恶果的报应最终还是落到了自己头上,最后一个被他亲手捉拿的“猪崽”竟然是自己来厦寻父的儿子——本着能给家庭带来物质供养的愿望干起罪恶勾当的张天乙,却在阴错阳差间掳走了自己的儿子,亲手将自己儿子推向出洋为奴的无底深渊。影片的结尾,张天乙以肉身抵住迸发的土炮,通过牺牲自己拯救他人完成了“英雄转变”。在神灵信仰对人物张天乙的笼罩下,他或是变通、世俗地苟且求安,或是高尚、英武地奔赴死亡,正是这种独特的人神对话方式深深影响了闽南百姓的生活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此同时,影片在呈现闽南民间神灵文化、宗族内部荒谬的权力配置和荒谬的宗族械斗时,选取的是一种冷静的旁观者视角——甚至将“殖民压迫”这一叙事重心放置在一边,毫不留情地把“宗族制度”“好斗恶习”“信仰异化”这些的闽南地域需要反思的民风民俗,与人物的死亡、囚禁、屈辱的结局缠绕在一起,唤起对传统糟粕的戒备与批判。
二、《小城春秋》:中共地下组织革命斗争的“风暴眼”与华侨抗日的中继站
电影《小城春秋》改编自厦门籍作家高云览的同名小说,以“5·25”厦门破狱斗争这一中共福建党史上的光辉事件作为影片矛盾冲突的核心,讲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厦门革命者的生活与斗争。作为福建电影制片厂生产的第一部故事片,“当时制片厂定下调子,拍摄的故事片必须取材于一部成功的、为社会所认可的小说,而且要能体现福建地域特色”。最终,高云览真实反映1927年—1936年间厦门地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与《青春之歌》“一南一北,互相辉映”的小说《小城春秋》脱颖而出,登上银幕为中国影坛吹来了一阵“东南风”。
电影文本将独属于厦门的景观植入影像中,将“小城”这一地域支点植入“春秋”,完成了对小说文本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厦门经验”的承袭——以鼓浪屿的自然风光揭开故事的帷幕,镜头视点首先从画面的左端向右平移,画面中鼓浪屿洋楼林立,海面平静无波,随后从对日光岩的特写渐渐拉至全景,再给鼓浪屿上的特色建筑一个整体展现。鼓浪屿承载了革命青年畅谈理想时的意气风发,共产党员吴坚与恋人书茵的相知相遇也与鼓浪屿的浪漫气息相得益彰,恋人、友人离别时的欲说还休,更是凝练成鼓浪屿岸边平静海面上等候的小舟,向着夕阳缓缓驶去。随后,在“抗日救亡运动宣讲会”、张贴“抗日救亡告示”等人物行动下,“南普陀”“中山路”“思明电影院”等厦门城市地景以走马灯的形式得到展现,电影故事开始走向对中共地下组织在厦门的具体斗争活动的讲述。
“厦门经验”的另一面在于电影故事与“厦门一角”的地缘政治史实相契合,为影片注入了深刻的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内涵。20世纪30年代中国“当时的革命活动不论在哪里进行,都是带着革命者建设新型国家的理想和抱负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名党政府进行斗智斗勇”。与此同时,厦门自晚清时期被列为通商口岸以来,文化事业发达并拥有兴盛的报刊出版基础,成就厦门作为抗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宣传活动的孵化地与最前线。在电影《小城春秋》中,由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厦门爱国学生、爱国群众组织的报刊“厦联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然虽国难当头,国民党当局却丝毫没有放松对中国共产党的压制,不顾民族危难而以各种理由禁止一切抗日宣讲活动,查封厦联社及其他爱国进步组织。在厦门活动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吴坚遭到国民党侦察处长赵雄的逮捕并“因言获罪”,赵雄一方面通过以往的兄弟情谊利诱、软化吴坚的革命信仰,另一方面又利用因政治无知误入侦察处当秘书的林书茵与吴坚的旧时恋情打动吴坚,暗合了时代对革命者的政治属性与个人情感属性的两个核心评价向度,具有“青年投入革命、融入集体事业的隐喻性指向”。电影画面闪回在过往意气风发的少年交游、温情的恋爱与当下吴赵二人剑拔弩张的对质之间,影片的叙事节奏也随着自然景观(鼓浪屿风光、海洋风光等)向人文景观(中山路、南普陀、厦门大学校舍等)的镜头流动中逐渐加快,契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在厦门这座小城展开的、如同“风暴眼”般看似平静实则险象环生的史实基调。
“艺术作品常常通过转喻的方式来表现对象。不同于社会学直接运用科学方法来解析城市,电影善于转喻式地通过人群来表现城市”。厦门所蕴含的独特乡土文化气质与风情在吴七这个乡土形象的暴烈、耿直和肝胆,以及秀苇这个小城女性的单纯与多情中得以窥见,而影片对厦门地缘文化中更为突出的个性与特质的建构则集中在对华侨群体的刻画中。厦门扼守出入南洋海上通道的关键位置,是福建人民移垦东南亚国家的主要出发港,承载了华侨群体的“原乡”想象;同时又是这一特殊时期毅然选择归国抗敌的华侨志士的主要登陆港,更是成为华侨群体归国抗日的中继站。华侨群体为厦门带来的不仅有城市风貌、生活方式等表征上的变化,更是参与到了厦门城市人文气质与爱国精神的建构中,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华侨群体以厦门作为祖籍国危难求援的“地缘纽带”“情感纽带”,以厦门作为救国行动的中继站,与厦门城市形成了强烈的关联。因此,在“城市—人群”这一关系中,华侨群体是在地缘上作为侨乡的厦门最为显著、直接的表征,《小城春秋》正是自觉利用了华侨与厦门城市之间的强烈关联,将故事人物薛嘉黍这个抗战时期的老华侨设置为认知、表达厦门的有效路径。
自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来,旅居海外的华侨同胞同仇敌忾,有的倾资为国为乡兴办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有的奔波筹钱支持人民军队,有的投身于文化救亡工作号召一致对敌,更有的踊跃回国参战、奔赴战场前线英勇杀敌。电影《小城春秋》中的人物老华侨薛嘉黍就是归国抗日华侨群体的一个缩影,薛嘉黍本着“祖国安危系最重要之事”全力支持厦联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组织工作,对国民党当局“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公开禁止共产党的抗日宣传活动、借此加害共产党员的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在共产党员吴坚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时,更是亲自出面与敌人进行周旋并设法营救,运用自己的家财、人脉不断地支援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斗争,保护在厦门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生命安危。
相较于原著小说,电影《小城春秋》精简了对薛嘉黍生平经历、家族背景的刻画,将华侨群体爱国爱乡精神之缩影的人物薛嘉黍作为观影者感知厦门的“中介”,集中地将薛嘉黍作为革命斗争与抗日行动的启蒙者与实干家来进行人物形象塑造,联结华侨群体在抗战时期为祖国鞠躬尽瘁的一段佳话的同时,忠实地还原了作为华侨同胞并投身于“东南亚华侨文化救亡运动”的小说创作者高云览本人的厦门情怀。虽然影片展现的只是厦门革命斗争记忆的一个截面,“5·25”厦门破狱斗争这一史实的本真面貌也会在经过影像、戏剧的重塑之后有所失真,但以华侨来联结厦门城市,所传递出来的一定是这座城市独有且真实的人文气质与爱国精神。
三、《英雄小八路》:两岸对峙的战地前线与坚韧御敌的英雄之城
电影《英雄小八路》经历了从真实故事到话剧改编再到银幕呈现的过程,首先由厦门禾山中学(现厦门市何厝小学)的总辅导员、语文老师王添成根据当时处于两岸炮战前沿地带的厦门市禾山第四中心小学的“前线少先队员支前活动大队”的真实故事,写作了《英雄小八路》的话剧剧本,后由上海戏剧学院陈耘老师结合自己访厦的调查采访编成话剧《英雄小八路》,最后在上海市委的牵线下交由上海天马制片厂完成电影拍摄工作。
作为一部“为了让更多的青少年学习‘英雄小八路’的勇敢精神,同时,也为了向党的40周年献礼”的“十七年电影”,电影《英雄小八路》担负更多的是以社会主义理想引导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艰巨任务。影片所呈现的这段战争记忆在20世纪60年代的“观念系统”之下,复现于厦门、金门这两个由不同意识形态符号建构的空间中。展现厦门前线百姓生活空间是画有“军民协力,坚守海防”“炮击金门,严惩美蒋”等口号的古厝民居;金门空间则由欢快的爵士音乐、喝红酒吃牛排的生活风格,国民党旗帜与“USA”等符号进行建构。小英雄们在战地前沿人民公社的组织和引导下,伴随《给解放军叔叔洗衣裳》《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音乐,在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中为解放军战士洗衣服、送茶水、修工事,与“美蒋”派来的间谍特务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一名名优秀的战士;而金门上的“美蒋”据点最终被炮火摧毁,“美蒋”军队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轰击下抱头鼠窜,金门一片焦土狼藉。在厦门、金门空间的对立中,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厦门空间更多承载的是那个时代人们对新生政权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想象,“焦土狼藉”的金门空间则是对国仇家恨的释放;同时,这样一种将重大历史事件(题材)细化到平民人生的讲述方式与创作方法,更能激发观众对时代精神的充分认同,将家国观念、军民融合等集体意识和集体记忆深深植根于全体观众共同的价值观念中,形成了一致的国家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达到了正本清源、社会教化的传播效果,从而产生了“英雄小八路和那个走出自然灾害困境的时代相辉映,成为亿万人崇拜的英雄”这样独特的观影体验。
“时代的主旋律不是标语口号式的空喊所能表现的,它必须在异彩纷呈的题材、风格、样式和艺术手段中渗透出来,必须在丰富多彩的人物、情节、细节中凸显出来”,在肯定《英雄小八路》对弘扬时代精神以及教化价值上的成功时,不应该回避影片在艺术手段和细节处理上的单薄。历史上,受到抗日战争及国内局势变化的影响,厦金两地先后被日本侵占,国共内战期间两地成为海峡两岸对峙的前线战地,炮火威胁、亲属隔绝的状态维持了数十年之久。尤其在两岸军事对峙时期,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派遣军队以金门岛为前哨据点,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扰袭和破坏活动。《英雄小八路》影片的开端即是金门岛上“美蒋”军队发射过来的炮弹炸伤了厦门百姓、炸毁了小英雄们的学校,步入了新中国、拥有了新生活、展现了新面貌的厦门,因为特殊的地缘而不得不再次卷入战争的旋涡。然而,作为故事发生地的厦门却只居于电影舞台的次要位置,厦门空间中客观存在的建筑景观以及长期形成的市容市貌被以闽南古厝为内景与海岸战地为外景的电影叙事空间所覆盖,厦门的独特景观、地缘文化被时代的共性同化到难以辨认;电影中作为故事主人公的一群“厦门少年”被典型化为“少年先锋队”融入宏观叙事之。就地缘而言,厦门岛、金门岛均为福建省东南沿海岛屿,两地直线距离仅10余千米,历史上长期处于同一行政管理体制之下,在相同的地缘文化辐射下保持着一体化程度极高的地域关系与血缘亲情。《英雄小八路》在主流政治话语以及创作理念的框架下,“搁置”了地缘上隔海相望、一衣带水的厦金两地重要的“亲属分离”主题、“同根同源”主题,而简单地以正邪对立来对厦金关系进行艺术表达,实为一件憾事。
结 语
《海囚》《小城春秋》《英雄小八路》分别将厦门镶嵌在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和厦金炮战三个大背景中,呈现了中国战争记忆中的“厦门一角”。在对厦门地缘政治、地缘文化要素的自觉认知与合理建构中,《海囚》突破了仅作为战争“受害经验”储存器的简单介质功能,拥有了对宗族关系、民风民俗的反思性内涵;《小城春秋》抓住华人华侨群体与厦门城市的情感联结,以转喻的方式通过人物来表现城市,搭建起观影者对厦门经验、厦门气质、厦门风貌进行感知的桥梁;从《英雄小八路》对集体记忆的诠释来肯定其在社会教化功能上的“得”,以地缘政治、地缘文化的视角探讨其在对厦金关系表达上的“失”,在一定程度上为厦门电影创作乃至类型电影创作提供了思考和启示。
2019年起,中国电影金鸡奖长期落户厦门,厦门市积极“以节促产”。近年来,厦门凭借其美丽的岛屿风光和海滨景观、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众多具有独特美学风格的校园,每年吸引上百个影视剧组来厦拍摄。厦门高颜值、现代化、充满青春气息的海滨城市形象也随着《第一炉香》《紧急救援》《西虹市首富》《快把我哥带走》《同桌的你》《以家人之名》等影视作品的火爆而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厦门的城市形象逐渐“模糊化”,成为全球化时代下在地特征不明显的现代都市,甚至是虚拟的“西虹市”。反观本研究所讨论的三部电影,则强化了“厦门”特殊且无可替代的地缘属性,建构了厦门的历史文化记忆,也从电影与地缘文化的互动视角,构成了当前厦门电影产业发展热潮和建设“全域影城”背景下,如何发展“厦门电影”的一个别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