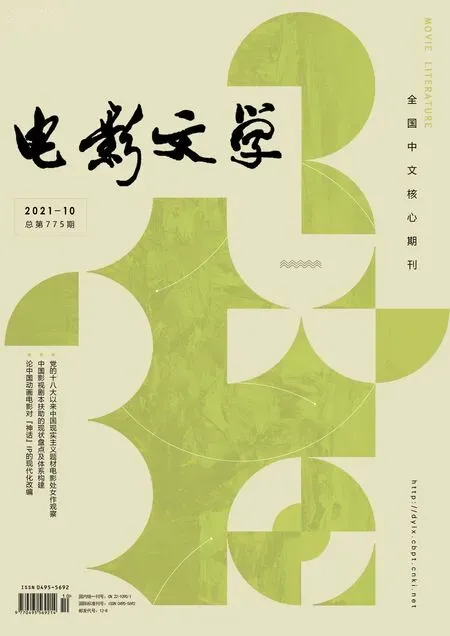糖炒栗子
1.外景 四合院 夜
一只野猫从屋脊上跑过,抖落了一层积雪。
大腹便便的房东穿过院子,手里摆弄着一副牌,正往院门走去。
王有福拎着一个包袱、一个生锈了的暖瓶和一塑料袋杂物,低着头快步走向厢房,正巧与房东走了个迎面,急忙闪躲房东的目光。
正屋的灯灭了,房东妻子的身影伏在窗前。
房东妻子:行啊,打牌都专挑年三十儿,我看你就是成心的!
“哐”的一声,窗户被狠狠地关上。
2.内景 厢房 夜
昏黄的灯光下,一只粗糙的大手正笨拙地按着老式黑白屏手机的键盘,屏幕上出现“刘工头”几个字,未几,电话里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的提示。
斑驳的木桌上摆着几个安全头盔和矿灯,一张全家福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赵米仙拿起相框,轻轻地抚摸着,不由得发出一声轻叹。
一阵窸窣声传来,房门被打开了,呼啸的风声霎时侵入了屋子。
王有福走进来把东西轻轻地放在火炉旁,站在狭小房间的一角,看着桌旁静坐的赵米仙,一言不发。
良久,赵米仙仓皇起身,毛衣被桌上的钉子钩住,露出手臂上依稀残留的文身。见到毛衣袖口被扯坏,赵米仙的眉头皱了起来。
王有福从床底下拿出一把螺丝刀,上前撬起了钉子。
赵米仙捻着袖口的毛线头,悄声靠在窗户前,往院子里看去。
3.内景 正房 夜
赵米仙把铁丝做成的钥匙揣进兜里,两人蹑手蹑脚地走进里屋,绕过火炕。
房东妻子翻了个身,王有福大惊,被门槛绊了个踉跄,碰到了房东妻子悬在炕沿上的胳膊,被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赵米仙回头,向其摆了摆手,往衣柜走去。
墙上悬着一面大镜子,镜子反射出赵米仙从抽屉中翻出一个月饼盒,他打开盒子,发出了声响,金条明晃晃的光从镜子里闪过。
房东妻子突然睁开眼,看到一旁的王有福,失声大叫。
王有福惊慌失措,上前死死捂住她的嘴。
赵米仙迅速地把盒子里的现金和金条塞进袋子里。
房东妻子拼命地挣扎,慌乱中,王有福顺手拿起桌上水壶。
赵米仙匆忙跑过去制止。
没等赵米仙说话,“哐啷”一声,瓷片散落到地上,王有福瞪大了眼睛。
4.外景 荒野 夜
烟花的绚烂光火在天边消散又绽放,远处的村庄依稀亮着温馨的光。
赵米仙和王有福一前一后扛着一个编织袋,往远处的荒山走去。
编织袋被轻轻放在地上,赵米仙把铁锹递给王有福。
王有福看着赵米仙的脸,眼眶溢满了泪水,哽咽着哭了起来。
赵米仙收回铁锹,从兜里掏出两颗炒栗子给他,转身自己挖起坑。
雪地平整如初,赵米仙跪下磕了一个头,王有福也照做。
风雪袭来,雪地上的脚印渐渐消失了。
5.外景 候车大厅 晨
候车大厅墙上挂着的横幅格外醒目:用真心的笑容照亮回家的旅途。
一个年轻的妈妈提着行李,背着孩子,从收银员手中接过零钱和方便面。
一张褶皱的五元钱掉落,女人挤过人群,低头寻找。
赵米仙起身,箭步上前捡起了钱,递给了女人。
王有福举着买好的车票向赵米仙招手。
6.内景 正房 晨
房东满面红光,醉态尽显,他踉跄地走进屋子,翻身上炕。掀开被子却搂了个空,疑惑间起身张望,看见地上的红色脚印,愣在原地,大骇,滚下炕去。
7.外景 村头 晨
警车在村头停下,聂洪峰拉起手刹,警笛声戛然而止。
两个正在屋前择菜的妇人见状,匆匆收了板凳,关好家门。
聂洪峰皱了皱眉头,将胸前的警号牌扶正,对身后的同事使了个眼色。
8.内景 火车车厢 日
检票员走进车厢,不耐烦地翻开记录册。
王有福匆忙从口袋里掏出车票,车票上依稀粘着一个血红的手印。王有福伸手去抹,血色晕染开来。
检票员渐渐走近,王有福忐忑不安地推醒赵米仙。
赵米仙睡眼惺忪,检票员的手已经向两人伸了过来。
赵米仙气定神闲地从外套内口袋里掏出车票,递给检票员,随即突然转身,捂住王有福的鼻子。
检票员拿着车票和记录册,看着两人。
赵米仙掏出一张卫生纸,匆匆卷好塞进王有福的鼻孔里,对他使了个眼色,拿过他的车票,笑着递给检票员。
检票员用两根手指捏住车票,看了看票面的血迹,又瞥了一眼王有福,在记录册上画了一笔,而后离开。
两个列车警察走进车厢,一人叫住了检票员,拿过记录手册翻看着,另一人不时往车厢里张望。
赵米仙拉起王有福,背对着警察,往相反的方向走出车厢,两人在车厢连接处站下,假装点火抽烟。
警察从两人身后走过,一个年轻的警察拍了拍王有福的肩。
王有福面如土灰,慢慢转过头。
年轻警察抽出一根烟,王有福把打火机递给他,手不住地颤抖。
年轻警察看了看王有福,走去了下一节车厢。
两人看着警察离去,赵米仙拉着王有福向车尾走去。
车窗外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黑色的电线杆和枯树快速向后移动,铁轨交错又分离。
王有福紧攥着手,赵米仙拉下门阀,呼啸的风声涌进车厢。
9.外景 荒野 日
赵米仙从雪堆里艰难地爬起,抖落身上的雪,四处张望。
王有福从远处跑来,扶起赵米仙,却又不小心摔倒。
两人躺在雪地上,仰面看着天空大笑起来。
刺目的阳光穿过流云照下来,列车驶远,消失在旷野之中。
雪地上延伸着两行脚印,直至消失在一棵高大的松树前。
赵米仙脱下鞋底磨没了纹路的军用棉布鞋,抓起一把雪,捂住脚踝。
王有福脸冻得通红,担心地看着赵米仙。
赵米仙把帽子摘下来,戴在王有福的头上。
三两只乌鸦从枯黑的枝杈上飞起,积雪落到王有福的帽子上。
赵米仙拿出手机,屏幕上的信号只有一格,他将手机举高,四处寻找信号。
10.外景 荒野 夜
风雪声混杂着鞋底踩在雪地上的“嗞嗞”声。一轮明月挂在漆黑的夜空中,寒冷的光映在雪地上。
一声犬吠突然响起,狼狗把两人扑倒在地。
远处照来一束手电筒的光,一位穿着绿色军大衣的老人喝住了狼狗,向两人伸出手。
11.内景 护林人家中 夜
黑白电视里正在播报新闻,嘈杂的声音时断时续:昨日,来山市曲阳村一人疑被其租户杀害,警方正在大力搜捕调查。
王有福慌忙跑过去关掉了电视。
烧酒在炉火上冒着的热气把玻璃窗晕上一层水雾,赵米仙擦亮窗户,看见护林老人正在擦拭门口的皮卡车,两人目光对视,老人冲赵米仙笑了笑,赵米仙点头笑着回应。他打开包袱,从里面拿出一根金条。
12.外景 山路 晨
天色破晓,朝阳从远处茂密的松林间探出头来,一辆皮卡车飞快地开出林区。
13.内景 汽车 日
一排监控探头从车顶掠过。
赵米仙抓过后座的包袱,戴上一个老旧的墨镜。
王有福系好包袱,看到里面的金条少了一根。
赵米仙撕下车内后视镜上挂着的日历牌,露出新的一页:1998年2月23日大年三十。他打开了车载广播,欢快的《春节序曲》响起。
两人哼唱起来,打开了护林老人送的烧酒。
14.内景 警察局 日
几位严肃的老警察认真地注视着监控屏幕,赵米仙和王有福的车出现在屏幕上。
15.内景 汽车 日
赵米仙透过后视镜看去,只见一辆警车正紧跟不舍,车中的聂洪峰正盯着自己。
赵米仙深吸了一口气,狠狠踩下油门,仪表盘指针逼近200。
熟睡的王有福被猛然的加速晃醒,慌张地看向窗外,随即从后座探身关掉了广播。
透过车窗,收费站渐近,一排闪动的警灯依稀可见。
赵米仙紧握方向盘,紧皱着眉头盯着路边护栏,急打方向盘向其冲去。
16.外景 高速公路 日
皮卡车横穿两个车道,撞开了护栏,冲下高速公路,开向茫茫雪地。
几辆警车紧随其后。
17.内景 汽车 日
王有福慌乱地摇下车窗,探出头向车后望去,警车愈加逼近。
赵米仙看着前方与天空连成一片的茫茫雪地,踩下油门,放开方向盘,打开车窗,转身拿起酒瓶点燃,扔向后方。
王有福模仿照做,翻出打火机。
18.外景 雪地 傍晚
皮卡车失去控制,向冰湖开去。
打头的警车停了下来,其他警车也都在远处停下,聂洪峰和几个警察下了车,看着前方直冲湖中心的皮卡车。
冰面破裂的声音传来,汽车坠湖发出的巨大声响在山谷间回荡,皮卡车消失在湖面上。
聂洪峰愣了下神,半晌,脱下外套,带领警察往湖中心跑去。
19.内景 汽车 傍晚
冰冷的湖水从车窗灌进来,赵米仙艰难地打开车门,把王有福拽到前面推了出去。接着,他自己也向车外游,然而衣袖处散乱的毛线头被排档杆缠住,几番挣脱未果,赵米仙随着逐渐下沉的车坠入湖底。
20.外景 雪地 傍晚
王有福爬到冰面上,抹掉脸上的水,望见远处正在逼近的聂洪峰等人,立刻拔腿往前方跑去。
聂洪峰:站住!否则就开枪了!
两声枪响在空旷的雪原炸开,久久回荡。
聂洪峰停住脚步,把手枪摔在地上,怒视着身后的同事,白雾从他喘着粗气的口中升腾起来。
正在湖面打捞皮卡车的众人也被枪声惊起,一齐往远方看去。
迎着夕阳的方向,中枪的王有福渐渐放慢了脚步,倒在洁白的雪地上,两颗炒栗子从他的口袋里滚落出来。
聂洪峰:是谁?谁?
一个提着气枪的狩猎人从林中慌忙跑出,惊叫一声,而后瘫倒在地。
夕阳染红了天空,金色的光芒洒在无垠的雪地上。
聂洪峰拉起瘫倒在地的狩猎人,一副银色的手铐铐在了狩猎人的枯瘦手腕上。
聂洪峰俯身解下王有福身上的包袱,拿在手里颠了颠,递给了身后的同事。
一阵手机铃声在雪地上响起,聂洪峰捡起地上的外套,翻出手机。
电话那端:爸爸,爷爷叫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吃饭?妈妈还做了糖炒栗子,你再不回来可就没有啦。
聂洪峰:跟爷爷说,爸爸马上到家。
电话那端:洪峰啊,别听你家朵朵瞎说,咱爸都给你留着呢。你先忙你的,注意安全啊。
聂洪峰:我没事,你们先吃,别等我。
聂洪峰挂断电话,俯身合上王有福的眼睛,未果。他低下头,顺着王有福的目光看去。
晶莹的白雪中,两颗剥了皮的栗子躺在不远处,在夕阳的余晖中格外显眼。
聂洪峰捡起栗子,把它们放回了王有福的衣兜里。
一只狍子欢快地跑过雪原,消失在林中。
(剧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