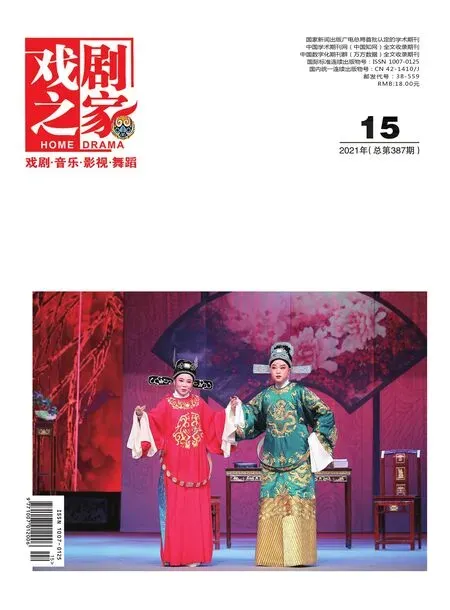浅析“外域影人”视角下的贵州少数民族电影的影像特点
——以影片《滚拉拉的枪》《鸟巢》为例
(贵州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2000 年后,一批以贵州少数民族为主题的电影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例如:宁敬武导演的《滚拉拉的枪》(2008)《鸟巢》(2008),宋海明导演的《水凤凰》(2009),张弛导演的《地下的天空》(2008),郦虹导演的《苗娃》(2014)《姑鲁之恋》(2015),白海滨导演的《山那边有匹马》(2016),和成导演的《天使的声音》(2018),周沫导演的《我来过》(2018)及史震飞导演的《苗寨情缘》(2018)等。有趣的是,这批作品的导演,并非贵州籍也无生活在贵州的相关经历。他们的电影属于外域影人的“他者描写”作品。“外域影人”这个概念是相对于贵州本土导演或是在贵州有生活经历的导演而言的,相对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而言,这批导演应属于文化上的“他者”。在这些作品中,比较有代表的应属宁敬武导演的《滚拉拉的枪》,该片入围了柏林电影节新世代单元。影片《滚拉拉的枪》与其姊妹片《鸟巢》皆讲述了贵州苗族少年漫长的寻父之旅。本文将对两部影片进行内容分析及文本分析,旨在归纳、总结、探索以“他者”为主体的电影人是如何在影像中构建“贵州少数民族”的银幕形象。
一、贵州少数民族景观的呈现与表达
电影是用画面来描述故事与传达思想。正如让,谷克多(Jean Cocteau)所说的:“电影是用画面写的书法。”电影的纪实本性,使得电影画面拥有形象上的准确性。画面的造型看似是违背了以摄影记录自然的最高目标。然而,无数前人的实践告诉我们,画面的造型与纪实之间并不一定就是相互冲突的,画面的造型常常也有助于使电影实现纪实的作用。画面的造型无疑是电影创作者创造性的发现与再现现实世界最集中的体现,同样,画面的造型也最能决定影片的整体风格。由此可见,若要探究外域人视角下的贵州少数民族电影的影像特点,那么对相关影片的视觉文本分析是尤为重要的。本章节将从狭义上的电影画面的造型,即异域自然景观、远景构图、山地视角三方面入手,来探讨画面造型在再现贵州少数民族人文自然风格中的重要作用。
(一)民族地域景观呈现的叙事作用
民族电影最为鲜明的特征是表现少数民族地区及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不同的地理空间构成了不同风情的民俗特色。例如:影片《红河谷》常用大而全面的俯拍镜头展现草原、黄河以及祭祀性场面。在澄静瓦蓝的天空下,“经轮流转”和“牦牛奔突”的空镜头场面展现了藏族电影独具特色的影像语言。谈到视觉图景,最吸引“外域影人”的莫过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原生态的异域景观与自然风光。在宁敬武导演的影片《滚拉拉的枪》《鸟巢》中,我们看到了黔东南从江地区聚集的苗寨、层层叠叠的梯田、狭窄蜿蜒的石板路、古朴简单的木楼等。当然,影片中呈现的自然风光的视觉美感也紧密地与叙事相融合。在宁敬武导演的两部影片中,有着大量展现丛林深处的场景。如此茂密的植被揭示了苗寨人世代相传的严规:村人卖柴,一人一次只能徒步挑一担柴到城中,仅解决油盐之困,不许以此赢利。正因如此,这也激化了矛盾的发展,引起后续事件的发生。例如,在影片《滚拉拉的枪》中,苗族男孩滚拉拉要在“成人礼”之前获得一把枪,可是仅靠一人徒步挑一担柴去卖的赚钱方式,根本不可能在“成人礼”之前攒够买枪的钱。于是滚拉拉踏上了寻父买枪的路途。再例如,在影片《鸟巢》中,小主人公贾响马想要亲眼看看父亲信中所说的北京“鸟巢”,为了买火车票,响马和伙伴出现在山林田地,但因为这世代相传的规矩,他们很快发现仅靠卖柴是不可能在开学前凑齐车费的,故事也由此展开。
(二)“山地视角”画面造型的天人合一思想
再说到画面构图,画面构图是按照视觉美感及故事内容对各种视觉元素进行排列与组合。画面构图是为了展现作品的美感及主题思想。谈到贵州少数民族影像文化的表达,首先需要展现的是地域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性较多地体现在地域空间中的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在贵州少数民族电影中,画面的构图更多的是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众多少数民族电影中,常常用大远景展现人在自然环境中的渺小,人是自然中的一部分。在《鸟巢》及《滚拉拉的枪》中,影片多次出现不规则构图,这种不规则构图常常表达出田野山间的自由感。在画面的整体构图中,村寨、田野、森林占绝大部分的比重,而人在其中的占比较小。这不仅展现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思想,也展现着与浩瀚自然相比,人的渺小与应该对自然保持的敬畏。
电影拍摄的角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画面的构图,画面构图又体现着创作者的思想与立意。例如,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常使用一种拍摄角度,即以日本人坐在榻榻米上的高度作为镜头拍摄视角。这样一种传统的、静观的视角呈现,让我们体会到了浓郁的日本式家庭的风味。影片《滚拉拉的枪》多以俯拍镜头以及仰拍镜头为主,这种非常规视角,展现出独具贵州特色的地貌视角。贵州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七,苗族人依山就势,让村寨与环境相互融合。我们很难判断这样的拍摄角度是受地势束缚,还是导演的特意为之。总之,这样的拍摄角度,形成了浓郁的山区画面造型风格。然而,当滚拉拉离开村寨走进县城时,导演的镜头多通过平拍和中景的画面构图,展现出滚拉拉在县城中身陷“围城”、无法看清全局的迷茫状态,这也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导演通过电影人物所表达的渴望回归自然的影片主题。
综上所述,“外域影人”对贵州少数民族影像画面的造型,简要归纳为以下特点:异域景观与自然风光的呈现,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画面构图,及山地地势所造成的非常态拍摄视角。由于电影画面含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在解释上存在大量的含混性及灵活性。笔者在这里的总结,多有探讨的意味。总而言之,尽管这一批影片导演是文化上的“他者”,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构建了贵州少数民族电影画面造型的风格。
二、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呈现与表达
(一)仪式化叙事
如果说“山地视角”的画面构图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电影的地域美学,那么仪式性场面的展现则集中地体现了贵州少数民族电影的地域文化。仪式是少数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也必然是“外域影人”最想要表达的文化元素。和其他民族性电影一样,贵州少数民族影像有这样一个显著特征:通过仪式性文化内容的展现来再现民族文化、强化民族认同、展现地域美学等。仪式往往体现一个民族共通的价值取向。一个民族的行为、信仰、传统往往是其特有文化的产物。如何将其他民族的观念呈现在银幕上并使大众理解其文化内涵,仪式性场面的展现,无疑是最有效的。其次,电影与生俱来就是一种仪式的艺术,一方面,观看电影就是一项充满仪式感的文化行为;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生动立体、声光结合的试听艺术,电影给予仪式一种前所未有的表现力。导演宁敬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到:“看过电影的观众肯定会发现苗族人民的生活理念与大众的主流价值观完全不同,在当下绝大多数人的眼中,美好生活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多挣钱、买大房子、讲究吃穿,但苗族人的生活态度更接近生活的本质……”因此,导演在影片中融入了大量仪式性场面,以此向大众传递贵州岜沙苗族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例如,影片《滚拉拉的枪》就展现了岜沙人对“树”的崇拜。岜沙人在其出生之时,父母就会为其种一颗生命树,人死之后,家人会用这棵生命之树为其制作棺材,并在其埋葬的地方再种上一棵树,寓意万物有灵,生命不息。岜沙男孩到了十五岁,将举行“成人礼”,在“成人礼”上穿新衣、剃头、朝天鸣枪等,这体现着岜沙苗族人的情感纽带和精神寄托。这种情感纽带体现了他们对于传统文化与家乡聚落的敬爱,精神寄托则具体表现为他们对于父亲所代表的勇敢与独立的男子气概的追寻。
(二)歌舞性表达
特定的仪式往往与民族音乐与舞蹈相伴。民族音乐与民族舞蹈始终以鲜明的民族形式为依托,融入其所在的影像时间和空间语境,成为电影中不可替代的重要部分。这些少数民族电影音乐,充分发挥了音乐的表现性、叙事性的艺术功能,形成了记录民族历史、传达民族思想、抒发民族感情的影像记忆。影片《滚拉拉的枪》中出现的苗族音乐多达10 首,《鸟巢》中也都有苗家人用歌声为他人送别的场面。其中包含了情歌、古歌、习俗歌、劳动歌等,唱出了苗族人对于世界、自然、生活的崇拜、认识与敬畏,这是一种直白的,朴实的情感表达,更是对民族文化的高度凝练。
三、“外语影人”视角下的创作局限
仪式与歌舞场面的展现是“外域影人”对贵州少数民族的影像呈现与文化表征,它同样表达了“外域影人”对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探秘、挖掘、重组与再现。歌舞性表演及仪式性场面的展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贵州少数民族电影的独特美学,但是影片对仪式的使用也造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即浓烈的舞台化风格。长久以来,电影该师从戏剧,还是应该摆脱其束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由于戏剧起源于仪式,戏剧具有与生俱来的仪式性,两者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在影片中展现仪式性的场面很难摆脱“舞台戏剧片”的影子。那么,如何用电影的表达方式表现仪式性场面,做到既保留仪式的地域识别度,又能够充分体现电影的特性,将是一个值得探索与思考的问题。
在“外域影人”的“他者化”视角下,为了配合剧情发展使情节更加曲折生动,或是为了在影片中加入异域风情的审美元素加强影片艺术性表达,或是出于让其他民族观众更好地了解贵州少数民族的习俗的目的,影片中难免有将少数民族原有仪式简化,使其脱离原有文化语境,与真实的少数民族习俗存在差异的现象。例如有苗族观众曾指出《滚拉拉的枪》中传授唱歌与唱情歌等习俗与现实并不相符。因此,如何平衡“他者”与“主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也是“外域影人”在拍摄少数民族电影习俗之时,应该考虑的一大问题。
四、结语
宁敬武导演的作品无疑是填补了贵州少数民族影像的空白,“外域影人”的他者解读在引起情感共鸣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民族观念与文化经过“他者”的解读、翻译与重组,能够在跨文化传播上获得更大的情感共鸣。然而,“他者”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影像也极容易因为文化猎奇心理,陷入对民族文化的表面解读。因此,在拍摄贵州少数民族影像时,要避免陷入以“奇”为主的美学风格或者在影片中堆砌民族元素,这就涉及到了“原生态”本质与艺术创作规律之间的矛盾。如果少数民族影片仅仅表现的是“奇”与“原生态”,将陷入雷同、僵化、陈词滥调的局面,从而走向符号化,被外域世界设定的“贵州标准”所束缚。异域景观与民族符号不应该孤立存在,应与人物塑造、情节叙事等相融合。讲述贵州少数民族故事,探究贵州少数民族影像风格,是文化自信,亦是自觉。
注释:
[1]支菲娜.贵州电影的历史及美学——兼论“新西部电影”是否可以成立[J].贵州大学校报艺术版,2019,7(17).
[2]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M].何振淦,译.北京:中国电影理论出版社,2006.
[3]里奇.小津[M].连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4]张勇.民族仪式——西非电影的形式透视[J].当代电影,2019,(7).
[5]李屹.重返心灵的故乡 导演宁敬武的贵州情愫[N/OL].贵州市报,2009-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