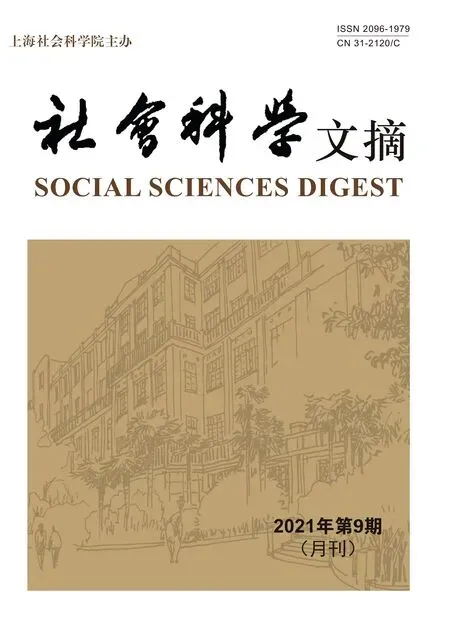“大一统”含义流变的历史阐释
文/晁天义
自西汉直至晚清乃至当代,人们关于“大一统”一词的理解和使用分别有两种虽有联系但内涵不同的所指。本义层面的“大一统”初见于儒家经典《公羊传》隐公元年(前722),被今文经学家认为是《春秋》“微言大义”的核心内容之一。用今天的话来讲,《公羊传》所谓“大一统”的本义是“推崇一个(以时间开端为标志的)统绪”。然而及至晚近以来,“大一统”本义逐渐被人们忽视,在很多场合下被理解为“大统一”,即“大规模的统一”或“大范围的统一”。
一
在先秦(尤其是两周)时期的现实及理论中,“三统”与“一统”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整体。只有在“通三统”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大一统”;也只有通过“大一统”,才能进一步保障“存三统”。因此,基于当时的政治实际,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者自然既要强调“通三统”,又要强调“大一统”。
曾一度流传于儒家学派中的“三统说”经过秦汉时期的斗争最终与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五德终始说”融合为“三统五运说”。秦汉之后的统治者不再像西周时期的统治者一样温情脉脉,也不寄望于靠那种“存二王之后”的迂腐办法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他们更加笃信的是“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之类的暴力强权理论。在这种环境下,一度被儒家奉为金科玉律的“三统说”必然成为一种游离于现实之外、停留于纸面之上的理论。
在郑玄等人的推动下,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同时开启了今文经学自汉末至晚清长达一千余年的萧条时期。在这一千多年当中,儒家学说无疑几乎在每一个王朝统治时期都是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但其中真正受青睐的则是儒家中的古文经传统。至于以强调托古改制,且以“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知名的公羊学思想,则几乎淡出了政治家的视野。因此,尽管《公羊传》与《春秋经》等今文经学文本一直存在于所谓“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当中,但其中如“大一统”之类的微言大义却始终没有得到真正重视,更不用说发掘新义,付诸实践了。
二
文本虽然一经产生就成为一种相对恒定的存在,但是它本身并不会说话,它也决定不了自己说什么话。相反地,文本是否“说话”,以及用怎样的方式“说话”、说什么样的话,不仅取决于文本本身,更取决于时代需要。从元代开始,知识阶层当中就已出现将“大一统”理解为“大规模统一”的现象。如小兰禧、岳铉等纂修的《大元一统志》,又称《大元大一统志》。所谓“大元大一统志”,显然应当理解为“体现元代大规模统一的志书”。《元史·文宗本纪》诏曰:“世祖皇帝既大一统,即建储贰,而我裕皇天不假年,成宗入继,才十余载。”“既大一统”,应理解为“已经完成大规模的统一”较妥。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力图借助传统儒家经典概念强调天下统一的意义,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良苦用心。
尤其到了晚清时期,在沉寂一千多年之后,时代更需要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说话”了。西汉统治者需要的是借助公羊学历史理论构建意识形态,说明自身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而对于晚清统治者来说,亟待处理的一方面是国内统治的危机,一方面则是国外势力的威胁和压制。在内外压力下,如何凝聚国家力量,维护领土与主权完整,成为晚清以来中国人面临的历史使命。在此背景下,“大一统”再次出现在人们的笔端或口中,然而却是以“大规模统一”的含义被理解和使用的。
近代以来,知识精英阶层对于实现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最为敏感,故而在“大规模统一”层面使用“大一统”概念者数不胜数,其中具代表性者如梁启超、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钱穆、杨向奎等人。梁启超在1902年就曾感叹:“美哉中国之山河!美哉中国之山河!中国者,天然大一统之国也,人种一统、言语一统、文学一统、教义一统、风俗一统,而其根原莫不由于地势。”此处将“大一统”之“大”,理解为人种、言语、文学、教义、风俗等多项内容之“大”,以“稍具独立之资格”反比“大一统”,可见他是将“大一统”之“一统”理解为“统一”无疑。
1926年,顾颉刚提出关于中国古代疆域观念的如下看法:“我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中国汉族人所居的十八省从古以来就是这样一统的。这实在是误用了秦汉以后的眼光来定秦汉以前的疆域。我这一次讲话,要说明的意思,就是:秦汉以前的中国只是没有统一的许多小国;它们争战并吞的结果,从小国变成了大国,才激起统一的意志;在这个意志之下,才有秦始皇的建立四十郡的事业。”其中将“一统”与“统一”对举,可见作者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两个概念的。
1935年,傅斯年刊文强调中国自从春秋战国,“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如果说傅氏的前半句话尚可以从“大一统”本义角度理解的话,结合后半句就可以发现他指的实际上是“大统一”(即“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无独有偶,郭沫若先生在创作于1942年的《屈原》第二幕中,也将“大一统”理解为“大统一”。屈原对楚怀王说:“老百姓都希望中国结束分裂的局面,形成大一统的山河……你如果照着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的大一统是会在你的手里完成的。”作者以今况古,将“大一统的山河”与“分裂的局面”相比,可见“大一统”指的是政权、领土的完全统一。
钱穆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中国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与此前诸位先生所指有所不同,钱先生所谓“大一统”除了包括“广土众民”“举世莫匹”等要素外,似乎还包括时间之久远——“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
如果说以上学者只是在不同于本义的层面上使用“大一统”概念,而未深入经典本身的话,杨向奎先生则直接从这个概念的出处即《春秋经》及《公羊传》入手,将“大一统”解释为本义与引申义并存。在《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一书中,杨先生对于“大一统”的解释时而紧贴公羊学理论,时而径直抛开公羊学理论,将它解释为国家和领土的高度统一。与其他学者宽泛笼统地谈论“大一统”、将其理解为“大统一”不同,杨向奎由“大一统”本义推导出国家统一、思想统一等新义,从而为引申义赋予具有“经典来源”的合法性。这种做法恰如“入其室而操其戈”,最具感召力和说服性,但也最容易引起这个概念的混乱。由于这一解释从源头上将两个类似的概念彻底混同起来,引起人们对经典本义的误解,自然难免导致一些今文经学信仰者、推重者乃至研习者的不满。
三
“大一统”含义的流变,有助于我们思考几个与历史认识论或历史阐释相关的理论问题:
第一个问题,即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某一历史真实是否只有一种“真相”?或者说所谓“历史真相”是否具有可以为我们所把握的唯一确定性、固定性?在19世纪的客观主义史学家看来,这个问题是荒唐的。他们认为,历史事实一旦发生便确定不移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历史学家设法寻找证据,如实恢复其真实面目而已。因此客观主义史学家的答案是:历史只有一个真相。不过到了20世纪初期以来,人们逐渐发现问题并没有这样简单。比如说,就“大一统”这个概念来说,什么才是它的本义或“历史真相”呢?回到传统典籍中加以考察不难发现,不同时代的人所理解的“大一统”不尽相同,甚至相去霄壤。
就我们所知,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五种关于“大一统”的表述。第一种是春秋晚期孔子所持的“大一统”,表现在文本中就是《春秋经》隐公元年的“元年春,王正月”。第二种是“七十子”后学尤其是公羊学家所说的“大一统”,文献上的证据就是《公羊传》所谓:“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第三种是西汉中期董仲舒所说的“大一统”,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第四种是东汉何休所理解的“大一统”:“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第五种则是元代尤其是晚近以来人们所理解的“大一统”(即“大统一”),如前引钱穆所谓:“(中国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以上五种观点,只是举起荦荦大者而已,自古及今几乎在每一个时代人的心目中,都有其所理解的“大一统”。我们相信,除了那些别有用心者之外,大家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最符合经典原义,也最符合历史的真实。
由此可知,传统观念中那种所谓完全确定、毫无变化的文本“本义”“历史真相”其实恐怕是不存在的。一个概念一旦经由作者表达或创作,便形成一个有生命的文本。这个文本自然而然会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而展现出其或弱或强的生命力,而不是僵尸一具。对于一桩历史事件而言,道理也是如此。
所以说,“历史真相”并非像客观主义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仿佛是一个扁平的、单一的、固定的存在。相反地,历史事件一经发生便瞬时成为永久的过去。至于如何理解和解释这桩过去的事实,则成为历史学家永无休止的话题,进而会在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心中和笔端留下不同结果。因此,在讨论“大一统”这个概念,或者孔子这个人物时,就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所说的是哪个时代、哪些人物心目中的“大一统”或孔子。事实上,19世纪以来客观主义史学家的实践及其失败已证明他们理想中那种绝对的客观主义认识目标、那个“高尚的梦想”其实并不能实现。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自20世纪前半期以来逐渐出现了对那个“高尚的梦想”的强烈质疑。
第二个问题,为何会产生多种关于“历史真相”的理解?导致对“历史真相”认识发生分歧的原因是什么?传统认识论的主要回答是:这是由于认识手段、材料、条件不足等客观原因造成认识者对“历史真相”的“误解”。这种解释,自古而然。比如说,古人就曾将儒家经学“微言大义”的丧失归结为作者之死。如《汉书·艺文志》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这种解释显然旨在强调经典作家的作用,却忽视了时代环境变化对理解造成的更为本质的影响。
导致文本含义流变的根本因素其实正是时代环境,亦即理解者的处境。比如说,孔子对“大一统”的理解一定与从他所处的春秋晚期礼坏乐崩、王权凌夷的社会相一致的。孔子去世之后,“七十子”后学关于“大一统”的传承和阐释,则体现了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要求和时代主题。同样的道理,秦汉时期的政治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历史上一度存在且为儒家所向往的“存三统”“大一统”变得不合时宜。对于汉代儒生来说,就只能在“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层面发挥“大一统”学说。至于元代尤其是晚近以来,当民族认同甚至国家主权、领土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大一统”自然就被解读为“大规模的统一”。不仅如此,这种解读还会被倒推到数千年前的历史时期,以便加强这种理解的说服力和可信性。
伽达默尔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任何一种理解都是处境化的理解,没有人能超出特定的环境开展理解。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对于“大一统”的理解,春秋晚期与西汉时期不尽相同,而东汉时期也势必与西汉时期相去甚远,晚近以来与此前的理解结果则仅有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尽管每一种理解都自认为最符合“大一统”的本义,但是其实都直接或间接、明显或隐晦地表达了理解者所处环境的要求和理想,因而带有特定的时代印记。可见,“历史事实”之所以有多重、文本含义之所以不断变化,根本上是理解者处境的变化使然。
第三个问题,对“历史真相”的不同理解,是否具有同等的价值或合理性?持客观主义立场的历史认识论认为:由于历史的真实只有一种,因此其他各种关于历史真相的理解都是“误解”。既然如此,“误解”显然不具有认识论上的价值或合理性。这实际上是一种偏狭的观念。事实正好相反,任何一种理解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立场和前见。如果我们固守客观主义史学认识论的话,就会发现每一次处境化的理解其实都或多或少是对文本原义和作者本义的“背离”。按照绝对客观主义的标准,这种背离显然不可饶恕,因为它意味着关于一个历史对象的理解竟然有多个答案。实际上,这种认识如果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自然科学的研究机制的话,对于人文学科领域而言则很不适合。理解者不能离开自身特定的理解处境,也不能完全抛开自己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等一系列“前见”。由于必然陷于不同的理解处境、具有不同的理解“前见”,每一个理解者对相同的研究对象必然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认识结论。宋人苏东坡《题西林壁》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同样的事物,理解者有不同看法,因为他们的处境有差异。进一步而言,因为处境不同,故而每一种认识必然具有其他认识所缺少的独特优势。
任何一种理解都在某种程度上享有真理的同时,也具有某种确定的缺陷;同样的,任何一种被称为“真理”的认识结论,也具有其相对性。这就是何以历史研究不会有一个绝对的终点,历史学在不同视域的交融中不断趋于前进的原因所在。就“大一统”概念而言,《春秋经》《公羊传》《春秋繁露》《春秋公羊传解诂》的记录和表述都不完全相同。然而不能笼统以时代早晚判断哪种解释更加合理,更具价值。这是因为每种解释都立足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代入了特定的时代命题,因而都有其合理性。当然,承认多样性理解的价值并不否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而只是防止了那种绝对的客观主义倾向。总之,历史研究者应该同时在防止绝对客观主义与防止相对主义的两条战线上战斗,坚持一种“中间方案”或“中间道路”,将历史认识视为一个不断展开、永无止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历史客体本身的面貌和价值得到了揭示,历史学的价值也会随着处境的变化历久弥新。这是阐释学提供给我们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