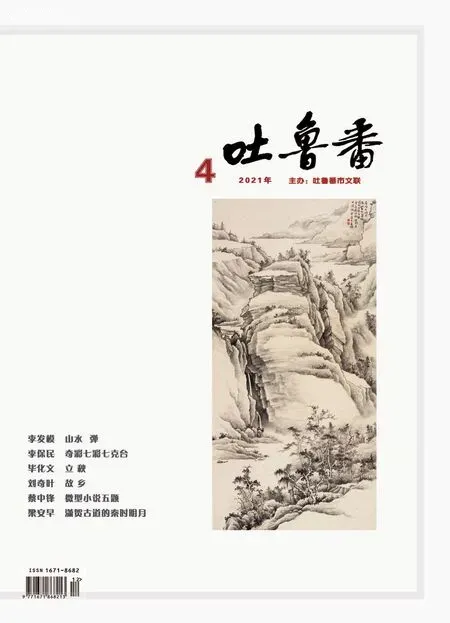鄯善 早在我体内扎根
2021-11-13 01:29:11申广志
吐鲁番 2021年4期
申广志
窑洞式的弧形屋顶,原本是用来排水的
可,鄯善,不下雨、雪,只下土
褥子般厚重的棉窗帘、棉门帘
原本是用来御寒的,可,鄯善
偏拿它将阳光捂得严丝合缝,以此避暑
一街多巷,除11或00号“班车”外
摇曳着铜铃,绽放着彩篷的驴“的”
与炊烟一道,袅娜出渐次温馨的生活
三十年过去了,刚下高铁,就有预感
寻访故地,如同竹篮打水
但,又拗不过记忆的怂恿、煽动
那曾热得移床露天,裸睡整宿
床单上仍留有“大”字汗痕的首扎营盘
已被豪横的油田机关,置换门楼
拆去旧宅。那曾渴得暴饮坎儿井明渠水
一刻也不想松口的再迁驻地
已让不断开疆拓土的砂石料工区
夷为深坑。连永恒的坐标——墓穴坟头
也不知是火葬了,还是移往
更为荒凉、沉静的别处
呵呵,这瞬息万变的岁月
一丁点历史的痕迹,也不肯留下
可,水足了,电通了,路畅了,人富了
村隆作了城,城绿成了村
我一次次背井离乡的青春放飞,不正是
为了追逐,这先来后到的现代文明
其实,鄯善,早在我体内储存、扎根
包括随手扔进干河坝,理应
风化成沙的半颗龋齿……
难怪,一走进园艺场,空位至今的牙床
便开始隐隐作痛
猜你喜欢
当代党员(2025年1期)2025-01-18 00:00:00
当代党员(2023年8期)2023-04-25 13:42:42
国际公关(2020年1期)2020-04-16 12:50:22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2018年0期)2018-11-09 01:01:12
制造技术与机床(2017年7期)2018-01-19 02:29:25
中国漫画(2017年3期)2017-06-29 22:11:00
成功营销(2017年1期)2017-03-16 21:54:36
现代农村科技(2017年7期)2017-02-03 03:16:03
儿童故事画报(2015年8期)2016-01-27 00:11:29
计算机与网络(2014年1期)2014-03-25 10:5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