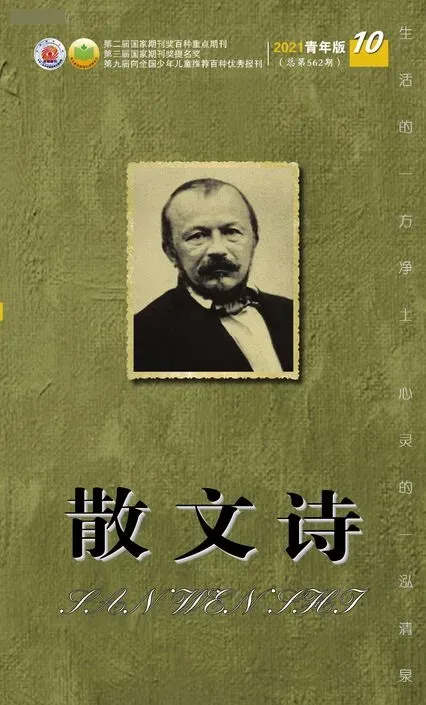蒙古马
王占斌
1
当长调卧成青山,群马在青草的丛林里嘶鸣,大风就从蒙古高原的鹰翅上落下豪迈,成为马鞍上一道站立的闪电。
蒙古马的双目如星,鬃毛若长剑,在大草原上寻觅彪悍的骑手。
锡林郭勒、科尔沁、呼伦贝尔和察哈尔,熟稔的名字一次次被暮色清洗后,包裹进毡包。如果说草原上的烈酒被马头琴温热,蒙古马的野性,一定是牧马人酒醉后赤红的脸膛。
赤红的豪情和梦想,在一片辽阔中回荡。马蹄的鼓点,深深的痕迹印入大地,像马莲,像绽放的雷,像蒙古人流淌的血性,在银碗里疾速燃烧。
马匹的腹内敞亮,上马高山草甸,下马沙地草场,在荒漠的尽头,蒙古马的视野辽阔,辽阔在高高的山冈。
2
邂逅一匹蒙古马,如同邂逅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弟。它一声不吭,在塔拉的晨曦中倾诉着坚韧。曾经掺杂的匈奴、东胡,以及鲜卑、突厥的印记,已然褪得痕迹全无,命运让它有了自己的名字。
在蒙古高原,大兴安岭或阴山纠正了蒙古马的发音。顺着乌拉盖一路向东南,圈出河套的马蹄,这奔腾不息的母语的河流,成为欢快而又润泽的马槽。
太仆寺是有记忆的,曾经的马市烙印一样,刻在蒙古马宽阔的额头,也刻成一枚地名的印章。它们成群结队地被作为钢铁,从察北流落到大同、宣化,蒙古马,背负落日的铁骑一路呼啸而来。风沙总是在边塞扬起,蒙古马的铁蹄一路绝尘。更多的时候,它形同于一柄马刀,用锋刃饮尽疆场的黄昏,用嘶鸣掩埋住血腥和寒冷。
3
该怎样指认一匹蒙古马的前世和今生,套马杆归入蓝天之鞘,草原上的野花比马奶酒光鲜。马头低垂,向着青草低低潜伏的方向。
在百岔川岩画中,一匹凝固的蒙古马喘着粗气。它身材矮小却目光坚定,将历史的沉重和使命,全神贯注在油亮的马蹄上。
勇敢的蒙古马,毫无顾忌地冲进了风雪。饮狼烟的悲壮,也饮草原上的琴声,像一条条被命名的河流,蒙古马流淌着高原的血脉——蒙古人的血,这是被母亲的脐带缠绕的图腾。
仿佛日出烘托的一抹血性,地平线上放出光芒,放荡不羁的灵魂被长调和马头琴喂养。
在每一个苏木,你不得不低头注视蒙古马。
这桀骜而又勇敢的灵魂,草原上奔腾的可汗!
4
在蒙古高原,一匹匹蒙古马是一面面旗帜,是北风的密码和钥匙,忠实守护草原的星辰和北斗,它们指向哪里,哪里就一片肥沃,哪里就摆满毡包。
黄昏的牧场,马群安详,牧马人寂静地注视着远方。
这隐秘而又空阔的草原,河流装订了蒙古史诗,一直向东流淌,蒙古马的眼眸像书页中的灯盏,照耀着呼伦贝尔,照耀着鄂尔多斯,照耀着所有的草原。
蒙古马,北风中呼啸的绝唱,马头琴和牧鞭的交响。颂歌之上,高原厚重的尘土飞扬,那雄健的蹄音燃烧成篝火,燃烧成时代穿行跳跃的鼓点,每一次律动都应和蒙古人内心的歌声,点染蒙古高原的青春。
大地上的青草和野花,牢牢拴住蒙古人的根系,蒙古马目光坚定,带着它的勇敢走向远方
像一面面旗帜,像最绵长、最坚毅的长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