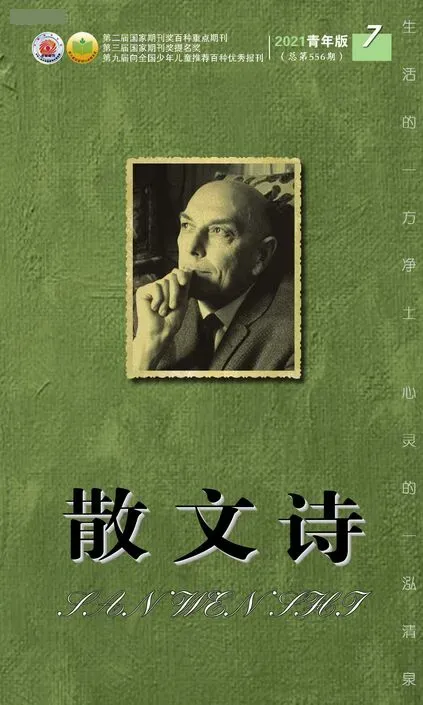白海螺
诺布朗杰[藏族]
一片笑声中,我能留下什么?
一片哭声中,我又能留下什么?
把一群字从纸上撤走,再安置另一群字在纸上。
把字泼黑,再把字洗白。
字让纸延年益寿,字又让纸遭到灭顶之灾。
清白是字,糊涂是字。
药方是字,凶器是字。
爱是字,恨亦是字。
字是法律,字是我的罪状。
字是白海螺,安放我的灵魂。
都是假的。
你觉得你的手是你的吗?你觉得你的嘴是你的吗?
你功成名就,那就由我来自毁清誉。
你好好看看我,我是被夜晚惊醒的一盏灯。
我被点着。
妄想用我的文字窥探我。
我要写的始终没有写出来。
草草一生,写着白海螺。写着我的使命。
白海螺是我故乡的坐标;白海螺是我祖先的骨骼;白海螺是我一声又一声的叹息。
我一次次失声痛哭。我的眼泪,是寄存在纸上的海。
到处都是捷报,只有我在诗里告急。我不知道怎样安放我内心滚烫的词语。
不要逼我。我不会用我安身立命的文字来讨好你。我只向真理低头。
那么拥挤,那群人都向青史中干嘛去了?
能放下的都放下。不能放下的也要放下。
放下不重要的,是智慧。
放下重要的,是顿悟。
放下名,得名。
放下利,得利。
那么,我的眼泪该放在哪里?用一滴泪去唤醒另一滴泪。
或者,眼泪本来就是因为放不下而诞生的。痛苦,绝望,亦是如此。
告诉我:穿越时间与死亡的白海螺放在了哪里?
我用白海螺呼吸。累了的时候,我唱自己的歌。
我的词语正在酣睡。
鹰,迟迟没有出现。经幡在我头顶的雨中,与天空对话。
我抬头,默默看天。默默看着白海螺。
词语的黄金在纸上舞蹈。
我在一张纸上发呆,一匹绝种的马突然就闯了进来,化作我纸上的一滴泪。
我的表情过于僵硬,好多眼泪不适合流在我的脸上。我把它们一一安置在纸中。
一匹马在我的语境中,竟然没有了张力。
我黯然神伤。
我的词语在眼泪中浸泡得太久,好多句子已经面目全非,我无心晾干它们。生火的时候,就请点上它们吧!
反正,白海螺是我纸上的星辰。
我在时间的怀中忽睡忽醒,鼾声不断,像是被时间瞄准的猎物。
我烫手的语言还能燃烧什么?或者,为自己挠痒?
我要提醒你们:小声点,别把逝者吵醒。
不得不说,白海螺是时间的遗物。
在我的故乡,少了一枚白海螺。
在我的纸上,就一定会多出一枚白海螺。
让纸空着。语言已经丧失了说服力。
不要读我。
若有疑问,自己去考证,这要比读诗更节省时间。
可以的话,把我的清贫带到拍卖会上,估一估价。
看,他戴的假发比我的满头真发还要逼真。我不好意思,狠心剪掉了头发。
我不喊了,我得留一点声音给失踪的白海螺。
我想,我一定能找得到它。
空空。那么多废话,不开花,不结果,盘根错节在我可有可无的诗句中。
我是我的眼泪;我是我的血;我是我的骨头。
如果无纸,我就是我的纸。如果无字,我也将是我的字。
绕开我,我怕我的眼泪溅到你身上。
绕开我,我怕你的体味影响我的伤口。
绕开我,我也空空。
为了装下不明不白的白海螺。
你无法抵挡铁沦落为匕首的结局。
如同你无法掌控生命里频频出现的风雪。
你拿着钥匙,不知道是上锁,还是开锁。
你左右徘徊。其实,我也在徘徊。
若无法看清前面的路,徘徊是有意义的。
不要老顶着我的句子不放,任何语言都是形式,都会过期。
我要寻找的白海螺毫无头绪。
我要说的话又漏掉了一句。
我在一截废弃的木头上寻找佛珠。
我并不是虔诚的朝圣者,我不真实地站在这里。
有时候,也学着用佛珠装饰一下胳膊。
当然,我也磕头。
我想要用一座寺院,把我额头上的灰尘洗刷干净。
星星是鹰啄亮的夜晚。我也向一截木头索要火焰,看能不能提炼出几颗星星。
其实,我最需要寻找的,是一截木头的根。
根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白海螺,也就在哪里。
星星和夜晚生长在一起,爱和眼泪生长在一起。
我和白海螺生长在一起吗?
不是的。
我反反复复地说过,白海螺丢了。
真的丢了。
但我相信雨总会停下来。我要说的是:
他们的眼睛,需要眼泪。
他们的灵魂,需要晒太阳。
我是我的悲歌,我是我的绝唱。
我要把纸的黄昏用光。
高处的,风带走。低处的,水带走。
带不走的,统统都留在我的纸上。
我要打发所有跟我上路的词语,去寻找白海螺。
找不到,我就眺望。
你见过白海螺吗?
白海螺上,有我祖先的指纹。
放风马祈福,管闲事招灾。
是这样吗?重重的疑问打扰着我。
无话可说的时候,就该让纸空着。
可是,你为什么还在喋喋不休?别觉得读了一点点经,就认为自己是喇嘛。
告诉你,我用白海螺储藏阳光。
可你为什么要误解我?为什么要中伤我?
等煨桑台上无人煨桑,我就在那里焚烧我的诗稿。
让火焰读我的诗。
我写诗,就是开药方。
我的诗思想凌乱,字迹模糊。你能容忍吗?
太轻了,诗。
诗是蚂蚁的口粮。
你只知道我仰起头是为了看天,却不知道我仰起头还为了不让眼泪落下来。
请问:你想在我的诗句中,读到什么?
白海螺真的丢了,没有下文。
让我来充当下文。
我见过英雄。
英雄们身上有伤,手中有刀。
遗憾,我忘记在哪里见过。我现在连白海螺是什么时候丢的,都想不起来。瞧我这记性。
面对无解的历史,我失忆。
我也见过很多写火的人,他们没有写出火的精髓。
并不是所有的火,都需要燃烧。
我的纸里包着火。我纸上的火,你能看见吗?
人类需要歌声,只是我无心唱歌,我比较适合念悼文。
看,墓碑替死者站立。
把合十的手放下来,祷告已经换成劝告。
也无需解释,很多解释纯属多余。
青稞无法喂饱他们。我要置身夜晚,去播种星星。
幸福的人,我祝你快乐!
我说的白海螺,你一定不会懂。如果你碰见大海,就当是我的眼泪。
纸容不下我。
真想把纸上的脚印擦掉。
带着白海螺,踉踉跄跄地从纸上下来。
我喝够了词语的药。
我等白海螺出现。
大雨覆盖着我。
我已经习惯了没有公鸡时,毛驴报晓。
所以,请灯收回光,我就当是停电了。我能看见。
还没到秋天,为什么急急地收掉果实?
不用回答。不用解释。更不用引经据典。
那些振振有词令我讨厌,没有一句能让我一眼认出白海螺。
罢!地球太小,我们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宇宙。
词语的光芒被纸独吞。
我在白纸深处流浪。我是被漏掉的部分。
我写下太阳的发问:天空凭什么一直高高地在我的头顶?
然后,我写下我的回答:不要老往高处看。作为人,应该有在世的倒影。
不要跟踪我,我的手里只有这些弱不禁风的词语。
是不是有点蛛丝马迹,就好办多了?
不要为难我,很多问题无解,你偏要盯着答案。
即便你知道了答案,又能如何?
我必须坦白一句:那枚我反反复复念叨的白海螺我还没找到。
找到了,我一定会双手奉上。
火是镜子,能照见我们身体里的铁。
举着火把,可你还是看不见自己。这时候,有人看见你举着火把。
神也这样,一直为人们举着火把。
白海螺呢?应该是声音的火把。
此时,有人正在查阅资料,据说是找某个典故的出处。
恼人的典故太旧,不用也罢。更不用绞尽脑汁翻找。
是我们的脂肪过多,该减肥了。
不要朝我挤眉弄眼。
我应该恭喜你,是你让谎言变漂亮了。
你笑了。我想知道,你真的在笑吗?
不管你认不认同,我都要说:声音是耳朵的方向。
顺着声音的方向我踱步。我的耳朵却始终没找见白海螺。
良马也得拴住。白海螺跑到哪里去了?
为了让耳朵找到白海螺,我可能要破禁语戒了。
听见了吗?我已经开口说话了。
我有时候在想:白海螺真的出现,会有人把它举过头顶吗?
或许,白海螺真的白不了了。或许,我应该把白海螺丢弃在我贴着膏药的一连串省略号里面。
白海螺可能是我父辈头上迟早要拔掉的一束白发。只是我不忍心拔掉,用文字把它染黑。
词语的保险柜早已撬开。
歪理只管正放,没人拦你。
痒的地方有虱子。
我只祈求:疼的地方,有白海螺。
心要说的话,被嘴抢着说了。
现在,嘴无话可说了。
无话可说的时候,我就写诗。诗就是我的白海螺。
当然,这个比喻有点不合理。
诗的骨头难啃,我请眼泪一起读。
世上站着的人回到纸上,应该也是站着的。
我心甘情愿为那些站着的人,跪着。
并倾尽所有美好的词语,去书写他们。
离开的时候,能留下的,都留下。
白海螺就是走的时候留下来的。现在,我找不到它了。
我这一纸的茫然,该向谁诉说。
我不知道什么是不朽。你给我说说,好吗?
可是,都快朽完了,你才跟我说起不朽,是不是有些迟了?
死于虎口,活于虎腹。
我只知道:长话短说,长书短写。
我的语言,需要白海螺。
白海螺埋伏在我心里,长长的低音,你听不到。
小心,我满纸的刺,会扎到你。
我呢?即将成为昨日风里的风,雨里的雨。
只字片语,能说明什么?
不要老想着用黄金装饰自己。只有甘愿做土,才有望成路。
我的诗在命运的漩涡里打转。
我的身体是冰冷的词库,幻想用充满墨水的词语表达自己。
有时,真理是在争议中存活下来的。
我过分地要求你,可我又能得到什么?
只能把无用的舌头,献给沉默。
瞧!火的伤口上,站着火苗。
白海螺,这实词之实,虚词之虚。
我从火苗上取下来。投入火中,妄想把肉身和灵魂分开。
取走,我身体上那不甘沉默的噪音。
花照样开,雨照样落下,痛苦的人照样涕泗横流。
万花开遍的春天,你已经挤不进来了。
留给你冬天,只因你更适合在冬天独自开放。
我束缚住了我,但我更渴望你拥有自由。
落日的黄金被群山没收。
日出,一定是你留在世上孤独的背影。
生命只是时间的壳。
白海螺也是壳。
乌鸦:一首不合群的诗。
邀请过来。
在我的诗里,坐坐。诗与诗相爱,或者,反目成仇。
纸的伤口,露出词语的骨头。
望你容忍,所有振振有词,都有它的弊端。
就像白海螺,它不应该频频出现在我的诗句里,影响我。
这样,我就可以放大快乐。把内心的忐忑,略写。
看透了,那个在诗里装腔作势喊疼的家伙。以至于我有时候忍不住想在自己的文字里喊疼,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那么假。
无奈,你错误的问题,我却还要给你标准的答案。
我还是得苦口婆心地告诉你:白海螺,是可以听见的声音。
有什么不可能,你都让秋天迟到了一会儿。
树叶离开树,是为了保住根。
词语离开纸,又为了什么?
可以吗?
给你端上鸡汤,让我咽下鱼刺。我已经疼惯了。
鱼在水里,你担心被淹死。
怕水的是不是你?或者,你的担忧纯属多余。
我从来没有见过孕育白海螺的大海。但我知道,鱼永远穿着那一件用海水缝织的衣服。
我常常梦见那盗螺人把白海螺还回来了,并在我的诗里忏悔。
也常常梦见祖祖辈辈用旧的故乡,在我的诗里发出新芽。
白海螺。
我来收尾,你来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