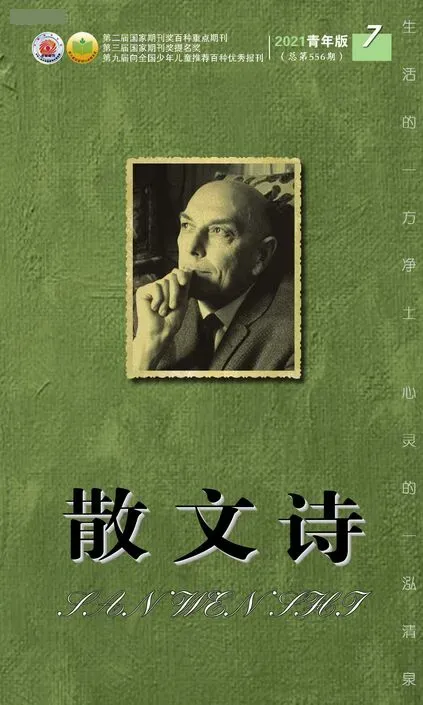忆:雪前·林间
贾延泽
小城雪前
是一个12月中旬的午间,在中国东北地区一座普通的四线小城,雪前。
迷蒙的天色,让人不能照常透过今天云间的太阳来分辨时间,甚至晨昏,准确地来说,那只是一抹浮在天上可以在今天直视的光,近似于一种不大规则的圆形。由于云层在周围的遮挡,那团光反而比平常可视的范围更大。
代价是它没那么明亮、耀眼了。
由于已到午时,通往拦河堤的小路上已鲜少有人,偶尔会碰到几位头发灰白的长者,带着他们蹦跳的孩子,或是宠物狗,却是脚步匆忙地催促着他们赶路,以便能吃上暖胃的饭菜。读初高中时,一直光顾的那家理发店里面,理发大哥趁着店里没有顾客,去隔壁的小餐馆买回来盒饭套餐独自吃了起来。四线城市的路不宽,又住在城边,晌午没有车流,因此,走在马路对面,就能看清对面商铺里的大致活动。
河堤上,上一场雪盖下来的痕迹只消退了十之一二。温度感觉还是暖的,流动的河面没有完全冰封,靠着河岸的两侧结着看似厚实的一层冰,处于河中心线的水一如往常前后拍打,向那天上团光沉落的一边流去。可能由于最近雪下得频繁且量大,河里面水花追逐的节奏,甚至比七月里偶尔避暑停工的几天还要快。
在梯形的河堤上,只有顶部那条与河流平行的人行路被清扫了出来,而其余的两侧坡地里,雪还是与杨树根部平齐、填满了低矮灌丛的缝隙。
这种日色朦胧的枯林,只剩天光犹然可辨。
深一脚浅一脚的我,就这样在可见河流的一侧坡地躺着,听着时快时慢的水声,笃定方向没有偏离。
颜色
又是雪前,又是河边。
冬日里难得的水汽渐渐涨了起来,而随着午间气温越来越高,水汽越发漫溢,配合着那些含着大量小冰晶的云和地上的雪,逐渐模糊了头顶与足下的界线。于是,所有的静止,所有的运动;一切寂静,一切碎裂,当这条接线被沟通时,都终归于一片迷蒙。
或许,这就是造物未开时一切的本来面貌,是古代传说里那位大神尚未觉醒前的世界的样子:没有山岳河流,不分晨昏日月。颜色于其中,是我们给出的一个定义,而我们,却又是万万年后为这已然泾渭分明的世界增色的作品。
相传,那是因为有一位神明不堪寂寞,造出了人类。
当混沌褪去,任何的事物都可以勾勒轮廓时,不论作为媒介的,是语言,还是刀笔,其中就必须要有颜色了。很难去评判谁才是可有可无的尾缀,只是世界里的界线,越是交错,越是分明,颜色种类的需求就越多。
这,只是必然。
山河日月是盘古的颜色,芸芸众生是女娲的颜色。
我们的颜色——伴随着世界的复杂,从水墨丹青到十色画笔,再到如今的七彩霓虹……
色彩变多了,是因为我们的需要不再只是轮廓能被填满。我们甚至分门别类地给了它们各种名号:“合成色”“自然色”……每一种不同的集合里包含的颜色各不相同。于纷繁复杂的颜色里,相信每个人都能准确答出的是彩虹的七色。我们自幼初见彩虹,便会问自己的父母,那七条泾渭分明、组成拱形的东西都是什么,大人告诉我们,那些叫做颜色,从最上面开始,分别又叫做“赤、橙、黄……”没人会去在意彩虹和彩虹七色的命名者们为什么会赋予这个名字给它们,只是明白它们各自鲜明地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就必然地要给它一个名号,而后再给出相应解释性的定义。就像后人把盘古的左右眼叫做日月、女娲的泥塑称为男女。万年前的初夜,人类第一次陷于失去太阳而不可见万物的状态时,他们便管这叫做——黑。远古神灵早已身归混沌,他们只管依着自己的需求开天地、育万物,而不知且不管后人会如何称谓他们留下的作品;我们何不也只管使用更为精细的媒介来勾勒、定义面前这个十色、百色、千色流丽的世界,以填满尚望不到尽头的欲求?于此之中,名号和他的定义,就索性抛却吧。需求永不会被填满,文明从不被精细复杂而定论为先进。不信的话,我们只需抬头,或是放眼一瞥——日月轮替、人海更迭,上古时的机制依旧运转:吐故纳新、生生而不息……
神明与我们,各自在自己的主宰期创造着、呼应着自己的需求,而颜色这两个字存于其中,无论是过程,还是创造物,都变成了一个名号,一个多余的形容词。
那个最初的混沌,容纳众神之灵体,也是我们终将归去其中的地方。那些个剥离了一切的纯粹,迷蒙着,哪里有什么“颜色”二字可做区分。
岁月,只是一条链接,带来每一场繁华落尽后特有的平静。
当它被彻底打通时,就引导了一种文明去向另一片迷蒙之地,以此长存不灭。而打通它的人,正是所有文明里的每一个我们。有些遗迹理当被后世发觉,只不过那又变成了另一种新的炫目之物,即他们口里的,由我们定义的“颜色”。那时,我们必然对此种篡改心有不愿,但对这些关乎名号的定论却必然豁达——等着这些后辈也来到这儿,再同他们一起,欣赏岁月里不属于任何生灵的每一种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