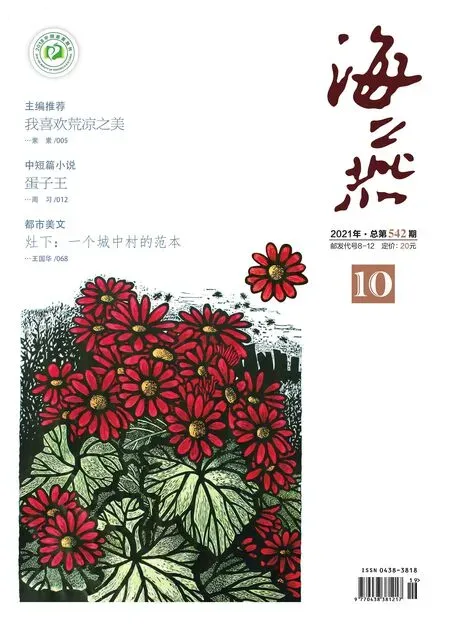马蹄铁
文 梁积林
天刚麻麻亮,应生就被一个不祥的梦折腾醒了。睁开眼的一刹那,首先看到后窗上有个人脸一探一探地向里张望着,加上梦里的情绪依然在身体里回旋着,着实吓了他一跳。他重重地咳了一声,仿佛在喝退着什么。他揉着眼睛,伸了个懒腰,才明白过来,分明是后院里的杏树枝被晨风吹得晃动嘛。
的确像个人。
他又定睛看了看窗口,咕噜了句什么,带着嘲弄,然后掀开被子,坐了起来。他侧了下身子,摸着墙上的开关按亮电灯。看到自己是和衣睡的觉,才想起昨晚半夜了才把水浇完,回到家已疲惫不堪,几下从脚上甩掉靴子,倒头就睡了。他是昨天下午从山里出来给地浇冬水来的。他家的地在两处,昨晚浇了头坝地,今晚二坝还有十多亩得浇。天已经很冷了,羊群也到了出山圈养的时候。本打算一早起来就去拾掇养殖大棚,晚上把剩下的地全部浇完,明早了进山。但他现在有些踌躇了。是那个梦,是那个离奇的梦让他心里不踏实起来。
他拿起手机看了看,才六点过些。他又按灭了电灯,向前面的窗外看了看,地上已有了亮光,白煞煞的,像落了霜。他转过身子,挪到了炕沿上。脚刚要往靴筒里穿,但他马上反应了过来。他踢了一下靴子,赤脚跳下炕,走到了窗口前。地上并没有霜,是一层蜃气,他明白过来。走到了昨天换靴子的地方,他穿上了那双四周已经脱了皮的登山鞋。
应生穿过客厅,在厨房旁的洗脸台前,草草洗漱完,然后进了厨房。他用烤箱炉子旁现成的柴火燃着了炉火,加上煤,又在锅里添了半锅水,搭在了炉火上。接着,他走回了客厅,站在正堂里挂着的爹的遗像前,端详了一会儿,继而,点燃了三炷香供在了香炉里。那个梦,怪怪的,爹在埋怨,并且还暗示着什么。他闭上眼睛,回味了一会儿。
先到坟茔里看一下去,他想。
厨房里,锅还没开,他索性把锅端下火了,免得来迟了,把锅烧干。
鸡咋样了?出了屋门,他又想起了另一个牵挂。
去年冬天,在外面闯荡了几年的儿子败阵回来后,一直在家待着。他让儿子和他一起养羊放羊,儿子不愿意,说他在琢磨个好营生。夏天时,儿子到县城的姑妈家去了一趟回来,决定要养鸡,说他管养鸡,姑妈管销售。立马就在后院里搭了个养鸡棚,从毛家碱坝一个姓毛的开的孵化场进了一千只小鸡,开始了养鸡营生。天冷后,鸡棚里得保持一定的温度,儿子不知从哪弄来了一个炮弹一样的炉子,架在了鸡棚中间。尽管他在山中,几天才出山来一次,但他心里却记挂得紧:可不能晚上睡得太死,不加火,炉子灭了,一棚的鸡可就完了。鸡棚里必须要保持恒温,这是姓毛的送小鸡来时,给儿子交代的。尤其眼下,又进了一批小鸡。小鸡最怕温度不适,弄不好会冻死的。
儿子在一进鸡棚的门里首支了个床,说是晚上值班,可见儿子还是很上心的。但是鉴于儿子先前的失误,他总是有些不踏实。
走到院子中间,他又转了个弯,向后院走去。他开了后院门,站在了鸡棚门前。他听到里面的鸡叽叽喳喳地叫着,心里实落了许多。但推开鸡棚门,他的心却一下子像里面的温度一样,凉了半截。他赶紧走到了炉子前,打开炉门,没有一点火的迹象。他又把手伸进了炉膛里,几乎没有一丝热气。皱起眉头的当儿,他咬了咬牙。
应生转过身,看到门侧面的床,看到儿子把被子闷在头上睡得正香。他走到床前,手搭在儿子屁股上面的被子上摇着。
“应文,应文,文文。”
被子里“哼哼”了几声,但儿子并没有醒来。
“应文。”他来气了,又大声叫了一声。
被子被忽地掀开了,并且有个人猛地坐了起来。但不是应文,是个女的。那女子只穿着三角裤头和小背心几乎是赤条条的。她吃惊地望着应生,脸上一种莫名其妙的表情。稍即,那女子像是突然反应了过来,“啊”了一声,动作急遽地扯起被子,裹在身上,闷住头,躺了下去。
应生措手不及,脑子一下被涮洗成了空白。他不知所措地大张着嘴,想说什么,或者解释什么。这时,那女子怯生生地从被子里伸出了头。
“叔。”她说。
“哦。”应生说。明显,他缓过了神来,并且找到了台阶。“火灭了。”他说,急忙走出了鸡棚。
走到院子中间,应生的心里一下明朗了许多。
上次从山里出来,不正是在院子里见到那个女子嘛。他刚进院门,看见一个女子牵着儿子的胳膊要往外走。儿子见到他,给女子介绍说:“这是我爹。”
女子赶紧松开牵儿子胳膊的手,叫了他一声:“叔。”随后先向院门外走了。
他问儿子:“她是谁?”儿子说是他在天津开汽车美容店时,雇用过的一个女工。
“商丘。”儿子说,显然说的是那个女子的名字。
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他莫名其妙地笑了一下。
“咋了,爹,你笑啥?”儿子笑嘻嘻地问。
“没啥。”他说。看着儿子散漫的样子,他在心里整肃了一下自己,带出了些威严。“那么她现在和你是什么关系?”
“女朋友。”儿子看他严肃的表情,也拘谨起来。“她和我电话联系上后,找我来了。在天津的时候,她就一直对我有好感,只是杨英追得紧,把她给撇了。杨英把汽车美容店败掉失踪后,是她一直帮衬着我。后来,无法维持生活,我回来了,她也回了老家。”儿子说,努了努嘴,又有了笑脸。“对了,她老家是河南商丘的,所以我们一直叫她商丘。”
昨天下午回来,应生没有看见她,倒把她给忘了。他进了门,换上靴子,拿了些吃喝就到地里堵坝、开渠等着浇水去了,连儿子都没见,以为儿子晚上在鸡棚里值班累了,正在睡觉休息呢,就没去打扰。他到鸡棚里看了看,见炉火很旺,没在意别的,就匆匆去了地上。
想透后,应生心里有了怨气,但想到儿子这几年的不易,又平息了下来。他走到厦房儿子睡的门口,敲了敲门。停了停,他推开了屋门。儿子在炕上睡得很沉。
“应文。”
儿子醒得快,一下就坐了起来。
“爹你啥时候来的?”儿子揉着惺忪的眼睛说。
他没回答儿子的话,却说:“你咋让她值班?”
“咋了,爹?”儿子说,“我连续值了几晚上班,时不时要加火,睡不上个囫囵觉,商丘说她值一晚上,就让她去了。咋了?”
“火灭了,你赶紧看去。”应生说,一转身,商丘已站在门口。商丘看了他一眼,低着头,进到了屋里。看到商丘小心翼翼的情态,他心里一下软了下来:人家一个女孩,大老远跑来,远离家人,本来就很孤单,能主动值班就不错了,还让她受委屈,实不应该。
“没事儿。”应生说,“鸡棚里还没有完全冷下去。赶紧去把火架着,一会儿温度就起来了。我去趟地里。”
“我已架着了。”商丘从外面进来低声说。
应生眉头一闪,露出了刮目相看的表情。真是难为她了。他转身看了一眼正在穿衣服的儿子,出了门。
应生出了院门,向远处看了看天空。他看到天空无比晴朗,只有西边一团白云,特别像那个“马踏飞燕”的旅游标志。他又想起最近在手机微信上看到,有专家把那个东西进行了重新认定,命名成了什么“马踏匈奴鹰”。他喜欢历史,常找些那方面的书,放羊的时候拿着看,知道他放羊的焉支山正是匈奴人曾经活动过的地方,心里莫名地产生了些自豪。他还总是念叨从书上看来的那句“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的匈奴歌,在别的牧羊人面前炫耀。他又琢磨了会儿那团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古怪,认定来认定去的,那些人真有能耐。他觉得,他就是看上一辈子羊,也不会把它看成骆驼的。
这时,眼角的余光突然有了异样。他马上向北异动的地方转了过去。他看到他的养殖大棚后面的那间板房门前,站着一个穿着大红风衣的女人。他又定睛看了看,像是应礼的媳妇。但又总觉得不像,她哪有那么洋气。
应礼是应生的一个远房堂兄弟,几个弟兄都分门另住了,应礼排行老小,一直在老房子里一个人住着。前些年,应礼去了新疆打工,后来领回来了个媳妇,结婚仪式还是应生给操办的。后来,两口子又一起去新疆打工了。但是,去年冬天,应礼的媳妇,叫什么来着,对了,叫当花花,却一个人回来了。说是应礼不在了,高空架模板时,摔了下来,死了。据说赔偿了八十多万呢。
当花花回来后,只在应生家来过一次,就悄无声息地在旧房子里待着了。应生使上儿子叫她过来吃饭,她也推托着不来。有天,村文书贾典找来了,说是了解应礼家的生活情况。先和应生说了几句,尔后,贾典就去了当花花家。接下来的几天,贾典每天都来,不过不是先到应生家,而是直接去了当花花家。在大棚里喂羊的应生总能看到,贾典一待就是老半天。春节前,贾典突然带了几个人,迅速把旧房子拆了,很快就建起了那座新板房,还给添置了些家具。
往后,贾典还来,应生就有些疑惑了。但他没往深里想。至于后来的风言风语可不是他传的。
春节过完,当花花就不见人了。
不知啥原因,贾典也辞了村文书,去了新疆。
看来是阔气了。
难怪……应生又心生了些疑虑。他昨晚浇完水回来已是半夜了,听到大棚那边嚷嚷闹闹的,一想,自家的羊又没出山,不怕羊被偷盗什么的,也就没多在意,认定自己听岔了。人劳累过度了,出现幻听了吧。
昨晚当花花的板房里一定是热闹非凡了。对,那是猜拳行令的声音。
他回过神来时,当花花已经进了屋里。居然连个招呼都不打,他心里猛地空了一下。突然又觉得自己少见多怪了,人家干什么与你何干?尽管那样想,应生还是有些悻悻然。
转身间,他又看了看那团白云。马蹄下面的那个“飞燕”还是“匈奴鹰”已不见了,而马蹄却更显劲爆了,分明还钉上了马蹄铁。似乎是好征兆。他想起曾经在哪本书上看过,要是家里挂上一块马蹄铁,会吉祥如意的。当时,他想过在哪里能找块马蹄铁,但也只是想想,随后也就忘了。
这时,他又有了找块马蹄铁的冲动,也许能冲冲儿子这几年的不顺。
得找,他下了决心。
赶紧先去坟茔里看看去,看看梦里显露的是否真实。
应生后悔没有穿靴子,昨晚浇过地后,地埂连小路上都漫上了水,泥泞得很难行。起先,他还掂着脚尖,一跳一跳择着干处走。一不小心,滑进了一个泥坑,他就放开了,索性把登山鞋当成了雨靴,不管泥水,径直向自家地头的坟茔地走去。
并没有梦里出现的那些迹象。梦里,有一股水把上块地的地埂冲开了一道口子,淌进了坟地,把爹的坟洇塌,棺材都漂在了水上,晃晃荡荡的。并且有一股水突然变成了银色,流出了茔地。爹被水呛着了似的,猛地站了起来,责怪着他。但是没有,坟地里干干的,只有一只老鸹在啄食着什么,听到应生走近的声音,“哇”了一声,振翅飞走了。
莫不是……他心里一急,小肚子那儿一抽搐,出了一身冷汗。最近山里各羊群上时有丢羊的事件发生,不会是偷羊贼听到他出山了,下了黑手。谁都知道他非常小心,每晚都要在羊圈周围巡睃上几次呢。近来,听到那个不好的风声后,他几乎整夜都不睡觉,在羊圈四周徘徊着。
应生赶忙掏出手机,拨打妻子的手机,但无法接通。而雇上放羊的邵明又不拿手机,给他手机他都不要,说我一个光棍汉,拿上个手机给谁打去。他们的羊圈在一个山坳里,没有信号,有事向外面打电话时,得上到半山腰,才能接通。想想也是,如果真丢了羊,妻子早把电话打过来了。他又把各种可能反复想了一遍,觉得没事,心里松弛了下来。梦嘛,不就是个梦嘛,哪有那么多的应验,也许就是昨晚他浇地时,水特别大,自己老是害怕水把上地埂冲垮,淹了坟茔,印迹下的。况且,早晨出门时,他还看到了天上的马蹄铁,迹象很好嘛。对,找块马蹄铁吧。不管书上说得实不实,相由心生,既然有了这个想法,就要做到,图个吉顺。
谁家有呢?应生把队里的人挨个想了一遍,最后他断定,科哥家肯定有。科哥虽和他是平辈,但和爹是同岁。生产队时,爹是会计,科哥是皮车夫,他们俩关系非常要好。科哥常到他们家去,他也随爹常去科哥家。记忆犹新的是,科哥总是给爹说钉马掌的事。他还和爹一起去看过科哥牵着马到铁匠铺钉马掌。爹去世几年了,而八十多岁的科哥依然健在。
别人家都早搬到了居民点上,而科哥家一直在离居民点不远的一个老庄子里住着。应生环顾着四周出了坟茔。他停下脚步,瞅了瞅远处。然后他向北一拐,前走了一段,跨过了一个水沟。那边是一块林地,科哥的家就在林地北面,一座土夯下的城堡式的墙院。很夸张的那种黑漆木门。应生推了推木门,门从里面闩着呢。他轻轻敲了敲木门,没有动静。他不得不用拳狠砸了几下,并且边砸边喊着:“科哥。”
一会儿,听到了应门声:“谁呀?来了。”
门闩响动着,门开了,开门的正是科哥。
“怎么这迟了,还闩着门呀?”应生笑盈盈地说,“科哥的身体看起来还好得很。”
“好啥?”科哥说,咳了几声,“也不行了,最近动不动就感冒了。今天还行,好多了。”
“儿子和平娃呢?”
“两口子都在新疆,包着地种呢。你说,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可又在城里买了楼房,住不上几天嘛。”能看出来,虽然听起来科哥是在埋怨,实则是在炫耀,脸上闪着荣耀的光辉。
“年轻人嘛。”应生说,随着科哥进了庄门。
“进屋,应生。自打你爹不在了,你也不来我们家了。”科哥说。
“忙得很。多的时候都在山里放羊,顾不上嘛。”
“总是有事吧,进屋说嘛。”科哥像是近视,眯起眼睛看着应生。
“哦。”不知为什么,应生心里突然有了种陌生感,看着科哥脸上密密麻麻的皱纹像是隔着多少座山。他犹豫着不想说了,但看到屋墙上挂着的各种各样陈旧的铁活,却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有马蹄铁吗?科哥。”
科哥愣怔怔地看着他。
“就是马掌。”他赶紧又说。
“噢……”科哥长长地醒悟了一声。“你找那个东西干啥?”
“也不干啥用。”应生斟酌着,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跺了跺脚上的泥巴。“听说,听说马蹄铁能辟邪。”他说,搓了搓脸,一笑。
“这倒没听说过。”科哥说,“我还以为你给啥人收文物呢。总有些贩子找上门来,问这问那,我才懒得理呢。去年,付楼镇要建什么民俗博物馆,还有人来过几次,把两对大车轱辘拉走了。应该有,以前家里新的旧的好多,不知道捣腾到哪儿了。”
科哥走上台阶,在墙上各处挂的铁活间“咣啷咣啷”地翻腾着。应生也上前翻找起来。
“有呢,有呢。”突然,身后有个古怪的腔调,语焉不详地喊了几声。
“这娃子。”科哥转过了身,“庄门就不能开,一开就闯进来了。”
原来是兰新。据说是修兰新公路那年生的。生下后不久,爹妈就上了工地,兰新由爷爷奶奶养着。有天晚上,兰新发高烧,没有及时送医院治疗,昏昏迷迷的,把脑子给烧坏了,不仅半聋半哑,还有些神志不清。
“兰新。”应生说,“你说的啥?”
兰新“嘿嘿”一笑,双手抖动着,跳了一个蹦子,“有呢。”
“你不要看这娃整天疯疯癫癫的,可灵光了。看起来傻,别人说的啥心里清楚得很。虽然吐字不清,但说出句话来带着神气呢。”
“可惜了。说明他原本是个聪明娃。”应生说。
兰新像是听懂了应生说的话,竖了一下大拇指,“嘿嘿嘿”地向后院跑了。
“又说呢。”科哥说,带上了异样的神情,“你雇上放羊的那个邵明怎么样?没发过疯吧?”
“今年才雇上,倒是没有疯癫过。雇的时候别人说他有精神病,看起来却是很正常。几个月了,也没什么反常的表现,只是不多说话。”应生凝神地看着科哥说,“咋的?”
“那个人我可清楚得很,马二场的嘛。你知道我半辈子都是给生产队里赶皮车的。那时候,我们常赶上皮车去马场拉草、硎柴,每次都要在马二场住上一晚。邵明才十七八的小伙子,没读上几天书,也是因为那个病,就在场里放马了。正常的时候,使唤起来特别勤快,但是犯起病来,可就变成另一个人了,见谁打谁,拿起啥来都往人的身上使呢。”科哥停了停,憨笑了一下,像是言外有意地说,“可得要小心,关键是见了女人就往倒里放,流着口水,嘴里‘哼哼唧唧’的,沉浸得很。几下就把女人的衣裳扒光了。我亲眼见过那么一次。”
应生身体一紧,像是受了什么惊吓,心里一下虚慌起来。
“发疯前有啥征兆吗?”应生急忙问。
“有啊。”科哥表情凝重地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长时间盯着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人看,眼睛直愣愣地发着狠光,过上一两天就发病了。这是马二场的人提起邵明来常说的。”
直愣愣地盯着一个地方看。
应生在脑海翻检着邵明的举动,猛然间,好好的邵明,就有了许多异样。最近几天,邵明总是目光呆滞地看他的妻子。尤其是做饭擀面的时候,随着妻子身子的晃动,邵明的身子也在一前一后地摇晃着,嘴里还发着一种怪异的“咝咝”声。他以为邵明在哼歌呢。还有好几次,他见邵明在用眼睛剜他的妻子。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绝对有。
关键是见了女人就往倒里放。
一块烧红的烙铁,“刺啦”一声烙在了应生的心上,让他猛地抽搐了几下。好像事情正在发生,好像事情已经发生。莫名的恐惧洪水一样淹没了他的全身,让他颤动不已。
“我得走了。”应生声音空洞地说。
“你咋了?”科哥关切地说,“庄子里阴得很。总不会像我那天,外面天热,进到屋里,又急急把衣裳脱了,身上猛地一下凉飕飕的,像是被抽了筋一样难受,紧接着就病下了。”
不会的,几个月了,都没有犯病的迹象,也许邵明的病早好了。应生像摒弃什么似的,甩了甩手,鼓了点意志,心里亮堂了许多。但是,不管怎样,他得赶紧进趟山去。
“没事。”他说,“我想起来了一件急事。”
“马掌还没找着呢。”
“科哥,你找一下,我到后晌了来取。”说着,应生急匆匆地走开了。
进了院门,他连泥鞋都没有顾上去换就发着了摩托。
儿子应文听到了,从屋里走了出来。
“爹,你干啥去?”儿子奇怪地问。
“我进趟山去。”他急躁躁地说。
“不是晚上还要浇水吗?咋又急着进山去?”儿子不解地说。
“你别管了,我去去就来。”
“那个……”儿子欲言又止地说。
“啥事我来了再说。”应生不耐烦地说。
“可是,你连早饭都没吃呢。商丘已经做好了。”
“不吃了。”说着,应生一把油门,起动了摩托。
停下摩托后,应生先到羊圈门口,看到圈里空空的,知道羊群已上了山。他松了口气,身体也爽朗了许多。但他还是有些疑虑。进到帐篷里,看到妻子正在做饭,反而让妻子吃惊不小。
“咋这么快就来了?”妻子问,“地不会这么快就浇完了吧?头坝地和二坝地又不在一个时间点上。”
“他没把你怎样吧?”
“谁?你说的啥?我咋听不懂。”妻子讶异地说。
“邵明。”
“他在那个帐篷里睡着,我在这个帐篷里,能把我怎样?你又不是第一次出山,咋问得怪兮兮的。听人胡说啥了?”
应生摇了摇头。
“我做了个不好的梦。”
“啥梦?梦见我和他怎么了?”妻子“扑哧”一笑,“你有病呀。”又补了一句,“神经病。”
“不是的。”
“梦了啥我才不管呢。人都一天到晚忙的。”妻子说。
应生一屁股坐在了地铺上,但他马上又站了起来。
“那我回去。大棚都还没拾掇呢。”他说。
妻子白了他一眼。“这会儿,饭都做好了,等邵明把羊赶上进圈后,吃过午饭了再回不行。忽儿来了忽儿去了,就为了一个梦,你疯了。”
应生“嘿嘿”一笑,又“咚”地一下坐回到地铺上。
“啥梦呀?”尽管那样说,妻子还是好奇。
“还是不说的好。”他说。但他马上又不由自主地咕哝了出来:“一个失财的梦嘛。”
妻子咧了咧嘴,“咦”了一声,带上了嗔怪的表情。“你刚才不说是那个嘛,怎么又成了失财梦了?”
“给你一时说不清。”应生说着,立起了眉头。“你知道邵明有病吗?”他说。
“啥病?”
“精神病。”
“人是你雇来的,你不说,我从哪里知道?”妻子似乎并没有显出害怕,随心所欲地说着,摆起了饭桌。
“羊来了。”听到山坡上的吆喝声,应生赶紧起身,出了帐篷。
圈好羊,进到了帐篷,他一直观察着邵明。邵明依旧是过去那样,他问上一句,邵明“嗯”上一声,然后就默不作声了,至多漫不经心地看上他一眼。
饭端上桌子后,应生突然说:“邵明,问你个事。你不要生气。”
“啥?”邵明随意地抬了下眼皮说。
“你以前是不是得过病?”他用试探的口气问。
“你说的是精神病吧?”邵明停住了手中的筷子说,“有过。”
“现在还犯吗?”应生问,声音里带着一种热切的关心。
“早好了。”
应生“噢”了一声。
邵明放下了手中的筷子,脸上和嘴唇簌簌地动着,看起来有了很想表白什么的冲动。
“是这样……”邵明说,声音颤抖,像是正在打开一个心结。“听家里人说,我的病是这样得下的。妈怀着我大肚子的时候,有一次,她到商店买货回家的路上,正好下了雪,妈一滑,猛地跌倒在地上,把我的脑子给震坏了。妈说我是倒胎。妈说她当时就开始流血,早产下了我。妈说我刚生下时并没看出不对,但稍大了点,我就开始犯病了。到医院里一检查才查明了原因,但没法治。”邵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接上说,“现在好了。前几年,不是建高铁嘛,我没事可干,就跟上一个工程队去打工。在一场那边修祁连山隧洞时,我被顶板上掉下来的一块岩石砸伤住了院。那块岩石正好落在了头上,幸好戴着安全帽,不然早没命了。我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才醒来。醒来后,我就觉得和以前不像了,至于哪儿不像,我自己也说不清。反正不再犯病了。”
正说着,帐篷门突然一黑,闪闪晃晃进来一个人。回神一看,是圈沟村的文大眼。
“那个……”邵明还想往下说,文大眼已粗声粗气地嚷嚷开了。
“昨晚上一只羊让贼娃子偷摸走了。还是只顶尖的羯羊。应生,你这边,有啥情况?”
“这儿安稳得很,狗都没叫一声。”应生笑着说。
“咋没?听得远处狗叫得凶,我在羊圈周围扰了半夜手电。”应生妻子说,斜睨了应生一眼。
“我就知道应生胡说呢。”文大眼说。
应生“嘿嘿”笑着说:“那么狗叫的时候,你干啥去了?”一副揶揄的神情。
“喝醉了。”文大眼大大咧咧地说。
“快坐,坐下吃饭。”应生妻子说。
“我就是到你这里吃饭来了。找了一早晨羊,没个眉目,把人走得又累又饿的,离我们的羊圈又远,只好到这儿来了。”文大眼说着,已接过应生妻子递过的饭碗,拿起筷子,迅速扒拉起来。
吃了一阵,文大眼松了口气,又咧咧开了。
“养上这么几只羊,又苦又累的,挣不了几个钱,还不如到外面闯荡去。”说着,文大眼侧过脸望着应生。“听说了吧,你们村的贾典和当花花在新疆可是搞大发了。昨天从新疆回来了。”
“你咋知道?”应生奇怪地问。
“和我村上的扁成一起回来的,扁成说的。我昨晚就是和他喝的酒。”文大眼言之凿凿地说。
“干的啥搞大发了?总不是拿上应礼的赔偿钱充大方吧。”应生不屑地说。“难怪贾典对当花花那么殷勤,才是看上钱了。”
“才不是呢。”文大眼说,“呼噜呼噜”喝了几口汤。“不知道他们干的啥生意,反正许多人都在入股,每个月都准时分红,可利索了。连扁成都入了五万呢,半年就分了一万红。”
“真的?”
“真的。”
应生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看着文大眼。
“你还不信,我都思谋着把羊群卖了入股去。那群羊总能卖几十万,你算算,一年下来,能分多少红。比放羊的收入多多了吧?还不累人。”文大眼说兴奋了,很有派头地一拍桌子说,“应老大,怎么样,和我一起卖羊入股吧?”
应生沉默不语,冷眼看着文大眼。
“有啥犹豫的?这么好的事。”文大眼催促着说。
“要入你入去,我还是吃我的苦吧。安身。”应生说着站了起来,“我得赶紧出山浇水去。”
“这……”
刚进居民点,兰新迎了上来,嘴里喊着:“坏事了,坏事了。”
应生刹住摩托,问:“咋了?”
兰新并不回答,只是傻笑了几下,跌了一下脚,向远处走了。
摩托到院门口,应生看到,当花花家板房门前围着许多人。他停下摩托,想上前去看个究竟,但又一想,还是没有去凑那个热闹。
应生进了屋。屋里也是许多人,在嚷嚷着什么。
“咋了?”应生问。
科哥也在。科哥说:“几个警察,找贾典和当花花来了。新疆来的警察。”
“啥事?”
“不知道。”科哥说。
“听说是……”刘凯很急切地抢着说。
“不确切的事,你不要胡说。”科哥截断了刘凯的话。
“给你。”科哥说。
应生看到科哥手里拿着块马蹄铁,接了过去。
“还是兰新找到的。你刚出门,他就从后院拿上出来了。”
“这娃。”应生笑着说。
这时,儿子走到了应生跟前说:“爹,你出来给你说个事。”
走到屋门外,儿子怯生生地说:“爹,死了五十多只小鸡。”
原来印证在这里。应生一愣,但他马上说:“没事,没事。”
他举起手中的马蹄铁,迎着太阳一看,崭新崭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