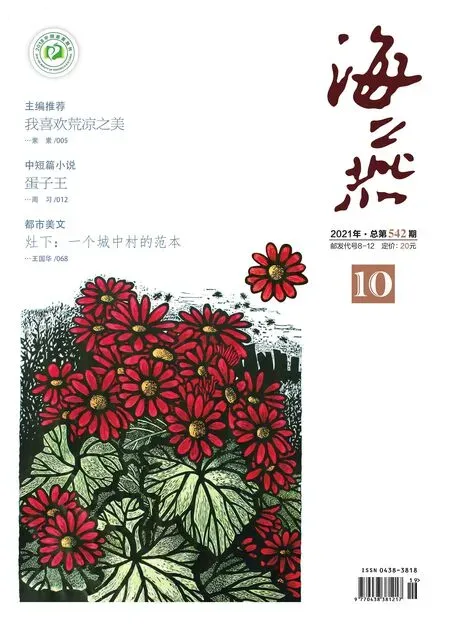顶 光
文 尚书华
1977年入冬的第一场雪后,文工团又要到林场巡回演出了。
侯敏生一上班就去找团长请假,说他家里有事去不了。团长手端着一个大茶缸,正伸着脖子往下吞药丸子。不知是药丸子没嚼碎,还是侯敏生的话噎了他,喀喀地卡在嗓子眼咽不下去,好半天才算顺溜到了胃里,脸憋得紫红,眼泪都呛出来了。
家有什么事呀?团长没瞅侯敏生,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叠得板板正正的方格手绢,连眼睛带嘴抹了一把。
我媳妇她……侯敏生吞吞吐吐,有点不想直说实情。
你媳妇怎么了?
她……她怀孕了。
团长一听,从鼻孔里放出一股冷笑,我还以为你媳妇出什么大事了呢!怀孕,这不太正常了吗?
我是想说,我租得那个房子太偏远,还有一段儿陡坡路,赶上下雪天,路太滑,怕她摔着。
你在家她就摔不着啦?
她是护士,常倒夜班,我在家可以接送她。
算了吧。谁家母鸡不下蛋?谁家老婆不生孩子?用不着那么娇惯,这根本算不上理由,再说也从来没有这个先例。
侯敏生还想再说点什么,嘴还没等再张开,团长端起大茶缸咕咚咕咚又喝了两口水,一抹嘴巴说,好啦好啦,年轻人得要求进步,就你这种不求上进的态度,别说入团入党,就连分房子什么时候能轮到你都难说!
团长最后这句话显然点到了侯敏生的死穴。他今天找团长请假的确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清楚,仅凭媳妇怀孕这一条理由,请假不参加巡回演出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请假能把自己要福利房的事在团长那里挂上号。没承想,自己话还没说到位,团长倒是用这事敲打了他。
侯敏生不是那种榆木疙瘩脑袋不看事的人,他清楚,再跟团长磨叽下去,指定没有好果子吃。于是借坡下驴。是啊,团长说得对,年轻人就应该勇于克服困难,不能遇点麻烦就找组织,给领导添堵。唉!都怨我,房子租得太偏远、太不方便,这要是住上了家属区的福利房不就好了,哪还有这些乱事?
团长听出弦外有音,扭过脑袋白愣他一眼。侯敏生故意装作没看见,捋一把遮在额前的长发走开了。
其实,侯敏生请假不想参加巡回演出,说到家,就是想难为一下团长,把要福利房的事再加个筹码。因为房子实在是太重要了,分不到福利房就只能租房住,租房住心里就永远不踏实。他硬着头皮找团长也是有隐情的。他是怕去山里这段时间不在家媳妇被人偷了。当然,他不是对自己媳妇不放心,而是对他租房的那个房东不放心。
那天他在班上,不太忙,闲来无事就想溜回家一趟。他媳妇这几天连替别人顶了三个夜班,正在家睡觉,几天没见到媳妇,他想回去“慰问”一下。
县城不大,虽说家住在郊区,可单位离家并不算很远,骑自行车也就是十多分钟。
房东家是自己盖的三间大瓦房,独门独院,一头儿自己住,另一头儿租给了他们。房东是县物资局的司机,媳妇在副食商店工作,两口子干得都是肥缺,小日子过得殷实富足,让周围邻居着实眼红。
侯敏生到了家门口,在推开院子门的一刹那,眼前的一幕让他心里一咯噔:房东正翘脚抻脖地趴在他家窗玻璃上往屋里瞅,听见门响,神色慌张连忙弯下腰,掩饰地在窗台下就手抱起一抱柴火,跟侯敏生连个招呼也没打,红着脸回屋去了。
侯敏生心想:这家伙是做贼心虚了。趴窗上瞅啥?一准是偷看我老婆睡觉。哼,这是惦记上我媳妇了。
他走进外屋。这时房东早已进了自己的内屋。他推了一下自己家的屋门,里边插着。他想敲几下,叫醒媳妇起来给他开门。可又一想,媳妇睡得正香,若给叫醒一准不会高兴,再加上刚才见到的那一幕,回家来的那份兴致也就蔫萎了。他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外屋,走出院门,骑上自行车回单位了。
从那以后,侯敏生心里就揣上了一块心病。
文工团进山演出了。第一站是赤柏河林场。这是个小林场,职工、家属加一起超不过一千人。可小归小,什么都不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商店、学校、卫生所、灯光球场、俱乐部样样都有。林业局有的是大木头,运到山外就能换钱,财大气粗,人称“林大头”。侯敏生原本在地区京剧团工作,是个演武生的角儿,就因为林业局工资高,福利待遇好,再加上父母都在本地,年事已高,需要照顾,他毅然决然地从地区调到县城,转入到林业局文工团,心甘情愿地从专业变成业余,从主角变成配角。
这台节目侯敏生任务不重,有一个男生小合唱,一个朝鲜族舞蹈,还有一个群口快板,都是集体节目。可他演出前后的任务却很重,他是灯光组组长。说是组长,其实就俩人,他领导一个女演员给他打打下手。林场俱乐部利用率不高,设备不完善,没有舞台灯光,每次演出都需要文工团自己安装聚光灯,演出完后再卸下来带走,到下一个点接着用。这个活儿侯敏生一到团里,团长就交给了他,并委任为组长。说他年轻,身手敏捷,上上下下灵活。侯敏生初来乍到,工作上不好挑肥拣瘦,领导安排啥是啥,痛痛快快答应了。结果干起来才知道,这活儿是别人都不愿干的一个又险又累的差事。
一般的俱乐部从舞台到顶棚高度都在八九米左右。笨重的聚光灯需要一个个吊到顶棚,再分配到面光区、顶光区、侧光区对准舞台中心调试好。20多个聚光灯吊上吊下都靠侯敏生一个人,那个女演员只能在下面帮着拴拴灯、接接灯什么的。顶棚很简陋,房梁与房梁之间只是搭着几块木板。侯敏生用绳子把聚光灯吊到顶棚后,再小心翼翼地踩着一块块木板,演杂技一般把一个个灯分放到每个光区,然后再一一做好调试。紧张加上忙累,这些活儿全部干完,每次都是一身热汗,可没有谁看见过侯敏生在顶棚忙累成什么样。倒是大家在舞台上忙着搬布景、摆道具、试服装,团长抱着膀儿站在舞台中心区吆五喝六,侯敏生在上面擦把汗的工夫把下面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侯敏生来团里三年多了,进山巡回演出少说也有七八次,所以他对各个林场俱乐部的顶棚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哪家高哪家矮,哪家宽哪家窄,哪一段儿需要爬两步,哪一段儿需要躬身钻过去,他是闭上眼都能画出图来。由于越来越熟练,活儿干得就越来越快,过去需要一个小时,现在四十分钟就干完了。干完了活儿的侯敏生并不着急从顶棚下来,喜欢坐在房梁之间的木板上往下俯视,看下面的人东一头西一头,搬搬挪挪,蚂蚁搬家一样忙活。
今天侯敏生的活儿干得就很顺利。一个个灯安置好后,让专管舞美灯光的庞师傅在操纵台给上电,他把面灯、顶灯、侧灯一一都做了调试。一道道带着色彩柔和的光柱火力交叉般对准了舞台的中心,霎时绚烂一片。
此时坐在顶棚上的侯敏生跟舞台上的人的关系有点像门镜,他能看清楚舞台上的一切人,而舞台上的人看不见他。他的眼睛宛如摄像头,把舞台上的一切都记录了下来。而舞台上的人并不知晓这些,他们习惯了来自观众席的目光,以为凭借头道幕、二道幕、三道幕、边幕条就可以遮挡住自己,万万想不到会有一双眼睛从头顶俯视下来。
侯敏生看见有两个人躲在边幕条后抱在一起亲嘴,灯光骤亮时匆匆撒手,装得跟没事一样。他看清楚了,男的是乐队拉大提琴的小樊,女的是吹长笛的小苏。他知道这两个人正在搞对象,热恋之中,如胶似漆。侯敏生是过来人,体验过年轻人在恋爱时那股劲儿,他觉得有点好笑,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却搞得偷偷摸摸,做贼似的,闹不好都能吓出病来。他还看见平时嘚瑟巴嗖的女演员巩小惠借换服装的工夫,趁别人不注意往男演员佟大帅兜里塞了个苹果,佟大帅瞟了巩小惠一眼,没推没拒没客气,那神情很是习以为常,看上去不像是第一回塞。这事让侯敏生很感兴趣,心想:有点意思,看样子这俩人是好上了,而且好上不是一天半天了。佟大帅是团里舞蹈队的男一号,平时留个大背头,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甩俩八字脚,高傲的凡人不接语。团里舞蹈队新来的几个小姑娘都很巴结他,渴望能跟他跳个《常青指路》双人舞什么的。而他在她们面前总是一脸不屑,俨如一位高高在上傲视一切的王子。而他越是这样摆谱,那些女孩子越是崇拜他,佟老师长,佟老师短的,有事没事都想找点由头接触一下他。女孩子们面上讨佟大帅喜欢也没啥大惊小怪的,这个给块糖,那个给把瓜子是常有的事。而今天让侯敏生感到蹊跷的是,巩小惠的苹果不是当众给的,是偷偷塞的,这可就不同寻常了。巩小惠平时嘚瑟归嘚瑟,可给人的印象不是那种投怀送抱的轻浮女人,可眼前这一幕……难道女人都会……侯敏生坐在木板上,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独自在家的媳妇,想起了那个让他放心不下的房东。侯敏生呆呆愣愣半天,突然打了个激凌,差点从顶棚掉下来,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收回神,顺墙梯轻手轻脚退了下来。
接下来几个林场演出都很顺利。每天一个点,起早贪黑。林场与林场之间的距离都不是很远,近的十多公里,远的二十多公里。今天要去的是一个叫鸳鸯地的中心林场,稍远些,是全局最大的一个林场,职工家属有两千多人。昨晚下了一场雪,本来就跑不快的内燃机车开得更慢,逛荡逛荡半天也走不出多远。车是送林场职工到山场作业的那种简陋的绿皮车厢,面对面两条大长座,中间有一个煤炉子,很少生火,门上的玻璃掉得精光,坐在车里顶多是避点风,温度跟外面没啥两样。大家几乎都抄着手,把团里统一发的军用黄大衣的绒领立起来,把头埋里面,闭着眼,一个个睡着或没睡着东倒西歪随着内燃机车的节奏迷迷糊糊晃动着。
车厢外,雪霁后的蓝天高远空阔。近处,一棵棵高大的树木傲雪挺拔。远处,雪野茫茫,银白一片。
侯敏生坐在离车门最近的旮旯处,这位置车开起来就是风口,没人愿意坐在这儿。由于有了昨天晚上的意外收获,此时,他生出一份好奇心,眼睛时不时就想瞄一下昨晚偷着亲嘴和偷着塞苹果那两对儿。偷着亲嘴那一对儿,人家是谈恋爱,只要当众亲近得不过分,是用不着躲着藏着的。所以,此时两人坐在侯敏生的对角处相依相偎,一副坦然自若甜甜蜜蜜的样子。再看另一对儿,佟大帅坐在车厢中间的地方,巩小惠坐在他对面,车厢特别窄,相距最多一米远,两个人能相互触碰到脚尖。佟大帅后脑勺抵着车厢皮,双臂抱膀儿,叉开着腿,看样子是睡着了。巩小惠没睡,眼不眨地瞅着佟大帅,那眼神巴不得从他脸蛋上瞅下块肉来放嘴里嚼嚼。她偶尔左右瞥一眼,看有没有人瞅她。目光正好与侯敏生看她的目光相撞,脸颊顿时泛起淡淡的红晕,很不自然地装成很自然的样子把头扭向了一边。
侯敏生清楚佟大帅是有妇之夫,听说跟她老婆关系一直不是很好,结婚四年了还没有孩子。巩小惠刚刚离婚不久,据说也是因为丈夫嫌她太能嘚瑟,招来不少风言风语,丈夫不堪忍受,离了。这样两个人有点暧昧,似乎也是黄瓜秧攀上豆角架顺藤随蔓的事。佟大帅比侯敏生早到团里三年,再加上舞蹈跳得好,属于文工团的台柱子,分房今年排到了第一位。团里有明确规定,分房一看年头,二看表现,有劣迹或受处分的一票否决。侯敏生心里想:佟大帅啊佟大帅,你可千万悠着点啊!
车到鸳鸯地林场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冬天白昼时间短,天很快就黑,必须抓紧时间卸车装台。
企业文工团比不了专业文艺团体,分工明确,专业性强。这里往往是一个人身兼多职,撂下耙子拿扫帚,就是主要演员、台柱子也没有装大爷的份。装车卸车,装台卸台,这些活儿没有专门哪些人干,必须得大家都动手才行。
侯敏生原来在地区京剧团时,他是角儿,这些活儿用不着他干。可现在不行,现在台柱子都得干,更何况他就是个普通演员。好在他这个人很实际,到哪山唱哪山的歌。刚来团时,团里排演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他饰严伟才,文武带打,演得出神入化,在全林业局产生了轰动效应。后来又排演了一台《智取威虎山》,他饰演杨子荣,再添风采,名声大振。可待革命样板戏的风潮一过,他便失去了用武之地,渐渐闲置起来,只能演些有三没四杂七杂八无关紧要的节目。沦落到这种境遇,说不憋气窝火是假的。可憋气窝火又能怎样?还能再回原单位去吗?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能分到福利房,有房就有了一切。可他清楚自己风光已去,跟组织上吃老本是解决不了问题了。进山前他找团长请假时,团长撂给他的那句话,已经明明白白暗示他:若想要到房,只有乖乖听话,让干啥干啥,才有希望。不然,门儿都没有。
从布景灯光道具车停的地方,到俱乐部舞台,少说也得有150米,且步步登高。侯敏生扛着最大最重的减光器箱子,累得直喘粗气,两条腿有些发颤。平时这个箱子至少得两个人抬,可今天一是因为坡陡,两个人抬不好走,二是因为他也是想表现一下。团长一手拎了一把小提琴盒子,从侯敏生身边路过时,看见他累成这样,说:行!这次表现不错,就这样表现下去,房子就有盼头喽!侯敏生听了团长的话,被箱子压得涨红的脸有点哭笑不得,刚想回句话,团长三步两步很快蹿到前面去了。
侯敏生咬牙挺着把箱子扛到了舞台上,放下时已是大汗淋漓。正气喘吁吁,有人递过来一个手帕,轻声说:看你累的,擦擦汗吧。说话的人叫秦雅平,是团里新近招来的一位声乐演员。虽说她到团里没有多长时间,可业务进步很快,民歌唱得柔情甜美,人长得也漂亮且很朴实,给大家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侯敏生瞅着递过来的手帕,有点踌躇,不知当接不当接。秦雅平看出了他的为难,说,嫌脏?侯敏生慌慌地瞅她一眼,连说,不是不是,赶紧把手帕接了过来。侯敏生擦了两把脸,想把手帕再还给秦雅平,可她走了,又搬运东西去了。侯敏生望着她的背影欲喊又止。他清楚秦雅平对他是有好感的,女人的手帕轻易是不会用来给男人擦汗的。他索性又擦了几把,一股好闻的女人特有的气息钻进了他的鼻孔,那是一种容易让男人想入非非的气味。
侯敏生给秦雅平留下好印象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那是秦雅平来团里不久的一次演出,在森铁处所在地的一个镇子上,秦雅平在下榻的招待所化完妆,在去往俱乐部的途中遭到当地几个小混混骚扰。为首的小混混拦住秦雅平,挤眉弄眼流里流气地说想跟媚姐交个朋友,说着说着竟然动起手,用两根手指上去挑她的下巴颌。这情景正好让侯敏生给撞上了,二话没有,上去就给了那小子两个电炮,直打得那家伙捂着脸蹲地上嗷嗷直叫,边叫边喊他的小兄弟:快上、快上!那两个小子冲了上来,可他们哪知道眼前这个人是练过武功的,凭空手打斗,三个两个哪是他的对手,啪啪几下,就把两个小子摔到了一边。剩下的一看这身手,哪还敢上,踉踉跄跄地跑了,边跑还边嘴硬地喊:等着,等着,看老子怎样收拾你!
秦雅平被刚才的一幕吓蒙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哪里经历过这些,待那帮小子一走,她像从恶梦中猛然醒来,一下扑到侯敏生怀里哆嗦着放声嚎啕。他安慰着她,说,别怕,有我在,什么都不用怕。她还是很害怕,死死地攥着他的手不肯松开,直到到了俱乐部近前,有了灯光和人群她才不得不把手撒开。
秦雅平抹干眼泪悄悄补上妆上台演出去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团里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只有他们两个人彼此把这事埋进了心里。
全部灯光、布景、道具都运到俱乐部后,大家按自己的分工开始装台。侯敏生带上手电筒顺墙梯攀上了顶棚。跟往常一样,吊灯、安灯、试灯。待面光、顶光、侧光都一一试过后,他又是一脸汗水。秦雅平的手帕还揣在他的口袋里,掏出来,擦两把脸,他又闻到了那股好闻的气味。这气味让他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他甚至不想把这个手帕再还给秦雅平了,他打算买个新的还给她。
他习惯坐在房梁与房梁之间连搭的木板上小憩一会儿,向下瞅着一个个黑色的脑袋瓜在顶光的照耀下闪着乌亮的光泽,在舞台上晃来晃去。从上面往下看,是看不出人的高矮的,也看不见人的表情,但是能看清人的动作,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看得很清楚。有一个人的脑袋瓜与众不同,顶光打上去,有些反光,那是团长的脑袋,顶部的头发早早谢掉了,从上面看下去,像是顶了个白色的瓷碗在台上到处转悠。还有那些布景,从观众席的角度看,跟真的似的。可从这顶棚上往下瞅,简直就是一堆垃圾。侯敏生心想,这要是有个变魔术的节目,可糟了,一准得被看露。看来无论是人还是物,只要换个角度,就容易被人看透、看穿、看出破绽。
侯敏生从顶棚下来后,赶紧化妆,第一个节目就有他。好在他在专业剧团干过,动作麻利,加之化得又不是人物妆,简单,不复杂,所以很快就把妆化好了。化好妆,穿好服装,就在后台静静候场。
后台很简陋,有几面供演员化妆和换服装用的镜子,还有几张放服装用的长条桌,男演员守一头,女演员守一头。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女演员可以随便到男演员这边来,而男演员轻易不能到女演员那边去,去了是犯戒,会遭人讲究。侯敏生注意到,巩小惠这阵儿就到男演员这头来了,她借口找东西,走到佟大帅跟前,瞅别人不注意,把一个桔子悄然塞进了他的兜里。佟大帅正对着镜子化妆,显然从镜子里他是能看见巩小惠的,可是他愣装没看见,没理她。巩小惠不以为然,并没显出不悦的样子,倒是俏皮地一侧身,把后背给了佟大帅。巩小惠穿的演出服装是连衣裙,后背上有个拉链,故意没拉上,就是留着让佟大帅拉的。这是一种小默契,用不着说话,佟大帅心领神会,随手给拉上了。巩小惠得到了满足,美滋滋地回到女演员那头去了。
头遍铃声一响,所有的开场节目演员都从后台匆匆赶到边幕条候场。开场节目是一个集体舞蹈《百花吐艳》,阵容很大,所有年轻的男女演员几乎都上了场。二遍铃声响过后,灯光骤亮,大幕徐启,艳美的民族服装在绚丽的灯光下分外灿烂。演员情绪饱满,观众热情洋溢,台上台下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氛围。谁也没料到一开场就有这样的演出效果,可把团长美坏了,音乐刚结束,他就眉开眼笑地在边幕条内小声而兴奋地催促道:抓紧,抓紧啊,抓紧换服装,别耽误下一个节目。演出有了这样的反响,演员们自然个个都很高兴。退场时,侯敏生紧挨着佟大帅和巩小惠,不知他怎么想的就冒出了一句:这要是谁能给大家发个苹果、桔子什么的,那可就更卖力气了!他的话引起了共鸣,好多人跟着说,对,对,这要是团长能给发点水果,咱一卖力,没准舞台都能跳塌了!
后台响起一片哄笑声。
侯敏生说这话时,有意无意瞄了一眼巩小惠和佟大帅。开始两个人也跟着哄笑,可当侯敏生的目光与他俩的目光撞到一起时,俩人似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侯敏生好像话中有话。佟大帅并没露出什么异常表情,巩小惠却是狠狠地斜瞪了侯敏生一眼。
演出顺利进行。由于开场气氛热烈,导致演员、观众情绪高涨。演员卖力表演,观众热情鼓掌,不时产生共鸣。可临到秦雅平上场的时候出问题了。
下一个节目,女声独唱:歌剧《洪湖赤卫队》插曲《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表演者:秦雅平。报幕员报完幕,退场走进边幕条,演员该上场了。可此时秦雅平并没在边幕条旁守候,眼看舞台空场了,一场事故在所难免。舞台监督急得在后台抻着脖子直喊:秦雅平!秦雅平!突然,全场的灯灭了。团长大声问:是停电了吗?侯敏生回了一句:总闸的保险丝烧了。台下一阵哗然。片刻,报幕员打着手电走到前台,跟观众解释说,总开关跳闸了,马上就修好,请大家少安毋躁。
没用两分钟,灯光重新亮起。秦雅平从上场门边幕条一侧从容上场,先是给观众深深鞠了一躬,又向乐队指挥颔首示意。音乐奏响,甜润清亮的歌声一出口瞬间征服了观众,吵乱的剧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谁也没有意识到两分钟前后台发生了什么。
原来,秦雅平在后台睡着了。进山巡回演出前她母亲有病住进了医院,她本打算跟领导请假留下来照顾母亲,可思来想去,没好意思张口。三天前,妹妹把电话打到了林场,跟她说母亲的病情加重了,问她能不能回来。她清楚,演出不结束,领导是不可能给她假的。心一着急,就失眠了,连着两个晚上没合眼,就这样,化完妆坐在后台睡着了,误了场。
侯敏生每到演出时,只要没有他的节目,总是手里捧本书守在操作灯光的老庞师傅跟前。有时帮着换换色片、调调天幕景什么的,没事就看他的书。听到舞台监督着急喊秦雅平的名字,他知道坏了,一准是秦雅平误场了。他灵机一动,顺手拉掉了总闸。
化险为夷,虚惊一场。秦雅平却根本不知道是侯敏生帮了她一个大忙。
全场演出结束时,大家都沉浸在成功的兴奋之中。
卸台比装台快多了。一是因为卸比装省劲儿,容易;二是因为大家都想早点干完早休息,所以干得快。可再快侯敏生的活儿也快不了,他一个个安上去的灯还得他一个个卸下来,而且刚演出完,2000瓦的聚光灯热得烫手烤人,得凉个十几分钟才能动手,所以他差不多回回都是最后一个收工。
散场后的俱乐部空空荡荡。两个瓦数不大的白炽灯泡把个偌大的屋子照得昏昏暗暗。大家干完份内的活儿各自都回下榻的招待所去了。只有侯敏生还在忙活,像个大老鼠似的轻手轻脚地在顶棚上窜来窜去。当他卸完最后一个顶灯,直起腰擦把汗时,猛然听到舞台二道边幕条后一声尖叫,他大喊一声,谁!紧接着一道雪亮的手电光射了过去。他看清了,是团长,从后面死死地抱着秦雅平,秦雅平拼命挣扎着。侯敏生看到这一幕,一跃身,搂着边幕条从顶棚滑下来了。团长早已松开手,可他想溜走已经来不及了,侯敏生已站在了他的面前,并用手电筒郑重地照着他那张老脸,强光耀得他眼眯缝着睁不开,面目有些狰狞。秦雅平蹲在地上泣不成声。侯敏生攥紧的拳头正要举起来,团长说话了,噢,是小侯啊,这么晚活儿还没有干完,看来全团你是最辛苦的啦!好吧,什么也不用说了,下次团里分房子第一个就是你。说完,若无其事地转身走了。
侯敏生扶起蹲在地上的秦雅平,边替她拭着眼泪边问她:你为啥不早点回招待所?秦雅平抽泣着说: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顶棚上面,我想陪你。再说,这段路我一个人也不敢走。侯敏生听了深深叹了口气,拉起秦雅平的手,说,走吧。
巡回演出结束了。从进山到出山正好半个月。
最后一个演出点离县城很近。节目演完后,大家一致要求连夜赶回县城。在外面时间有些长了,都很想家,特别是年轻人。
林场有送通勤的大巴,演出一结束就赶往县城。
侯敏生到家已经是半夜了。院门插着,他摁响了门铃。好半天,他住得这头儿灯才亮起,媳妇推开门,怯生生地问:谁呀?
侯敏生回了一句:我。
怎么这么晚回来?媳妇边嘟哝边过来开院门。
侯敏生有点诧异:往常都是当司机的房东出来开门,今天他为什么没出来开?是没在家吗?
侯敏生进了院子,没回答媳妇的话,直接进了里屋。
媳妇说: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
不用。侯敏生脱掉外衣,把牙刷放嘴里,信手胡乱刷了两下,脚也没顾得洗,一头钻进了媳妇的被窝。在外面冻透了,进屋还没暖和过来,手脚冰凉。刚碰到媳妇暖乎乎的身子,媳妇就像触了电似的一激凌,说:别动我啊,书上说了,这个时期不能干那事儿。说完一侧身,把后背给了侯敏生。侯敏生像个受了极大委屈的孩子,又像被霜打了的茄子,顿时蔫了。
这种情况下他是很难入睡的,睡不着就胡思乱想,想团里的事,想男女之间的事。他烙饼似的翻过来倒过去,还时不时咳嗽两声。蓦地,他闻到一股淡淡的烟味。心中好生奇怪:哪来的烟味呢?抽抽鼻子仔细嗅了嗅,那烟味好像来自于自己的枕巾,这下,他更加胡思乱想起来……
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侯敏生看见男房东轻手轻脚地溜出了院门。他心里嘀咕:这伙计在家呀。
巡回演出回来后,补休了两个星期天。上班第一天的早会上,团长针对这次巡回演出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并在会上把侯敏生好一顿表扬:侯敏生同志,服从领导,听从指挥,大公无私,任劳任怨。装车卸车、装台卸台、专挑重的沉的搬扛。特别是装灯卸灯,孤自一个人在黑乎乎的顶棚上,提心吊胆,爬来钻去,太危险、太不容易了!鉴于侯敏生同志的表现,团里决定为他申报本年度局劳动模范,并在团里分配福利房时排在第一位。这时,大家开始有些骚动,绝大多数人的表情是赞同的,有房子住的老同志显得不以为然,结了婚没房子住的年轻人却是个个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特别是佟大帅明显流露出不满情绪。心想,凭什么?他侯敏生哪方面比得上我?来团时间他比我晚三年,论演技,他只能演个京剧、跑个龙套,我可是场场晚会都挑大梁啊!再说,谁都知道分房我排第一号,他侯敏生在我后面差了六七位,凭什么一下就跑到我前边去了?佟大帅越想越窝囊,额头上青筋都鼓起来了,正想站起来跟团长理论两句,一抬头,瞅见对面坐的巩小惠正在瞄她。他蓦地想起那天侯敏生看他和巩小惠的眼神,陡然意识到了什么,佟大帅不仅脸色变得紫红,额上还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散会后,大家观察到,侯敏生对团长宣布的决定似乎并不感兴趣。对佟大帅对他的不友好态度更是不屑一顾,表现得淡定从容。
自那以后,人们能看到的是,侯敏生每天排练节目之外,总是攥本书躲在旮旯里悄默声地读,时不时还往本本上记点什么。
那段时间,在团里很少见到秦雅平,她请了长假,在家里照顾病重的母亲。偶尔来团里一趟,取些外地寄来的书籍资料什么的。
相安无事的日子匆匆过去了三个月,转眼迎来了春暖雪融的季节。
一天,文工团突然传出一条特大新闻:侯敏生和秦雅平同时考上大学了,而且是在同一所艺术学院。这条消息不胫而走,在整个林业局都产生了轰动。
分管文工团的局工会主席得知消息后,立马把俩人找到办公室谈话,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俩都是台柱子,是人才呀!不错,上大学是好事,应该支持。可单位需要你们,怎么能说走就走呢!生活上有困难不怕,咱们研究解决嘛。没房子住是吧?我跟你们团长说说,只要局机关分下来房子一准有你们俩的。
侯敏生和秦雅平坐在那里一声不吱,任工会主席苦口婆心。
气氛沉闷了好半天,工会主席见俩人没有任何反应,清了清嗓儿,换了种口气说:实在要走也行,局里不给你们开任何手续,就算自动离职,你们看着办吧!说完,不再理这俩人。
侯敏生觉得气氛有些尴尬,给秦雅平使了个眼色,俩人蔫不声地走了。
后来,听说俩人念完大学都留校当了老师。再后来,还听说工会主席为了孙女考艺术学院去找过他们。